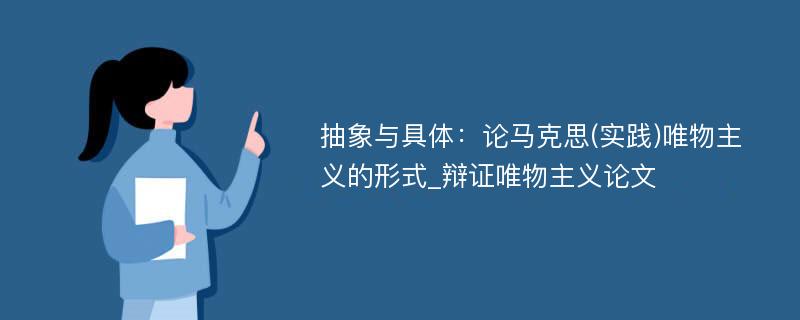
抽象与具体: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形态论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唯物主义论文,抽象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如果说哲学范畴具有无所不包的普遍性,那么它也可以运用于自身。当我们运用一般与个别、抽象与具体这样的哲学范畴来研究唯物主义的诸形态时,似可看到,这样的研究甚至有助于辨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究竟是什么形态”这一当今哲学争论中的重大问题。
唯物主义有多种形态,比较熟悉的如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客体唯物主义、直观唯物主义等;当今哲学争论中的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等;还有一些新概括的如(加拿大)邦格的科学唯物主义、张岱年的分析唯物主义、金岳霖的实在唯物主义等。这就是说,唯物主义也是一般和个别的统一,即呈现为一般的唯物主义及其各种具体表现的个别的唯物主义。
列宁曾对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作过卓越的说明,他说:“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无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注:《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按照列宁的说明,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一般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没有脱离个别而具体存在的一般,具体存在的只是表现了一般特性的个别。其二,一般仅集中表现了个别的本质部分,而不能表现个别的全部,个别比一般更丰富。
马克思在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性质时,曾用果实与其具体表现的苹果、梨、草莓、扁桃的关系,从反面生动地说明了一般与个别关系,与列宁的上述观点相通。他说:“如是我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得出“果实”这个一般的观念,如果再进一步想像我从现实的果实中得到‘果实’这个抽象观念就是存在于我身外的一种本质,而且是梨、苹果等等的真正的本质,那么我就宣布(用思辨的的话说)‘果实’是梨、苹果、扁桃等等的‘实体’,所以我说,对梨来说,决定梨成为梨的那些方面是非本质的,对苹果来说,决定苹果成为苹果的那些方面也是非本质的,作为它们的本质的并不是它们那种感触得到的实际的定在,而是我从它们中抽象出来又硬塞进去的本质,即我的观念中的本质——‘果实’。”(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1页。)按照马克思的说明,果实与苹果、梨、草莓、扁桃的关系即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其一、一般只能从现实的个别中产生,脱离个别而存在的一般是不可能的。其二、个别的本质是由个别之所以成为个别的那些方面决定的,而不是由一般来决定的;如果由一般来决定个别,则“是得不到内容特别丰富的规定的”(同上,第72页),个别之间有着相互区别的因而不可相互混同的各自特征。
通过马克思和列宁对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说明的分析,可以明确得出这一结论:一般是抽象概念,个别是具体概念。所谓一般是抽象概念,即是说一般是思维的产物,它虽然潜藏于个别之中,但它的出现则是人的思维运用的结果;一般是不可感触的,是不能单独地具体存在的。所谓个别是具体概念,即是说凡具体可感存在的,只能是个别,它虽然含有一般的某些规定,但个别之成为个别,是由自身拥有的那些方面决定的,每个个别都有自身的丰富的规定性。
如果我们用马克思、列宁所揭示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来研究唯物主义,就会看到,唯物主义只是一个一般的抽象概念,它相当于马克思所说“果实”;并没有所谓的一般的唯物主义,实际存在的只是各种具体形态的唯物主义,诸如朴素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辩证的、科学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它们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苹果、梨、草莓、扁桃等。这些具体形态的唯物主义,虽然有着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定,但重要的是其自身各有的丰富的特殊规定,正是这些各具特色的唯物主义,才使得“一般的”唯物主义得到了多方面的展现,并推动着唯物主义的前进发展。
把“一般的”唯物主义确定为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抽象概念,以及确定各种具体的(或个别的)唯物主义各自有着丰富的规定性,初看起来,也许是无甚意义的。但是,若联系到我国哲学改革的艰难历程以及把哲学改革推向富有成果的前进方向,则这种确定就有了不可轻视的重大意义。
二
既然“一般的”唯物主义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各种具体的唯物主义,那就意味着,新的具体的唯物主义会不断地涌现,而每一种新出现的具体的唯物主义,也只能依其自身的“那些方面”来确定,而不能以“一般的”唯物主义来判定。然而,在我国新时期的哲学改革中,常见的情形却是,用“一般的”唯物主义来判定新出现的具体的唯物主义,即用“果实”来判定苹果、梨、草莓、扁桃等。这就是说,在哲学唯物主义的研究中,我们常见的思维方法是用一般限制个别,用抽象压抑具体。
在新时期哲学改革的讨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实践唯物主义这一具体形态的新唯物主义的出现,然而这一新形态的唯物主义从其出现到现在,却一直受到是否是唯物主义的质疑、责问和批评,而批评者所持的武器,就是抽象的并不存在的“一般的”唯物主义。
“一般的”唯物主义并不存在,但存在着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定,即人的思维从各种唯物主义中抽象出来的一般本质,因而这种一般规定不是具体的存在,而是抽象的观念的存在。这种抽象的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定是什么呢?就是列宁指出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即:“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外部世界,承认物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并且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着”。(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79页。)凡是具备这个前提的,就是唯物主义,反之,就不是唯物主义。
然而,在哲学改革的讨论中,却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即把唯物主义的抽象的一般规定演变为具体的“一般的”唯物主义,然后再用这种“一般的”唯物主义来判定出现的具体的实践唯物主义。
这种演变而成的“一般的”唯物主义是由后人构建的(马克思哲学形态的)辩证唯物主义吗?并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由列宁揭示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并未涉及辩证法;而且,在责难实践唯物主义的阵营里,在本体论问题上,都是坚持自然本体论的,如果说辩证唯物主义在这一点上坚持的仅是前此的各种具体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而前此的各种具体的唯物主义又是马克思所说的旧唯物主义,那么,由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经由自然本体论演变而成的“一般的”唯物主义,就只能是马克思以前的旧唯物主义。
站在这种自然本体论的“一般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反对实践唯物主义,矛头主要集中在实践唯物主义所特别突出的“实践”上,在他们看来,实践可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分,而基本的倾向,是把实践划入唯心主义的范畴。比如,有论者提出:“如同在哲学中的经验一样,从基于不同的本体论前提的‘实践’概念中,也可以引出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这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唯心主义。”(注:见《评超越哲学》,《人文杂志》1990年第2期。)还有论者提出:“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对于马克思的自然主义或唯实践主义的偏离,去解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注:见《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唯实践主义?》,《光明日报》1989年10月16日。)再有论者提出:“把实践作为本体,实际上是把人作为本体,实践本体论与人本主义是相适应的。”(注:见《关于主体和主体性问题》,《求是》1991年第15期。)实践唯心主义、唯实践主义、实践——人本主义,这就是自然本体论的“一般的”唯物主义责难实践唯物主义不能成立的称谓。
实践唯物主义的提出者认为,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的形态,实践唯物主义是否是唯物主义,实践是否是唯物主义的概念,这要看马克思本人是如何讲的。马克思曾说,在任何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依然保存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又说:“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论述与列宁指出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说,作为一种具体的(实践)唯物主义,它包含了“一般的”唯物主义的抽象的规定,因而它是唯物主义。
但是实践唯物主义不是任何其他的唯物主义,而是一种具体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其特色之处,在于显示其唯物主义的实践性,实践真的像实践唯物主义的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可以是唯物的也可以是唯心的,甚至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概念吗?这也要看马克思本人是如何讲的,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这就是说,实践是人类改变环境的活动。从中可以看出,首先,实践不是凭空而出的,实践的确立有赖于实践对象的存在,无实践对象则无实践可言;而作为实践对象的环境或自然界,马克思早已确立了其优先于人的意识的地位,因此说,实践本质上内含了唯物主义的因素。其次,实践的目的是改造外部世界,而改造的目的是实现人的主观愿望,然而要使实践结果与人的愿望相一致,则必须首先正确地认识外部对象,因此说,实践要求以正确地认识外部对象为前提。最后,既然实践要求客观地承认外部对象,又要求客观地认识外部对象,这就意味着,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活动。实践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实践属于唯物主义的概念,这应是确定无疑的。
由是观之,在哲学唯物主义的研究中,或在哲学改革中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时,切不可用并不存在的,只是抽象观念的“一般的”唯物主义来判定新出现的具体的唯物主义,更不可将某种具体的唯物主义(如马克思以前的旧唯物主义)演变为并不存在的、只是抽象观念的“一般的”唯物主义并用其来责难、拒斥和否定新出现的具体的唯物主义(如实践唯物主义)。若上升到哲学思维方法的高度上讲,则就是不应以抽象的一般去抑制具体的个别,而应由具体的个别去表露内含的抽象的一般,由此开辟一个允许(可能是无限的)具体的个别出现、存在和发展的宽松的环境。
三
如果说实践唯物主义以具体的唯物主义形态,经过长期的论争摆脱了“一般的”唯物主义的抑制而(并不牢固地)存在了下来,那么,随之而来的,则遇到了抹煞自身的独立地位、合并到其他形态的唯物主义之中的境地。具体地讲就是不承认实践唯物主义是独立的马克思哲学形态,即使它可以存在,它与辩证唯物主义也是相通的、一致的。比如,有论者提出:“无论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也好,还是‘实践’的辩证法也好,它们都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尚待进一步研究和发挥的组成部分,并且只有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开花结果。”(注:见《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及其辩证唯物主义方向》,《求是》1989年第17期。)还有论者提出:“从辩证性和实践性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唯物主义的区别,是两种不同角度的理解,各有其合理性,二者可以互相包容、互相补充。(注:见《关于新旧唯物主义差别性的另一种理解》,《江淮论坛》1992年第5期。)”
这种作法,若从一般和个别、抽象和具体的关系看,就是没有顾及列宁所说的“任何个别都没完全包括在一般之中”,以及马克思所说的任何个别都具有“内容特别丰富的规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这样两个思想因素:其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上,只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形态,由此暗含了把辩证唯物主义上升为“一般的”唯物主义的倾向;其二,既然如此,就有意抹杀实践唯物主义的独立地位,或者用辩证唯物主义去对抗、取代实践唯物主义,或者把实践唯物主义融入、消化于辩证唯物主义。这种作法,就是用具体排斥具体,以抹杀具体之间的区别(或各自的丰富规定性)而反对、压抑新的具体出现,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就是用苹果去取代和融化梨、草莓、扁桃等。
实践唯物主义是针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缺陷而出现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且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哲学基础。在哲学争论中,对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式的教科体系批评甚多,主要的至少有两点:其一,辩证唯物主义是哲学史上辩证法成果和唯物主义成果的结合,但是这一内容到底多少是马克思所独有的?关于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的最高代表费尔巴哈已几乎论述了全部的观点,为此恩格斯和列宁曾不只一次地赞扬过他。关于辩证法,作为辩证法思想发展的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对辩证法的论述已达到完备的形态,为此,马克思曾不只一次地赞扬过他。如果把并未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研究中作出重大发现,只是用唯物主义改造了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内容,这显然名不副实。其二,辩证唯物主义承接了马克思所反对的旧唯物主义的客体性传统。这种客体性传统就是撇开人的社会实践,单纯地去研究自然界的本质,即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判的“变得片面了”、“敌视人”和“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一客体性特征,显示了其与马克思所创立的原本的唯物主义之间的距离是相当大的。
马克思的哲学是彻底摒弃了客体性的以实践为根本特色和基本内容的主体性唯物主义,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页。)。
辩证唯物主义未能摆脱旧唯物主义客体性的樊篱,原因在于它同旧唯物主义一样,把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即在人的意识之外的自然界进一步当作了自己全部哲学的基础,形成了所谓的自然本体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则不然,它虽然同旧唯物主义一样承认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前提,但未把它上升为自己全部哲学的基础。在这之间,马克思从人的主体性出发,不同于旧唯物主义仅坚持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的作法,而赋予了自然界客观实在性和待人规定性的二重品格。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显示了马克思坚持着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主张自然界的待人规定性,则显示了马克思哲学特有的实践特色。当自然界成为人的实践改造的对象时,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虽然存在,但已转化为被人的实践改造的为人对象性。因此,实践唯物主义仅把自然界当作自己哲学的基本前提,而把实践当作自己全部哲学的基础,形成了实践本体论,自然界成为实践本体论中实践的人的对象性存在。
马克思把实践当作自己全部哲学的基础,集中地反映在他对事物、现实、社会和世界的看法上。如何看待现实事物?马克思本应同旧唯物主义(包括辩证唯物主义)一样认为是在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但他虽然明知这一点,却不这样强调,而是要求把“事物、现实和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并从主观的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什么是现存世界的基础?马克思本应同旧唯物主义(包括辩证唯物主义)一样认为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物质,但他虽然明知这一点,却不这样强调,而是特别指出: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9页。)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本应同旧唯物主义(包括辩证唯物主义)一样认为是独立于人的意识的社会性的物质存在,但他虽然明知这一点,却不这样强调,而是特意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由此可见,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主义,从攸关哲学性质的本体论上看,决不是同旧唯物主义一样坚持自然本体论的辩证唯物主义,而是主张以实践为本体的实践唯物主义。
由是观之,在哲学唯物主义的研究中,或在哲学改革中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中,切不可用由后人最初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形态(如辩证唯物主义)去反对、取代有可能出现的新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种形态(如实践唯物主义),也不可将已经出现的新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如实践唯物主义)消解和融化入最初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如辩证唯物主义)。若上升到哲学思维的高度上讲,则就是不应以一种具体(或个别)作为一般(或抽象规定)去反对另一种具体(或个别);不应以一种具体(或个别)作为绝对标准去排斥别的具体(或个别)。原因很简单,具体(或个别)由于自身的不能完全包括于一般(或抽象规定)的丰富规定性,才得以相互区别,并获得存在的权力。因此,在评判一个新出现的具体(或个别)时,不是看它与原已存在的具体(或个别)是否相符,而是看它自身所特有的丰富规定。只有这样,“一般的”唯物主义的研究才能不断地被推向前进。
标签:辩证唯物主义论文; 本体论论文;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