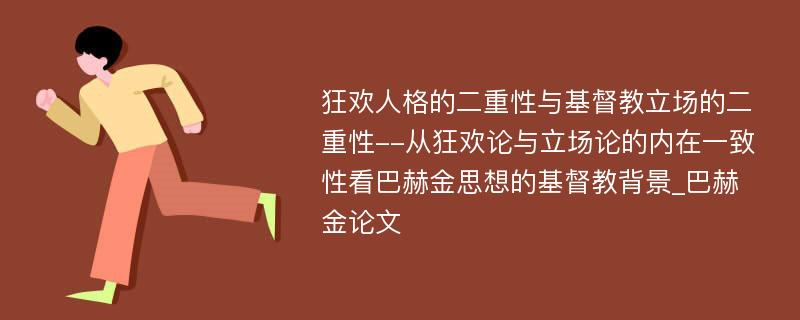
狂欢人格的双重性与基督位格的双重性——从狂欢论与位格论的内在一致看巴赫金思想的基督教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重性论文,巴赫论文,基督教论文,基督论文,在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10-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01(2008)03-0118-07
巴赫金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自上世纪中后期以来一再引起全球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在世界范围内对他的研究方兴未艾。在国外,尤其是当代俄罗斯,巴赫金主要是作为思想家而得到推崇和研究的。俄罗斯学者往往从宗教哲学的角度对巴赫金学术遗产进行观照,将其诗学置于西方哲学或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文化语境中给予诠释。在这种研究中,他们往往将巴赫金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家并列,十分强调巴赫金思想的基督教背景。国外学人深厚的哲学运思功力、广博的文化学术视野使巴赫金研究不断向纵深拓展。反观国内,巴赫金研究虽一度热闹,却一直停留于文艺学层面,鲜有哲学、文化视阈上的深度探讨,特别在巴赫金思想与基督教文化联系的研究方面,更是一片空白。
实际上,在西方思想与俄罗斯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巴赫金,他的人生、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的一生的学术活动,都与基督教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研究巴赫金不涉及基督教文化背景是无法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广度的,而巴赫金与基督教文化的联系,自其早期著作到晚年的谈话中从未间断。本文将主要从巴赫金关于狂欢形象的论述与基督教位格论的某些内在一致出发,探讨巴赫金思想的基督教背景。
狂欢作为巴赫金叙事话语的核心范畴之一,贯穿着这位思想家的存在追问与诗学建构全过程。而在狂欢叙事中,巴赫金尤其强调其生与死同在、新与旧共生的双重性意义。与此相应,对于狂欢行为和狂欢化艺术作品中的主人公形象,巴赫金同样反复重申他们身上的双重共生特点。他认为,艺术作品建立于狂欢文化背景之上,便意味着作品将塑造一体双身的主人公形象。
巴赫金对狂欢节及其他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的研究,以及对文学尤其是文学形象的变形与夸张的狂欢文化渊源的探究,都置于双重性的视界之下。而双重性(амбиваленнтнoсть),在巴赫金的阐述中可以看到,其内涵的主要方面便是死亡与诞生、新与旧的对立共生、正反同体,这种对立共生与正反同体,体现的是宇宙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交替与更新精神。他指出:“狂欢节具有宇宙的性质,这是整个世界的一种特殊状态,这是人人参与的世界的再生与更新。”[1]8民间节日活动的双重性意义和相应的节日文化,尤其是狂欢文化的双重性内涵,就具体生动地显现于死亡与再生、交替与更新的因素之中。
巴赫金在阐述狂欢文化与文学的形象体系的时候,不断强调这些形象的一个独特之处,即它们的一体双身性。他指出,这种特殊的人物形象是狂欢文化与文学形象系列的一道独特景观。一体双身正是狂欢节及其他民间节日文化中的双重性精神在其形象上的鲜明体现。
死亡与再生的因素在节日中最外在的表现就在狂欢广场上的各种游艺、表演仪式及其相应的狂欢形象之中。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上的主要仪式:推举狂欢国王,而后给他加冕和脱冕,最能体现宇宙与社会历史的交替和更新精神。“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2]在这里,加冕和脱冕都具有深刻的双重性,是一个合二为一的仪式,加冕本身便意味着后来的脱冕,脱冕又预示了新的加冕。加冕与脱冕本身就是一个交替的过程,同时也是个双重的存在。加冕的对象,这个狂欢国王往往是奴隶或小丑,是和真正的国王正反颠倒、上下易位的角色,于是在这位小丑国王身上一切都具有相对的意义:他说明任何貌似牢不可破的制度和秩序,任何显赫的权势和地位,都是相对的。加冕意味着脱冕,也就意味着这国王的灭亡的命运,而死亡就意味着新生。这样,在加冕与脱冕的交替之间表现了更新交替的不可避免,以及新旧交替的创造意义。尤其是在脱冕仪式中,人们摘掉王冠,扯去国王的服饰,夺走其权杖并击打、嘲笑和辱骂他。在这里,促其灭亡,正是为了再生,这是一个蕴含创造意义的死亡形象,特别鲜明地表现着狂欢节的交替与更新精神。国王这一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形象及其相应的制度、秩序,被狂欢广场上人民大众的激情所颠覆。
狂欢文化和狂欢化文学中的变形与夸张的结果便是怪诞形象,这种怪诞形象同样体现着深刻的双重性意义。“怪诞形象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体现(或显示)变化的两极即旧与新、垂死与新生、变形的始与末。”[1]29怪诞形象在原始艺术中出现的时候,就是与四季交替、宇宙的死生相联系的。在拉伯雷作品中,它仍然保留了自己的独特本性,其未完成性,死亡与新生的双重性依然鲜活有力。怪诞人体突出强调、夸张的部分往往是人体与死亡—诞生相联系的部分,即巴赫金所言人体向外部世界开放、世界进入人体或从人体排出之地,它永远在吸纳与排泄、孕育与诞生,永远在被创造也在创造着。它通过交媾、怀孕、分娩、弥留、吃喝拉撒等等行为来揭示自己的本质,显现自己的存在意义,即不断生长和不断超越自身界限的本质意义。
怪诞形象以其未完成性与世界融为一体表现其吸纳-排泄、死亡-新生的双重性意义的同时,也力图以一体双身的形象来表达同样的交替与更新精神。在狂欢文化语境下,“怪诞人体形象的基本倾向之一就在于,要在一个人身上表现两个身体:一个是生育和萎死的身体;另一个是受孕、成胎、待生的身体”[1]31。怪诞人体是处于生-死、过去-未来临界点上的独特形象。“在怪诞人体中,死亡,不会使重要的什么终结,因为死亡不涉及生育的人体,相反,死亡使之在新的一代中得到革新。怪诞人体事件总是在一个人体与另一个人体之间的交界处,即似乎是在两个人体的交叉点上进行的:一个人体交出自己的死亡,另一个让出自己的诞生,但它们都融合在同一个一体双身(界限内)的形象中。”[1]373死亡与诞生在怪诞人体里如此奇妙地融合在一起,象双面的雅努斯:一面是死亡,另一面却是新生;一面是过去一个阶段的结束,另一面又是未来的开端。两种相反的内涵和属性,却都在一个身体上显现。换言之,怪诞人体是双重形象在一个肉身里的奇妙组合:两个形象,两种内涵,却只有一个身体,或者说,在一个身体里集合着两个人——两种思想、两种情感、两种趋势、两种意义……从而形成了狂欢文化与狂欢化文学中的特殊的形象体系。
无独有偶,在西方文化史上,像巴赫金笔下的狂欢人物那样,在一个形象身上寄寓两个人物、两种特质,在一个身体里集合着两个人——两种思想、两种情感、两种趋势、两种意义等,这样的形象古已有之。这就是基督教教义中的耶稣基督。
在基督教世界,关于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共生的理念是各派共同的基本理念。基督教的三大宗派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尽管在神学和宗教礼仪的一些问题和具体仪式上存在差别,有的差别甚至很大,但在关于基督的位格的理念上,各派之间却非常一致。因为这一理念乃是基督教的最核心观念之一,背离了这一信仰的基本理念,基督教便不成其为基督教,至少在正统派看来便成了异端。
《约翰福音》以借自希腊哲学的“道”(λoγo)来讲述耶稣的传道经历和阐述基督教的教义。
其第一章便是:“道成肉身。”它开宗明义写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又说:“道成了肉身,位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根据教义,这道就是神性。太初时代上帝正是借助这种神性创造了天地万物,包括有生命有理性的人。正是这道,后来化为肉身,成为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把神的恩典和真理带给人类,将神性显现给人。于是,神性就构成基督位格的重要部分。《约翰福音》又强调,基督身上的神性直接源于上帝。道成肉身的基督,他身上的道是亘古不灭的存在,他先于天地万物,更是先于基督降生为人而已然存在的。后来,为了拯救人类于罪的渊薮,为了重建伊甸乐园,他化为肉身,成为基督。因此,基督就是神性(道)的肉身显现,神性就是基督位格的构成。“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歌罗西书2∶9)。著名新教神学家开姆尼茨解释道:“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意味着道的整个神性,即包含上帝的儿子所有他的属性的全部神性实质。他居住在基督内,即他被赋予的人性内。‘有形有体地’一词并不意味着实体的渗透或混淆,而是位格的合一。”[3]14
在“道成肉身”这一行为中,道所取的肉身这一形式就是基督人性之所在。根据基督教教义,上帝在基督肉身中定了罪案(罗马书8∶3),并借着他的身体与人类和好。《歌罗西书》(1∶21-22):“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又(《加拉太书》4∶4-5)而《希伯来书》(2∶13-17)则写道:“看那!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子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显然,基督的人性就体现于基督的肉身里。上帝借着基督的这一肉身与人类和好,涤除人身上的污点、罪孽使之变得圣洁无瑕。他虽然是上帝的儿子,却是圣母玛利亚所生,因此有着和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躯。基督的人性就来自他的这一血肉之躯。道成肉身的基督,以他那丰富的内心世界体现出他也是个活生生的有感情的人,他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动人心弦。《福音书》记载,耶稣知道自己被出卖将要被捕、被钉上十字架的当晚,带领众门徒在客西马尼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马太福音》26∶37-39)。他的人性的一面让每一位信徒每一位读者怦然心动。对此开姆尼茨总结说:“真正与基督里的人性有关的教义就是:在整个时间的长河中,上帝的儿子把真正、完全与我们同质的人性与其本身结合起来,他拥有人性特征的身体和理性灵魂。这一人性就是纯洁无罪的,但它也具有一切作为对我们罪的惩罚而降临于我们本性的软弱。在其降卑时期他取了此软弱以成为我们的牺牲品。”[3]24
于是,神性与人性在这里结合成一个位格联合体。在基督里,尽管这两种分离的、不同的性同时共存,但却只存在一个由二性组成的不变的位格。这一点历来为东西方教会所共同强调:基督的二性联合成为一个位格的整体。“一方面,基督依其三位一体性便与圣父同体;另一方面,依其人性,他又与我们同体。因而,存在着两种体性,却只有一种现实的仪容,只有一个位格,同时是真正的上帝和真正的人。这一自立体包容了两种本性。在变成另一个的时候,它依然是它,神性没有被转化为人性,人性也没有被转化为神性。”[4]27耶稣基督既是上帝的儿子,也是童贞女玛利亚的儿子,他来源于神,他是亘古不变的道的化身,同时他又有着人的血肉之躯和灵魂心智。神性与人性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离也不可分割,所以尽管二性共存,却只有一位基督。这样,道的神性取了与我们同质的人性,人性因道成肉身而为基督所拥有。上帝的儿子的神性丰满地居位在基督的肉身中,子的人性中体现着父的神性。道成肉身的位格合一中,神性与人性实现了真正的相通,在基督身上,由于神性与人性的交融而实现了与上帝的交融:他是上帝的儿子,又是人的儿子;他是上帝,他也是人。上帝与人在此便紧密共融成为一个基督。
著名的迦西顿公会议(Chalcedon)上最终制定的基督论教义文本可以看作是对基督位格的神——人合一论的总结:
“依据教父传统,我们一致宣布,必须承认单独的和惟一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他有完美的神性和完美的人性,因有神性而是真正的上帝和与圣父同体的真正的人,因有人性而与我们同体,除了罪,一切都与我们相同,依神性在一切世代之前为圣父所生,依人性在近期为上帝之母、处女玛利亚所生,是为了我们和我们的拯救,作为单独和唯一的基督、子、主,这独生子(the Only-Beggotten)以没有混合、没有变化、不可分割、不可分离的两种本性来让我们认识他自身;以这种方式,合一不会破坏两种本性的差别,但是,相反,每种本性的特性在一个单独的位格或自立体中结合时,只会更为牢固,而这单一的位格或自立体不会分割或分开成为两个位格,它依然是圣子、单生体、上帝与道、主耶稣基督的同一个,而且是单独的位格。”[4]80
自上述分析可见,巴赫金关于狂欢人物的一体双身的阐述,与基督教教义关于基督位格的神人合一的论证之间,有着明显的内在一致性。
基督教语境中的基督就是神性和人性合一的双重存在,基督的位格是一个神——人一体的位格。在他身上,来自上帝的神性与来自圣母玛利亚的人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于是在基督的身体里便既有神,又有人,神与人在这里成为一体,成为一个共同的存在,也就显现为同一个人。这就是教义所说的“基督内存在着神性与人性,二者合一成为一个位格。只有一个位格”。“基督内神性与人性的结合非常紧密,彼此相通。因此只有一位基督,一位主”。换言之,虽然在他身上神与人同在,但是只有一位耶稣基督。于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被描述为一个一体双身的形象。
巴赫金对狂欢节和狂欢化艺术作品中的怪诞人体形象的观照中,最为精辟的分析就是:“怪诞人体形象的基本倾向之一就在于,要在一个人身上表现两个身体:一个是生育和萎死的身体;另一个是受孕、成胎、待生的身体。”他认为,狂欢节上的加冕和脱冕仪式中的小丑国王形象是典型的双重性形象,在这个形象中,小丑是国王,国王是小丑。小丑——国王——小丑既是狂欢节加冕——脱冕的情节进展过程,也是人物的角色转换过程;同时还表示着这个形象的一体双身性:这个形象就是拥有国王与小丑双面一体的雅努斯。
狂欢节上的笑声和火焰形象同样是深刻双重性的,同样体现着死亡——诞生的合一。狂欢节的笑声里有对旧世界旧事物的嘲笑,也有对新世界新事物的欢笑。这笑是对旧世界死亡的送别;同时也是对新世界诞生的欢呼。而狂欢节的火,既是毁灭世界之火,也是更新世界之火。总之,民间节日的这些形象中,死与生在一体双身的形象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互相映衬、互相依存,相反两极的意义结合于同一个形象之中。
狂欢节的广场语言中充满了粗言俚语骂人脏话,同时也有极度夸张的赞美语言,甚至还有以“最最最”的语句表达的自我宣传。赞美与辱骂于是构成广场语言的一体双身性。这语言里虽然有辱骂、有赞美,从赞美过渡到辱骂,从辱骂过渡到赞美,但并没有分成两个部分,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是“广场语言”这一整体的事物,体现着民间文化的狂欢精神,是来自大众的充满正反双重意义的群众话语,它是一事物的两面,而非两种事物。巴赫金说:“广场话语是一个具有两副面孔的雅努斯。广场赞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是反讽的,正反同体的。它处于辱骂的边缘:赞美中充满了辱骂,其间无法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也无法指明,赞美从哪里结束,辱骂又从何处开始。广场辱骂也具有这样的特征。虽然赞美和辱骂在语言中泾渭分明,但在广场语言里两者似乎属于某个统一的一体双身,这个一体双身夸中带骂,骂中带夸。因此在不拘形迹的广场语言中骂人话(尤其是下流话)如此频繁地用于温柔和赞美的含义……”[2]187
这种来自狂欢节及其相关的民间文化的形象体系,作为民间文化形象的传统,在渊源于民间文化的狂欢化文学艺术作品中得到表现。在拉伯雷的《巨人传》里,一体双身的形象就是以这种形式显示着变化的两极:旧与新、垂死与新生、变形的始与末。这样的人体往往突出身体上与生育、生长、吸入、排出等环节相关的部位,如巨人张开的大嘴、大肚子等。在这里人体以独特的一体双身性体现着狂欢的双重性内涵,人体的下部与宇宙的下部一样,既是死亡埋葬之所,又是诞生成长之地。死亡与新生相伴相随是这种怪诞人体形象的最本质的特点,世界的交替与更新的节律在这种形象身上体现得尤其鲜明。巴赫金特别指出了巨人庞大固埃出生的情节是典型的表现死亡与新生一体双身的例子。小庞大固埃过大的身体一出生,他的母亲便死了。死亡与新生在此“打了个照面”。
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这一传统则表现为大量的双重人格形象的塑造。
在巴赫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体裁的狂欢文化渊源已经决定了他在创作中将塑造一体双身的主人公形象,即双重人格形象(двoйник)。双重人格形象正是古老的狂欢节形象和狂欢文化的双重性在陀氏创作中的回响,是狂欢人格的双重存在的鲜明体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世界里,体现狂欢节双重性的成对形象比比皆是。这种形象总是力图将事物形成中的两极或事物产生对比的双方聚拢来,使之形成具有双重意义的形象,体现对立和对照的双方相互映衬、互为表里的宇宙观意义。在这里,一切都与自己的对立面对照共存着:他总是在创作中让两个对立面走在一起,使之互相反映在对方眼里,互相熟悉和理解。如爱情与仇恨、信仰与无神论、高尚与卑鄙、贞洁与淫荡等等,种种的相反两极属性奇妙地融合于同一个形象身上,生与死、老与少、正与反、夸与骂、否定与肯定等等相对立的属性,仿佛纸牌上的人头像,上端与下端互相反映与对照共生,这就是典型的狂欢人格的双重性形象。这种人格的一体双身构成了陀氏小说人物形象鲜明的、本质的特点。
显然,巴赫金对狂欢人格的阐述与基督教对耶稣基督位格的定义之间,有着叙事上、思维上乃至精神上的许多同质点。尽管巴赫金论述的对象、内容与教义全然不同,但是分析的方法、辨析的角度却有着非常鲜明的相似性:两者都强调了形象的一体双身性。尽管身处前苏联时代的巴赫金迫于环境的压力对自己的宗教意识讳莫如深,对自己的研究中涉及宗教的问题总是刻意回避,还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正如他晚年在一次谈话中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写作所言:“我不能直接述说有关主要的问题……这就是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关于神的存在的哲学问题。我总是在那里来来回回,不得不克制自己。一个思想出现了,又是来来回回地转。甚至要谴责教会。”[5]但是,只要仔细体味上述他对狂欢文化形象的分析,就不难看出其中与基督教关于基督位格的阐释之间显而易见的一致性。
众所周知,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思想是西方文化精神的核心组成部分,俄罗斯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一员,其文化精神的宗教色彩自不待言。基督教对于俄罗斯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意义,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为过。因为“它是一切有意义的事物的源泉:在它的内在世界中开出了所有的艺术之花,它将责任心融入科学思想和文化的建构之中,它提高了人类个体的价值,它诞生了博爱,它织就了道德伦理之网,它培育了社会救济体系,它带来了教育的光明,它成为立法的基础”[6]6。可以说,西方文明的基本价值体系都建立在基督教精神的基础之上,对于俄罗斯尤其如此。
在全球文化语境下,俄罗斯文化以其独特性傲立于世。这种独特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宗教性。俄罗斯文化正是以其浓郁的宗教性而著称于世。在俄罗斯,宗教性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精神特性的最重要的成分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常常使用同义词表达人的民族性及其宗教属性。相应的,人们更经常使用‘东正教徒’来指代‘俄罗斯人’。”[7]13“东正教在俄罗斯被其信徒称为‘俄罗斯的信仰’。”[7]10俄罗斯文明的发展与基督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发展息息相关。这一点即使在对宗教多有贬抑的前苏联时代也得到承认:“俄罗斯的文明化开始于基督教化”,“基督教自‘罗斯之洗’时期起就具有发展俄罗斯物质和精神文化以及使俄罗斯社会文明化的永久的进步意义。”[7]15俄罗斯哲学往往以神学的形式来表述,现代俄罗斯思想界涌动着浩浩荡荡的“寻神”潮流;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众多俄罗斯作家在寻找人类的拯救之道时,往往在《圣经》里得到答案。可以说,整个俄罗斯民族都深深地浸淫在基督教文化的传统之中。正如格林茨基神甫在《基督东正教信仰的基础》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对于俄罗斯人而言,“信仰是心灵与生俱来的品质,是造物主给予的一种秉性”[6]7。“当人们有了信仰,这信仰便处于其心灵活动的中心:智慧、情感、意志充分依赖于信仰的对象。这信仰不停留于或隐或显的非现实的层面上,而是贯穿于心灵成为一种特性。”[6]7
对于俄罗斯民族信仰的虔诚,著名的东正教神学家、哲学家C·H·布尔加科夫(C.H.Бyлгаков)在《东正教》一书中作过精辟的描述:“对东正教来说,对神之子基督的信仰不是基督学学说,而是生命本身,此信仰贯彻于东正教全身,每个人都拜倒在救主脚下,带着信仰的快乐呼唤:‘我的主,我的神。’每个人都参加他的圣诞,都为他在十字架上的痛苦而痛苦,都在复活节同他一道复活,都为他的来临而战栗。没有此信仰就没有基督教。”[8]显然,信仰的虔诚已经成为俄罗斯民族的独特的宗教品格,甚至已经成为每一个成员的天然情感。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巴赫金,作为俄罗斯民族的一员的巴赫金,其精神世界的基督教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在他的成长过程里,基督教文化已经作为深厚的精神营养流淌在他的血脉之中,作为他的最重要的心理积淀潜移默化于他的灵魂里,作为他的思想方法的重要基础构筑于他的潜在意识之中。这种影响在他的精神世界、他的思维领域无处不在。在建构他的思想体系的时候,在阐述他的诗学理念以及用这些理念来分析文艺作品和艺术形象的时候,这种影响便会在无形中显现出来,使他的理论建构不可避免地打上基督教思想的烙印。所以,当他在论述西方的狂欢文化双重意义的时候,当他在双重性的立场上来建构其狂欢诗学话语体系的时候,当他以双重性思想来观照陀思妥耶夫斯基、拉伯雷、果戈理、歌德、塞万提斯等经典作家的创作的时候,关于基督位格的理念、人与上帝对话的理念及其他宗教因素,无疑会成为内在的重要思想渊源。具体到巴赫金笔下狂欢人格的双重性与基督位格的双重性的一致性上,即使目前我们无法确证巴赫金在写作时有意识地借鉴了基督教教义的叙事传统,但作为巴赫金意识中的重要文化积淀的基督位格论对他的影响,却是可以肯定的。
其实,早在20年代前期完成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里,巴赫金已然对双重人格的理论问题作出了初步阐述。他区分了自我眼中之我(я-для-себя)与他人眼中之我(я-для-дpyгoгo),指出这两个“我”同时存在于我身上是人的自我的存在方式。他还特别指出,对自我眼中之我与他人眼中之我、自我与他人的双重存在问题,自新柏拉图主义以来西方思想史始终给予极大的关注。而基督教思想中的这种人格双重存在关系的特色就表现在自己眼中之我与他人眼中之我、自我与他人的对照共生。他列举了基督教关于自我存在思想的几大来源:“(1)犹太教以集体的体验为基础将人的内在性(即身体需求)用完全特殊的方式予以阐明,并强调他人范畴的主导地位;(2)纯属古希腊罗马的思想:神的人化(泽林斯基)与人的神化(昂纳克);(3)诺斯替教的双重人格与禁欲主义;最后(4)新约基督。”[5]153这里,“新约基督”已经作为自我存在论的重要渊源得到强调,而“新约基督”正是基督教教义中神性和人性位格合一的基督,说明这一观念在巴赫金的早期学术思考中已经占据了重要地位,也表明了他的思想中的重要的宗教渊源,说明他对双重人格问题的研究中基督教因素是至为重要的一大因素。
正是由于基督教因素在巴赫金思想中的重要作用,俄罗斯学者在巴赫金研究中特别强调其宗教背景。在他们看来,巴赫金诗学中关于人格的双重存在的思想、主人公与作者平等的思想、对话思想、狂欢思想等等,都与俄罗斯古老的东正教传统息息相关。例如俄罗斯巴赫金研究的权威学者柯日诺夫就认为,巴赫金的对话思想来自五百年前俄罗斯的东正教思想家圣·尼尔·索尔斯基,而他的“民间笑文化”理论则来自16—17世纪俄国东正教中的“狂信苦行基督”这一文化现象[9]。柯日诺夫还在回忆中谈及1970年巴赫金75岁诞辰时,在审完柯氏所写的巴赫金学术生平概要时,特别肯定了其中的一个结论:“德国哲学思维的系统性、逻辑性和客观性与俄罗斯宗教创作的深刻的有机融合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理念。”[9](Бм.Бак)则指出:“巴赫金是深刻的传统的,他的伦理学与美学渊源于俄罗斯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道德基础,这些道德基础与东正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紧密的联系。”[10]这位学者的评价中肯定地道出了巴赫金这位思想家身上基督教传统的重大影响。另一位学者И.H.舒露基娜分析并断言,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与作为基督教异端的诺斯替主义有着精神上的内在一致性[11]。上世纪末著名学者博涅茨卡雅(H.К.Бoнецкая)与柯日诺夫关于巴赫金思想的基督教背景的论争中甚至有“福音书即狂欢”这样的命题[12]。苏联解体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俄罗斯学者在研究巴赫金时,往往把他作为整个西方哲学或俄罗斯宗教哲学的一部分加以考察,将他与欧洲其他著名思想家及20世纪初的一批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并列[13]。无疑,他们宽阔的学术视野和开放的研究方法是值得我国巴赫金研究者借鉴的[14]。
标签:巴赫金论文; 基督教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基督教教育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耶稣论文; 人性论文; 东正教论文; 道成肉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