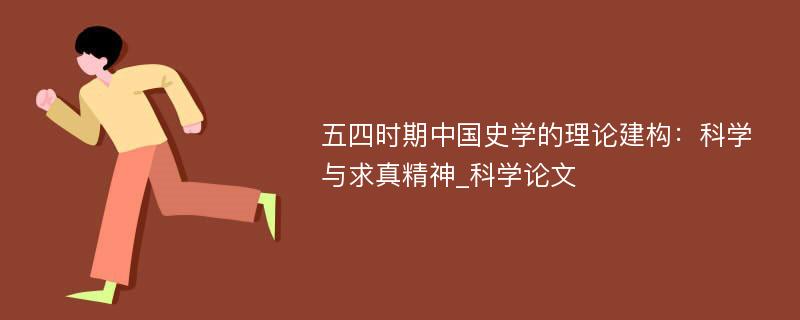
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理论建树:科学与求真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建树论文,中国论文,理论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史学从晚清以后开始渐显区别于古代史学的若干“近代化”特征。王国维说,“道咸以降之学新”[1] (卷23 《 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P720),即指新旧中西诸种因素影响与制约之间中国学术的发展趋向,其中“以降”二字的历时性意味颇为明显,准确体现了中国史学自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趋新过程。事实上,学术变化较之社会变化往往更为平缓滞后,即使19世纪后期被李鸿章称为“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但史学的“近代化”依然若隐若现,直到五四时期,近代中国史学的真正“变局”才终于形成。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所造成的危机日益严重,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发生了变化。史学的变化总是与客观历史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彼时出现的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对当代史的撰述、对外国史地的介绍等方面的热潮,因为与救亡图强和爱国主义这样的中国近代史的主题直接相关而具有近代色彩,但是中国史学主流仍然是传统史学的延续,史学仍然局限于传统史学的藩篱之中。
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号召,呼吁“史界革命”。当时的梁启超视史学为“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2](P1),此新史学思潮浸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政治诉求大于学术关怀,批判意识多于理性分析。新史学思潮的骤起,既是时代影响史学所使然,也是史学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的具体表现。客观而言,近代史学不同于传统史学之处在于,近代史学受到社会的影响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嬗变趋势,其中包含有近代民族主义、今文经学、进化史观等复杂因素。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史学的发展及其近代化的特征,在各个方面为古代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然而,到五四时期之前,史学主流仍然是传统史学的延续,对史书的校勘、考订、续补、辑佚等工作依然是绝大多数学者的案头工作,史学尚未获得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独立地位,史学自身从观点、方法到内容都还没有突破传统史学的基本轨迹。
笔者认为,史学毕竟是一门相对独立的人文学科,有着自己的学科特性和学科范畴。近代以来救亡图强、挽救民族危亡的严峻现实,从外部刺激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趋势,但这尚不具备传统史学转型的全部条件。换句话说,爱国主义激情还不是影响替代学术研究的全部因素,它只是对史学转型起到了一个强烈影响的外部推进作用。然而,近代社会的变迁不可能不影响到史学,史学的真正转型还需要从其理论、观点与方法等诸多史学的内部因素中产生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经过19世纪后半期的酝酿、发展,特别是20世纪初期新史学思潮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与新的历史观的引进,直到五四时期对民主与科学的大力提倡,才得以初步实现。五四时期是中国史学转型的重要时期,五四时期是现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开始阶段,中国现代史学在五四时期初步建立起来。
五四时期的时代主旋律是民主与科学。陈独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科学),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3](P242-243)民主与科学这两个词是外来的,但是这两个词所代表的含义和内容,却是中国从上到下所急需的和必需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到来,成为开启中国通往现代化之门的钥匙。
五四时期是思想空前解放、思想文化领域空前活跃的时期,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期。由于民主与科学的提倡,使人们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估定。中西学术交融的趋势,也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在五四时期所独具的时代特色中才得以进行。民主和科学的提倡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遍及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领域。民主和科学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在观念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条件,中国现代学术也是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飙中开始建立起来。
内涵丰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掀起的狂飙,是促成中国史学转型最重要的推动力。五四新文化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新、旧史学的冲突和承继,中、外史学的碰撞与交融,构成了史学转型的复杂景象,带来了中国史学从观念到方法、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全面更新,并由此动摇了传统史学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理论根基,为现代史学的建立扫清了思想障碍。五四时期史学成为近现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顾颉刚说:“中国史学进步最迅速的时期,是‘五四’运动以后到抗战以前的二十年中。这短短的一个时期,使中国的史学由破坏的进步进展到建设的进步,由笼统的研究进展到分门的精密的研究,新面目层出不穷,或由专门而发展到通俗,或由普通而发展到专门;其门类之多,人材之众,都超出于其他各种学术之上。”[4]( 《 引论》)五四时期史学无疑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五四时期史学自身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五四时期西方史学思想和方法的涌入,无论在规模和系统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其他学问的变化,如文学、哲学和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等,也辗转影响到了史学。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莅列其中,自觉地将中国与西方史学相结合,史学主流力求融会中西、贯通古今,显示出了崭新的气象。
五四运动至今已经过去了90年,五四时期中国史学转型过程中所推崇的基本理念和学术精神,已经成为影响自那以后直到今天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因素。深入认识和讨论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相关理论问题,依然具有常新的意义。
一、科学与“科学方法”
“科学”二字在五四时期大行其道。讲求“科学”的历史学,是中国史学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赐的直接收获。五四时期对科学的大力提倡,使中国史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国史学的学科独立、史学研究的规范化和规模化等,都与重视科学关系密切。其中最突出的,是从认识论层面对历史学学科性质的思考与讨论,以及因崇尚科学而产生的直接效应——“科学方法”。“科学方法”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广为流行。
用科学的标准与规范看待历史学,关乎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即历史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科学”。这个问题在19世纪的西方就已经成为争议问题。在中国,“早在19世纪末年,主要是20世纪初期,中国史学界,对于历史和科学的关系,历史是否能成为科学,以及怎样成为科学的问题,也曾经有过一系列的介绍和论述”[5](P282)。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涨时期,科学几近成为人们信仰与崇拜的对象。胡适在20年代初曾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和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6](P2-3)因此,历史学究竟是不是科学的问题,也就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历史学的科学属性还有问题,似乎历史学的地位也就随之下降,假如历史学连“科学”都不是,那它还有什么价值呢?
尽管如此,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界对历史学的性质问题仍然存在不小的争议。崇信“科学”者大有人在,而历史学是否为“科学”,则难以得到统一的认可。譬如,以梁启超、何炳松为代表,持历史学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历史发展中没有因果律这样的观点;李大钊承认各种科学“自异其趣”,都各自具有各自的特点,史学也是如此,但是他坚信历史科学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张荫麟等人认为历史学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学衡派(以《学衡》杂志聚集在一起的一批学者)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但是把历史发展的本质归结于心理的、主观的,肯定历史学的科学性,又将其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中;还有一些人则断然否定历史学的科学性质。可见,五四时期对历史学性质问题的讨论已逐渐展开,并基本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个在西方史学界开始出现并引发长时期争论的问题,在中国史学界又开辟了“战场”。这个讨论本身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说明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已经能够走出旧的道德说教的束缚,获得了其学科独立的地位。只有在史学独立的语境中,对历史学性质的探讨才能成为可能,在思考历史学自身属性与科学之内涵外延的关系和互动中,开始现代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对于历史学研究具有普遍性意义。
虽然,在对历史学性质这一认识论层面的探讨中见仁见智,而科学的历史学这一命题在方法论层面却获得了基本一致的认同。提倡科学,重在一种渗透到各个学术研究领域的科学精神,而表现出来的,则是对研究中的科学方法的大力提倡。这就是以胡适为代表所提出的“科学方法”。他自述说:“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7](P94)胡适反复强调这样的意思:“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8](P216)其贡献在于,把中西结合之“科学方法”上升到了方法论层面。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要求建立科学的历史学,尽管对于究竟什么是科学的历史学、历史学是否是科学的等问题有着不同见解,但是在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这点上,意见基本是一致的。顾颉刚说:“我们研究的主旨在于用了科学方法去驾驭中国历史的材料。”[9]朱希祖认为:“用治生物学、社会学的方法来治学问。换一句话讲,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治学问。”[10]陈训慈也说:“史学当有条件的采用科学方法,已为必然之趋势。”[11]建立科学的历史学,给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提供了从事实出发、重视证据、用科学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的思想方法。
获得此种认同的理论前提之一,是摆脱经学束缚的五四时期中国史学有可能纯然将史学“求真”、考辨史料、重现事实作为其“终极”学术目标。时人确信,“科学方法”便是走向这一目标的通途。胡适借古人“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的诗句,强调“科学方法”就是“金针”。“科学方法”的科学二字契合时人对科学的“崇拜”意识,“科学方法”的实际效果是为历史考证方法提供了方法论依据,“科学方法”的内涵是将“历史学拉到朴素的事实的层面上来”。何兆武指出:“五四的功绩在此,五四的缺点也在此。它力图把历史学拉到朴素的事实的层面上来,但事实本身却并不构成其为历史学。历史本身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实证的,历史学也并非是一门实证的科学,尽管它并不排斥自己有其实证的一方面;然而归根到底,它在其本性上并不就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也不可能把自己限定在实证的范围之内。证件或史料本身是不会说话的,说话的乃是掌握了这些材料的人。”[12](P137)“科学方法”实际上是逆向回答了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即通过方法论的认知,把历史学限定为一门实证科学,历史学的“科学”属性便可以得到确认。同样原因,历史学的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被“科学方法”所制约,尽管在正面讨论历史学性质的时候,梁启超、何炳松、张荫麟等人也强调历史学的人文特征,但是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科学方法”所标志的历史考证学渐成主流,遂使历史学的“求真”与实证性功能在五四史学得以彰显。
认同历史学的实证性,排斥历史学的非实证性,只见历史理性,未见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中的非理性成分,强调历史事实,忽视历史解释,这便是科学和科学方法带给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理论认知,现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由此起步。
二、“求真”与“致用”
中国古代史学一直强调“据事直书”的“求真”精神,但这是囿于传统史学范畴内的。传统的历史考证学以实事求是和无征不信为基本准则,仅从概念上言之,这与五四前后要求为学术而学术、把“求真”作为首要目标的治学宗旨并无二致。不同的是,旧史学在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方面,在观念上和认识上均有诸多的束缚和局限,五四时期史学则是单纯就学科功能而言“求真”。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激烈批判旧史学,但是新史学的目的并非求真,而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2](P7-10)。五四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旧礼教、旧道德、旧信仰,努力打破长期束缚在人们头脑中的精神桎梏,传统史学中被奉若神圣的儒家经典、传统价值观念、道德伦理说教和旧史学所具有的鉴戒功能、教化功能、资治功能等,多成为五四时期史家所抨击和怀疑的对象。现代意义上的史学“求真”,始于儒家经典神圣光环的被打破,以及对学术“独立”的追求和对学术研究自身的“尊重”。
在1911年,王国维提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余谓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1] ( 《 观堂别集》卷4 《 〈 国学丛刊〉序》,P877-878)王国维所阐述的“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的道理,首次从理论上论证了史学求真的必要性。史学致用固然是史学的重要功用,但史学还有着其他一些学科所不具备的“无用之用”的功用,此“无用之用”的功用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史学更重要的功用。无论是“有用之用”还是“无用之用”,“事物必尽其真”、“道理必求其是”才是学术研究的宗旨,因此,史学首先应当追求的是“求真”。
五四时期中国史学讲求科学,重视材料和证据,史学“求真”更成为多数五四时期史家所信奉与追求的首要目标。过分强调求真就会与致用发生矛盾,一些五四时期史家或在求真的目标下轻谈致用,或不谈甚至否定历史学的致用功能。梁启超说,学者应该“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学问的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13](P78)他以“求真”、“求博”、“求通”为标准来衡量治学,其中又以“求真”为首位。[14](P113-114)顾颉刚则认为,学问“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15] ( 《 自序》,P25)
过分强调历史学的“求真”属性是五四时期史学的一个特点。然而,求真与致用是史学相伴而生的矛盾统一体,史学“求真”呼声甚高,则史学“致用”必有反弹,此为二者之间的张力使然。五四时期同样有人重视史学的致用功能、非常关注史学的社会价值。柳诒徵说:“我们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应用。”“我所希望于研究历史的人,并不在乎成为考据家,或历史家,而在乎自己应用。”[16]陈训慈也说:“实则史之范围与价值,断不仅前事之记载,其在学术上之地位,与对于社会之关系,且远在其他社会科学也。”[17]主张史以致用,是就史学的目的和功能而言,柳诒徵等人强调正人心,讲史德,进而阐述史学在伦理道德上的作用,“此点从前道德史家笃主之,言之太过。但前事观摹,足以助吾人之节操,其功效未可全没”[18]。缪凤林说历史的意义是“温故而知今,彰往而察来,畜德而日新,崇善而去恶,生活之超脱,胸怀之扩大,爱国之心发,精进之心生”[19]。
从王国维宣称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到五四时期史家对史学求真的刻意强调,再及一些史家对史学致用功能的重视,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史学功用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把史学求真定于一尊,关注史学的独立性,摒弃史学研究中的一切功利目的,是转型中的中国史学对旧史学的一种否定。同时期另一些史家突出史学的致用功能,把史学与个人修养、爱国主义等联系在一起,也不能说是守旧与倒退的表现,他们实际上是将所谓史学的“无用之用”具体化了。史学的求真与致用是史学自身功能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中国传统史学一直在据事直书与经世致用的张力下求得和谐,但囿于传统史学的诸多局限,在理论上和实际上不可能突破传统史学被赋予的种种致用功能,求真也多表现为在某种致用功能规定下的求真。五四前后的中国史学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历史观、史学方法等方面都力图突破旧史学的桎梏,对史学功用的认识也是建立在新的现代史学意义上的。因此,无论是从史学自身还是与史学相关的各个方面来看,关于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探讨已不同于以往,而是完全处于一个新的起点或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便有可能是某些矫枉过正式的看法,如史学仅在求真,或史学就是致用,这是在新的条件下从理论上探讨这个问题的开始。求真与致用不是对立的,致用是以求真为前提,不能强史以就我,但史学却不能局限于求真。从20世纪中国史学的总体发展趋向看,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变化趋势表现得十分复杂,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仅就五四时期史学而言,追求史学“求真”,具有斩除“思想荆棘”的作用,也是强化学科独立意识的自然反应。“求真”和“致用”交错影响到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研究走势。
三、借鉴西方史学与融会中西史学
随着近代以来国人“开眼看世界”的视野扩至西方的思想文化领域,到了19世纪末,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渐次输入中国。新史学思潮中包含的进化论观念、对历史学概念与范围的界定、对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的重视、对史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讨论等,均与吸收借鉴西方史学有关系。当时输入西方史学还处于最初阶段,存在着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梁启超说,当时“新思想之输入”的特点是:“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批评“畴昔之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也”。[13](P71-72)柳诒徵不满译介者的不负责任,他说:“译寄初兴之时,颇有诵述威尔逊、浮田和民之学说者。威尔逊氏之说有广智书局之《历史哲学》,浮田氏之说有进化社之《史学通论》、文明书局之《新史学》,其中所言原理,多可运用于吾国史籍,惜译者未尝究心国史,第能就原书中所举四史示例耳。”[20](P116-117)
五四时期迎来了输入西方史学高潮。五四时期介绍和引入西方史学已经不是先前那样以从日本转译西方史学著作为主要渠道,而是多由西文原著直接翻译过来。由于从事西方史学输入的人员主要是在欧美留学的留学生,他们“多为直接受过欧美现代史学或科学方法正规训练的专业史学家,如何炳松、陈哲衡、徐则陵、李济、李思纯、陈翰笙、胡适等”[21]。西方史学较之以往更为有系统地被翻译介绍到中国、被宣讲于大学讲坛,其规模和内容,与晚清时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有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理论(何炳松译《新史学》)、法国朗格诺瓦和瑟诺博斯的史学方法论以及德国的兰克史学。借鉴并融汇中西以建设中国史学的努力也有成效。胡适将传统的乾嘉考据方法联系于西学中的“科学方法”,从而突出了中西学术间的相通之处,为中西史学的结合起到了具体的示范作用。梁启超借鉴西方史学的理论观点,将中国传统史学从理论到方法重新整齐阐释,其视野之广阔,见解之新颖,思路之清晰,都值得称道。何炳松做了大量的介绍引进西方史学的实际工作,尤其注重借助西方学理发掘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价值。
限于客观条件和主观原因,五四时期借鉴与融会中西史学仍然存在着种种问题,反映了中西学术交融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当时留学西方或接受了西方教育的人,尚难把代表着西方学术界的最新成果系统地介绍到国内。胡适宣传的实验主义,并非当时西方哲学思潮的主流;德国兰克史学在中国史学界一度被作为实证史学的代名词,这与兰克史学本身其实存在着很大距离[22](P238-279);在西方批判唯科学主义的时候,中国史学正流行“科学方法”;“尽管鲁滨孙的著作很多,而且风行一时,他的学术地位并不甚高”,“他只是一个历史知识的传播者,而不是一个研究者;他并没有对于某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作出卓越贡献”,“实在他的基本主张并无任何新奇之处”。[23](P3、6) 何兆武说:“某些西方近代的重要史学流派的思想和方法并没有(或者很少)被介绍到中国来。新康德学派在西方曾经风行一时,而介绍到中国来的,梁启超之后竟成了绝响;另一个近代西方极有势力的流派,新黑格尔学派,在中国史学界也全无介绍。”[24](P395)
面对形形色色的各家各派的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产生有持久影响的并不很多,五四时期的史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真正接受、消化和理解。多数传入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并未被真正消化便复归于沉寂。如何炳松在谈到通史编撰时说:“吾国近年来史学界颇受欧化潮流之激荡,是以努力于通史编纂者颇不乏人。其对于西洋史学原理之接受,正与一般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新文学家同,一时顿呈饥不择食活剥生吞之现象。偏而不全似而非是之通史义例,因之充斥于吾国现代之史著中。”[25](P13)五四时期,除了胡适所倡导的“科学方法”在史学研究中产生明显的影响之外,多数西方史学流派的理论与方法并没有为大多数专业史家所重视,在众声喧哗的五四时期思想学术领域匆匆来去,很少被运用于具体的史学研究中。此外,西方的学术思想也是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着的,刻意追求和了解其变化发展的内容,并将其运用于中西学术交融中去,在当时的情况下,也的确难以做到或力不从心,结果便会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如在当时西方已认识到唯科学主义所带来的消极作用,而在同时代的中国学术界发生的科玄论战,却以“科学”战胜了“玄学”而告终。
杜维运说:“中西史学各自独立发展两千余年,不通生息。自十九世纪末叶起,百年之间,双方开始交流,而认识未至透彻阶段。”[26](P7)五四时期是有规模引进西方史学和有意识融汇中西史学的首次尝试,对西方史学发展的了解有限,判别西方史学价值的能力微弱,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少有进展,都成为制约中国史学借鉴西方史学的因素。20世纪前期西方史学的强势地位,也使中西史学间处于某种失衡的态势,“饥不择食活剥生吞之现象”说明五四时期的中西史学交融是以一厢情愿为基础的。固然,近代以来中国史学落后于西方,但是以中国史学的悠久积淀,知识层面的碰撞与交流还需摒弃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我们必须避免把有关历史思维的西方文化传统当作比较的基础。”[27](P119)有效避免在中西史学交叉研究中出现的以中附西的不平衡现象,不仅需要人们用新的视角对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作更深入全面的研究,而且还有待于对中西史学比较本身的理论与方法作进一步的充实与完善。五四时期中国史学为我们开启的一系列新课题,的确让后人深感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