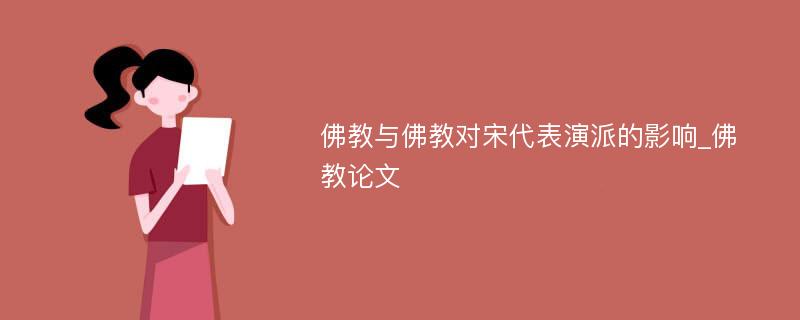
論佛禪詩對宋代理學詩的影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論佛禪詩對论文,理學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從佛禪詩問世,中國古代哲理詩便出現了新的面貌。佛禪詩屬於宗教性文學,它是引用佛教名相概念、歌咏佛教史迹、反映佛學義理、體現佛教思想方式、表現佛理體悟、呈現佛教境界,並以弘揚佛法、指引修行方向、指導修行實踐爲創作意圖的詩歌類型,其創作主體是僧侶、居士和受佛教文化薰染的文人士大夫,形式上包含偈、頌、贊等。 佛禪詩從內容上又可大略分爲佛理詩、佛境詩、參佛詩。這三類詩歌不可避免地也有交叉的部份。相比較學界通常所說的佛理詩而言,本文所謂佛理詩是狹義的、工具性的。它浸潤著佛理,往往以直接宣說佛教教義、佛理思辨爲通篇主旨,是弘揚佛教的方便法門,詩中直白地引用佛教名相的現象比較常見,如鳩羅摩什《十喻詩》演述大乘空宗妙旨及言意之觀,智藏《奉和武帝三教詩》論儒、道、佛三教之异同而贊佛祖和阿羅漢之“三明”神通。因爲缺乏抒情氣息、較少感性形象,賞鑒以演說佛理爲主的佛理詩基本上只有從理性入手這唯一途徑。 佛境詩主要包括居留、游觀佛寺的紀游詩和山水禪意詩,前者如慧遠《廬山東林雜詩》、蕭統《開善寺法會》、王安石《悟真院》;後者如惠令《和受戒詩》、王維《過香積寺》、常建《題破山寺禪院》,其中以表現山水禪意爲主旨的佛境詩可稱爲禪境詩。禪境詩大多出自禪宗一系。佛境詩注重静態的審美效應,多於置身靜境中體道悟理,求取自然靈契和人生覺悟,並以剎那觀照而得的意象直呈自證境界,創造了以現量直觀爲主、佛理與詩藝相渾融的審美範式。佛境詩是心地證悟的產物,就藝術水準而言,是佛禪詩的成熟形態。張寂《重刻和天臺三聖詩序》引汪大紳之言說:“若夫道人之詩,一自真性情中流出。通天地萬物之靈,而無所作爲也;涌泉源萬斛之富,而不立一字也。苟得其意,雖漁歌樵唱,鳥語蟲吟,乃至山河大地,墻壁瓦礫,有情無情,若語若默,一一皆宣妙諦,塵塵皆轉法輪。”這段話對道人之詩的描述主要是佛境詩的寫照。 參佛詩指描寫禮佛贊佛、游觀法會、齋戒誦經、念佛參禪等佛教生活以及士僧交游的詩歌,它以贊嘆、叙事、描寫爲主要手法,如支遁《四月八日贊佛》描繪釋迦牟尼的降生、佛陀的威儀和行迹等,《咏禪思道人》描寫禪思道人坐禪的外境、風神和心理狀態及禪法內容等。 運用詩體形式來闡述義理,這是佛禪詩影響理學詩的主要方面。這種影響是和玄言詩交光互影,並多方鏡鑒,共同發生作用的。單就文學史的淵源而言,佛禪詩灌溉理學詩的具體表現或明顯,或隱微,大約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佛典術語、燈録語録語彙以及與佛教有關的意象的運用 佛教給中國古代詩歌添加了海量的新材料、新語彙。佛禪詩大量引用佛典和佛經用語,從而影響到理學詩在語彙上的更新。這種情况頗爲常見。如支遁《八關齋詩三首》中的“法鼓”、“三界”、“清修”,支遁《四月八日贊佛詩》中的“甘露”,支遁《五月長齋詩》中的“滄浪”,支遁《咏利城山居》中的“埃塵”,傅大士《四相詩》中的“有漏”,傅大士《浮漚歌》中的“浮漚”等,就成爲理學詩人筆下的常用詞。再如佛禪詩中與佛教人物有關的語彙有“釋迦”、“彌勒”、“彌陀”、“菩薩”、“文殊”、“維摩”、“大士”、“波旬”等,與佛教地名或建築有關的意象有“鹿苑”、“化城”、“靈山”、“須彌”、“閻浮”、“净域”、“寶地”、“伽藍”、“梵宇”、“梵宮”、“梵王宮”、“梵剎”等。這些意象都爲理學詩人所慣用。不過,因爲理學家認爲佛教神話虛妄不根,所以這些包含非理性內涵的語彙較少滲入到理學詩的整體藝術構思中。由於時代的變遷,理學詩人在所作佛境詩、參佛詩中使用的典故更多地取自禪籍和禪林公案,而不是早期佛教經典。至於“空”、“幽”、“寂”、“靈”、“净”等形容事物特徵的辭彙,雖不爲佛教所專屬,卻染有濃重的禪寂意味。在理學詩人的山水詩、題畫詩、咏懷詩等類型的詩歌中,如此語彙,不可或缺。 理學詩中的有些意象是虛化了的,不能作純粹的直觀呈現。如理學詩中有海量“心”意象,其出現的前提是佛教對心性的關注,以及佛禪詩對“心”概念的吟咏。“心”在佛典中泛指一切精神現象,如“心地”、“心樹”、“心波”等詞指稱意識,心目即意識與眼識。“心田”指一切善惡種力含藏之所,“心鏡”指清净無染之心性,心香指心中虔誠如爇香供佛。在宋詩中,“心”這個意象往往染有理學的風味,這是和宋學的心學背景以及寫心的理學詩論相關聯的。 理學詩人在與僧侶、居士、施主等佛教信仰者的唱酬中,難免書寫與佛教人物、佛教寺庵有關的本地風光,並使唱酬詩染上佛家色彩。如李復《戲酬楊次公》云:“法云說法元非法,六月洪爐舞飛雪。寶香一瓣下天來,須彌座上金光發。三界風雨動雷音,八部人天歸象設。昔年關西舊夫子,今日淮南大檀越。揚眉師利傾千偈,隱幾維摩無一說。試開門戶立家風,頓超初地無生滅。百川萬折必朝宗,東南到海無分別。紫陌紅塵拂面來,鐵壁不容通水泄。衆形畢現明鏡靜,浮雲飛蓋秋空澈。眼見億萬歸彈指,境落毫厘差永劫。野犴不是師子兒,磨了觜頭三尺鐵。全湖巨浸一浮漚,結果開花今幾葉。昔人卷簾仰天笑,得道固應由慧業。一言可盡千語迷,不如靜看水中月。”①楊次公名杰,次公其字,無爲軍人,因自號無爲子。嘉祐四年進士。因爲從游胡瑷之門,故所學頗有根柢。早期傾心禪宗,留心釋典,歷參諸老宿,得從天衣禪師而開悟,是不變儒形而心游相外之人。其人“嘗上殿神考。頗問佛法大概,楊並不詳答,云:佛法實亦助吾教”。②從李復此詩看來,楊杰此人已把生活沉浸在佛教之中。詩的開篇即提示觀諸法性空的般若智慧。“非法”即法空,意謂萬物皆由因緣而生,没有獨立性,故無實體存在。“洪爐舞飛雪”用的是“紅爐點雪”的禪林語典。《景德傳燈録》載:“石頭曰:‘汝見什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紅爐上一點雪”比喻一切法所依的無常和虛幻。“寶香”指供奉神佛所燒的香。須彌座是安置佛、菩薩像的臺座。“金光”指神佛之光。“三界”在佛教術語中指衆生所居之欲界、色界、無色界。八部指一天、二龍、三夜叉、四乾闥婆、五阿修羅、六迦樓羅、七緊那羅、八摩睺迦。“關西舊夫子”是李復自稱,其人先世家開封府祥符縣,“以其父官關右,遂爲長安人”。③“今日淮南大檀越”指楊杰出知潤州、提點兩浙刑獄。檀越意即施主。“揚眉師利傾千偈,隱幾維摩無一說”,用的是《維摩詰經》第五品《文殊師利問疾品》的故事。“初地”指佛教寺院。“無生滅”意謂諸法之實體無有生滅之相,與“無生”同義。“彈指”是佛教術語中的一個時間量詞。一彈指,即彈指一次所需要的時間,佛教經典用來形容極短暫的時間。“永劫”指永恒的劫波,意即永無窮盡的世界成壞周期。“得道固應由慧業”是說成就阿羅漢的果位要有智慧的業緣。“迷”與“悟”相對,指不如實知見事物。 王次澄《南朝詩研究》言道:“‘佛理’乃超乎感性知識,而臻於自性知識之領域,往往僅可自知而不能言說,若强詞解釋,則必失真且無可會意矣。然於不能不說時,當以象徵寓托之法,求其不觸不背,不脫不黏,由人自悟,乃得徹悟真知。”④佛經中最爲中土詩人樂道的象徵寓托是“水月”喻、“蓮華”喻。永嘉玄覺禪師《證道歌》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禪宗以一統萬、會萬歸一的道理,在朱熹看來,即是“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⑤懶瓚《樂道歌》以無形的水月譬喻隨緣自適的人生態度:“水月無形,我常只寧。萬法皆爾,本自無生。”皎然《水月》以水之虛無、月之皎潔比况佛教般若的妙意難傳:“夜夜池上觀,禪身坐月邊。虛無色可取,皎潔意難傳。”“蓮華”喻則呈現著佛法的潔白、清净和完美。佛禪詩常用蓮花出污泥而不染的特質象徵菩提自性的清净高潔。傅大士《行路難》第四章云:“若捨塵勞更無法,喻如蓮花生淤泥。”寒山詩云:“我自觀心地,蓮花出淤泥。”理學詩人也常用“水月”喻、“蓮華”喻。如林之奇《題雪峰如藏主水月圖》:“千江有月一一同,一月普現千江影。謂一爲月影非實,影既非實月何有。是一即千千即一,水月究竟無實相。隨見有月月在水,亦無究竟非實者。譬如觀音妙色身,對物而見千臂眼。於是千臂千眼中,何者爲正何獨非。菩薩一體作一用,千體同是無剩法。此水此月亦復然,照用齊行一無欠。俯不見月仰亦無,千月闕一固不可。上人此庵憩缾錫,終日宴坐常湛然。散一爲千彌六虛,攝千歸一不盈寸。我知上人環堵中,能廣能狹能方圓。空諸所有何必然,作是見者名邪見。”⑥項安世《題袁才舉明景軒詩》云:“入與神明居,如月出秋水。出與塵坌交,如蓮花泥滓。蓮雖不拒泥,終不與泥同。月豈必在水,亦在潢污中。”⑦這些詩句將諸種譬喻意象妙合而凝,以官感領會理趣,假色相以明心性,故能詞章與義理兼美,感悟和思理互補,其中感悟爲精髓,譬喻爲形態。 二、詩歌文體形式的新變 佛學和理學的新內容要在詩歌中得到表現,必然要求相適應的新形式。就理學詩而言,其義理內涵和詩歌形式的新構造是相互依存的,內容的變化意味著形式的變化。爲了找到表達義理的方式,並以形式上的變化來豐富新內容的開掘,理學詩在內容事實和文體形式上都對佛禪詩有所借鑒。形式制約內容的一例在理學詩的工具性上有所表現。如《法句經》、王梵志詩曾被當作開悟群迷的教材。這類佛禪詩內容上的通俗性、系統性對理學詩人有所啓示。袁桷《書湯西樓詩後》曰:“至乾、淳間,諸老以道德性命爲宗,其發爲聲詩,不過若釋氏輩條達明朗,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絶。”⑧朱熹《訓蒙絶句》九十八首、《齋居感興》二十首等即是“若釋氏輩條達明朗”的研幾窮理的道理之詩,或稱“道氣”之詩,同時也是理學普及讀物的上佳範本。鶴林寺僧壽涯曾爲周敦頤拈出傅大士灼見道體的偈語“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偈即是周敦頤《書舂陵門扉》所云“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的範本。傅大士之偈源自《老子》,展示的是統攝天地萬物的道本體,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周敦頤之詩則說明宇宙萬象莫非道體之妙,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此類以理學話語成篇、與道相適的詩在某些理學家的詩集中幾乎俯拾即是。 佛教和儒學的價值指向之一,是克制情欲而凸現人倫理性,將自然狀態的人改造爲道德自律的人。像《法句經》這樣的偈頌體經典提倡倫理道德,傳揚精神解脫法門,不啻於一部格言詩集。邵雍《伊川擊壤集》中的四言詩多言世道人情,發揮外指性的教化作用和道德教化作用,也帶有格言警句的性質。如《偶書》采用格言警句慣常的對比手法褒善而貶惡:“賢德之人,所居之處,如芝如蘭,使人愛慕。凶惡之人,所居之處,如虎如狼,使人怕怖。妻强夫殃,奴強主殃,臣強君殃。尾大於身,冰堅於霜,辨之不早,國破家亡。”這類對賢德之人、凶惡之人的分辨,可以和《法句經·惡行品》對凶人、吉人及罪報福應的解說比照閱讀。邵雍《好勝吟》云:“人無好勝,事無過求。好勝多辱,過求多憂。”《法句經·好喜品》云:“貪欲生憂,貪欲生畏;解無貪欲,何憂何畏?”這二者都是針對貪欲問題發出的訓誡,流露出人生導師的口吻,如同勸善助化、誡罪非違的箴銘格言,“外示警俗之貌,內藏達人之度”(皎然《詩式》評梵志詩語)。不過從思想內容方面來看,邵雍規誡人倫的詩章原於六經,罕及佛老,見識囿於淺顯的人生哲理層面,甚至幾於凡庸,錢鍾書歸之爲“道德之詩”。從風格上看,《伊川擊壤集》中的四言詩詞句平淺質樸,近於“體同於詩,厥旨非詩”⑨的偈頌,而不同於雅頌、《安世》、《諷諫》、《自劾》之閎奧淳深、莊嚴典則,也不同於《黃鵠》、《紫芝》、《八公》之瑰奇風藻。 佛禪詩對理學詩文體形式的影響更大。隨著佛典的翻譯,中國出現了諸種通俗易懂、不加藻飾的新文體。漢譯偈頌以及中土僧侶、居士等所作的偈頌贊唄即是我國最早產生的佛理詩形態,如三國時維祗難等譯《法句經》、謝靈運《維摩詰經中十譬贊》等。李綱《雙林善慧大士録贊》有兩句談到偈頌體在形式和內容上的自由度:“歌頌句偈自成章,縱橫顛倒皆通達。”⑩王次澄說:“偈原爲印度文學形式之一,其作用在於總攝經義,隨佛經譯傳而行之中土。就其形式言:不拘聲韻,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體;就作法言:不用比興,純爲直說;就其精神而言:非訴之情感,而繫於理性,故全無詩味。由此得知,南朝佛理詩之格言形式乃沿襲佛偈而來,當無可置疑。”(11)《全宋詩》中所收僧詩有不少是參禪悟道的偈子或頌古,而宋代文人中不乏創作偈頌者,如“慶曆中,士大夫多修佛學,往往作偈頌以發明禪理”。(12) 理學詩人筆下也有少量的偈頌作品,這一般是他們與詩僧交游的產物。“僧不詩,則其爲僧不清;士大夫不與詩僧游,則其爲士大夫不雅。士大夫利與僧游,以成其爲雅;而僧之爲詩者,得操其權,以要取士大夫。才一操觚,便時時有詩僧二字在其鼻端眉宇間,拂拂撩人”。(13)在宋代,詩僧與士大夫間出以各自的目的,常以詩偈相交。如圜悟克勤禪師曾作偈示川陝宣撫使張浚曰:“收光攝彩信天真,事事圓成物物新。內若有心還有物,何能移步出通津。”張浚讀後,也投偈呈心云:“教外單傳佛祖機,本來無悟亦無迷。浮雲散盡青天在,日出東方夜落西。”道非云日,而云日可以見道。浮雲聚散,日出日落,青天不生不滅,不增不減,比喻道在時空中的普遍性和永恒性。此理儒釋所同。 陳瓘也有和詩僧以偈唱酬的經歷。他被貶謫到合浦時,詩僧惠洪覺範在長沙,陳瓘寄信給覺範,有偈曰:“大士游方興盡回,家山風月絶塵埃。杖頭多少閑田地,挑取《華嚴》入嶺來。”(14)覺範好議論政事,遭到朋友們的譏諷:“獨陳瑩中曰:‘於道不妨,譬如山川之有飛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精進。’余心知其戲,然爲之不已。大觀元年春結庵於臨湘,名曰‘明白’,欲痛自治也。瑩中聞之,以偈見寄曰:‘庵中不著毗邪坐,亦許靈山問法人。便謂世間憎愛盡,攢眉出社有何嗔。’”(15)陳瓘的詩偈反映出理學精英濡染禪風時的精神狀態。 宋代文人出家爲僧的情况不爲少見。謝枋得有《吾友張四居士爲僧敢献善頌》:“天臺羅漢形模,也學丹霞剗草。少年大振宗風,好箇五山長老。”(16)所用“丹霞剗草”故事,發生在鄧州丹霞天然禪師身上。丹霞天然投入南岳石頭門下,“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諸童行各備鍬钁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沐頭於石頭前,胡跪。(石)頭見而笑之,便與剃發,又爲說戒”。(17)真德秀有《净豁持缽求度爲說偈言》云:“一真不昧人中佛,五戒俱全俗裏僧。必待方袍與圓頂,維摩龐老又何曾。”此偈引著名居士維摩詰和龐居士爲例,說明只要真心修道,一真不昧,五戒俱全,在家與出家没有什麼區別。净豁讀罷,對真德秀說:“如此則不須受度矣。”於是,說偈云:“青編讀後方爲士,黃牒頒時始是官。不拜皇朝真爵命,要行所學也應難。”真德秀說:“解讀青編,便無黃牒亦得。”(18) 理學詩人創作悟道偈頌,需要深湛的佛學學力和對佛教悟道生活的積極參與。在無垢居士張九成身上,曾發生過一個參究“柏樹子話”公案。有一次,他參謁寶印楚明禪師,詢問入道之要。寶印楚明禪師提及“趙州柏樹子”話頭,張九成記在心頭:“一夕如廁,以柏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夜月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19)“正恁麼時”爲唐宋時代的口語,是就在當下的意思。“末句”用的是玄沙師備的故事。玄沙師備欲參尋知識,携囊出嶺,築著脚指,流血痛楚,嘆道:“是身非有,痛從何來?”便回到雪峰義存禪師身邊。雪峰義存問他爲什麼不遍參去,玄沙師備說:“達摩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雪峰義存深以爲然。(20)張九成耳聞蛙鳴,釋然契入,精神上與自然天籟融合爲一家,玄沙則因脚痛而悟。悟入的途徑有別,而領悟的禪機無差。張九成還有一則偈語的創作場景,非常富有戲劇性,僧俗之間打耳光、掀桌子,互鬥機鋒,最後各作一偈。(21)這種偈語隨主觀而興發,意到則言遣,簡截明快,趣味橫生,與相對比較清雅藴藉的傳統文人詩形成了反差。杭世駿《鄭筠谷詩鈔序》說:“宋室理學鬱興,伊川《擊壤》、橫浦偈頌,欲以陶咏性天,發揮理道,譬猶蕢桴葦鑰以爲樂,羹藜飯糗以爲食,操奇觚者或迂而笑之。”(22)此處橫浦偈頌當是指近於偈頌體的張九成《論語絶句》百首。 司馬光對士大夫多修佛學,喜作偈頌以發明禪理的風氣深爲憂慮,擔心儒家主流傳統價值和地位就此失落。他在《解禪偈》六篇的小序中說:“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解禪偈六首》云: 憤怒如烈火,利欲如铦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 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 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 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 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 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23) 司馬光仿擬偈語的目的不是爲了會通儒佛,而是要說明儒學寶庫中本就擁有禪學的理念,士大夫們無須到禪門中尋覓新的思想資源。其實,佛學的精髓在於它的心性之學,而不在什麼“阿鼻獄”、“極樂國”這類粗陋的宗教話語系統中。《解禪偈》意在教誨,實爲策勵士子學儒辟佛而作,內容上承續了《法句經》等漢譯佛教經典的說理性、議論性特點,教示以孝悌忠信、仁義道德等儒學義理,其形式上接近於四句爲一首的別偈之體,字數整齊,韻律自然,短小凝練,便利諷誦,文辭允正,淺顯簡潔,間雜譬喻,較少文飾。如果把這組詩看成聯章體,那麼章與章之間可以說是采用了佛門偈頌常用的對比和排比手法。 宋代文人創作的偈頌習染了禪門詩偈的樸拙之風,有時采取近體詩的形式,但並不嚴格遵守格律規定,所作絶句就多有孤平現象,如林希逸《三偈寄白沙和尚》其三末句“爲向白沙會下來”(24),就是一個孤平句。 偈頌是言理之體。爲了讓短小精練的偈頌成爲有力的論證工具,使其所含義理更爲豐富堅實,偈頌作者常采用組詩形式,如寶志有《大乘贊》十首、《十二時頌》十二首、《十四科頌》十四首,傅大士的組詩有《還源詩》十二章、《獨自詩》二十章、《行路難》二十篇、《行路易》十五首等。這種大規模的義理宣述及其章法給理學詩人以啓示。理學詩人將哲理組詩發揚光大,如邵雍有《首尾吟》一百三十五首、《安樂窩中吟》十三首、《年老逢春》十三首。郭鵬《詩心與文道:北宋詩學的以文爲詩的問題研究》認爲,邵雍的“連作詩”和佛道韻文有著緊密的關聯。 到了唐宋時代,傳統古典詩歌的體式、規格和創作程式,都已經大體穩定。雖然變化的努力也貫穿其中,但無論是古體還是近體,變中自有不變,而不變中的變化主要體現在詩歌的風格和內容上。及至理學詩出現,傳統古典詩歌的社會功能和文化內涵都有所改變,表述內心情感、人生經驗的衝動有所減弱,詩之“名”仍存,詩之“實”已不同。擊壤體是在形式上受偈頌影響最大的理學詩體,因而也最具文體上的創造性。它爲中國古代哲理詩的發展開拓出一種新的體式。邵雍之所以能任意搬弄文字,是因爲偈頌體的多樣性對古典詩體的格律桎梏起到了破體啓示,打破了傳統詩歌語言系統的封閉性。偈頌似詩非詩,韻或不韻,句式多樣,包括五言、七言、三言、四言、六言、雜言,語言文白夾雜,雅俗兼具。邵雍《伊川擊壤集》中的詩歌總體看來也是不拘長短,輕視聲律,句子組織有一定的自由度,除占主導地位的五七言詩歌外,整飭有序的四言詩、六言詩也不少見,間雜有三言詩和雜言詩,三言詩如《堯夫吟》:“堯夫吟,天下拙。來無時,去無節。如山川,行不徹。如江河,流不竭。如芝蘭,香不歇。如簫韶,聲不絶。也有花,也有雪,也有風,也有月。又温柔,又峻烈,又風流,又激切。”(25)這與郊祀歌《練時日》、《天馬來》等漢樂章古奧的風格不類。雜言詩如《觀性吟》說:“千萬年之人,千萬年之事,千萬年之情,千萬年之理,唯學之所能坐而爛觀爾。”(26)《風霜吟》:“見風而靡者草也,見霜而殞者亦草也。見風而鳴者松也,見霜而淩者亦松也。見風而靡,見霜而傷,焉能爲有,焉能爲亡。”(27)這種有主導節奏的雜言體與《詩經》中無主導節奏的雜言詩以及漢代《日出入》、《天門》等不同。邵雍創作雜言詩時有追求對應的明顯意圖。以上所舉詩歌,句式之破常示异,似文非文,明顯乖違了標準詩歌語言的律式。 學術界歷來有玄言詩頗似佛偈的議論,同樣情形,有學者視擊壤體爲禪偈體。劉衍文《雕蟲詩話》說:“前乎康節,若白香山《讀禪經》詩云:‘須知諸相皆非相,若住無餘卻有餘。言下忘言一時了,夢中說夢兩重虛。空花豈得兼求果,陽焰如何更覓魚。攝動是禪禪是動,不禪不動即徐徐。’紀河間於《瀛奎律髓》卷四十七中批云:‘竟是偈頌,何以爲詩?”(28)因爲邵雍的詩有偈化現象,所以禪僧有化用邵雍詩意作偈語者,如邵雍《清夜吟》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前兩句被化用爲“一輪明月當空照,萬里清風宇宙寬”和“月到天心白,波歸海上清”等。《清夜吟》也在敦煌佛教文獻中被發現,由此可見當時人是視之爲禪詩的。 偈頌體詩的若干篇章間或采取對話體、問答體,如《法句經·香華品》說:“孰能擇地,捨鑒取天?誰說法句,如擇善華?學者擇地,捨鑒取天。善說法句,能采德華。”《伊川擊壤集》中也有對話體的詩歌、問答體的句式,如頗多禪偈意味的《能寐吟》云:“何故不寐?湛於有累。何故能寐?行於無事。”(29)《答傅欽之》有云: 欽之謂我曰:詩似多吟,不如少吟。詩欲少吟,不如不吟。 我謂欽之曰:亦不多吟,亦不少吟。亦不不吟,亦不必吟。(30) 擊壤體的篇章結構受偈頌體影響,對古典傳統也多有因革。如《首尾吟》起句結句用同一詞句,造成回環呼應的效果。這種結構明顯受長篇偈頌於每個詩節首句和尾句重複同一語句的啓發。(31)《安樂窩中四長吟》中間以“一編詩”、“一部書”、“一炷香”、“一樽酒”平頭鋪作兩聯,《春水長吟》長律開頭四聯和《花前勸酒》、《春秋》二首,均拈出兩字,在五律中參差反復,轆鱸映帶,使得變化越加複雜,而語調越發流轉。(32)這些手法都濫觴於偈頌體詩的“程式”。 三、修辭手法上的因襲創變 佛典偈頌普遍地運用了多種修辭手法,如排比、對比、反復、譬喻、設問、反問等。《華嚴經》、《法句經》中的偈頌常高頻率運用排比和鋪陳手法,其特點是用一個字或幾個字置於句首或句尾作排比,也有用整句話來反復排比的情形。如《華嚴經》卷六中的一組偈頌將“若”字置於句首反復排比,卷七中的一組偈頌將“入正受”、“三昧起”置於前後句句末反復排比,卷六中的另一組偈頌將“放華莊嚴净光明”、“供養一切諸如來”兩句反復作排比;《法句經·吉祥品》中的偈頌將“是爲最吉祥”作爲最後一句反復排比。邵雍詩歌也有類似排比和鋪陳手法的運用,舉隅如下: 君子與義,小人與利。與義日興,與利日廢。 君子尚德,小人尚力。尚德樹恩,尚力樹敵。 君子作福,小人作威。作福福至,作威禍隨。 君子樂善,小人樂惡。樂惡惡至,樂善善歸。 君子好譽,小人好毀。好毀人怒,好譽人喜。 君子思興,小人思壞。思興召祥,思壞召愤。 君子好與,小人好求。好與多喜,好求多憂。 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道行,好殺道絶。(33) 可以辨庶政,可以齊黎民。 可以述祖考,可以訓子孫。 可以尊萬乘,可以嚴三軍。 可以進諷諫,可以揚功勛。 可以移風俗,可以厚人倫。 可以美教化,可以和疏親。 可以正夫婦,可以明君臣。 可以贊天地,可以感鬼神。(34) 排比和鋪陳改變了傳統美典在語言使用上的節制和省净,起到了加强語勢、語調和語氣的作用。三國時維祗難等譯《法句經》有一種前後兩章以一正一反的對比來表達一個完整意思的形式,如《惡行品》第九章云:“莫輕小惡,以爲無殃。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罪充滿,從小積成。”第十章云:“莫輕小善,以爲無福。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伊川擊壤集》中有以一首詩前後兩部份正反對比者,如《不善吟》:“不良之人,禀氣非正。蛇蝎其情,豺狼其性。至良之人,禀氣清明。金玉其性,芝蘭其情。”(35)《不同吟》:“君子之人,與己非比。聞善則樂,見賢則喜。小人之人,與己非惡。聞善則憎,見賢則怒。”(36)《伊川擊壤集》中也有以組詩形式兩兩相明,舉義不單者,如《興亡吟》、《內外吟》、《善惡吟》;或以上下兩句,對比反襯者,如《答人書》等。此舉數詩以窺一斑: 瞽鯀有子,堯舜無嗣。餘慶餘殃,何故如此? 堯舜無子,瞽鯀有嗣。福善禍淫,何故如此?(37) 卿相一歲俸,寒儒一生費。人爵固不同,天爵何嘗匱? 不有霜與雪,安知松與桂?雖無官自高,豈無道自貴?(38) 邵雍的這些詩歌和《法句經》一樣,通過對比、設問、反問等手法,將“辭樸而旨深,文約而義博”的特點彰顯得更爲分明。邵雍尤其喜歡大量使用反問句,反問數四,貫若連珠,如《辛酸吟》:“辛酸既不爲中味,商徵如何是正音?舉世未能分曲直,使誰爲主主心平?”(39)《人鬼吟》:“既不能事人,又焉能事鬼?人鬼雖不同,其理何嘗异?”(40)《偶書》:“紛紛議論出多門,安得真儒號縉紳?名教一宗長有主,中原萬里豈無人?皇王帝伯時雖异,禮樂詩書道自新。觀古事多今可見,不知何者謂經綸?”(41)使用設問句者如《後園即事三首》其一:“太平身老復何憂?景愛家園自在游。幾樹緑楊陰乍合,數聲幽鳥語方休。竹侵舊徑高低迸,水滿春渠左右流。借問主人何似樂?答云殊不异封侯。”(42)在邵雍詩中,設問手法的使用不如反問頻繁,對答之詞多在有意無意之間。 偈頌體的譬喻常常舉衆物而言一法。劉克莊《遣興》云:“六如偈簡常持念,四勿箴佳最切身。”(43)六如偈指的是漢譯《金剛經》中著名的“六如”喻:“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伊川擊壤集》中也有連用譬喻,多方形容者。且看下列幾組比喻如何將人與物的抽象性質形象化: 良如金玉,重如丘山。儀如鸞鳳,氣如芝蘭。(44) 意遠情融,氣和神逸。酒放微醺,綃鋪半匹。 如風之卒,如雲之勃,如電之欻,如雨之密。(45) 如鸞如鳳,意思安詳。所生之人,非忠則良。 如鼠如雀,意思驚躩。所生之人,不凶則惡。(46) 旁引廣譬,具網兼羅,使得通常比較質樸的擊壤體詩歌變得意象紛涌 佛經中還有般若十喻,即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虛空,如響,如犍闥婆城,如夢,如影,如鏡中像,如化。理學詩人借鑒了佛釋詩以譬喻明佛理的修辭特點,將人生哲理融於般若十喻這樣的比喻中,讓讀者在形象中明理。如林希逸《題達磨渡蘆圖》:“是身如幻本來空。”(47)《再用前韻謝桃巷》:“漆園未悟身如幻。”(48)吳潜《聞同官會碧沚用出郊韻》其三:“細閱人生幻泡影。”(49)《五用出郊韻》其二:“如電如陰如幻境,還知生熟路頭不?”(50)楊時《病中作》:“此身如幻病何傷。”(51)樓鑰《吳少由惠詩百篇久未及謝又以委貺勉次來韻》:“普納萬象如虛空。”(52)陳藻《寄黃景咏》:“人世大都如夢覺,雖然如夢話難忘。”(53)此外,理學詩人筆下用得比較好的還有“火宅喻”等表現大乘空宗觀念的比喻。 四、詩歌語言的俗化和白話化 禪宗語録和偈頌多用白話,具有平白淺易的語言風格。唐代更有一個由王梵志、寒山、拾得等人組成的俗化的白話詩派,其詩歌創作多用自然的民間口語和俗語,涉及“擔水挑柴,無非妙道”的日常生活主題,富有機智幽默的理趣,性質上屬於白話偈頌與民間歌謠相結合的通俗文學。胡適《白話文學史》說:“佛教盛行的時期與後來禪宗最盛的時期產生這一類白話詩最多;後來理學代禪宗而起,也產生了不少的白話說理詩。”(54)這暗示著理學詩人和唐代白話詩派之間有某種淵源。理學詩尤其是擊壤派的詩,受《法句經》等佛典偈頌和唐代白話詩派的影響,具有俚俗化和白話化的傾向。擊壤體的典型特點是語言白俗,概念較多,形式上不拘格律,自由揮灑筆墨。胡適認爲邵雍是一個白話詩人。他的《國語文學史》例舉了邵雍《生男吟》、《謝西臺張元伯雪中送詩》、《自况》、《每度過東街》、《無酒吟》、《南園賞花》、《林下》、《年老逢春》十三之一等白話詩,並說:“這種白話詩真可以代表當時白話文學的一種極端趨向。當時與邵雍往來的一般名人,都很像受了他的影響,都做這一類的詩。如司馬光、程顥、富弼等,都可說是白話詩人。”(55)接著,他又舉了司馬光《花庵詩呈堯夫》、《和堯夫年老逢春》,程顥《秋日偶成》等詩作爲白話詩的例證。理學詩人大多追求語言的平易自然,若以胡適所舉的這些白話詩作爲判別標準,那麼理學詩人的作品有相當多的數量可以納入白話詩的範疇。如陳著《旦起誦邵堯夫詩》云:“二十年前塵路忙,如今都住寂寥鄉。梅花時節溪山好,菜粥人家門戶香。否往泰來天外事,早眠晏起枕中方。案頭只有堯夫集,參得透時滋味長。”此詩是模仿擊壤詩風的。不過,相對於模仿者,邵雍的詩更爲接近口語,更不尚藻飾,更通俗化,下面不妨再舉幾首邵雍的“白話詩”: 人生一世吟 前有億萬年,後有億萬世。中間一百年,做得幾何事? 又況人之壽,幾人能百歲?如何不喜歡,強自生憔悴。(56) 歡喜又歡喜,喜歡更喜歡。吉士爲我友,好景爲我觀。 美酒爲我飲,美食爲我餐。此身生長老,盡在太平間。(57) 比三十年前,今日爲艱難。比三十年後,今日爲安閑。 治久人思亂,亂久人思安。安得千年鶴,乘去游仙山。(58) 不願朝廷命官職,不願朝廷賜粟帛。惟願朝廷省徭役,庶幾天下少安息。(59) 這些詩歌的結構是口語語調和語氣的擴展,語體效果在於流露出主體的情態語勢和聲吻神氣。詩中没有渲染和誇飾,只是質樸平淺地陳天道、稽物理、悉人情,個別地方使用俚語、俗語,打諢打乖,不守傳統,不合典雅,與用語雕琢的美典文人詩對比鮮明。陳著的詩近於擊壤派,在語言的通俗化方面可與邵雍媲美。其《西上罕嶺》云:“此去向南西,山高山復低。不逢清話客,已覺倦扶藜。”(60)其《題畫扇》曰:“松下披衣坐著,飛瀑岩前洗脚。畫向塵污人看,教知山林之樂。”(61)其《題王之朝所惠扇》曰:“八十三歲衰翁,執熱也要清風。此凉來自何處,來自羲之手中。”(62)其《次韻如岳醵飲西峰寺分韻成詩十四首見寄》其八云:“不到西峰爲日久,一日一日一日又。明日有約爲此游,一片雲山想依舊。”(63)閱讀此類詩歌,從審美上看,和誦讀佛典偈頌或佛教白話詩有相似的感覺,即“理勝於詞,質而不韻,雖同詩法,或寡詩趣也”(64)。在筆者看來,上舉詩章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白話詩,因爲其中運用口語的成分比較大,我們可以稱之爲白話化的文人詩。以現代的文學視角來看,擊壤體是古典詩走向白話詩的語言嘗試,《伊川擊壤集》是北宋時代的《嘗試集》。 從總體上看,邵雍詩歌和直寫胸臆的寒山詩都有或俗或雅,涉筆成趣的風格。朱國楨《涌幢小品》比照二者說:“佛語衍爲寒山詩,儒語衍爲《擊壤集》。”(65)他將《擊壤集》與寒山詩相提並論,是因爲二者都是哲學思想的詩化形態,都有著覺世唤醒的社會效能,其散文化的傾向、相對自然的口吻、隨意化的語詞運用擴展了詩歌語言的表意功能,給說理提供了便利。比照《四庫全書》館臣對寒山詩的評價,當能更清楚地看出《擊壤集》與寒山詩的相似之處,《四庫全書·寒山子詩集提要》曰:“其詩有工語,有率語,有壯語,有諧語。至云:‘不煩鄭氏箋,豈待毛公解。’又似儒生語。大抵佛語、菩薩語也。今觀所作,皆信手拈弄,全作禪門偈語,不可復以詩格繩之,而機趣橫溢,多足以資勸戒……多述山林幽隱之興,或譏諷時態,能警勵流俗。”(66)概而言之,《擊壤集》與寒山詩俱以說理爲本,以資勸戒爲用;體式上都不拘格調、韻律,信手拈弄,不以文字爲長;語言風格都以明快質樸爲主。在創作構思上,他們既不苦吟以求工,亦不以工爲厲禁。如邵雍《二色桃》云:“施朱施粉色俱好,傾國傾城艷不同。疑是蕊宮雙姊妹,一時俱肯嫁春風。”(67)雖無高致,但可稱工麗。寒山子云:“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月響,短舞萬人看。”與邵雍《懶起吟》、《二色桃》等同樣工致。就兩者奉行靈悟興會、自然拾得的創作共性而言,可以說寒山詩是禪門的擊壤體,擊壤體是儒門的寒山詩。後來道學派的詩人也多視寒山、擊壤爲同一類型,如唐順之《答皇甫柏泉郎中書》自評其詩文說:“其爲詩也,率意信口,不調不格,大率似以寒山、擊壤爲宗,而欲摹效之而又不能摹效之。”(68)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稱“白雲居士石沆”:“其爲詩,陶冶性情,蕭閑疏放,雅以寒山擊壤自命。”(69) 儘管寒山詩對於擊壤體起到了示範作用,但擊壤體並非直接導源於寒山詩。兩者之間的根本區別在於,擊壤體屬於文人詩,其語言雖有白話成分,甚至部份詩篇近似打油體,但主要語言構成成分還是接近白話的淺易文言。這種淺易文言介於書面語與口語之間,既有書面語的精確與典雅,又有口語的暢達與靈活,適於表達理學家對於精神天地的探詢暨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價值觀。《伊川擊壤集》采用屬於士大夫話語系統的智性語言表述的道理確是深刻細密,表現了這種語言對理學精神的建構作用。《伊川擊壤集》中並非篇篇都是心學性理的說教,其中部份作品還體現出源自士大夫話語系統的古詩之美。文言是古典詩美的家園,擊壤體的淺近文言守住了古典詩美的最後邊界。而寒山詩屬於農禪一系的禪門白話詩,直白如話的詩句中含有大量的俗字俚語,其語言屬於平民話語系統,所說的禪理也比較淺顯。擊壤體以自由活潑的個性化特徵在古近體詩的體式之內時時突破其格律規範,解構著格律詩體的莊嚴性,顛覆著傳統詩學的權威性,吹響的是通俗語言衝擊高雅詩歌形式的進軍號,而典型的寒山詩已經不屬於格律詩的範疇,吟唱的是民間歌謠俗曲和禪門偈頌的混合調。 除邵雍一派外,其他宋代理學詩人受佛禪詩影響,也創作了一批通俗化的詩歌。如陸九淵《語録》有這樣一首白話詩:“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70)陳建《學蔀通辨》卷五有按語指出這首詩是有來歷的。《傳燈録》載智通禪師偈云:“舉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出頭天外見,誰是我般人。”陸九淵白話詩所顯示的精神心術、氣象言語,得到了佛禪氏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之主體精神的孳乳。陸九淵四兄九韶作有《誡子弟詞》: 聽聽聽聽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惰懶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 聽聽聽聽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定定定定。 聽聽聽聽聽聽聽,好將孝弟酬身命。更將勤儉答天心,莫把妄思損真性。定定定定定定定,早猛省。 凡聞聲,須有省。照自心,察前境。若方馳騖速回光,悟得昨非由一頃。昔人五觀一時領。(71) 前三首是“晨揖,擊鼓三疊”後家中子弟所唱,最後一首是“食後會茶,擊磬三聲”後所唱。在文體上,《誡子弟詞》和邵雍《訓世孝弟詩十首》類似,接近於民間歌謠和佛偈。“聽聽聽聽聽聽聽”一字七疊,更帶有鮮明的口語化色彩。 五、詩歌審美意境的佛化、禪化 與俗化和白話化的佛禪詩相比較,佛境詩多有雅化的審美意境,是雅文化的一種言說。佛境詩的意境由主體介入客體的意向和客體召唤主體的結構在互動共生中構成。按照接受美學的解釋,佛境詩的“境”造成了詩歌本文中開放未决的可聯接性的空白、游移視點的參照域內部的非主題性部份的空缺和否定,進而構成了本文的潜在結構。而意境中的“意”無形無相,空有不離,多是由讀者填充到空白中的。佛境詩,尤其是禪境詩,在“空”“靜”觀的指引下,每常通過直呈自然的美麗和神秘,融內心外物於一體,形成空靈幽遠的意象和弦,創造出清寂之境或禪定境界,並表現雙融性相、物我兩空的體道悟境。 從時空性來說,唐前佛境詩數量較少,其數量大增的階段是唐宋時期。宋代姚勉《雪坡舍人集》卷三七《贈俊上人詩序》說:“漢僧譯,晋僧講,梁、魏至唐初,僧始禪,猶未詩也。唐晚禪大盛,詩亦大盛。吾宋亦然。禪猶佛家事,禪而詩,骎骎歸於儒矣。”(72)姚勉所說的“禪而詩,骎骎歸於儒”,是指僧侶創作的以儒家詩法爲標準的文人化的禪境詩。其實,宋代士大夫文人,包括理學詩人,學詩如參禪,也創作了不少禪境詩,這才是真正的“骎骎歸於儒”。有些不用禪語而有禪意的山水詩,將宗教的解悟淡入審美的超越之中,本質上也屬於禪境詩。 自原始佛教到龍樹以來,“明月”一直被大乘佛典喻爲菩提智或光明藏。禪境詩常塑造明月當空、光明遍照的境界,以顯示體用不二、境智一如的自性清净心。如皎然所謂“禪中境”多表現禪定的寂樂,其代表性畫面就是:碧峰之巔,明月高天。皎然《五言聞鐘》:“古寺寒山上,遠鐘揚好風。聲餘月樹動,響盡霜天空。永夜一禪子,泠然心境中。”(73)《七言送維諒上人歸洞庭》:“孤月空天見心地,寥寥一水鏡中山。”(74)《五言答豆盧次方》:“別來秋風至,獨坐楚山碧。高月當清冥,禪心正寂歷。”(75)《五言答俞校書冬夜》:“月彩散瑤碧,示君禪中境。”(76)“禪中境”即以詩境呈現的法悅之心,飄逸著清空的靈氣,可謂冰心玉質,激潔思存。寒山詩重現了以清迥虛曠的長空爲明月背景的“禪中境”:“岩前獨靜坐,圓月當天耀。萬象影現中,一輪本無照。”(77)詩人月下靜坐,端身正念,以孤寂的身心默思參禪。這時他胸臆上明朗而住一輪清净圓滿明月,這便是一塵不起、清純無染的菩提心相。菩提心相寥廓無象,五藴都空,而言語道斷,禪不可說,只有舉萬殊之一殊,“以有象者之能净,見無相者之本空”。(78)理學詩人爲了表現自身心地的廓然自清、完足具備,也喜歡用圓滿、清凉、皓潔的水月意象來呈現寂静圓明、空諸所有的世界,如朱熹《月榭》詩云:“月色三秋白,湖光四面平。與君淩倒景,上下極空明。”前兩句表面文字是描寫寶月流輝,澄潭布影,內藴含義是各具一太極,各自一天機,後兩句寫身心沉浸在水月交映的天地裏,爲寂靜的自然對象所充滿,無垢明净,內外澄明,色相俱泯,萬慮全消。這水中之月、鏡中之象、相中之色與“大空”的禪境別無二致。這種禪境禪意用黑格爾的話說就是:“從主體和內容(對象)的一團混沌中把內容拆開拋開,而且把內容轉化爲一種清洗過的脫净一切偶然因素的對象,在這種對象中獲得解放的內心就回到它本身而處於自由獨立、心滿意足的自覺狀態。”(79) 人融於自然,成爲自然生態中的一個生態位。這在佛偈中會表現爲一種和樂的意境。唐代義净翻譯的《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二十三的五言偈《春時可游戲》云:“春時可游戲,春時可爲樂。我即是春花,共爲游賞事。”此偈講述春時游戲賞玩之樂。筆調間流露出的輕快感、愉悅感,能讓讀者感受到春天節物的駘蕩美好,生命情調的妙不可言,感受到審美主體與周邊春色的融合無間,所謂“鳥語花香,而浩蕩之春寓焉”。(80)此偈雖無直說之理,但秉存翠竹黃花無非般若的義理,在形而下的物色中恍惚可見形而上的活潑生機。這對理學詩以尋春、賞春象徵求仁的詩歌有所影響。朱熹《春日》、《春日偶作》、《出山道中口占》抱持以山水通於理道的孔門心法,在類似的快感和暖意之間,注入仁學的精神,把“仁”放置到“理一分殊”的理學核心理念中作審美的表現,言在於此而意在於彼,著語不多而妙理曲包。通過這些理趣詩,感春成爲理學家分內之事,春日景象成爲理學即事即理的境界。而且,這些狀春色以明仁、寫春花以載道的詩歌誨人之餘亦能娛人,有益之中亦復有味。濡染其理者,不妨資其教化;愛賞其詞者,可以掇其芳華。 置身於琳宮梵宇之中,理學詩人普遍有著變宗教文化爲審美文化的藝術敏感,同時又有化叢林世界爲虛靜天地的道學慧根。劉子翚《屏山集》中與佛禪有關的詩篇主要是善寫方外之情的游寺詩,如《過報德庵》云:“循溪踏危矼,路入筼簹塢。森森翠欞間,一幹橫清雨。茶烟日月靜,石壁軒扉古。盡茲北山旁,小勝無遺取。”(81)如此空山古寺,呈現的是一種靜觀的山水生態,而“靜”是定慧參禪的底色。《題靈鷲窗》描寫了對僧侶閑居環境的清賞:“翠合初疑無路往,停鞭邂逅成清賞。僧爐坐穩紙窗明,細雨忽來山竹響。”(82)第三句是静默的觀照,可謂賞音於澹,與道默契;第四句是自然的律動,“聲雖流而常寂,聽若遇而非綠”。(83)動靜兼攝,喧寂一如,構成當下便是的現量直觀。此時此地,在寺廟的文化空間中,這就是無言的禪味。他如《晨興》、《次韻張守同往華嚴》、《游密庵致明有喜雨詩次原韻》、《過天竺寺》、《山寺見牡丹》、《宿雲際偶題》、《致明携酒來雲際》、《宿回向寺》、《過丹峰庵》、《約致明入開善不至二首》、《游密庵三首》等詩,都描繪了寺院的清幽環境、行履的灑脫自然以及創作主體在此境中的孤獨體驗。那蕭寺殘鐘、溪流急響、山房細雨、譙門鼓角、禪關松韻、雲間孤月等心靈化的意象包含著“瞬刻永恒”的禪意、融合天籟的禪味。 自然的意義總是相對於主體心態而言的,世界只對思想者呈現它的“真意”。詩僧和理學詩人都會融合心中詩意與眼中情境,都努力觀照生命之真與自然之真,但洞幽貫微所看到的“真意”畢竟理禪有別。禪者常在默坐澄心中對自然真如作原真的感悟。法眼文益詩曰:“幽鳥語如篁,柳搖金綫長。烟收山谷靜,風送杏花香。永日蕭然坐,澄心萬慮忘。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法眼宗認爲,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嗚咽,種種幻色都是菩提真性的顯現,應當用澄明襟懷來感應。詩偈前半部份書寫春日景致,構造出聞聲悟道、見色明心的氛圍。後半部份寫長日蕭然而坐,參破了時間,超越了物我,對萬物產生了澄明的感應,繼而忘懷萬慮,臻至物我一如的空空之境。儒者也有兀然而坐,萌發詩性智慧,徹見天地玄機的體驗。李復《東齋獨坐》云:“飛雨日蕭蕭,秋風收晚暑。掩關兀然坐,默與玄相遇。坐久忽相忘,玄我無賓主。神游出八纮,鴻蒙見氣母。”(84)此詩開頭天籟行空,曠蕩無倫,帶有一定程度的流逝感,但以下諸句放縱其心於氤氳磅礴之際,“凡六合以內外,皆不得而囿之”。(85)以上兩詩异床而同夢者在於以森然的物境開頭,接著寫澄心默照,久坐相忘,忘卻賓主之後是對本原的體悟。貌同而心异者在於前詩體悟的是無言的“空”之體性,後詩體察的是元氣的本原。(86)理學詩人雖然或多或少的浸潤了釋道精神,但理學觀念仍然在他們的價值觀中具有壓倒性的地位。 對於宋代理學詩人來說,生活禪意化就是生活藝術化。入得禪境,可以更新對審美境界的存在體驗;領會禪意,可以進入一種帶有自賞性質的精神陶醉狀態。寫作禪境詩是在暫時隔離理學抽象思辨的審美路徑上超越現實生活的方式。理學詩人筆下的入禪文本大多是感性的審美存在,即便其意義和內藴中可以尋覓到明心見性的理學精神氣息,但主要顯示的還是一個虛我而靜己、平衡而寧和的生命樣態。其言說方式是通過意境的塑造暗示主體的本來面目。 佛禪詩對理學詩的深刻影響並不止於天水一朝。如明代的陳莊體“詩語如禪語”(87),既是理學詩的嗣響,又深染佛禪詩的氣息。陳獻章等性氣詩作者端坐澄心,頗近禪風,“蓋以高明絶异之姿,而又加以靜悟之力。如宗門老衲,空諸障翳,心境虛明,隨處圓通。辨才無礙,有時俚詞鄙語,沖口而談;有時妙義微言,應機而發”。(88)其“高妙”和“粗野”的兩重風格,“妙義微言”和“俚詞鄙語”共存的特質,都反映出與佛禪詩的內在聯繫。 ①李復:《潏水集》卷十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②朱彧:《萍洲可談》卷三。 ③《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五,《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④王次澄:《南朝詩研究》,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96頁。 ⑤參見劉因:《四書集義精要》卷四,《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⑥林之奇:《拙齋文集》卷二十,《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⑦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全宋詩》第44冊卷二三七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27361~27362頁。 ⑧《清容居士集》卷四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⑨齊己:《偈頌序》,見陳尚君輯校:《全唐詩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1472頁。 ⑩李綱:《梁溪集》卷一百四十,《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1)《南朝詩研究》,第98~99頁。 (12)潘永因:《宋稗類鈔》卷二十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34冊,第618頁。 (13)鍾惺:《善權和尚詩序》,賀復徵編:《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4)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七,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56頁。 (15)覺範:《明白庵銘序》,《湖廣通志》卷一百十五,《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6)謝枋得:《疊山集》卷十二,《四部叢刊》本。 (17)釋普濟:《五燈會元》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261頁。 (18)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一,《四部叢刊》本。 (19)《五燈會元》卷二十,第1350頁。 (20)宗杲集並著語,张天昱注释:《正法眼藏注释》卷二,長春:长春出版社,1995年,第197~198頁。 (21)《五燈會元》卷二十:“適私忌,就明靜庵供雲水主僧惟尚禪師,才見乃展手,公便喝。尚批公頰,公趨前。尚曰:‘張學録何得謗大般若?’公曰:‘某見處只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尚舉‘馬祖升堂,百丈卷席’話詰之。叙語未終,公推倒桌子。尚大呼:‘張學録殺人!’公躍起,問傍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公毆之,顧尚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尚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尚答曰:‘從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沖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爲乳。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爲汝說。我心與佛天無异,一塵才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净,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爲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銷冰。汝今微有疑與惑,鷂子便到新羅國。”第1350~1352頁。又張九成此二偈爲《全宋詩》所失載。 (22)杭世駿:《道古堂文集》卷九,《續修四庫全書》第1426冊,第286頁。 (23)潘永因編:《宋稗類鈔》卷七,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年,第596頁。 (24)林希逸:《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5)邵雍:《伊川擊壤集》卷十八,《四部叢刊》本。 (26)同上。 (27)同上,卷十六。 (28)劉衍文:《雕蟲詩話》,《民國詩話叢編》第六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426頁。 (29)《伊川擊壤集》卷十七。 (30)同上,卷十二。 (31)孫尚勇《佛教經典詩學研究》稱一首或數首偈頌間所具有的詩句重複現象爲“程式”。該書中所舉重複程式之例有:“瞿曇見衆生,縛在牢獄中。與愛作僮僕,策使諸境界。宛轉老死海,不覺亦不知。是故十力者,常起大悲心。瞿曇見衆生,熾然三種火。常在諸惡趣,種種苦所害。怖畏諸惡道,無有依止處。是故十力者,常起大悲心。瞿曇見衆生,樂著於諸有。放逸心自在,貪著諸境界。常被種種害,而不生怖畏。是故十力者,常起大悲心。瞿曇見衆生,無明黑所覆。種種曀所障,不離一切蓋。諸見亂如絲,無有能解者。是故十力者,常起大悲心。瞿曇見衆生,墮在八邪見。爲愛久住處,以是常縛心。如是諸難中,樂不生厭離。是故十力者,常起大悲心。瞿曇見衆生,起於顛倒心。於苦不净中,而生樂净想。無常無我中,而反我常實。是故十力者,常起大悲心。瞿曇見衆生,依止羸薄力。常爲重擔押,無心生厭離。起於堅固想,染著不能捨。是故十力者,常起大悲心。瞿曇見衆生,在有貪海中。利養覆心故,常求愛境界。貪心如野火,熾然不知足。是故十力者,常起大悲心。瞿曇見衆生,具造諸苦業。常爲諸憂悲,苦惱之所逼。爲拔彼衆生,種種諸惱害。是故十力者,常起大悲心。”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16~117頁。 (32)參見錢鍾書:《談藝録》,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89頁。 (33)《伊川擊壤集》卷十六。 (34)《伊川擊壤集》卷十八。 (35)同上,卷十九。 (36)同上。 (37)同上,卷十五。 (38)同上,卷四。 (39)同上。 (40)同上,卷十二。 (41)同上,卷五。 (42)同上。 (43)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四三。 (44)《伊川擊壤集》卷十八。 (45)同上,卷十四。 (46)《伊川擊壤集》卷十七。 (47)陳思編,陳世隆補:《兩宋名賢小集》卷三百二,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綫裝書局,2004年,第270頁。 (48)《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四。 (49)見梅應發、劉錫同撰:《四明續志》卷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0)同上。 (51)楊時:《楊龜山先生全集》卷四二,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4年,第1531頁。 (52)樓鑰:《攻媿集》卷四,《四部叢刊》本。 (53)陳藻:《樂軒集》卷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4)胡適:《白話文學史》上卷,《胡適全集》第十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91頁。 (55)胡適:《國語文學史》第三編,《胡適全集》第十一卷,第122頁。 (56)《伊川擊壤集》卷九。 (57)《伊川擊壤集》卷十。 (58)同上,卷十六。 (59)同上。 (60)陳著:《本堂文集》卷一,清光緒四明陳氏校刻本。 (61)同上。 (62)同上。 (63)同上,卷三。 (64)《談藝録》,第227頁。 (65)《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三。 (66)同上,卷一百四十九。 (67)《伊川擊壤集》卷二。 (68)唐順之:《荆川集》卷四,《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集部第72冊,第390頁。 (69)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第602頁。 (70)陸九淵:《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459頁。 (71)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五丙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24頁。 (72)姚勉:《雪坡舍人集》,《叢書集成新編》第131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年,第696頁。 (73)皎然:《杼山集》卷六,明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本。 (74)同上,卷五。 (75)同上,卷一。 (76)同上。 (77)解缙等编:《永樂大典》全新校勘珍藏版第二卷,北京:大衆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313頁。 (78)《談藝録》,第228頁。 (79)黑格爾:《美學》第一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188~189頁。 (80)《談藝録》,第228頁。 (81)劉子翬:《屏山集》卷十四,《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2)同上,卷十三。 (83)同上,卷十《聞藥杵賦》。 (84)《潏水集》卷十。 (85)葉燮:《原詩》內編下,見丁福寶輯:《清詩話》,西南書局點校本下册,第527頁。 (86)《莊子·在宥》:“云將東游,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成玄英疏:“鴻蒙,元氣也。”《莊子·大宗師》:“伏戲氏得之,以襲氣母。”陸德明釋文引司馬彪曰:“氣母,元氣之母也。” (87)《陳獻章集》卷五《次韻張東海》,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499頁。 (88)《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白沙子九卷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