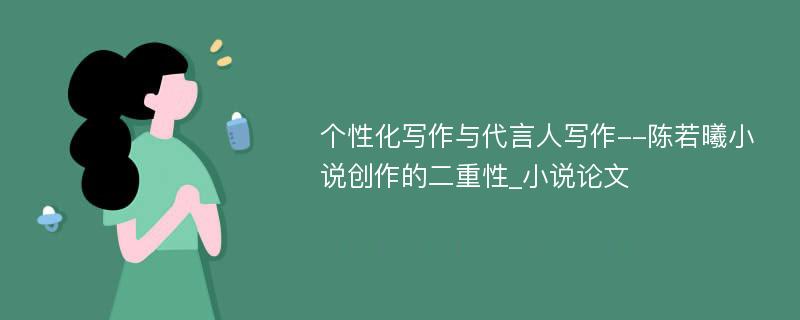
个人化写作与代言人写作——陈若曦小说创作的双重品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品格论文,代言人论文,小说论文,陈若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女人从政和对政治生活真正感兴趣的目前还是极少数,而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她们对社会政治热切关注的实是凤毛麟角,而陈若曦则是这少数中的一员。”(注:朱蕊:《陈若曦印象》,《港台文学选刊》94年第12期。)这无论是对陈若曦还是其创作都已是公认的评价。陈若曦留学美国时,结识留美博士段世尧,受他政治热情的影响,从“害怕政治”,一变而“热衷政治”(注:陈若曦:《述说四十六年》。)。1980年,为“高雄事件”二度谒见蒋经国,1985年,又受到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接见,谈论“一国两制”方法统一祖国的可行性问题,后又投身于世界环保运动,俨然一个热心的政治活动家和社交家。从台湾六、七十年代经济的变革和社会的转型,到七、八十年代的政治民主化运动,从大陆六、七十年代的“文革”到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都在她小说中有所涉及,海峡两岸政治的风云变幻,都在她作品中留下痕迹,其小说创作,可谓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实现了她“坚持写实主义道路,为文言之有物,也崇尚民族和社会使命感强烈的作家”的承诺。不过,如果我们细心地考察一下她的小说文本,并进一步追问:陈氏作为一个作家最成功之处何在?其作品最感人的东西是什么?就会发现上述公认的评价仅指出问题的一面,也没有击中陈氏创作的要害。实际上,她的小说夹杂着“私人话语”和“公共话语”,交织着个人化写作与宏伟叙述。表面上看,她是“少数中的一员”,她的内心深处仍是和大多数女人一样,其创作也和大多数女性作家一样,女性化的个人化写作是她的擅长,背离这一方向,她的创作就可能出现游离、断裂,从而削弱感人的艺术力量。
个人化写作是个人经验的自由书写,个人情感的自然渲泄,反映个人的愿望,这种经验、情感和愿望没有被作者放入历史之河来观照。值得注意的是,这经验、情感、愿望并不完全直接指向作者,而是那个拘于一己范围之内体验、渲泄的叙述者,甚至人物。她(他)们可能与作者几近于同一,也可能有很大背离。对于女性作家,个人化写作还包括被道德、伦理、男性话语权威压抑了女性意识和经验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流露。代言人写作的作者并不代表他个人,而是充当“普遍知识分子”的角色,他站在民族、国家、人民的立场上说话,反映民族、国家、人民的愿望,从历史的角度,揭示一定社会时期的本质。这两种写作迥然不同,但也不存在一条绝无可能跨越的鸿沟。陈染认为“每一个个体都代表着全人类”(注:陈染:《另一扇开启的门》。),陶东风则认为私人经验的“提升”是“赋予私人经验以深广的人性内容与哲学、文化内涵,是自然地在“小我”的基础上的扩大而提升,而不是‘小我’迫于‘大我’压迫消失”(注:陶东风:《私人化写作:意义与误区》《花城》97年第1期。)。陈氏有的小说中的“小我”被“自然地”“提升”, 有的则“小我”和“大我”并存,并呈现出断裂。
陈氏创作热情的勃发,与其说是内部的觉醒,还不如说是外部的催发,她是在非自觉意识的支配下拿起文学之笔。1960年,《现代文学》创刊,她由应付必修课的作文,转而为刊物创办人赶任务的创作,写下了《钦之舅舅》、《灰眼黑猫》、《巴里的旅程》、《最后夜戏》等作品,在这过程中,她创作的主体精神的觉醒,使她发现她的写作走向了非自我化,其创作成为“他者”,因而她果断地改道,“回头再写我熟知的乡土人物”(注:陈若曦:《述说四十六年》。)
使其前期写作非自我化的因素之一是:在意识层面上背离了代言人的身份。陈氏家境贫寒,使她易于同情弱者,又自幼目睹日本对台湾人民的欺压,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童年乡村生活的记忆和因此滋生的社会责任感,使之不可能全身投入西方现代派文学,否定人生价值,崇尚虚无,她更关心的是在社会层面上改善劳苦大众的生活问题,而不是弃此不顾的形而上的问题。
因素之二是在意识层面上背离了女性作家的角色。西蒙·波娃说:“女人不是自然之物,是‘文明’塑造出来的”。女人是“自然之物”还是“文明”之物,暂且不论,但女人在感知方式和感知对象上,与男人大有不同,她们有自己的“表达”和“理解”,是明白无疑的。就史而言,大凡男人的故事都是外向性的,场景是宏大的,性质是群体的,其书写也属于那种堂皇叙事,女性史则不然……,它的场景是狭小的,事件是内向性的,性质是个体的,其书写非但不是堂皇叙事,而且带有一种谵妄的巫性。女人感情细腻,观察细致,情感多于理性,内在体验重于外在经历。西方现代派文学抛弃具体的生活形态和情感体验,追求纯粹的形而上的思考,与陈氏作为女性的“理解”和“表达”是相龃龉的。
陈氏早期作品呈现出一种含混,游离和断裂。作为民众代言人的陈若曦,希望反映民间疾苦,反映台湾社会现实,作为现代派的一个成员,超越具体生活形态的存在主义、神秘主义、精神分析理论也在她作品中走马观花地呈现。《灰眼黑猫》的主题话语之一是西方神秘主义,在文本中获得一种神秘的体验,在这神秘中体验激动、恐惧和生活的“意义”;主题话语之二是提示在封建制度下妇女的悲惨命运。两种主题话语呈分裂状态,甚至相互消解,就形成了人们对陈氏早期作品的普遍感觉:不成熟。《巴里的旅程》是存在主义教义的宣讲,而《最后夜戏》则接近于现实主义文本了。
陈氏早期作品中也有不少细腻生动,甚至是不厌其烦的琐碎的精采写实,这是她女性经验的一种无意识体现。尽管陈氏一开始就不是以意识到的女性意识来写作,尽管陈氏一开始就不打算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写作,但女性经验还是无意识的控制了她的书写,使其印上了女性的戳记。《钦之舅舅》的神秘主题也掩盖不住她对自然景物的那一份敏感和女性特有的淡淡的温情和忧伤,《收魂》中琐细的收魂仪式的描写也不失女性的那种精细。不过这一时期她的女性经验描写撒播在文本之中,不能形成鲜明女性文本,同时代言人的身份也在似是而非的理念推演中暧昧不明。
怀着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陈氏远渡重洋,来到大陆,可惜生不逢时,正值大陆“文革”,结果是心灵的一场无以言说的浩劫。也是这场罕见的浩劫,使她再度拿起文学之笔,决心做一个时代的“书记官”。《尹县长》、《耿尔在北京》、《晶晶的生日》、《大青鱼》便是对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记录”,而且是一份女性“书记官”带有很强女性色彩的“记录”。“个人经验与想象一旦与生活真实连在一起,便具有极大的震撼性”(注:邵健:《HERSTORY:陈染的私人生活》,《作家》1997年第2期。)。陈氏这期作品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也正是源于此。
“女性没有广阔斑斓的生活内容,没有宏远深邃的历史意识,女作家大都以身边之事,眼前之景,以一刹那触发的情绪感悟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注:邵健:《HERSTORY:陈染的私人生活》,《作家》1997年第2期。),但这并不妨碍为社会和民众代言。 《大青鱼》写的是“场景是狭小的”、“性质是个体的”个人日常琐事。妇人久病,其夫听说因外国记者来参观,有平日少见的蔬菜鱼肉上市,欣然而往,买得一条大青鱼,乐悠悠地归家,谁知半路被“劫”,老工人无奈何将鱼送回,气急败坏地连鱼钱一同“奉送”了。文本中没有堂皇的宏伟叙述,然而这并没有妨碍陈氏成为一个称职的“书记官”,记录那个具有时代特色又属于个人的一瞬间,历史地、本质地反映现实。其原因在于老工人买鱼而不得愤然离开的“一刹那情绪感悟”暗合了当时因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普遍物质匮乏、人民生活艰难而敢怒不敢言的普遍情绪,个人化写作与代言人写作达成共谋。《晶晶的生日》、《耿尔在北京》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相对而言,稍后的《向着太平洋彼岸》没有获得如此的成功。它的主题话语为关系国家民族、政治的宏伟叙述,其文本的力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话语,并用爱国主义、祖国统一神圣的公共话语作为内聚力整合文本的各个部分。我们仔细地考察文本的各个部件就会发现这有点勉为其难。为了强调代言人的身份,作者广泛地涉猎了台湾、大陆的政治生活。台湾的“高雄事件”,与此相关的左翼、“台独”、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斗争和政治民主化运动,大陆“四人帮”倒台后形势的转变、新时期初期人才的极其缺乏、社会风尚的变迁,都在文本中与读者匆匆见面,未及深谈便一晃而过,留下失之交臂的遗憾,从而也无法在接受整合时为整体尽其所能,相反地起了掩盖、侵蚀、消解整体的作用。文本的另一个主题话语是中西文明的碰击及华侨在这碰击中的态度,利娜等新一代华裔的选择无疑削弱了整合全篇的主题话语的力量。故而陈氏尽管表现出分享主流意识话语、甚至推演主流意识话语的热情,实际上其作用是很有限的,同时她女性经验和个人书写的隐退,也使其作品失去了她其它作品中涓涓细流却感人至深的情感力量。
“HISTORY的叙事理所当然是一种完整的宏伟叙事,而HERSTORY 的叙事,则表现为碎片叙事”(注:胡彦《女性写作…从身体到经验》,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6年第7期。)。 《归》和《纸婚》则是陈氏长篇小说中“宏伟叙事”和“碎片叙事”的两极,代言人写作和个人化写作的两极。
《归》再现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文本直接叙述的时间虽仅一年,地点也集中在南京和武汉两个大城市,但涉及了“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上至高层的路线斗争、江青的专权、林彪叛党,下至红卫兵大串连、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及返城,全国上下清一色的军事化体制,工农兵大学及政治挂帅造成教育质量下降,乡村、城市的普遍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匮乏,都进入了文本。这些确实触及了“文革”时期社会的一些本质。《归》中人物众多,人物关系也颇为复杂,人物之间的对立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戏剧性冲突。人物、环境、情节的复杂关系基本上统一在两个主题话语之下:揭露文化革命的罪恶,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肉体和心灵上的摧残;年青一代的盲从、迷茫和觉醒,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时代的走向。陈的努力基本实现了她社会、民众代言人的身份,《归》也成为一部比较成功的反映“文革”生活的现实主义之作。
《归》中是不是没有个人化写作?个人经验和情感是否被过滤、消除掉了呢?其实不然,她个人的声音还是顽强地混杂在宏伟叙述之中,虽然被宏伟叙述掩盖着,我们还是可以听出来。
《归》看起来人物众多,作者也保持客观和冷静,让人物自由言说,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辛梅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她虽然以第三人称出现,是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叙述者,但她是整个文本中最主要的聚焦者。文本中极大部分人物都是通过她而呈现出来的,其它人物几乎没有直接表露内心的机会,而辛梅则可以自由地进行外部聚焦和内部聚焦的转换,已十分接近于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的地位,也与隐含作者的距离大大地拉近了。隐含作者也可以借她来书写个人情感和个人经验,实际上也确实如此。陈氏借她书写了很多对使她“思想混乱,精神崩溃”的“文革”的个人情绪。这种个人情绪没有纳入理念预设之内,没有接受理性的整合,以一种自由的声音游离于文本之中,干扰了理性的大合唱,也使其代言大打折扣。辛梅对毛泽东雕像、画像的几次心理感受以及她作为一个“海外华侨”深入大陆生活种种的不适、惊奇和不满,便是没有被“消音”的个人声音,它明显与“深邃的历史意识”和冷静的理性思考存在距离。
《归》的个人化写作还体现在书写方式上,“题材的‘私人化’,决定了女性写作在艺术结构方面的弥散化和意绪化……。‘讲故事’不是女性的优势所在”(注:邵健:《HERSTORY:陈染的私人生活》,《作家》1997年第2期。)。陈氏也不例外, 而“讲故事”和善于组织故事往往是显示长篇小说作者才华的重要地方。陈氏为了绕过这一关,采取了散点式结构和设置女性聚焦者的方法。
陈氏擅长女性化的“碎片叙事”,《归》中也确实充塞着许多“新闻碎片”,而辛梅则起了连接这些“碎片”的作用。将小说文本划分成南京、武汉、南京三大块,也多少减少了“碎片”堆积的感觉。武汉这一章从主题方面考察,作用是不大的。因为亚男和方正的设置也主要是体现“文革”对知识分子包括归国知识分子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作者设置这一章的主要作用是让辛梅广泛地猎取“新闻碎片”,通过故友重逢的交谈来展现这些“碎片”,并借他们之口对这些“碎片”进行针砭。这样处理减小了文本部件之间所需的而陈氏不善于“讲故事”因而难以提供的内聚力。
从整体上看,由于个人话语的插入,由于陈氏女性经验和女性化写作的局限,《归》不具备那种规模宏大、气势恢宏、高屋建瓴的史诗效果,在很多问题的思考上仍欠深刻,也不可能表现出深邃的历史意识。同时,由于个人化写作又被宏伟叙述所压抑,使得《归》也没有她在此之前的《耿尔在北京》、《大青鱼》及之后的《纸婚》那种深入肺腑的感染力。
也许是人为,也许是巧合,《纸婚》朝个人化写作又迈进了一步,走到了陈氏个人化写作的极点。
《纸婚》的日记体解决了陈氏不善于讲故事的困难,同时也无须为“一刹那间情绪感悟”提供形成文本的内聚力,从而可以自由地书写个人经验,流露个人情绪。
“他习惯早起淋浴,也许蓄胡需要整理,他早上占用浴室的时间相当长。
这时我已穿戴整齐,在厨房里烧咖啡,为两人煎荷包蛋了。
‘真香呀!没有咖啡,光一个淋浴我还醒不过来。没办法,简直上瘾了。’
他咖啡喝得浓,只加奶,不加糖”(注:陈若曦:《纸婚》。)。
“许久不曾享受这样安祥美好的晚餐了。七月的夕阳特别长,直跨过阳台,抱住了桌腿,还把亲吻印上了我的脚背,温而不热。厅堂里亮得金黄朦胧,空气中弥漫着辛辣的柠檬香味。院子里绿油油的生查子,几时已开始结果,万绿丛中点点红,显得生机盎然”(注:陈若曦:《纸婚》。)。
文本中到处充斥着这种个人经验和个人情绪。门前天堂鸟花开的欣喜,后园绿草碧的快乐,暮霭来临时的感伤,寒雨朦朦的凄凉,一顿可口饭菜带来的满足,一次淋漓沐浴引起的痛快,恋人一皱眉的忧伤,朋友一举足的喜悦,它们日复一日,周而复返,自生自灭。它们也纯粹是个人的,与时代无关,与历史无关,仅是“往事的某一瞬间所携带的气味,颜色、空气的流动与声音的掠过”(注:林白:《记忆与个人化写作》。)的感受,在历史的抽象中,它们可能会因不是与历史必然性相吻合的心理历程被忽视,但在《纸婚》中成为叙述的中心。
作为个人化写作,《纸婚》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尤怡平在这场婚姻中女性经验和女性意识的自发流露。这场婚姻,本无感情可言,交易成功后,各奔东西。是什么使尤怡平后来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和项住在一起,陪伴他走完人生中最后一程?是母爱,也是异性之爱,更是女性作为弱者象征的被压抑的强者欲望的变相表现。
“络腮胡使他显得成熟而且豪迈,有一份艺术家的飘逸……,他说话低沉而带有磁性,而且未开口先露出笑容……,对女性很牵就,而且彬彬有礼,唯恐冒犯了对方”(注:陈若曦:《纸婚》。)。
这说明项一开始就以其男性之美获得怡平的好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只是这份爱美之心被千百年来“郎才女貌”的男性话语所压抑,男性把女性作为对象来欣赏,而不耻于或不屑于女性把自己作为对象来欣赏,女性也只好压抑这一意识。怡平的好感随着项病情的加剧,他对她越来越依赖,越依顺而递加,她甚至因“左右他的举止”而“暗自庆幸”。这在姨妈、表姐、上官看来不可理喻。我们也可以在道德层面上解释为怡平的善良,而我则更愿意阐释为怡平许许多多年来被压抑的女性强者意识的潜意识流露。女性在男性面前仅能成为弱小的象征,只有在孩子面前才成为强者,给弱小者以关怀、仁慈,人们习惯称之为母爱,因而我们也将怡平的那一份备至的关怀和难以割舍的恋情阐释为女性善良、仁慈而忽视其深层的心理动力,而不愿把它视为反抗男性强权的对异性的爱的表征,而不愿意正视项因病柔弱给怡平带来的不被道德容纳的个人满足。
尽管如此,陈氏也没有忘记她代言人的承诺。她至少企图将下述的三个问题纳入历史的范畴之中。一是美国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她企图让项来完成这一推演,二是同性恋的社会根源以及对待爱滋病的正确态度,她试图让项及其的同性恋朋友来完成这一推演;三是“等待戈多”式的虚无和无望的形而上思考,这在小说结尾部分表现得很突出,并与整个文体出现某种滑离。由于这些理性思考和宏伟叙述撒播在大量的个人话语中,无法构成整合文本的力量,而呈游离状态,使《纸婚》无法成为一部反映美国“垮掉的一代”或同性恋题材的规模宏大、主题深刻的现实主义之作,陈氏也难以成为一个站在历史至高点上的代言人。但是,《纸婚》仍不愧为一部感人至深、艺术圆熟的力作,陈氏也不失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陈若曦在她的小说创作中,一直充当着个人化写作和代言人写作的双重角色,而其所长不在于那种“场景是宏大的”、“性质是群体”的宏伟叙述,而在于那种“场景是狭小的”、“性质是个人”的女性化个人叙述,她要做一个成功的代言人,关健在于将宏伟叙述溶入个人化写作,使个人化写作与代言人写作在某个契合点达到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