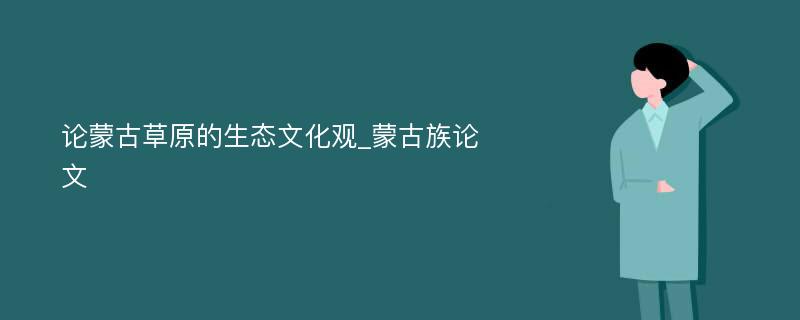
论蒙古族草原生态文化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族论文,草原论文,生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蒙古族在严酷而封闭的内陆草原自然环境中长期从事牧业和狩猎业的生产生活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游牧文化。而草原生态文化观则是这种游牧文化的核心和实质。这是因为,首先,蒙古族的草原生态文化观是从蒙古族所从事的游牧和狩猎的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产生并指导着这个伟大实践,使蒙古族能够生存和发展。其次,蒙古族的草原生态文化观,凝聚着蒙古族人民的最高智慧,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崇高精神境界。再次,蒙古族的草原生态文化观塑造了蒙古人的独特性格和民族精神。最后,蒙古族的草原生态文化观对蒙古族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锻炼和提高了蒙古人的理论思维能力。
天人观是生态文化观中的最基本的观点,在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历来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观的基本内容,反映着不同文化形态的特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东西方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西方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对立性的一面,东方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统一性的一面。蒙古文化属于东方文化系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首先承认并强调二者的统一性,闪耀着“天人合一”思想的光辉,但同时又看到了二者的对立性,具有西方文化“天人对立”思想的若干特点。
作为蒙古族草原生态文化观中最基本观点的天人观包含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人和自然的关系;第二,人和神的关系(人和萨满教的关系);第三,人和理智、理性观念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贯穿着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思考和回答,成为蒙古族哲学思想的基本线索。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这种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凝聚着游牧民族的生存智慧和哲学沉思,决定着蒙古民族历史过程的独特性和观念思想的深刻性。这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和实践基础,换句话说,这是由牧业和狩猎生产的特点和游牧文化的实质所决定的。
牧业生产是在双重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具有植物性和动物性的特性。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把这个特点概括后写到:“他设法依靠他自己不能食用的粗草来维持生活,把粗草变成他所驯化了的动物的乳品和肉类。”这是“人类技能的一种胜利”。〔1〕就作为一种生产技能,一种生产方法来说,牧业具有农业和工业兼而有之的特征。牧业先靠土地提供饲养牲畜的水草等条件,这一点与农业直接生产自己消费的粮食一样,但也有区别,农业直接靠自己栽培的食用植物而生活,而对牧民来说,野生植物仅仅是牲畜的饲草,饲草只有通过牲畜的身体加工,变成肉、乳、油、毛、皮等等,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而这一点又类似工业的加工生产,但又有区别,工业的加工是人直接参与进行的,而野生植物的加工是通过牲畜的活动来完成的。汤因比对游牧和农耕作了详细比较后指出:“驯化动物显然是一种比驯化植物高明得多的艺术。因为在这里表现了人类的智慧和意志力对于一种更难控制的对象的胜利”。〔2〕这就是说,牧业生产是以牧草为第一生产, 以牲畜为第二生产的能量转化过程。这个过程只有在土地、牧草、牲畜和劳动者之间,特别是在牧草和牲畜之间形成平衡协调关系,较好地驯化“更难控制的对象”即牲畜,才能顺利地完成。因此,在蒙古族草原生态文化观中,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独到而新颖的。
第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
人如何对待大自然,是关系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东方人历来主张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认为“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3〕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是朋友, 而不是敌人,应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和谐相处。“将‘天人合一’与‘战胜自然’的观点结合起来,这是理之当然,势之必至”。〔4〕这就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精神。
这一精神始终贯穿了蒙古族草原生态文化观中,但表现的方式方法不一样。古代蒙古人一向把天地万物看成是大自然的构成部分,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共存共荣,大自然的一切现象都是天地的产物,而天地是由气演化而成的。“世界是由混沌的气团构成的,其清轻气上升飘浮形成腾格里(天),其浓重气下降沉淀形成嗄扎剌(地)。”〔5〕人在天地之间,是天地恩赐并养育的。天是“慈悲从爱的父亲”,恩赐了人的生命;地是“喜乐好施的母亲”,抚育了人的形体;野兽是“天地之命所生之”,〔6〕甚至饲养牲畜的水草也是天地赋予的, “向天神求雨,向地神求草”。认为天地万物都有其产生的理由、存在的合理性,都是在相互通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中生存和发展的。当然,天地万物相互之间也有区别、矛盾、冲突,其结果是达到生态平衡,相处共荣、协调发展。北方游牧民族所信仰的萨满教中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实际上反映了自然与人的关系,充满着生态平衡的思想。
大自然历来对人具有两重性,有其恩惠的一面,也有其肆虐的一面。这两重性对于生活在自然条件严酷封闭的草原上的人们来说几乎无选择余地。因而面对两重性的命运,形成了两重性的心理特征和文化观念。这在蒙古族的古代传说、神话、宗教中得到充分反映。
蒙古族古代文化中的“万物有灵论”、“天父地母说”、“善恶观”、“查干哈日”的方位观、各种崇拜意识、宿命论、英雄观、天命论等思想都是针对大自然的两重性的,不但与所生活的自然环境有关,而且与生产、生活的需要紧密相联。一方面蒙古族十分热爱大自然,感谢大自然赋予的丰饶财富;另一方面又畏惧大自然的报应惩罚,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不使自己触犯天地诸神,受到不必要的惩罚,因而形成很多禁忌习惯和崇拜意识。“每闻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蝉避状。”〔7〕“其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底福荫。 彼所欲为之事,则曰天教凭地;人所已为之事,则曰天识著;无一事不归之天,自鞑主至其民,无不然。”〔8〕
另外,在蒙古族古代文化中充满着一种爱护牲畜、保护生态的意识和情怀。这是因为天地万物与牧业狩猎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在广阔草原这种生活条件不甚理想的环境中,牧民没有牲畜不能生活,同样牲畜没有牧民的精心照管也不能生存。“如果说牲畜不但把乳品而且甚至还把肉类也交给了牧民,那么牧民也至少替他们的畜牲找到了生活资料。无论哪一方面如果没有对方的帮助都无法较大量地在草原上生存。”〔9〕
蒙古族爱护牲畜、保护生态的思想和情怀既反映了生态平衡的客观要求,又体现了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主观愿望,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牧民们为了生活,有必要屠宰牲畜,但严禁无限制的种种不必要的杀生。在宰杀时有念咒和伴随某种从偶然的“死亡”中企求“永恒的生存”的祈祷方式,并且严格选择屠宰牲畜的品种和限制数量,同时还有一些禁忌规定,如“宰畜而食需缚其足,剖其胸,以手抓其心直至畜死,不许用断喉方法,违者死,籍其家,以尝首告之人”等等。〔10〕狩猎在其经济生活里占有重要地位。猎民要狩猎必须有足够的猎物和场所,所以猎民们不是捕光杀尽猎物的,而是有意识、有目的保护猎物,注意狩猎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即保持生态平衡。“若夫射猎,虽夷人之常业哉,然亦颇知爱惜生长之道,故春不合围,夏不群搜,帷三五为朋,十数为党,小小袭取,以充饥虚而已。”〔11〕在这种对牲畜猎物爱惜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求得适应和利用大自然的生态环境,协调与大自然的关系,获得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的愿望。
第二,遵循自然法则,保护牧场的思想
“天人合一”包含着“天道”和“人道”相结合的思想。人要认识和改造自然,必须要遵循自然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2〕牧业狩猎生产和生活不仅依靠良好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同时还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尊重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多样性,否则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而且相反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
牧场和牲畜之间的矛盾是牧业生产中贯穿始终的必须不断解决的主要矛盾。其一是牲畜的不断繁殖、数量的日益增多与有限的可利用的牧场之间的矛盾;其二是牲畜对牧场还具有一定的掠夺性。蒙古族学者道润梯步说过:“牲畜一进入草场首先就吃好的,好的不足了才吃次的,次的不足了就要转移牧场,游牧民自然跟随其畜群逐水草而辗转移动,这是必然的。”〔13〕一般情况下“此种游牧民族因其家畜之需食,常为不断地迁徙。一旦其地牧草已罄,则卸其帐,其杂物器具以及最幼之儿童,载之畜背,往求新牧地”。〔14〕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解决这一矛盾有两种方法,一是发动战争,掠夺和侵占别人的牧场;二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转移牧场。这就是游牧部落和民族相互之间发动战争的一个经济原因,也是牧业生产经常“游”的根本原因。
“游牧”(蒙古语“敖特尔”)是在粗放经营条件下,解决牧场和牲畜之间矛盾的最好办法,是保护生态环境,恢复牧场繁殖力和提高其使用率,增强牧业经济效益的有利措施。这种游牧生产和生活是在严格遵循大自然的规律、保护生态平衡的条件下,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的。这是游牧民族走“敖特尔”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是游牧生产和生活整个过程的本质和规律所在。“各部落各有其地段,有界限之,在此段内,随季候而迁徙。春季居山,冬近则归平原。”〔15〕根据季节气候的变化和特征,对牧草的种类长势,草场的大小好坏,牲畜种类属性,畜群的大小,迁徙地段的地形、水源等,进行详细分析研究,才能作出最佳的选择。这样既能保证牲畜的牧草饲料,又能促进生态发展的良性循环,有利于分群放牧,分工管理,也有利于牧业的生产和再生产。
游牧人在生活中所用的器具,颇适应这种游动的生活方式。从蒙古包的功能上看具有防寒、防风、防暴雨、制作简单、拆除方便、省料、省工、省时等特点。黑格尔说:“关于这种建筑物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目的和使命以及由它所建立的环境,要使建筑结构适合这种环境……要结合目的来考虑这一切因素之中,创造出一个自由、统一的整体,建筑师的才智就是要对这个课题的完满解决上见出。”〔16〕蒙古包恰恰是蒙古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聪明才智的结晶,是蒙古族草原生态文化观的生动体现。蒙古包的造型、轮廓、比例和节奏成为一种规范的形式美,而且搭建时的方向、地形以及自然环境也比较讲究。张德辉《塞北纪行》记蒙古四时迁徙:“大率遇夏则就高寒之地,至冬则趋阳暖薪木易得之处以避之。”〔17〕在辽阔的草原上蒙古包象颗颗珍珠,与笼罩四野的苍穹相和谐,与绿色的自然风光相映照。
蒙古人所用的交通工具也颇能适用于大自然环境,是由草原地域的生态环境和牧民的生活特点所决定的。草原地带凸凹不平,山丘较多,冬天积雪过膝,夏季草深,沼泽多,沙漠多,因此,所用的交通工具必须结实耐用,而且载重量较大,速度较漫,装卸方便,行住两用。交通工具各种各样,根据季节和地势情况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但是大量的经常使用的车子叫勒勒车。这种车的轮子较高,车轴心长,车辕也长,便于在沼泽、草地、荒滩上自如地前进。
天苍苍,野茫茫,广袤无垠的草原是游牧民族赖以繁衍生息的地方。但是广阔的草原,地势复杂,气候寒冷,土地贫瘠,灾害频繁,有很多不毛之地。换句话说,水草丰美的牧场是有限的,牧场的载畜量是有限的,给牲畜提供的生活资料也是有限的。而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则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且在日益增长着。因此,畜牧业虽然能供给牧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但不能供给一切需要,这就产生了有限的资源财富与人们日益增长着的需要之间的矛盾。
解决这个矛盾必须立足于发展畜牧业,增加牲畜头数和质量。对游牧民族来说牲畜是一种循环产品,而不是最终产品,其再生产过程复杂,周期长,技术要求高而严。这是一个植物、牲畜、环境和人的相互作用的一定的自然综合体,也是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其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就会受损或者中断。如有良好的自然环境,水草丰饶,风调雨顺,牲畜“只须加以看管和最简单的照顾,就可以愈来愈多地繁殖起来,供给非常充裕的乳肉食物”。〔18〕可是现实情况是北方草原是干旱性的,降雨量少,且不平衡,经常遭到“黑灾”、“白灾”的威胁和袭击,遇到严冬雪灾“家畜只能用蹄掘雪求食,设若解冻后继严冻,动物不能破冰,则不免於饿毙”。〔19〕牲畜增长缓慢,天灾人祸,疾病流行,死亡率大增。牧业生产的脆弱性、单一性、流动性等性点,一方面容易创造丰富的动产性财富,另一方面也形成了致命的弱点,大起大落,时好时坏。不稳定性几乎成了游牧生产和生活的规律。
不稳定性是带有规律性的,其关键是牧草。随着牧草的荣枯,牲畜有规律地出现夏饱秋肥冬瘦春亡循环往复的现象。因此,必须在生产和生活中树立忧患意识,全面考虑生产和生活条件,一切从长计议,统筹安排。其中最根本性的问题是合理的利用牧场,有限度地使用紧缺物资。因此,牧场的选择和保护是首要的最基本的要求。
牧场是牧业发展的基础。凡破坏牧场者应受到法律的惩罚或者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禁于水中洗濯身上的衣服,禁便于水中等规定与生活在水源珍贵的草原地带有密切联系,体现了对水源的珍惜和保护。成吉思汗“大札撒”中规定:“其国禁,草生而地者,遗火而炙草者,诛其家,拾遗者,履阈者,马之面目者,相与淫奔者,诛其身。 ”〔20〕
蒙古族在长期的对生态平衡的认识和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草原生态伦理观。蒙古人把自我的生命,融入天地万物,形成浑然一体的大生命。在这个大生命圈中万物与人都有各自的伦理、德性、把人的伦理、德性转移到整个生命世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伦理观,表现出其传统文化中的泛伦理主义倾向。如蒙古人认为马有献力之德性,狗有忠诚之德性等,因而有时把人的忠诚性格拟成生物的德性,用比喻的方式表述人的能力和德性。
第三,树立抗争意识,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有人根据游牧业的随季节逐水草转移的特点,认为“人成了牲畜的附属物”。这个看法值得商榷。游牧过程中牲畜走到哪里,人跟到哪里,反之,人走到哪里,牲畜也被赶逐到哪里。人与牲畜都是游离的,但是,人始终是牲畜的主人、管理者。以天然牧场为物质基础的牧业,在一定意义上更需要发挥人的主动性、能动性作用。牧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人们在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术和知识经验,不断地认识牧业生产的规律,保护了生态平衡,从而创造了不少适应牧业生产和生活的独具特色的放牧、饲养等管理方法,保证了牧业的健康稳定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不能忽视人的作用。
在大自然面前,人需要有积极性、主动性及聪明才智。在牧业生产中人与自然的对立矛盾是明显的。大自然的灾害是经常的、难免的,有时是无法抗拒的。严重的旱灾,往往给牧业以致命的摧毁,使之一时很难恢复。特大的暴风雪,可以吞噬、数以万计的牲畜,使其家庭迅速破产,甚至导致游牧国家的瓦解、衰亡。灾荒一方面对生态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和损失,同时也对生态系统的进化、更替、重建起了促进作用。正是在不断反复中物种得到改良,孕育出适应草原环境和游牧社会经济需要的、具有很强生命力的马、牛、羊等牲畜。面对着没有回旋余地的灾害,游牧人为了生存没有怨天尤人、等待观望,而是正视困难和灾害,同时更重视自己的主体地位,据《蒙古秘史》记载,窝阔台汗时已学会了打井引水,解决人畜的饮用问题,打破了全靠天然河流湖泊供水的情况。
牧民们生存的空间多在高山戈壁,荒漠沼泽,季节变化无常,干燥少水。“其气候寒冽,无四时八节,四月八月常雪,风色微变……其产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至八月又枯,草之外咸无焉。”〔21〕况且,对人类来说,征服动物确实比征服植物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技术要求和感情投入。在这样的条件下,牧民们的视野得到开扩,增进了他们的生存智慧,铸造了他们强悍的体魄和不怕艰难困苦,自强不息、刚健豪迈的积极进取精神,也塑造了既有守旧依赖、崇拜迷信、知足常乐而又有豪迈粗犷、耿直豁达、开放外向、易于接受新生事物的二重性心理特点和性格。这些游牧文化的思想内容和精神素质,恰恰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对立的实践中培养出来的,而这种游牧文化也孕育、陶冶出无数个草原英雄。蒙古民族之所以能够绵延世泽,富有大自然那样的顽强生命力,是因为它拥有生存智慧和发展活力,是因为蒙古族创造了草原生态文化,又得益于草原生态文化的缘故。
注释:
〔1〕〔2〕〔9〕[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第211、 210、216页。
〔3〕《吕氏春秋·贵生》。
〔4〕《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华书局出版,第18页。
〔5〕嗄拉桑:《蒙文诠释》第751页。
〔6〕《蒙古秘史》,第281节。
〔7〕〔8〕〔20〕〔21〕[宋]彭大雅:《黑鞑事略》。
〔10〕《马可·波罗游记》中册,第346页,注四。
〔11〕[明]萧大亨:《北虏风俗·耕猎》。
〔12〕《老子》第51章。
〔13〕《蒙古族古代军事思想研究论文集》第二集,第395页。
〔14〕〔15〕〔19〕《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第29页。
〔16〕黑格尔:《美学》第3卷,上册,第63页。
〔17〕张德辉:《塞北纪行》,转引自刑莉:《游牧文化》第9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