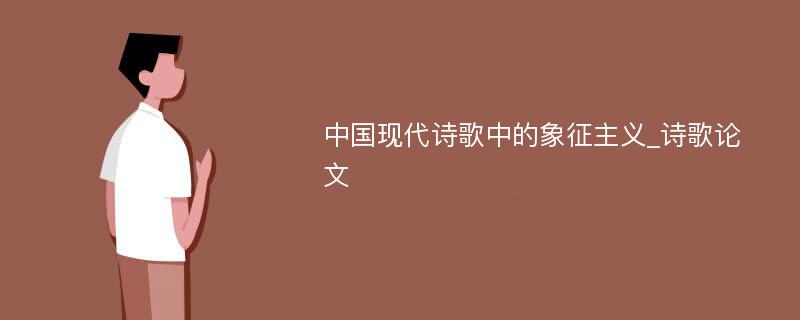
中国现代诗歌中的象征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象征论文,歌中论文,主义论文,现代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57年,惊世骇俗的《恶之花》像“光辉夺目的星星”(雨果语)出现在法国诗坛,继后魏尔伦、马拉美、兰波、瓦雷里等人步涉波特莱尔后尘,竞相争辉,形成了举世瞩目的象征主义文学思潮。在本世纪初,当中国文学冲破传统束缚与世界文学发生广泛联系的时候,也是法国象征主义成为世界性文学思潮之际,因此象征主义文学也就必然地与中国新文学发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联系,以其异域的新声唤醒了东方古国的诗魂。
一
源起法国的象征派诗歌、戏剧是我国新文学中影响最大也是介绍最早的一个派别。早在本世纪初鲁迅、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中,便收了俄国象征派作家安特来夫、迦尔洵等人的十多篇小说和寓言,其后《新青年》、《新潮》、《东方杂志》、《少年中国》等刊物都发表了有关象征主义作家及其诗歌和戏剧的评介文字。在时代的内在要求和艺术自身规律制约下,对西方象征主义的广泛介绍必然在文学创作上引发出美丽的艺术之花。纵观中国新文学的整个文学创作,我们可以看到象征主义文学以这样三种形态存在于新文学的创作过程中:(1 )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其代表作家是鲁迅。他在《域外小说集》所附的《杂识》中称安特来夫的作品“其文神秘又深,自成一家”,称迦尔洵的作品“文情各异迥殊凡作。”在《现代小说译丛》中又称安特来夫的创作是“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的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长明灯》等作品就用扭曲变形的方式把人物浓缩到几乎去形存义的状态用以象征现实内容,带有明显的象征主义文学的特点。而鲁迅《野草》的象征主义特点就更为突出,《野草》不仅在想象与现实的交叉中,把零星的现实物象化为深不可测而又意味深远的境界,揉化进深邃的现实内容,而且在一些篇章中还在现实与想象的交叉中,赋予诗篇超越现实具体生活的内容而具有更为广阔的象征意义。(2 )在五四新文学中象征主义不仅与现实主义艺术原则合而为一,同时也和以郭沫若、田汉等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艺术原则发生了深刻的联系。对于郭沫若来讲,他与象征主义之间的联系主要是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他在《批评与梦》中曾写道:“真正的文艺是极丰富的生活由纯粹的精神作用升华过的一个象征世界。”他在《神话的世界》一文中又说:“他(指具体的世界——引者注)可以使我们对于无知的自然界如对亲人,他可以使我们听见群星的欢歌,听见花草的笑语,使我们感觉得日月的光辉如受爱人的接吻,窥探得岩石的秘密如看透明的水晶,一切平面都变成立体,一切无情都变成有情,我们的坟墓变为母胎,我们的活尸也才从母胎中诞生。”
郭沫若的如上表述很显然是从诗歌艺术创作的一般基本美学原则去认识所谓的象征主义,并且基本上属于浪漫主义“泛灵论”的范畴,但同时也使我们想到世界是一片象征的森林,万物之间息息相通,味觉、触觉等都可以相互转换的象征主义美学原则。田汉曾在1921年写过《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刊登在《少年中国》上。他的剧作《灵光》所创造的“绝对之国”、“欢乐之都”、“凄凉之境”将“眼睛看不见的灵的世界”以另一种真实显示了出来,与象征主义剧作家梅特林克的《青鸟》所创设的“夜之宫”、幸福之宫、未来之国,有着极为相似的一致性,但“象征”的境界所蕴含的内容则与象征主义截然不同。田汉不是用“象征”来表现个人价值不被社会理解的忧郁痛苦,而是用象征的手法表现他那种浪漫的理想的善良的情思。(3 )如果说象征主义思潮在中国新文学的小说和戏剧中主要表现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统一创作过程,那么在诗歌领域则形成了一个以李金发为代表的中国象征主义诗歌文学思潮。其主要代表作家是20年代的象征派诗人和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对于40年代的九叶诗人来讲,他们虽然仍旧有着象征主义诗歌的某些特点,但在诗的总体性及思想内容上已经和西方象征主义发生了很大的区别,开始把象征主义融入现实主义中。这一特点也表现在由30年代进入4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何其芳、戴望舒、卞之琳等人的创作中,因此40年代的九叶诗派和何其芳、戴望舒、卞之琳等人的诗歌创作已经不能看作是中国文学中象征主义的余绪,只能看作是象征主义向现实主义自觉转折中的一种表现形态,本文对此就不作论述了。
中国的象征主义诗人大都强调诗歌艺术的暗示和音乐性,强调感觉和想象,以此去创造那种缥缈不定朦胧幽深的诗歌意境,把苦闷的忧郁和梦幻的哀伤以及内心个性追求不能实现的骚动困扰作为诗歌艺术的表现主题,具有十分明显的西方象征主义特点,虽然这些诗人有些仍旧带有浓重的浪漫气息(王独清的诗歌),但从总体上看浪漫主义已不是贯穿其篇章的主要艺术表现方式。
当我们对中国新文学中象征主义文学思潮的三种存在形态作了简略地说明之后,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确定本文所论述的总旨了,这就是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诗歌、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为主要论述对象,同时对其它兼有象征主义特点的作家附带提及,以期对中国新文学中象征主义的特点以及与西方象征主义的区别和象征主义进入中国文学内在历史的、社会的、艺术的必然性作一探讨。
二
西方象征主义文学思潮在发展过程中的代表人物波特莱尔、魏尔伦、马拉美以及瓦雷里等人的文艺美学观点和对诗歌的追求并不完全一致。波特莱尔曾把包含有生活热忱的忧郁性特征看作是诗的最高表现境界,瓦雷里则认为诗的世界和意境与梦境相似而同实际事物无关,从而提出了“纯诗”的理想,要求诗首先要探索词语的各种联想之间的关系所引起的效果。虽然象征主义诗人之间的美学观念有着某些差别,但他们的这种区别仅仅是侧重点的不同而已。实质上“忧郁的梦幻情思”与“诗的纯美理想”是他们共同具有的追求,只不过波特莱尔与魏尔伦更多地强调前者,而马拉美和瓦雷里则把后者作为第一要义。因此当我们把中国新文学中的象征主义与西方象征主义相联系说明中国象征主义的特点时,象征主义文学的这两大特点便构成了我们所要论述的核心。
“忧郁的情思”里包含着生活的热忱是中国和西方象征主义所共同具有的一个突出特点。那么这种不幸的忧郁之美是如何形成的呢?面对这种“忧郁的不幸”,人在生活中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忧郁”作为自我理想与社会现实相对立而产生的一种思想情绪在西方象征主义诗人那里是以个人的自由和价值追求与社会现实的尖锐对立而引起的。从19世纪中期以后至20世纪上半期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各个阶级、阶层、集团之间的斗争空前激烈,他们在不断地分化和重新组合,这使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都处于动荡不安、分崩离析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的个性自由追求和理想无疑陷入了整个社会的矛盾冲突中倍受践踏,因而波特莱尔认为世界是残酷的,而马拉美则认为诗人的处境“正是一个凿墓穴的孤独者的处境”。由此象征主义者大都认为“自然”和“现实”是“残杀”和暴虐,诗人应该脱离自然,进入自己绝对自由的梦之境界,以发挥自己的个性,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近代文化中所洋溢着的那种理性精神开始瓦解,而被一种人类生存的危机感和悲观意识所代替,痛苦的心灵便被“忧郁”的情思缠绕。对于中国的现代知识者来说他们面临着也同样是个性自由生存愿望与黑暗社会现实的尖锐对立。我们知道本世纪初在中国大地上所掀起的伟大的“五·四”解放运动,是以个性的自由反叛封建传统的束缚,以谋求人的解放为目标的,但是在缺乏西方现代理性得以广泛传播、封建势力十分强大的历史背景下,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进程所存在的内在矛盾的纠缠中,“人的个性解放”在1925年左右便显露出自身的悲剧性特征。正如郭沫若所说:“我们没有这样的幸运以求自我的完成,而我们又未能寻出路径来为万人谋自由发展的幸运,我们的内部要求和外部条件不能一致。我们失却了路标,我们陷于无为,所以我们烦闷,我们倦怠,我们飘流,我们甚至常想自杀。”〔1〕这种苦闷忧郁之思正是这一时期现代知识者的普遍性心态。 也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了象征主义的文学作品,乃至开始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流派。在30年代具有象征主义特点的诗人则是自我的个性理想在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对立中惨遭蹂躏,他们感到青春与人生是那样的渺茫,人的命运是那样的不幸。他们又怎么能不生出忧郁的梦幻呢?
在中国的象征主义诗歌里,“忧郁”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在对社会整体性否定的基础上,对“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无限度寻求而又不能如愿的困扰,不是在“自我”与社会的对立中,极端地走向自身,发现生命存在危机的情思,而是在个性生命热忱与社会现实的对立中,对引起生命发展困境的社会性问题的思考,因此我们看到中国象征派诗歌的忧郁往往是与具体的社会性问题联系在一起。李金发的诗要表现的是“对于生命抑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丽。”对生命欲的抑揄,在李金发的诗里就具体地表现为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中个人自身的忧郁感伤:飘零异域的愁思,失去恋情的哀叹,个人受社会蹂躏后的苦闷等等成为其诗歌表现的基本内容。因此中国的象征主义者普遍地表现出一种倾向,这就是对民族社会命运的强烈关注。在他们看来社会如果变得美好起来,他内心忧郁也许就会转化为一种快乐的欢欣,对于现实的关注远远超过了他们对于人类所存在的一些永恒性问题的思考。这样一来,由于他们不是把“人”放在哲学的高度,从人类生存的困境出发去看待这种忧伤,所以他就缺少在罪恶和黑暗中傲然承担这种苦难的能力,缺少直面现实缺陷和永不停息追求的个人强力意志精神,而总是要寻求解脱。因此我们看到“夜”这一中西象征主义者都着力表现的主题却表现出极为不同的特点。在李金发笔下的“夜”虽然充满了悲愤,记忆发出奇臭,“我们之躯体,既遍染硫磺”,但他所希冀的则是“枯老之池沼里,终能得一休息之藏所么?”(《夜之歌》)穆木天《夏夜的伊东町里》却有胖胖的农家姑娘,朴素的老妇,有柳荫中的插花,河边的泊舟和那朦朦胧胧的灯光……这是一个清新幽深的田园之境以慰他疲惫哀伤的心,石民却愿在夜晚“悠悠地凭着清仙以浮游”,“而且如白云之抱明月以长终”(《良夜》)。30年代现代派诗人戴望舒笔下的《夜》,是那样的清爽和温暖,飘着青春与爱的香味……何其芳的《圆月夜》则充满了柔美的情意,羞涩的花瓣被吻红了,摇坠了眼里纯洁的珍珠……。”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国象征主义诗人笔下的“夜”是受伤的灵魂得以抚慰的归宿。而在波特莱尔和魏尔伦的笔下“夜”则是一个溢满了强力意志精神的人对于不幸的诅咒和敢于承担这种苦难的心灵在夜里对于人类命运的思考。波特莱尔笔下的夜晚,充满了邪恶的魔鬼,“卖淫在各条街巷大显身手,”“以赌博为乐的客饭桌旁”,“聚满了婊子和骗子,”无情的贼子撬开人家的大门,“为了混上几天,给情夫穿衣裳。”(《黄昏》)魏尔伦《夜的印象》则挂满了绞架的萎缩的尸身,士兵持枪走路对着雨的长矛、寒光闪闪。他们俩人是以这样痛苦凝重的笔触展现夜的罪恶,我们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对生命自身的强力发现是没有胆量这样赤裸裸的描写这种罪恶的。由此我们看到中国的象征主义者对于人不幸命运的把握是软弱无力的,他们的个性意志也是不怎么健全的。在中国具有象征主义特点的诗歌中唯有鲁迅的《野草》在对人的命运的把握上达到了现代性的世界高度,在他的笔下也有“夜”,夜里有惨遭蹂躏的粉红色的小花,有闪着许多遗憾的眼睛的天空,有夜游的鸟,更有那直刺青天的刺树。尽管他孤独而又处境险恶,但他仍然默默地铁似地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看到现实的不幸与险恶而毅然抗击这种黑暗的精神正是鲁迅和波特莱尔在思想上所具有的一致性,在这里鲁迅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升华为一种人类命运的思考,而且有了相当的深度。当我们从如上的比较中来进一步分析中国象征主义诗派的价值时,我们说除了鲁迅的《野草》这部并不是典型地象征主义作品之外,其他诗人都由于个人意志精神的微弱而削弱了诗篇的意义,当然他们的忧郁与苦闷骚动不安的内心痛苦也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叛,但生命的热忱蜷缩到自我的纯粹幻化境界中(西方象征主义也追求“梦”,但那个梦是高傲挺立的)时,其反社会力量又是多么的无力。
中国象征主义诗歌中“忧郁与哀伤”的内容所呈现出来的具体性、现实性特点,一方面使他们对于人自身价值的理解没有达到西方象征主义者的高度,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他们一种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献身精神。他们的眼光往往由个人的忧郁转向对社会的关注,在个人与整个民族的历史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行动目标。鲁迅始终关注着民族的命运和国民的灵魂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就是李金发、冯乃超、王独清等较为典型的中国象征主义者,也把改造国民的命运看作是自己的追求,他们不时地从纯美的宫殿走进纷扰动乱的现实世界。30年代的何其芳、戴望舒等人在民族遭受殖民者蹂躏的背景下,则不无痛苦而又欢欣地抛弃了自己以往“诗美”的追求,走向了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何其芳在致吴天墀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话典型地说出了30年代现代派诗人的心态,他说:“两年多来,我很肯定地认为一个人应当怨天忧人—这个成语是有毛病的,我的意思着重在‘忧人’。……这两个旧字眼是不大体面的,因为令人联想怀才不遇的意思。而我一点儿也没有的……我之牢骚并不是纯粹从个人出发而是对着整个社会环境,所以若是愿意用冠冕堂皇一点儿的话说,就是不满意现状。”不满现状的“忧郁”往往转化为对现状的改造和批判,对光明的向往和寻求,因此到四十年代九叶诗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心态已经与整个民族解放联系在一起,而与西方象征主义极端关注自我的思想拉开了距离,使我们无缘听到象征主义幽深痛苦的凝重之音了。
三
“包含有生活的热忱而又遭遇不幸的忧郁和哀伤”作为中西象征主义的基本表现内容,他们大都要求通过诗的象征和暗示、想象和音乐性加以表现,并且还要造成这样一种效果:“能引起人的揣摸和猜想”、“能引起愁思的迷蒙梦境。”也就是一种“纯艺术”或“纯诗”的境界,他们之所以要达到这种目的,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是他们反叛社会,以“纯诗”对抗现实、以幻想的美支撑起个性灵魂的结果。从艺术自身来看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具有的每一种情绪和感觉,我们每一刹那的意识,都是各各不同的。因此我们不可能通过普通文学的常规和一般的语言来恰如其分地传达我们的感觉,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他意识中的每一个顷刻都有特殊的音调,以及这各个因素相互联系的独特方式,诗人的任务就是去发现创造那唯一能够表现他的个性的情绪的语言,这一种语言必须使用象征。这种象征是特殊的、多变的、朦胧的,因而不可能经由直接的陈述和描绘来表现,而只能通过一系列的语调和形象暗示给读者,所以象征主义者坚信,诗歌当产生出有如音乐一般的效果。
中西象征主义诗歌虽然都重视诗的想象、比喻、暗示和音乐性特点,以达到神秘朦胧的境界,但在诗的整体效果上则有差异。朱自清在谈到李金发的诗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他的诗没有寻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来却没有意思,他要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或感情,仿佛大大小小红红绿绿的一串珠子,他却藏起那串儿,你得自己穿着瞧。”〔2〕他又说这是法国象征派诗人的手法。 朱自清先生的这一段话的确说出了李金发诗歌的特点,但运用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则未必确切,凭我们的阅读经验,西方象征主义诗歌往往局部意念难以弄清,而整体感觉则相当完整,也就是说在奇特意象的联结和组合中能够显现出一个朦胧神秘的忧郁世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这里牵扯到中西象征主义者的基本艺术观念和艺术的感知世界方式之间的差异。
西方象征主义者对于诗歌的想象、象征、暗示、音乐性特点的重视是建立在对现实的直接否定基础之上的。波特莱尔就把自然理解为残杀和暴虐,主张艺术须脱离自然,纯从人的地位和艺术家所独有的观点出发,运用想象达到美的境界,由此他特别强调个人的感觉、官能、情绪并使想象绝对化。马拉美则认为诗人所面对的世界应该是“纯粹观念”的、“永恒”的世界,诗人需通过直觉才能把握这个世界。瓦雷里则要求诗人描绘诗人所感觉的世界的幻象,这个世界的幻象也就是赋予内心的观念以感性的外衣。在这里我们看到西方象征主义者把诗看作是个人主观的产物,既无法为理性所把握,也不能直抒胸臆,只能借助于自我感觉的意象来暗示,这也就是“象征”的诗境,或叫“思想知觉化”,即为抽象观念和不可捉磨的内心隐秘找到了“客观对应物”(艾略特),建立了“情绪方程式”(庞德)。当西方象征主义诗人从哲学的意义上确立了诗的表现对象是自我纯粹的主观世界,而客观世界是自我主观的象征对应物时,我们发现他们的诗歌创作过程就是一个整体的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以直觉方式相互对应的过程,因此尽管诗中的个别句子难以理解,但诗的整体意境则相当完整。
中国的象征主义虽然也是把诗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对立起来以表现人的主观世界为核心,但他们的主观世界亦不具有西方象征主义那种哲学意义上的完整性,而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生活的具体性与诗人主观世界相互交叉的特点。李金发曾说,世界任何美丑、善恶皆是诗的对象。诗人能歌吟人,但所言亦不一定是真理,也许是偏执与歪曲。我平日做诗不曾寻求和表现真理的观念,只当他是一种抒情的推敲,字句的玩艺儿。(李金发《诗问答》)在这里我们看到李金发的“主观世界”缺少一种哲学意义的支撑,而未能从人的主观世界的整体性出发去直觉地把握这个世界,而是把自我一些无目的感觉拼凑在一起去抒发感情,这也就必然带来了诗的局部清晰而整体无意思的弱点,因为他没有西方象征主义者那样在作家心灵与宇宙的神秘精神之间寻找到所存在着的某种对应。这种诗歌艺术境界的不同实质上牵扯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在李金发身上的对立与冲突。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核心无疑是对于“人的发现和寻找”,他们那种深刻的哲学思辩意识和对于人自身的大胆肯定,使他们有可能把人从具体中抽象出来,发现人的灵魂特质,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明显地表现为一种“实践理性精神”,对于具体事物的重视以及对于现世的热情往往使我们不能在哲学思辩的深刻性上去探究人的存在价值。当李金发在西方象征主义影响下返归人自身,去表现自我的内心世界时,他对于现实的把握也就未能在“有一个哲学观念”的统一中达到完整,而呈现出艺术直觉的某种具体性和散乱性的特点,也许30年代的象征派诗人看到了早期象征主义的这种弱点,所以他们在接受西方象征主义的基本艺术观念的前提下,又特别推崇古典传统诗歌,卞之琳说过:“亲切”与“含蓄”是中国古诗与西方象征诗完全相通的特点。废名在《谈新诗》的书中明确提出现代派诗是温庭筠与李商隐一派的发展。在这里现代派诗人的这种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自己哲学意识的淡薄而在中国古诗中去寻找诗的境界的完整性特征。当他们一方面呼应着西方象征主义文艺是无目的、只为了抒发自己的幻想、感觉和情感的声音,一方面又没有那种思辩的哲学意识作为支柱的时候,传统诗歌那种感情中包含着理性、主观中又具有客观性内容、理性与情感合一的意境,自然成为其把西方象征主义中国化的最好途径。然而一旦走到这一步西方象征主义已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自身而是成为中国的象征主义了。
中国新文学中象征主义诗派的出现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人对自身的认识,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在他们对艺术本身特征的探索过程中,为中国新诗开创了一条新的路子,丰富了中国新诗的艺术表现形式,形成了一个既不同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自由诗派,也不同于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格律诗派的象征诗派。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派,无疑在中国新诗建设的历史过程中,吸取着异域的营养,为新诗的建设提供了新鲜的内容。
注释:
〔1〕郭沫若:《文艺论集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版,第7页。
〔2〕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据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6月影印。
标签:诗歌论文; 象征主义论文; 李金发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西方诗歌论文; 象征手法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野草论文; 现代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