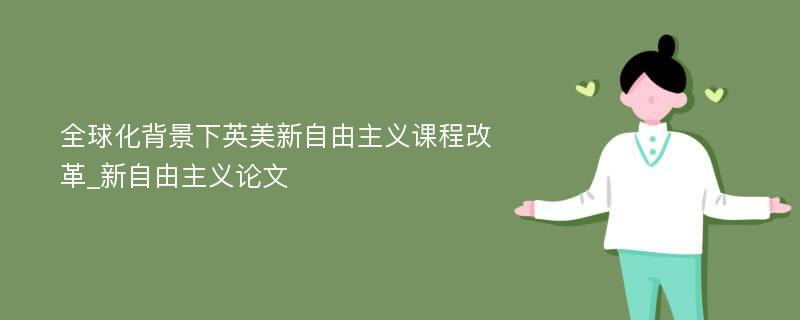
全球化背景下的英美新自由主义课程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英美论文,课程改革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乔姆斯基认为:“‘新自由主义’,顾名思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理论体系,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其初始人。”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
1990年美国经济研究所牵头,召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的会议,最终达成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华盛顿共识”,核心内容是开放市场、私有化和政府放松管制,它构成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的经典模式。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安全战略问题拧紧美国人的神经,小布什执政的共和党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恰如西班牙《起义报》评论:消除对“自由经济”的威胁,即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威胁,是美国通过战争捍卫的主要价值观。(注:何秉胜.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5.)
经济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逻辑强制性延伸。“全球化似乎被正确和错误地视为一种极度单一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它意味着受到自由哲学推崇的经济主义已经渗透到包括教育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类的活动领域。”(注:邬志辉.教育全球化——中国的视点与问题[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6、267.)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市场角逐的日趋激烈,人力资本日益流行,面对国际石油危机、国内反越战呼声日趋高涨,教育改革逐渐成为美国政府和民众关注的焦点。
80年代初期,一系列科学研究结果和调查报告对公立学校现状提出批评,触发了美国商界人士、政府官员、公众等对公立学校的激烈指责,认为公立学校不能帮助学生在学业上——尤其是数学、外语、科学等关键科目上达到优异水平,从而无力适应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高科技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需要。“我们社会的教育基础,正在平庸主义的浪潮中不断被磨蚀,这将威胁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注:(美)约翰·丘伯,蒋衡等译:政治、市场和学校[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23.)
国家危机把教育和商业化竞争紧紧捆绑在一起,面对危机,商业领域中的社团、企业领袖纷纷动用各自的政治资源,要求高质量的学术教育,认为学校质量问题已经影响到商业集团的利益,呼吁“重建美国教育的商业蓝图”,运用市场挽救美国教育。缺乏效率和灵活性的、由国家控制的集权教育体制受到批评,他们认为教育不应该是政府提供一种服务,而应该是自由市场的一部分。市场内部的有效权利是非中心化(Decentralized),通过提供商品交易和自由竞争等途径,提高教育效率和质量,确保学生和家长的中心地位和影响力。 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1955年发表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中指出:“我们相信,若要对我国教育体制动大手术,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私有化之路,实现整个教育服务中的相当大的部分交由私人企业个人经营。”
美国政治家约翰·乔布和泰利·莫在《政治、市场和美国学校》一书中指出:“市场通过它们自身的特性,能够培养高效学校所必须拥有的自治,……消费者不会有购买低效学校的产品的需要,因此这些学校就会从市场中消失。”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放弃传统公共教育理念的民主、公平职能,知识和课程的选择越来越受市场机制的操纵,并且对于市场寄予偏执、浪漫的幻想,正如撒切尔内阁教育大臣约瑟夫爵士指出的:“盲目的、非计划的和没有协调的市场智慧完全优越于精心设计的、理性的、系统的、合作的、有科学依据的和尊重事实数据的政府计划。……市场体制是国民经济的最佳发生器:它能够以人类思维不能理解的方式,在没有强制、指导和官僚干预的情况下,协调和满足无数个体的不同需要。”(注:汪利兵:当代英国教育市场化改革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01,(6).)
在新自由主义的哲学里,知识的价值都是由市场来裁决,凡是有利于市场,就是利于社会的:凡是有市场价值的知识就是有用的、有全球竞争力的。市场商业价值凌驾于其他一切价值之上,要求课程和教学必须对商业的成败负责。“教这门课能让我们赢利吗?”“作为大学的顾客,学生们对某某教师满意吗?”
新自由主义为了培养国家的全球经济竞争力,试图从根本抛弃教育的公共性和道义价值。“‘全球竞争力’(global competitive)这一符咒给公共教育事业尤其是教师造成更大的恐惧、惶惑,使得学问固有的高尚品质几乎得不到任何尊重。如今, 教育必须不断表明其各个专业和课程是怎样服务于市场的。”(注:(加)大卫·杰弗里·史密斯,郭洋生译: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13、20、4、12.)
一、新自由主义课程改革强调功利性、实用性的知识,对“虚无飘渺”的精神、价值、意义嗤之以鼻
知识的生产与传播随着教育事业的日益商业化,而带来事实与价值的分野,知识的内在意义、人性的关怀早已抛于脑后。科学文化丧失启蒙时代的深层次的目的性和价值性使命,日益显示出效率、控制和功利的内涵。在市场原教主义支配下,分数至上和学历主义盛行,学校日益趋向工具化和实用化。实用性和工具性课程占据讲台中心位置,人文课程受到排挤;只重视知识灌输和技能培养,忽略人文素养的养成。在商业化、市场化的炒作下,学校染上了传道求名、授业求利的铜臭味,精神家园、理想净土早已荡然无存。
新自由主义对课程改革影响是通过提升国家经济“全球竞争力”来实现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要求学校课程必须着眼全球市场、按照全球竞争力的标准加以改革。全球竞争力这一符咒使得学问固有的品质几乎得不到任何尊重。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为确保美国全球霸权地位安全延续到新千年,委托有关部门就公共教育现状,起草了包括《国家在危机中》(A Nation at Risk)等一系列报告,这些报告半遮半掩地攻击公共教育,且矛头直指教师和师范学院,谴责教育未能与真正的“全球竞争力”的认识和要求保持一致。像文科以及有关环境、种族和性别平等等社会问题的课程,这类软项目(soft program)开始丧失经费来源。启蒙时代知识整体性美梦已破裂,加拿大安大略省长呼吁大学人文课程应该全部砍掉,因为“它们完全不合经济效益”。(注:(加)大卫·杰弗里·史密斯,郭洋生译: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13、20、4、12.)
“市场隐形课程强调的是学习的职业性而非社会性,强调的是社会关系的竞争性而非合作性。教育的职业化使‘战略’知识(strategic knowledge)——即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能提高经济生产效率的知识取代‘社会’知识(social knowledge )——诸如人文学科或伦理与道德学科的知识而获得特权地位。”(注:邬志辉.教育全球化——中国的视点与问题[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6、267.)
二、新自由主义课程改革将课程实施定格在僵化的预期框架内,教学与师生当下的生活感受相脱离
新自由主义者将课程实施(教学)看作与汽车和面包一样,是市场上待售的商品,期待交易完成之后,实现预设的目标。所以从幼儿园到博士后各个层次的教育中经常听到这类说法,“等你完成这门课程(学年或作业等),你就能……”
教学是生产可预见的商品,市场将预设的未来变成现实,“假如教师认为课程是一件产生于既定的逻辑前提,指向于既定的逻辑结论发展的既定商品,而教学就是将它付诸实施的行为的话,那么,作为以真理为归宿的教学的生机便遭到阻滞。在这个过程中,教学本身就沦落为某种形式的程序操作,教师的存在无需与学生的存在、与作为某种开放的、可解释的、能够引向可能未来的东西的课程之间真正的际遇。”(注:(加)大卫·杰弗里·史密斯,郭洋生译: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13、20、4、12.)
理想中的教学意味着师生当下生命的交流、情感的体悟、智慧的激发,是师生在课堂上唤醒和共享真理,净化心灵之旅。新自由主义者却将课程的实施视为商品交易的过程,教学是向顾客提供满意的商品服务。新自由主义教学一直过分地按“将来时”进行,在重将来轻现在和过去的时间框架内进行。
新自由主义教育似乎是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未来却是现在不变的延续,“具体花样可能会因时势而变,但精神实质依然故我:教育仿佛是为了永远也不会发生的某个东西做准备,因为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讲,一切反反复复发生过了。于是在教学期望中,树立了一个让教学始终面向未来的未来面具,而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未来,因为未来已经在现在中。”(注:(加)大卫·杰弗里·史密斯,郭洋生译: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13、20、4、12.)
三、新自由主义课程决策权集中商界领袖、企业家和私有经济大师,排斥课程理论专家和一线教师的声音
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的导言中论述: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和过程:相当一批私有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多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新自由主义课程改革代表的是商界精英、大企业家和大私有者利益,他们经常指责学校课程无法适应技术发展和市场起伏波动需要,发动大规模的媒体攻势,“我们的毕业生简直不具备对路的技能”、“我们的学校耽误了我们……耽误了我们子弟”,试图彻底改革教育议程。
商业界巨大压力以及激发的公众的不满意度,促使课程改革成为国家和州政府的重要议题,1988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两党竞选人为了争取商界、企业界的选票,都把教育改革作为重要议程,乔治·布什乐称“教育总统”。
二战后,英美自由主义国家经历从经济民族主义向全球经济转型时期,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正在不断淡化民族国家界限,国家公共教育职能不断受到侵蚀,公司和市场对教育的支配权不断加强。国家教育职能的流失可能会导致“公司殖民主义”。
新自由主义课程政策的设计师是企业家、商界领袖和大私有者,他们对教师的经验和感受置若罔闻,在他们看来,教师在课程决策中只不过是公仆,“传递别人的邮件”,“教师反抗全球化势力,尤其是反对教育事业商业化和技术化的呼声,在另一方听来不过是些毫无意义的尖叫,并且谴责教师既忽视了自己作为普通公民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同谋关系,又忽视了历史形成的为较大秩序服务的责任。”(注:(加)大卫·杰弗里·史密斯,郭洋生译: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13、20、4、12.)
四、新自由主义课程管理去中心化,增强地方和学校课程开发自主权,将顾客选择理念引入课程设计
新自由主义崇尚市场主义至上原则,将市场因素、竞争和对顾客的快速反应引入课程管理。面对企业界、大私有者对课程学术质量低效,教育行政机构平庸,对公众的需求反应迟钝的强烈指责,新自由主义者极力主张建立一个富有活力和吸引力的课程管理和开发机制,为家长和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消费。
英美自由主义国家先后经过教育市场化重建、校本管理、择校运动,赋予地方和学校极大课程管理自主权,增强课程开发的灵活性和弹性,满足市场经济多元选择以及引起的经济界对多样化个性人才的需求。新自由主义将学校课程决策和开发权力分散给市场和消费者,致力于科学技术开发研究,培养具有全球竞争能力的人才,推崇竞争和能力主义,但是却缩小了教育的公共性和平等性。
“私有化教育将导致更多的不平等,竞争将强化富有和贫穷之间的界限,增加种族和民族之间的隔阂。”事实上,所有的政府都有责任为公民提供适切的公益教育,承载着重要社会功能的教育不能完全推向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正在制造一种社会分裂:一小部分人将在经济自由全球化的机遇中受益,而大部分人被排斥到社会边缘以外。
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倡导“小政府、大市场、民营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理念,同时日本跨国公司和经济全球化发展也强化了商界对政府教育改革的话语权,教育改革一切依赖于“市场判断”,减化政府和行政的责任,强调“自我选择”和“自己负责”,扩充儿童、家长选择的自由化,忽略教育公共性和保障弱势群体利益,结果诱发了课程管理放任自由、儿童基础学力下降、“班级解体”等教育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