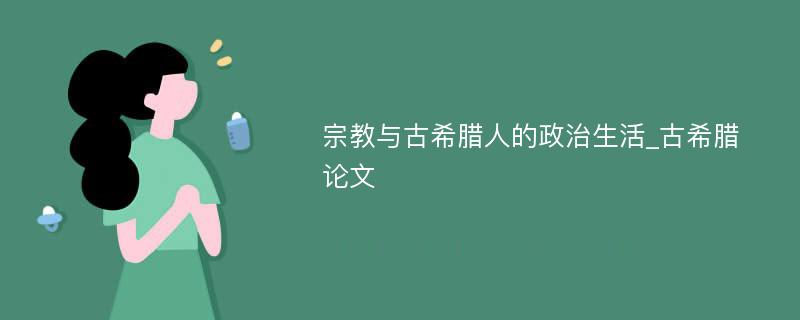
宗教与古希腊人的政治生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腊人论文,政治生活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多神教为特征的宗教信仰是古代希腊人重要的精神支柱。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古代居民一样,希腊人头脑中充满着神圣的情感。宗教深植于古希腊社会的土壤之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古希腊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让-皮埃尔·韦尔南所说,古希腊宗教“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神圣”。[1](P272)国外学术界对于神话和古典宗教的系统研究开始于近代,卡尔·奥特弗雷德·穆勒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斯·缪勒为代表的“自然神话学派”,罗伯逊·史密斯、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简·艾伦·赫丽生和吉尔伯特·莫雷为代表的“神话仪式学派”,①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和让-皮埃尔·韦尔南为代表的“巴黎学派”,从不同的视角对古希腊的宗教和神话作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韦尔南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他独辟蹊径,从历史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希腊宗教与神话。其著作《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和论文集《神话与政治之间》,分析了宗教伦理和政治理性之间的联系。[2]此外,德国学者瓦尔特·伯克特对古希腊宗教的研究也十分引人关注,他注意发掘古希腊宗教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对仪式和神话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伯克特运用丰富的考古学、铭文和文献资料撰写的《屠戮者:古希腊祭祀仪式与神话的人类学》和《希腊宗教》等著作至今仍然是古希腊宗教研究最重要的参考书。[3,4]近年来,国内古典史学界在古希腊宗教和神话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② 本文拟在吸取国内外学术界有关神话学和古希腊宗教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神话和仪式两个方面,探讨古希腊宗教的政治功能,并对其在城邦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进行分析,以图更全面地认识古希腊的社会文化和当时人们的思维特征。
一
古希腊宗教是多神教,它有众多的神祇和不同的神系。它不存在一位至高无上、全知全能的神,每一位神各司其职,主要掌管一个领域。这种多神宗教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克里特和麦锡尼文明时期,生殖崇拜在远古希腊人的宗教生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蛇崇拜和地母神崇拜便是这一崇拜的具体表现。在黑暗时代民族迁徙和融合的过程中,古希腊人以自身信仰的神灵为主体,继承了克里特-麦锡尼宗教信仰的基本因素,并吸收和改造了古代埃及与西亚的神话传说,逐渐形成了一套多神信仰的宗教体系。到了黑暗时代的晚期,随着城邦的出现,经过荷马史诗和《神谱》的系统化表述,终于形成了奥林匹斯宗教这一在古希腊世界占正统地位的宗教。除此之外,古希腊民间还流行着某些具有神秘主义特征的宗教。奥林匹斯宗教崇拜12位主神,他们分别是神人之王宙斯、天后赫拉、海神波塞冬、智慧女神雅典娜、太阳神阿波罗、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爱神阿佛洛狄忒、战神阿瑞斯、农业女神德墨忒耳、火神赫淮斯托斯、灶神赫斯提亚和神使赫尔墨斯。在古希腊人看来,他们是居住在希腊北部的奥林匹斯山上的“神圣家族”。
古希腊宗教是一种复杂的象征结构,它通过神话、祭祀仪式和形象化等形式而得以表现。韦尔南指出:“神话、祭祀仪式、转义的表象,这是三种表达模式——口头的、行为的和想象的——通过这些模式,希腊的宗教经验表现出来。”[5](P22)古希腊神话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开天辟地、人类文明起源、神和英雄的故事等种种传说。在古希腊城邦社会背景下,神话作为一种自觉的语言艺术形式有其独特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含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自古流传下来的神话不断被改造、加工和重塑,以满足社会和政治的现实需要。在此,我们将以雅典人在古风时代晚期和古典时代对古传神话的改造和建构为例,从以下三个方面说明古希腊神话对希腊人政治生活的影响以及它和城邦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
首先,古希腊神话创造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增强了民族和城邦的凝聚力。在这一点上,雅典土生神话具有典型意义。古希腊神话称:因为需要武器,雅典娜去找火神和锻冶之神赫淮斯托斯。赫淮斯托斯刚被爱神阿佛洛狄忒拒绝,于是就爱上了雅典娜,企图强奸她。在他发起了进攻之后,她跑开了。尽管赫淮斯托斯是瘸子,但他还是设法追上了雅典娜。由于她的反抗,赫淮斯托斯的强奸企图没有成功,但是他把精液射在了雅典娜的腿上。她厌恶地把精液擦到地上,但当精液接触地面时,该亚(地母)就受孕了,不久之后,一个孩子从地里生出,他就是后来成为雅典国王的厄里克托尼俄斯。雅典娜把他放在有盖的箱子中交给国王刻克洛普斯的三个女儿看管,并禁止她们开箱观看,因为这孩子身上缠着一条蛇。其中两个女孩违反了禁令,发疯后跳崖自杀。此后,雅典娜就把厄里克托尼俄斯带到她所在的卫城神庙里自己抚养。该神话把这位英雄塑造成了地母该亚的儿子。事实上,厄里克托尼俄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与土地极有关系”。[6][7](P225~227)这样一来,雅典人就成了土生土长的民族,成了神祇赫淮斯托斯和该亚的儿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雅典娜的孩子。土生神话把雅典人建构为一个想像中的平等共同体,大大增强了他们作为阿提卡土著居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其次,古希腊神话被城邦政治家所利用和改造,成为他们进行政治宣传的工具。雅典人编造的“政治神话”有很多,其中有关英雄提修斯的传奇故事最有代表性。
据说,提修斯是雅典国王埃勾斯的儿子。在古希腊神话中,他最初的形象是铲除妖怪的勇士和始乱终弃的负心汉。他得到克里特公主阿里阿德涅的帮助,杀死了居住在迷宫里的怪物米诺牛。在把阿里阿德涅带走后,又把她遗弃在那克索斯岛。此外,提修斯还和珀里托俄斯一起劫走了海伦。大约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雅典政治家开始了对古传的提修斯神话的改造和创新工作,一些诗人、剧作家和艺术家也参与了这一过程。在梭伦时代,提修斯可能就已经受到雅典人的尊崇。庇西特拉图为了给自己的僭主统治寻求支持,不但加强了对城邦宗教祭祀仪式的掌控,鼓励对城邦保护神雅典娜的崇拜,设立了崇拜酒神的狄奥尼索斯节;而且在塑造提修斯的民族英雄形象上也作出了很大努力。他去掉了赫西俄德的诗歌中“对于帕诺皮欧斯的女儿艾高的可怕激情折磨着提修斯”这句有悖于提修斯英雄形象的叙述,在荷马的《奥德赛》第十一章对地下世界的描述中,插入了“提修斯和庇里托俄斯,神的光辉的儿子”这样的诗句,还鼓励人们创作关于提修斯的诗歌。[8](P163)按照普鲁塔克的说法,西蒙主导雅典政坛时,根据神谕在斯库罗斯岛找到了提修斯的遗骨,接回雅典隆重安葬,并以该岛国王吕科墨德斯杀害了提修斯为由攻占了那里。[9]通过这一行动,西蒙不但为雅典的侵略行为找到了合适的借口,而且也提高了自己的声望。上述事例表明,随着雅典城邦社会的发展和自身实力的提高,雅典的统治者和政治家为了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逐步把提修斯塑造为雅典的民族英雄,其形象不断丰满完美,在政治宣传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王以欣所说,神话人物提修斯是时代需要的产物,是雅典国家和政治家们塑造的符合时代精神的政治和社会样板。[10](P468)蒂勒尔和布朗也指出:“像所有历史时期和所有文化中许多其他人一样,雅典的领袖们也利用了神话的能指。神话的情节和人物早就准备好并被以新的意义填充。最著名的神话能指是提修斯,如同一系列政治家所解释的那样,他成了雅典民族特征的一个符号。”[8](P161)
再次,古希腊神话表达了传统的性别观念,维护着父权制社会的性别关系。在古希腊神话中,很多传说都涉及了两性的性别关系,其中有关雅典娜女神的两则神话生动地反映了在古希腊,尤其是在雅典父权制社会中男女两性的地位。第一则神话与女性的生育权利相关。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讲述的雅典娜从宙斯的头颅中出生的故事,[11](P886~926)剥夺了女性仅有的生育权。第二则神话关系到女性的政治权利。据说,在阿提卡的第一个国王刻克洛普斯统治时期,智慧女神雅典娜和海神波塞冬为取得这个地区的庇护权而发生了争执。国王在请教了德尔斐的神谕之后,根据传统习惯召集了由男女两性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进行表决,男人们投票赞成由波塞冬充任庇护神,而妇女们则支持雅典娜,由于妇女方面多了一票,所以雅典娜获得胜利。这个结局激起了波塞冬的愤怒,并驱使着男人们进行报复。从那以后,妇女们就失去了投票的权利,不再被称为雅典人,新生儿也不能取母亲的名字。[12](8,55)[13](18,9)神话是现实社会生活的镜子,也是其缔造者思想观念的产物。这两则神话不仅反映了以雅典妇女为代表的古希腊妇女在父权制社会中处于无权地位的现实,而且也为这种现实作出了神话学的解释,宣扬并维护了男尊女卑的传统性别观念。
二
祭祀仪式在古希腊宗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比信仰对民众更具有吸引力。法国古典史家潘特尔指出,人们常说,希腊宗教是一种“仪式性”的宗教。古希腊人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有节奏地受到各种仪式的控制,因此希腊公民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和每一个阶段都紧密地与宗教相联系。[14](P27~28)举行抚慰或者讨好鬼神的宗教祭祀仪式是城邦公民生活的重要内容。
古希腊人的宗教仪式包括祈愿、颂诗、占卜和献祭等形式,其中献祭在古希腊人的宗教仪式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形式包括血牲祭、奠酒祭以及其他的奉献。[15](P343~345)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色诺芬都在他们的著作中谈到了古代斯巴达人在战争期间的献祭活动。希罗多德在《历史》中介绍了斯巴达国王所享有的特权,指出,他们在战时有权随时对任何国家开战,而其他任何斯巴达人都不能加以阻止,违者会受到诅咒。在出征期间,他们可以随意把多少牲畜用作牺牲,并且有权把所有牺牲的皮和脊肉保留给自己。[12](Ⅵ,56)色诺芬在《斯巴达政制》一书中描述了国王带着军队出征时向神献祭的情景:
首先,在斯巴达,他向作为军队首领的宙斯及其与宙斯有关的神献祭。如果祭祀是吉利的,取火者就会从祭坛上取火并且走在所有人的前面来到边界上。一到达,国王就再次向宙斯和雅典娜献祭。唯有这些神表明他们赞成,国王才会越过边界。在最后的献祭中取的火此后会一直举在军队之前,并且不会熄灭。接下来献祭各种各样的牺牲品。每次国王献祭,都始于黎明前,因为他想第一个赢得神的喜爱。[16]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则对雅典军队远征西西里出发时进行奠酒祭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写:号声命令全体肃静,船员们按照习惯举行航行前的祈祷。全军将士在传令官的号令下从金银酒杯中倾酒奠祭。岸上的公民和其他赶来向远征军祝福的人也都参加祈祷。当唱完凯歌奠祭完毕的时候,军队起航。[17](Ⅵ,32)战争期间举行的献祭活动表达了古希腊人祈求神灵帮助他们在保卫城邦的战争中获胜的愿望,坚定了他们打败敌人的信心。
占卜是古希腊人经常举行的一种宗教仪式。古希腊人相信,神会以某种信号、前兆或者迹象的形式向人们透露其旨意。古希腊人的占卜方式多种多样,大体可以概括为人为占卜和自然占卜两种。人为占卜所依据的是对动物、植物、物体或者现象的外部特征和对于献祭牺牲的内脏进行的观察。自然占卜包括对梦的解释等形式。古希腊人在召开公民大会和出征打仗时都要进行占卜活动。法国著名古典学家库朗热(Festel de Coulanges,又译为古朗士)指出,雅典人在开会前必须先举行宗教仪式。祭司进行献祭后,用圣洗水撒出一个圆圈,公民就在圈里开会。在某人进行演讲前,有人在静默的人群中进行祈祷。然后还有鸟占,若空中出现凶象,大会立即散去。[18](P152)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在希波战争的普拉提亚战役中,斯巴达的士兵排列成行,每人各就各位。他们头戴草冠,艺人吹奏歌曲。处于队伍后边的国王杀牲献祭,脏腑若无吉兆,就得重复再占,如此进行二三次以至于四次。而在这段时间里,波斯骑兵已经驰近,用箭射死了无数的士兵。但斯巴达人仍然按兵不动,他们把盾放在地上,并不抵抗,静候神的命令。待出现吉兆,斯巴达的士兵才举盾挺剑进入战斗,竟大获全胜。[12](Ⅸ,61~62),[18](P154)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人对占卜所持的认真态度。
神谕也是一种自然占卜的形式。古希腊人希望祈求的神谕既包括私人事务,也涉及宗教和政治事务。[15](P347)在关系到城邦安危和每个公民利益的殖民建邦、政治纷争以及战争与和平等重大政治问题上,遍布希腊各地的神谕所对希腊人的决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所最负盛名,该神谕所中的女祭司皮提亚(Pythia),由于她们所扮演的与神联系的特殊角色,往往成了调停者和仲裁人。在祈求神谕的过程中,皮提亚坐在三足器上,吸着岩石裂缝冒出的瘴气,处于入迷状态,高声谵语,一旁的男祭司则把这些话语记录下来,作为阿波罗的旨意传达给请示神谕者。古希腊人在采取重要的政治、军事行动和殖民建邦之时,往往要到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所请示神谕。殖民城邦的建立者(oikist)在殖民之前,一般要到阿波罗神谕所请示神谕。在那里,他被授于宗教权力并得到关于殖民地点的启示。[19](P2)斯巴达人得到德尔斐神谕的支持,在利翁、阿尔息达和和达马刚三人的率领下建立了殖民地赫拉克里亚。[17](Ⅲ,92)深受干旱之苦的铁拉人,根据德尔斐的神谕,在利比亚建立了殖民地。[12](Ⅳ,151)德尔斐的神谕不仅支持了吕库古在斯巴达实行的政治改革活动,而且也为梭伦夺取萨拉米和当选雅典执政官助了一臂之力。[12](Ⅰ,65),[20]在德尔斐神谕的帮助下,斯巴达人帮助流亡的阿尔克麦昂家族推翻了雅典的僭主统治。[12](PⅤ,P63~66)据说,斯巴达人还根据德尔斐神谕的暗示,把爱利斯人提萨门奴斯吸收为斯巴达公民,负责卜筮事宜,帮助斯巴达人获得了5次战争的辉煌胜利。[12](Ⅸ,33~36)
古希腊人的祭祀仪式可分为公共性质的仪式和秘仪两种,前者与城邦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殖民等活动密切相关,凡是城邦公民均可参加;后者只有某些教派团体的成员才有资格参加,祭祀仪式在秘密的状态下举行。公餐是希腊城邦祭祀的主要仪式之一,古希腊人相信,城邦的命运与公餐的兴废有关。在举行这种仪式时,全体公民都集中起来,一起向城邦的保护神表示敬意。聚餐时,公民身穿祭服,头戴花冠,以讨神的欢心。斯巴达的公餐制十分著名,该城邦的公民举行两次公餐。在雅典,人们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参加公餐的人员。对不肯承担这种职务者,法律将予以严罚。[18](P145~146)
在古希腊人的公共祭祀仪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丰富多彩的宗教节庆活动。为了向提供各种保佑的众神表示敬意,古希腊各城邦产生了许多宗教节日。古希腊史专家卡特利得奇说,公元前5至4世纪,雅典每年的宗教节日不少于120天,并可能多达144天。[21](P99)在雅典,最吸引人的宗教节日是泛雅典娜节。这个节日是阿提卡地方纪念护城女神雅典娜·波利阿斯的庆典。节日每年举行,持续两天。从公元前566年起,每4年举行一次大泛雅典娜节,庆典至少持续4天。在这期间,人们进行火炬赛跑等各种竞技比赛,获胜者的奖品是装有圣橄榄油的泛雅典娜奖瓶。庆典最隆重的场面是泛雅典娜游行,在传说中的雅典娜诞辰祭月(Hekatombaion)28日举行。[22](P55~58),[23](P198~199)在这举城同庆的欢乐时刻,年高德劭的老人拿着橄榄树枝,正当壮年的男性牵着献祭的牲口,意气风发的年轻男子骑在马上,美丽的少女挎着篮子。[24](P105)游行者将雅典妇女织好的法衣系在带轮子的圣船的桅杆上,从雅典的制陶区出发,经过市中心,最后送到雅典卫城,穿到雅典娜的木雕像上。在斯巴达,人们庆祝吉姆诺佩第(gymnopaidiai)节,在节日期间,人们唱着歌向阿波罗表示敬意,这个节日也具有纪念斯巴达人在公元前546年战胜阿尔哥斯人这一事件的意义。[25](P247)
除了公共的祭祀仪式之外,古代希腊人也举行一些秘密的祭祀仪式,其中最著名的仪式叫作厄琉西斯密仪。这个密仪是古希腊人纪念得墨忒耳和珀耳塞福涅(也叫科瑞)两位女神的节日,前者是丰产和农业女神,司谷物的成熟;后者是地狱的女统治者,司谷物生长和土地的丰收。古希腊神话称,科瑞被冥王哈得斯诱拐,成为他的妻子,得墨忒耳悲痛欲绝,离开奥林匹斯山四处寻找女儿,不久来到厄琉西斯,成为当地国王的乳母。得墨忒耳离开后,大地荒芜,宙斯无奈同意科瑞回到母亲身边。然而,在科瑞离开冥国之前吃了几颗石榴子(婚姻不断的象征物),这样一来,科瑞每年只能有2/3的时间跟着母亲,其余1/3时间则在冥界当冥后。得墨忒耳见到女儿后,重返奥林匹斯山,大地又重新结出果实。该仪式于每年秋天的鲍厄特龙翁庙月(Boedromion,公历9月至10月)在厄琉西斯的一座圣所里举行。节日开始于15日,约持续9天,最初几天的纪念活动在雅典举行。在该月的20日,入会者组成庞大的队伍向厄琉西斯进军;21日晚上他们进入圣所参加秘仪;22日献祭庆祝;23日回到家中。在密仪的表演中,地下世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其中一个情节是当地下世界的门被打开后,祭司宣布一个神的诞生,然后默默地向人们展示玉蜀黍穗。厄琉西斯密仪与科瑞从冥国回到母亲得墨忒耳身边、大地回春长出青苗的神话相一致,它象征着死亡后的再生。密仪除了给人们以再生的希望外,还给密仪参加者以在死后世界过幸福生活的许诺。厄琉西斯密仪因其秘密的特点而引人关注,泄露秘密的惩罚是死亡。[4](P286~288),[26](P342~356)当然,并非与该祭祀仪式有关的所有事情都属于秘密,该仪式的一些活动是公开的,厄琉西斯秘仪的游行、参加仪式者所唱的歌曲以及他们带的奉献和祭品,可以被人们看到和听到,场面十分壮观,只有在圣所中举行的秘仪才是秘密的。[22](P25)
古希腊各城邦在宗教节日期间举行的各种祭祀、娱乐、竞技和饮宴等活动,使古希腊人心中充满了对神的感激和作为城邦公民的自豪感,增强了城邦的团体凝聚力。日常生活中不断举行的宗教仪式不但表达了古希腊人期盼风调雨顺、多产丰收、幸福安康的愿望,坚定了他们战胜敌人的信心:而且也增强了城邦公民对于共同体的认同和归属感,密切了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三
为什么宗教会在古希腊人的政治生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首先,它是由古希腊城邦的特征决定的。古希腊城邦既是一个公民集体,也是一个排他性的宗教祭祀集团。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城邦本来是一种社会组织,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公民团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③ 维尔南认为,在古希腊的每一个城邦里,都有一种特殊的宗教组织。多神论体系紧密无间地错杂在各种水平层次上的社会政治组织的形式中:这种宗教,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政治宗教。在这整个阶段中,最基本的社会事实就是城邦的创建,而宗教则是这一重大现象的表达之一。[1](P229)他们的主张准确地表达了城邦作为公民集团和祭祀团体的特征。正因为古希腊城邦的这两个特征,这使得宗教介入了城邦的政治生活。
古希腊宗教在建构城邦公民身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参加祭祀、节日庆典等活动的资格是拥有公民权的重要标志。法国学者西萨和德蒂安在《古希腊众神的生活》一书中强调,希腊身份与生俱来,但公民身份是后天的。一级级、通过渐进的三个层次加入:被氏族承认,在德莫注册,在城邦里活动。[27](P186)古希腊的各级社会组织——家庭、氏族、胞族、部落、德莫和城邦都参与了公民确立其身份的过程。家庭是雅典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若干崇拜同一圣火、祭祀同一祖先的人所组成的团体。古希腊的婴儿约在出生的第五天时,被家人抱着围圣火跑数圈,见家中的女灶神赫斯提亚,[24](P92~93)便从家庭和家神处得到最初的身份。家庭与城邦的中间环节是氏族、胞族、部落和德莫,这些社会组织都具有宗教和接纳未来公民的功能。例如,伊奥尼亚人的各胞族每年都会在派安涅普西昂月(Pyanepsion)庆祝为期3天的阿帕图利亚(Apaturia)节,在节日的最后一天里,新的胞族成员会被登记在册,使他们将来有资格获得公民权,并为此而向神献祭品。[28](P118)德莫是古希腊社会的地域性组织。年满18岁的男性青年,在其父母所隶属的德莫内通过一定的入籍仪式便可取得公民权。德莫具有财政功能,并负责组织当地的祭祀仪式和节庆活动。[28](P440~447)城邦是希腊公民进行祭祀、公餐和节庆等公共活动的场所,各城邦都有自己的守护神、英雄和宗教节日。雅典人把雅典娜女神看作城邦的保护神,敬奉英雄提修斯,并举行纪念智慧女神雅典娜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等节日的庆典活动和涤罪等仪式。正是通过参加家庭、氏族、德莫和城邦等社会组织的宗教祭祀活动,希腊公民的身份逐渐获得认可。
在古希腊城邦中,举行宗教仪式是城邦公民共同的重要事务。城邦的各级社会组织都是宗教祭祀团体,家族、德莫、胞族、部落和城邦的首领同时也是祭祀的领袖。古希腊家庭中的父亲是家中圣火的大司祭,在家中举行各种祭祀活动时,他的职务最高,负责宰杀牺牲、口诵保佑全家的祷辞,家庭和家祭都因他而得以相传。[18](P76)城邦的首领同样负责全城邦的宗教祭祀活动。在雅典,主持全邦公祭是其官员的重要职责。执政官监督纪念医神阿斯克勒庇乌斯等节日的游行队,还管理狄奥尼索斯节和塔格里亚节的竞赛;王者执政官负责秘密祭和雷奈昂的狄奥尼索斯祭,并指挥祖先祭祀;军事执政官奉祀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和战神厄尼阿利乌斯,安排纪念战争死者的丧礼竞技,祭祀哈尔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革之灵。[29]城邦的政务既包括人的事务,也包括神的事务。例如,公元前594年,雅典执政官梭伦在改革时颁布的法令的内容大大超过了狭义的“政治”范畴,除了颁布政治、法律改革措施外,对祭祀仪式、祭品价格和日历等也作出了规定。[27](P195)由此可以看出,希腊宗教是维系古希腊社会组织内部团结的精神纽带。共同的宗教把古希腊的家族、氏族、胞族、部落、城邦和民族成员联系在一起,广泛流传的神话传说、反复的祭仪使他们产生了对共同体的认同和归属感,参加祭祀等活动是公民权的重要标志。
其次,它与古希腊人的传统思维特征密切相关。从古风时代后期起,随着古希腊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古希腊人发现了理性,并在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涌现出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欧几里得等杰出学者。他们力图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解释自然和社会,为后来数学理性、逻辑理性和实验理性在西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在当时,科学尚处于萌芽和起步阶段,希腊人并没有把神话与哲学、文学、历史截然分开。神话仍然是古希腊世界通行的话语,神话思维是当时人们普遍的思考与表达方式。包括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哲学家在内的广大希腊人都受到了敬畏神灵观念的深刻影响,在他们的思想中,信仰与理性难以分开地纠缠在一起。从当时希腊人对待死亡和瘟疫的态度,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古典史家詹姆斯·朗格瑞吉在其论文《古典时期雅典的死亡和传染病》中以丰富的史料证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与其在神话与英雄时代的前辈一样,几乎不采用任何医疗措施来阻止传染病的蔓延。当时绝大多数的雅典人都认为,是超自然因素导致了瘟疫的爆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瘟疫,最重要的事情都是清洗宗教性罪孽和抚慰神明,尤其是抚慰阿波罗。因此,虽然经过了理性精神的洗礼,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在如何对待传染病这个问题上,与神话和英雄时代的人没有明显的不同。[30]
从历史学领域来看,公元前5世纪,希腊出现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这两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们努力以理性和求真的精神来叙述人类的过去,奠定了西方历史学的基石,并分别开创了西方社会文化史传统和政治军事史传统的先河。然而,在进行历史叙述时,他们仍然难以完全摆脱传统的神话思维模式。被称为西方“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梦兆和神意,英国著名古典学家康福德在对希罗多德的《历史》和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两人对薛西斯入侵事件的描述都以相同的神学思路为基础,并涉及“罪恶的狂妄自大终会遭到嫉妒神灵的惩罚”这样一个神学理论。[31](P119)作为古希腊富有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历史著作中不乏严肃、理性的思考,极力避免受迷信的束缚;但是,他无法克服时代的局限,在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叙述中产生了把历史神话化的倾向。康福德对修昔底德作了深入研究,指出了传统的神话思维模式对他的影响,称其著作为“神话化的历史”。[31](P2)这一倾向明显地表现在他对一对同性恋人刺杀僭主希帕库斯事件的描述上。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雅典僭主希庇阿斯的弟弟希帕库斯爱上了美少年哈摩狄乌斯,向后者求爱,但遭到了拒绝。于是,希帕库斯和他的哥哥想了一个办法来报复哈摩狄乌斯。他们先是邀请哈摩狄乌斯的一个妹妹带着一个篮子来参加泛雅典娜节的游行。但当这个姑娘到达之后,他们又叫她回家,说她根本不配担当这个任务和参加游行。哈摩狄乌斯十分愤怒,便和自己的同性恋情人阿里斯托吉顿一起杀死了希帕库斯,并因此而成为雅典反僭主的英雄。[17](Ⅵ,56)康福德认为,修昔底德对刺杀僭主事件的描述是按照狄奥库里兄弟神和海伦的神话模式将传说非定形化,接着通过虚构,加入了莫须有的人物。[31](P116~118)此外,修昔底德对雅典占领派罗斯和对斯巴达国王波桑尼阿斯结局的叙述也反映了他对超自然的力量“命运”作用的相信。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宗教对古希腊人的政治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神话作为古希腊世界通行的话语,在城邦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被人们不断地改造和重塑,以满足政治现实的需要;它在增强民族和城邦社会的凝聚力、进行政治宣传和维护父权制社会的性别制度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祭祀仪式作为古希腊人广泛参与的宗教实践活动,参与了公民身份的建构过程,强化着人们对共同体的认同感,传承着城邦与民族的文化传统。宗教之所以处处渗透到古希腊人的政治生活中,是由城邦的公民和祭祀团体的特征以及当时人们的思维传统所决定的。
收稿日期:2010-12-20
注释:
① 关于神话仪式派的发展史和相关著作的情况可参见:Lowell Edmund,ed.,Approaches To Greek Myth,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0,pp.23-90.
② 王以欣的《神话与历史:古希腊英雄故事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商务印书馆,2006年)和吴晓群的《古代希腊仪式文化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是这方面研究的力作。同时,拙著《古希腊的妇女——文化视域中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的第六章对古希腊妇女与宗教问题进行了研究。
③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5b,1276b,1278b;译文见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13-129页。
标签:古希腊论文; 雅典娜论文; 雅典论文; 宗教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 神话论文; 神谕论文; 祭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