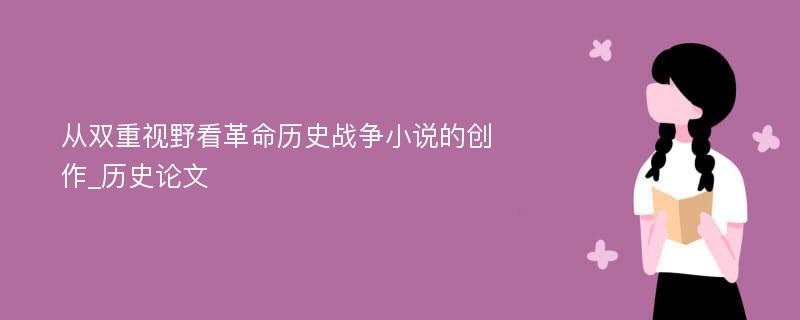
双重视阈下的革命历史战争小说创作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争论文,历史论文,小说论文,视阈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1)02-0053-06
革命历史战争作为文学叙事的对象,在解放区文学时期就已经出现。那时,“我们已经有了若干反映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与人民军队”[1](P513-515)的作品,周扬统计,“在《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所选的117篇作品中,表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人民军队的就有107篇”。“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作品叙述的是那一时期的‘当代生活’,也就是说‘现实’和‘历史’还并没有拉开距离,……但是随着战争年代的即将结束和新的时代的开始,当年关于革命斗争的现实叙述,就逐渐有了‘历史’的意味。”[2](P96)并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形成了一个创作高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作家在新的时代文化语境中“重写”革命历史,对信仰、理想、忠贞等精神的守护,为受市场化和消费主义影响而患上精神贫血和“软骨症”的文学增添了“血红素”和精神“钙片”。本文拟从历史观和英雄性两个理论视阈观照20世纪下半叶革命历史战争叙事,爬梳、总结其成就和不足,以期为革命历史战争小说创作的进一步繁荣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战争叙事,革命历史观起着支配和统摄作用。革命历史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由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而发展成型,并最终成为支配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叙事对革命历史认知的主导历史观。毛泽东的历史观主要表现为革命发展史观、阶级斗争史观、人民史观[3]。毛泽东的人民史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强调个人的历史创造作用的继承和发展。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高度肯定人民群众在中国革命历史的不同阶段,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4]。“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5](P139)肯定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历史作用,不仅体现出毛泽东的人民史观思想,而且也是毛泽东人民战争观的精髓所在。
在革命历史观的规约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战争叙事基本上是在革命历史观的视阈内展开的,因此,也就体现出一些共同性的内容。注重革命历史进程中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历史规律的总结;强化革命历史战争中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人民性);凸现革命历史战争中阶级斗争的二元对立和冲突……在此,仅以《保卫延安》、《红日》为例来说明革命历史观对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的统摄作用。这两部小说分别以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延安和山东解放区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叙事内容。在具体的历史叙事中,一方面通过敌/我双方的军事斗争,在敌我双方的正义/非正义、进步/反动、革命/反革命较量中,形象地阐释了前者终将战胜后者的历史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则在根据地人民对革命战争的支持叙事中,充分揭示出人民群众的作用和力量,艺术地表现了革命历史叙事的人民性特征。凡此等等,鲜明地体现出革命历史观对革命历史认知的规约作用。以革命历史观为指导的革命历史战争叙事,无疑真实再现了革命历史的主流走向,符合革命历史事实,它对革命历史本质规律的透视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其深刻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包孕主流意识形态意旨的革命历史观的强势地位和作用也导致革命历史叙事对非主流的革命历史的忽略,革命历史复杂性某种程度上被遮蔽。历史本色的弱化,历史必然性的充分性强化迫使历史偶然性因素缺席,这一切最终使革命历史叙事中的历史呈现出单质化的倾向。
就此一时期革命历史战争的英雄性表现而言,由于题材本身的特殊性,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强化其审美认知功能的政治教化内涵,使得开掘英雄形象的英雄性内涵成为此一时期革命历史叙事的主导审美价值追求,并在一体化的文学体制下,还建构出一套革命英雄主义的话语规范。
革命英雄主义话语规范主要体现在:一是要着重表现英雄形象的道德思想品格。“英雄人物的光辉灿烂的人格主要表现在对敌人及一切落后现象决不妥协,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那种高尚品质上,他之所以能打动千百万群众,成为他们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也就在于他所表现的那种先进阶级的道德的力量。”“至于一个人物如果具有和英雄性格绝不相容的政治品质、道德品质上的缺陷或污点,如虚伪、自私甚至对革命事业发生动摇等,那就根本不成其为英雄人物了,他还有什么价值值得人去称赞和歌颂呢?”[6]这样的论述里,英雄的人民性、阶级性、革命性无疑是英雄政治品质、道德品质的主要构成要素,而且它们还是英雄形象的灵魂,在英雄的诸多英雄性蕴涵上处于价值优先的地位,起着主导的决定性作用,甚至成为判定、区分英雄与非英雄的唯一标准。同时,又特别强调要表现“新时代的英雄”的“集体主义思想和高度的纪律性”[7]。二是体现在怎样写好英雄人物方面。要求作家“所凸现的东西,一定是属于最充分最充足地足以表现人物的社会本质的东西;他所舍弃的,一定是属于非本质的,和主题无关的不必要的东西”[8]。对于英雄形象塑造上如何处理英雄身上的缺点问题,周扬明确指出,“我们的作家为了突出表现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使他在作品中成为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这是可以的而且必要的”[6]。在这里,何谓缺点,何谓不重要的缺点,已无关紧要,最为关键的是要突出英雄人物高尚的政治、道德品质。
由于受革命英雄主义话语规范的规约,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战争小说创作中的英雄形象,其英雄性内涵大都表现为阶级性、革命性、人民性、集体主义精神和党性的内涵,而这些内涵成为构筑革命英雄最为重要的道德人格内容,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在血与火、生与死的激烈斗争冲突中,烛照出英雄们超凡的智慧和勇气(如《保卫延安》、《红日》、《红岩》等中的英雄形象)。但英雄作为个体的人,其人性因素或弱化或缺失,英雄最终成为高耸云端、不食人间烟火、通体散发着神性光辉的“玻璃人”。英雄形象因过分承担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而使形象的审美意义大打折扣,因此英雄人物大都成为“扁平型”人物。尽管也有一些作家在创作中比较注重英雄的人性因素表现(如《洼地上的战役》、《百合花》等),但数量的有限性,不足以改变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小说创作革命英雄话语的整体特征。
当历史前行至“新时期”,文学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变化共同推动革命历史叙事走向复苏、繁荣的历史进程。新时期的最初几年间,在风起云涌的“伤痕文学”主潮中,出现了《湘江一夜》、《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山菊花》、《澎湃的赤水河》、《霹雳》等反映革命历史战争的小说。这些小说创作或构思的时间大都是在“文革”后期,一方面受当时伤痕文学主潮的影响,其主题意蕴往往表现为缅怀革命先辈的英雄业绩,讴歌他们的英勇斗争精神。另一方面,革命历史观也给革命历史叙事以一定的制约。杨佩瑾在谈到《霹雳》创作时曾坦言到:“我在写《霹雳》时,正是粉碎‘四人帮’前后,当时,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完美’的理论还笼罩着整个文艺界。”“我常常感到遗憾的是,我是带着写秋收起义和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题材和主题的框框下去的,写作中努力创作使生活中活生生的形象改造得符合原先的某些概念。”[9]现实的因素和传统的影响,使新时期头几年的革命历史战争创作还基本停留在既往的创作水准上,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由政治/文化型向经济/市场型转型的步伐日益加快,这种转型最终在90年代所确立、实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战略目标中得以全面展开。一个多元社会文化形态共存的新的社会文化结构取代了过去单一的政治主导型社会文化结构。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支配、制约革命历史战争叙事的革命历史观因主流意识形态掌控力的削弱而弱化。尽管主流意识形态并没有彻底放弃对革命历史战争题材创作的规约,但其规约方式却发生了变化。“对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特别是涉及领袖人物的作品,一定要持严肃、慎重的态度,按照中央的规定办。如果不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不以中央和军委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基本结论为依据,是写不深、写不好的”,“强调这一点,不是说对‘走麦城’的东西,对历史上的失误和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不能触及,不能反映,关键是在创作过程中,要把现象和本质分清楚……即使写阴暗面,也要着眼于给人以启示,使人看到光明,增强信心”[10]。这段话固然体现出主流意识形态对革命历史战争题材创作进行规约的意旨,但它并非以过去那种粗暴的政治批评性方式干预创作,而是试图在学理的层面上以引导的方式强调作家要以革命历史观和战争观为指导进行创作。
如果说社会文化形态的多元性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要求以革命历史观看待和表现革命历史战争的规约作用,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关于历史的认知不仅构成对革命历史观的挑战,而且,也为作家提供了认知革命历史的新视角和新工具。新历史主义批评针对结构主义批评割断文本与历史连接的批评策略,强调文学批评的“历史诗学”特征,并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历史批评的新历史观。它对“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占优势的社会、政治、文化、心理以及其他符码进行破解、修正和削弱。因而,他们尤其表现出对历史记载中零碎插曲、轶闻轶事、偶然事件、异乎寻常的外来事物,卑微甚或简直不可思议的情形等许多方面的特别兴趣,历史的这些在‘创造性’的意义上(我不打算说是‘幻想的’或‘想象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诗学的’,因为它们对自己出现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支配和服从的结构,以及文化符码等规则、规律和原则表现出逃避、超脱、抵触、破坏和对立”[11](P106)。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强调历史的“话语”性特征和历史话语建构过程中的叙事性特质。海登·怀特认为:“历史话语所产生的东西是历史学家掌握的关于过去的任何信息和知识的阐释,这些阐释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从简单的编年史或事实的罗列一直到高度抽象的‘历史哲学’,但它们的共同性在于它们都把一种再现的叙事模式当做理解作为独特‘历史’现象的指涉物的根本,用克罗齐的一句名言来说,没有叙事,就没有独特的历史话语。”[12](P294)强调“通过情节编排进行解释”而建构历史话语,体现出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对历史建构中主体力量和作用的肯定,也是对传统历史观的彻底解构。上述的这些理论,也给中国作家对历史的认知以一定的影响。莫言在论及他的创作时曾言道:“我觉得写战争不必非要写真实的战争过程,那是拼战争史料。我根本不是写历史,只是把我自己的感情找个寄托的地方……干吗非要熟悉当时的环境?按你心目中的战争去写就行了。”[13]莫言表现抗战历史的审美追求,以及乔良在革命历史战争创作中,揭示历史所蕴涵的思想意蕴,为当代提供参考借鉴的创作意旨,都显现出西方现代历史哲学思想影响的印记,也体现出有别于传统革命历史观的新历史观倾向。传统革命历史观影响力的弱化和新历史观的出现,使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革命历史战争叙事比之既往的此类题材创作呈现出纵深开掘的特征。其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体现在革命历史叙事由历史本质、规律向历史原色的审美转变。所谓回到历史原色,就是对遮蔽历史认知的遮蔽物进行去蔽,从而抵达历史的深处,透视历史的复杂性蕴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革命历史观统摄作用的弱化,革命历史战争的叙事开始向革命历史原色叙事转变。例如对长征这一中国革命历史的重大事件的叙事。由于受革命历史观和体现主流意识形态意旨的历史教科书对长征历史阐释的影响,既往的此类题材创作鲜明地体现出,或凸现其历史意义和作用,或谱写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等审美特征。不可否认,对长征历史的这种表现与抒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体现出一定的历史理性精神。然而,长征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内蕴也被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强光所遮蔽,革命历史的残酷性、内部的冲突斗争和局部的失败在既往的长征历史叙事中缺席。随着革命历史观的破解,这些缺席的历史内容在长征革命历史的原色叙事中被一些作家加以大胆地表现与抒写。湘江之战,是长征历史的一次重大事件,也是红军的一次败仗,而“红军史只记下八个字:湘江一战,损失过半”(《灵旗》)。战败的历史事实和战争的惨烈在寥寥八个字的记述中被删除。但在乔良笔下的历史原色描绘中,湘江之战完全是一次溃败,是一次悲壮、惨烈的败仗。“红军败北……白军大开杀戒,狂犬般搜杀流散红军。砍头如砍柴。饮血如饮水。一时间蒋军杀红军,湘军杀红军,桂军杀红军,狐假虎威的民团杀红军,连一些普通百姓也杀红军。尸曝山野,血涨江流。”湘江之战的原色叙事弥补了正史所回避的历史内容。正史和教科书对长征的战略大转移的表述在《灵旗》的原色叙事中则成为另一种表述。“两个月后,中央红军将沿着他们走过的路线开始漫无目标的长征。”“他们在走,只是走,他们并不知道这是长征,这个史诗般的命名是后来的事。他们不知道往哪里去……他们也不知道到头的那个地方叫延安。”这种表述是符合长征历史的真实描述,体现出对长征历史进行原色叙事的特征。在《灵旗》中,革命内部的矛盾斗争也在“那汉子”做逃兵的原因中而得以展现。当年的青果老爹因党代表的引领和教导而参加红军。然而,“党代表死了,不是被敌人杀死的。是被自己人当做敌人活活打死的。他亲眼看见了他的死。很惨。说他是AB团,还说他是社会民主党”。“后来连折磨死党代表的那几个人也死了,罪名和党代表一样。这更叫人不明白那样一个笑眯眯、手臂上被敌人马刀砍下三处疤的人,怎么会一下子就成了敌人?而那些把他活活折腾死的人,怎么又成了他的同伙?不明白。外边被敌人杀。里边被自己杀,这样的队伍能成气候?他心冷了。”在青果老爹脱离红军队伍的原因叙事中革命内部斗争的历史敞开了。对长征革命历史的内部斗争冲突,20世纪90年代的长征题材创作中也给予一定的表现与抒写。赵琪的《苍茫组歌》和邓一光的《走出西草地》都不同程度地涉及长征革命历史中红军内部非常残酷的斗争——揪AB团的历史事件。
其次,表现为对革命历史叙事的解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由于受新历史主义、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少数非军内作家的革命历史战争创作体现出解构革命历史战争的叙事特征。这种解构特征主要表现为置换革命历史内容,消解革命历史的意义,质疑历史必然律,凸现历史偶然性因素的作用。既往的革命历史战争叙事,由于受革命历史观的阶级价值论的支配,在革命者投身革命的历史因素表现上,形成一种模式化的叙事,基本上都表现为,或出于阶级压迫,或是受到革命引路人的教育、指引,或是革命家庭的熏陶(如少剑波、杨子荣、林道静等),这实际是革命历史观的阶级价值论规约的结果。这种表现模式也体现出革命历史的历史必然性特质。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革命历史战争叙事,解构了这种历史必然性。“那汉子”(《灵旗》)因为到苏区贩盐时恰逢“扩红”,而且对“笑眯眯”的党代表有好感因而参加红军。“父亲”(《父亲是个兵》)造反,参加革命的最初原因在邓一光的笔下竟然是因为不满地主的一碗不熟的红烧肉。梁大牙(《历史的天空》)原本是要到蓼城投奔刘英汉的“国军”,但途中错过撤退的国军队伍,当遇到凹凸山抗日游击队时,在是否参加游击队问题上犹豫不决的时刻,看到了东方闻樱和另一个女战士:“冲着他笑得尤其灿烂,心头顿时一热,一句话便冲口而出:‘那好,他娘的这个八路就咱当上了。’”就这样他参加了革命队伍。这些投身革命的偶然性因素叙事,非常明显是对既往出于阶级对立的革命必然性的消解,也是对既往创作所叙述的革命必然性的超越。
革命历史战争小说创作,就其英雄的英雄性开掘与表现而论,比之既往的创作,体现出纵深开掘的特征。其表现为:一是从文化层面烛照与表现英雄的英雄性和人性内涵;二是开掘英雄身上世俗性因素。1985年,莫言的《红高粱》问世,《红高粱》的文学意义不仅体现在超越革命历史话语的规约,开掘了民间抗日的新题材,更是在文化的层面上,烛照、挖掘英雄的英雄性和人性内涵。在《红高粱》中,莫言以极富浪漫主义的笔调,刻画了余占鳌这一蕴涵着中华民族“民魂”的民间英雄形象。面对外敌入侵,余占鳌在直觉的抗暴本能和朴素的民族爱国意识的引领下,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和不怕牺牲的精神,驰骋抗日疆场,成为不屈服于异族淫威的抗日民族英雄。与此同时,莫言还在他与戴凤莲的爱情叙事中,揭示出余占鳌蔑视封建道德的礼规,张扬生命热力,豪饮生命琼浆的自由意识。“正是建立在民间崇尚生命力与自由状态的价值取向上,作者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写‘我爷爷’和‘我奶奶’的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与行为,才能那样自然地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的美。”[14](P483-484)此外,莫言又通过杀死“花脖子”、处理其族叔余大牙奸污民女曹玲子事件和“独头蒜”等情节,透视表现余占鳌与封建宗法道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一面。诚如有的论者所言:“他的民族意识、自由意识、复仇意识可以使他成为狂放不羁、敢作敢为、众心诚服、驰骋疆场的抗日英雄;但这一切的后面,他又是个恪守宗法观念、王权思想,热衷于传宗接代、血缘纽带的庸人……余占鳌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民魂!”[15]
如果说《红高粱》是从一个宽泛的传统文化视阈去烛照、透视英雄的英雄性和人性,那么项小米的长篇小说《英雄无语》则是从亚文化——客家文化的视角,透视、表现“我爷爷”的英雄性格及其与中国客家文化传统精神的渊薮。同时,又历史地真实地表现“我爷爷”身上背离正常人性的反人性内涵,两重蕴涵的交织,建构出一个既往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不曾有过的“紫色”的英雄形象。“作品之于‘我爷爷’的刻画,几乎是时而朦胧,时而清澈,或时而与凡人没有什么两样,时而又显现出人生经历的惊心动魄、离奇曲折,但其中的忠诚、勇猛、无私、顽强,却可以视为他英雄主义精神中的最具原色特点的基本性格。”[16]作家以生动、传神的情节和细节描写,描绘了爷爷身上所彰显的英雄主义精神的原色特点。在毕节,爷爷获取了国军围剿苏区的详细作战计划,乔装打扮,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九死一生,把情报送到苏区,使红军及时调整战略部署,挫败了国民党的铁壁合围计划,跳出包围圈,免遭灭顶之灾。正是爷爷的忠诚、勇敢、机智,挽救了党和红军。到南昌后,爷爷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凭其忠诚、机智和勇敢,再一次获取敌人破坏上海党组织的情报而保全了上海党组织,并伺机逃跑,回到延安。与此同时,作家还以“复调”式的笔法,叙述了我破解具有史诗意味,反映客家人历史文化的《迁徙诗》,并从中析理出客家人的文化精神传统——勇猛、顽强、机智等精神因子。这一叙事与爷爷一生的曲折惊险经历叙事构成“对位”叙事,从而为爷爷的英雄性格提供了历史文化的依据,也进一步诠释了客家文化精神传统与爷爷身上英雄性的历史文化渊薮。项小米在谈到自己为何在文本中表现客家文化时,曾言到:“我自己感到那是我小说里很重要的一块,也是我力气用的最大的一块。”“我之所以使用这一块,那是因为小说的主人公‘爷爷’‘奶奶’必须要有一个文化依托。”而且“小说中的‘爷爷’之所以这样对待事业和女人,无不是客家文化在他身上的投影”[17](P298-299)。无论是作家和评论家,在这里都触及了英雄与文化的关系问题。
《英雄无语》在聚焦爷爷的英雄性的同时,也挖掘了他身上的背离正常人性的反人性因素。爷爷的英雄性格和反人性的性格特征,共同建构出一个不同于红色英雄的“紫色”英雄形象,比之被提纯、净化的红色英雄形象,这一英雄形象承载着更多的历史文化蕴涵,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审美意蕴。
所谓世俗性,就是对人的世俗情趣的形而上的概括和总结。它肯定人的肉体生命价值,尊重个体生命的自然欲求,提倡“珍爱自我,美化生活,追求纯感性的陶醉和愉悦”[18](P36)。世俗性是世界范围内世俗化文化思潮的必然衍生物。“在西方,‘世俗化’是与‘宗教化’相对立的一个词。西方文化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以来的一部现代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性不断挣脱宗教束缚的历史。而在中国,‘世俗化’则是与‘政治化’相对立的一个词。至少从明清之际的人性复苏到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再到‘文革’结束后新时期的个性解放,90年代的商业化大潮,‘世俗化’的声音一直都与反对封建主义‘理学’、批判僵化的‘礼’、远离‘斗私批修’的政治梦想这些文化目标相联系在一起。”[19]就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而言,受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西方文学思潮、尤其是90年代潮起云涌的商品大潮的影响,文学创作中的世俗化倾向由80年代初的潜在状态转至为90年代的显在状态。
在20世纪90年代的革命历史战争叙事中,一些作家因其创作的英雄形象的世俗化倾向,才真正实现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战争创作英雄性开掘与表现的超越。在《狼毒花》中,权延赤塑造了一个最具世俗情趣的英雄形象——常发。作家以传记体的叙述手法,于常发极具传奇性的战斗生活和日常生活叙事中,挖掘他身上所具有的英雄性质素和世俗性因素,建构出一个英雄性和世俗性相互渗透、杂糅的英雄形象。一方面,作家充分地透视、表现了常发身上的英雄性品格:超乎寻常的非凡技艺;百步穿杨的精准枪法和骑马如飞、能使马面壁人立的精湛马术;作战勇敢、富于智谋;对革命无限忠诚等。另一方面,作家又充分地表现了常发世俗性的一面。他总是离不开美酒和女人。为了这两样东西,他不惜以地位、官职为代价,甚至违反军纪。他嗜酒如命,或痛饮、或豪饮、或狂饮,活脱脱一个再世的刘伶。文本中有这么一个情节,最典型地说明了常发嗜酒如命,对其难舍难割的眷恋之情。他曾被叛匪在囚笼中关押七天七夜,溃烂的伤口长出蛆虫。当他被成功解救后,闻到旁边一个大酒缸里散发的浓郁酒香味,便不顾一切地爬进去,猛灌狂饮,无暇顾及酒缸中漂浮的蛆虫,并不时发出酣畅淋漓、充满快意的大笑声。除却美酒,常发每到一处,总是要制造一些风花雪月的故事。在部队驻地,他强暴房东的女儿,几近被枪毙,但这并没有使他喜好女色的行为有所收敛。在东北,又一次不顾部队的纪律约束,和苏军的女军官喝酒、调情,乃至发生关系。酒和女人,对任何一个男人来说,都具有一定的诱惑力,它们也是男人世俗人性欲望满足的对象。然而,对特定战争环境中的军人而言,它们往往是军规军纪所约束的对象,更何况是在此问题上表现出放纵的态度和行为。作家正是借常发与酒和女性关系的叙事,表现、刻画了这个视军纪法规为一纸空文,超越道德律令,挥洒个体生命热力,张扬生命主体的自然本性,遵从自我生命意志,体现出世俗性色彩而又不乏英雄性品格的英雄形象。表现英雄的世俗性因素,在20世纪90年代的其他革命历史战争叙事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如在《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和《亮剑》中的李云龙身上,作家都比较注重对他们人性欲望的捕捉与表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战争叙事,在英雄形象的塑造上,也有些许英雄世俗性的表现与透视,但是,受革命英雄主义话语的规约,作家或没有充分展开叙事,或融入革命性的内涵,因而使得革命英雄形象呈现出净化的色彩——红色英雄,造成英雄形象的审美蕴涵复杂性的流失。“事实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审美领域中世俗幸福的关注,其最终目的在于防止世俗幸福的描写模糊人物的阶级特征。毕竟,必须充分照顾到个体意识的爱情需求潜藏着削弱革命者阶级意识的可能。”[20](P83)但是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在整个社会转型中,多元文化语境的出现,尤其是社会文化中世俗化倾向的日益强劲,更是为英雄主义叙事的世俗性提供了合理的文化依据和基础[21]。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革命历史战争叙事的英雄世俗性开掘与表现上,并没有像其他题材的创作那样,表现出鄙俗化的恶俗倾向,这固然与革命历史战争题材的特殊性——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有着一定的关联,但是,也不可否认,军旅作家特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避免鄙俗化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
标签: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战争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文学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艺术论文; 人性论文; 红高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