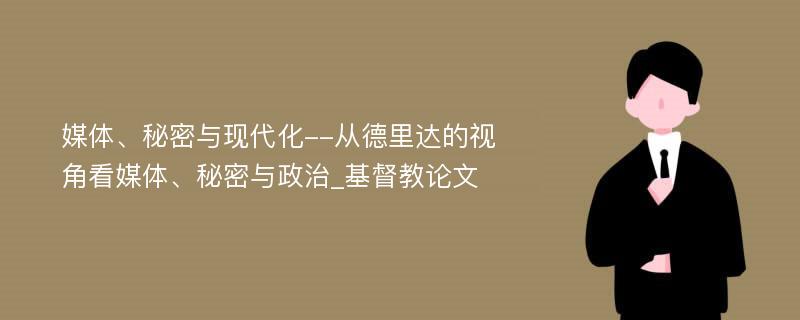
媒体、秘密与现代性——从德里达的视角思考媒体、秘密与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秘密论文,媒体论文,现代性论文,视角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7-0005-09
媒体既是现代性的产物,又是现代性的工具,也是现代性的瓦解者。媒体,尤其是互动性媒体,正使全球化成为真正的现实。它体现并推动资本、技术与权力的空前结合,也实现了所有互联网用户的大脑联网;它在全球传播宗教,但也日益把自身变为宗教;它大大扩大了公民参与,从而改变了全球政治生态。德里达甚至在20年前就谈论网络民主的可能性。然而,他注意到,就像民主与无赖是一对孪生兄弟一样,网络民主与网络暴力总是相依相伴。如果说当今社会正在通过这种网络民主和网络暴力形成某种社会免疫机制,那么,网络空间的形成在打破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限方面所起的作用将影响深远。德里达曾对宗教、电视(或者说一般意义上的媒体)与全球化的关系做过一些有趣分析,他在“9·11”事件发生以后于纽约发表了题为“自身免疫性:真正的自杀与象征性的自杀”(Autoimmunity:Real and Symbolic Suicides——a Conversation with Jacques Derrida)的谈话,以及《尤其不要记者们》(Surtout pas de journalists)一文。早在1995年他就出版过《档案热》(Mal d'archive,亦可翻译成“档案病”或“档案狂”)。2003年,他写的一本小书《生成、系谱学、类与特性》(Géneses,généalogies,Genres et le génie)问世。这些文本与《对秘密的喜好》(A Taste for the Secret)、《信仰与知识》(Faith and Knowledge)等著作一起构成了他对媒体、秘密、宗教、政治和全球拉丁化等问题的相对完整的论述。如果我们从他的视角去审视一下媒体与秘密的关系,审视一下媒体、现代性与“全球拉丁化”(globalatinization)的关系,我们对当今政治生活的理解将会获得新的灵感。我希望,我的解读能让德里达的文本呈现出不同的意义,而这恰恰是解构的要义之一。
德里达曾用过“媒体的宗教”一词,如果我没有误解他的意思,他是要凸显和说明人们对媒体的崇拜,强调媒体如何影响宗教以及宗教如何借助媒体而变得全球化,确切地说,他要说明宗教、全球化与媒体化有何内在联系。他提醒我们要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一进程。从“媒体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Media)这个字眼中可以引出两种影响深远的观念:第一,它让人想到媒体正在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宗教”;第二,它让人想到正在媒体上传播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因为后者正借助媒体的力量传播到全世界并深深影响乃至支配了现代国际政治和国际法体系的基本话语。
就第一点而言,我们每个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它的见证者。德里达在《尤其不要记者们》一文中沿袭了黑格尔的提法将基督教称为“精神的宗教”。他把伊斯兰教、犹太教和佛教称为秘密的宗教,因为这三种宗教在他看来十分强调个人的内心体验,特别是神圣的体验。
他把基督教称为言说的宗教、公开的宗教并认为基督教内在地包含着对公开化和媒体化的要求,因为他认为基督教希望传播“好消息”,希望将福音传遍全世界。因此,基督教在现代媒体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传播手段。对他来说,基督教在近代之前常常站在科学的对立面,而在近代以来它试图维持对科学的最终统治,并且当科学有可能威胁其最终信条时它会对科学予以限制。基于宗教理由对生命科学技术的限制就是如此。启蒙运动以后它又试图借科学来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但它与科学的和解中也包含对科学的反对。当它试图依靠现代媒体,如电视、互联网和广播,来传播自身的信条和教义时,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用科学的方式反对科学,用技术的方式反对技术。不仅如此,基督教在他眼里越来越依赖现代技术武装起来的媒体来实现自身的全球化。他正确地指出了当今的所有宗教都有媒体化现象,但基督教的媒体化的结构和力量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它比任何其他宗教更有普遍化的要求、公开化的要求,这自然与其排他性的要求有关,也与其世界主义的概念和世界公民的概念有关。德里达认为,媒体化是普遍化和公开化的体现和强有力的手段,但他对基督教的媒体化始终保持某种警惕,这首先是因为他一辈子都在捍卫差异,捍卫作为差异的基础的每一事物的独特性,而普遍化的企图和普遍主义的尝试都是对独特性的威胁。现代媒体固然满足了人们对于交流和沟通的需要,并且深深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也改变了世界的性质,但它也在创造公共空间的同时使世界变得同质化,人的个体性和独特性,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正在遭受侵蚀,甚至正在消失。
我这里想特别谈谈当代人对媒体的严重依赖,这种依赖在德里达看来恰恰与基督教的全球化的使命是合拍的。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何基督教比其他任何宗教更热衷于利用媒体的力量来扩大自身的影响。法国学者阿克瑟罗(Axelos)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说过,谁控制着媒体,谁就控制着民众的意志。今天,市场化的力量正将每个人卷入媒体之中,受媒体的影响乃至左右。今天的商人、政治家、演员一旦脱离了媒体,人们就会产生各种猜测。他们对媒体的依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致有人即便生病了也要强打精神在媒体上露面或发声,因为脱离了媒体,他们就无法充分显示其存在和价值,而显示自身仿佛代表了他们对于公众的意义,表明了他们的影响力。即便被美国四处追杀的恐怖分子也不忘记时不时地借助媒体显示自身的存在。实质上,媒体不但为一些人“报价”和“保价”,而且借此证明媒体自身的力量和有效性。媒体与公众人物相互需要。这里的公众人物首先是指政治人物,其次指商人、艺人和公共知识分子。由于媒体的日益商业化,媒体尤其与商人相互需要。对于商人来说,媒体是叫卖的最好平台,也是培养消费者的平台;对于政治家来说,媒体既是显示其存在的手段,又是发挥其影响力的手段;对于演员和其他公众人物来说,媒体与公众对他们的关切度密切相关。但不管是上述哪种人物,对媒体的依赖和恐惧是同时并存的。随着互动式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发展,普通公众与媒体也在加深相互依赖性。德里达甚至早就提到网络民主的可能性。在《无赖》一书中,德里达还发现,随着网络而出现的所谓的全球化或世界化“比以往更不平等和更具暴力,因而比以往更多地被人引用并更少具有世界性”①。
基于此,我们在享受媒体的好处时,当然不应当忘记对媒体保持批判性立场,而后一点恰恰是媒体的本性。我们可能像德里达一样注意到,媒体是世界的眼睛。媒体不仅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便捷,而且使我们的社会公众也能享有曾经被少数人垄断的信息,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使无数个大脑同时接受知识并进行合作型创造成为可能。今天的媒体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表达普通人的要求与呼声,更能体现普通人的集体智慧,更能对各种权贵发挥监督作用。随着互动式媒体的出现,交流和分享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富有魅力的潮流。然而,我们也可能注意到,正是通过不断的重复,媒体往往使一件小事迅速成为一次重大事件。我们虽然不能说“9·11”事件是一件小事,但可以确认这次事件是通过电视图像的反复播放而成为主要事件的。另外,现代网络媒体使一些公众同时患有“偷窥癖”和“暴露癖”。人们热衷于观看和打探别人的秘密,也热衷于晒出自己的秘密。在这种情况下,“隐身”和“匿名”才有意义并成为控制和反控制的战场。就连各国的情报人员也加入了媒体的合唱。他们不仅到各种互动媒体上去“捞取”秘密,而且忙于防止自己的秘密被泄露。然而,捞取秘密本身就是泄露自己的秘密。因此,在这样一个贩卖和“泛卖”的时代,在马尔库塞所说的媒体正深入到个人卧室的时代,个人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就在情理之中了。在《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中,马尔库塞把通过舆论而进行的私人聚会和媒体向个人卧室开放看作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主要倾向之一。②
就第二点而言,德里达对于媒体与宗教全球化的关系的看法比较独特。德里达自造了一个词“全球拉丁化”(globalatinization)。这里所说的拉丁化自然不是指大家都来说已经死去了的拉丁文,也不是指大家都无保留地接受拉丁人的思维方式和所有文化观念。按德里达的见解,全球拉丁化的一个明显表现就是“宗教”的全球化,确切地说是基督教的全球化。“宗教”一词是拉丁人的发明,是罗马人的发明并且仅仅属于罗马人。当人们试图将罗马人的独特经验普遍化的时候,那种将以拉丁文来表述的观念灌输到其他人的心灵中意味着通过某种外在力量进行强制性的推广。基督教一直是这种推广的有力手段。通过对“宗教”的解构,德里达不仅发现了“宗教”的媒体化和普遍化的过程在本质上的一致性,而且揭示了“宗教在本质上和语源上是基督教的”。他对不能或不愿给独特性和个人秘密留下空间的任何宗教思维感到恐惧。也正因如此,他对基督教通过媒体而进行的全球化过程表示忧虑和不满,而对他称之为“秘密的宗教”的伊斯兰教、犹太教和佛教则怀有某种同情。
德里达在《信仰与知识》里对“宗教”一词进行过一番考察。在他看来,“宗教”(religion)一词的含义看似清楚,实则非常模糊。正因如此,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是以宗教的名义发生的。实质上,“宗教”这个词只是拉丁人的发明,“宗教”也仅仅属于拉丁人。其他民族没有“宗教”一词或类似的东西并不是什么坏事,而可能恰恰是好事。因为“这个普遍化的名词包含一种同一性的幻觉,它也是某种抽象经验的结果,是忽视具体内容和具体差异的抽象化思考的结果。语言、民族、罪恶、拯救、牺牲、正义、屠杀、性别等等方面的问题莫不与这个抽象的名称相联系”③。可是,所有运用“宗教”一词的人从未就“什么是宗教”达成一致,法国语义学家邦维尼斯特(Benveniste)甚至考证出religion(宗教)一词在拉丁文里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起源。在拉丁文中,“宗教”被称为religio。西塞罗、奥拓(W.Otto)和霍夫曼(J.B.Hofmann)等人认为,这个词源于religere,其词根是“收获”和“聚集”的意思;而以德尔图良、柯伯特(Kobbert)、埃尔努-梅耶(Ernout-Meillet)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则认为,religio源于religar,其词根的意思是“联结”和“联系”。④
然而,不管一些语源学家如何强调“宗教”一词的原始意义的重要差异,我们毕竟看到不同教派的人、具有不同信仰系统的人渐渐认可人类有某种类似的神圣经验并试图用统一的名称去称呼它们。此外,“宗教”一词的两个不同起源并不能说明它们没有联系,因为上面提到的“宗教”一词的一种原始意义,即“收获”和“聚集”与它的另一种意义“联结”和“联系”并非没有联系。常识也告诉我们,聚集本质上已经就是联结了。但德里达据此论证说,把原本不统一的经验说成是统一的经验并用一个貌似大家认同的名称去称呼那种经验无异于语言暴力。进而言之,“宗教”是独特的经验普遍化的结果,它本身带有强制的性质。而现代媒体把这种强制发挥到了极致,也把普遍化的要求发展到了极致。或者说,现代媒体事实上是全球拉丁化的普遍工具。这种工具既可以为全球拉丁化服务,也可以为非拉丁化服务,甚至可以用于反拉丁化本身。这就是现代媒体的双重特性。看不到这种特性就看不到媒体与全球拉丁化的内在联系,也看不到现代媒体具有自我否定的能力。这种能力的确可以在短期促进宗教的全球化,但最终也蕴含瓦解自身的可能性。
因此,我的基本看法是,媒体传播了“宗教”,也瓦解了“宗教”。从表面上看,“宗教”借媒体的力量而传遍全球,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全球化的动力之一。然而,媒体也丢失了宗教的灵魂。这不仅仅是因为媒体使宗教所依赖的秘密不再是秘密,而且是因为媒体使人们分散了人们分享共同精神空间的兴趣和对秘密的兴趣。这就是说,媒体在本质上是与宗教经验相互冲突的,因为媒体是以公开性为存在条件的,它的功能和职责就是揭示、显示、公开。虽然德里达和纳斯先生注意到基督教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将好消息或福音传播开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因而意味着将其公开化和媒体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是,借言说和形象而存在的媒体并不能通过公开化的功能保证媒体上的基督教的精神的可靠性、完整性和有效性。相反,媒体上的形象几乎总是污染、扭曲和侵蚀那种宗教精神。媒体传播的只是宗教知识,而非宗教经验。
众所周知,“电视”一词television在字面上意味着“远看”,但通过“远看”来传播的宗教在我看来事实上恰恰瓦解了自身。德里达没有提到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几乎所有宗教都离不开仪式,而仪式始终意味着在场,意味着某种秘密。远看的仪式是无法让我们找到身临其境的感觉的。只有在参与仪式时我们才可能有对于仪式的神圣经验。况且,仪式让我们以五官和心灵体会神圣的经验。媒体上传播的宗教只是传播了某种信息,它无法有效运用人的五官,它充其量只能运用人的视觉和听觉。信仰不仅是借助声音和形象来确立的,信仰需要全身心的体验、领悟乃至迷醉。声音和形象无疑是宗教精神传播的重要载体,但媒体上传播的宗教声音和形象受到了污染,它们与其他声音和形象的混杂干扰了人心的宁静,给灵魂带来了纷扰,因此媒体实质上会消耗和侵蚀宗教精神。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一部分宗教界人士希望远离电视和其他媒体,至少不愿受它们的过多干扰。
另外,我们也不应忘记一个重要事实,现代性是与基督教的世俗化过程息息相关的,也是与启蒙运动所宣扬的普遍主义的理念密切相关的。西方启蒙运动虽然在18世纪的一些法国思想家那里表现为对基督教的批评,但这种批评并不彻底,并且批评的结果是基督教的世俗化。现代性的一个后果是政治与神权的分离,另一个后果是资本、技术与权力的合流。就长远影响而言,第二个后果是现代性最为根本的方面,也是影响现代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根本因素。即便第一个后果在将来消失了(在短期内还看不到这种可能性),第二个后果仍将维持强有力的趋势。对这种趋势保持足够的警觉对保护个人自由与尊严、对保护少数族群和边缘人群的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互动式媒体的出现使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自己的记者,他们在媒体上发出自己的独特感受和见解,并以自己的视角去观察自己和别人的世界,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认知方式去评判他们所看到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每个人都想出场和在场。“微博”这个词在德里达先生健在时尚未在我们的社会流行起来。而今,这个词的流行以及它所表达的意义已使过去少数人拥有的东西不再成为专有的东西,从而使外在灌输的普遍化的东西丧失了它原有的神圣性。随着每个人成为自己的发言人,代言人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以他人的名义说话和做事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了。这恰恰是瓦解普遍化的东西的过程,也是使秘密不再成为秘密的过程。
但是,秘密究竟意味着什么?只要个体还是一个个体,这个个体就有着自身的秘密。从广义上说,秘密是与独特性相关的东西,甚至是维持独特性的那种东西。它服从“我”的“我性”或专属性。它是最为本己的东西,甚至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用Nicholas Boyle在《德里达》一书中的说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做事、思考、感受或经验事物的独特方式,每件文学作品以及解读这种作品的方式也是独特的。“作品的这种独特性与作者独一无二的专门术语、风格和签名有关。每个人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不同地写作(和阅读)”。⑤
德里达在不同的地方都谈论“秘密”并且试图呈现“秘密”(secret)一词的不同意义。但对他来说,秘密是可以谈论但不能说出来的东西,因为说出来的东西都不可能是秘密。秘密从最终意义上说只是个人内心的独特经验。德里达还赋予秘密以神圣的性质,这一点源于并且反映了宗教领域的秘密与神秘之间的本源性关系。因为在西方文化里,秘密在很大程度上还与宗教经验有关。德里达在解读基尔凯戈尔以及解释亚伯拉罕与耶和华的关系时,就试图说明其中蕴含着的秘密问题。在德里达看来,对亚伯拉罕的审判本应包含保守秘密的要求,包含不能说出那个绝对者对他说出的东西的要求。“所有这些必须是绝对秘密的——只是我们之间的事情。它必须无条件地成为私人的事情,是我们的内部事务并且不可了解”。⑥
从语源上讲,“秘密”问题的确涉及如何处理神秘的东西。不可见性、非透明性、晦暗性、专属性和不可预见性都是秘密的应有之义。在古法语和拉丁文中,“秘密”(secretus,secernere)原本意味着“掩盖”,“过滤”,后来引申出“幽暗”、“秘密”、“神秘”、“偏僻”等等含义。不能公开和不能分享始终是“秘密”的基本意义。德里达在一本自传性作品(题为Circumfession,这个书名几乎是不能翻译的)中甚至说,秘密就是“仅仅由我碰到的”东西,或者说,秘密仅仅是我专有的东西。“专有”维持了我对某物的所有权的不可让渡性,因为一物一旦成为可让渡的东西,这个东西就不是我专有的东西,它对我的唯一所属性就改变了。此处的唯一所属性表现出独特性的结构。它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它是不能重复的东西,也是不能为他者分享的东西。它必须用专门的术语来表示,此术语指称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它与其他东西具有异质性,差异即它的本性。它自身的边界同时就是对它物的限制。为了说明和捍卫独特性(如个人的独特性、作品的独特性、语言的独特性和文化的独特性,等等),德里达一辈子都在同“同质性”作斗争,因为从根本上讲对抗现代性意味着打破同质性,重视异质性,也意味着打破同一,重视差异。他举了许多例子来证明和解释独特性是什么。比如,专名、签名、文学作品、对这类作品的解读、个人专有术语,都是独一无二的。也许有人会说,专名并不专,因为不同的人可能用同一个名字。比如,可能有很多人都叫“王卫东”。但是,“王卫东”这个名字的意义恰恰是在与某个独一无二的那个王卫东的关系决定的。换言之,当我用王卫东这个名字时,我指称的那个王卫东是相同的,是我心中想到的那个人。签名也遵循类似的逻辑。签名能得以成立并作为某人认可的唯一标志,就是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签名毋宁就是专有的标志,是自己对自己专属性的声明。它是无声的授权,只不过这种授权确证了自身的权威的唯一性。德里达为分析法国诗人蓬日(F.Ponge)而撰写的作品《签了名的蓬日》或《符号海绵》(书名为Signeponge/Signsponge,它同样不可翻译,德里达用它同时表示多重意思)就花了很多篇幅来讨论签名问题。但他试图说明,即便是专属的东西也包含矛盾和否定自身的因素和力量。比如,别人能够伪造某个人的签名就是例证。或用他本人的话说,“伪造的可能性总是规定着被称为签名的事件的结构本身”⑦。这表明,签名其实是“我不能占有的东西,是我不能使之成为我自己的东西的东西”⑧。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德里达始终让我们意识到思考独特性时不得不面临的矛盾和困境。
第二,独特性的结构显示了超出自身并与一般性发生关联的可能性。德里达同样在很多地方讨论过这个问题。在谈到阅读时,德里达一方面承认阅读的独特性,但又认为“绝对纯粹的独特性是不适用于阅读的”。独特性要变得可以阅读,就必须分裂自身,就必须分有“种、类、语境、意义、意义在概念上的一般性”⑨。也就是说,独特性并非自身存在的。在此,独特性的独一无二性并不属于自身。绝对的占有之所以是不可能的,是因为独特性在显示出来时就已经不是独特性了。比如,签名通常被视为独特的,但“签名必须既继续存在,又同时消失,必须为了存在而消失,为了消失而存在”⑩。名字在德里达看来则代表空洞的秘密。人的生活既是对这个空洞的填充,又是对这个空洞的暴露。在《激情:一种躲躲闪闪的赠与》一文中,德里达说:“存在某种秘密。但它并不掩盖自身。”(11)德里达在此试图表明秘密的矛盾性质。我们一方面想保守自己的秘密,另一方面又想吐露秘密,因为秘密本身就是对人的心理压力。秘密在本质上的专有性使秘密必须保持其无条件的私人性。但我们越是想保守秘密,我们也越是在暴露秘密,因为当我们极力保守秘密时,我们已给秘密与非秘密划定了一道界线。这道界线越是分明,秘密的轮廓越是清晰。就像极端的光明意味着绝对的黑暗一样,绝对的秘密也意味着绝对的非秘密。秘密与非秘密的辩证关系就像黑洞与非黑洞的关系。人既然不是离群索居的动物,他在公共生活领域的存在总能留下生活过的痕迹。这个痕迹就是秘密的索引,它给所有人打开了一道门缝。
德里达的确重视秘密的专有性和独一无二性,但专有并不足以成就秘密。专有的东西必须有不可示人的方面才能成为秘密。因此,真正的秘密,必须在保有独特性或者独一无二性的同时,也必须是不可见的、不可言说的。德里达说,秘密就是可以谈论,但不能说出来的东西。用德里达在《对秘密的喜好》中的话说,“如果有什么绝对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秘密”(12)。可是,正如纳斯教授所说,秘密意味着不可见性、不透明性、不可交流性、不可传达性以及不可预见性。它抵制任何形式的言说和曝光。德里达说自己喜欢秘密而不是非秘密。他对不给秘密留下空间的政治和文化感到不安和恐惧。因为他认为如果不保护个人对拥有秘密的权利,我们就会处于专制的空间中。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德里达反对任何宗教中不给秘密留下空间的思维。
德里达从许多方面来解构“秘密”概念。除了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的,从宗教经验、签名、个人专用术语、名字等方面来谈论秘密之外,他还从死亡、档案、自传、文学作品等方面来解构秘密。在他看来,死是最大的秘密。“死始终是一种秘密的名称,因为它表示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它提出了一种秘密的公开名称、共同名称,提出了没有名称的专名的共同名称。”(13)同时,他认为,关于死亡的语言不过是一种秘密会社的漫长历史而已。它既不是单纯公共的东西,也不是单纯私人的东西,它介于两者之间。“显然,对这种绝对/秘密的最有诱惑的比喻就是死,是与死有关的东西,是被死带走的东西——是那种成为生活本身的东西。的确,与死的关系是对秘密的这种特殊经验的特殊维度,但我以为,一种不朽的东西也会有同样的经验。”(14)一个人可以告诉我们他所经历的所有东西,但唯独不能把自己的死告诉别人。能告诉给别人的死已经不是死,而是生。死是绝对不可言说的东西,死带走一切,当然也包括秘密。死的反面,即不朽,也不能告诉别人,能述说出来的不朽已经不是不朽。不朽就像死一样是绝对不可破解的。虽然我们都可能热衷于谈论不朽、渴望不朽,但我们作为有死的人只是在渴望自己达不到的东西,以便消除或减轻自己对死的恐惧。对生者来说,死是绝对的外在性、他者性。我们也许可以用任何名称去命名死,但死永远是那些名称之下的秘密。生只是在迈向这个隐藏着的深渊。但死不等于那个隐藏着的东西。这是生的困境,也是死的困境,是有死的人面对自己向往的不朽时的困境。
谈起秘密,人们不能不想到政治。德里达声称,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秘密主要与政治相关。经济的、军事的和个人的秘密最终是在政治秘密的背景里显示其意义。因此,现代政治哲学不得不研究这个秘密问题。过去,人们谈到秘密时总喜欢谈到宫廷政治阴谋。其实,现代民主政治既使秘密成为必要,又使秘密最终不能成为秘密。德里达甚至说,假如没有民主,秘密也无所谓秘密。政治从来就是有秘密的。政治是通过控制秘密而成为政治的。其中,控制档案就是控制秘密的制度化形式。档案之关乎政治就在于这种秘密。对秘密的忧虑使保密成为必要,而对秘密的忧虑乃是对某种专有权和垄断权的忧虑。民主的本质因素之一就包含对档案的垄断权的最终放弃,因为档案在一定年限之后就会公之于众。在这种情况下,档案是为公众而存在的,而不仅仅是为控制档案的人而存在。公开档案在一个开放社会里意味着解密,意味着秘密的分享,意味着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设定档案的公开时限本身就表明权力对档案的控制,对秘密的控制,也表明档案如何与活人的政治社会生活相联系。
德里达在解读H.Cixous写的《曼哈顿》这部作品时说过:“一方面,这种秘密就像天性一样,保留着一种力量、一种权力、一种自身的动力。——这种法律的力量,这种秘密,始终是某个人的权力。没有在他人面前的约定,就没有秘密。”(15)放弃这种控制意味着对专有权的放弃。对真相的了解就是从这种控制的放弃开始的。因此,德里达说,“在这种意义上,一种受到保护的秘密始终是一种丧失了的秘密”(16)。在《档案热》(Mal d'archive,亦可翻译为《档案病》或《档案狂》)中,德里达还通过分析档案的起源来分析控制档案的过程与控制秘密的过程以及政治权力的运作过程如何密切相关。他甚至说,“没有对档案的控制,没有对记忆的控制,就没有政治权力”(17)。政治权力与档案在西方历史上一直是相互联系着的,在古希腊时,各城邦的执政官就被称为archonte,此词与“档案”(arkhe)属于同源词,因为最初时放档案的地方既是官员的住处,又是发布命令的地方,它是政治权力的代名词。换言之,在古时候,档案主要是服务于政治和法律权威的。行政官员有处置和保管那些档案的权力,“他们有权力解释那些档案”(18)。
然而,在今天的社会里,档案的存在方式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利用这些档案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档案的电子化使储存和共享变得非常便捷,但也使秘密难以成为秘密。由于档案存储与互联网的互通,泄密与窃密变得比较容易,同时公众对档案的兴趣与日俱增,人们对秘密的好奇心也与日俱增。作为现代性的产物的互联网技术既扩大了人们的兴趣范围,也容易使许多人对某些秘密的兴趣交织起来并形成一个共同体,从而加大了利用政治权力控制秘密的难度。维基揭秘事件给许多国家带来的外交难题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已。当互联网技术变成全球性媒体平台和每个人的信息发布平台以及社交平台时,信息的真假难辨以及真理与意见的界限的模糊化将给政治的未来构成难以预料的挑战。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档案始终是一种证据(gage,又可译作抵押——引者),并且就像所有证据一样是未来的证据”(19)。电子档案与互联网的可能的互通不单单改变了传统的档案形态,而且打破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传统划分。原来能够在私人空间运作的东西现在不得不变成公共空间的东西,档案的所有权、公开权和复制权不得不发生转变,这种转变使各国的政治改革与司法改革不可避免。否则,它们就会被网络民主和网络暴力所淹没。现代资本、技术和权力的结合既是它们的动力,也是体现它们的现代性本质的基本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德里达也用“现代性”概念,但他本人对这个词并未作清楚的界定,也未对它加以详细阐述,这不免让人稍感遗憾。也许,他认为“现代性”是一个人人熟知的无需解释的概念。但正如黑格尔所说,“熟知并非真知”。我在此想继续提出人们反复提出过的问题:“现代性”意味着什么?按照比较可信的说法,“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源于拉丁文的modernus(现代),而modernus的使用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它最早与modus(方式、样式)有关,包括“新颖”、“时尚”、“时髦”等意义,后来专指随基督教的兴起与传播而流行起来的新观念、新潮流。因此,“现代性”的观念的形成和发展的确像德里达分析的那样与基督教的兴起与传播有关。但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性是以启蒙运动的宏大叙事为基础的。它反映了启蒙运动的思维模式、文化潮流、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建筑是它的包装,解放是它的基调,技术是它的工具,统一是它的诉求,普遍进步是它的信念,资本主义是它的名称,思辨哲学是它的表达。”(20)当代人对现代性的第一个直观的感受是技术理性及其产物的无所不在。电视以及作为电视的延伸的其他高技术媒体既是现代性的展示,又是它的诠释,更是它的传播工具。它越来越服从资本和权力的逻辑,甚至代表了资本、技术和权力的统一,它仿佛有了自主性并遵循自身的法则,即灌输和支配的法则,当然也有受欲望推动的货币世界的法则。
在这个受欲望推动的世界上,媒体煽动需要,刺激需要,强化需要并且制造需要,不管这种需要是真的需要还是假的需要。它通过广告不断告诉你,你应当有什么样的新奇的需要,于是,你渐渐由不需要学会了需要。资本的逻辑是制造需要和满足需要的逻辑,也是刺激无限需要的逻辑。现代性建立在理性的精心设计的基础上,其中包括对需要的设计。比如,一部电视机有许多功能,但消费者一开始并不需要那么多功能,甚至压根儿没有想到需要那些功能。但使用说明书让你知道了那些需要并且尝试学习那些需要。即便你用不上那些电视功能,你也被迫花钱买下那些功能,因为你假定你将来有那些需要,而且标准化生产也迫使你接受那些假定的需要。你只能把一些“需要”储备起来。你对新需要的多少直接决定了潜在市场的规模。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秘密,也是现代性的秘密。
于今,我们没有人怀疑电视、广播乃至互联网是现代性的产物,但媒体也强化了现代性。它通过将声音和形象结合起来并且超越了时空障碍而成为在场的见证,它也能使局部的现象成为普遍性现象,至少貌似成为这样的现象。媒体彰显了技术理性在现代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也构建了全新的全球性精神空间。它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并且成为其他方面的全球化的先导和手段。全球化与普遍主义观念的传播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近代,基督教充当了全球化的先锋,同时也借助各种组织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活动使自身获得普遍传播。但是,这种传播活动不同于传统的、由教会组织的可以看得见的活动。如果说殖民主义运动构成了普遍主义观念传播的第一阶段,那么,当代经济的全球化和通讯技术的全球化使普遍主义观念的传播进入了第二阶段。而普遍主义观念的盛行是与电视和其他类型的高技术媒体(如因特网)的使用广度和深度密切相关的。德里达向我们暗示其中蕴含的危险,这种危险也是现代性的危险。
德里达在《无赖》中特别指出“9·11”事件的参加者就是全球化的直接后果,也是现代性的后果,媒体在制造这一后果方面所起的作用需要好好反思。因为这一事件的参加者从现代媒体的夸张性描述中以及对仇恨的煽动中得到了动力,他们在美国接受训练,乘着美国的飞机、以美国人的方式撞击了作为资本主义财富和技术象征的双子塔。这一事件无疑是不幸的,给美国人民,也给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造成了莫大的悲伤。它改变了传统的战争概念,也在一定意义上让人们重新思考恐怖主义的长远后果并重新思考媒体的本质。这一事件通过媒体的戏剧化和反复对观众的心灵撞击仿佛建构了事件的结构和可能性。当“9·11”事件发生时,德里达正在上海,他是从电视上“见到”这一“事件”的并在与我们座谈时预言美国要发动战争,要进行警察统治,要限制个人自由,而后者恰恰意味着个人秘密不再成为秘密。美国为了反恐的需要采取了怀疑一切的做法,这当然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管理的成本。德里达的预言后来成了现实。在“9·11”事件发生以后的十年中,美国的部分对内、对外政策仿佛是按德里达先生所预言的轨迹来制订和实施的。这令人吃惊地显示了德里达先生的先见之明。双子塔崩塌的电视画面的反复播出给美国人造成的精神创伤是严重的,它所造成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恐怖气氛恰恰是恐怖分子想要达到的效果。CNN等媒体在客观上做了恐怖分子无法做到的事情。媒体以自身的逻辑实践着他者的逻辑、强制的逻辑。
这种逻辑既是打破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分界的逻辑,从而也是使秘密不再成为秘密的逻辑,又是把神圣经验变成世俗经验的逻辑。媒体在促进当今社会的人道化方面,在促进人类心灵沟通方面,在促进个人发言权的提高方面,在推动人类的学习能力并改变人类的生存处境方面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对媒体本身保持清醒的头脑并建设性地对媒体本身采取批判的立场对人类的未来无疑也是重要的。
作者附言
本文源于笔者对美国学者纳斯(Michael Naas)教授在复旦大学的报告(2011)的评论以及他本人对我的评论的回应。本文根据英文稿扩充和修改而成。他的报告题为“媒体与现代性:德里达与媒体的宗教”(Television and Modernity:Jacques Derrida and the Religion of the Media)。这次对谈是我们对德里达的共同解读,通过这种解读我们都希望在另外一种语言中通过某种互文性拓展对德里达的解释空间。在本文中,我滤去了与纳斯教授的多数谈话内容,而主要谈谈我对德里达先生的某些著述的领会,也部分地表达我对媒体、秘密与现代性的一些看法。
注释:
①德里达:《无赖》,第209页,汪堂家、李之喆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②Herbert Marcuse,One-Dimensional Man,Beacon Press,1991,p.19.
③汪堂家:《汪堂家讲德里达》,第1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④J.Derrida,Acts of Religion,ed.by Gil Anidjar,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2,p.71.
⑤Nicholas Boyle,Jacques Derrida,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pp.119—128.
⑥J.Derrida,"Above All,No Journalists!" trans.Samuel Weber.In:Religion and Media,ed.Hent de Vries and Samuel Web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56.
⑦J.Derrida,"Between Brackets I",in:Points…interviews,1974—94,ed.Elisabeth Web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5—25.
⑧J.Derrida,A Taste for Secret,with Maurizio Ferraris,trans.Giacomo Donis,Cambridge:Polity Press,2001,p.85.
⑨N.Boyle,Jacques Derrida,p.120.
⑩J.Derrida,Signeponge/Signponge,trans.Richard Ran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p.56.
(11)J.Derrida,"Passions:An Oblique Offering",trans.David Wood,in:Derrida:A Critical Reader,ed.by David Wood.Oxford and Cambridge,MA:Basil Blackwell,1992,pp.5—35.
(12)J.Derrida,A Taste for Secret,with Maurizio Ferraris,trans.Giacomo Donis,Cambridge:Polity Press,2001,p.57.
(13)J.Derrida,Aporias:Dying-Awaiting(One Another at) the "Limits of Truth",trans.Thomas Dutoi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74.
(14)J.Derrida,A Taste for Secret,with Maurizio Ferraris,trans.Giacomo Donis,Cambridge:Polity Press,2001,p.58.
(15)J.Derrida,A Taste for Secret,with Maurizio Ferraris,trans.Giacomo Donis,Cambridge:Polity Press,2001,p.30.
(16)J.Derrida,Géneses,généalogies,Genres et le génie,Paris:Galilée,2003,p.30.
(17)(18)J.Derrida,Mal d'archive,Paris:Galilée,2008,p.13.
(19)J.Derrida,Mal d'archive,Galilée,2008,p.37.
(20)汪堂家:《利奥达与后现代概念的哲学诠释》,载《复旦学报》,2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