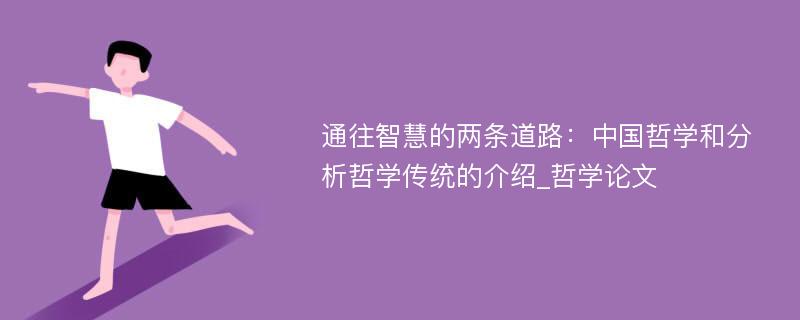
《两条通往智慧之路?——中国哲学与分析哲学传统》导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导言论文,之路论文,两条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中国哲学与西方分析哲学(或分析传统的西方哲学)被认为是彼此遥远、无 关乃至对立的。两种传统中都有很多人将对方传统的哲学实践视为仅仅具有边缘价值。 首先,人们认为它们各自的反思思维模式和方法论路数是截然不同的;其次,人们认为 两者所关注的问题不同。这两方面的考虑均指向哲学上的一系列基础问题,特别是哲学 方法论问题。现在,随着不同文化共同体和思想传统之间的非同以往的交流趋近,在不 同哲学传统之间进行沟通的愿望和对于它们如何能够相互学习、以互补方式携手共建共 同哲学事业的关注在哲学界日益紧迫。这种关注与哲学方法论问题有内在联系;这是因 为,一方面,不同哲学传统所特有的看待问题的角度或见识在很大程度上与思维模式和 方法论取向有关。另一方面,哲学方法论问题一直是哲学反思实践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 的问题;从一个更广阔的、超出某一哲学传统自身疆域的角度去考查哲学方法论问题具 有特殊价值。
与上述考虑相应,本卷文选的中心论题在于下述三个在本卷中密切相关的目标:(1)通 过一种涉及中国哲学传统和西方分析哲学传统的比较分析来探讨哲学方法论问题;(2) 促进不同哲学传统之间与有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哲学教育背景和不同方法论路数的哲 学家之间的对话与理解;(3)更具体来说,研究中国哲学传统和西方分析哲学传统这两 种具有特色的主要哲学传统如何能够相互学习、以互补方式携手共建共同的哲学事业( 特别是在看问题角度、指南性方法和工具性方法这些方面)。
本卷的中心论题所涉及到的若干关键词项(“哲学方法论”、“中国哲学”、“分析哲 学”或“分析方法论”)需要予以起码的初步澄清。“哲学方法论”这一词项在此用以 表示在哲学反思探究中多种多样的对哲学研究对象的处理方式;它要么是指工具性方法 ,要么是指针对研究对象某一方面的角度取向性方法,要么是指由哲学家所预设而引导 和规范其如何运用角度取向性方法或工具性方法的那种指南性方法。“中国哲学”这一 词项在此用以概括从古典时期(大致指从公元前11世纪中期到公元前249年周期的最后几 百年)直到清朝发生在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想运动及其当代的发展。而对中国哲学 的研究则不仅包括以往对中国哲学的学术研究,而且包括对中国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当代 研究。“(西方)分析哲学”这一词项曾被狭义地用来仅仅表示20世纪西方的当代分析运 动,或被广义地用来表示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经由笛卡尔、英国经验论和 康德直到当代分析运动这一整个作为西方主流哲学(之一)的分析传统。“西方分析哲学”这一词项在本卷中是在其广义上运用的;它的所指不妨被称之为“分析传统的西方哲 学”。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所使用的诸如“西方分析哲学”和“分析传统的西方哲学 ”这样的词项本身,除了表示在这一传统中的西方哲学与这一传统的某些方法论路数之 间的某种历史性联系之外,并不旨在蕴涵这些方法论路数内在地或概念上惟一地与西方 哲学相联系。“分析方法(论)”或“分析的方法论路数”这些词项的意义在本卷是探讨 的主要对象。在对于“哲学方法论”的含义作出起码的必要澄清的情况下,人们不妨暂 时地将“分析方法(论)”视为概括地指称历史上在西方分析传统占支配地位的那种对哲 学研究对象的处理方式。不过,需要提醒读者注意本卷各个作者在其论文中用“分析方 法(论)”所表达的含义。
由于所探讨的问题涉及哲学基础问题并具有高度争论性,本文集强调其反思批判性质 、不以先入之见预设某种取向或倾向来赞成或反对某种特定方法论取向或处理方式。在 本文集中,论文作者从不同角度提出并论证了有所区别、乃至极为不同的观点;由此, 本文集强调不同观点之间的反思对话、相互理解以及进一步的哲学反思和哲学进步。中 国宋朝的诗人苏轼曾在其诗中写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注:参 看苏轼《题西林寺壁》一诗。)这一诗句可被借用来传递本文集用以实现其目的之批判 性比较方法的要旨。的确,本文集为此而努力对相关的有代表性的方法论路数作出均衡 选择,从而得以从不同角度探讨其中心论题。虽然本书直接关注的焦点是在哲学方法论 方面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分析传统哲学之间的关系,但是文章作者的方法论路数和观点对 当前哲学领域的诸多元哲学或元方法论态度具有广泛代表性。本书也在另外一种含义上 是国际合作和全球哲学对话的结果:论文作者来自具有不同学术或文化背景的不同地理 区域,譬如美国、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英国。此外,几乎所有论文(两篇文章除外) 均针对本书主题而为本文集所作、在此首次发表;所提出的诸多创新观点将会对本文集 所关注问题的学术研究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16位作者的15篇专题论文分别被纳入从不同角度、但以某种相互联结的方式处理本书 中心论题的下述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哲学:学科性质与方法论
第二部分:中国哲学与哲学分析(Ⅰ):方法论上的角度取向性
第三部分:中国哲学与哲学分析(Ⅱ):检验性例证分析
第四部分:比较哲学中的方法论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这些不同部分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其中许多文章的综合性质,这些 专题论文的组织划分方式不是惟一的。读者可以根据其特定兴趣和特定关注问题而选择 不同的阅读顺序。在以下内容里,我概述一下我的组织策略和每一部分是如何相关于本 书主题以及各部分之间的联系。
第一部分的文章分别从某些分析传统的观点或从东西方传统中的其它观点出发,在元 哲学的层次上讨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的性质及其方法论特征。一个考虑是这样的:本 文集的直接研讨对象是中国哲学与分析传统的西方哲学就哲学方法论而言的关系;为此 ,人们需要首先对于究竟什么是分析方法论及其当代取向有一个公平的理解。莱舍尔(
Nicholas Rescher)和莫顿(Adam Morton)作为两位各具特色的当代著名分析哲学家,在 其各自的论文中会使读者对分析方法论及其某些当代发展形式有第一手的更新了解。莱 舍尔将哲学及其关键的方法论特征刻画为基于系统考虑的理性猜想;他同时也强调两种 看来似乎相互对立、但实则相互支持的研究哲学基本方式(即修辞的方式和论证的方式) 之间的和谐一致。纳维里(Robert Cummings Neville)则从某些其它角度(譬如实用论和 儒家的角度)批判分析传统中的笛卡尔式“方法学说”;他将“分析方法”宽泛地解释 为被规范的争辩,并将哲学学科刻画为造就哲学资源、探究真正问题以及提出假设和为 之作出论辩。不过,实用论精神和对真正问题的关注也为分析传统中的某些哲学家如莫 顿所强调。莫顿将哲学刻画为类似于工程学那样的探求;他提出一种关于受先天限制的 常识与它们的以真和证据为关注对象的理论相应物之间关系的、介于两种相互对立的支 配性指导方针(即奎因式观点与斯特劳森式观点)之间的实用论的中间路线。唐力权(Lik Kuen Tong)则从一种基础性形而上观点出发来批评他称之为“唯理论分析传统”的 “教条性实体论”的取向;与此同时,他系统地阐述其场有哲学观,把哲学刻画为人类 的贯彻至极的学道探求。第一部分的四篇论文向读者不仅提出了如何批判性地思考哲学 之性质及其方法论特征的各自见解,而且提供了在这一问题上的相对均衡的背景材料。
第二部分的论文通过一般性理论辩论来直接探究分析方法论与中国哲学(研究)之间的 关系问题。在对西方传统中的分析方法与中国传统(古典时期或现代时期)中的某些有代 表性的方法论思路进行批判性考查的同时,该部分中的每个作者均或多或少系统地提出 了其本人关于研究中国哲学(以及一般来说研究哲学)的方法论思路。成中英(Chungying Cheng)和刘述先(Shu-hsien Liu)都力图将解释学方法与分析方法相融合来开展中国哲 学的研究,并将中国哲学中有价值的见解融入世界哲学;但两人是按不同的方式来提出 论证的。成中英对其本体诠释学纲领提出了系统的理论表述,并通过概述这一理论如何 能够纳入奎因关于逻辑和语言的哲学、它如何能够克服认识论中的盖提尔难题来例示其 解释力。刘述先则通过考查他本人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之演变过程来例示其方法论观点; 与此同时,他强调了卡西尔式解释学和新儒家的“理一分殊”命题的重要意义。霍大维 (David L.Hall)则采取了一种实用论的、历史循环论的和种族中心论的元方法论思路; 他着重论述对比了中国元话语叙述中与西方分析传统中的某些相互区别的关键性问题境 况(譬如“连续”对比“分立”),并强调双方所作出的自觉努力来营造相互理解的条件 。李幼蒸(You-zheng Li)从一种综合性的符号学角度对中国哲学研究予以批判性考查; 通过考查中国哲学的语言构成、概念构成、学科构成和文化构成,他说明一种跨学科的 符号学方法如何会使中国哲学更加富有成效地与西方思想展开对话。需要注意的是,在 这一部分的论文中,对分析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也许不同于分析传统哲学家对它的原有 理解;因此,多少更带有中立性的词项“哲学分析”用于这部分的标题,可以更恰当地 包容这些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
在第三部分中,处理分析方法论与中国哲学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通过与上一部分 的一般性理论辩论形成对照的另外一种方式处理的:某些在广义上理解的分析性思路被 预设来运用于处理中国哲学中的某些重要问题。陈汉生(Chad Hansen)通过区别形而上 的超越、认识上的超越和道德上的超越以及深入解释道家的见解来论证:中国思想中的 道德上的超越在于道德共同体的语言,而不是在于认识上的超越。他富有特色地运用分 析性思路上的“语言”解释性方法,强调社会语言实践中所蕴藏的使用规范。在其讨论 儒家自我与自我道德修行学说时,信广来(Kwong-loi Shun)将儒家思想视为一有机融贯 整体而专注于分析这些思想之间的相互联系;与此同时,他强调运用概念分析与语言分 析方法来澄清和阐释早期儒家典籍中一些相关的关键词项。冯耀明(Yiu-ming Fung)探 讨了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即某些涉及终极关注的中心命题(如天人合一)是否应当并能 够加以概念分析和逻辑分析。他力图从分析的观点并通过若干哲学上有趣的思想实验来 解构他视之为新儒家虚构神话的某些中心命题。在本文集中,这些处理方式被视为检验 分析性思路究竟是否会对我们理解和研究中国哲学作出重要贡献的例证。倘若这些作者 在本书中所提呈的研究工作的确会帮助我们深化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并对哲学研究作出贡 献,那便是成功运用分析方法论的一个令人信服的标志。
第四部分中的论文专注于比较哲学(特别是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中一系列相关的方法 论问题。艾林森(Robert E.Allinson)的论文着重于讨论如何看待比较哲学的性质与地 位的问题。他致力于使被视为与哲学本身相分离的比较哲学非神秘化,而将比较哲学重 构为一体化哲学。余纪元(Ji-yuan Yu)和布宁(Nicholas Bunnin)共同撰写的论文讨论 了是否存在某些开展比较哲学研究的一般性方法;作者力图说明亚里士多德的“拯救现 象”三部曲方法(确立现象;分析现象间的对立;拯救包含在意见中的真理)可以扩展到 比较哲学领域。范诺登(Bryan Van Norden)在论文中批评了麦金太尔关于不同思想传统 间的不可通约性命题;他通过分析孟子和奥古斯丁关于人类错误行为的看来不同的各自 解释来论证其观点。我(Mou Bo)本人的论文则通过对于哲学方法的不同方面的地位和功 能及其关系的元哲学分析来讨论哲学方法论之结构,并通过分析苏格拉底和孔子的哲学 方法来例示所论证的观点。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部分所讨论的方法论问题以及作者在这 里所提出的诸多观点,并不仅限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而是论及关于不同 哲学传统或同一传统内部不同思维模式、不同方法论思路或观点的比较研究。因此,这 一部分中作者论证的很多方法论观点具有关于哲学研究的一般性方法论蕴涵。
正如在开头部分所强调的那样,本文集的所有作者都在参与反思对话。倘若这种反思 对话按照苏格拉底式辩证法的方式来理解的话,那么,这场反思对话尚未完结。正如戴 维森所指出的那样,
苏格拉底式辩证法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它们超越了仅仅试图让自命有知者认识到 不相容性。一个方面是参与对话的双方都能期望有所获益;另外一个方面是:不像书写 论文那样,这种对话呈现的是一个造成变化的过程....在下述两者之间是有极大区别的 :一是彼此有很好相互理解的人们之间的一场争论;一是获得相互理解本身构成所论难 题的大部分内容的一场交锋。但在下述两者之间存在甚至更大的差距:一是在其中的对 话参与者使用清楚概念(不论他们是否使用相同的词语来表达这些概念)的一场交锋;一 是这些概念本身成为关注焦点的交锋过程。以写作形式开展的讨论几乎完全掩盖了这种 区别。写作将积极的对话解释者的数目降低为仅此一个,即读者本人,从而弥除了在其 中词语能够适应对话过程中形成的新用法和新观念的思想双向交锋。(注:D.戴维森: 《辩证法与对话》(“Dialectic and Dialogue,”in G.Preyer et al.,eds,Language,Mind and Epistemology,Kluwer,1994),第432页。)
戴维森的要点(如果我对其理解是正确的话)并非否认哲学写作能有效地介入哲学对话 ,而是强调苏格拉底式方法论精神的一个方面:所有对话参与者(在我们这种情况下不 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均被期待以开放的态度不拘一格、认真看待其他可供选择的看问题 角度,从而在对话过程中形成和改进我们的思想观点。在这种含义上,本文集所展开的 讨论仅仅是对话的一个开始而非终结。它不仅欢迎作者方面而且欢迎读者方面的进一步 思想交流、反思和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