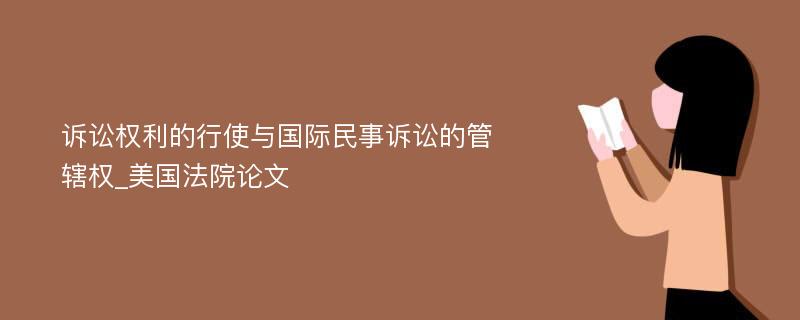
诉权的行使与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辖权论文,民事诉讼论文,诉权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4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512(2007)01—0026—08
权利总是有一定的范围的,其行使有一定的限制,不能滥用。诉权也不例外,虽然诉权是一项重要的权利,然而其行使也不能滥用,更不能非法行使诉权。在实践中,当事人滥用诉权的情形时有发生,包括滥用起诉权、反诉权等等。很多当事人明明知道自己不具备诉权的行使要件,却依然行使诉权,甚至虚构事实、伪造证据,诬告对方,以达到自己的非法目的。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了禁止滥用诉权,在英美法上,滥用诉权可以构成侵权行为。《布莱克法律词典》(第八版)将滥用诉权界定为不当地或者侵权性地使用合法签发的法院传票来获得非法或者超过传票范围的结果。1977年的《侵权法重述(第二次)》第682条规定,为了非法的目的滥用诉权要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责任。学界也对此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①
一、诉权的行使与送达
诉权要得到承认、行使要有效,有关案件必须为法院所受理,或者说法院要对有关案件行使管辖权,而法院受理同送达是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对送达的认识不同,对于其与管辖权的关系认识也存在不同。
(一)送达与管辖权
1.送达建立管辖权
英美法系国家法院行使管辖权是以传统普通法的“效果”原则及这一原则的例外——自愿服从作为依据的。因此,这些国家常常通过送达而确立对人管辖权。在历史上,英美普通法认为,对被告的对人管辖权主要是法院司法强制力的一个功能。② 起初,英国普通法法院在对人诉讼中不会作出判决,除非被告已经实际在法院出庭。③ 在19世纪初的美国,法院要对对人诉讼作出判决,也必须抓住被告。④ 后来,实际上的人身拘捕被象征性的拘捕所取代,法院不再像对待被起诉的刑事罪犯一样拘捕民事被告,而是通过传票传唤被告。
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很多美国判例都表明,对出现在法院地的被告送达后就可以取得管辖权,并且作出判决,不管被告是居住在那里还是暂时出现。⑤ 通过送达建立管辖权这个传统一直延续着,在1990年的“Burnham v.Superior Court”一案中,传统的规则虽然受到挑战,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送达完成后,就取得了管辖权。⑥ 直到现在,美国联邦法院和各州法院仍然以传票的送达作为对人管辖权行使的依据。在“Kadic v.Karadzic”一案中,第九巡回法院裁定在被告与美国没有任何实质性联系的情形下,被告即使是短暂过境美国,其也可以因此而被送达,法院也就取得管辖权。⑦
2.送达与平行诉讼
在大陆法系国家,虽然送达没有像在英美法系国家那样重要,可以因此而建立管辖权,但仍然起着解决平行诉讼的作用,这部分我们将在后面论述,这里不赘述。
(二)送达的有效性
那么,如何判断送达是合法有效的呢?美国法院认为,送达的核心功能是通知被告诉讼,以一定的方式在一定的时间内给被告提供了一个公平的机会提出答辩、抗辩和反对。⑧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被告是否得到足够的通知。⑨ 这样,甚至电子送达也是可以的。⑩ 如果被告逃避送达,例如拒绝接受文件,此时送达人只要非常接近被告,清楚地把送达法院文件的意图说明,并且作出合理的努力把送达的文件留下给被告,送达就算完成了,就是合法、有效的。(11)
相反,如果送达意图不明确,被告没有得到有效的通知,则送达很可能被认定无效,不能行使管辖权。在“Weiss v.Glemp”一案中,(12) 法院就认定对波兰红衣主教的送达无效,因为送达人仅仅拿着一个书面的东西,说“你要这个……”,主教的随行人员说“不要,不要”,并且将纸丢在地上,法院认为原告这样试图的送达“不是以合理的方法通知”被告,而且送达人所拿的文件不明确,可以是小册子、抗议信或者其他非法律性文件。而且证据没有显示被告企图逃避送达。
由于美国认为送达是私人之间的事情,与国家主权无涉,所以允许向国外进行各种方式的送达,也允许其他国家在美国境内直接送达。而以德国、瑞士等为代表的国家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送达程序属于“司法”或“公权力”行为,不能由私人完成,所以反对外国法院对其本国国民进行直接送达。我国也是持相同的看法。
(三)送达有效性的例外
英美法系国家对送达放得比较开,自由度比较大,一般只要有送达的意图并且将文件以合理的方式通知被告就构成送达。但在有些情形下,送达可能就是无效的。例如,对享有特权与豁免的人进行送达经常会被认定不合法、无效。在1965年的“Hellenic Lines,Ltd.v.Moore”案中,美国法院就认为:“在国务院已经通知法院对突尼斯驻美大使进行送达将会损害美国的对外关系和外交职能的正常履行后将本应送达给突尼斯的传票送达给突尼斯驻美大使就是不合适的。”(13)
此外,对外国国家元首进行送达,常常构成对该外国及其领导人的冒犯。如果允许对在本国领域内进行国事访问的外国领导人进行送达并行使管辖权,那么本国政府及领导人在国外也可能遭遇同样的情况与问题,这对本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标、利益都是不利的。因此,英美法系国家在实践中不允许在国内向来访的外国领导人进行送达,不论是送达给本人还是希望通过该领导人转交给第三人,更不能因此而行使管辖权。
(四)小结
上述可见,送达与诉权的行使密切相关,当事人要通过适当的送达来行使诉权。当事人不适当的送达既是滥用诉权,也不能实现其诉权。为了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各国应从送达抓起,不能允许当事人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滥用送达、诉权,也不能为当事人滥用送达、诉权留下便利的空间,更不能为当事人滥用送达、诉权提供协助。此外,通过过境送达而行使管辖权,这样的管辖依据是不合理的,是一种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反对的“过度管辖权”,这样的管辖权依据客观上鼓励了当事人挑选法院、滥用诉权,给被告造成困扰和压迫,很可能就会损害被告的合法权益,是一种司法沙文主义(judicial chauvinism)(14) 的表现,并不符合国际礼让和司法文明。如果减少这样的过度管辖权依据,那么正当行使诉权就更加可能了。
二、诉权的行使与管辖权的冲突
在国际民事诉讼中,诉权的行使与管辖权冲突密切相关,管辖权冲突实际上为滥用诉权提供了便利。因此,我们要通过适当地解决管辖权冲突来防止诉权的滥用,鼓励当事人正当行使诉权。下面我们简单探讨一下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管辖权冲突的概念
虽然理论界和实务界都认识到管辖权问题的重要性,但对什么是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则有不同看法。(15) 我们认为,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是指一国法院或具有审判权的其他司法机关受理、审判具有国际因素或涉外因素的民商事案件的权限。(16) 它旨在解决某一特定的国际民商事案件究竟应由哪一个国家的法院管辖的问题。至于在此后要确定由该国哪一级、哪一地的法院管辖,则是该国国内民事诉讼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也有学者将国际民事诉讼法中的诉讼管辖权称为“国际管辖权”(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
关于如何确定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主要有国籍管辖、地域管辖、专属管辖、协议管辖、应诉管辖等。由于各国关于管辖权的立法不同,特别是关于管辖依据的规定不同,在国际民事诉讼中常常会产生管辖权冲突的问题。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是指在国际民事诉讼中与某一国际民商事案件相关联的所有国家或者都主张管辖权或者都拒绝管辖的情况,前者称为管辖权的积极冲突,后者称为管辖权的消极冲突。(17)
管辖权冲突的存在,给诉权的行使和滥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可能,使问题更加复杂。由于管辖权的消极冲突的情形比较少,在此我们不作讨论,仅仅讨论一下管辖权的积极冲突与诉权的行使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二)不方便法院
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各国都规定了广泛的管辖权依据,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司法沙文主义的问题,这是管辖权积极冲突的根源所在。为了克服管辖权积极冲突而导致的问题,一些国家实践中便运用不方便法院(forum non conveniens)原则来拒绝行使管辖权、减少讼累,保护本国的利益。
不方便法院原则,起源于苏格兰,之后开始为其他国家所采纳。(18) 虽然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本来目的并不是用来解决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积极冲突的,而是为了解决因受诉法院的审理所产生的不方便问题,但由于受诉法院可以以不方便为由而拒绝审理,客观上的确有助于解决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积极冲突。
虽然不方便法院原则在不同国家有不尽相同的适用,但一般都是指当本国法院享有管辖权,但如认为它对案件行使管辖权非常不方便或不公平,且存在其他较为方便审理该案的外国法院时,该法院可以拒绝行使管辖权。(19)
在美国,为了所有当事人的利益和正义的目的,防止原告滥用诉讼程序,选择对被告极为“烦扰”、“压迫”的法院,在1947年的一个案件中确定了不方便法院原则。为此,法院采用两步分析法,第一步就是确定有一个外国法院可以审理,第二步就是平衡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20) 到了1981年的“Piper Aircraft Co.v.Reyno”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不方便原则有了进一步的阐述。(21) 最高法院评价不方便法院的标准已从原来较为严格的“滥用程序”的标准转变为较为灵活的“最适当法院”的标准,限制部分外国原告进入美国法院,这为联邦下级法院以及州法院在国际案件中,拒绝由外国原告提起的诉讼创造了条件。(22) 现在,美国法院还是会以不方便法院原则撤销原告的诉讼。(23)当然,对于在美国有住所的个人,法院一般认为自己是方便的法院,不会要求其去外国法院起诉,而会驳回被告援引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抗辩。(24)
在英国、加拿大、荷兰、新西兰、比利时、希腊、瑞士、芬兰、阿根廷等国,也都确立了类似的制度,以防止原告挑选法院,对被告造成不公平,也影响本国有限的司法资源。
(三)平行诉讼
平行诉讼,也称为未决诉讼,是指相同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基于相同事实以及相同目的,同时在两个以上国家的法院进行诉讼的现象,包括重复诉讼和对抗诉讼两种。平行诉讼的存在是当事人行使诉权的表现之一,但也可能是当事人滥用诉权,这对当事人的利益保护不利,也浪费司法资源。
关于平行诉讼,有些国家是允许平行诉讼继续进行的。有的国家让当事人自行选择审判法院。这两种方法并没有解决平行诉讼的问题。为了解决平行诉讼问题,《布鲁塞尔公约》第21条规定了“先受理原则”,其第1款规定:“相同当事人间就同一诉因在不同缔约国法院起诉时,首先受诉的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应主动放弃管辖权,让首先受诉的法院审理。”第23条规定:“属于数个法院有专属管辖权的诉讼,首先受诉的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应主动放弃管辖权,让首先受诉的法院审理。”至于如何判断“首先受理”,则看送达的先后,先送达者为先受理,就可以继续行使管辖权,而其他后受理的法院则应终止管辖。
对于并没签订解决平行诉讼条约的国家之间,如何解决平行诉讼以更好地促进公平正义,更好地规制当事人行使诉权呢?除了前面提到的可以以不方便法院原则来解决之外,本国法院拒绝或者中止管辖权,还可以考虑借鉴英美国家的禁诉令制度。禁诉令是指由一国法院所作,对系属该国法院管辖而在外国法院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下达的,禁止其在外国法院诉讼的命令。(25)
在我国,理论界、实务界对于禁诉令的看法还是存在很大争议的。(26) 然而,不管如何,我们都还是有必要认真研究这种制度,对于当事人滥用诉权,我们可以考虑利用禁诉令来阻止。
(四)管辖权协议与仲裁协议
管辖权协议与仲裁协议存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当事人约定了争议解决方式。因此,当事人之间存在管辖权协议与仲裁协议的,应该尊重当事人的意思,除非该协议本身有问题或者有其他可以否定的事由。关于仲裁协议,由于《纽约公约》的存在,各国基本上都会予以尊重,如果当事人订有仲裁协议,一方滥用诉权去起诉,那么法院就会不予受理、受理后也驳回起诉。对于管辖权协议,虽然各国观点不一,但我们认为应该尽可能尊重当事人的意思,不允许当事人事后反悔、滥用诉权。
(五)小结
管辖权冲突的存在,客观上为当事人滥用诉权提供了机会和可能性。对此,各国应该加强在管辖权冲突方面的协调,通过订立国际条约来解决。同时,各国法院都应该从善意的立场出发,妥善地解决管辖权的冲突,自我抑制管辖权的行使,从而尽量减少当事人滥用诉权的机会,避免给相关人员造成困扰和不便。
三、诉权的行使与管辖豁免
由于管辖豁免的存在,当事人的诉权的行使也就会受到一定限制,有些当事人明知被告享有管辖豁免,却依然执意行使诉权,结果很可能是消耗自己的精力、财力和心血却没什么结果,同时也对被告带来困扰和不便,浪费了司法资源。目前,关于管辖豁免,公认的有外交特权与豁免、国家豁免。
(一)外交、领事特权与豁免
为了论述方便,下文将把外交、领事特权与豁免简称为外交特权与豁免。
关于外交特权与豁免,国际社会通过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为了履行由此而产生的国际义务,各国一般也都制定了相应的国内法。因此,如果对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人提起诉讼,其诉权的行使一般都难以实现。例如,在美国,外交人员和领事人员都可以享受豁免,不受美国法院的管辖。当然,外交豁免必须基于接受国的承认。(27) 否则,就不能享受豁免。对于去美国的外国地方政府的官员,如果不是负有外交使命,那么一般是不能享受外交豁免的。“外交身份的全部特权与豁免一直以来都是这些受到承认、执行外交职能的外交人员”。(28) 在United States v.Foutanga Dit Babani Sissoko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作为“特别顾问”的身份并不能享受外交豁免,因为美国国务院并没有向其出具证明。(29) 当然,法院注意到实践中美国国务院在诉讼中出具的证明。在“Republic of Philippines by Cent.Bank of Philippines v.Marcos”案中,国务院授予在美国作证的菲律宾总检察长外交身份;(30) 在“Abdulaziz v.Metro.Dade County”案中,沙特王子及其家人在诉讼开始后获得外交身份。(31)
可以肯定,如果某一当事人针对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被告提起的诉讼,一方面,其是不正当地行使诉权,另一方面,有关法院应当不行使管辖权,驳回其起诉。
(二)国家豁免
1.国家豁免原则及其新发展
国家豁免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及其财产免受其他国家国内法院的司法管辖。(32) 作为一项古老的国际法原则,国家豁免一直以来都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奉行和遵守,至少各国在公开场合都不否认。
传统上各国一般都主张绝对豁免,但现在都主张限制豁免。2004年,联合国通过了《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也采取限制豁免立场。它在肯定国家豁免作为一般原则的同时,作出了对国家豁免加以限制的具体规定,规定国家从事主权活动享有管辖豁免,但国家从事商业活动,则不能享受豁免,其他国家可以行使管辖权。公约较好地解决了保护国家利益与保护私人利益两者之间的平衡问题。公约第10条第1款规定,“一国如与外国一自然人或法人进行一项商业交易,而根据国际私法适用的规则,有关该商业交易的争议应由另一国法院管辖,则该国不得在该商业交易引起的诉讼中援引管辖豁免”,以保护私方当事人在合同或交易中的正当利益。同时,为避免外国私方当事人对一主权国家滥用诉权,公约特别强调“一国应避免对在其法院对另一国提起的诉讼行使管辖”。对另一国提起诉讼,不仅是“被指名为该诉讼当事一方”,而且也包括“该诉讼实际上企图影响该另一国的财产、权利、利益或活动”。
可以肯定的说,虽然现在主张限制豁免的国家越来越多,但任何国家无论如何都不应以限制豁免为借口而对国家的主权行为进行管辖,不能受理、审理当事人针对国家主权行为提起的诉讼,应当制止当事人滥用诉权的行为。
2.外国国家元首与政府官员的豁免
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国司法实践中,美国法院认为,尽管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豁免适用于个人,甚至包括国家元首,但法院在判例中已经指出,豁免适用于在自己权力范围内行使权力的外国官员。(33) 正如美国法院在判决中所指出的,《外国主权豁免法》并没有规定外国元首的豁免,而是规定国家的豁免,因此法院就只好根据1976年之前的实践来作出判断,也就必须考虑行政部门的意见。(34) 在1976年以前的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认为:“行政部门对豁免的意见是最终的,应该为法院所遵守,不受法院的司法审查。”(35) 在1945年的“Republic of Mexico v.Hoffman”一案中,美国法院认定“法院并不拒绝政府认为合适的豁免理由,即使原来不承认某些豁免理由,但如果现在承认了,我们法院也不拒绝”。(36)
对于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官员授予豁免,这既是国际礼让的要求,也是国际法中国家豁免原则的应有之意,更是《外国主权豁免法》的可以推定出来的精神。如果毫无限制地允许对行使权力的外国官员提起诉讼,这无异于减损外国主权豁免,毕竟《外国主权豁免法》是阻止直接对外国主权提起诉讼的。(37)
虽然美国法院承认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官员享有豁免,但却认为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官员的私人行为不能享受豁免。至于是否授予豁免,通常关键的问题是判断该外国官员是以个人身份行为还是作为政府官员行使权力的行为。(38) 对此问题,要考虑一个针对外国官员的诉讼是否“仅仅是一个对其所代表的国家的伪装的诉讼,因而实际上等于直接对主权提起诉讼”。在“Park v.Shin”一案中,第九巡回法院裁定,关键看是否会因此而干涉了雇佣该官员的外国的主权或者政策制定权。(39) 此外,美国法院还认为如果外国官员超越了其权限,那么就是个人行为,就不适用于《外国主权豁免法》,也就无权享受豁免。(40) 即使在起诉时仍然在任也不例外。(41)
至于如何判断外国官员的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在其权限内,不应根据所谓的国际法或者法院地法来判断,只能根据该国的国内法来判断。因此,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被判不能享受豁免,因为其行为不是根据作为菲律宾总统的权力作出的。马科斯虽然是总统,但并不是国家,也必须遵守适用于他的法律。(42)在“Trajano v.Marcos”一案中,马科斯夫人也不能享受豁免,因为她承认是擅自行事,而不是根据菲律宾法律。(43)
主权豁免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授予主权者免于被诉的权利,(44) 如果根据国际法或者法院地法来判断外国主权者的行为是否合法,那么就必然需要实体审理,而这与免予被诉的目的和意义相背。(45) 因此,在“Siderman de Blake v.Republic of Argentina”一案中,第九巡回法院甚至裁定即使违反国际人权法的强行法也不减损《外国主权豁免法》对外国主权的豁免。(46) 在“Sampson v.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一案中,美国联邦第七巡回法院认为,违反国际强行法并不是《外国主权豁免法》规定的豁免例外,也即是说,即使外国违反了国际强行法,仍然可能享受豁免。(47) 当然如果损害发生在美国境内则除外。(48)
在实践中,必须要注意的是应准确适用、解释外国法,以免歪曲外国法的内容而视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其本国法,并以此为借口不授予豁免。对于外国官员的行为的判断也必须慎重,不能以此为借口侵犯别国主权和内政。
3.豁免的主动授予
虽然美国法院不时受理针对外国国家、国家元首、政府官员、国家财产的起诉,但实践中法院也可能是依职权审查是否涉及国家豁免。在美国宪法的传统上,法院根据“政治问题理论”一般不会对政治问题进行司法审查,表现在国际民事诉讼中,由于可能影响外交关系,不利于行政部门解决对外交往这样的“政治问题”,所以法院也会主动审查主权豁免的问题。即使外国被告没有出庭抗辩,对诉讼不理睬,法院仍然可能以国家豁免而裁定没有管辖权,宣布撤销案件。
虽然《外国主权豁免法》结束了“双轨制”,把国家豁免问题的决定权完全转移到法院,但美国国务院不涉足外国国家豁免问题并不是绝对的。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在1976年11月2日致司法部长的信表示,美国国务院对于在法院诉讼中涉及美国重大利益的外交关系问题仍将以“法庭之友”的身份进行干预。(49) 实践中,美国国务院会出具一个利益声明,宣称法院如果行使管辖权可能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对外关系、国家利益产生影响,要求法院撤销案件。
(三)小结
虽然当事人享有诉权,但故意对享有管辖豁免权的主体提起诉讼,是滥用诉权的表现。各国法院对这种滥用诉权的行为应该有所抑制。它们应该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遵守公认的国际行为准则,主动地审查管辖豁免的问题,不受理当事人滥用诉权的案件,以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的企图得逞。
四、结语
随着国际民商事交往越来越频繁,国际民商事争议越来越多,当事人滥用诉权、挑选法院的机会和可能性也在增加。如何从管辖权的角度防止和消除当事人滥用诉权,以避免不必要的司法困扰,就成了一个在国际民事诉讼中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诉权的行使涉及送达、管辖权冲突、外交特权与豁免、国家豁免等问题,在实践中,对于当事人滥用诉权还是有一定限制的,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加以制止。当然,问题的关键是除了当事人不要滥用诉权以外,各国法院也要从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国际合作、国际礼让以及公平正义等的角度出发,恰当地行使管辖权,这样既能降低本国司法成本,节约本国司法资源,也是对当事人、其他国家负责任的态度,有利于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愿诉权正当行使!
注释:
① See Michele Taruffo,Abuse of Procedural Rights:Comparative Standards of Procedural Fairness,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9.
② [美] Robert C.Casad:《论美国民事诉讼中的管辖权》,刘新英译,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4期,第110页。
③ Sec Nathan Levy,Jr.,“Mense Process in Personal Actions at Common Law and the Power Doctrine”,78 Yale LJ.52,58 (1968).
④ Hart v.Granges,1 Conn.154,168 (1814).
⑤ Vinal v.Core,18 W.Va.1,20 (1881); Roberts v.Dunsmuir,75 Cal.203,204,16 P 782 (1888); Smith v.Gibson,83 Ala.284,285,3 So.321(1887); Savin v.Bond,57 Md.228,233 (1881); Hart v.Granger,1 Conn.154,165 (1814); Mussina v.Belden,6 Abb.Pr.165,176 (N.Y.Sup.Ct.1858); Darrah v.Watson,36 Iowa 116,120-121(1872); Baisley v.Baisley,113 Mo.544,549-550,21 S.W.29,30 (1893); Bowman v.Flint,37 Tex.Civ.App.28,29,82 S.W.1049,1050 (1904).See also Reed v.Hollister,106 Ore.407,412-414,212 P.367,369-370 (1923); Hagen v.Viney,124 Fla.747,751,169 So.391,392-393 (1936); Vaughn v.Love,324 Pa.276,280,188 A.299,302 (Pa.1936).
⑥ Burnham v.Superior Court,495 U.S.604,109 L.Ed.2d 631,110 S.Ct.2105 (1990).
⑦ 70F.3d 232 (9th Cir.1995)).这种管辖权依据是否合理,值得探讨和研究。
⑧ Henderson v.United States,517 U.S.654,672,116 S.Ct.1638,134 L.Ed.2d 880 (1996).
⑨ United Food & Commercial Workers Union v Alpha Beta Co.,736 F.2d 1371,1382 (9th Cir.1984); Chan v.Soc'y Expeditions,Inc.39 F.3d 1398,1404 (9th Cir.1994); Mullane v.Cent Hanover Bank & Trust Co.,339 U.S.306,314,70 S.Ct.652,94 L.Ed.865 (1950).
⑩ Rio Props.,Inc.v.Rio Intern.Interlink,284 F.3d 1007 (9th Cir.2002).
(11) See Errion v.Connell 236 F.2d 447,457 (9th Cir.1956); Novak v.World Bank,703 F.2d 1305,1310 n.14 (D.C.Cir.1983); Doe v.Karadzic,1996 WL 194298 (S.D.N.Y.Apr 22,1996); Trujillo v.Trujillo,71 Cal.App.2d 257,162 P.2d 640,641-42 (1945); In re Ball,2 Cal.App.2d 578,38 P.2d411.412 (1934).
(12) 792 F.Supp.215 (S.D.N.Y 1992).
(13) 120 U.S.App.D.C.288,345 F.2d 978,980-81 (D.C.Cir.1965).
(14) 也有学者翻译为“司法霸权”,参见杨良宜、杨大明:《禁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0页。See also,Donald J.Carney,“Forum Non Convenie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3 Buff.Jour.Int'l L.117,131 (1996).
(15) 参见蔡彦敏:“论国际民事诉讼的管辖权”,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5期,第118页。其中列举了六种观点,作者本人也提出了一种观点。
(16) 黄进主编:《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638页。
(17) 刘力:《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页。
(18) 袁泉:《不方便法院原则三题》,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6期,第141页。
(19) 徐卉:《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
(20) Gulf Oil Corp.v.Gilbert,330 U.S.501,508,91 L.Ed.1055,67 S.Ct.839(1947).
(21) See Piper Aircraft Co.v.Reyno,454 U.S.235,254,70 L.Ed.2d 419,102 S.Ct.252(1981).
(22) 参见徐伟功:《学术视野中的不方便法院原则》,《东方论坛》2003年第3期,第83页。
(23) See ICC Indus.v.Isr.Disc.Bank,Ltd.,170 Fed.Appx.766(2006); Carey v.Bayerische Hypo-Und Vereinsbank AG,370 F.3d 234(2004).
(24) See Iragorri v.United Technologies Corp.,274 F.3d 65,75(2d Cir.2001)(en banc).
(25) 参见徐卉:《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178页;杨良宜、杨大明:《禁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2—493页;刘卫国:《英美民事管辖制度中的‘禁诉令’评析》,载《美中法律评论》2005年第4期,第36页;欧福永:《论中国对禁诉令的利用与应对》,载《中国国际私法学会2006年年会论文集》,第673—675页。
(26) 参见欧福永:《论中国对禁诉令的利用与应对》,载《中国国际私法学会2006年年会论文集》,第673—675页。
(27) See United States v.Lumumba,741 F.2d 12,15 (2d Cir.1984).
(28) United States v.Enger,472 F.Supp.490,506(D.N.J.1978).See also Tabion v.Faris Mufti,73 F.3d 535,536(4th Cir.1996)(外交豁免给予苏丹大使馆的一秘和顾问);Logan v.Dupuis,990 F.Supp.26,26(D.D.C.1997)(外交豁免给予加拿大常驻美洲国家组织代表团的代表);Fatimeh Ali Aidi v.Amos Yaron,672 F.Supp.516,516(D.D.C.1987)(外交豁免给予以色列大使馆的军事参赞).
(29) 995 F.Supp.1469,1470(S.D.Fla.1997).
(30) 665 F.Supp.793,799(N.D.Cal.1987).
(31) 741 F.2d 1328,1329(11th Cir.1984).
(32) 参见龚刃韧:《国家豁免问题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1页;黄进:《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33) Chuidian v.Philippine Nat'l Bank,912 F.2d 1095,1103,1106—1107(9th Cir.1990).
(34) United States v.Noriega,117 F.3d 1206,1212(11th Cir.1997).
(35) Spacil v.Crowe,489 F.2d 614,617(5th Cir.1974); Isbrandtsen Tankers,Inc.v.President of India,446 F.2d 1198,1201(2d Cir.1971); Rich v.Naviera Vacuba S.A.,295 F.2d 24,26(4th Cir.1961); Ex Parte Republic of Peru,318 U.S.578,589,87L.Ed.1014,63 S.Ct.793(1943); Compania Espanola de Navegacion Maritima,S.A.v.The Navemar,303 U.S.68,74,82 L.Ed.667,58 S.Ct.432(1938).
(36) 324 U.S.30,35,89 L.Ed.729,65 S.Ct.530(1945).
(37) Chuidian v.Philippine Nat'l Bank,912 F.2d 1095,1102 (9th Cir.1990).
(38) Chuidian v.Philippine Nat'l Bank,912 F.2d 1095,1106 (9th Cir.1990).See e.g.,Jungquist v.Sheikh Sultan Bin Khalifa Al Nahyan,115 F.3d 1020 1028 (D.C.Cir.1997)(认为是个人行为,不能享受豁免);Doe v.Bolkiah,74 F.Supp.2d 969,974 (D.Haw.1998)(认为是职务行为,授予豁免).
(39) 313 F.3d 1138,1144 (9th Cir.2002).
(40) United States v.Yakima Tribal Court,806 F.2d 853,859 (9th Cir.1986); Chuidian v.PhilippineNat'l Bank,912 F.2d 1095,1106 (9th Cir.1990);Re Estate of FerdinandMarcos,Human Rights Litig.25 F.3d 1467,1472 (9th Cir.1994).
(41) Cabiri v.Assasie-Gyimah,921 F.Supp.1189,1198(S.D.N.Y.1996).
(42) Re Estate of Ferdinand Marcos,Human Rights Litig.25 F.3d 1467,1471 (9th Cir.1994).See also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v.Marcos.862 F.2d 1355,1362(9th Cir.1988).
(43) 978 F.2d 493,498 (9th Cir.1992).
(44) El-Fadl v.Cent.Bank of Jordan,75 F.3d 668,671 (D.C.Cir.1996).
(45) Id.
(46) 965 F.2d 699,717—718 (9th Cir.1992).
(47) 250 F.3d 1145,1149—50 (7th Cir.2001).相似的结论,See Smith v.Socialist People's Libyan Arab Jamahiriya,101 F.3d 239,244 (2d Cir.1997);Princz v.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307 U.S.App.D.C.102,26 F.3d 1166,1173 (D.C.Cir.1994);Siderman de Blake v.Republic of Argentina.965 F.2d 699,719(9th Cir.1992).
(48) Letelier v.Republic of Chile,488 F.Supp.665,672(D.D.C.1980).
(49) 黄进:《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