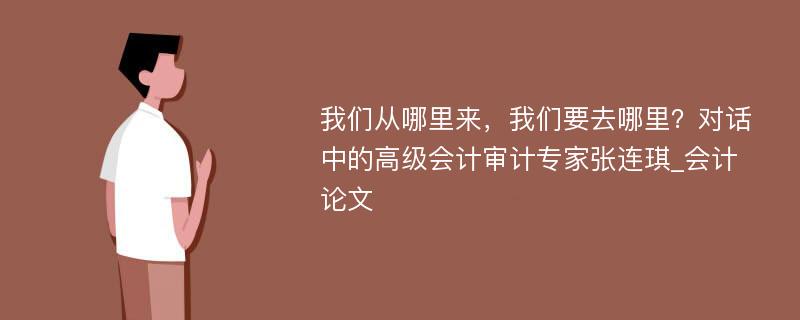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对话资深会计审计专家张连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哪里去论文,会计论文,专家论文,从哪里论文,张连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篇)知所先后 则近道矣
《中国会计报》:您怎么认识回顾会计六十年变迁的现实意义?
张连起:我始终认为如果不了解走过的路,就不知道现在为何这么走以及将来该如何走。还是那句话:不管走多远,都应知道出发点在哪里。
正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站在新中国成立60年和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这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中国会计要寻找发展坐标,必须首先要梳理历史,认清历史,准确把握新中国会计60年的思想史、挫折史、中兴史。
建国初期(1948~1957年)扔掉西方的,贴近苏联的,传承自己的
《中国会计报》:建国初期我国会计学的发展呈现怎样的特点?
张连起:在清理旧有思想的同时我们也曾放弃过会计所蕴含的合理内核,那是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百多年的会计结晶。
新中国成立伊始,1950年1月和3月,著名的民主人士章乃器先生在上海《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应用自己的会计簿记原理记账》、《再论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在会计界发生思想的萌动?我想这充分说明了会计服务经济社会的特性,会计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游离于经济发展之外。
在当时经济向苏联“一边倒”的形势下,章乃器先生主张首先要继承和发展我们自己的会计记账方法,收付记账法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而外来的借贷记账法就不是民族的、大众的,也不够科学。
这种说法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也有很多人发表文章进行讨论。两种观点并存:一个是新的、西方的,一个是旧的、中国的,究竟哪个好?见仁见智。后来争论被搁置了,不过,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会计界除旧布新的最先举动便是“讨伐”西方会计记账方法。
1951年以后,我国全面引入苏联的会计理论和方法。这种“引入”首先是通过翻译大量教材并在报刊上进行宣传。其中马卡洛夫的《簿记核算原理》影响颇大,甚至于奠定了后来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会计学的思想基础。这本书认为社会主义会计和资本主义会计有本质不同,并提出了阶级性是会计的一个显著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的邢中江和黄守宸两位教授发表《怎样建立新中国的会计基础》一文指出,旧中国的会计完全是模仿和抄袭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的会计理论是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会计和资本主义会计有很多区别,社会主义会计的定位,是为国家预算做服务的,体现在会计方法、目标、资金运作方式等各个方面。他们的思想上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会计界的主流思潮,与苏联专家是完全趋同的。
当时的中国会计界有一种“终于将西方那一套东西扔一边了”的解脱,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会计学发展的特征可以用三个动词概括:一个是“扔”——扔掉西方的;一个是“贴”——贴近苏联的;一个是“传”——传承我们原有的会计方法,使之成为“民族的、大众的”,而阶级性的讨论则贯穿其中。
“大跃进”“文革”时期(1958~1976年):大力简化,意识形态至上
《中国会计报》:这种非常时期,我国的会计学发展又呈怎样的变化?
张连起:或许只有非常时期才能看出会计的嬗变,非常时期产生非常会计思想。
我收集了一部分大跃进时期的会计类杂志和书籍。那时候的人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们走在大路上”,“一天当一百天”,“赶英超美”。这种思想必然要在会计学的发展上投射出影子,那就是简化会计。
会计要怎样跃进呢?首先是破除迷信。1958年《工业会计》的一篇社论指出,会计人员的迷信是很深、很多的,迷信外国、迷信书本、迷信制度、迷信专家,这种迷信一定要破除,才能解放思想。
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当时的破除并不是建立在对会计学发展规律的全面把握之上的,而是盲目的破除。当时人们主张,只要又红又专,高小毕业——基本上等同于现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水平——就可以当核算员,并被称为“人民的核算员”、“红色核算员”。
其次是大力简化。不光在会计领域,在别的方面也一样,人们主张突破一些旧有的思想观念和旧规则,所以就导致了快速的会计简化。原来财政部规定的报表有十几种,后来就变成了只有一张。科目也由原来最多的1000多个简化为66个,这还只是我查阅文献掌握的数据,当时有的报表中的会计科目可能更少。
许多不可思议的现象发生了,比如“以表代账”、“无账会计”,只要表单车间可以用,群众核算可以用,就是革命的会计。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性,鼓励工人参与财务核算,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色。
《中国会计报》:“文革”时期的情况怎么样?
张连起:“文革”时期,某些会计人员被认为是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典型,被下放劳动。会计工作,我了解的很多事情就是“混乱”和“瘫痪”。那时候“利润”这个词基本上不能提,成本管理、费用管理倒可以提,叫节约。与之对应,会计也有好多语录,比如“为了中国革命,节约每一个铜板。”
其实节约也就有利润,但不能提利润,因为利润是资本主义的,是“封”“资”“修”的,这也直接导致了会计的意识形态至上。
在上世纪70年代,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有些企业“三不记”:不记利润、不记奖金、不记成本。
从“大跃进”到“文革”,不少企业只有一张表,叫资金平衡表。这张表一边是资产,一边是基金。现在的会计平衡等式是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那时是资金来源等于资金占用。
例如购入固定资产,现在是用企业拥有的现金直接去买,记一笔“借:固定资产,贷:银行存款”即可,那个时候不是这样,“打油的钱不能打醋”,购置固定资产相当于财政支出,要专户核算。会计科目记成“借:专用基金——更新改造资金,贷:专项存款”,同时还要做一笔“借:固定资产,贷:固定资产基金”,也就是基金会计。
别以为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它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核算制度——计划经济以及“大一统”经济的特点,企业的自主权很小,会计核算是为国家核算。那时会计所能做的,集中在勤俭节约、“节约闹革命”这些宏大命题上。
新时期(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鱼傍水活水傍鱼
《中国会计报》:您怎样概括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这段时期的会计学发展?
张连起:新时期会计30年,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经济的改革必然导致会计的改革,开放的经济必然产生开放的会计,这从一系列变化中表露无遗。
“文革”使会计发生历史性断层,改革开放伊始即对建国初期的议题继续讨论,包括记账方法、会计属性、会计职能等等,可谓百家齐鸣。
计划经济时期的会计观认为,会计就是为社会主义企业、机关事业、信贷系统和各级预算单位服务,可以简单概括为六个字:记账、算账、报账。会计被简单地框入一种管理工具。
新时期的会计不再定位于单一的管理工具上,出现了两论并立的格局。一种观点认为会计是信息系统。另一种观念认为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两论”无高下之分,只是切入的角度不同,均丰富了会计的思想内涵,也对会计的属性做了一次厘清。其间,不少学者还明确提出会计没有阶级性,从而预示着会计不再成为政治的“婢女”。
这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会计人思想解放运动的一次接续。这种接续使得中国会计走出了一个完美圆环。1978年12月份之后,共和国告别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会计于是抛掉了自身的束缚,还原了应有的本色。经济是文明之子,会计乃经济之子,故会计乃文明之孙。会计紧随文明的进步,它与经济社会发展,完全是鱼水关系:鱼傍水活水傍鱼。
随着会计之门的打开,我们开始进行大量的补课,而之前我们中途逃学了,很多课没有上。于是,会计界开始大量引进西方会计的一系列思想、方法,从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没有选择权、不需要职业判断,到适应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需要、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报告纳入准则模式和专业判断平台;从“与国际会计协调”、“与国际会计接轨”到“与国际会计趋同、等效”,中国会计果断地采取了“拿来主义”,尽管免不了有时“跛足”,但这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阶段。
我常常在静静的午夜神驰于会计的忧患:如果说历史上中国会计错过一些机遇,那么,今天的我们到了把握战略机遇、构建充满生机的中国式会计理论与实务大厦的时候了!
(中篇)以史为鉴 思进图变
《中国会计报》:通过回顾上述几个时期的历史,我们能从中得到哪些启示?
解放思想仍任重道远
张连起:60年前,中国的会计形态是多极化的。大银行采用借贷记账法,老商号采用收付记账法,其实无所谓谁先进、谁落后。而建国初期的会计论争充分反映了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变迁下人们对会计本质的理解,这让我们意识到,会计内涵是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而变化的。
综观60年新中国会计的发展道路,直接复古不行,全盘“苏化”不行;全盘西化不行,唯“美”是从也不行。就像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样,我们也要着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实务体系,这看似一个普通道理,但这对于重塑中国会计战略大目标是不可或缺的。
至于阶级性的讨论,我想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那些具有独立精神的学者。陶德,便是其中之一。时任新华书店总会计师的他,在1951年提出“会计没有阶级性”,这一刊发于《新会计》杂志的观点在那个阶级分明的时代,可谓石破天惊。当时的一重量级媒体曾撰文批判说:那种认为会计没有阶级性的观点和论调是很荒谬、很危险的。
此后,陶德最终没能幸免于特殊时期的各种打击、迫害。不过也恰是陶德这样的一批学者让我们看到了会计界真正的思想家。“阶级性”的枷锁禁锢了会计界30年,现在还不能说会计摆脱了所有精神枷锁,会计界的思想解放仍任重道远。
会计不是政治,但为政治所深深影响
张连起:“大跃进”和“文革”时期,会计的背后往往是政治。此时会计的“道”不存在了,“术”也随之失去方向——这里的“术”是会计核算方法。有些企业就一本账,既是总分类账又是明细账,大致把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等分分类就可以了,尽管当时财政部也有核算要求,但在企业那里被废止、停顿。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斗争就是一切的时代,“核算无用”、“三年不算账也跑不到国外去”等一些论调很有能量。人们不可能将心思放在精细核算上,核算自然也成不了体系。填写表单也只是为了统计工作量,侧重于实物量,而不侧重背后的交易行为以及收益概念。
“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对会计发展的抑制是毫无疑问的。企业会计只是国家的一个出纳,没有自主性,而一旦企业没有了作为独立核算主体的地位,会计的许多功能也自然被剪裁了,这尤其值得反思。
我以为,会计与政治的关系值得研究。“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样本。现在说会计服务经济社会大局,没有说服务政治。而在“大跃进”尤其是“文革”时期,会计是典型的服务政治,因为政治就是一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为纲对会计的影响极为深远,会计不是政治,但被政治所深深影响。
会计发展不需要革命
张连起:特殊时期的“以表代账”等现象,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它有历史的规定性,我们应站在更高的层次去看这问题。
当时的破除迷信是浅层次的,就像“文革”前“破四旧”一样,还没对中国文化有彻底的了解,简单地把糟粕和很多精美的艺术品一起砸了,会计在“大跃进”时期就是走的这条路。
我们要从中反思,会计发展不可能没有新旧转化,但不需要大破大立,不需要革命。我们经历了很多革命,建国初期是“革”旧中国的命。会计发展要走渐进改良的道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会计,告别革命!
(下篇)以道驭术 发展唯实
《中国会计报》:如何评价上世纪20、30年代这个特殊的会计发展期?
张连起:早在1949年之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很丰硕的实务研究成果,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代表人物。19世纪20年代,中国会计界有两位不能忽略的代表人物,如今在美国的大学图书馆和国会图书馆里能找到他们的论文,当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都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的名字是:杨汝梅和陈焕章。我们可以遗忘掉许多名字,但这两位会计大师的名字应该被永远铭记。
杨汝梅的英文著述《无形资产论》在当时国际会计界引起很大反响,直到现在都有重要研究价值,其中译本后由潘序伦事务所出版。中国第一个理财学博士陈焕章撰写了《孔门理财学》,他引用《易经系辞》的话“理财正词,禁民为非曰义”,旨在说明理财的目的是达到公正,防止肆意舞弊。他首次提出理财的正解即公平正义、防范财务舞弊。他们为现代会计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学养和丰硕的实务成果。
在他们之后又出现了谢霖、潘序伦、顾准、徐永祚等大师先贤,这些先生的思想都与彼时的西方会计界保持同步呼吸,甚至独领风骚。每每想起他们,我都感到深深的愧疚。
《中国会计报》:您认为我们以后的路怎么走?
张连起:一点浅见是,我们需要站在新中国会计60年这个坐标上,继奇花之往,开异彩之来。我们有过全盘苏化的教训,有过阶级斗争的挫折,也有过解放思想的振兴,还有唯“美”是从的反思。
会计是具有思辨性和不确定性的。在梳理、回顾和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会计发展史的基础上,确认中国会计发展的大目标,建立中国特色会计理论与实务体系已经迫在眉睫。因为没有指引就没有方向,我们就可能迷失在喧嚣和嘈杂中,迷失在抱残守缺和一叶障目中。
我和国内许多有造诣的学者、专家讨论的时候,经常听到的是“老美怎么怎么说”云云,随手翻翻会计文献、准则,就会发现到处都是硬译、硬搬、硬植,既没搞明白人家的规范背景,也没搞清人家的对象土壤,更没搞清人家的体质类型,一味拿来,榫不对榫,卯不对卯。
当前,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加新兴市场的经济体,出现了许多自己独有的经济现象,如多种经济成分的改制、互融、并购、重组等等,而所有这些又都衍生出了相应的会计问题。这些会计问题的解决多依赖实务界的摸索,整个过程缺少科学理论的指引。
以道驭术,道不远人。当代会计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如今剧烈变革的发展时期,我们应充分利用机会调整自己的会计“肌体”,真正告别喧嚣、浮躁、物质主义与实用主义。
我以为,找出中国特色会计发展之道,要坚持“三不一实”: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外、只唯实。中国会计究竟应该有怎样的哲学观,有怎样的战略观,有怎样的发展观,有怎样的运动观,有什么危机观,这些会计之“道”应首先被确立。所谓以“道”驭“术”,“道”的问题解决了,会计政策怎么选择,会计估计怎么形成、会计核算方法怎样选择也就顺理成章。“化而裁之谓之变,举而措之谓之通”,“道”一通,一通百通。这也是我左手捧读国内外会计审计准则、右手捧读中华文化经典所得出的初步结论。
《中国会计报》:在您看来,具体方向和步骤大致应有哪些?
张连起:首先要确立一个新战略观,也就是大的发展目标。对于理论界而言,不应醉心于做那些看上去很漂亮,但对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没有实际价值的论文,而应多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问题,比如说分配的公平和效率、结构性减税、国有企业改制中的资产计价、产业结构转型和创新型企业价值问题等等。这些领域虽有人涉及,但没有形成体系,或者只是单纯的搬来西方理论,没有结合中国实际做对策研究、案例研究。
我看到的不靠谱的文章太多。“没有会计学家”的说法也不是危言耸听。不少会计学者孤芳自赏,用一堆所谓的数字模型求证出一些令人云里雾里的结论。实证研究固然重要,但实务研究也不是雕虫小技,认为实务研究不入流的观点其实也不入流。我以为,只有确立新的战略观,才能真正确立“中国特色会计的理论与实务体系”。
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似乎回避“中国特色”这个词,认为它是保守的、是封闭的、是“土会计”,其实不然。要避免会计领域的南橘北枳现象,必须确立“中国特色会计理论与实务体系”,这不是为了跟风和卖弄,而是在深入研究国际会计准则“俱乐部化”和国际会计“抱粗腿化”的必然结果。中国会计的发展利益不会由别人争取,中国的大国地位决定了会计应有独立的声音。会计发展方向不应由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体指定。
其次,要建立新的“优术”观。“明道而优术”,不仅要道路明晰还要“优术”。重大会计政策、重大会计估计等会计方核算方法等都应优化、固化,并形成体系。以目前经济形势的迫切性,我们太应该将此做成集成化、系统性工程。
新“优术”观告诉我们,要每时每刻进行检讨和反思。国际金融危机给会计带来的新课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迫、都深广,金融工具的属性、生态体系以及系统性风险等都是值得会计界开展深度研究的。
值得一提的是,有那么一个时期,会计学者和专家,纷纷走近车间,走近成本管理第一线,走进会计实务第一线。这种走近,不仅仅是简单体现生活,而是发现实务中的问题,并寻找对策,总结成理论继而指导实践,打通了实务和学术之间的“墙”。这就是可贵的传统。
再次,要确立新危机观。标志是“萧条会计学”的建立。经济危机和风险是相伴而行的。原来我们对经济周期研究太少,会计运行的周期理论研究不够。之所以提出危机观,是因为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重视强化财务会计,经济低潮时孕育发展高潮。
新危机观包括许多要素,比如要“去存货化”,要进行现金流量管理,要推进并购重组以及根据企业周期特点调整财务战略等。
总之,建立新战略观、新优术观、新危机观是中国特色会计体系的大目标。除此之外还包括新哲学观、新价值观等,从而构筑一个总系统、“大屋顶”。
《中国会计报》:构建这样的总系统是否需要很长时间?
张连起:“人”字,阳刚的一撇,阴柔的一捺。一个伟大目标的实现最终还是要归结到“人”的身上。当前,企业财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跟企业现在规模的发展,跟国家推动一系列的调控政策、振兴规划差得太远了。我们需要橄榄形人才结构,让更多的人拥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和广阔视野。但是,包括注册会计师在内的高端人才可能没得到重用,“千里马拉磨”的现象还时有存在。
财务会计与企业发展战略、核心竞争力、企业的寿命周期等很多方面相关。也就是说,财务人员不了解企业发展战略,不了解一些金融知识,不了解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很难做出正确的应对策略。
有人片面强调会计地位,我觉得“有识才有为,有为才有味”。这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新价值观。所谓“有识”,就是财务与业务要整合,把握相关生产流程、业务流程,投融资过程等,继而进行流程再造、优化管理链条、改善融资环境等。
有人埋怨财务会计在企业中的作用、职能没得到充分发挥,这当然因人而异,而且一定要明白这样的道理——财务永远就是财务,不可能因为重要就可以取代其他职位。
做会计有3种境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目前大多数人还在第一层次徘徊,被动反映、被动核算、被动应付。进入第二境界的会计人已是凤毛麟角,进入第三层境界的会计人能有几稀?
确立中国会计发展大目标,是当代中国会计人共同的历史使命和战略使命。这个“道”就是天道,而我们则要走在大路上、正路上,替天行道。
在“大会计”语境下,每一个管理者、监督者、实务工作者、学术研究者,都应该为中国会计大目标而努力。如此大的系统工程,可能不是这一代人所能完成,它需要几代人生生不息的努力。但我想,谁让你叫“会计”呢,既然做了会计,就只能向着远方的地平线;纵然没有远方,也只能留下背影。
标签:会计论文; 中国会计报论文; 会计职业论文; 财务与会计论文; 大跃进论文; 财会论文; 中国特色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