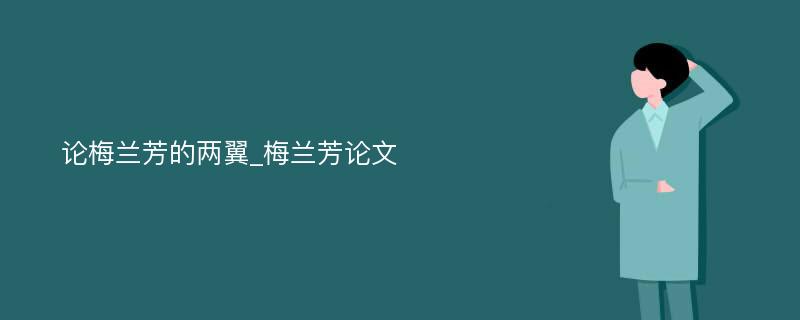
论梅兰芳的两个翅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梅兰芳论文,翅膀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在他所创办的国际大学的座右铭上,曾引用这样一行古老的梵文诗:“整个世界相会在一个鸟巢里。”言简意深,显示出人类社会自从20世纪以来“世界精神”越来越成为文化主潮。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梅兰芳访美演出,把根据“世界的需要”做了一番改革的中国京剧介绍给西方世界,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电影由于汲取东方营养,造成所谓“双向影响”。如一位美国评论家所云:“梅兰芳的艺术无疑超越了东西方之间所存在的障碍。”这就构建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以此为正式开端,梅兰芳已经不仅仅是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了,他毫无愧色地属于了全世界,成为进入世界这个“鸟巢”的一只东方“金凤凰”。
梅兰芳何以能取得这样的世界效应?仅仅因为他那古典美的华夏魅力吗?抑或因为他那含蓄美的东方人格吗?不是,不完全是。重要的在于:梅兰芳借助了他的两个翅膀,才得以腾飞于世界艺术之林。
所谓“梅兰芳的两个翅膀”,一曰:齐如山的“中国的世界观”,一曰:张彭春的“世界的中国观”。前者是从中国出发,了望世界的一种思路,它恪守本色,唯属守本色,才向外部世界展示。这是强烈的民族精神。后者是从世界出发,回眸中国的一种思路,它坚持开放,唯坚持开放,才在内部世界改革。这是雄阔的世界意识。两翼共振,完成了梅兰芳独特的文化发展战略:中国京剧进入世界。
齐如山,一位“国剧”通。民国元年,因看梅兰芳的《汾河湾》提出长篇意见为梅氏所尊,从那时开始“傍”梅。齐如山编写了《嫦娥奔月》、《天女散花》等系列梅剧,人称“中国的莎士比亚”,这时,齐如山的创作,就有了两种宗旨,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一是为梅叫座:一是想借此把国剧往世界去发展。”
这个“把国剧往世界去发展”的思路,便是齐如山的“中国的世界观”。
人中国出发,了望世界,齐如山主要做了这样的贡献:(一)自民国四年编创《嫦娥奔月》以后,强化了古典歌舞的意韵,引起外国人的兴趣,以致使“观梅剧”成为外人游华的一大内容,与游长城并列。(二)用了7年左右的时间,做出国舆论准备,包括诸如《中国剧之组织》的撰写。(三)为访美筹款,变理想为现实。
从中国出发,了望世界,齐如山并不偏狭。他曾几次去过欧洲,看了不少西洋戏,并有所研究。根据自己的座右铭“不由恒蹊”(即:“不走别人常走的路”)齐如山总结国剧的基本原理为:“无声不歌,无动不舞”,这就为中国京剧在理论上确立了自己的特色并与西洋话剧、歌舞剧划清了界限。他恪守这个本色,在对外国人虽不懂中国歌、舞的意义却感兴趣的事实做了一番调查研究之后,认为可以到国外展览我们的国粹。与众不同,世人都认为是梅兰芳到美国演出,而他却始终坚持这是:中国剧往外发展。他是“梅党”中坚,但他绝不把梅兰芳等同于中国剧。
在到了美国“应该怎样演法”上,齐如山的观点是:“一切照旧”,是:“拿中国戏,给外国人看”。他坚信“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国剧自能赢得洋人欢迎,采取了以不变应万变的方略。当然,象脸谱、髯口之类“一点也没有更动”,这决非什么“守旧”。只是,齐如山举了一个例子:“与我们同时到美国的有一个日本戏班,他登的广告是:‘我们这是极合于美国人眼光的日本戏’,对此一句话,就完全失败了。”我们相信这个范例,因为它过分迁就了外国人。却不能引申出来:我们可以根本无视人类文化环境的变迁以及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异。面对变化了的文化环境以及观众群,我们不需要一种应变的能力吗?
假如事情仅仅到此为止,那么梅兰芳会因齐如山而留下若干缺憾。然而,梅兰芳是幸运的,恰恰在这样的时候,张彭春出现在梅兰芳的面前。张彭春的出现,完成了齐如山所不能完成的历史使命,使梅兰芳可能留下的缺憾得到及时的弥补。
张彭春,何许人也?
一位天津老乡亲。他曾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与耶鲁大学研究教育与戏剧。1916年张彭春初自美国归来加入南开新剧团执导其第一批剧目《醒》与《一念之差》。为中国话剧第一导。1929年后,张彭春赴美讲学,行前曾赠曹禺一套英文版的《易卜生全集》,对那位后来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的大剧作家起了“导师”的作用。
奇迹在于:正是这位中国话剧第一导竟与梅兰芳结下不解之缘,再度出任梅兰芳访美、访苏演出总导演,助梅在中外艺术交流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以致梅兰芳评价他:“干话剧的朋友,很少真正懂京剧,可是P·C·张却也是京戏的大行家。”中国京剧本无导演制,有之,则实由张彭春起。我们完全可以说:张彭春是中国京剧第一导!
1945年,张彭春在重庆南开中学的一次演说里曾经做过这样高屋建瓴的论述:“在演作技术上,世界戏剧感到自己技术的死板,受写实主义的束缚,而中国戏剧在这方面,可给我们不少刺激的参考。”“中国的戏剧,如何才能得到世界地位,决不是闭门自诩可成的,必须注意到世界的需要。”
这个中国戏剧“必须注意到世界的需要”的思路,便是张彭春的“世界的中国观。”
从世界出发,回眸中国,张彭春主要做了这样的贡献:(一)据美国的一部《中国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称:“梅兰芳于1930年赴美上演,张彭春自动出任梅剧团总管及发言人,向完全不懂中国戏剧传统及技巧之美国观众解释梅剧之意义。”(二)经张彭春加工的编剧,回国后基本定型,成为范本。(三)如马明先生在《张彭春与中国现代话剧》一文所分析的那样。张、梅合作是一场戏曲改革,成为“话剧史和京剧史上最早出现的范例”。
从世界出发,加眸中国,张彭春决不外行。他向梅兰芳提出并为梅氏所采纳了一系列主张:废除捡场陋规,净化戏曲舞台,不能为开打而开打,剧本力求精练与集中,减少纯交代性的场次等。特别是梅兰芳所演各剧,经张导演多次。为求变化,把梅剧的各种舞抽出来,诸如《天女散花》的绸舞、《霸王别姬》的剑舞等。为求表演,增加了《贞娥刺虎》。从整体上组成婀娜多姿的东方歌舞系列。凡此煞费苦心的安排,既出于适应外国人的欣赏心理的考虑,更出于学贯中西的宏观把握下而对国剧所做的一场微调。如果说齐如山是采取了以不变应万变的方略的话,那么,张彭春的方略则是:万变不离其宗。他没改变国剧的本色,他是通过一场改革,让国剧的本色更适应国际文化市场的审美需求。
所谓“梅兰芳的两个翅膀”,大抵如此。
概言之:“中国的世界观”,民族精神,从大文化的视角看,即鲁迅所谓:有民族色采的文学,倒容易成为世界的。“世界的中国观”,世界意识,从大文化的视角看,即歌德所谓“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歌德谈话录》1827年1月31日)“中国的世界观”正面为:强化自我,负面为:唯我独尊。“世界的中国观”正面为:宏观把握,负面为:微观失调。齐如山与张彭春好在:都没有走向负面,而将其正面最光辉地展示出来。这样,即“宏观把握”,又“强化自我”,“鲁迅的民族精神”加“歌德的世界意识”,恰合成一个梅兰芳的“移步而不换形”论。即:既是东方古典特色的,又是随世界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从中国到世界,从世界到中国,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螺旋形的发展、螺旋形的升华,这样盘桓而起,扶摇直上,为梅兰芳腾飞造成一股强大的动力。无论齐如山或者张彭春都只能是半个梅兰芳,半只“金凤凰”。唯有两翼共振,盘桓而起,才是一个梅兰芳,一只“金凤凰”,才能完成梅兰芳的文化发展战略,实现中国京剧腾飞于世界艺术之林的伟大使命。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应该忘掉了齐如山的业绩,不应该冷淡了张彭春的功德,我们更应该认识梅兰芳驾驭齐如山的“中国的世界观”与张彭春的“世界的中国观”的浑宏之气、潇洒之风。
如此说来,梅兰芳的两个翅膀,难道仅仅是梅兰芳的?难道不是中国文化、中国经济、中国的一切腾飞于世的两个翅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