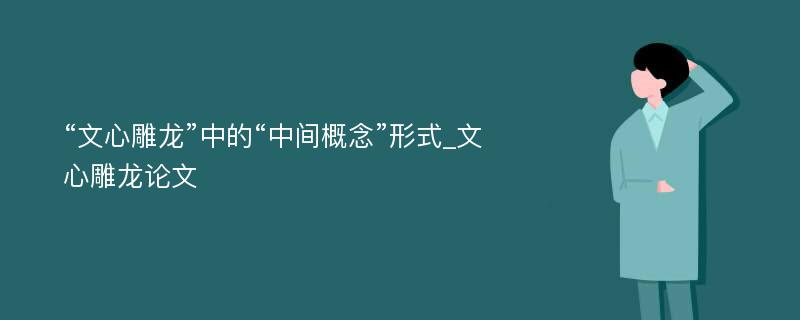
《文心雕龙》的“中间概念”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形态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9)04-0064-04
刘勰的杰出之处在于他仅用3万余字的篇幅就论述了文学活动流程里所要面对的绝大多数问题。刘勰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在于“互证法”的运用,使《文心雕龙》获得了最为经济的体系结构①,另一方面则在于他大量使用了一些中间概念形态的术语,使行文中语言得以节俭。
《练字》篇云:“夫文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矣”,认为文章的关键之一在于语言,文字乃是文章的细胞。刘勰在《指瑕》篇里说:“夫立文之道,惟字与义”,这里“字”,当指字形,即所谓“言语之体貌”,是文字符号本身;“义”则应为文字符号所蕴含的意义。用今天的话说,是能指与所指。文字是言语物态化、凝固化的体现,文章由文字组织、排列而成,包含形体与意义的聚合,这聚合不是随意的,它由种种规定所限制,这就形成行文的种种要求。在《神思》篇里他要求作文要“博而能一”,文章要义脉贯注,不能杂乱无章,任何文章,都应有一定的主旨,要以此为核心组织文章,排列字句。以此为原则,刘勰创作《文心雕龙》,也是以一个或一组核心概念为主,来结构《文心雕龙》的概念体系,从而构建起《文心雕龙》的理论地基的。
王元化论述:“人(圣人)通过自己的‘心’创造了艺术美”,“在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中,‘心’这一概念是最根本的主导因素”,“刘勰在文学起源论中把‘心’作为文学的根本因素,但是他在创作中却时常提到‘心’和‘物’的交互作用”;[1]61,62,65韩国学者金民那认为:“在《文心雕龙》的文艺美学理论中,‘心’与‘文’的问题占有最基本、最重要的地位”[2]579;张少康认为:“在刘勰的思想里,文学的本体乃是作为主体的心和作为客体的道与物以及作为形式的辞与象之和谐而完整的统一体”[3]580。张说甚为全面:《文心雕龙》正是以“心”、“物”、“文”几者之间的关联为核心展开,从而勾勒出双向互动的从创作到欣赏的文学活动流程,结构起《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的理论体系。
据粗略统计,《文心雕龙》中出现频率较高且较为重要的文论词有:文、心、正、旨、志、言、事、奇、味、物、采、性、思、骨、风、美、神、华、真、气、通、理、象、情、道、势、意、义、语、实、趣、质、辞、韵、体、变等以及它们之间的转化合成②。如果我们以今天的视角对其进行分类的话,这些概念、术语大致可划分“物”、“心”、“文”三类:如果把“物”看作是自然物与社会事物的总和的话,那么“物、事、义、通、变”等及其组合的概念、术语当可归入此类;“心”当然是人心,指主观诸要素,在《文心雕龙》中主要指作者之“心”与读者之“心”,这样,诸如“才”、“性”、“情”、“志”、“神”、“心”、“思”等及与之相关的概念、术语即可划之麾下;而以我们今天对文学的认识来看,“文”③所包属的概念、术语应含“言、采、华、实、语、辞、势、美”等及其组合构成。
显然,这种划分颇为勉强,《文心雕龙》中有很大一部分概念、术语是不能简单归入这三类的某一类的,问题的关键倒不是因为这些概念或者术语超出了“物”、“心”、“文”的范围,难度恰恰在于,它们游移于“物”、“心”、“文”之间,形成一种中间概念的形态,使得我们难以进行科学的、明确的划分,这也是造成《文心雕龙》难以解读的原因之一,有人甚至将其归咎为刘勰对问题认识不清。凭心而论,这种“缺陷”不单是刘勰个人的,而是整个民族的,它可算得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大特色。
任何概念的形成,都是人类对该概念所指称的事物的多重印象与经验的叠加,而且,只要对该事物的认识还没有穷尽,叠加就没有止境。就是说,能指的形成并不能封死所指的变化,意义生成中尚有新的意义生成,与原有的意义组合重叠,在历史的语境下不断增生,这是任何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概念必然的发展轨迹,而那些消失了的概念则多与死亡了的事物息息相关。任何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概念都是指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从某种程度讲,概念的发展史可以看作是人的发展史。中国古代文论语境中的概念生成恰恰具备了这一特点,在此语境中,人不是为物存在的,物也不是为人存在的,他们各自澄明地敞开,虚位以待,一旦交往则彼此关联,在互相沟通中显现自身,形成“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神思》)的局面,在证明自身的同时又印入对方的元素,以期完满。注重事物普遍的关联而不是独立的形态,使得概念与概念之间,概念发展的此阶段与彼阶段之间为开放型而非封闭性的格局,从而概念本身能够不断汲取新的元素,不断增强自身的涵盖范围。而这些概念本身,因此具有了在此意义与彼意义间流动的特征,我们可称之为“中间概念”。正是这些“中间概念”的存在,使《文心雕龙》中的各个篇章、论述的各个问题之间的关联得以凸显。
《文心雕龙》中的“中间概念”的生成方式大概有两种:一种是概念所指称的对象本身同时具备了“物”、“心”、“文”几者的某些因素而游移其间,从而使概念的意义或呈此义或呈彼义,甚至亦此亦彼。比如说,《文心雕龙》出现的较多的“文”,就明显的具有这一特点,“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情采》)指出其同时具有“物”、“心”、“文”的元素,这样,在《文心雕龙》的概念体系中,“文”就拥有了多层次的意义,仅以《原道》篇为例:
1.文之为德也大矣。
2.……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
3.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4.旁及万品,动植皆文。
5.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
6.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7.人文之元,肇自太极。
8.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其中,1、2、3、4有文字、文章之意,具有“文”的因素,2、4则指事物的形状、花纹等物的因素,6、8的含义就不是那么稳定,乃是一种游移状态了。“《文心雕龙》全书单独用‘文’字时含义有多种,有时指文学、文章或词藻、文采;有时指文化、文明、学术;有时指一切事物的形状、颜色、花纹、声韵、节奏等”[4]2。再如“气”:可指物的面貌,“写气图貌,即随物以宛转”(《物色》);也可指人的气质,“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正”、“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体性》);自然,它还可以指作品本身的气势:“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风骨》),指作品的辞气:“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诏策》)。不惟如此,这种“中间概念”还贯穿于从作者的传意到读者的会意的整个文学流程;如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很有一席之地的“味论”,在《文心雕龙》中论述颇为全面:
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宗经》)
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
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
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论说》)
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
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通变》)
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于淫侈。(《情采》)
繁彩寡情,味之必厌。(《熔裁》)
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下句,气力穷于和韵。(《声律》)
体植必两,辞动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载。(《丽辞》)
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
若夫善奕之文,则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从杂而至。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配之则芬芳,断章之功,于斯甚矣。(《总术》)
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物色》)
“味”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主要是作为接受的术语出现的,然而通观《文心雕龙》全书,“味”游移于创作与接受之间,在作者、读者及作品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双向互动关系,显然是以“中间概念”的形态存在的。
在此基础上,这类概念或术语还可向外衍生,扩展,与其他词组和形成新的概念或术语,如“文”,在《文心雕龙》中与他词结合形成的复合概念或术语有:“文采”、“文风”、“文思”、“文骨”、“文象”、“文势”、“文艺”、“文体”、“文释”、“文笔”、“文心”、“文人”、“文士”等;再如“风”,则有“风人”、“风力”、“风化”、“风味”、“风转”、“风格”、“风景”、“风情”、“风辞”等组合,虽然形成的新的概念或术语单个的看,它们或者已分属“物”、“心”、“文”中的某一类,但系统的看,由某一单体概念或术语衍生、扩展形成的概念或术语体系,依然在“物”、“心”、“文”间流动,由此可见,“中间概念”在《文心雕龙》中的活跃程度。顺便说一下,这类文论词占了《文心雕龙》概念、术语体系的大部分,是《文心雕龙》“中间概念”生成的主要方式。
《文心雕龙》中“中间概念”生成的第二种方式是:不同类别的单体概念或术语相互沟通进行组合,由于双方均保持了原有的意义从而使形成的新的概念或术语同时具有了亦此亦彼的意义。比如“体性”,“体”既可指“人体”,又可指“文体”,“性”则指人的情性,二者合一后,就兼有风格和体裁的双重意义;“风骨”的含义也具有该特点,徐复观认为:“气乃由内在之情性通到外在之文体的桥梁”,“而风与骨乃由气之自身所形成,故风与骨即人之生命力在文章中之表现,使读者可通过风与骨而接触到作者的气,亦即接触到作者的生命力,于是情性与文体之关联,更为具体化了”[5]237,指出“风骨”的组合,打通了“作家—作品—读者”的关节,其对《文心雕龙》中存在的“中间概念”形态,可谓心领神会。这些“中间概念”在“物”、“心”、“文”中自由切换,使它们之间形成连贯、照应、互补、阡陌交通的网状结构。在此结构中,“物”、“心”、“文”在各具独立的态势,分别承负着自己的角色的同时,以开放性的形态吸纳他者的元素,形成多层面的制衡,刘勰对文学流程表述最为精彩的一段话是: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则见其心。(《知音》)
把文学活动的流程一语包揽,可谓慧眼。
总之,单体概念的独立形态表明刘勰已经注意到“物”、“心”、“文”各自独立的存在,而中间概念的大量使用则表明在传统语境下刘勰更注重“物”、“心”、“文”的互动与互补。这样,《文心雕龙》中“物”、“心”、“文”几者在于文学活动流程中构成完整的系统,而大量的“中间概念”则在“物”、“心”、“文”之间充当连接角色。正是使用了这一策略,刘勰建立起“物”、“心”、“文”几个不同范围的概念术语体系之间的交错相通而又经纬分明的立体的动态的《文心雕龙》的概念术语体系,从而架构其《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
注释:
①参见刘振伟《论〈文心雕龙〉中的互证结构》,《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2期。
②本统计以朱迎平《文心雕龙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及周振甫《文心雕龙辞典》(中华书局1996年版)为主要依据。考虑到《文心雕龙》中的复合概念均由这些基本的单体概念或术语组合而成,且关系极为密切(在后文有所述及),故在此只列单体概念或术语。
③《文心雕龙》中“文”共出现500余次,其含义极不确定,本文除引用文字外,所提到的“文”均取当下“文学、文章”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