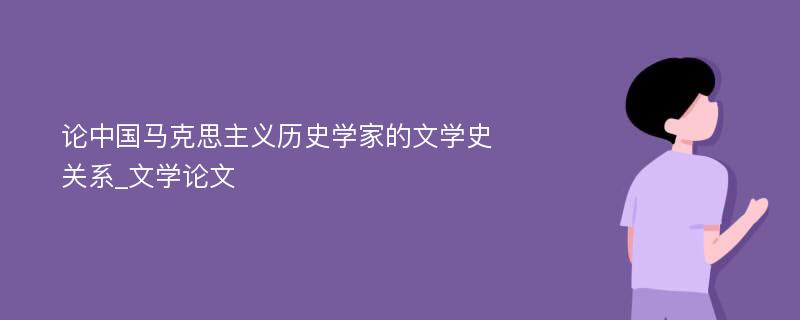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论文史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家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关系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史关系是中国传统史学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传统史学有着文史不分的传统,倡导“良史莫不工文”;同时,随着史学发展所带来的史学自觉意识的加强,又有了文史相分的格局,刘知几和章学诚等还有专门的论述。中国史学发展进入现代进程以后,随着西方近代学科理论体系的传入,文史关系的讨论在承继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吸收近现代史学与文学的学科理论,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一是对史学与文学学科性差异的内涵作了不同程度的现代性解释;二是有关文学思维与史学思维的学科认识形式异同成为讨论的重要内容;三是对文与史撰述原则与方法异同的研究范围加以扩大;四是对史家文学才能的内涵有了新的理解;五是新史学的史料观还使史家将文学作品视为重要史料并广泛加以运用。在中国现代文史关系的理论探讨和史学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史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突出的理论成就。本文拟从现代史学发展的大背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史家有关文史关系的理论及其贡献作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评析。
一
李大钊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对文学也有一定的研究和实践。他对文史关系做过很多论述,其基本观点是,两者既存在密切的关系,又存在严格的分别。
首先,从学科演化和发展的角度出发,他强调了文学和史学的互通性。李大钊说,古代文史相通,是因为“文史的发源,都源于古代的神话与传说的缘故。这些神话与传说的记载,即是古代的文学,亦是古代的历史”;他进而认为文史的分化虽是学术进化的必然结果,使治学走向“专”和“精”,但是也导致了“于‘贯通’之义,几付之阙如”的弊端,以至于“学者于此,类皆疆域自守,老死不相往来”;因此,他主张在文史分科的同时也应当重视综合的研究,贯通其界域,“以成相辅相益的关系”;并认为,“然其间终有互相疏通的自然倾向,大有朝宗归一的趋势”。① 在谈到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时,他将文学、语言学作为与史学有密切关系的“第一类”学问。在中国新史学发展的初期,李大钊能结合现代学科理论对史学与文学的分合关系做出辩证分析,对中国史学的现代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不仅历史论述须借助“文学美文”,而且历史研究亦有与文学思维相通之处。李大钊说:“史学由个个事实确定,进而求其综合。而当为综合的研究的时顷,一方欲把事实结配适宜,把生成发展的经过活现的描出,组之,成之,再现之;于他一方,则欲明事实相互的因果关系,解释生成发展的历程。由第一点去看,可说史学到某种程度,其研究的本身含有艺术的性质(不独把历史研究的结果用文学的美文写出来的东西是艺术的作品,就是历史研究的本身亦含有艺术的性质)。由第二点去看,史学的性质,与其它科学全无异趣。”② 这里,他提出科学的艺术化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必然,历史的科学研究离不开艺术思维,这已是现代历史认识论问题,突破了传统文史关系主要探讨两者撰述方法的局限,具有重要意义。
再者,史学和文学在社会功能上具有一致性和互补性。李大钊说,“凡一种学问,必于实际有用处,文学、史学都是如此。”史学和文学“一样可以帮助我们为人生的修养,所以也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文学是可以发扬民族和社会的感情的”。而史学对于人生,既可以像文学那样激励民族情感,还“可以得到一种观察世务的方法,并可以增加认知事实和判断事实的力量”。因此,“二者帮助人生的修养,不但殊途同归,抑且是相辅为用,史学教我们踏实审慎,文学教我们发扬蹈历”。③ 李大钊从加强人生修养、提高认识能力和培养民族情感方面提出文学和史学既各具其用又相辅相成,从而对传统文史功能作了不少现代性发展。
李大钊在指出文学和史学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同时,又结合现代学科理论对两者的区别作了较深入的阐述。
第一,就史学与文学的性质而言,两者是根本不同的,史学应求“真”,是科学,文学应唯“情”和唯“美”,是艺术。李大钊说,“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也就是说,史学以求真为根本,所以,“史学既与其他科学在性质上全无二致,那么历史科学当然可以成立”。④ 他认为,在当时“史学尚是幼稚的”,且由于研究“人事现象”而“极其复杂”,但不能就此否定其科学的性质。⑤ 关于文学的本质,他说:“文学家的笔墨,能美术地描写历史的事实,绘影绘声,期于活现当日的实况。”⑥ 他又说:“一般最流行的文学中,实含有很多缺点。概括讲来,就是浅薄,没有真爱真美的质素。……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新运动的土壤、根基。”⑦ 这即是说,真正的文学不仅应当反映现实,而且应以情感和美为本质。
第二,正是基于文史性质的不同,李大钊阐述了历史研究中文学运用的限度与方法。他说:“研究历史的学者,不必为文豪为诗人,而且就史实为科学的研究,与其要诗人狂热的情感,毋宁要科学家冷静的头脑,至于记述历史的编著,自以历史文学家执笔为宜……但为此亦须有其限度,即以诗人狂热的情热生动历史的事实,应以不铺张或淹没事实为准。这样子编成的历史,含有两种性质:一方是历史的文学,一方是历史科学的资料。”⑧ 这里,李大钊不仅强调史学和文学的界限,也区分了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的不同,而所谓历史撰述中文学的运用亦不限于文学化的语言,还指对宏观史事的构建和叙述离不开文学的想像来帮助。
李大钊对史学和文学关系的探讨是较全面深入的。他突破传统文史关系认识的限域,从现代学科分类、文史认识方式和两者价值功能的角度阐发了史学与文学合与分的辩证关系,尽管是粗线条的,却在现代学术建立发展初期具有重要价值。
二
郭沫若为了配合社会生活和现实斗争的需要,从事了大量的历史研究和文学艺术的创作与理论探索。尤其是他的史剧理论涉及大量文学和史学关系的阐述,因此,他有关文史关系的思想反映在他的史剧创作理论中。⑨
郭沫若对文史关系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他结合史剧创作对文史关系作较深入的思考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及40年代中前期的史剧创作高峰期,其重点是在阐明史剧创作要以历史研究为基础的前提下,着力区分史剧创作与历史研究的本质差别。他说:“但我相信聪明的读者,他全知道我始终是站在现实的立场的。我是利用我的一点科学智识对于历史的故事作了新的解释或翻案。我应该说是写实主义者。我所描画的一些古人的面貌,在事前也尽了相当的检查和推理的能事以力求其真容,我并不是故意要把他们漫画化或者胡乱地在他们脸上涂些白粉。”⑩ 这里指出史剧创作必须以历史研究为基础,历史文学作品的精神实质是与真实的历史面貌遥相呼应的。同时,他又明确指出了文学创作与历史研究的根本差异。他说:“历史剧作家不必一定是考古学家,古代的事物愈古是愈难于考证的,绝对的写实,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合理”;“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剧作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11) 所以,他批评说:“中国的史学家们往往以其史学的立场来指斥史剧的本事,那是不免把科学和艺术混同了。”(12)
他的《历史、史剧、现实》则对此问题有全面深入的阐述。第一,史学(家)与史剧(家)的任务不同。他说:“史学家和史剧家的任务毕竟不同,这是科学和艺术之别。”史学家的任务是“发掘历史的精神”,而“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如何“发掘”呢?他说,“史有佚文,史学家只能够找,找不到也就只好存疑”;对于“历史并非绝对真实,实多舞文弄墨,颠倒是非,在这史学家只能纠正”。如何“发展”呢?他说,“史有佚文,史剧家却须要造”;对于“古人的心理,史书多缺而不传……便须得史剧家来发展”;史剧家须还给“颠倒是非,舞文弄墨”的历史以“一个真面目”。不过,郭沫若尽管强调两者的任务不同,但依然认同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即以不同的手段还“历史的精神”以真面目。第二,任务的不同导致历史研究与文学创作的方法和手段不同。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不怕伤乎零碎,愈零碎才愈逼近真实”;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注重在构成而务求其完整,愈完整才愈算得是构成”。即是说,历史研究是以客观地求得史料的真实为标准,着眼于具体的历史事实之真,史剧创作只须求得历史精神之真,着眼点在于塑造完整的形象,而非其中的事件或人物究竟是否完全符合史实。第三,史剧创作是以历史研究为前提和依据的。他说,“自然,史剧既以历史为题材,也不能完全违背历史的事实”,“大抵在大关节目上,非有正确的研究,不能把即成的史案推翻”,因此,“创作之前必须有研究,史剧家对于所处理的题材范围内,必须是研究的权威”。“优秀的史剧家必须得是优秀的史学家”。(13) 在他看来,历史之真包括具体的历史事实之真与更高层面的历史精神之真,好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历史文学作品,必须是对社会历史生活本质之真的揭示和反映,是对具体历史事实或人物的本质或精神之真的提炼与升华。
总的说,郭沫若此时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史剧创作如何运用史学研究的成果和正确对待史剧的历史真实问题。然而,他的这些思考和探讨却涉及到了文史关系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1)史学之真与史剧(文学)之真内涵的不同,一是“发掘历史之真”,一是“发展历史之真”,即“科学与艺术之别”;(2)实现史学之真与文学之真在方法上的异同;(3)分析了文学如何表达和反映历史之真。上述这些问题实际涉及到史学与文学的学科性质与任务,史学与文学的认识形式和表述方法三个层面。
到了40年代后期,郭沫若虽然没有从事史剧创作,但是却对两者的关系作了不少重要的论述,体现了对文史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他一方面继续肯定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的区别,说:“我们要知道科学与文学不同,历史家站在记录历史的立场上,是一定要完全真实的记录历史;写历史剧不同,我们可以用其一分材料,写成十分的历史剧,只要不背现实,即可增加效果。”(14) 但是,他思考更多的则是历史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辩证关系。
首先,郭沫若坚持科学研究对文艺创作的必要性,并从科学与文艺的从属关系角度作了论证。他说,“任何创作都不能不经过一道研究过程……没有研究便没有创作”,科学之所以是文艺的前提与基础,在于科学认识和科学精神是人类认识的最高层次,他说,“科学是人类智慧所达到的最高阶段,是人类精神辨别是非、认识真理的最高成就。在今天人类的一切部门的认识都不能离开科学,而尤其重要的是科学的精神。科学的精神是什么?这是祛除主观的成见(私),而以客观的真实(公)为依归的纯正的精神动向。认识客观的真理便依据真理以处理客观或促成客观的进展,而使之服务于人生,以增进人类生活的幸福,这便是科学的精神”,因此文艺认识是从属于科学认识和科学精神的,“文艺工作假使是属于研究或批评的范围,那完全是科学的一个分枝,……即使是属于创作的范围,我们也可以说只是科学精神的另外一种化装表演而已。文艺创作本质是人生的批判”;而且,“文艺的主观也必然要经过科学的客观才能养成”。所以“文艺工作和科学精神是分不开来的”。(15) 强调科学性和历史真实性是史剧等文艺创作的基础,这是郭沫若对文史关系认识的一个重要转向。
其次,文学艺术对科学(研究)也有渗透和辅助作用。郭沫若反对将科学等同于纯客观,或将艺术等同于纯主观的观点,说:“真正的科学精神并不是纯客观的机械式的态度,它是要经过客观真理之明朗的认识以养成主观定见之坚毅的操守。科学正是在养成主观的能动力量而不是阉割它。”(16) 也就是说,科学研究除了要有抽象(理性)的思维,还离不开形象思维。所以说,“写历史要根据史料,史料是有限制的,历史家要根据史料加以推理和判断,实际也就是想象。好的科学家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当然,他是按照规律来想,而不是胡思乱想。”(17) 这里强调了想像这一文学形象思维在历史建构和叙述中不可或缺的功用。他还指出文学有助于人们认识真实的历史,是对史学认识功能的补充,说:“其实,写历史剧原有几种动机,主要的就是在求推广历史的真实,人类发展的历史。我们在过去的人类发展的现实里,寻求历史的资料,加以整理后,再用形象化的手法,表现出那有价值的史实,使我们更能认识古代真正过去的过程。”他又说:“历史家把事实现实的记录下来,戏剧家就在认识了这历史的真实以后,用象征的比喻的手法,写出更现实的历史剧来。”(18)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郭沫若在有关史剧的论述中对文史关系继续作了一些阐述。其中主要是强调史剧必须以历史的真实为根本。他在论述史剧创作如何仔细分析史料时说:“仔细的分析不仅单指史料的分析,还要包括心理的分析。入情入理地去体会人物的心理和时代的心理,便能够接近或者得到真实性和必然性而有所依据。”(19) 他在谈到《蔡文姬》的创作经验时又说,“我在写作中是尽可能着重了历史的真实性,除掉我自己的经历使我能够体会到蔡文姬的一段生活感情之外,我没有丝毫意识,企图把蔡文姬的时代和现代联系起来。那样就是反历史主义,违背历史真实性了。”此剧“有一大半是真的”。(20) 1962年,他对史学和文学的辩证关系作了精要的论述,他说:“我是想把科学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想把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说得更明白一点,那就是史剧创作要以艺术为主,科学为辅,史学研究要以科学为主,艺术为辅。”(21)
总之,郭沫若对文史关系的理论探讨是与他的史学实践和文学创作紧密结合的。他对文史关系的讨论不是就理论谈理论,而是来源于他丰厚的史学实践和文学创作。他对历史研究与文学创作在功用上互助关系的认识,对史学之真与文学之真及其求真方法的理论思考,对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两种不同认识方式在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中不同地位的认识,大大丰富和深化了文史关系的理论探讨。
三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历史剧讨论中,翦伯赞、范文澜和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家也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问题作了探讨。他们基本都主张,艺术真实以历史真实为基础,经过必要的艺术加工,历史真实可以上升为艺术真实。对于这些观点,此不具论。下面,主要就他们对文史关系所作的其他阐述加以总结。
关于历史叙述中语言表述的问题。它主要包括历史叙述中逻辑性语言、写实性语言和文学性语言的恰当运用,不同类型的史学著述对这些语言的运用是不相同的。关于语言对文章思想内容的表述所起的重要作用,中国传统史学作过这样的表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马克思恩格斯则强调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22) 范文澜说,史学文章写得“应该切实些、清楚些、简要些、生动些,一方面能够适当地表达自己所要说的话,另一方面使人看了不讨厌”;“韩愈所说的‘文以载道’,是经验之谈。一辆破烂车子载着大道理,人家会拒绝它走进自己的眼睛里。自己写的文章别人是否愿意看,完全在于自己。写了一辈子的文章,看的人只有几个,那又何苦呢?如果一个人写的文章大家都喜欢看,岂不很好。”(23) 侯外庐在谈到科研人才培养的原则时,强调逻辑性语言和写实性语言的重要性。姜广辉回忆说:“侯先生指出,文字表达要清清楚楚,但不要只讲词藻。应当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内容胜于词藻,而不是词藻胜于内容。写科学论文,不宜用文艺的写法。理论文章要用科学语言,说理清楚透彻。”(24) 翦伯赞则将语言的作用上升到哲学高度,说:“体裁是历史学的形式,而言语,则是历史学的本体,因为任何形式的历史学,都必须借文字来表现其内容。”(25) 这是对语言文字在史学中地位和作用重要性的新认识。他还提出历史文章的语言表述应当做到艺术性和准确性的统一,说“文章要写得生动一些。但我们不是写诗歌,可以全凭感情,也不是写剧本,可以虚构。我们是写历史教科书,既要生动,又要准确、严肃”;“不要一二三四罗列现象,要条理清楚”;“文章要剪裁,删除繁芜误用的辞句。句子要锤炼,去掉不必要的字眼。不论是文章的剪裁或句子的锤炼,都不是为了美词而害意”。(26)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史家既重视历史著述语言表述的文学性,又强调要坚守表述的准确性。
对于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马克思主义史家作了充分肯定和深入发掘。其中,翦伯赞的论述最深刻。他认为在认识历史的真实性上,文集、诗集、小说和剧本等历史上的文艺作品有更大的魅力,“经过野史杂记和文艺作品的参证,对于正史上的史料,自然可以获得不少的补充和订正”。(27) “在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作者对当时社会所涂绘的阴影;不过他们所涂绘的阴影,有浓有淡而已。所以我以为集部之书,当作史料看,它们正是各时代的社会缩写,正是各时代的人民呼声,正是千真万确的历史记录。而且其中的历史记录,往往是正史上找不出来的。”“总之,自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之传奇小说,乃至现在的许多文艺作品,他们表现出中国文学自己发展之一系列的历史过程;也反映出历史上所不载的社会发展的内容,所以它们是文学,同时也是史料。”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提出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要超过史部史料,“因为史部诸史,是有意当作史料而写的,其写作的动机,则抱着一种主观的目的。……这种主观意识之渗入,当然要使史实受到程度不同的歪曲,乃至涂改,以致减少了史料的真实性。至于史部以外的群书,则并非有意为了保存某种史料而写的,而是无意中保留了或反映出若干的史料,这样无意中保留着或反映出的史实,当然要比较真切。固然,在史部以外的群书中,其行文记事,也夹杂着主观的意识,特别是各种文艺作品,如诗词、歌赋、小说之类,甚至还具有比史部诸书更多的主观意识。但是在这一类书籍中所表现的主观意识之本身,就是客观现实之反映;因而他不但不破坏史料的真实,反而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更真实的史料。”(28) 翦伯赞对文艺作品史料价值的充分肯定和深刻分析在现代中国史家中是少见的,对正确认识和充分使用文艺作品来研究历史很有启发。
四
白寿彝是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家中最重视文史关系研究的。其特点和贡献是,对中国传统史著在历史文字表述、史文烦简和“于序事中寓论断”等方面的优良传统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反复呼吁当代史学工作者要加强文学修养。
在白寿彝有关文史关系的探讨中,最重要的是对“历史文学”的阐述。他明确将历史文学作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内容,认为“历史文学发展的规律”与史料学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编写形式发展的规律构成了中国史学发展的三大技术规律。(29) 他主编的《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和《中国通史·导论》卷及《中国史学论集》等书对此都有专门论述。他所说的历史文学是指历史文字表述的文学艺术性,是属于历史撰述方法论层面的问题。他说:“历史文学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指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另一个意思是指真实的历史记载所具有的艺术性的文字表述。我们这里所说的历史文学是用的第二个意思。”(30) 他的贡献即在于结合中国古代优秀史著,发掘和总结了中国古代史学重视文字表述的优良传统,对历史文学的内涵作了拓展。
关于历史著述语言文字的文学艺术性,他说:“历史的表述必定要依靠文字,在文字写作上,于不失真实的条件下,注意到艺术性或文学性,这还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31) 他认为:“《左传》最大成就在历史文学方面”,它在这方面的成就“成为以后史学家和文学家学习的典范。而史学和文学的密切联系,也是《左传》所创始的中国历史著作上的一个传统”。(32) 他结合《史记》、《左传》、《国语》、《战国策》和《资治通鉴》等史著,提出中国传统历史记载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写人物、写战争、写场面、写语言和写世态五个方面。他通过对《史记》的分析,特别强调了描写历史人物时文学才能的重要性,说,“必须使历史人物活现在纸上,才能显示出历史著作的吸引力。《史记》以写人物为最好”。(33) 他又说,“从史学的角度看,最重要的还不在于《史记》善于刻划人物的形象,而更在于透过人物的言语、活动和遭遇,去揭露当时的政治情况,去说明、判断历史问题。”(34) 关于史文的烦简,他结合刘知己《史通》和顾炎武《文章烦简》有关论述,提出要正确看待这一问题,说:“史文烦简,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字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对历史的见解问题,对材料的取舍问题。”(35) 关于史论与史事的关系,他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的“于序事中寓论断”的思想,认为并不是任何历史上实存的史事、人物及事迹都要“实录”,有些没有意义的东西就不应写出来。他还对《史记》“寓论断于序事”的几种方式作了总结,指出除了最基本的历史叙述形式外,还有两两对照和细节的描写等。
白寿彝还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学进行了总结,其《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将此归纳为六个字:准确、凝练、生动。后来,又将“准确”改为“确切”,并对三者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作了深入阐述,他说,“确切,包含表述的真实、正确和恰当。这就有一个态度问题、认识问题和技术熟练程度的问题。”“凝练和生动比确切更有技巧方面的意义,但也不是单纯技巧问题。”“凝练”主要表现为“尚简”和“用晦”,“寓论断于序事”则是“用晦”的一种主要表述方式;“生动”是指熟悉表述对象,言之有物,要有感人的生活气息。(36) 可见,在白寿彝看来,确切是凝炼和生动的基础,而凝炼和生动又是确切的发展。可以说,这六个字既是白寿彝对中国史学撰述优秀传统的总结,也是对现当代史学撰述提出的基本原则。这六个字充分体现了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准确(确切)是科学性的要求,体现了学科特色;凝练和生动则是属于艺术性的要求。白寿彝对传统历史文学的阐述及其提出的现代史学撰述的六字原则,是对中国传统史学文史合一内涵和精神的现代发展。
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历史文学的传统,白寿彝反复呼吁史学工作者应当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重视历史文学的传统,指出这对更好地发挥史学的价值功用和扩大史学的社会影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说:“一个历史工作者必须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不要说我们历史上的大历史家都是文学家了,仅就一个普通的历史工作者来说,他对于文学没有一定的修养,是不能胜任这个工作的。”(37) 因为,历史工作者是要用丰富的历史事实来教育广大人民,让他们对人类的历史前途有更深刻的了解。而要普及历史知识,提高大家的认识,就必须写得通顺、明确、系统和生动,使别人愿意看。但是,他认为现在的史学作品在很大范围里只是给同行们看的,“这个圈子太小了,历史学的作用太小了。应该放大这个圈圈,让更多的人看”。(38) 为此,他呼吁高校应该讲史学名著,而不只是讲几篇历史文选,提倡用背诵名篇的方法领会古人的文风,以培养历史研究者的文学修养。白寿彝结合历史文学对史学研究者提出的修养要求,也丰富了传统的史家文学修养论的内涵。
五
现代史学有关文史关系的认识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文学与史学的学科关系问题,它主要是指史学和文学作为不同学科的性质特征、相互关系及其功能价值,属于知识本体论的范畴;二是文学创作与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的异同及其在两门学科间的相互运用,属于认识论的范畴;三是文学化的语言表述和历史著述的思想内容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如何恰当运用文学化的语言来表述历史真实性,属于史学著述的撰述方法问题;四是史学家必须具有文学艺术的思维方式和文学化语言运用的能力,这是属于史学主体知识结构和意识的问题,即史家素质论;五是文学作品作为历史研究资料的合理性和使用范围,这是属于史学中的史料学问题。尽管现代史学的不同流派和史家对这些问题阐述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或是只就其中一个或某些问题进行讨论,但总体上不出这几个方面。
中国古代史学关于文史关系的认识包括文史不分和文史两分。关于文史不分的传统起源甚早,孔子已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到后来,“良史莫不工文”以及历史撰述的“事核”与“文美”并重,已然成为赞否史家及其史著的标准。可见,文史不分主要是讲史学著述中要重视文学艺术性语言运用,属于史著撰述的问题;同时,也指史家应当具有的文学才能。另一方面,随着史学发展带来的史学自觉意识的加强,文与史又走上了相分的道路;(39) 一些史家还专门就史与文的不同作了论述。刘知几和章学诚在认同历史撰著的文学性表述时,(40) 又对文与史的本质差异作了较深刻的论述。刘知几反对文人作史,嫌文人过于重视文艺表达的形式而忽略了历史的真实,说:“史之叙事也,当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矣”(《史通·鉴识》)。章学诚的阐述更为深刻,说:“一切文士见解,不可与论史文……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已”(《章学诚遗书》卷十四,《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他又说:“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语也。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假文辞以达之而已”(《文史通义·内篇五·答问》)。用现代话语来说,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史学与文学的不同学科特性。不过,从根本上看他们仍主要是就史学与文学的撰述原则和表现方法不同而言的,还不具有真正的现代文史学科相分观念。总之,中国传统史学对文史关系的讨论基本没有明确从两者学科性质及其特征的异同来谈,更未上升到学科认识论的高度来讨论两者的异同,对历史建构中艺术思维的运用和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也缺乏系统论述。
随着西方新史学观念和近代学科分类理论的传入,新的文史观也传入中国。作为新史学一大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吸收西方新文史观念和继承传统文史理论的基础上,从各个层面和角度对文史关系作了新的阐发,理论贡献突出。关于史学与文学的性质和功能,他们对传统的文史两分作了现代的学科论证,提出史学属于科学,文学属于艺术,李大钊和郭沫若的阐述较为明确深刻。同时,又分析了科学与文学的相关性,郭沫若论述了作为科学的史学和作为艺术的文学的统一性,认为文学艺术创作必须以科学的研究为前提和基础,李大钊则论述了史学与文学功能的互补性和一致性。关于史学与文学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其在各自领域中的运用,李大钊、郭沫若和翦伯赞等运用现代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理论,在坚守史学科学性的前提下,既明确了史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存在思维方式的质的差异,又突出强调了史学研究离不开文学艺术的思维方式,尤其是郭沫若明确提出了“史学研究要以科学为主,艺术为辅”的主张。再者,关于史家的文学修养,除了进一步发展传统史学所说的要重视’历史著述中文学性语言的使用,李大钊、郭沫若实际是提出了史家必须具有文学艺术思维方式,包括历史认识建构和著述中的想像等新要求。此外,关于文学作品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传统史家虽然认识到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但深入的理论探讨不多。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新史学及其新史料观的传入,文学作品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已成为各派新史家的共识。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此作了重要的理论阐述,其中,翦伯赞对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作了全面论述和充分肯定,提出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要高于史部的史料,对充分重视和挖掘历史上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传统文史关系讨论的基本问题,即历史撰述中文学艺术性语言的运用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家也有继承和发展,尤其是白寿彝提出的“历史文学”及其历史表述的六字原则,不仅拓展了历史著述中文字表述的内涵,又对传统史学历史叙述中语言文字运用优良传统有不少新的阐释。
总之,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文史关系的大量理论探讨深化了中国史学有关文史关系的理论,为现当代史学如何更好地处理文史关系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路。
注释:
① 李守常:《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3、35页。
② 李守常:《史学要论》,第14页。
③ 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211、216、217页。
④ 李守常:《史学要论》,第55、17页。
⑤ 李守常:《史学要论》,第18—19页。
⑥ 李守常:《史学要论》,第44页。
⑦ 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45—446页。
⑧ 李守常:《史学要论》,第44页。
⑨ 有关郭沫若史剧创作理论及其实践的研究很多,有关专著有十多部,如,田本相、杨景辉的《郭沫若史剧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傅正乾的《郭沫若史剧理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韩立群的《郭沫若史剧创作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研究论文更多。但这些研究基本是从文学角度,而非文史关系的角度来讨论的。
⑩ 郭沫若:《从典型说起——〈豕蹄〉的序文》,高国平编:《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541页。
(11) 郭沫若:《我怎样写〈棠棣之花〉》,《郭沫若全集·文学》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7页。
(12) 郭沫若:《孔雀胆二、三事》,《郭沫若全集·文学》卷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8页。
(13) 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高国平编:《郭沫若论创作》,第502页。
(14) 郭沫若:《谈历史剧——在上海市立戏剧学校演讲》,高国平编:《郭沫若论创作》,第508页。
(15) 郭沫若:《文艺与科学》,高国平编:《郭沫若论创作》,第100—101页。
(16) 郭沫若:《文艺与科学》,高国平编:《郭沫若论创作》,第101页。
(17) 郭沫若:《谈戏剧创作》,高国平编:《郭沫若论创作》,第517页。
(18) 郭沫若:《谈历史剧——在上海市立戏剧学校演讲》,高国平编:《郭沫若论创作》,第506、507页。
(19) 郭沫若:《我怎样写〈武则天〉》,高国平编:《郭沫若论创作》,第497页。
(20) 郭沫若:《蔡文姬·序》,高国平编:《郭沫若论创作》,第464—465页。
(21) 郭沫若:《武则天·序》,高国平编:《郭沫若论创作》,第499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5页。
(23) 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7—218页。
(24) 姜广辉:《侯外庐先生谈科研人才的培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8年第2期。
(25) 翦伯赞:《论刘知己的史学》,吴泽主编:《中国史学论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页。
(26) 翦伯赞:《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
(27) 翦伯赞:《怎样研究中国历史》,王学典编:《史学理念》,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28) 翦伯赞:《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王学典编:《史学理念》,第54、56、26页。
(29)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商榷》,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30) 白寿彝:《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9页。
(31)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6页。
(32) 白寿彝:《中国史学的童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33) 白寿彝:《〈史记〉新论》,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第73页。
(34) 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一),第195页。
(35) 白寿彝:《谈历史文学》,白寿彝:《中国史学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第515页。
(36) 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2—348页。
(37) 白寿彝:《谈历史文学》,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第520页。
(38) 白寿彝:《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第388页。
(39) 如,郝润华的《论六朝时期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便从史书内容、体例、语言表述等方面的变化,指出到汉代,特别是到六朝时史学与文学开始走上分离之路。
(40) 参见汪杰:《论刘知几、章学诚关于历史文学的理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