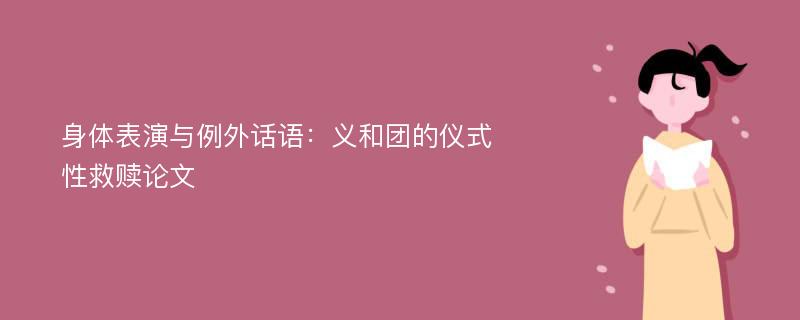
·体育学研究·
身体表演与例外话语:义和团的仪式性救赎
李 文
(汕尾市体育运动学校,广东 汕尾 516600)
[摘要] 义和团身体表演的仿生对象是以巫武为基础的。其中,巫术冠以其神秘色彩预设了神人互通的本能具象,武术的戏剧操练朦胧了神人隐匿的身体潜能。神巫因素与武术因素共生于义和团的身体思维中,两者的“合谋”促生了团民身体意念的自我救赎并创设出多数人共有的乌托邦秩序,进而为“神人合一”的过渡提供了前提性可能。不论辩解的是,身体在神人之间的转换也为义和团的杀戮行为完成了自我救赎的道德教化,即将罪恶行为斥诸于世俗身体中并在神灵身体中得以解脱。
[关键词] 义和团;身体表演;巫武;过渡仪式;救赎
在身体的发展史上,日常身体的存在表现出一种被诸种禁限性文化规制的形态。通常被规制的身体处以一个不平等的状态中,饱受歧视、毫无伦理颜面的存活也随发了卑贱的心理暗示,进而产生了对自我身体的抵制,赤裸裸的低贱身体抑制终难掩其植根于内心的抗争情绪,与之相呼应的诱发了系列的身体叙事样本。政治巫术中的事鬼敬神、秘密教门中的入社仪式、神鬼通灵中的巫(觋)术、狭义性质的戏剧公演等都是事实例证,涉入其中的身体刻意臆造出一种表演姿态并从其原型中脱离出来成为触发激情事件的一个表达焦点。不可置疑的是,身体必然是在某种意识形态中隐喻着肯定现实秩序和否定现实秩序的乌托邦因素,或者说,它们为身体的表演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场合,通过身体的表演将参与者的想象世界赋予真实性的幻想体验。义和团的身体经验就一直秉持着对自我的依恋,通过身体的仪式操练确立了“降神附体”与“刀枪不入”的虚妄事件。
1巫武合流:义和团的身体表演
义和团是由山东冠县流行的义和拳与鲁西北的神拳,以及大刀会、红拳会等民间秘密结社聚合而成[1]。其中,其前身组织源流中神拳是最早提倡“降神附体,刀枪不入”。义和拳设立初衷则是习练舞拳弄棍之术以看家护院,本身不具有巫术气息,山东冠县一带就留下义和拳“不念咒,不喝符”的传言。而大刀会、红拳会等则是将画符扶乩、喝符念咒、设坛排阵等巫术形式与武术粘合一体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行事方式诡异,巫(觋)风习厚重,也最早催生了“刀枪不入”的说法。
日本学者佐藤公彦在其《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就义和团源流之一(即鲁西南大刀会武术金钟罩)的一段史料揭露了“刀枪不入”以一种技艺形式作为招收门徒以换取贽币,但在实验其术时,虽画符念呪故弄玄虚,一旦扳捩关便显异常之态,而后只当学术未精落荒而逃而被众人视作妖言惑众之术。史料所载之事虽略显荒唐,扩大了身体抗击底线,将武术器械之枪替之于火药之枪。一开始大刀会所摆弄的“刀枪不入”之术神灵概念并不浓郁,或者说,刀枪不入的习练功法的确可提高身体的抗击打能力,但练就其术需要经过身体循序渐进的历练,多数人了逃避身体的磨难借助巫术形式以达速成的障眼法更易被效仿,巫(觋)气息的浸染提供了一个捷径。在很大范围上带有巫(觋)形式的“刀枪不入”的演练实质是一种招揽门徒、广敛钱财的旁门伎俩。官方也将之和杂技路演区分开并定性为匪徒传习练气的邪术。大刀会势力的扩充得利于当时社会“盗贼之渊薮”与官方维安的无力,保身卫家的需求促生了对神功的膜拜,习练功法时掺和了神位的躬拜,身体被烧香磕头所牵引。大刀会巧助农民的危机意识与身体欲望,声称掐诀念咒,画符饮吞,排砖排刀,浑身上下无所不排,一夜即成,不畏棒击刀砍,不畏火枪洋炮,民众争相附之[2]。
1.2.4 16S rRNA基因PCR-RFLP 选用4种限制性内切酶HinfⅠ、AluⅠ、HaeⅢ和MspⅠ对16S rRNA基因PCR扩增产物进行酶切[27]。酶切反应体系为3 μL 16S rRNA基因PCR扩增产物,5 U内切酶,1 μL缓冲液,ddH2O补足至10 μL,于37℃水浴酶切反应12 h。3%琼脂糖凝胶(TAE) 200 V电泳40 min,UV检测酶切结果,TIFF格式保存。
如果没有朱红灯,大刀会神功的滥觞程度恐怕只会局限于点。洋教的横行野蛮行径和官方的袒护激化教乡械斗事件,各个村落自发性地组织起来习练拳棒。为了聚集众多零散的拳场,与教会对抗,朱红灯利用早期走民游方获得声望和关系游说于拳场并得到支持。在功法上巧设名目,将早期需苦练的“金钟罩”置换成“降神附体”,“身体”的具象呈现替代于“身体”的虚妄出场,涉入之神都为本土东方民间宗教侍奉之神,与西方外来教会形成强烈的抵御成分。朱红登在其中则扮演着神人角色,在着装装束上(红色装束、红色褂子、红裤子、红头巾)模仿神灵装扮,民众对此也衍生情感依赖,同时也促生拳场的广泛设立,并吸收附近乡村的昆阳拳、青令拳、颜合拳等,各地拳厂设堂口公开聚集习练。在神拳的演练过程中,安上神位,请诸神下凡,有符有咒,符加于顶,或配身畔,则若疯若癫,力大寻常数倍。义和团的身体开始以“神”的角色入场,不同于先前民众对“神”观念的认知,更确切来说,民众把教会视作亵渎东方自然秩序的存在,种种忧患的滥觞都归结于教会。神灵的超自然能力存在已经和日常生活中的身体产生支配关系,习练神拳,参与焚毁教堂,使自己归列于“神兵”之中也就具有神谕性质。
义和团所兜售的“降神附体,刀枪不入”之术不过是传统硬气功、武术与巫术杂糅而成。义和团的身体表演不是任意做作,而是循着“神巫传统”和“武术幻影”释义身体的原始指向。其中,神巫因素中模糊世俗社会与神圣社会的界限,武术因素逾越真实与虚幻的禁锢。
1.1 神巫模拟:模糊世俗与神圣的界限
义和团在引入身体表演的模拟对象时,选择了最简单和有效的形式—巫术。选择巫术和当时巫术文化泛化相关,巫术思维活跃于乡民头脑中,但和西方基督教会相比,巫术隐喻“巫婆神汉”,和耶稣不可同日而语,也没有东方诸神体系的威慑感,因此,隐去了巫觋的名号,自封宗教神祗,巧借巫术仪式的表演力在身体上进行疯癫操练以迷惑乡民。神拳仪式的巫术成分穿插整个过程,或向东南扣头、或念咒、或烧香、或吞符,或动作兼有之[3],具体的史料也记载:
又闻练拳之时,聚童子数人,立向东南,传教者手提童子右耳,令童子自行念咒三遍,其咒言为“我求西方神母阿弥陀佛”,咒毕,童子即仰身着地,气几不续。迟即促令起舞,或授于棍棒当刀矛,两两对战,如临大敌,实则入醉如梦。久之,师向该孩童背心用手一拍,唤童本名,则豁然醒,立若木鸡,拳法亦忘尽,与战斗时判若两人[4]。
义和团的武术内容涉及范围广,成分复杂,总体上来看,大致包含了三种,其一,民间秘密结社的拳种和器械技法,包括梅花拳、五祖拳、八步拳及红拳等:其二,民间公开路演的杂技技巧活动,主要是硬气功法式的金钟罩、铁布衫、排打及排枪等:其三,以乡村市场为重心的武戏表演,三者之间以线性关系并入义和团的武术体系之中。在学界主流观点中,义和团前身就是源以民间武术组织,习练的武术招式实际上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质,每个拳种有着自己的拳技特点和拳理功法。以梅花拳为例,源以昆仑派武术,组织上文武分场,入门弟子先进入武场,练拳术,习拳理,基本动作就包括了“桩步五势”和“行走”,练拳时向四面八方循环画圆,组合练习,功力深厚者甚至能够做到“手无定手,脚无定步、势无定形...随势布局”[11]。文场则以画文章为主,兼具烧香治病、占卜吉凶及阴阳八卦等文理内容。梅花拳虽“文武分场”,但其文场的设立重在修身养性,抛弃杂念,神灵概念并不泛滥,和道教内丹养身术阶段的炼心、炼气的功法类似,以求身心圆融贯通。严格来说,它是一种虚妄的神秘境界追求,和巫术性质差异较大,至多算是一个教门无上功法的致性归真。史料也记载:“查北方民俗刚强,好勇斗狠是其故习。此项拳民所习各种技勇,互有师承,以之捍卫乡闾,缉治盗匪,颇著成效”[12],由此可知,虽然有时神灵会被用来当作装饰成门派的象征体,但习武的本质冲动不在于玄幻的神灵隐喻。至光绪二十二年,教民与乡民关系逐渐恶化,压抑已久的无助心态被武戏中的侠士秉性救赎,梅花拳的角色承担也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在“十八魁”事件后,赵三多将其归依门下,举起反教义旗,将“梅花拳”易名成“义和拳”,但是在扩增拳徒过程中,其民间宗教虚幻色彩亦开始逐渐厚重。造塔焚香,在亮拳前,“先要叩头,烧香、供关公、关平、周仓,以求不被刀枪棍棒所伤”,文场中的“送神咒”、“心血咒”等都在战斗前被念诵,祈求神灵护持。梅花拳原有组织样态即文武分场中的文场意识形态开始被强化。
首先,按照“坛”文化礼制,规制了牵涉其中的人与物的外在形象。在义和团作法过程中,仪式的参与者通常身穿特殊的服饰,在初期主要以红色为主,间有黄色,在义和团进入京津地区后,穿着趋于一致。按照九宫八卦理路分出不同的支系,乾门者色尚黄,头包黄巾,以花布为裹,腰束黄带,左右足胫亦各系指许阔黄带一;坎门者色尚红,头包红巾,腰束红带,左右足胫亦各系指许阔红带一[13]。服饰上对其纹样、色彩、饰物徽记等方面与正常穿着产生视觉上的差异,另外,“坛”的设立隐喻神灵的在场并巡视着祭坛的仪式发生,能否触发神谕关键在于团民以何种身体方式取悦于神明,磕头礼拜、喝符念咒等具有迷乱性的连贯动作普遍存在于义和团的娱神行为中。总体而言,服饰穿着的异类、自我身体的呈奉无非是营造一种非同常境的氛围,强化其与世俗社会的超常行为并初显与之分离的征兆。整个过程还处以“前阀限”阶段,仪式中的参与者以世俗性身份来趋合神灵癖好,身体的外在形态被神灵喜好所规制,也因此映射了坛中人神秩序的尊卑有序。
第二天,辛娜给王树林送来了协议书。他们在王树林公司不远的一家咖啡馆见面了。狠话既然出口,王树林亦无意服软。他故作轻松地说了一句,你出手很快啊,看来早有准备。废话少说,你要是没有异议,就签字吧。你既然决定了,我也不强求了。王树林快速地看完了协议内容,落笔前,他竟迟疑了起来。
从巫武合流的身体生成过程来看,巫术冠以其神秘色彩预设了神人互通的本能具象,武术的戏剧操练朦胧了神人隐匿的身体潜能,神巫模拟与武术幻影共生于义和团的身体思维中,两者的“合谋”促生了团民身体意念的自我救赎并创设出多数人共有的乌托邦秩序。
义和团单借助身体的神巫模仿只能限于舆论与心智上蛊惑人心,进而促生出战斗场面就是在头脑中形成一系列想象中的神鬼斗法。但诸多史料也证明团民不都是乌合之众,义和团成员分布混杂,上至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9],在各地设立的拳场也会传习“踢脚、甩手”、“跑架子”等技击招数,“日夜操练刀矛拳法”,其中也不乏“刀枪锤械各项技艺娴熟”之人[10]。
1.2 武术幻影:逾越真实与虚幻的禁锢
同时,为保护辖区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他带领全体干部落实好“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食品放心工程三年行动”方案和“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等工作任务,深入排查整治食品药品安全隐患,严厉查处食品药品违法违规行为,守住了涵江不发生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的底线。2014年组建以来,分局共开展食品药品安全执法检查100多次,抽检各类食品药品1500多批次,查处各类食品药品案件290余件,罚没金额360余万元,办案成效得到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的通报表扬。
依循着社会人类学家对巫术“三位一体”的研究线索,可以发现,义和团的仪式、咒语与禁忌有别于一般的巫术形式,是介于神话征引与巫术仿生之间的合成。义和团的巫术仿生仪式不是一成不变的移植其原有动作程序,仪式的巫形态主要限于“上法”与“禁忌”,其巫术因素除了常规性的跪拜磕头、烧香、焚表、念咒等固有仪式体系外,其他则依赖于身体的癫疯表演在情绪上煽动拳民,身体“异状”越似“走火入魔”,神灵附体的机会就越大。在巫觋仪式模仿时,因各地巫术文化和神灵偏爱对象不一,操练的身体仪式各不相同,但身体大多表现出一种神智迷乱、口吐白沫、浑身颤抖、乱舞狂跳之态。在身体进入到疯癫状态之前,念咒可为身体的表演增加迷离色彩,义和团的咒语名目繁多,所念之咒多和所请之神相关,如比较典型的“避枪炮火咒”曰: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枪佛来。铁神铁庙铁莲台,铁人铁衣铁避寒,止住风火不能来。天地玄黄,日月照我”[5]。这些咒语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解释性的,因为有些神是内部所创设的,子虚乌有的神祗加重了民众的吸引力。当拳首在表演身体的“刀枪不入”并奏效时,目击者在迷离的咒语刺激中都幻想自己的身体也能够拥有这般神力,纷纷投效。但是当乡民习练此术而不灵验时,义和团也会利用禁忌来确保法术的不可置疑,巧妙说辞,利用五行相克原理予以推脱,比如妇女“秽物”与神灵相克,所以也定下了在施展法术时禁房事与禁见秽物等禁忌。1774年山东爆发起义后,王伦的部队在攻打临清时实施多种法术,颇有效力,守城士兵为之无奈,一老兵提议“呼妓女上城,解其亵衣,以阴对之”的策略,将其克制[6],可以看出,当时义和团所兜售的法术迷惑范围已不局限于拳民。
义和团的武术实用技法在团众迅速扩张时期并未被大范围的正规组织习练,各地设立的拳坛亮拳的招式多为花拳绣腿,图增表演戏感,虽然拳师所传授的武术技法也涉及一些实用性的拳棒之术,但幻术成分弱化了其技法本能,从实用性的武术技法到虚幻色彩弥漫的武戏亮拳,拳民的武艺被拟具成神拳足以与枪炮抗争,而这正暗合于乡民头脑中出来的武侠世界。
海螺肉脱腥前共鉴定出33种挥发性成分,脱腥后共鉴定出27种挥发性成分(结果中去除了硅氧烷类化合物)。由总离子流图图4(A,B)可知,海螺肉脱腥后响应值明显降低,说明红茶处理效果显著。
2人神合一:身体聚合的过渡仪式
制川乌凝胶膏剂基质处方优化及体外释放研究…………………………………………………… 吴 璐等(1): 37
美国人类学家范热内普对神人转换理论抽象概括为“过渡仪式”,他将仪式看成是一个动态的过渡进程,内含着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分离—过渡—聚合:维克多特纳则对“过渡仪式”理论补充了“阀限”概念,强调从世俗到神圣的轨迹变换是以“阀限”来确立人神身份的界限,两种理论解释了仪式参与者在不同阶段的身份角色变化,从而建立了神人在时间和空间上共时性的跨界融合。义和团的的身体表演也是一个典型的过渡性仪式空间,依循着一个有序的仪式结构在身体中发生人神的聚合。
单是简单的模仿巫术,身体的表演或许只是延续了一般意义上巫觋文化原型,当宗教与巫术相结合时,巫术仪式的解释功能范围就逐渐扩大,甚至改变巫术的性质。巫术与宗教虽都涉及到神的意志,但宗教是一种外在意志的依附,巫术则是自我意念的崇拜,两者的杂合提供了肉体与灵魂在世俗社会所缺乏而又有所奢望的东西,互为呼应。要使神拳贴近于民,神灵概念必须符合民众的传统日常经验,以往传统观念中神灵多高居庙堂,人神关系难以逾越,要使得身体的降神仪式能够契合于乡民的幻想,将诸神的外在文化特质和习性添加于巫术仪式之中增加戏剧性是一种较为普遍性的做法。路云亭在论证义和团仪式的戏剧学功能时指出:选择在露天性公共空间演出,带有强烈的原始化、戏剧化和巫术化表演特色,团众喜爱的神灵戏和帝王戏,构筑了团众对晚清江湖世界的权力幻想,战斗戏和侠客戏中的强人形象根植于晚清华北地区民众的假设性和想象性世界,弥补了团众急需的神灵缺位[7]。当拳坛的仪式表演者已经不再是凡夫俗子或巫婆神汉时,任何肢体动作都改变其原有的意义体系。戏剧中的神灵对象可不加选择性地附身,例如猪八戒附体之人,则“忽倒在平地,向四处乱爬,唇上粘上许多泥土”:而孙悟空附体之人,则“又耍金箍棒,又要上树”[8],诸多事例不举繁多。神灵的在场排除了民众心理上的忧惧障碍,戏剧程序的公开表演又提供一个模拟性的镜像,穿上戏装,分不清世间英雄或戏中神明,难辨虚实,将乡民的意识置于神灵规训体系中,神人关系逐渐模糊,乡民的身体疯癫表演的也就构成了对外部虚幻世界的想象载体。
义和团所建构的身体仪式概念不仅表现为巫武合流的具象外在形态,还涉入到身体意识派生出来的神人对话机制,其中模仿巫武具象形态是实现人神对话的原始镜像,但身体的神灵附体单依赖于纯粹的巫武表演还缺乏超越世俗的可能性,因为在原始的神话观念中强调的是秩序性和等级性,所架构的神界和人界是相互隔离的,两者共时性对话的前提是人的本体意识超越世俗身体的具身性。
义和团的仪式意义就在于构建出另一个与世俗社会互相隔离神圣空间,凡俗事务将会被排斥,同时也意味着仪式过程身体会被迫滞留于世俗社会中。换句话说,人神的交流工具依赖于从具身肉体抽象出来的灵魂,即灵魂离开肉体去到神灵空间,而滞留于世俗社会中的身体则表现出理智与情感丧失的情景,出现一系列反常行为,从昏迷—颤抖—巫武表演—清醒整个过程身体按照世俗观念中逆反性的行为来展现,在身体的癫狂表演中观众自然而然被狂迷的场面所感染,加以仪式参与者对其先前身体行为的否决并添加“灵魂出窍”的记忆图景,选择性的建构了义和团的神灵对话情景。从另一方面来说,灵魂与肉体的分别搁置与灵肉合一也是通过“阀限”意义上的标识,是介于“分离”和“聚合”的中介状态,滞留于世俗社会的身体在灵魂的虚幻离身、肉体的巫武表演中完成了人神角色的过渡。
在“后阀限”阶段,肉体与灵魂再次归一,重新返回世俗社会,然而这不是以往那个备受摧残的身体,身体在经历过阀限阶段的灵魂出窍后,获得了神灵的垂恋并且将经验延伸至世俗社会的各个场合,其中就包括了战斗和交往行为。根据史料记载,义和团在交战前一般都要举行上法仪式以取得所谓的“刀枪不入”之术,而在世俗社会中确可寻得其武术原型,但习练其术需历练无数次的跌打磨搓和药水浸泡,配以运气吐纳,三五年方可小成,是硬气功的一种表演效应。后来得以神灵的相助,骗术成分才开始逐渐明显。概而言之,在战争过程中的上法仪式只是给世俗中的团民提供心理依赖,进而容纳伴随着身体的各种虚妄和缺陷,以获得了一种比较持久的具有神力相助的身体。
3仪式身体的例外话语:排斥罪恶的自我性
义和团身体表演无论是神智迷乱性或是理智清醒性,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人对神力的企望,类似于宗教信仰意识,但骨子里却是透视出人在支配着神灵的巫术思维[14]。需要指出的是,通常巫术意识中的神灵相当大的部分是狐仙鼬怪这种“神格”低下者,而义和团的巫术仪式却扩大了其神灵范畴,神灵对象的替代可以为义和团的种种行为预设出一种自我慰藉的道德空间,转移了对自我罪恶的讨伐,试想在支撑义和团屠杀教民的神灵中若以带有妖魔性质的狐仙鼬怪为主体,团民的身体近乎疯癫的演绎也难以诠释其行为是合乎“正统”的。
虚拟装配仿真技术在运载器装配中的应用…………………… 刘东,屈旋,刘文博,徐振国,干继远(12-261)
从原先教民与团民你死我活的生死较量到神鬼博弈,身体的表演促生了性质的变化。《拳事杂记》中记载“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15],和常规性的战斗相论,这种普遍存在于义和团势力所及之地的杀戮行为其实很难用人间常规伦理去规制,换句话说,非人格化的身体摧残是为杀鬼而准备的献祭行为。战斗时“逐一吞符诵咒,焚香降神”的神鬼战斗情景模拟为团民肆意的集体杀戮行为转接到了神灵身上,团民个体的杀戮罪恶则退到其次的位置上[16]。巫武合流形成的身体表演完成了在伦理层面对自我身体的排斥与忽视,获得了自我的罪恶救赎,一旦自我身体不再具有人间道德的话语评判,可以确定的是,身体的疯癫表演也就具备了建构义和团神灵知识体系的基本特质。
在义和团的神灵知识体系中,疯癫并没有完全被理性排斥,原因在于二点:一是疯癫看起来和某种终结性的真理相关,它是一种类似神启的、能够揭示终结性的神秘性体验;二是疯癫能够体验出人的某种悲剧性虚无感[17]。从义和团疯癫身体的表现形态上来看,巫术提供了一种悲剧笼罩下的身体激情表达方式,武术的戏剧配合渲染着身体的终极潜能,看似状若痴癫、穿凿附会的巫武表演,实则促生了民众对自我身体的排斥。从义和团所创制的仪式可以看出,神人衔接仪式对受众是不附设任何门槛苛约,乡民只需贡献自己的身体,模仿仪式动作,身体便会神灵相助,这对于地痞流氓、和尚道士、散兵游勇、乞丐以及农民等群体自然有着强烈的归附感,惯以的身体衣不遮体甚至遭人厌弃一旦体验仪式的疯癫历练获得身份的默许,被神灵占据的身体便可寻得庇护空间,在一个虚幻空间中的所有参与者都不由自主被某种幻觉集合到一起,而幻觉的集体性合一会挣脱身体的伦理绑架,进而造就出歇斯底里的身体。
4结语
或许巫武合流的身体表演仪式在幻觉中超越现实与虚构的界限或混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中无法去对世俗社会中的身体确立其存在的意义。义和团在仪式操练过程展现的身体经验显然是荒诞不经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所创造的身体叙事样本必然需要一个妥当的处置方式,最后只能将罪恶行为斥诸于世俗身体中并在神灵世界得以解脱,也完全符合团民对身体所赋予的秩序意蕴,即肯定现实秩序和否定现实秩序的乌托邦因素都被身体置于一个仪式场合中表达出来并完成自我救赎。
参考文献
[1] 谭广鑫.巫武合流:巫术秘密结社组织中的巫术影响研究[J].体育科学,2017(2):87-96.
[2] 佚名.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三分册[M].山东人民出版,1961:183.
[3]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M].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84.
[4] 中国史学会.义和团(1)[M].上海:上海出版社,2000:238-239,
[5] 王火选辑.义和团杂记[J].近代史资料,1957(1).
[6] 韩书瑞.山东叛乱:1744年王伦叛乱[M].刘平,唐雁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00-101.
[7] 路云亭.义和团仪式的戏剧学功能[J].文化遗产,2011(1):82-89.
[8] 董作彬.庚子佚事,义和团史料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9] 柴萼.庚辛纪事[G]中国史学会.义和团:第 1 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30.
[10] 编委会.拳事杂记[G]义和团:第 2 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240.
[11] 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M].宋军,彭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96-298.
[12]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15.
[13] 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丛刊:义和团第1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270.
[14] 周宁.天地大舞台—解析义和团运动戏剧性格的启示[J].戏剧,2001(3):51-67.
[15] [日]佐原笃介,浙东沤隐:《拳事杂记》,载《义和团》第一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6] 止庵.神拳考[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17] 夏天成.疯癫、疾病与身体——福柯疯癫叙述中的身体[J].医学与哲学,2018(4):25-28.
Physical Performance and Exceptional Discourse :Ritual Redemption of Boxers
LI Wen
(Shanwei soprts school, Shanwei 516600,Guangdong)
Abstract :The Boxer’s body performance basically simulates witchcraft,in which the witchcraft presupposes the intrinsic image of God-man interaction with its mysterious feature.The dramatized practice of Wushu obscures the hidden physical potential of God-man.The witchcraft and Wushu coexist in Boxer’s bodymind,and the merger between body and mind gave birth to the self-redemption of Boxers and created the Utopian order shared by the majority of people,thus providing the prerequisite possibility for the transition of "the unity between “God and Man".No matter what the argument is,bodily transition between God and man has also accomplished the moral education of self-redemption for the killing of the Boxer,which can reprimand the evil behavior in the secular body and free the body of the god.
Keywords :boxer; physical performance; witchcraft; rites of passage; redemption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63( 2019) 05-0098-06
DOI: 10. 13773/ j. cnki. 51-1637/ z. 2019. 05. 022
收稿日期: 2018-12-08
作者简介: 李文(1991—),男,江西赣州人,硕士,研究方向:体育运动与社会发展。
[责任编辑:付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