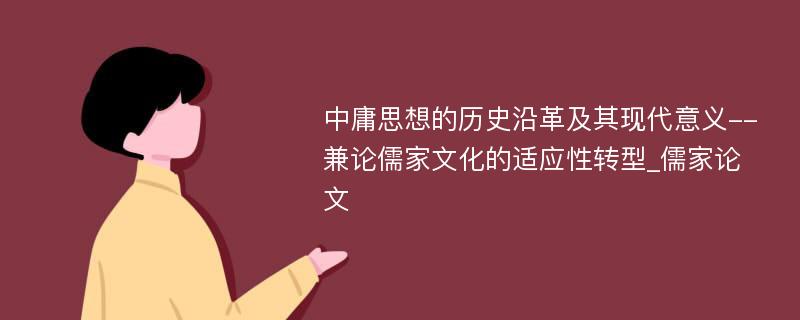
中庸思想的历史流变及其现代意义——兼论儒教文化的适应性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教论文,中庸论文,适应性论文,意义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庸”的概念始见于《论语》,但“中庸”的“中”字,作为道德规范和政治原则却产生于更早的时期,据《尚书·盘庚中》记载,商王盘庚的时候,由于黄河连年泛滥,于是决定迁都于殷,在作出这一决定时,他告诫百姓“谋长,以思乃灾”,从长远考虑,迁都以摆脱灾祸,在“万民”不与他“同心”时,他说:“汝分猷念以相从,各设中于乃心!”意思是说:你们应当各各把自己的心放得中正,跟了我一同打算。这里可以看出,中的思想首先起于社会处于变动状态时,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命令。其中“中”的意思就是要合乎标准,目的是服从。
到了周朝,由于被统治的殷民不服,政局动荡,于是周公列出两条原则,一是统治者自己“克永观省,作稽中德”〔1〕;二是“兹式(法)有慎列用中罚。”指出“民之乱(治)也,罔不听狱之两辞,无或私家于狱之两辞。”只有“惟良折狱,罔非不中”〔2〕,才能安民。
可见在周代,周人将殷王要民以中对待统治者转化为要求统治者以中待民,这就使中不单纯是指合乎标准,而且也包含“适度”的含义。“中”不仅用于德,而且也行之于刑,成为了一项政治原则。
从“中”的起源可以看出“中”正是出现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们需要秩序的时候,而孔子所在的时代也正是“礼崩乐坏”,在这样的时候孔子于是也呼求中庸之德。
从以上可看出,中庸首先是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提出的,这个问题首先是关注作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而“庸”这一观念的提出,则又将其作为一般政治原则来进行关注。理解这个概念的原始问题背景也许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概念本身。在我看来,儒家中庸观念正是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即和的问题,“如何使一个混乱的社会达到有秩序的和谐”,“如何使社会政治秩序与个人道德秩序达到普遍和谐”,使人们能够“各正其份”,“各得其理”,这正是中庸政治伦理所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如何中庸呢?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以后的历史中几经流变,其洋洋大观已远超乎中庸本身,而在我看来,有两种见解是极其关键的,从它们相近的概念解释中却会导致出截然不同的实际后果。这两种观点一种是“中和以为用”,另一种是“无过无不及的常然不易之理”。
二
据清俞樾考证,中庸乃中和祗庸四字的节略。何谓中和祗庸?《礼记》孔颖达《疏》云:“案郑《目录》云:名曰中庸者,以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可见在中庸概念里包含着中和之为用的观念。关于“中和之为用”,学术界常将《礼记·中庸》中记录孔子言论的一段话当作关于中庸的经典解释。
子曰:“舜其大智也欤?”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乃舜乎。〔3〕
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就是“中和之为用”的中庸之道,从这里可看出三点:
一、孔子这里关注的是社会政治问题,即要用于民,而不是要达到某种绝对的世俗之外的本体,因而对作为社会的“用”的观念很强调。
二、这种中庸并不是如后人所批评的是无原则的调和折衷,因为隐恶而扬善,执的是善的两端,可见这里存在善的界限,事实上反观《论语》,孔子是最为厌恶貌似厚实实则是非不分、一味奉迎的人,斥之为“乡愿”。这一点今人已多有指出,这里不再赘述。
三、但问题是:这里暗含着一个假设,即善的东西有可能是多样的,对立的,但却并没有一个在人们“迩言”之外更绝对的单一的善来加以裁量和权断,于是只能从这多元的善中取其中,那么这种中又是什么呢?只是从众多善中找到可调和的度,孔子重礼与仁,可是礼在先秦时期是一个含义十分广泛的社会学范畴,在儒家人文主义中它本身作为最高社会伦理范畴,而并不具形而上含义,这样礼在政治文化中并非如西方的《圣经》神圣不可动摇,而是由传统经典记载,循历史演变而来的各种善的集合。它本身常处于变动之中,孔子虽说“吾从周”,但却坚决反对拘泥古法,说:“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也。”〔4〕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寻求中庸的形而上归宿,而是实际行动,但在实际行动中,各种善的标准又并不相同,由于对绝对善的“敬而远之”,这种缺乏最高权威的情境只能导出“中和之为用”的主张,它在实际上的表现是,在尊重传统道德(礼)的前提下,对各种善折中调和以达到和谐,也只有这样,社会秩序就会和个人的道德秩序达到一种平衡。
孔子主张礼虽有常规,但也随时变化而有损益,因而中庸之道的关键在于“时中”,所谓时中,并非“时时而中”,而是“权”,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唐棣之华,偏其反而’。”〔5〕不拘泥于一时之执中,似乎“偏其反而”的中庸形式正是达到“权”的中庸形式的真谛。荀子说:
与时屈伸,柔以若蒲苇,非慑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申),非强暴也;义以应变,知当曲直故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义屈信,变应故也。〔6〕
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中和之为用”的中庸之道,中是在人们依据传统流传下来的各种不同的善中取其相互可包容的交叉域作为中正度,如果有对立的两种善分别走向各自的极端就只取其中,如果有一方善过于极端,则偏于另一方,使双方达到一种平衡,总之是通过对各种善的并存的认同而实现中。我们可以发现这里恰恰放弃了对某种最高善的终极关注,而所关注的是在一个社会中,如何达到使可接受的众多善共存和谐的问题。其目的正是为了解决上文所提到的社会和谐的问题,如果每个人的善德可以和睦相处,当然社会秩序就会归于统一,这里社会功用的目的其实具有了最真实的意义。孟子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也,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也。”〔7〕这句话本身正反映出“中和之为用”的思想本质,一种暗含着承认道德多元倾向的政治伦理。
但是,即算是这种并没有真正的绝对原则的“中和之为用”思想,因为仍然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讨论政治,以道德为出发点,就不可避免地寻求道德终极。这种矛盾是显然存在的,如果礼是至德,又怎么能随时变迁呢?随时而变,那么中的标准就难以把握,岂不太容易流于乡愿吗?从逻辑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确是难于回答的,从孔子的角度看似乎只有通过做,通过力行来近乎仁,但从儒学道统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却必须追溯,在德治主义传统思维模式里,这种追溯会将政治和谐的目标转化为寻求最高善的问题,中庸的意义也就将在既定的词语结构下发生流变,这样的流变我们正可以从《中庸》及其以后的理学中找到它的痕迹。
三
《中庸》一书很可能是《彖》、《象》、《系辞》和荀子用中论的混和物。子思学派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8〕这样就将中庸之道贯穿于天人之间,上升为宇宙论。另一方面子思学派又对“中庸”作了新的阐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结中节,谓之和。”〔9〕这里中节得到了强调,表面上看这与上述孔子的“礼为用,和为贵”的思想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里的节却因为上升到天命,从而具有形而上的本体,因而“和”会很容易地被赋予合乎某种先验标准的含义,而这就使其渐渐失去“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原始含义。
当然,《中庸》本身也仍然包含着许多原始儒家的思想,如和而不流的君子之道等,但随着历史演进,《中庸》的神秘主义倾向得到更多的发展,以至超过社会政治领域的范围。中庸作为至德得到士大夫知识分子更深的发挥,一方面它被看作个人道德人格的完善;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伦理,它却发展出一种来自于天道的道德绝对原则,到了二程理学,这种原则完全哲理化,形成中庸思想的另一面,即“无过无不及的常然不易之理”。
这方面,最著名的也许是程颐的一段话: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10〕
这里程颐明确地把中定义为不偏不倚,把不易之定理作为庸的本义,尔后朱熹在把二程这段话收入《四书章句集注》后,也说:“庸是常然之理,乃古万世不可变易底,中只是个恰好道理。”〔11〕这里中庸作为至善,已完全显示出道德一元论的倾向。
这种至德的观念当然可以追溯至孔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的说法,但是孔子本人却并未详加论述。但理学显然不满于此,他们将庸不解作“用”,而解作“常行”、“常理”,常是对变而言的不变,不变的也就是绝对的,而不偏不倚地合乎这种绝对的标准,就是中庸,作为这种绝对标准的庸就是“天命之性”、“天理”。而在天人合一的模式里,天理所决定的传统礼法秩序便是社会绝对应遵守的制度。朱熹显然反对那种求天理要超越现世到彼岸去的看法,而是试图在日常生活中保卫其礼教规范,克制人们私欲来实现不易之理。只有革尽人的私欲,在生活中时时而中(这里的时中与“中和之为用”的“时中”显然不同),而无过无不及,时时中乎天理,才是中庸。
我们可以将“无过无不及的常然不易之理”的政治原则作如下总结:一、达到社会的和必须共同遵循一个先定的绝对的道德原则及其所规定的秩序。二、每个人都应通过抑制自己的非礼的私欲来使自己合乎这种绝对原则支配下的礼教秩序。三、如果能够通过某种修养教化,使人时时遵循这种原则,使社会各阶层“各正其分,各安其理”,那么就可以实现社会普遍的和谐,如果由于“世不教,民不兴”〔12〕,就要由承继道统的知识分子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改变混乱状况,恢复和谐的统一。
正因为认着天地只有一善,“阴阳只是一气”〔13〕,从这样一种中庸思想,我们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一种道德一元论倾向的发展。
这种绝对主义的倾向自然不会满足于无过无不及的常理,到了明末清初王夫之那里,他对朱熹的无过无不及进行尖锐的批评,认为“中庸二字,必不可与过不及相参立而言。”〔14〕“狂狷总是不及,保所得过?圣道为皇极,为至善,为巍巍而则天,何以中为极至,参天地,赞万物,而无有可过,不欲使人谓有止境,而偷安于苟得之域。”〔15〕这种“无过之境”的中庸自然便超越了世俗中人可达到的境界而成为永恒的追求。
然而这种永恒追求的中庸究竟包含着什么内容?是否还可以中庸名义声称?这些王夫之并未详加论述,随着晚清末年急风暴雨式的变革,王夫之的思想未来得及深入地关注便在对中庸的彻底批判中淹没了,这以后中庸的政治思想再难得发展,但中庸观念作为一种日常伦理,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却依旧在今天的社会中随处可见。
四
从以上中庸思想的流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庸概念本身就包含着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一种是在社会功用原则下的“中和之为用”;另一种中庸则是在绝对天理基础上的“无过无不及的常然不易之理”。这样两种概念的理解又是在同一个问题下统一起来,即如何使社会的秩序达到和谐。这个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问题无疑具有一种整体主义的倾向及社会有机论的暗含前提,其思维特征仍是儒家的实用理性,他们共同关心的仍是如何适应变革中的现世。当然他们都尊重传统的礼及其所规定的善。当一个社会共同体处于封闭状态时,他们的政治主张是相似的,然而当这种共同体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一种外来的文明进入而破坏了原有的和谐状态时,对于恢复和谐状态的道路,这两种中庸观念却会产生截然不同的主张。
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随着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定为钦定教科书以后,“无过无不及的常理”逐渐成为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精英意识形态,成为一般学者知识分子的共识,但是“中和之为用”的观念也依旧广泛地存在于民间,尤其对明清之际的商业阶层产生着重要影响。这样概念的对立也就导致了两种传统的分化,儒家被分为儒学与儒教二个层次,儒学传统以先秦儒家经典为代表,并以后代儒学知识分子不断解释和发微的书面经典儒家思想及其所体现的儒家道德修养为追求,而儒教传统是其中的社会伦理、经济伦理、宗教伦理、政治文化在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经过世俗化、社会化所积淀而成的儒家的教化。前者类似于人类学的“大传统”,后者可称为“小传统”。而“无过无不及的常然不易之理”这种在现世中追求形而上理想的中庸价格自然会成为读圣贤书的中国儒学正统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并演变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以文天祥、海瑞这样为保取历史道统而不惜牺牲现世生命的道德榜样来证明其现世的真理性。但是在社会动乱中,如果外来的文化冲击太大,社会已处于激烈动荡的情况下,这种道德一元论又容易排斥外来文化,产生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心态。随着礼教秩序在近代崩溃,中庸概念本身也无奈地退出意识形态的舞台。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儒学的中庸。
另一方面“中和之为用”这种对现世的多元善采取折衷、妥协以达调和的中庸之道却在宋明以后,在正统儒家的不屑中成为儒教影响下的民间社会的伦理原则,而且在动乱不定的时代里,一些靠近民间的儒家知识分子也往往认同这一观念,他们在相对稳定的社会里,表现出对传统的尊重,但是当外来文明进入以后,却能以实用理性的态度,对各种相互冲突的道德采取折衷调和,既不急于排斥反而常常认可外来文明的既成冲击,又不彻底否定而是试图保留现有的传统规范,他们在中和的思维倾向上通过自己不断地变更或实验来找到相互融合的调和适用点,从而完成一种渐进的转换。当然这里的度是依据双重标准(传统和功用),这个标准很容易产生失范,形成善德与恶德的执中,但在这种实际的渐进转换过程中,社会本身经过不断地试错和纠正,却能逐步走向一种新的规范,而这种新的规范又可以被人们认可为本有的传统精神的新的发扬。我们可以把这种中庸称之为儒教中庸。
这种儒教的中庸以往常常被混同于儒学的中庸,但在实际的社会政治领域里两者又有着很不相同的行为倾向和后果,从而造成关于中国人是否中庸的认识上的混淆,而儒教中庸在我看来,有必要更深入地进行分析,大体说来它具有这样一些原则:
一、对终极形而上的道德敬而远之,不关心也不讨论。
二、注重现世的道德生活,尤其是尊重仍保留在现世的各种善,承认道德的多元。
三、从整体主义的政治实用理性出发,主张通过整个社会的“中和”来寻求某种社会的平衡以保证各种善德的全面发展。
可以说,中国儒教社会政治文化最基本的精神正是为寻求社会的和谐而进行对传统的适应性转换(我之所以称为适应性转换,是因为它以适应性为倾向,以相互适应作为目标来对原有的传统道德秩序和外来的道德秩序进行变更和改造,通过调和的方式来完成这种转换,这种转换显然不同于创造性转换——林毓生语,所以我称之为适应性转换)。一方面它也许缺乏韦伯所说的“人对于‘现世’的紧张对峙”〔16〕,但另一方面它又会在这种伦理的指导下,在社会变迁中表现出对传统既有制度的弹性,它往往不再死守原有的正统制度和意识形态(但也决不轻易抛弃),而是注重调整实际发生的各种非正式关系,以保证社会实际的运转不致中断,社会各种道德关系不致于破裂,这样原有的社会关系便发生转换,通过执中的方式,中国民间社会便会重新适应一个新的已经变化的现世。而支持这种适应性转换的中庸伦理在我看来正是韦伯所说的中国儒教文化适应性的一个更深的原因。
五
韦伯作为一位中国学研究的“伟大的外行”,其所著的《儒教与道教》一书却以其独特的方法论启迪着后来中国学的研究者。
他认为在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类似西方的理性资本主义,除了物质因素外,最基本的是因为缺乏一种像禁欲的新教那样的精神气质。他认为“中国的宗教意识是把用以制服鬼神的巫术性宗教仪式和为农耕民族制定的历法结合起来,并赋予他们以同等的地位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17〕,这样,“作为终极的、至高无上的道,不再是一个超世俗的创世主,而是一种超神的、非人格的,始终与自己同一的,时间上永恒的存在,这种存在同时是永恒的秩序的超时间的表现,这种非人格的天威并不向人类‘说话’,它是透过地上的统治方式自然与习俗的稳固秩序——也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以及所有发生于人身上的事故,来启示人类。”〔18〕这种“人道统摄天道”〔19〕产生了“追求秩序的理性”,“使儒教对世上万物采取一种随和(Unbefangen)的态度”,“它将与这世界的紧张性……减至绝对低弱的态度”〔20〕,因而对于中国人,“正确的救赎之路在于适应那永恒的、超神的世界秩序——道,也就是适应那些由于宇宙和谐而产生的共同生活的社会要求,所以虔诚地顺从世俗权力的固定秩序显得尤为重要。”〔21〕韦伯认为由于“从来没有出现一个超世的、提出伦理要求的上帝作过伦理的预言”〔22〕,因而儒教缺乏任何“自主的伦理”,它的“任务只在于适应此世”。〔23〕
韦伯这里显然是把中国的儒家传统看作一个整体,而并未作儒学与儒教两个传统的区分,因此,在儒学知识分子那里仍然存在对形而上追求的困境意识,而并非韦伯所说的对此“毫无兴趣”。也正如狄白瑞在《中国的自由传统》一书中所表明的,中国理学知识分子存在着个人自主性,存在先知式的启示。〔24〕但是在我看来,韦伯的观点却正揭示出中国儒教社会的适应性特征这个更普遍更深刻的一面。
因为正如以上分析,尽管儒学在内心道德上存在对形而上的超越,存在道德理想与现实社会的紧张对峙,但一旦落到社会政治层面,天人合一,社会现世的和谐仍是作为首要目标,因而韦伯在这里的社会学结论就没有什么错误,但是韦伯这里并没有明确地指出在适应无言的道与现实的对世界的适应性之间究竟是通过什么政治伦理原则来完成过渡的,尤其是现世在发生大的社会变动的时候,而在我看来,正是中庸政治伦理,尤其是儒教中庸思想使事实上的中国社会将适应天道与适应现世统一于社会政治层面。
由于儒教中庸并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道德内容(因为天是空寂的),而它又被置于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因而也就使儒教伦理暗含着对多元道德的接受,因此一旦新的文明原则为世俗权力所默认,儒教社会便会以追求社会共同和谐为目标,寻找双方可对接的交叉点,同时努力防止或淡化对立方的不可调和点,并以各种方式在不断对接的过程中适时淘汰和平衡极端的主张和原则,从而达到社会共同要求的和谐。
60、70年代以来东亚现代化的崛起,使人们重新看待儒家传统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普遍认识到东亚现代化不同于韦伯的西方理性资本主义,从经济上看是这些国家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采取了正确的发展战略;从文化上看,有人认为儒教伦理可以替代新教伦理,成为现代化的动力,而不是阻力,尤其是新儒家试图从儒家中发掘出韦伯所没有看到的创造性精神。
然而正如上述所示,我想我们是否可以换另一种思路,即儒家文化成为东亚现代化的动力恰恰在于它的适应性转换呢?东亚现代化是一种后起的在外来文明的刺激下产生的现代化,因而可以推论:东亚移入的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正提供了一种新的制度、环境来激发出人们追求财富的创造性精神,而中庸政治文化又使人们能主动寻求自己的日常工作伦理与制度文化的对接点,正是在这种求和的伦理倾向下人们才会逐渐产生出理性化秩序,也才能在保持对传统的一贯性的基础上来适应这种秩序,而也许正是儒教伦理这种神奇的适应性转换才使东亚社会不像其他某些后起的现代化国家那样在其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现代与传统的极端对立和分裂,而是在渐进过程中较快适应自由主义伦理,并对其完成改造,从而或许会产生一种又被传统精种认同的新的道德秩序呢?
注释:
〔1〕《尚书·酒诰》。
〔2〕《尚书·吕刑》。
〔3〕〔4〕〔8〕〔9〕〔11〕〔12〕朱熹:《中庸章句集注》,见《四书五经》,天津古籍书店,1993年,第3页,第14页,第1页,第3页,第6页。
〔5〕《论语·子罕》。
〔6〕《荀子·不苟》。
〔7〕《孟子·尽心上》。
〔10〕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31年,第100页。
〔13〕朱熹:《朱熹文集》卷五十,《答扬元范》,转引自庞朴:《中庸平析》,第98页。
〔14〕〔15〕王夫之:《读四书大全》卷上,转引自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社科出版社,1989年,第175页。
〔16〕〔17〕〔18〕〔20〕〔21〕〔22〕〔23〕M ·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洪天富译,第359页,第35页,第35页,第257页,第258页,第259页,第270页。
〔19〕见熊十力:《原儒》,台北明文书局,1988年,第7页。
〔24〕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李弘祺译,1983年,第7页。WW章克团
标签:儒家论文; 现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庸论文; 国学论文; 读书论文; 政治倾向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孔子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