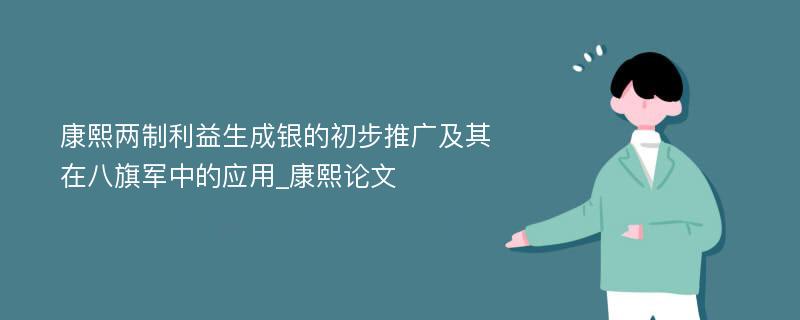
关于康熙对生息银两制的初步推广及其在八旗军队中的运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银两论文,康熙论文,军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康熙时期的生息银两制度状况,学术界虽有较多研究,但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系统的阐释。近年来,韦庆远先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上刊发的系列论文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确是颇见功底的史论佳作;特别是“分阶段各具特点”的观点,(注:韦庆远先生的三篇系列论文题目为:《康熙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初创和运用》、《雍正时期对“生息银两”制度的整顿和政策演变》、《乾隆时期对“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分别刊发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1987年第3期、1988年第3期。以下引注简称: 《初创和运用》、《整顿和政策演变》、《衰败和“收撤”》。)应该是今后该研究领域的基本框架之一。但是,他认为,生息银两制度最早源于内务府而扩及于其他部院衙门、康熙时期是生息银两制度的初创阶段、(注:韦庆远:《初创和运用》。)以及八旗军队中推行生息银两制度始自雍正上台之后的观点,(注:韦庆远:《整顿和政策演变》。)则是值得商讨的。
向商人放贷帑银并收取本息这样一种生息银两制度的基本型态和主要活动内容,早在顺治及其以前的关外时期就已存在;它最初实行于户部并由户部主持管理,到康熙初年才被推广到内务府,(注:参阅拙文《关于清代生息银两制的兴起问题》(以下引注为《兴起问题》),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到康熙中期又被推广到八旗军队、个别驻防及其他部院衙门之中,到康熙晚年又被大大收缩。可以说,康熙时期对生息银两制度的政策经历了两大阶段,即康熙初年到康熙五十六年的推广阶段和此后到去世为止的收缩阶段。
一
康熙皇帝在其执政的六十多年中,对生息银两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推广和运用。如果说这种推广为整个有清一代军政旗营各级衙门广泛地推行生息银两制度开辟了先例的话,康熙时期无疑是一重要时期,堪称“创办阶段”。然而,仅就该制度的基本型态而论,则不能说是康熙的“初创”,因为它在康熙之前就已形成了。(注:参阅拙文《关于清代生息银两制的兴起问题》(以下引注为《兴起问题》),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康熙只是将这一制度加以次第推广和运用,并在此过程中对之进行了某些运作环节的改革,从而创设了“公库”制、“恩赏”制和“广善库”制等各具特色的生息银两制度经营管理方式。
公库也称“官库”,即康熙从户部帑银中拨出一定数额的款项交给八旗都统衙门及其他部院衙门主管,贷借给八旗、驻防旗丁和官吏人等,定期定额收缴本息的制度。其主要目的是解决旗丁债务和生计问题,并对官吏人等进行特殊照顾。康熙皇帝究在何时创设这一制度,目前还难以确定。就现在掌握的文献材料推测,似乎应在康熙三十年(1691)。据康熙二十九年十月谕户部:“曩日满洲初进京时,人人俱给有田房,各遂生计;今子孙繁衍,无田房者甚多,且自顺治年间以来,出征行间,致有称贷,不能偿还,遂致穷迫。今将满洲兵丁旧日债负作何清结,俾各遂生计,该出征兵丁回日,酌议之。”(注:《圣祖实录》(二),卷149,卷150,中华书局影印本《清实录》五,第644页,第664— 665页。)可以看出,康熙对旗丁的缺少房地、生计贫困问题十分关切。当西北地区战事即将结束之际,他要户部商酌一项解决方案,同时也是作为对出征凯旋旗丁的慰勉犒赏措施。到康熙三十年二月,他再次发出谕旨,除重申旗丁生计问题外,还要求户部动支库银替八旗满蒙护军校、骁骑校、另户护军、拨什库、马甲及其子幼等下级军官和贫穷兵丁清偿债务;汉军则以佐领为单位,各划拨银5000两令其偿完债务,所剩余银由各佐领收贮,以备公用;考虑到旗丁完债后“有不得已而称贷之事”及由此引起向户部借支的“事务繁扰”,康熙决定:“今发帑银交与八旗,将各旗内部院堂官派出,会同该旗都统、副都统,视其需用之事借给,于每月钱粮内陆续扣除”。康熙认为,“如此,则兵丁不至窘迫,将来可免称贷之累,永有裨益矣”。(注:《圣祖实录》(二),卷149,卷150,中华书局影印本《清实录》五,第644页,第664—665页。)
上述康熙三十年间开始由户部向八旗划拨专门款项,派令八旗之中在部院衙门供职的堂官会同八旗都统衙门负责管理,向旗丁贷放银两并从其月饷内扣还的制度,是否为公库制的开端呢?在笔者看来,这是极有可能的,起码应视为公库制的雏型,理由是:
第一,清政府用户帑替旗丁还债之举早在康熙二十年(1681)三藩之乱平定时就实行过,“共费五百六十万金有奇”,(注:萧一山:《清代通史》一,中华书局影印本,第478页。 )但并未能解决旗丁贫困称贷问题。所以,康熙三十年除依照前例颁户帑清理旗丁债务,又拨户帑作为向旗丁贷放的专项基金以资急需,并从其饷银内陆续扣还。可见,基金措施与以往只为旗丁清理债务的一次性拨款有原则区别,是康熙经过思考之后对解决旗丁贫困称贷问题作出的政策性调整,也是康熙认为可使旗丁“不至窘迫,将来可免称贷之累,永有裨益”的规章制度。(注:《圣祖实录》(二),卷149,卷150,中华书局影印本《清实录》五,第644页,第664—665页。)
第二,据康熙四十五年(1706)上谕:“朕念八旗禁旅为国家根本所系,时加恩爱养用,俾其生计充盈,或动支公帑数百万代清积逋,或于各旗设立官库资济匮绌……,康熙四十二年又曾颁发帑金贷给八旗兵丁共六百五十五万两有奇,至康熙四十五年冬,除陆续扣完外,尚未完银三百九十五万六千六百两有奇。后仍行按月扣取,恐各兵营办器用、赡养室家必有不敷之虑……兹特大沛恩施,式弘抚育,将未经扣取银两通行豁免。”(注:《圣祖实录》(三),卷227,《清实录》六,第278页。)康熙五十六年上谕说:“设立八旗官库以济官兵,四十五复施恩将官库未经扣完银三百九十五万六千六百余两尽与除免”。(注:《圣祖实录》(三),卷275,《清实录》六,第699页。)又,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上谕户部:“今各佐领借支未还银两,如仍向各佐领按数扣除,则兵丁粮饷必致不敷。著将官库利银七十万两抵还此银之数,免其扣除。”(注:同上,卷222,第233页。)这几则材料联系起来考察,则其一,八旗官库制在康熙四十二年以前就已建立,其二,从官库借贷帑银的旗丁须从月饷内陆续扣还本息(按制度要求)。既然康熙三十年向八旗划拨户帑,派令八旗内部院堂官会同八旗都统衙门负责贷放给旗丁并从其饷银内扣缴归还之制已经符合官库制的基本特征,那么,笔者以此认为,官库制开始于康熙三十年。(注:关于官库、公库的称谓问题,从《清实录》的记载来看,八旗、部院衙门似乎不甚一致,但就其经营方式来看,属于生息银两制度的同一类型。康熙、雍正、及乾隆皇帝称公库的为多。其开始推行的时间,未见有人考证。笔者在此持康熙三十年之说还有待发掘更多的材料验证。)
二
康熙时期除设立八旗公库,一些驻防和行政衙门也设立公库。康熙四十二年(1703)十月,盛京礼部侍郎哈山奏称:“臣部所役网户采牧校尉等八百二十五人,内无力婚娶者百六十余。此等人役因无室家,往往不务生计,逃避官差,请发盛京户部银四万两,仿公库例,派员经理,一分生息,以六年为期,本还户部可得息银二万八千余两,陆续给与无妻壮丁完娶银,人五十两,仍将余银生息,久远有益。”此奏被议定实行。(注:蒋良骐:《东华录》卷19,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0 页。)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京口驻防旗丁经镇海将军马三奇奏准,仿公库例,借银45000两,“以资生理,按月一分起息, 于月饷中扣除”。 (注:《高宗实录》(二),卷141,《清实录》十,第1027—1028页。)该年十一月,吏部讨论山西巡抚噶礼奏参潞安知府白邦杰“借欠官银一年限满未完”一案,“请将白邦杰降俸二级,令其戴罪完结”。康熙就此谕令:“凡借官银者,因不能完银,治罪。若留任追赔,必希图还债,以致尅剥小民矣。嗣后凡牧民官员借欠官银不能完纳,即令离任追赔,已还后准其开复。如不能还清,即以家产抵偿。如此则官银不致亏欠而亦无剥民之事矣。”(注:《圣祖实录》(三),卷 231; 《清实录》六,第312—313页。)在当时,贷借官银的旗丁、 官吏是要照本纳息的,旗丁归还期限以月计,衙门官吏则以年计。
公库制在实行过程中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最后由于弊窦百出撤除了一些系统和单位的公库。首先撤除的是八旗公库。康熙时期曾有三次向八旗公库划拨巨额户帑。康熙三十年拨款数额虽然不详,但就康熙四十二年的第二次拨款655万多两估计,第一次公库拨款不会太少。 第三次拨款在康熙四十五年(或四十六年)。当时考虑到旗丁借欠库银若继续按月扣还,“恐各兵营办器用、赡养室家必有不敷之虑”,所以康熙谕令“将未经扣取银两通行豁免”。(注:《圣祖实录》(三),卷 227,《清实录》六,第278页。)可是,如此一来, 旗丁借款漫无节制,视同饷银一般到官库借支,用康熙的话说是“官库事务渐至纷扰”。这就迫使康熙改变措施,下令“停止八旗之库,设立总库”。(注:《圣祖实录》(三),卷275,《清实录》六,第699页。)关于“总库”,也就是第三次公库拨款数额,史无明文记载。但是,总库“每月扣取钱粮”之事仍在进行,而且使康熙“深为厪念”的是,“领取银两兵丁,甫出部(指户部——引者)门即被人持取,公库即行扣除,又复偿还私债,兵丁所剩甚少,以此养赡身家、奉行差务断然不足”。(注:《圣祖实录》(三),卷275,《清实录》六,第699页。)以这种普遍频繁且持续近十年之久的公库借贷扣还情况蠡测,第三次公库拨款数额绝不会少于第二次。所以,笔者估计,八旗公库的三次户帑拨款总数当在1500万两左右。对于清政府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财政开支,而对旗丁来说虽可济一时之需,却不能解决贫困称贷的根本问题——正如后来雍正批评的那样:“从前皇考恩养兵丁,屡加赏赉,代偿甫欠,又设立公库以利济之,惠泽虽频,空乏如故,曾何裨益乎?”(注:《世宗实录》(一)卷7,《清实录》七,第227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谕户部:“停止公库,将现今未行扣完银一百九十六万八千两有奇通行豁免,自五十七年正月为始,著给与兵丁全份银两”。(注:《圣祖实录》(三),卷275,《清实录》六,第699页。)至此,康熙时期在北京八旗中推行了26年的公库制寿终正寝了。随后,其他衙门和驻防旗丁的公库也相应撤销。
三
康熙时期还出现了后来雍正、乾隆时期广泛实行的“恩赏”制和“广善库”制。据乾隆五年(1740)十二月宗人府奏:“从前圣祖仁皇帝因念宗室日繁,如遇喜丧事件,不无艰窘,特赏资生银两,自奉行以后未经详定章程。酌议:嗣后凡现任王、贝勒、贝子、公等之子及已薨、已革而其子已袭爵分产者,概不许支领;又,一二品宗室人员亦不准支;如业经亡故,遇有喜丧等事,系亲兄弟、伯叔与近支子弟承办者,照承办人职衔支给。再查侍卫处,例支恩赏银两,其宗室侍卫既经宗人府领给,侍卫处应行停止。”(注:《高宗实录》(二),卷132, 《清实录》十,第926页。)这则材料说明, “恩赏银两”在康熙时期已实行于宗人府等衙门,只是当时未定详细规章,于何人该领赏、何人不该领赏、赏额的具体标准以及限制条件等事项未予明确规定,因而存在着一人有数重身份与职爵重复领赏,另外一些应该领赏却不能领赏等问题。
宏观而论,恩赏制、广善库制、公库制等均属生息银两制度的范畴,都是生息银两制度的经营管理形式,它们的称谓也可以互用称代。但从微观处着眼,它们在运行管理规则方面又存在着差别。恩赏制是把库帑管理经营所取得的利息赏赐给有关人员,受赏者没有偿还帑银本息的义务。公库制和广善库制则是将帑本直接贷借给有关人员,这虽然亦可称之为“赏”,但受“赏”者却是债务人,须定期额缴还本息——后两者的区别在于利息高低不同:公库制月息一分,广善库月息五厘。据乾隆六年(1741)四月上谕:京口驻防曾实行公库制,所借户帑45000 两,月息一分,由旗丁饷银内扣还;“至康熙五十八年(1719)经何天培奏请,以余利银九万一千九十两作为帑本,照广善库之例,以五厘起息,奉旨久行在案”。(注:《高宗实录》(二),卷141,《清实录》十,第1027—1028页。)康熙四十三年(1704)、四十四年(1705),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通过钱法堂奏请,分别向所属“炉头”借放户帑10万两,不但利息极轻(分别为2厘、3厘),而且还本期限也很长(分别为6年、20年);所还本息并非白银,而是新铸大钱。 (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第270—272页。参阅韦庆远《初创和运用》。)当时京师地区“若以白银十万两可换新铸大钱十四万吊,现用小制钱可换十五万吊,是伊等先占朝廷三万两之帑银矣”。(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第270—272页。参阅韦庆远《初创和运用》。)借贷条件是如此优惠,无怪乎被清廷视之为“赏借”,也无怪乎被纷纷请求“赏借”。(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第270—272页。参阅韦庆远《初创和运用》。)即使是公库一分利息也大大低于市场利率(一般为月息三分),所以亦成为商人、官吏、兵丁百计追逐而唯恐求之不得的“赏借”标的。
当然,公库制、广善库制与恩赏制之间的区别只是大致而论。事实上,它们在推行过程中是可以变通的。如康熙四十二年十月盛京礼部所设“网户”公库,其利息虽为一分,但归本期限却是6年, 所营利息是“给与无妻壮丁完婚银(每)人五十两,仍将余银生息”,即营运利息的分配去向和流通方向又类似于恩赏制。再如前述户工两部宝泉、宝源局向“炉头”借放的库银,名义上是为“官库”(即公库)生息,但实际利息要比该制的标准利息低得多,归还期限也长得多。再如京口驻防原设公库月息一分,后来就奏请改照广善库之例,“以五厘起息”。这些事例说明,康熙时期推广运用生息银两制度还是初步的,其各项规制细则尚在摸索试验阶段。由于材料缺乏,除公库制外,其他的恩赏制、广善库制等具体出现于何时已不可考,但就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公库制出现在前,其他规制大概是在公库制试行的基础上逐渐改进而形成的。
四
康熙时期推行生息银两制度与前代明显不同。前代实行生息银两制度虽不排除营利目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官商周转资金的困难,以便实现官衙、军队与社会之间的物质交换。(注:如《盛京原档》第201号:正红旗吴守进(据《太宗实录》载, 时任户部参政)“勒索官庄庄头”和官商人等财物,“修实胜寺佛座采买颜料时,故令其包衣邵麻子增值冒破,发库内货物贸易以为长短,吴守进将余价归入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盛京刑部原档》,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92—93页)。顺治即位诏旨:“柴炭钱粮,向来派顺天、保定、山西六十八卫所掌印官于军饷内扣除解兵部给发商人承办。今卫所军饷久停,前项银两,户部即于应发军饷内除出,径自招商办买,以供内廷烟灶……。”(《世祖实录》卷9,《清实录 》三,第96—97页)这些记述均说明,由户部负责设立官商,向其贷放帑银以解决官商周转资金,实现官衙、军队与社会之间的物质交换的必要性。(参阅拙文《兴起问题》)。)天聪、崇德年间对兵丁赏赐主要源于“战利品”,并不依赖生息银两。顺治入关后,受落后的农奴制的惯性作用,八旗官兵分配给“圈占”的房地,其租息收入分配再加定额领取的粮饷,则“战利品”赏赐虽较以前大为减少,但生计尚不至发生大的困难。其时内务府和宗室人口较少,赏赐所费有限,所以,户部调拨少量款项再加内务府收入,也不存在依赖生息银两作为赏赐基金问题。事实上,由户部主持管理官商贸易与生息银两事宜的惯例也未扩及内务府。(注:参阅拙文《关于清代生息银两制的兴起问题》(以下引注为《兴起问题》), 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至康熙时期,旗入中“闲散余丁”人数激增。这些人既不当差,也不能从事生产以自食其力,由此逐渐养成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吃喝嫖赌的奢糜习气,随之又扩散到八旗军队之中,终于导致旗丁典买房产、生计维艰、债务累累。康熙中后期就是企图运用生息银两制度作为手段来解决旗丁贫困称贷问题的。虽然户帑本身不以旗丁为营利对象,但是,“设立公库以利济之”的目的却很明确。(注:《世宗实录》(一)卷7, 《清实录》七,第227页。)试观康熙最盛时期,户部库银总额有5000万两, 而八旗公库生息本银的拨款前后几达1500万两。同一时期,康熙贷放给商人、官吏、官营工业职工人等的生息银两不为不多,若与八旗公库相比仍是较少的。(注:据韦庆远《初创和运用》的研究,康熙时期向内务府系统的官吏或盐铜商人发拨的生息银两额数计有:康熙三十九年李煦奏借10万两;四十年曹寅、王纲明等共奏借10万两;四十二年批借淮商100万两; 四十三年批借芦商70万两;四十五年江宁织造曹寅担保,依例向该织造衙门库吏、笔帖式等批借各4000两;前述共200 万两左右。此外, 康熙四十三、 四十四两年向户工两部宝泉、宝源二局“炉头”共批借20万两。据《清实录》载,到康熙五十六年收缩生息银两之前,这个规模变化不大。虽然韦先生所提供的材料尚不包括同一时期向随军经办军需的官吏、官商以及赴朝鲜、日本贸易物件的官商、官吏的生息拨款,但我估计这些款额总数不会超过200万两(参阅《清实录 》六,第596—597 页、第785页;另参阅拙文《兴起问题》)。考虑到该时期盛京内务府和部院衙门向商人、官吏人等的贷款数额又不会超过关内,则关内外这类生息款额总和当在350万两—700万两之间,可见要比八旗公库生息银两额数少得多。)因此,康熙时期的生息银两制度,除用以解决官商流通资金、照顾近侍宠幸和衙门官吏,其实施重点在于推行八旗公库以解决旗丁贫困称贷问题。
可是,康熙时期推行生息银两制度的效果并不理想。如前所述,这是把在商人之中实行的经济制度进一步推广运用到八旗军队与政府衙门之中,虽然帑银利息很低,但是,旗丁不能、也不善于运用这笔借款赚钱营利,而是将其投入消费领域很快就挥霍一空,单凭微少的月饷收入是无力归还帑本利银的,从而使公库流动资金严重亏欠呆滞。在这种情况下,康熙为了使旗丁月饷收入足额以稳定生计,只有豁免旗丁所欠本息。最后只得终止实行八旗公库制,没有达到“永有裨益”的初衷。
生息银两并非仅限于金融经济问题的范围。旗丁将借贷的生息银两视同饷银,随手花费,甚者惟知纵酒酣饮,鲜衣肥马,过于费用,“不数日间仍如未沛恩之时”。(注:《圣祖实录》(三),卷212, 《清实录》六,第150—151页。)这不但是康熙所始料不及,也使他的子孙雍正、乾隆为此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官吏借贷生息银两亏欠不还者甚多,他们在管理经营过程中又千方百计地投机分肥。(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第270—272页。参阅韦庆远《初创和运用》。)由此导致了官场上的市侩习气,加重了贪污之风。康熙时期曾有“惩贪倡廉”之举,却收效甚微。雍正上台后不得不采取严酷的惩治手段,才使每况愈下的吏治官风有所改观。然而,狂风骤雨过后,一旦有适宜的环境,康熙时期播下的贪种又会迅速滋长蔓延起来。乾隆时期吏治恶化就是明证。诚如韦庆远先生所言,康熙时期的生息银两制度“具有客观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具有自己的生命力”;它的实施取得了相当的经济效益,但也存在着严重缺失,总而言之“是失于纵弛和宽滥”;“如非在方针和方法上作较大幅度的纠正和变革,要再维持并发展下去是很困难的”。(注:韦庆远:《初创和运用》。)康熙皇帝也觉察到这一点。他在晚年基本上收撤了八旗军队、内务府及政府衙门的巨额生息银两。还在康熙五十六年四月,他的亲信兼两淮盐课监察御使李煦代盐商奏请“再借皇帑”:“窃两淮众商于康熙四十二年蒙我万岁天恩借给帑银一百万两。据众商口称:‘自借皇帑之后靠万岁洪福,生意年年俱好,获利甚多。万岁发的本钱极其顺利,我们四十二年借的已完在库。今求代题再借皇帑一百二十万两,商等认利十二万两,分作十年完纳,我们再领圣主本钱,两淮生意就好到极处了,务求据呈题本’等语。奴才以钱粮重大,何容冒昧具疏,而事关商情,又不敢壅于上闻,谨将商人呈子恭进御览,伏乞睿裁批示遵行。”(注:《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七册,第 823页。)李煦在此折中以请示“睿裁”的口气婉转地表达了他支持向淮商借帑的态度。可是,康熙对淮商完纳课税与归还帑银本息状况不满,折中朱批:“何偿他们完的?可笑!”折尾总批:“借帑一事万万行不得,再不要说了!”(注:《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七册,第823 页。)对于康熙向自己的宠幸近臣和官商批借生息银两及由此出现的亏欠“烂账”问题,朝廷上下颇多议论,主管钱粮出纳的户部甚至为此还与康熙皇帝发生过矛盾冲突。(注: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六月,户部尚书赵申乔同户部堂官“具折面奏时不胜忿激,奏称‘朝廷库帑,商人等侵蚀二百余万,现今铜斤不能继续,作速停止商人采办,仍交与各官差官员’等语”(《圣祖实录》卷264,《清实录》 六,第596页)。 )康熙最终也不能无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康熙拒绝向淮商批借新的帑项,且于该年十一月下令废止八旗公库。对于以前已经批拨出去的生息银两,康熙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属于八旗兵丁借欠的予以豁免;驻防旗丁公库运行状况良好的,收回原借本银,而以所盈利息作本建立广善库;属于官吏、官商借欠者,下令追回。(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曾规定:“凡借官银者,因不能完银,治罪。”“凡牧民官员借欠官银不能完银,即令离任追赔,已还后准其开复。如不能还清,即以家产抵偿”(《清实录》六,第312—313页)。这些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因人而异,不是十分严格。康熙五十八年(1719)陕西巡抚噶什图参奏李锡等七名官吏借欠帑银一案,“李锡系拟立决之犯,佟图襄、祖业弘系革职之人,武廷适系致仕之人”。他们被发往军前效力赎罪时借欠军需银60600两,“又呈称力竭不能应付”。 康熙对此怒火中烧,决定:西宁用兵之时,“李锡等仍留彼处效力行走,如仍前不悛,照原拟取来京城正法;佟国襄、祖业弘、武廷适另行议罪”;其所欠库帑即令有司“查明伊等家产,作速变价偿还”(《清实录》六,第785页 )。可是“皇商”王纲明在康熙五十四年就被户部奏参亏欠库帑,要求改由户部派员承办铜斤。此案经过康熙的干涉庇护,交九卿反复讨论后仍交王纲明承办。结果,王氏再次亏欠铜斤运本。康熙为弥补王氏亏欠以归户帑,又批准其从户部领价“采买两江、浙江、闽、湖广五省营驿马匹,于每匹额价银节省三两填补以前亏空”。康熙驾崩后,王氏失去靠山,该五省向嗣君雍正反映:“王纲明所交之马疲瘦不堪,易于倒毙”,请求自行采买,仍“每匹扣银三两交部为王纲明补垫亏空”。雍正对此当然很恼火,下令免除该五省马匹扣银,决定将王氏欠项“另行清结”(事见《圣祖实录》卷264、卷266,《世宗实录》卷9,《清实录》六,第596—597页,第601页,第617页, 《清实录》七,第167 —168页)。 从政策方面来说,康熙五十六年以后要求清理生息银两积欠,但由于康熙对近臣宠商过分照顾,致使以前的积欠中有许多变成无法收回的“烂账”,康熙以此有了“宽滥”之嫌。)由于八旗兵丁和官吏、官商是生息银两制度的主要推行对象,批拨给他们的生息帑银额数居该时期生息拨款的绝对多数,而驻防旗丁人数比八旗少,见诸资料实行生息银两制度的只是个别地方,估计没有普遍推行;故此,向驻防批拨的生息银两数额是很有限的。所以,康熙五十六年以后对生息银两制度实行了收缩政策。(注:笔者查阅了《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和《清实录》,从康熙五十六年四月驳回李煦代淮商奏请“再借皇帑”折、十一月废止八旗公库之后直到康熙去世为止,再未发现康熙批借新的生息帑项;在现存的生息资本活动方面,除个别驻防公库所盈利息改为广善库资本以外,亦未见增拨新的帑本;对以前批借给官吏、官商的帑银则进行清理归还。据此,笔者将康熙五十六年四月在李煦奏折上的朱批“借帑一事万万行不得,再不要说了”视为政策性批复,因而认为康熙晚年对生息银两制度施行收缩政策。)从京口驻防公库改为广善库之例可以看出,收缩阶段的生息银两制度在运行规则方面也在趋向定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