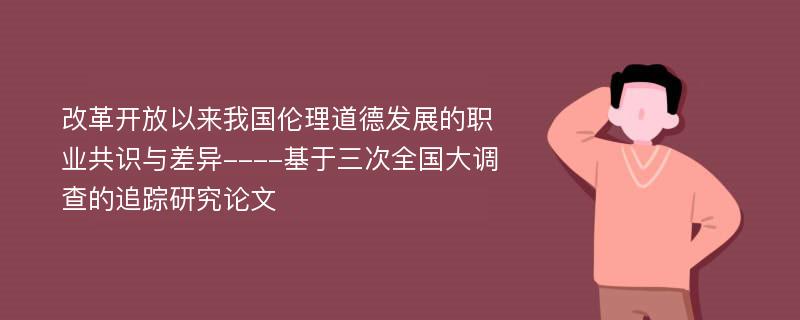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伦理道德发展的职业共识与差异
----基于三次全国大调查的追踪研究
牛俊美1,杨振动2
(1.南京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1166;2.河海大学 商学院,南京 211100)
摘 要: 通过三轮全国调查,可以发现,当前我国诸职业群体在伦理道德方面已经形成许多共识,同一性是其基本方面;但由于历史与现实伦理境遇殊异,诸职业群体在整体道德气质上存在较大差异,不同职业群体间伦理道德发展不平衡乃至分化的现象比较突出。为建构和谐伦理关系,不仅应在全社会营造充满伦理关怀的良好氛围,引导诸职业群体走向健康的道德观念和理性的道德态度,还应当实施三大战略: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价值取向,通过合理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安排,不断提升诸职业群体,尤其是农民、无业失业下岗人员以及工人和小生意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和职业道德教育,通过职业道德中间机制的作用,凝聚职业共识,实现社会的有机整合;培育实体伦理精神,提升职业之间交往实践的广度与深度,加深社会各职业群体之间的相互认同感。
关键词: 职业群体;伦理道德;共识;差异
改革开放40年,既是中国社会巨大变革的40年,也是职业分工急剧变迁的40年。在这一时期,受全球化、高科技、市场经济等因素影响,职业市场呈现出传统职业与新兴职业兴衰更替、多种职业并存与多元发展的格局。在这一历史洪流中,各职业特别是农民、工人、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的经济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深深地影响着诸职业群体伦理境遇和伦理关系的变迁,也从客观上造成了其道德生活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态势。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40年来我国不同职业群体的伦理道德发展状况,既是当前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深入推进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据此,本文通过分析以樊浩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组进行的三轮(2007、2013、2017)全国道德国情大调查数据(23) 本文采用数据均来自以樊浩教授为首席专家的三轮全国道德国情大调查数据库,即2007年全国伦理道德状况调查数据库、2013年全国伦理道德发展数据库和2017年全国伦理道德发展数据库,在文中分别以“2007年”“2013年”“2017年”标注。 ,尤其是将2013年和2017年两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对比,初步考察我国不同职业群体伦理道德发展的总体状况,从历时与共时维度勾勒诸职业群体在伦理道德发展方面存在的共识与差异,以对未来的发展和建设提供某种启示。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Compressed Air Energy Storage System for Grid-connection of Renewable Power GUO Zuogang,LEI Jinyong,DENG Guangyi(26)
一、伦理道德的“发展”理念及其职业共识与差异
关于伦理道德的理念,存在着“建设”与“发展”两种不同的视角。[1]如果不是基于“建设”而是基于“发展”的理念看待伦理道德,进而对伦理道德自身进行“发展评估”的话,那么,我们便不能将“建设者”或主管部门推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落实程度或建设者意志对伦理道德的影响程度作为测评指标,而应将重心放在对伦理道德自身发展所达到的实际水平的评估上。一般而言,伦理道德的发展水平主要体现在伦理关系、道德生活、个体伦理道德素质、伦理道德发展的影响因子等方面。其中,诸职业群体对诸伦理实体的态度、伦理关系及其范型、伦理观与伦理行为方式等,是反映其伦理发展水平的主要方面。
(一)不同职业伦理认同的共识与差异
1.伦理实体及其排序。按照黑格尔精神哲学理论,个别性的“人”与普遍性的“伦”同一而形成的伦理性的实体,在生活世界中主要有三种存在形态:家庭、社会、国家。其中,家庭是自然的伦理实体,国家是制度化的伦理实体,而社会则是二者相互过渡的中介,这三大伦理实体对于个人显然具有明显不同的意义。2017年伦理关系调查的首要任务是把握诸职业群体关于个人与家庭、社会及国家的关系及其排序。调查结果是:不同职业群体关于家庭-社会-国家关系的主流观念存在显著差异,低级白领、工人/小生意者、农民和无业失业下岗群体更为重视家庭,而高级白领的国家伦理意识明显高于其他职业群体。在对“家庭、社会和国家三者的重要性程度”进行排序时,高达54.2%的高级白领将国家置于首位,将家庭排于第二位;而其他群体则无论在选择第一重要还是第二重要时,排序结果都非常一致,次序都是家庭、国家、社会,两次选择家庭都占首位,足见家庭对于低级白领、工人/小生意者、农民和无业失业下岗群体的重要性。但是,在是否“为了家庭利益可以一定程度上牺牲国家利益”以及“为了国家利益可以一定程度上牺牲家庭利益”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上,各职业群体在家国之间都选择了国家利益至上。而对于国家之于个人存在的意义,不同职业群体中超过70%的人都表示“国家最重要,是我们的安身之地,国家富强个人才能过得好”。相比之下,在不同职业中,高级白领的国家伦理意识更加强烈,高达82.7%的高级白领认同国家之于个人和自己小家的重要性,这与高级白领所受的教育程度更高不无关系。
1.2.3 产量测定 一般油用牡丹定植3-4年开始结荚进入生产期,试验牡丹于2016年开始大量结荚,当年果荚7月底开始逐渐成熟。每种模式地块随机选择3个3 m×3 m大小的样方,分别于2016年8月2日、8月7日、8月12日将成熟果荚采摘带回实验室,阴凉处晾晒30 d。将牡丹籽与果荚分离,分别称重测产。
在某种程度上,低级白领与高级白领的伦理境遇比较相似,这一群体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从传统知识分子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性转型,也是所有职业群体中幸福指数和生活满意度较高的群体之一。68.7%的低级白领认为目前状态是“生活富裕,幸福也快乐”或“生活小康,幸福且快乐”,被调查的727位低级白领中,14.7%的低级白领认为自己目前生活非常幸福,对目前生活非常和比较幸福的人数之和占总数的81.3%,与高级白领的幸福率持平;被调查的722位低级白领中,对目前生活状态非常满意的占总数的15.8%,而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人数总计89.8%,也与高级白领的满意率总体持平。所不同的是,这一职业群体大多从事较低层次的白领工作,但学历普遍较高,社会地位也较高,是现代社会中间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对其总体信任度和伦理道德满意度也较高。他们不存在高级白领在伦理道德评价上的巨大舆论压力,是伦理道德表现相对比较稳定的职业群体,在推动社会主导价值体系及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发展新理念的传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他们在伦理关系上表现出对传统的某种延续,在低级白领的伦理世界中,父母子女、夫妇、兄弟姐妹、朋友四伦依然处于重要地位,这与高级白领将国家置于家庭和社会之上以及将同事或同学关系视为最重要的伦理关系之一的现代气质明显不同。但另一方面,在社会、国家层面,低级白领又呈现出现代性的一面,诸如社会公德意识较强,对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非常关心等,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仅次于高级白领,并且十分注重公正、责任等现代道德品质,这说明这一职业群体的道德气质与传统有着较大差别。传统与现代元素交织、传承与断裂并存,成为低级白领职业群体的突出气质标识。
3.伦理观与伦理方式。黑格尔曾精辟地指出:“在考察伦理时永远只有两种观点可能:或者从实体出发,或者原子式地探讨,即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逐渐提高。”[2]173在伦理观念上是“从实体出发”还是“原子式地探讨”导致了伦理行为方式上的根本差别。2017年对于伦理观与伦理方式的总体调研状况是:在家庭伦理关系内部,各职业群体“从实体出发”的伦理观与伦理方式占主流。对此,可分别从代际伦理关系、婚姻伦理关系以及同胞伦理关系等方面的数据得出结论。对于“无论父母对自己如何,都应当尽赡养义务”的调查发现,54.5%的人表示完全同意,37.5%的人比较同意,而完全不同意和不太同意者不到总人数的10%。而对于“是否离婚应该从家庭整体(包括子女)考虑”,完全同意和比较同意人数高达85.3%。至于“遇到困难的时候,兄弟姊妹通常都会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90.1%持完全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态度。以上关于父母与子女、夫妻、兄弟姐妹的伦理行为方式进一步印证了家庭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绝对伦理地位和不同职业群体对家庭伦理关系的整体重视。
我沿着山势拾阶而上,岁月的痕迹与湖湘文化的积淀就林立在这山间,文庙、湘水校经堂、船山祠、濂溪祠、屈子祠等纷纷闯入我的眼帘,繁华荟萃的湖湘文化和层林尽染的山中风景让我应接不暇。濂溪一脉的理学自湘南至此发扬光大,随着湘江一起浩荡地流向大半个中国。工善其事、业精于勤的湖湘伟人站在历史巨浪的潮头,魏源在和林则徐彻夜长谈后伏案写下《海国图志》,让国人睁眼看世界;曾国藩从双峰老家带着几百家勇横扫中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熊希龄带着湘西人的赤诚和坚韧从凤凰来此求学,最后成了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正所谓:此君一出天下暖。
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68.6%的人对遵守社会公德持“从实体出发”的伦理态度,但是,对于个体遵守社会公德的理由,不同职业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选择“个人是社会的一分子,应当遵守道德”和“遵守道德社会才能有序和美好”两项理由的群体总和由高到低排序是:高级白领75.7%、低级白领71.8%、工人/小生意者69%、无业失业下岗67.7%农民65.2%,在所有群体中,高级白领和低级白领的社会公德意识总体是最为强烈的。选择“遵守道德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实现”和“不遵守道德会被别人议论或谴责”两项理由总和的群体由低到高排列是:高级白领23.8%、低级白领28.2%、工人/小生意者30.7%、无业失业下岗32.1%、农民34.6%。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社会公德领域,诸群体的主流伦理观念是“从实体出发”,但是,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对此持否定态度,可见从个体出发的“原子式观点”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
与上述两大领域相比,职业活动领域的调查结果则不容乐观。2017年的调查显示,单位的伦理功能正在遭遇危机,各职业群体普遍认为职业劳动主要只是个人和家庭谋生的手段,只有25.3%的人认为职业劳动是为社会创造财富,对单位的伦理感在很大程度上受功利和境遇的影响。责任感与奉献精神严重缺失,对所在的单位严重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是目前所有群体在职场中的普遍感受。平均只有12.5%的人能够时常体验到对于单位的伦理归属感,而更多的人只是在个人利益与单位高度一致或者受某种情境激发之后才能产生对单位的一体感,即使是所有职业群体中职业伦理感最强的高级白领,也只有27.3%认同职业劳动的社会伦理属性,21.3%对单位有比较强烈的伦理认同倾向,大多数人在职业伦理领域呈现出“原子化”的游离样态。这与计划经济时代诸职业群体对单位的强烈认同感形成鲜明对比。
译文: However, some people are confused when they see misconduct in the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of officials, when unqualified officials are selected at some localities, and when unqualified officials are still promoted, even against regulations.[2]461
从以上关于诸职业群体伦理状况的分析可以发现以下规律:第一,家庭依然是现代中国社会诸职业群体最为坚固的伦理基石和最为可靠的精神家园,特别是对于低级白领、工人/小生意者、农民和无业失业下岗群体而言,家庭以及家庭伦理关系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构成中国伦理精神的特殊标识和文化胎记。但与此同时,调查中传递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信息是,家国关系远不如人们预料的那么紧张,诸职业群体尤其是高级白领的国家伦理实体意识近年来明显提升;第二,旧五伦中除传统的君臣关系退隐之外,其余四伦仍被诸职业群体视为最重要的伦理关系,其他关系中只有同事或同学关系得到高级白领的普遍认同,被诸职业群体一致认可的新五伦的出现仍尚待时日;第三,在家庭生活内部和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诸职业群体依然高度认同甚至坚守“从实体出发”的伦理思维方式,但在职业活动领域,从个体出发的“原子式观点”却在相当程度上盛行,成为“后单位制时代”伦理发展的突出难题。
(二)不同职业道德认知的共识与差异
道德部分主要调查的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哪些德目得到诸职业群体的广泛认同?德目是否因职业之别而呈现出差异?不同职业群体的道德观念在受古今中外多元道德思想以及受家庭、学校、社会、国家等场域影响方面有何差别?在冲突情境下的道德选择是否因职业不同而不同?
4.伦理行为中的矛盾与伦理冲突。家庭成员与社会公民,是两个既相互贯通又相互矛盾的身份存在。家庭与社会、国家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家庭伦理向社会伦理、国家伦理的移植和扩展问题,在家庭本位的中国社会一直是一个伦理难题,也是当今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过,以下几组2017年测评家-国关系之维的数据传递出的信息令人感到些许欣慰,那就是,在两个涉及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关系或公私关系的问题,即是否“为了家庭利益可以一定程度上牺牲国家利益”以及“为了国家利益可以一定程度上牺牲家庭利益”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上,不同职业群体在家与国之间都选择了国家利益至上。而对于国家之于个人存在的意义,不同职业群体中超过70%的人都表示“国家最重要,是我们的安身之地,国家富强个人才能过得好”。相比之下,在不同职业中,高级白领的国家伦理意识更加强烈,高达82.7%的高级白领认同国家之于个人和自己小家的重要性,这与高级白领所受的教育程度更高不无关系。
3.道德素质的受益场域。如果说道德素质是动态发展的,那么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近年来家庭、学校、社会(如工作单位、社区等)、国家或政府等诸场域对各职业群体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有何差别?调查发现,当今中国社会各职业群体道德素质的受益场域结构近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13年,各职业群体不仅对前三位道德受益场所的选择非常一致,而且重要性排序也高度一致,依次是:家庭、社会、学校。而2017年,虽然与其他场域相比,家庭、社会、学校作为各职业群体三个最重要的道德策源地没有改变,但排序却呈现出很大的职业差异。总的发展态势是,家庭的影响力明显下降,学校的影响力稳中有升,而社会的影响力则有升有降。总体而言,家庭对农民和无业失业下岗人员的影响最为显著,对低级白领和工人/小生意者的影响次之,对高级白领的影响最低。社会对低级白领和工人/小生意者的影响最为显著,对高级白领和农民的影响其次,对无业失业下岗人员的影响最为薄弱。而学校对高级白领的影响最为显著,对无业失业下岗人员的影响其次,对低级白领、工人/小生意者、农民的影响最低。所有群体中只有农民一个群体的选择排序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家庭、社会、学校。但对于农民而言,家庭影响的重要程度已然今非昔比,和五年前相比下降了24.2%,而学校和社会的影响度则分别增长了9.4%和14.4%。此外,家庭对于无业失业下岗人员的影响力也很大,对于无业失业下岗人员而言,家庭仍然是最重要的伦理道德策源地之一,但家庭的影响度五年来下降了12.1%,同时,学校的重要程度上升了16%,跃居第二位,而社会的影响度则相对比较稳定。低级白领和工人/小生意者的影响力结构比较一致,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社会、家庭、学校,其中社会的影响从第二位上升至首位。而高级白领的变化最大,学校的影响力从五年前的末位跃居首位,而家庭的影响力则从五年前的首位跌至末位,排序与五年前正好完全相反。
1.“新五常”。道德生活调查的基本任务是发现诸职业群体最重要和最需要的五种德性,即“新五常”。调查发现,与传统五常相比,现代中国社会的基德或母德从元素到结构都已发生根本变化,不同职业群体对于前五位德目的选择不尽相同,呈现出显著的差异。2007年和2013年的数据显示,在现代社会所存在的诸种德性的多项选择中,得到最大认同的五种德目依次是:爱、诚信、责任、正义、宽容。而2017年的调查排序则是:爱、诚信、宽容、责任、孝敬。这意味着,近五年来,五者之中爱、诚信、责任、宽容四个元素没有变化,但是排序有变,而正义只被低级白领列于第二位,被挤出新五常之外,为孝敬所取代。具体到各个职业群体,高级白领、农民和无业失业下岗人员三大群体的选择相同,依次是:爱、诚信、宽容、责任、孝敬,而低级白领的选择依次是:爱、公正、诚信、责任/诚信、孝敬,工人和小生意者的选择依次是爱、诚信、责任、孝敬。可以看出,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第二、三位德目的认同上。而“爱”“责任”“孝敬”三大德目得到了各职业群体最为广泛的认同,分别居于首位、第四位和末位。除此之外,尽管在各群体中的排序不同,“诚信”也受到了各群体尤其是低级白领的高度认同,而“责任”最被工人和小生意者所重视,位于第三和第四位。由此,如果忽略排名顺序,可以从多样选择中发现对于各职业群体最为重要和最为需要的五大德目分别是:爱、诚信、宽容、责任、孝敬。与传统五常相比,“新五常”中只有“爱”和“诚信”在基本内容方面与“仁”“信”相接,其他三德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责任”和“宽容”,具有非常明显的现代特征。而传统美德“孝敬”被列入“新五常”中,则与近些年来诸群体在伦理关系方面对家庭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趋向一致。
五大职业群体中,高级白领的伦理境遇与道德气质非常特殊。作为改革开放以来获益最多的阶层,他们在趋于等级分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处于最高等级,是整个社会的精英群体和优势群体。在当今所有职业群体中,他们对自己现状的评价表现为“三高”:对自己目前的总体状况满意率最高,生活幸福指数最高,生活状态满意度最高。关于当前状况,69.6%的高级白领认为“生活富裕,幸福也快乐”或“生活小康,幸福且快乐”,居于所有职业群体榜首。关于目前的生活幸福度,被调查的756位高级白领中,认为目前生活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占总数的81.3%,其中20.1%的高级白领觉得自己目前的生活非常幸福;关于目前的生活状态满意度,被调查的744位高级白领中,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总数的89.8%,其中非常满意的占总数19.5%。作为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主导性阶层,理论上必须也应当是伦理道德的示范群体,从调查数据来看,无论是国家伦理实体感、职业伦理素养还是社会公德意识,高级白领与其他职业群体相比都是最强的。然而,由于民众对这一职业群体的道德期望值普遍比较高,对其伦理态度、道德素养及行动取向和品质特性非常敏感,部分高级白领的一些不端行为如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极易引发民众比较强烈的不信任感和不满情绪,甚至进而转化为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因此这一群体又是社会公众好评率最低和最受争议的群体。虽然近些年来38.8%的公众对高级白领中的部分群体如政府官员的信任度有所改善,满意率也从2013年的51.1%提高到2017年的62.6%,但是与其他职业群体相比,高级白领在总体上依然是最不被信任和最不满意的群体之一。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上的强势与伦理道德方面的弱势,伦理道德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的强烈反差,深深地构成高级白领道德气质上的悖论特征。
2.道德生活的组成元素。调查发现,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民族多元文化交织和博弈的现代背景下,近年来我国社会诸职业群体的道德元素及其主导并未发生结构性改变,中国传统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市场经济道德一直稳居前三位,但是,这三大元素所占的比重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传统道德虽然仍是我国道德观念的主流,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社会主义道德、市场经济道德和西方道德三者的总和,才与传统道德大抵相当,但近年来,传统道德在各群体中的比例均下降了10%左右,其中,工人/小生意者和无业失业下岗人员的降幅尤为显著,工人/小生意者从2013年的63.10%下降到47.40%,无业失业下岗人员从2013年的68.40%下降到52.20%。与中国传统道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意识形态所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在各群体中均有所上升,尤其是低级白领、高级白领、无业失业下岗人员,涨幅均在8%以上。这说明意识形态日益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但显然还没有达到主导和引领社会道德的水平。而市场经济道德则有升有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除了高级白领由2013年的18.50%降为15.60%之外,其他群体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不难发现,市场经济道德对于工人/小生意者和农民两大群体的影响最大,分别从12.20%、8.20%上升为21.70%和14.00%。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西方道德的影响虽然越来越大,有非常多的人对西方文化之于我国伦理道德的影响持一种乐观的态度,但其实际影响远不如人们预想或主观感知到的那么强势。由此可以推断,现代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问题大多仍是内生性的,更需要从中国自己的文化内部入手寻找症结。
为了保证盾构设备安全,在K49+818处增设中间竖井,作为检修通道和通风作业通道。结合该桩号水文地质条件,并考虑盾构机掘进速度,在中间竖井四周设置降水试验井,以便水位降至安全水位,中间竖井能够顺利施工,从而减少盾构到达时发生涌砂涌水的风险[1]。
从以上关于诸职业群体道德状况的分析可以发现如下几点:第一,当代中国诸职业群体在道德方面的变化比在伦理方面更为显著,表达也更为多元、多样。与传统五常相比,社会的基德从元素到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五常”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中西古今融合互补之特征;第二,尽管诸职业群体的道德结构及其主导未变,但各个要素的影响力却发生了嬗变。总体来看,传统道德的影响呈下降态势,社会主义道德和市场经济道德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而西方道德的影响实则非常有限;第三,虽然家庭、社会、学校仍是三大主要道德策源地,但其影响却显现出巨大的职业差异。在诸职业群体中,家庭对农民和无业失业下岗人员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学校对高级白领的影响最为显著,总体发展态势是,家庭的影响力总体明显下降,学校的影响力稳中有升,而社会的影响力则比较稳定;第四,在面临冲突情境时,高级白领表现出较高的道德素质,对于组织集团行为的伦理-道德悖论的道德觉悟能力和警惕意识最强。
4.冲突情境中的道德素质及其突出问题。道德发展水平和境界不仅体现在一般的日常行动上,更反映在面对冲突情境时对道德的坚持和固守上。历次调查均选取几起典型的个体行为与集团行为的冲突情形作为抽样。2017年的对于“一些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提供特殊政策”的看法,总体而言,农民的道德敏感度最高,农民群体认为不道德和严重不道德的人数远远高于其他群体,并按照农民(70.9%)→工人/小生意者(66.8%)→无业失业下岗(63.4%)→低级白领(59.5%)→高级白领(59.4%)呈递减趋势。2013年和2017年的“如果您所在的单位有一项举措可以提高集体福利并使您个人得到利益,但会造成环境污染或社会公害,您会举报吗”的追踪调查显示,面对侵犯公共利益而使自己团体内部获利的“伦理的实体——不道德的个体”的集团行为,与2013年相比,各职业人群选择“会举报”的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高级白领的增幅最大,农民群体其次。无论是2013年还是2017年,高级白领选择“会举报”的比率都是最高的,这说明高级白领对于集团行为内在的伦理—道德悖论的道德觉悟能力和警惕意识最强。
二、诸职业群体伦理境遇的变化与道德气质的分化
以上分析显示,当前我国诸职业群体已就伦理道德的很多方面达成基本共识。然而,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多元化转型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基本结构的变化,不同职业群体的部分伦理道德理念存在差异、分歧乃至冲突,已是不争的客观现实。这一方面与诸职业群体于四十年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在社会关系、经济生活、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变迁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与诸群体对自己和社会现状的当下认识和评价密切相连。历史与现实两大因素构成诸职业群体伦理境遇的差异,由此导致其整体道德气质之间的殊异。
2.5.13 术后逆行射精 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后有一半以上患者出现逆行射精。原因可能为在术中切除膀胱颈部腺体时,破坏膀胱颈的正常结构及尿道内括约肌,造成术后膀胱颈功能不全而不能正常关闭,从而导致射精过程中精液向膀胱返流。因此,术中应尽量保留膀胱颈部的括约肌,以减少逆行性射精发生。
2.“新五伦”。如果说中国传统伦理以“五伦”为基本范型的话,那么,当今中国社会是否存在“新五伦”?数据显示,在最重要的五种伦理关系的选择上,尽管各职业人群目前尚未达到共识,但都不约而同地将家庭关系中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姐妹置于前三重要的位置,并且排序高度一致。如果将2013年和2017年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不同职业人群在最重要关系的选择上都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置于首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趋势变得愈加明显,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所占比例在各个职业群体中都有所上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农民和无业失业下岗人员这两大职业群体具有强烈的家庭伦理归宿感外,高级白领在对父母与子女关系的重视程度上也明显高于其他职业群体,增幅也较大,高级白领、农民、无业失业下岗人员均增长10%左右。同样,在2017年对“哪一种关系对个人生活最具根本性意义”这一问题的回答上,不同职业的选择也惊人的一致,都将家庭血缘关系置于绝对重要的位置,而且农民和无业失业下岗人员的选择比例再一次高于其他群体。除家庭伦理关系之外,朋友关系在当今社会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017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第四和第五位重要关系的选择上,除了高级白领将朋友关系置于第五位之外,其他职业群体均将朋友关系置于第四和第五重要关系。可见朋友关系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不同职业群体的普遍承认。而其他关系中只有同事或同学关系被高级白领列为第四位重要关系,但其重要程度仍不足以取代体现传统五伦中的君臣关系。
与白领相比,农民是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职业群体,也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拥有较低收入水平、较低教育水平和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弱势群体。同时,受教育水平、技能水平的制约,他们还是近十年来各职业群体(其中包括高达84.3%的农民)公认的获利最少的群体。这一群体的普遍特征是:第一,与白领阶层的高满意度和幸福度正好相反,农民对自己现状的评价表现为“三低”:总体状况满意度最低,只有50.7%的农民觉得生活富裕或小康,幸福且快乐,与高级白领和低级白领的高满意率形成明显对比;目前的生活幸福度最低,认为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农民只有68.7%;目前的生活状态满意度最低,觉得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占82.6%;第二,由于农民生活在相对比较传统和比较简单的人际圈中,他们是对当前我国社会人际关系和道德状况总体满意度较高的群体,对人际关系持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态度的占75.9%,是所有群体中满意度最高的;对道德状况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74%,总体满意度仅次于工人/小生意者的75.4%;第三,引人注目的是,尽管农民是对自我评价最不满意和最不幸福的弱势群体,但他们却是被所有职业群体所公认的伦理道德方面最为满意和最被信任的群体,公众对他们的伦理道德状况满意率和信任度高达85.1%的和87.4%,遥遥领先于其他群体。因此在这一意义上,他们又是不折不扣的道德上的“优势群体”和示范群体。伦理地位与道德地位倒置,德福严重分离是农民群体道德气质的鲜明特征。
处于白领和农民之间的是工人/小生意者和无业失业下岗人员两大职业群体。改革开放以来,这两大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总体明显下降,是社会变动中的失意和失利人群,也是社会生活中的困难群体。因为很多无业失业下岗人员大多是原国有、集体企业工人及其子女,而小生意者职业又是吸纳下岗工人和失业待业人员的一个重要渠道,因此他们的伦理境遇与道德气质整体上比较接近。他们对自己目前总体状况的满意度居中,两大群体的满意率都是58.3%;生活幸福度和生活状况满意度也比较接近,工人/小生意者的幸福度和满意度分别为73.8%和85.8%;无业失业下岗群体的幸福度和生活状况满意度分别为72.5%和84%。这两大群体的普遍特征是有着强烈的伦理认同倾向,尤其是家庭伦理归宿感和家庭道德责任感较强,他们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德意识,富有社会同情心,体现出较强的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相形之下,这两大群体的职业道德水准处于较低层次,现实的伦理境遇使他们很难对职业产生良好而持久的伦理态度,高达57%的工人/小生意者和51.5%的无业失业下岗人员认为职业劳动只是个人和家庭谋生的手段,这与高级白领40.6%的选择率形成强烈比照。这两大群体中,无业失业下岗群体由于种种原因沦为社会底层,他们处于贫困境地并缺乏社会保障,长期不受尊重,饱受歧视,对社会现状不满的心态更为突出,因此比其他职业群体更为珍视和青睐宽容的道德品质。这其实从侧面反映了他们对社会道德风尚的要求。总之,对伦理公正的渴求和朴实的道德精神,构成这两大群体道德气质的重要特点。
三、建构新时期和谐职业关系的对策建议
调研数据表明,当前我国诸职业群体在伦理道德方面达成许多价值共识,同一性是其基本方面;但由于诸职业群体的具体伦理境遇迥异,价值诉求多元,伦理表达方式多样,不同职业群体在整体道德气质上存在较大差异,诸职业群体间伦理道德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比较突出,各群体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互不承认、互不认同的伦理危机,成为当前我国伦理道德发展面临的突出而深层的难题。与生活世界中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不同,伦理上的分化是精神世界的分裂和价值世界层面的分道扬镳,极易发展为文化和政治上的对抗乃至两极对峙,因此其后果远比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更深远、更严重,如果处置不当,极易引发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进而发展为群体性事件,因此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为建构和谐伦理关系,避免诸职业群体之间的伦理冲突,一方面需要在全社会倡导和培育充满伦理关怀的良好氛围,普及尊重他人、平等待人的现代伦理观念,另一方面应当在合理正视和尊重道德价值多元前提下,引导诸职业群体走向健康的道德观念和理性的道德态度。落实于具体对策,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40] Peter Dutton, “Three Disputes and Three Objectives: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4, No. 4 (2011), p. 47.
首先,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价值取向,通过合理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安排,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提升诸职业群体尤其是农民、无业失业下岗人员以及工人和小生意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是从制度伦理层面防止各群体伦理道德差距进一步扩大和德福长期不一致的根本要求。伦理道德地位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之间的严重倒挂,不仅违背了和谐社会的标准,而且拷问着制度的合理、社会的正义。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刚性制度体系,不仅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公正,消除歧视,还能为底层的职业群体改变自身状况提供新的发展机遇,更重要的是,可以在全社会形成扶正祛邪、惩恶扬善、激浊扬清的良好道德风尚。当然,在加强制度体系建设的同时,也必须引导诸职业群体逐步形成对美好生活的正确认知和合理的心理预期,杜绝等、靠、要的消极依赖思想,理性地看待和处理与其他职业群体之间的关系,在全社会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和平、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才能为超越诸职业群体之间的伦理冲突、建构社会的伦理同一性提供坚实的伦理心理保障。
其次,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和职业道德教育,凝聚职业共识,从职业群体当中挖掘和寻找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资源,通过职业道德中间机制的作用,实现社会的有机整合。在现代社会,职业分化一方面造就了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高度异质性,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整合形成威胁;另一方面又为职业活动主体实现个人价值,提升自身伦理道德素质提供了历史契机与伦理空间。这是因为,不仅任何一种职业活动都内在着分工与协作两种基本要求,而且职业本身便具有超越自身而服务社会与他人的价值指向,个体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形成深厚的职业责任感并通过职业义务的践履而与他人、所在单位或组织以及社会、国家建立一种伦理精神联系,进而扬弃自己的个体性,达到与普遍性的统一。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集体意识形态,由职业群体发展而来的职业伦理是重建社会秩序,促进个体道德社会化,实现社会道德整合的重要载体。虽然职业伦理具有种种缺陷,如不同职业群体及其职业伦理本身之间存在冲突;职业生活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仅仅仰仗职业伦理难以实现职业领域之外的公共生活空间的道德整合等,但无论如何,职场仍不失为对个体进行伦理训练的重要场域,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和职业道德教育对现代公民伦理感和道德感的培育乃至社会公德的塑造都具有不可代替的意义。
最后,建构实体伦理精神,拆除诸职业群体之间的精神藩篱,提升职业之间交往实践的广度与深度,加深社会各职业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认同。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不是“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而是“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3]诸职业群体之间的伦理认同危机正是“我们如何在一起”的文明难题。在当代中国现实境遇中,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往往与他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高度相关,以至于以技术等级或专业化程度为基础的职业划分体系几乎成为社会学家进行社会阶层划分的基础。而这种类别划分一旦固化到各群体的自我认识中,便会不自觉地形成内群体与外群体之别,成为诸职业群体“在一起”的无形隔膜。因此,职业差异不但有可能加剧诸群体之间的异质性,使得不同群体的人之间很难进行平等接触和深度交往,而且还可能引起对其他职业群体的偏见、歧视、不信任、仇恨甚至道德排挤。于是,在现代社会,“学会在一起”便成为摆在诸职业群体面前的共同难题。这里的“在一起”不仅指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等外在层面的“在一起”,更在于思想、观念等内在层面的“在一起”。而伦理精神不仅是“从实体出发”的“多”与“一”的统一,还是“从实体间性出发”的此实体与彼实体之间的统一,更是“从实践出发”的“知”与“行”的统一。如此,实体伦理精神的建构和培育,便成为化解诸职业群体之间的伦理冲突,增强诸职业群体之间的相互认同感,汇聚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多重合力,进而建构社会的伦理同一性以及全民道德共识的极其重要的维度。
参考文献:
[1] 樊浩.伦理道德,如何才是发展[J].道德与文明,2017,(3).
[2]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 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 樊浩.“我们”如何在一起[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
A Study of the Moral and Ethical Consensus and Differences among Professional Groups since the Opening up and Reform
NIU Jun-mei1, YANG Zhen-dong2
(1.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66,China ; 2.Business School ,He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00,China )
Abstract: Through three rounds of national investigations, we can find that many professional groups in China have formed many consensuses on ethics and morality in the past ten years, and similarities are greater than differences.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ethical circumstance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in the overall moral temperament of the professional groups. In order to build a harmonious ethical relationship, we should not only advocate a good atmosphere full of ethical concern in the whole society, but also guide the professional groups to form a healthy moral concept and take a rational moral attitude. Furthermore, three strategies should also be implemented: first of all, based on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thought and value orientation, the sense of acquisition, happiness and security of professional groups, especially peasants, unemployed laid-off workers, workers and small business people, should be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rough reasonabl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Secondly, professional ethics construction and professional eth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through the intermediate mechanism of professional ethics to gather professional consensus and to realiz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society. Last but not least, the spirit of entity ethics should be cultivat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practice of communication among professions and deepen the mutual recognition among various professional groups in society.
Key words: professional groups; ethics and morality; consensus; difference
收稿日期: 2019-06-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4CZX059);“江苏省道德国情调查研究中心”阶段性成果(2013)
作者简介: 牛俊美,女,山西高平人,南京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东南大学道德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杨振动,男,河南新乡人,河海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57(2019)05-0026-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