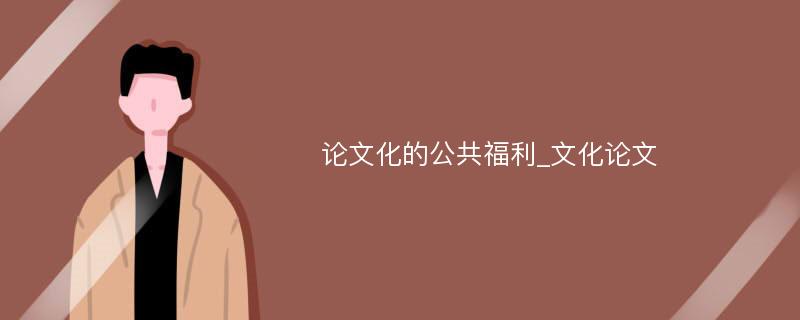
论文化的公益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益性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来没有比文化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了。人们“以自身生命的存在”为文化本体,彼此共处于一定的文化之中,人们总试图理解文化,但多半是既熟悉又不真知。在世纪之交,中国经济活跃、文化滞后的人文环境中,我们有必要从社会公益性的角度,对文化进行再认识。
其实人类从远古时代始,文化从来不是哪个私人的“劳什子”,每一件陶器的制作,每一片岩画的刻成,每一次语言的传习,每一种生产经验、哲学思想的出现,文化总是作为一种公益事业,为群体所创造,为群体所享用,而且功利目的总是大于娱乐目的,并以此为灵魂,引导人类从蛮荒走向文明。
一、文化的公益性是由文化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
现在有个较普遍的说法:“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似乎文化只是经济的附庸和“帮工”,无视文化的重要的社会地位。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文化的社会地位极为重视,认为文化艺术的生产,是人的“自由的精神生产”,“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而且是“属于分工的特殊部门”,是个“独立的领域”。并且强调,“只要他们形成了社会分工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的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注:恩格斯:《致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上)第114页。)
准确理解恩格斯这个科学论断,可以分三个层次:(一)文化,是既不从属于政治也不从属于经济的“独立的领域”,属于整个社会分工的“特殊部门”。(二)文化产品,甚至包括“错误”产品在内,都对“全部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甚至“影响经济的发展”,文化不是消极的飘浮物。(三)文化又是以经济为基础的,是以“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产物。
恩格斯在这里完整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文化观。文化的社会公益性,在于它对“全部社会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当然,不重视文化的社会公益性,甚至生产“错误”的文化,也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消极的或破坏性的影响。3000年前的古罗马帝国在经济、文化上都曾盛极一时,就因为从皇上到庶民的精神衰败,文化萎靡,贪图享受,消极堕落,导致经济崩溃,政治倾覆,加之日耳曼人南下,致使国家灭亡。文化与经济、政治并存,是支撑人类社会三维结构的三根柱子,哪一根弱了,整个社会就会发生倾斜。这三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而且各分工领域只有积极协调起来,方能构成稳定的社会。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保障体系。
二、文化的公益性是由文化自身的本质所决定的。
文化自身的特殊本质,由下列因素体现其公益性。
(一)文化的公开性。文化,虽然多是个人独立创造的,但它是属于社会的。任何一个作家、艺术家所创造的诗文、小说、戏剧、美术、音乐等作品,都是创造者自身生命存在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他们既有强烈的创造欲,又有强烈的发表欲。文化作品一但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媒体发表出来,便成为“公开性”的社会文化,为全社会所共有。
(二)文化的群体性。一种文化形式,或一件艺术产品,虽多为个体劳动,但在“个性”中所反映的往往是一个地域社会群体的智慧、心理、情绪和艺术意志。还有更多的艺术形式,如大型音乐、舞蹈、大型雕塑、戏剧、电影电视等,单个人是无能为力的,都是一个群体集思广益直接参与创作的,呈现为群体性的品格。
(三)文化的承传性。文化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人类社会的每一件同类文化艺术产品,在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都带有对历史文化继承的深深的印痕。在继承中有的发展,有的发现;纵向继承,横向发展。如此代代相传,便形成民族发展史上庞大的文化体系。而且这个承传性常常是跨越国界、跨越时代而发展的。
(四)文化的共赏性。不仅大型音乐、戏剧、电影电视等,需要进入一定的“场”而群体共赏,就是阅读型文化,如小说、诗歌、哲学等书籍,银屏型的如家庭电视等,也是社会民众居于不同方位不同时间的共赏。所以“共赏性”是客观的东西,它是艺术感觉与爱好的自由选择。文化感的高低取决于人自身的整体文化素养高低。文化感较差的人,往往缺少文化感受力,甚至视美为丑,或视丑为美,表现为扭曲了的鉴赏现象。
(五)文化的民俗性。在文化艺术的汪洋中,一个很重要的部类,是一定地域的民间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潜含着神秘的“巫术体系”。它的公益性,在于它不仅是本土民族心灵的祖圣,也是人们心理和行为的法典。民俗文化中的一些信仰、禁忌,有时要比社会法律更有制约的“迫力”。所以,民俗文化不仅表现了五彩缤纷的地方色彩,也有不可低估的民族凝聚力,这是不可忽视的现实。
(六)文化的功能性。一位荷兰哲学家说,“文化是动词”,文化不像一张桌子两只鞋子那样静止不动,文化最大的社会功能是“教化”。它以极大的社会穿透力,造就人的心理与人格,改变着人的思想道德、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并且形成改变人们社会心态的诸种“迫力”。不可忽视的是,不同阶级的文化,对于不同阶级的社会制度、道德法律,有极强的修补功能,文化自身在“化人”的传播中,也不断地改变着人文环境和自身形态。
三、文化的公益性, 总是由当代的社会群众直接受益来体现的。
文化的公益性体现为当代社会的人民群众直接从文化中受益,其中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
社会文化的公共设施,是文化公益的物质体现。如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电台、电视台、剧场、电影院、科技馆,乃至文化广场、教堂、寺院、历史文化遗址等,都是社会公益的文化设施,是一个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公众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是对青少年进行文明教育的重要阵地。马克思曾不间断地在大英博物馆里苦读了25年,终于以翔实的资料写成了《资本论》。人类许多重大的科研成果,都是图书馆、博物馆公益价值的体现。
文化的社会公益性更集中地体现在文化的精神领域。哲学是文化之魂,也是驾驭一个时代的无形的巨手。不同的社会哲学,在铸造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国历来有社会政治秩序和思想文化秩序相整合的传统。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哲学思想和国家学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中国人的统治思想,它也麻醉和毒害着中国人虔诚地接受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压迫,进而使这种制度得以维护和延续几千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才使中国文化的凝固、封闭状况有所改变。毛泽东、邓小平是当代中国的先驱者,他们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天才地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它是当代中国的革命的哲学,是当代中国人的灵魂和现代文化的精髓。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它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旗帜,是中华民族所共享共有的精神财富。它塑造了跨世纪辉煌的巨人中国的形象。
马克思对文学的社会职能评价极高,他说:“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理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注:马克思:《英国资产阶级》。)这些卓越的作品,正以人类的真、善、美和高尚的情操与思想,滋养着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事实说明,这样的作品越多,文化的公益含量也越高。人类所以比动物有更高的幸福感,就因为图书馆或家庭存有这么多种高档次作品,它使人类有更丰富的心灵感受。
但文化有公益,自然也有公害。一些封建糟粕、淫秽浊物以及粗制滥造的赝品等,也常常改头换面,冒充精品来“鱼目混珠”,这就需要有更多的鉴别能力较强的文化卫士,拿起批判的武器,鉴别、批判、淘汰,清除文化的垃圾。
四、文化的公益性是由管理者的公益观念所决定的。
有了公益文化设施,有了文化精品,不等于就是有了文化公益事业。今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披露了上海图书馆向社会开馆、北京图书馆向社会闭馆的新闻。这一“开”一“闭”,说明比文化设施更重要的是人,特别是“部门领导人”,要有较强的社会公益观和高层次的文化感。文化能否办成社会公益事业,最终还是通过操纵他的人来实现的。列宁把“掌管文化”与管理国家密切结合起来,他说:“我们缺少的不是文化,而是不善于管理。”(注: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一)第11页。)
目前有些模糊观念是与文化的社会公益性相悖的。
(一)只重经济效益,不重社会效益。
有些部门领导人认为文化投资大,效益低,索性一律作为商品推入市场,自负盈亏,自谋生路,也可以自生自灭。当然,有些文化部类,是可以做为商品在市场流通的,但多数的文化部类,只能看作社会公益事业,是不可以做为商品来赚钱的。如新闻文化,是社会重要的具有政治、思想、道德导向的公益事业,如果把新闻文化作为商品推向市场,以赚钱为目的,大搞有偿新闻,必然会造成许多虚假,从而导致社会思想混乱。列宁曾经尖锐地指出:“文学事业不但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的工具,而且它永远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注:列宁:《论文学》第4页。)
文化的社会导向作用,是一种巨大的无形的力量,它可以引导人们积极向上,塑造高尚的道德、人格、健康的开拓心理;也可以引导人们消极、颓废、怠惰,甚至走向犯罪。显然,以“赚钱模式”来经营文化,不断满足低层消费者的低级情趣,必将使全社会的文化思维、认知能力、鉴别能力,都降到可怕的庸俗的“零度”。
(二)只讲经济规律,不讲艺术规律。
人们的文化眼光,通常是随着社会思潮而变化的。“十年动乱”时期,人们习惯于用政治眼光来约束文化;而今发展商品经济,人们又习惯于用经济眼光来制约文化。
美国作家房龙说,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下,一切伟大的艺术都难于产生。法国罗浮宫那些精美的雕塑,是无法用经济概率加以验证的。四川乐山大佛,那是世界顶级的艺术瑰宝,据说那是三代人用了70多年时间才雕成的。再如王羲之的书法,郑板桥的兰竹,齐白石的篆刻,曹雪芹在“绳床瓦灶”间删阅十载的《红楼梦》,最初都不是作为一件商品才苦心经营的,不过是抒发个人思想情感的形式。如果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当年就把自己的艺术品看成是“赚钱的工具”,拿“时间”来计算盈亏,那么人类就没有这些文化瑰宝了。它们是超越任何经济价值的一种艺术家的良知,一种精神。“精神就是艺术家”。
(三)只看近期效益,不顾长远效益,见物不见人,不重视居于社会最大公益的人才培养。
增加文化公益的力度,是要有一定的经济投入的,真正伟大的艺术是靠优厚的物质条件来发挥其创造伟力的。培养人才,固然需要一定的经济投入,但更重要的是需要一定的感情投入、精神投入。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与时代无愧的作家和作品,那是空虚的民族。所以,在人类文明史上,伟大领袖人物对于伟大的文化名人都高度重视,因为他们是一个时代的“民族之魂”。世纪之交,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时代,也是恩格斯所说的“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然而,目前有两种社会心态极大地妨碍着出“巨人”、出精品。其一是从领导者到作家个人,都有些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不肯下大气力作极艰苦的磨炼,来弥补自己功力的不足。其二是一边呼吁出精品,一边又不为“独创精神”创造一种宽松、宽容的舆论环境,甚至为满足某种简单的心理平衡而求全责备,不惜压抑、扼制某些萌发的“独创精神”。这是目前人才与人才创作力量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培养人才、尊重人才、凝聚人才,是最根本的文化公益事业。如果不计较个人得失,而是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克服上述两种社会心态是不难的。没有巨大的经济投入,还可以有巨大的感情投入,为产生“巨人之作”营造宽松、宽容的舆论环境。良好的文化环境,是作家作品生成的土壤;良好的文化环境,也是社会公益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