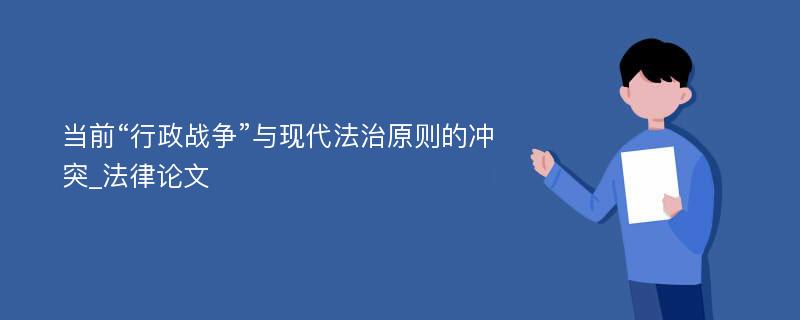
当前的“执行会战”与现代法治原则的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治论文,冲突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许是今年被定为“执行年”之缘故,民事案件(以及经济纠纷案件)的执行工作在各地人民法院受到了与以往任何时期相比都要高得多的重视,这不仅体现在声势浩大的执行宣传方面,而且体现在实际执行工作力度的显著加大上。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各地人民法院上下齐动员,采取“三个集中”的方式,即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亦有说“三个集中”为集中时间、集中人员、集中精力,参见《山东法制报·审判周刊》总第37期第1版),大张旗鼓地突击处理一批陈年积案。 由于其一般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短则1周、长则1月)即告完成,故与日常的执行工作相比具有集中、迅捷的特点而被美其名曰“执行周”、“执行月”。显而易见,这是各地人民法院为解决“执行难”这一长期存在于民事执行实践中的痼疾而使出的“杀手锏”。作为今年“执行年”一系列加大执行力度举措中的“重头戏”,其在各地人民法院所呈现出来的具体态式固然是五花八门,但概而言之,大抵包括(或曰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招数(或曰特征):
其一,通过电视、广播、电台、报纸等新闻媒体,对拒不按期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件所确定之义务的债务人也即被执行人的姓名(法人的名称及其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名称及其主要负责人)、所欠债务数额、本应自动履行的期限等进行曝光,借助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以迫使被执行人履行债务。
其二,由人民法院组织召开债权人、债务人大会,对执行程序中之债务人晓以利害,使其当场履行给付义务或订出具体的还款计划,督促其自觉履行。
其三,全院“上下皆兵”,集中人员、集中时间、集中物力,组织不同规模的“执行歼灭战”去“啃”那些陈年积案与“骨头案”。如据1999年9月8日《人民法院报》报道,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8月29 日11时至次日清晨,在短短的十几个小时之内,出动干警80余次,车辆20余部,对83起案件进行了执行,此一事例即为典型例证。
其四,与上述诸种举措相关联的是,不少人民法院往往在双休日、甚至当人们正在酣然入睡的深夜实施强制执行,此曰“午夜行动”、“零点行动”,其目的在于“突发奇兵”,以达到“攻执行债务人于不备”之奇效。
其五,在执行中,以对执行债务人实施诸项强制措施中最为严厉的司法拘留作为最后的保障手段,甚至不惜对其作刑事化的处理,以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罪予以制裁。
正是由于上述列举的诸项举措或曰特征,使得这些执行行动颇为类似于军事领域中的作战,故而笔者以“执行会战”对其予以概括。毋庸置疑,自各地人民法院纷纷大打“执行会战”以来,仅从执行结果而言,可以说一反以往相当长的时间内执行工作明显不力之“颓式”,一举解决了相当数量的陈年积案,从而部分地甚至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了由来已久的“执行难”。据报载,在全国法院响应上级部署而开展“执行工作宣传周”期间,依照26个高级法院的不完全统计,共执结案件55,300余件,执结标的额43.81亿余元人民币。对10,000 余名执行债务人实施了司法拘留, 对极少数暴力抗法分子进行了法律制裁(见1999年9月11日《人民法院报》)。显而易见,通过“执行会战”,不仅使得执行债权人本应早就予以实现的合法权利得到了切实实现,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对于那些恶意逃避债务的执行债务人来讲,无疑起到了“杀一儆百”之威慑作用。由此观之,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不为此而额手相庆,拍手称快。
二
尽管对于大打“执行会战”之骄人成绩不可加以任意贬低,然而我们在进行一番冷静、理性地思考之后,则会无奈地发现,“执行会战”在实施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已经在客观上部分地甚至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蚀了它的显赫战果,且从长远来看,其更是弊大于利。联系前述“执行会战”之具体举措,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弊端:
第一,“执行会战”的集中性特征,决定了其与日常对个别案件的执行相比,需要动用较后者多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力、物力、财力,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滋生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依照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第1款之规定,“执行工作由执行员进行”,这是基于“审、执分立”原则而确立的,是执行工作得以正常、公正、高效进行的重要保证,但在“执行会战”中,由于各地人民法院原本就很少的执行员根本不能满足这种大规模集中作战的需要,故而必然使得在相当多的执行场合由审判员来“担任”民事执行工作,这显然有违上述法律规定。二是“执行会战”中,全院上下一齐出动专政执行的结果,必然会对民事案件(以及经济纠纷案件)的正常审判工作形成巨大冲击,不仅会使得已经系属于人民法院中的民事案件、经济纠纷案件因此而被暂时“束之高阁”,从而得不到应有的及时解决,而且亦会因此而致使那些亟待解决但尚未系属于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和各类经济纠纷被拒斥于“法院之门外”,从而形成新的“起诉难”、“告状难”,这必然会影响到社会成员对民事诉讼这一纠纷解决机制的原有信赖,若果其如此,则肯定会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程起到不可小视的消极作用。质言之,大打“执行会战”之客观结果明显造成了我国本就相当稀缺的司法资源的“畸形”配置。在此意义上,大打“执行会战”无疑使得人民法院从以往长期以来“重审判、轻执行”的偏向明显发生了向“弃审判、保执行”的再度异变,这不仅“失之东隅”,而且亦没有起到“收之桑榆”之效果。
第二,在大打“执行会战”的情况下,众多案件之“执行完毕”往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牺牲程序公正为代价的。从诉讼理论上讲,民事执行相对于民事审判而言,其在程序公正的要求上固然较后者为逊而更加强调效率性,但这绝不意味着执行工作就可以一味地追求效率而不讲求程序公正。从广义上来讲,作为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设置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强制执行程序。其中从执行程序的开启到执行措施的采取,均有十分严格的程式要求须加以遵循,其对双方当事人自当如此,对于拥有执行之职权的人民法院而言,则更应如此。不言而喻,在短短的数天甚至一天之内突击式对大批案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陈年积案)予以集中执行之“执行会战”,其对执行程序之恪守程度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第三,在“执行会战”中,由于未能严格遵循(在少数情况下甚至于践踏了)我国民事诉讼法所明确设定的一系列执行程序规则,故其在实现债权人之债权的同时,往往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毋庸置疑,民事执行固然以实现执行债权人之债权为宗旨,但其同时无疑还须兼顾对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而绝不能以牺牲后者为代价,这一点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222条、第223条关于对被执行人的某些财产、收入应作适当保留而不得予以强制执行的规定中以及其他条文中所赋予的被执行人的某些程序上的权利,便可略窥一斑。但在“执行会战”中,由于受片面追求执结率之驱动,各地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往往置我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保护被执行人合法权益之规定于不顾,突破现行立法,大搞各行其是,如以登报公示等方式进行媒体曝光、任意对被告作扩大化的刑事处置、侵犯宪法所赋予公民的休息权这一基本权利而搞所谓(突袭式的)“零点行动”、“午夜行动”等等。
第四,“大呼隆”式的“执行会战”运动必将会给人民法院日后的日常执行工作留下诸多后患。其突出表现为:其一,客观上给某些人民法院更加不注重日常的执行工作委以口实,因为通过此次“执行会战”,极有可能使他们错误地认为日常执行工作开展如何,甚至开不开展都无关宏旨,只要不时地搞一些规模不等的“执行会战”,即可弥补日常执行工作之不足,其结果反而造成了新的“执行难”。其二,在“执行会战”过程中,有些人民法院原本积案不多,但为了完成上级硬性摊派的执结指标,不惜上门动员胜诉当事人提出执行申请,这不仅直接侵犯了申请执行人所享有的处分权和双方当事人均享有的期间利益(当然对于债务人一方来讲,只是间接地享有期间利益),而且由此所留下的隐患必将在不久的将来以较为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
三
综上观之,笔者认为,由于“执行会战”本身所固有的诸多弊端,故而其之实施虽从表面上看(在特定的阶段、特定的意义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执行难”,但若从长远观之,其对于解决“执行难”则无异于“饮鸠止渴”,而由此所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更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灾难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执行会战”之实施大大地违背了强制执行工作皆为个案执行(即审结一案,依法及时执行一案)且均须有严格的程序保障这一客观规律。基于此理,笔者主张,“执行会战”应当(而且可以)休矣。各地人民法院在当前以及今后若能将他们在大打“执行会战”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和劲头运用到日常的执行工作中去,一改以往的懈怠和懒散,以一丝不苟的态度认真对待每一个执行案件,并在执行每一个案件时依法穷尽所有可能的执行手段,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客观、按兵不动或“浅尝辄止”、敷衍了事的话,那么,即便在现有的(强制执行)法律框架之内,民事案件以及经济纠纷案件的“执行难”状况亦将会得到相当程度的克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