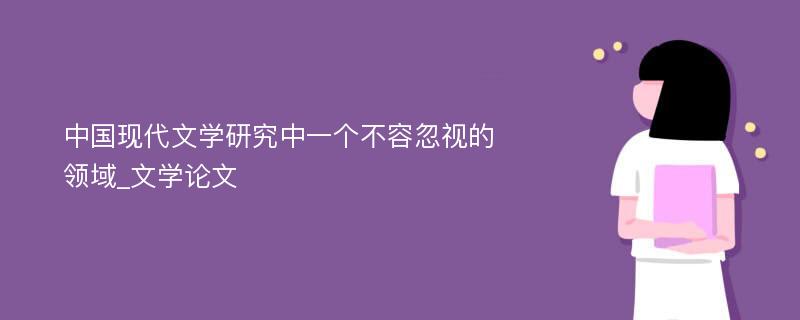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不应忽视的一个区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应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区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在若干年前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禁区,因为当时把西方传教士的所有活动都视为“文化侵略”,也就不可能肯定传教士推动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作用。近年来对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仍然很少有人研究,其原因在于认为西方传教士不是中国人,他们的活动不属于中国文学范围。其实历史的目标在于展现过去,西方传教士虽然不是中国人,但是他们用汉语所写的作品,对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当你试图说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时,离开了传教士的活动,就显得很不全面。当今西方如英国文学,一些重要作家往往都是其他民族而用英语写作的,如被伊朗追杀的拉什迪,就是印度人。西方传教士虽然不是中国人,但是他们用汉语写作的作品,已经融入中国近代文化大变革的背景之中,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这一课题,对于探索中西文化交融,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发生等等一系列课题,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只是作一个粗浅的尝试,以就正于方家。
中国文学受到印度佛教的影响,对这一影响,研究者众多,论著也不少。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传教活动在明清之际曾有一个高潮,但是至今还无人研究当时的西方传教活动是否对当时的中国文学产生过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只知道明清之际的传教士似乎没有多少文学活动,他们涉及到文学方面的著述只是在他们的中文著作中引用一些《伊索寓言》,这些引用和中文著作似乎并没有对当时的中国文学创作产生影响。
进入十九世纪之后,西方教会重新致力于对中国传教。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肯定:这些传教活动,对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影响较小而潜移默化的过程,第二阶段是影响极大甚至是具有指导意义的过程,这两个阶段可以甲午中日战争为分界线。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中国的留学生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西方传教士的作用也就淡化了,可称之为第三阶段。
表面看来,西方传教士的文学活动要在十九世纪40年代之后才产生,但倘若认真考察传教士的活动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我们不难发现,传教士对文学的影响可能要更早一些,它最早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文学传播模式,从而也就间接影响了文学。
中国古代的文学是由士大夫阶层垄断,文学活动的构成是由士大夫创作的文学作品,刻印成线装书后分送或者出售,供士大夫阅读。书商不仅不付稿酬给作者,有时还要向作者收取刻印费。因此,这时的文学活动,基本上不受“市场机制”的制约。士大夫衡量文学的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是“载道”,一是“雅”。市民等平民百姓阅读的“白话小说”既不“载道”,也不“雅”,因此不在当时的“文学”范围之内。即使在小说领域,由于稿费制度、著作权制度、版权制度的缺乏,“市场机制”也处在萌芽状态。
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文学从士大夫垄断的状态下解脱出来,面向普遍百姓。这一转变的关键则是报刊与平装书等新型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传统文学的传播方式。而中国文学的这一转变,最初便是由西方传教士引进的。1815年,英国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了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是第一份中文期刊,这是用雕板印刷的线装杂志,由教会免费散发。虽然它还没有运用机器复制,也没有进入商业化的营业方式;但是该刊已经把寻求士大夫之外的读者,作为办刊的宗旨。编者主张:“盖甚奥之书,不能有多用处,因能明甚奥之理者少故也。容易读之书者,若传正道,则世间多有用处。浅识者可以明白,愚者可以得智,恶者可以改就善,善者可以进诸德,皆可也。”(注:《〈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序》,《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第一卷第一期,1815年8月5日。)已经试图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寻求更多的读者。
报刊与后来出现的平装书从一开始就把读者对象定在普通老百姓身上,这就必然促使它们追求“俗”而不是“雅”。文学语言在士大夫手中,自然是越“雅”越好,士大夫十年寒窗,用功苦读,学的就是如何运用典雅的文言,这典雅的文言也就成为士大夫的专利。但对于西方传教士来说,他们愿意用白话或浅近文言的“俗”语。这是因为:首先,士大夫对西方的传教往往采取拒斥的态度,因而成为中国最不愿意接受传教的阶层,这就促使西方传教士在传教时更多注意到士大夫以外的平民百姓。其次,中国典雅的文言文实在太难学了,要做到运用自如,非下十年以上的苦功不可,而西方传教士很少有可能有十年以上时间潜心学习典雅的文言文。于是,客观与主观的条件都决定了他们运用白话或浅近的文言来撰写文章,说明他们要说的道理。这就决定了西方传教士开始写的文章就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文章不同。从1815年到十九世纪末,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大量报刊,也撰写了大量的文章,这些文章改变了中国古代的文章写法,显示出新的特点。
大体说来,传教士的文章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很少用典。传教士的文言很少运用典雅难懂的词句,有的文章干脆就用白话加上一些文言虚词,有的文章甚至如同说书前的引子,如《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第一号在报道新闻前便有一段话:
在广州府有两个朋友,一个姓王,一个姓陈,两人皆好学,尽理行义,因极相契好,每每于工夫之暇,不是你寻我,就是我寻你。且陈相公与西洋人交接,竭力察西洋人的规矩。因往来惯了,情意浃洽,全无一点客套,虽人笑他,却殊觉笑差了,不打紧。这段类似说书的话以前从不在正经文章中出现,传教士的运用,是一种突破。
二是不拘文章程式。明清以来,科举以“八股文”应试,文章程式受到文人重视。桐城派推重古文,从方苞的“义法”,到姚鼐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形成了一套作文规则,不仅“起承转合”须有“法度”,连什么词能进古文,什么词不能进,也有许多规定。西方传教士的文章以说清问题为目的,不拘文章程式,虽显生硬,但也常常明白晓畅,而且逻辑性强,比较自由。
三是运用了新式标点。标点符号本是源自西方世界,西方传教士很自然地将它们运用到中文期刊之中,马礼逊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已经运用标点符号,顿号、逗号、句号与专用名号都已出现在文章之中。
四是引入了许多新名词。传教士创办的报刊要介绍西方的情景,自然要运用许多新的名词,确定新的译名。这些名词有的便积淀在后来的汉语中,如法国,在中国古代一直称为“佛郎西”、“佛兰西”,传教士创办的报刊称之为“法兰西”,一直沿用至今。
只要看一看传教士文章的这些特点,便不难看出它们正代表了后来中国文章的发展方向。中国的文章后来由“报章体”发展到梁启超的“新民体”,文章更显明白晓畅,更富于情感,完全冲破了中国古代文章的格局。对照胡适在五四前《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不主义”更可看出文学语言的变化趋向。在这一变化中,西方传教士的文章可以算是先驱,西方传教士的文言文基础差,反倒帮助他们融通中西文化,打破传统士大夫的清规戒律,促进中国文学的变革。汉语表达由深奥走向浅显,西方传教士功不可没。
早期西方传教士也曾有过一些文学活动。中国最早翻译的西方长篇小说是英国班扬的《天路历程》,该书于1853年由英国来华的传教士宾威廉翻译成中文,于厦门出版。此后该书便屡有再版,连日本当时翻译《天路历程》,也是由上海美华书局出版的宾威廉的中文译本转译的。只是宾威谦翻译《天路历程》并没有把它作为一本文学名著,而是作为一本宗教著作,出于传教的需要来翻译的。译者不具备文学的自觉性,该书在当时也未对中国文学产生多少影响。
比较具有文学自觉性的西方传教士是英国的艾约瑟,他在传教士创办的杂志《六合丛谈》中,先后发表了《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希腊诗人略说》、《罗马诗人略说》等文,介绍了古希腊古罗马的一些文学概况。但由于这些作家的作品并没有翻译成中文,这些介绍也只能是“广中土之见闻”,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大。即使此时有外国传教士着眼于介绍西方文学,翻译西方文学名著进入中国,也未必能产生重要影响。其原因即在于中国文学创作的主体是士大人阶层,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以普通老百姓为读者。这一改变虽然预示着近代传媒变革的发展方向,预示着文学的普及俗化,但是普通老百姓在当时条件下毕竟难于成为作家,而当时的中国作家仍旧是那些拘泥于传统的士大夫,西方传教士要对中国文学创作产生影响,就必须影响这些士大夫。而士大夫因为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影响士大夫要比影响普遍老百姓困难得多。这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过程。
西方传教士找到一条影响中国士大夫的途径,这就是从“道”入手。事实上,传教士从来也没有想在文学方面影响中国,他们一直想的是如何改变中国社会。西方传教士后来发现,仅仅在社会下层传道,只能扩大教徒的数量,而难以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传教士狄考文指出:“不论在哪一个社会,受高等教育的人们,都是有势力的人们;他们控制社会情感和意见。”“作为儒学思想的支柱者是受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级,如果我们要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我们就要准备好自己的人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士大夫,因而能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注:《在华新教传教士1890年大会记录》第468页。 )狄考文的主张在当时成为在华新教传教士的共识,他们不仅要培养新一代的学生来取代士大夫,而且希望通过他们的著述来影响中国的士大夫。把西方文化之“道”融入文章之中,影响中国士大夫。
西方传教士受文化训练不足,难以撰写令中国士大夫倾服的“雅”文章。但是他们介绍西方之“道”,无论是西方科学,还是西方的社会制度,文化思想,却不能不引起中国士大夫的兴趣。西方列强一次次打败中国,逼迫清朝签下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促使有志于改革的士大夫探究西方之“道”。当报刊逐步打入内地,并且出现商业性报刊之时,西方传教士的报刊以介绍西学之“道”,开创了报刊文章的新局面。胡汉民曾经回忆道:“中国人之报,最先滥觞者为港澳之地,上海继之,于以流衍内地。港之《循环报》、上海之《申报》尚存于今日,即中国人最先之报也。其先发行日报者,以邮通外事为目的,故舍译报录新之外,他皆不甚注意。继而内地之报,率以词章八股之士为主笔。于是骈四俪六之语,风云月露之词,洋洋盈纸,主报者与阅报者,俱茫然不解报纸之真价,盖亦时代限之不足怪也。自林乐知,李提摩太诸人创《万国公报》,属中土人士为译述,旬月一发刊,虽专为基督教家言,然亦锐意以开导民智为任,破除文人结习,于报界一新其面目。”(注:胡汉民《近年中国革命报之发达》,新加坡《中兴日报》1909年1月29日、30日第1版。)说明了《万国公报》在当时报刊中的特殊地位。 其实《万国公报》不仅一新报界面目,也一新中国的文面目。曾国藩曾经指出:“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尔。”(注:曾国藩《致吴南屏书》。)说理是中国古文的一个薄弱环节,一直到吴汝伦、林纾都一直在设想:引彼西理,助我古文,开拓古文的新局面。西方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大量的说理文章,这些文章虽不脱模仿中国古文的痕迹,但也挣脱了古文的羁束,比较自由地说理,显示出“报章体”的能量。谭嗣同在1897年初作《报章文体说》,将文章区分为三类十体,断言“乃若一编之中,可以具此三类十体,而犁然各当,无患陵躐者,抑又穷天地而无有也。有之,厥惟报章,则其体裁之博硕,纲领之汇萃,断可识矣。”(注:《谭嗣同全集·报章文体说》。)其时维新派创办报刊还刚刚开始,谭嗣同对报刊的认识,有许多实际上来自于传教士创办的报刊。
西方传教士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为中国先进士大夫所接受。甲午中日战争,历来被中国看不起的日本,在学习西方“明治维新”之后,居然打败了中国,士大夫深感亡国在即,纷纷注意西学。此时西方传教士成为中国士大夫认识西学的主要桥梁,这也是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文学影响最大的时期。晚清的文学变革,一些文学运动的萌发,尤其是其指导思想,背后往往有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存在。
中国小说有悠久的历史,但小说的数量一直不太多。小说在晚清有一个突发性的急剧膨胀期,短短几年,晚清小说的数量几倍几十倍地增长。晚清小说的急剧发展与把小说作为开启民智,教育民众的工具这一指导思想有关,而这一指导思想的发端,则可以上推到西方传教士傅兰雅的“求著时新小说”。1895年6月, 傅兰雅在《万国公报》登出启事:“求著时新小说”,提出“窃以感动人心,变易习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注:载《万国公报》第77册,1895年6月出版。 )他希望中国文人能撰写小说,显示这三大积弊的害处。这是中国近代最早明确提出以小说来革除旧弊,除旧布新,开启民智,感化民众的设想。虽然傅兰雅的启事没有立即产生晚清的“新小说”,在应征的162 卷小说中,没有1 卷符合傅兰雅的要求,傅抱着“若过吹求,殊拂雅教”(注:傅兰雅《时新小说出案》,载《万国公报》第 86册,1896年3月出版。)的想法,勉强发了奖,小说却没有印行。但是傅兰雅的倡导,却在士大夫中产生了影响,肖詹熙于1895年创作小说《花柳深情传》,便自认是受了傅兰雅的促进。(注:肖詹熙《花柳深情传》序。)
康有为后来说起,他在上海书肆购书时听说小说卖得最多,便巳有了用小说教育民众的念头。(注:康有为《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南海先生诗集》卷五《大庇阁诗集》。)但在晚清“新小说”最主要的倡导者梁启超身上,我们可看到西方传教士“求著时新小说”之影响。梁启超最早提倡“新小说”是在1896年撰写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他提出:“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雅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形极相,振厉末俗。”(注: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载《时务报》第18册。)“专用俚语”,“穷形极相,振厉末俗”,都是傅兰雅的愿望,而“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就是傅兰雅指出的三大积弊,希望用“时新小说”来帮助革除的。梁启超在傅兰雅的主张上进一步发展,加上“借阐圣教”,“杂述史事”等古代小说已有的内容,和他自己设想的“激发国耻”、“旁及彝情”、“宦途丑态”等等。从中显然可以看到明显的传承关系。梁启超后来提倡“新小说”,发动“小说界革命”的最初设想,是受传教士提倡“时新小说”的启发。
西方传教士还为“新小说”提供了“政治小说”的模本。以往我们近代小说的研究往往只重视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而忽视了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其实后者的影响更早,更直接。1891年底至1892年4月, 上海《万国公报》连载了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的《回头看纪略》,它是美国贝拉米于1888年刚刚出版的乌托邦小说《回顾》的节译本。1894年广学会又出版了《回头看纪略》的单行本,易名曰《百年一觉》。它立即在中国先进士大夫中引起震动。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便提出“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书是大同影子”。(注: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中华书局1988年3月版,第133页。)他在写作《人类公理》时参考过《回顾》。光绪皇帝1898年订购129部西书,其中有《百年一觉》。谭嗣同在《仁学》中特别提到:“若西方《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梁启超将《百年一觉》列入《西学书目表》作了介绍。孙宝萱在日记中曾五次提到《百年一觉》,为之激动不已。(注:见《忘山庐日记》。)徐维则更明确点出:《百年一觉》“言美国百年以后事,亦说部之属。泰西人亦有此种书,甚可观。惜此本未全耳”。(注:徐维则《东西学书录》下册,第40页。)从小说角度肯定了该书。梁启超后来撰写《新中国未来记》,其构思便与《百年一觉》有相似的地方。因此,《百年一觉》实际上为“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提供了“政治小说”最早的模本。
中国古代虽然重视文学,也有人主张文学“经世致用”,但是却从未有人把文学作为“救国”的工具。中国近代文学思潮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文学救国论”的崛起,此后它一直影响着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仔细推溯“文学救国论”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我们又可以找到西方传教士的影响。1896年,广学会出版了传教士林乐知编辑的《文学兴国策》,它编辑了日本驻美公使森有礼70年代征求到的美国名流对日本改革的意见,实际上谈的是文化教育问题。但是《文学兴国策》用“文学”来涵盖文化教育,类似于中国古代把所有文字著述都当作“文”的概念。该书说明它是日本大使在美国征求各所大学学者和议员及“一切著名文学之人”的意见,表明它代表了西方当时对“文学”的看法。该书主张:“文学为教化必需之端。”“故国非人不立,人非学不成,欲得人以治国者,必先讲求造就人才之方也,造就人才之方无他,振兴文学而已矣,夫文学固尽人所当自修者也。”如果说《文学兴国策》的主张与中国古代传统重视文学教化的主张并无不同;那么,在“教化”的内容上则有了重要的区别:“夫文学之有益于大众者,能使人勤求家国之富耳”。新教伦理的“勤求家国之富”被视为“文学”的目标,所以作者论证:“文学有益于商务”,“能扩充人之智识,能磨炼人之心思,使天下之商,皆晓然于各国之物产,市面之消长,运货有至贱至捷之法,造船有至稳至快之式,而且设关收税,亦有至善之规”。“文学”要表现说明的是这些内容,它是商业通讯和各种各样的“说明书”。为了说明文学能够“兴国”,作者认为:“文学既兴,而士农工商四民之职业,各得其益,且可交资其益矣”。为了进一步印证这一结论,作者又用夸张的语气提出欧洲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有教化者国必兴,无文学者国必败,斯理昭然也,即如三百年前之西班牙,实为欧洲最富之国,嗣因文学不修,空守其自然之利益,致退处于各国之后,而不能振兴,此外各国,亦多有然”。另一方面,“普鲁士为欧洲至小之一邦,国人振兴文学,鸿儒辈出,卓越他邦,曾不几时,成为今之德意志联邦,与欧洲诸大国相同”。“文学不修”可以使强国变弱”,振兴文学“可以使弱国变强,小国变大”,文学的“救国”功能由此可见一斑。
以往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海内外学者,似乎无人注意到林乐知翻译的这本《文学兴国策》。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该书所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而是“文化教育”,它与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并无多大关系,它所用的“文学”包括所有的文字著述,这或许是人们忽略它的理由。但如果从“文学救国论”的兴起来考察,《文学兴国策》在中国近代便起了特殊的作用,它于1896年问世,其时正是“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年,中国知识分子纷纷转向西方寻找真理,中国学习西方由学科学技术正转向学政治思想。西方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后不断介绍的“西学”已经在中国确立了它的威信,出版该书的“广学会”是当时教会在中国办的最权威的出版机构,晚清影响最大的期刊《万国公报》当时就由它出版。翻译《文学兴国策》的林乐知曾经主持过包括《万国公报》在内的许多报刊和出版机构,翻译过大量西方著作,是当时中国著名的西方学者,所以该书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此外,甲午战争打败中国的是日本,最令中国士大夫震惊的是一个原来被中国看不起的小小岛国,竟然一下子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文学兴国策》似乎送来了日本富强的秘诀,不仅是日本的,也是欧洲列强和美国富强的秘诀,那就是将文学变成各种各样的教科书。它对当时中国士大夫的吸引力,自不待言。
中国士大夫几乎是立即接受了《文学兴国策》,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将它列为“最佳者”之一,《文学兴国策》几乎进入当时所有的“西学书目表”。谭嗣同在1895年还在后悔以前将时间花在钻研桐城古文和魏晋文章上,“处中外虎争文无所用之日,丁盛衰纽膂力方刚之年,行并其所悔者悔矣,由是自名壮飞”。(注:谭嗣同《三十自纪》,《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但是到了1897年,他已经撰写了《报章文体说》,为文学唱赞歌了。《文学兴国策》在中国造成最重要的影响是“文学救国论”的兴起和把文学当作教科书。
中国古代虽然有“文以载道”与“以文治国”之说,此二者与“文学救国”已经比较接近;但是并没有直接产生出“文学救国论”。以往有一种看法,认为晚清的“文学救国论”是中国面临亡国危机,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产物。这一结论其实似是而非。亡国危机,民族矛盾尖锐只是产生“文学救国论”的土壤,并不能直接生成“文学救国论”。在中国历史上,面临亡国危机,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多得很:六朝时期,以汉族为主的南朝与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对峙达数百年之久,处在亡国危机,民族矛盾尖锐的状态下并没有产生“文学救国论”。南宋时期,宋金对峙也达一百多年,士大夫慷慨悲歌,志在匡复故土,却没有产生“文学救国论”。明清之际,士大夫痛心疾首,反清复明的活动达数十年之久,虽然号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没有形成“文学救国论”。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亡国危机的紧迫形势只能是“文学救国论”的土壤,而直接的种子,则是“文学兴国策”。
要“文学救国”就要教育民众,就要有教育民众的“教科书”。中国古代并不是没有文学教科书,《三字经》、《百家姓》是教科书,韩愈文、杜甫诗也常常被人作为教科书。但是中国古AI写作《三字经》、《百家姓》等教科书的作者不会把自己的作品作为文学创作,而韩愈、杜甫在创作自己的诗文时也从来没有将自己的创作作为“教科书”来写。教科书的写作与文学创作的界限是分得很清楚的。这种区分一直到晚清都很明确:曾国藩为了使湘军士兵明确自己的责任,写作了不少供湘军唱的歌辞,用来教育湘军士兵,但是曾国藩从不将这些歌辞作为自己的文学创作。但在《文学兴国策》问世之后使不同了,教科书被作为文学的重要功能。梁启超推崇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出版。 )因为小说能做“教科书”。不仅“学堂宜推广以小说作教书”,(注:老棣《学堂宜推广以小说作教书》,《中外小说林》第1年第18期。 )而且“欲扩张政法,必先扩张小说;欲提倡教育,必先提倡小说;欲振兴实业,必先振兴小说;欲组织军事,必先组织小说;欲改良风俗,必先改良小说”。(注:陶佑曾《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游戏世界》第 10 期,1907年出版。)当时理论家提倡各种各样的小说,希望它们能够成为教育民众的“教科书”。最有意思的是不仅理论家提倡把小说作为“教科书”,连小说家自己也把小说当作“教科书”来创作,甚至明明创作的小说不是“教科书”,也把它当作“教科书”。李伯元创作的《官场现形记》明明不是“教科书”,他偏要说自己创作的小说是一本“教科书”,只是烧了下半部。(注:李伯元《官场现形记》第60回。)可见当时作家,确实有不少人把写“教科书”作为自己创作的使命。晚清许多小说家创作“教科书”,与西方传教士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然而,在中国社会广泛接受西学,西学成为“显学”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便不再满足于停留在西方传教士介绍的“西学”上,转而直接向西方寻求真理,这时,留学生便取代了西方传教士的地位,成为推动中国文化变革的中坚。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小,不再占有重要地位。大约在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便日趋缩小,1907年《万国公报》停刊,标志着西方传教士的影响逐渐衰微。
综上所述,西方传教士用汉语写作的论述,创办的报刊,提出的主张,由于发生在中国文化的转型期,它们作为西方文化对近代中国的最初挑战,对中国近代文学发生影响。这些影响是广泛的,它遍及文学观念,文学创作,文体形式,文学语言,以及文学的传播方式等各个方面,从而促进中国文学转型,走上变革之路。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当我们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探讨它的起源与萌芽,往往可以追溯到西方传教士的影响。这也是西方传教士影响的价值之所在。
但是,西方传教士的文学观念往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近代文学观念。他们依然停留在中世纪基督教的文学观念上,以文学劝善惩恶,把文学当作政治教化的工具,他们似乎也没有西方近代所形成的“文学独立”意识。这一缺陷也对中国近代的文学变革造成重要影响。从发生学的意义看,胎儿孕育时的“先天不足”常常会对他后来的成长带来不利的影响,这也在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中显示了出来,过分注重文学的“教化”作用,希望文学成为“教科书”的愿望延续了多年。从“五·四”时期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人的“思想标准第一”,到后来的“政治标准第一”,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于是,文学成为工具,成为载体,艺术标准难以独立也就伴随着文学的发展,艺术精神的失落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胎里病”。
标签:文学论文; 梁启超论文; 传教士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士大夫精神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天路历程论文; 万国公报论文; 晚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