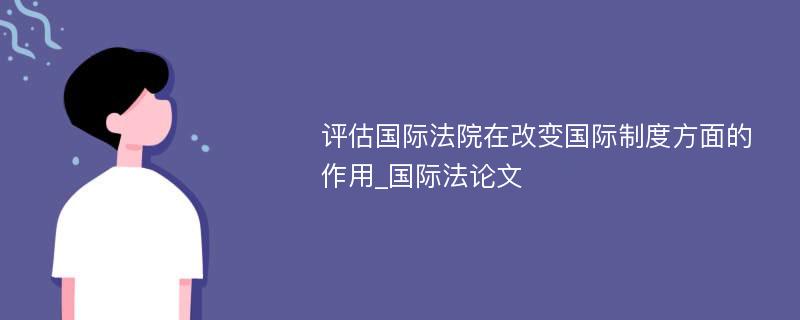
变动国际体系中国际法院作用的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论文,变动论文,法院论文,体系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09)03-0104-05
一、前言
一般认为,国际体系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威斯特伐里亚体系时期,国际社会组织化时期,全球化时代。[1]尽管就全球化时代一词的界定、这一趋势的起始时期仍然存在诸多分歧,不争的事实是,在这一变动的国际体系中,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均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其表现之一是,国际社会组织体系的核心——联合国——正面临着60年多来最大的变革。促使这一变革产生的原因是:“在我们这个年代,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各种威胁前所未有地相互交织在一起……有必要塑造一种更为广泛的新型理念……达成新的安全共识。”[2]其表现之二是,国际法的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横向扩展和纵向拓深,国际法等级化、碎片化的趋势已经出现。[3]在不存在统一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国际社会,如何保证国际法的统一有序发展正成为一个现实的挑战。与此相对应的是,国际争端日趋多元化、复杂化和专业化,国际性法庭因而大量增多,并造成如下两种后果:(1)国际性法庭之间司法权相互重叠,可能导致“挑选法院”及“歪曲司法运作”的问题。(2)国际法庭增多带来了判例相互冲突的严重风险。[4]概而言之,在国际体系由国际社会组织化时期向全球化时代变动的过程中,国际关系、国际法制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国际司法体系必然及必须做出适当的反映。
在其位,谋其政。作为联合国——国际社会的核心舞台和全球成员国最多、所辖事务最广的国际组织——的主要司法机关,国际法院注定必须在这一变动的国际体系中发挥主要的作用。事实上,与其它国际司法机关相比,国际法院确实具有相当明显的优势:首先,国际法院是唯一具有全面管辖权的国际司法机关,其它国际性法庭相比之下要么具有专业性,要么具有区域性。[5]联合国对于国际社会的非凡意义、国际法院法官的任职条件等因素均使得只有国际法院具备足够的潜能对一般国际法提供主导性的权威陈述及在维持国际法的一致性方面发挥重大作用。[6]其次,国际法院在处理诸如边界争端等某些国家并非特别关注其结局、但是却不能通过协商方式解决问题的特定种类的争端时特别有帮助;其三,鉴于越来越多的解决环境争端的需要,建立了一个特别的分庭以处理递交给它的环境争端的国际法院同样可以被期待将来在这一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四,对于中等力量的新国家而言,法院可以成为协调其利益的值得信赖的机构。
能者常需多劳。正因为上述两个原因,国际法院在一个变动的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尤显突出,正确评价其作用也尤为必要。
二、对国际法院不同时期作用的评价
以美国撤销承认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及国际法院所受理的案件数量为标准,可以清楚地看出,在1986年前后,国际法院的表现及国际社会对于国际法院的评价截然不同。
1986年以前,国际社会对于国际法院的作用颇为不屑。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在1985年的“美国侵犯尼加拉瓜的军事行动案”中对国际法院采取了一种相当蔑视的态度。[7]在该案中,美国不仅公开表达了对国际法院的不满、抵制法院调查事实的行为并拒绝参加法院其后的审判阶段,且两次在安理会针对尼加拉瓜试图执行国际法院判决的行为投下否决票,并最终宣布撤销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美国认为,国际法院更多地为政治因素所驱使,而非为对公正的追求所驱动。[8]考虑到美国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它的上述行为无疑会让人对国际法院的前景持一种比较沮丧的态度。与此同时,同样由于对国际法的普遍的怀疑,包括一些大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也对国际法院持保留态度,认为国际法院根本没有对国际关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做出相应的回应。许多发展中国家则视国际法乃至国际法院为西方国家的产物而不愿对其加以利用。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国际法院被视为一个软弱的、无所谓的机构,陷入了一种有趣的悖论之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集团均对其表示不满意。
令人欣慰的是,1986年以后,国际法院慢慢恢复了它作为一个公正的国际裁判机构的形象,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认可,所受理的案件日益增多。比较形象的一种说法是:国际法院正在经历一个复兴的阶段。两方面的事实可以证实这一说法。其一是: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法院每年的待审案件均只有一个或两个。在1990-1997年间,待审案件的数目增至9个至13个。从那时起,待审案件的数目一直是20个或更多。截止2008年7月31日,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数为12个。诉讼案件来自世界各地,所涉及的问题多种多样。[9]其二是:自1946年以来,截至2008年7月31日,法院已作出判决93个,发表咨询意见24项。法院的判决和咨询意见涉及领土纠纷、武力的使用、去殖民化、外交关系、庇护权、国籍、人权保护、过境权和经济权利等众多重大事项。①与此相应,国际社会开始对国际法院不吝赞美之词:“当所有外交努力用尽时,法院是和平并最终解决各种争端的最适合渠道”;“国际法院是联合国面对日益错综复杂的世界,确保在国际关系中真正推行法治的关键机构和主要机关。”[10]
事实胜于雄辩。要想正确地评价国际法院的作用,全面审视国际法院的司法实践并从历史的角度对其加以分析无疑是最为必要的。
三、国际法院近期的实践
(一)在咨询管辖权方面
法院在这一方面的表现依旧不太活跃。自1986年以来,法院共计发表咨询意见7项,平均每年0.35项。就其数量而言,相比法院1986年以前的情形,这一阶段所发表的咨询意见数量依旧不多,比例稍有下降。②就其内容而言,总的说来,法院的咨询意见秉承了解决重大国际法问题的传统。回顾历史,1948年,国际法院以审查一个在当时处于联合国利益中心的问题(接受联合国会员国问题案)开始其咨询意见。2004年,法院就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所发表的最近的咨询意见则直接涉及到整个世界均关注的、潜在影响整个国际社会秩序的两种权利——自决权和自卫权。介于二者之间的问题是:国际组织的豁免权和核武器使用的合法性等事项。国际法院通过对重大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既促进了国际争端的解决,又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
(二)在诉讼管辖权方面
1.利用任择条款的情形。自1986年至2008年7月31日,共20个诉讼案件基于任择条款被交至法院,平均每年0.91件,约占该时期总案件数(46件)的43%。③案件主要涉及两大诉讼主题:7个案件涉及海洋权益方面的纠纷,7个案件由前南斯拉夫针对北约在1999年对其使用武力的合法性而提出。总体上看,利用强制管辖权所解决纠纷的案件总数占全体纠纷数的比例上升了;案件的结局也相当令人满意。
2.利用仲裁条款的情形。自1986年至2008年7月31日,依仲裁条款向国际法院提出的案件共计30个。④案件主要涉及三大诉讼主题:武力的使用(15件,11件与前南斯拉夫有关)、条约的解释(6件)和海洋权益纠纷(3件)。至少从表面上看,与利用任择条款相比,利用仲裁条款的方式似乎受欢迎得多,利用率也相对高多了:平均每年1.36件,约占该时期总案件数(46件)的65%。⑤而且,基本上不存在拒不出庭或对法院判决视若无睹的蔑视法院的行为。
(三)两个特殊现象
1.利用法院分庭的情形。自1984年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利用分庭解决缅因湾海洋区域划界案以来,国际法院又以这种方式解决了5起争端。包括:边界争端案(布基纳法索诉马里,1986);艾尔西公司案(意大利诉美国,1987);陆地,岛屿和海洋争端案(萨尔瓦多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参加,1992);边界争端案(贝宁、尼日尔,2002);申请复核1992年9月11日陆地,岛屿和海洋争端案(萨尔瓦多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参加)案所作判决(萨尔瓦多诉洪都拉斯,2002)。
分庭的出现无疑主要为了提高法院的利用率。毕竟,作为一个争端解决机构,法院存在的目的主要在于解决法律争端。因此,理论上,一切有利于争端解决的方式都应该予以鼓励。尤其是在国际法院利用率低下的时期,促进分庭的利用是值得欢迎的。总的说来,从其作用来看,分庭所解决案件的数量总数尽管不多,但内容同样涉及边界争端的解决与国际投资争端等重大事项方面,利用这一方式的国家不仅来自发达国家集团,也来自发展中国家阵营。分庭解决纠纷的作用相当明显。尽管分庭的利用必然带来了一些问题,但这一法院利用方式的出现所带来的更多的是仍是希望而非失望。[11]
2.案件中止的情形。在这一时期,诉讼管辖过程中出现的另一重要现象是案件的中途停止。截至2008年7月31日,共有10例这样的案件。这些案件求助于政治方式而非司法方式的事实再次证明,法院只是国际争端解决方式的一种。但是不难发现,尽管案件中止意味着非司法方式的利用,法院在其中起到了促使案件以政治方式加以解决的催化剂的作用。[12]此外,在很多案件中,如果没有以法院公正的司法作为后盾的话,争端国之间达成妥协肯定要困难得多。毕竟,在纯由第三方裁断争端与自己尚有一定控制权的政治解决方式之间,国家“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心态会逼迫它做出明智的选择。因此,公正的说法应该是:中止案件一方面说明了国家不太愿意利用国际法院,但是另一方面恰恰证明了法院的作用所在。
综上所述,自1986年以来,国际法院的表现大致如下:1.法院发表的咨询意见秉承了解决重大国际法问题的传统,数量依旧不多,年发表率略有下降;2.在诉讼案件中,国家更青睐依仲裁条款而非任择条款提起诉讼的方式,海洋权益纠纷、武力使用的合法性和条约的解释乃诉讼案件的主要主题;3.利用法院分庭解决争端的情形和案件中止的情形略有增多。显然,各国越来越多地显示出了对法院解决争端能力的信心。但是,能因而宣示国际司法就此进入了永远的“春天”吗?“过去显示未来。”回顾历史并从头考察世界法院的表现应是可行的途径。
四、比较法的视角:国际性法院不同时期的表现
纵观国际法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国际法总是在遭遇并最终克服严峻的挑战后才取得重大发展的。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有组织的国际秩序中,规则程序的复苏乃包括热战和冷战在内的所有战争的遗产。[13]当前,国际社会已经经历了三次“世界大战”:一战、二战和冷战。因此,分析国际法院及其前身常设国际法院(以下简称“常设法院”)在三次世界大战后的表现、找出其共同点及其差异之处并分析其原因,对于正确评价国际法院的作用无疑大有裨益及必要。
从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案件的进行情况及争端国对法院的态度等角度看,常设法院与国际法院分别于一战和二战后经历了一个“黄金阶段”和一段“黑暗时期”:
1923年-1936年是常设法院受理案件的高峰时期,法院共做出32个诉讼判决,发表26项咨询意见。1946年至1962年则是国际法院受理案件的第一个高峰期,法院共受理31个诉讼案件和12个咨询案件。⑥在此阶段,在常设法院,有3个案件乃依据任择条款而提交,没有国家对此提出先决反对;有10个案件由争端国共同递交;不存在蔑视常设法院权威的情形。在国际法院的这一阶段,情形很相似:4个案件依据任择条款而提交,同样没有国家提出先决反对;有6个案件由争端国共同提出;除了阿尔巴尼亚在科孚海峡案中拒绝支付赔偿金外,不存在蔑视国际法院权威的情形。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将案件递交给法院的方式显示了争端当事国对通过国际司法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真正信任和通过第三方裁判争端的良好意愿。这一阶段无疑可被视为两大法院的“黄金时期”。
跟随这一阶段而来的是一段对两个法院来说都是的“黑暗时期”:从1937年到1940年,常设法院仅仅受理了7个诉讼案件,没有一起咨询案件,案件数量明显急剧下降。类似的是国际法院的情形:自1963年至1985年,国际法院仅仅受理12起诉讼案件,6项咨询请求,而且在其中7个案件中发生了国家完全蔑视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行为。⑦不难发现,常设法院在此时期案件大为减少的原因是最终引起二战爆发的国家间的敌对气氛。然则,国际法院的情况又如何解释呢?在此时期,法院平均每两年才受理1件案件,1967年,仅一个案件被递交法院,在接下来的4年,没有一个案件递交法院。原因同样很明显:这一阶段不断加剧的冷战气氛慢慢堵上了通过司法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大门。尽管无人预料得到:不久之后,求助于国际法院的高潮就将到来,国际法院再次进入一个“白金时代”——法院再度复新兴。
纵观一战、二战后常设法院及国际法院共同的先盛后衰,不难得出如此结论:任何法律体制均是导致其产生的政治体制的反映;对国际法的依赖程度取决于国际社会当时的政治气氛是否有助于国家愿意通过第三方裁判国家争端的司法方式解决其分歧;任何将法院解决争端的能力推至世界政治体制所能容忍的范围之外的努力都将失败。对比常设法院和国际法院,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常设法院经历近20年最终终结,而国际法院却挺过了冷战的严冬,迎来了另一段“青春”。
鉴于上述历史教训,因此,对于国际法院自1986年以来的实践抱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才较为适当。毕竟,如果以1989年“苏东剧变”作为冷战正式结束的时间,冷战才刚刚过去18年,国际法院重现历史——出现一段“黄金时期”,而后跟随一段“黑暗时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五、国际法院的前景
该如何看待国际法院的未来呢?从常设法院和国际法院在一、二战后均经历的局势来看,国际法院如今的复兴乃国际司法发展规律意料之中的事情,国际法院的未来由此看来似乎并不太令人乐观。但是,从国际法院最终战胜“冷战的严冬”而花开二度的事实来看,更没有理由加以悲观。毕竟,国际社会在不断进步,国际法治的气氛在不断加强,国际法的主体——国家的行为不断理性化。如上所述,从历史的角度看,对国际法院在一个变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只能抱以谨慎的乐观态度;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值得乐观的趋势似乎更为明显。
具体来说,国际法院近来工作中令人鼓舞的标志性事件有:法院越来越多地被利用来作为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方式。大量递交法院的案件中止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观点。毕竟,争端国为何要这么做呢?最合理的一种解释应该是:争端中力量强大的一方迫于国际法院最终公正判决的压力不得不私下与力量弱小的一方达成和解。也许有人因此质疑国际法院的作用,但是必须牢记心中的是,争端是否经由司法方式解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争端的最终及公正解决。即便是国际法院的裁判仅仅在争端的解决过程中起到了一个筹码或催化剂的作用,也是有益和有意义的,胜过于法院作用可有可无的状态。
第二个令人鼓舞的事实是,在1986年至今的这一阶段,蔑视国际法院的判决的权威的事实很少发生,尽管同时也应该指出:相当多的案件是以做出有利于被告国的判决而结束的。[14]这无疑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现象。遗憾的是,法院作用的更大发挥仍然受到一些因素的限制。其一是,大量其他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的存在。这已经而且必将继续限制法院作用的发挥。其二是,大量地区性的专业性的争端解决机构的出现。这也限制了法院的作用。其三是,法院自身在资金、人员方面也存在一些限制。
第三个令人鼓舞的事实是,法院的司法实践已经表明,它在解决诸如边境争端、国民待遇争端之类的特定争端方面非常有效。不断增多的环境争端也为设立了环境分庭的国际法院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机会。
综上所述,“对于国际司法而言,当前既非最好的时期,也非最坏的时期;既非光明的季节,也非黑暗的时分,而毋宁说是黎明前的曙光。”[15]正如国际法院自身所言,国际法院的未来取决于各国求助于法院的程度。因此,单纯讨论国际法院应不应该有及应该有多大的作用是没有意义的。增强各国对国际法院的信心和信任才是根本。[16]信心和信任无疑来自于强化法院公正公平形象的实践。换而言之,给予国际法院更多机会,更多表现其公正的机会才是加强法院作用最为基础和关键的事。因此,首先应该给国际法院提供与其职能相对称的人力物力资源;其次,不妨试着确定一系列可就其达成将有关争端递交国际法院的共识的主题。对咨询管辖权而言,情形尤为如此。当然,必须牢记,作为一种阶段性的措施,在此过程中,必须注意避免过度政治化的问题。
注释:
①数据资料由作者整理自国际法院官方网站:http://www.icj-cij.com.
②在其存在的60年间,法院共发表24项咨询意见,平均每年0.4项。其中,1985年以前共发表17项,平均每年0.425项。
③数据资料由作者整理自国际法院官方网站:http://www.icj-cij.com.
④在其存在的60年间,法院共发表24项咨询意见,平均每年0.4项。其中,1985年以前共发表17项,平均每年0.425项。
⑤在有些案件中,原告国家同时以任择条款和仲裁条款为由提起诉讼。本文作者在进行统计时,将同时以任择条款和仲裁条款为由提起的诉讼既视为以任择条款为由提起的诉讼,也视为以仲裁条款为由提起的诉讼。
⑥资料由本文作者整理自马克斯·普郎比较公法及国际法研究所.国际公法百科全书·国际法院、国际法庭和国际仲裁的案例[M].陈致中,李斐南,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1-571.
⑦资料由本文作者整理自马克斯·普郎比较公法及国际法研究所.国际公法百科全书·国际法院、国际法庭和国际仲裁的案例[M].陈致中,李斐南,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1-571.
标签:国际法论文; 法律论文;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论文; 法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