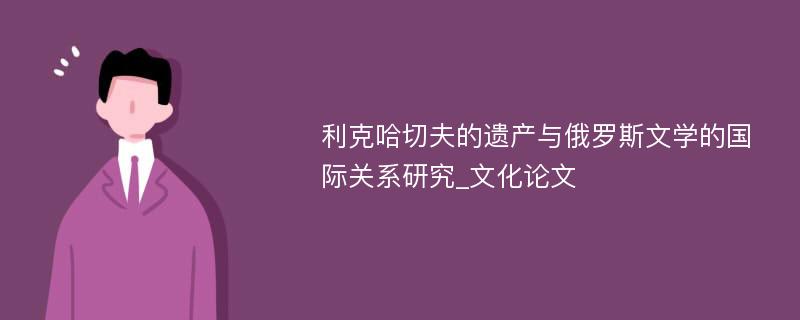
利哈乔夫的遗产及俄罗斯文学的国际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国际关系论文,遗产论文,文学论文,利哈乔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丛刊《前夜》第一辑《俄罗斯乌托邦》的序言中,利哈乔夫以他特有的隐喻方式写道,我们完全依赖于我们的一生都密封在内的神话和陈规俗套:“我们靠神话生活。神话不仅萦绕着历史,也萦绕着我们的个人回忆。我们的亲人和熟人,我们的城镇和乡村都被密封在神话之中。国家热衷于神话,急切地想奔向未来,既与神话斗争,又在某处拥有着神话。我敢断言,在其举止及其某些行为中一个人首先注意到的就是神话。神话超出了我们关于真伪的概念。”[1](9) 这里举一个神话的例子,我们的一些概念就“密封”在内。许多人都确信,利哈乔夫论述的仅仅是俄罗斯文化且只对此感兴趣。其实并不是这样,也不可能是这样。他出生在欧洲的首都之一彼得堡。在大学,他选择的是罗曼—日耳曼语方向,后来他从事研究已开始用教会斯拉夫—俄语。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撰写了两篇学位论文:一篇是有关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俄罗斯的莎士比亚研究,另外一篇研究大牧首尼康。大学期间利哈乔夫的恩师之一是B.M.日尔蒙斯基,20世纪最大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回忆道:“B.M.日尔蒙斯基开设的18世纪初英国诗歌研讨课是真正理解诗歌的一所学校。我们和他一起阅读雪莱、济慈、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的诗歌,分析其风格和内容。”[2]第1卷(118)因此,毫不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后来利哈乔夫在研究拜占庭帝国、斯堪的纳维亚和南部斯拉夫人对俄罗斯的作用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一生都在思考俄罗斯文化在世界语境中的地位。 利哈乔夫始终坚信,只有在交往、相互丰富和交流中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才有保证。他声称:“文学存在着,相互影响,文学相互影响的形式是其结构的一部分:即是文学进入其中的那种结构,以及文学在自身内部发展的结构。”[3](16) 正如我们所知,中世纪和近代文学专家们工作很少密切接触。与利哈乔夫的古俄罗斯文学研究有联系的一些论据、论题、结论和概括,无疑具有普遍的意义,使人以新的方式审视18-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我仅提及其中的某些部分。 在思考俄罗斯—拜占庭文学关系的规律性时,利哈乔夫明确地说出了对于理解文化间联系几乎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现在我们强调文化的这些内在需求的一个特点:与移植文化的一些个别因素,其罕见表现相比,在文化的整体移植中这些需求的显露更为强烈,更为明确。编撰文献的任何一部手稿、任何一部翻译、改写,以及历史和自然学的著作汇编可能是由偶然原因造成的:某个人的来访、修道院的个别需求、定制人的个体倾向,但在重复的、相互联系的大众性质的现象中,总是显露出普遍的需求、社会的需求,而不是个别人的需求,是规律的需求,而不是‘神赐’,是必要性的需求,而不是自由。”[3](20) 利哈乔夫总是赋予文化间的联系以巨大的意义,号召在其发展的动态中研究它们。他关注的是,既然11-13世纪古代罗斯广泛的文化共同性保障了其文化的高水平,那么在后来,这一水平得以保持首先是因为发展道路本身并未缩小,尽管文化间的联系的强度减弱了。与此同时,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以罕见的一贯性继续坚持认为,只有欧洲发展道路的共同性在随后所有的时代依然有积极作用。他声称:“东方对俄罗斯政治生活形式的影响,超出了精神文化的范围,是与文化敌对的”。[4](317)在这里利哈乔夫说出了对于比较研究极具前景的思想,以自己的方式发展了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的“汇流”理论。它的本质可归结为,深刻和富有成效的创造性的消化接受只有自愿选择才有可能,而暴力不会产生文化。既然与鞑靼-蒙古“共同生活”是迫不得已,那么,罗斯对于自己的奴役者来说就仍然是沉没的基捷日①,相反,“东方的”影响(特别是东方史诗),在鞑靼-蒙古征服前后(还有实用艺术、建筑、文字)还是相当强大的。 各民族的中世纪文本研究对于文本学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在利哈乔夫的《文本学》一书中有专门的章节——“翻译作品文本研究的特点”。我要强调的是,在这里利哈乔夫的结论是包罗万象的,即在最高的程度上,不仅对于相邻的文化,而且对相邻的时代的研究者而言是大有前景的。仅举一个概括性的论题:“总之,古代斯拉夫人的翻译——并非唯一的活动。翻译作品的生命与原作一样长久,不过,它更为复杂,因为,其中除了文本通常的生命,起着特殊作用的是与另一种语言文本,即翻译的源文本的相互关系。”[5](436) 利哈乔夫为研究文化中介现象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一现象是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关系研究中的中心问题,同时也是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利哈乔夫建议在超国家的文献中推广这一术语,这些文献以中世纪的神圣-学术的语言,即:拉丁语、教会斯拉夫语、阿拉伯语、梵文存在。他令人信服地证明,对于南部和东部斯拉夫人来说,古代保加利亚文献构成了这个伟大的统一的超国家的文献-中介的基础。 利哈乔夫在自己的一系列著述里证实了诸如“翻译”、“影响”、“吸收”这样一些术语,在研究拜占庭对古代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时的不足之处。他提出“移植”这个术语,坚持认为这里说的是“移植”的规模,伴随着重新审视和创造性地掌握“移植”的文化现象,实际上,利哈乔夫认为自己有权恢复“translatio”这个术语素有的本义,即同时具有“翻译”和“移植”的意义。他指出:“上述的一切使拜占庭文化影响现象的范畴得以突出,在文化影响中我们应当看到的不是‘影响’的表现,而是将拜占庭文化移植到斯拉夫土壤上的表现。文献移植,移栽、移植到新的土壤,在这里,在新的条件下,有时是以新的形式继续独立生活,就如同被移植的植物开始在新的环境中生活和成长。”[3](21-22)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多年来不断回到有关俄罗斯前文艺复兴的概念上来。在《十至十七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1973年)一书中这一概念得到最为详细的论述。令人好奇的是,正是在自己的这一理论中利哈乔夫从来没有特别坚持,就好像最初就同意了对手的论据。不但如此,他是一个真正的和杰出的辩论家,说实在的,他断言,俄罗斯没有过文艺复兴,也不可能有,他思考了那些可以解释为“前文艺复兴”的特点,并将怀疑论者和潜在对手的论据引入自己的文本中。因此,他发展了关于“自己的古希腊罗马”,即古俄罗斯文化的前蒙古繁荣时期的说法,古俄罗斯文化具有与14-15世纪的文化同样的基督教基础。利哈乔夫断言,“与此同时,另一种性质,另一种类型的异域文化总是具有最大的富有成效的意义。正是这个“他者”文化,两种不同文化的相遇具有最大的“遗传的能力。”[6](322)理论是在Н.И.康拉德的直接影响下得以深入研究的,在这种情况下利哈乔夫总是非常谨慎地使用术语、论证自己的观点,坚持的仅仅是提出有关“前文艺复兴”的特点问题的可能,即仅仅是关于现象的类似和征兆,这一现象由于历史条件不会过渡到文艺复兴。与此同时,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并非偶然地指出14-15世纪俄罗斯文化生活的特点与西方欧洲哥特式之间明显的相似:“俄罗斯的前文艺复兴——即晚期哥特式遥远的类似现象。”[3](123)在我看来,实际上利哈乔夫论证的并非“前文艺复兴”的独特性,而是俄罗斯文化里晚期中世纪的独特性。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意利哈乔夫很久以前的对手А.Х.戈尔冯克利的看法。他在最近一次利哈乔夫研讨会上发言时发挥了自己的观点。 然而,利哈乔夫的著述中提出关于俄罗斯前文艺复兴的问题本身,早在1940年代在最高的程度上就是非常及时和富有成效的。从一方面来说,利哈乔夫的概念在关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问题上对评价方法提出批驳,从另一方面来说,它鲜明地肯定了关于“自己的古希腊罗马”论题,令人以新的方式看待文化遗产的作用。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基于自己关于俄罗斯前文艺复兴的看法,利哈乔夫形成了俄罗斯的巴洛克的原创性概念,在他看来,在俄罗斯它不得不承担某些尚未展开的文艺复兴的功能,在许多方面具有启蒙的、“文艺复兴”的性质。 最后,这也许不是利哈乔夫所提出的许多理论中最无可争议的理论,它证明了俄罗斯与世界的文化进程,尤其是与欧洲的文化进程的不可分离性,与此同时,它还在共同的语境下明显地展现了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在这方面,利哈乔夫已经做出了很多研究。只要回忆一下他关于“时代风格”,即伟大的风格的论点就足矣。这些伟大的风格至少对基督教文明是共同的,包括在不同国家得以表现的文学和各种形式的艺术。例如,“源于古罗马文化的”和“宏大”的风格(利哈乔夫坚持这个术语),对11-13世纪整个欧洲而言是共同的。 众所周知,对于利哈乔夫来说,关于文化最多样化的表现的科学总是与保护文化古迹的活动不可分离的。他不仅在自己最著名的著作之一——《花园的诗歌》里论证了不同民族关于造园艺术的概念的相互依存性和相互制约性,而且设法挽救一些濒临灭绝的公园,并在蒙列诺公园发起成立了俄罗斯唯一一座岩石景观公园自然保护区。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对于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而言,这个公园是俄罗斯、芬兰和西欧的公园之综合的最高体现,所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是不同民族关于美的概念之综合。 从另一方面来看,他认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并依靠自己的文化领域的知识,包括园林艺术的知识,对民族性格加以了思考。例如,在《关于日本的第一印象》的特写中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写道:“俄罗斯庄园园林美学的任务之一是在散步者面前揭示多样化的远景,‘目光引向远方’。”日本的花园,虽然本身大,但‘对自己更大’,将目光锁在细节上,借助于多样性创造了巨大感。”[2]第2卷(353)正是这样,利哈乔夫认为,俄罗斯人和日本人对宗教地领悟世界有不同的表达:俄罗斯人力求在快速的运动中拥抱整个世界,而日本人能够在点滴中看到宇宙。俄罗斯人这种在文化中对世界的宗教态度体现为力求创造巨大的假说、新的悖论,而日本人——注重任何一个细节,在一切方面都强调准确。 在最后几十年的生活中,利哈乔夫越来越经常地关注20世纪的文化,号召研究俄罗斯侨民的遗产,因为它不仅是俄罗斯文化现象,相反,在侨民们不仅成功地适应异族的文化环境,而且作为桥梁,作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的媒介之时,它是西欧文化现象。 利哈乔夫在争论、撰文、作报告和接受采访时,以罕见的顽强一再说:“俄罗斯是欧洲国家。”在血缘上和信仰上都是欧洲国家。在《罗斯受洗和罗斯国家》中利哈乔夫写道:“我简要地说,弗拉基米尔从拜占庭对基督教的接受使俄罗斯脱离了伊斯兰和多神教的亚洲,使罗斯与基督教的欧洲接近起来。这个好还是不好——还是让读者去评判吧。”[2]第2卷(104)与此同时,只要我们很久以前,早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前就在欧洲,目前也在欧洲,他就提出“打开通向古代罗斯的窗口”。 利哈乔夫在《欧洲文化的三大基础和俄罗斯历史经验》一文里尤为详细地论证了自己关于俄罗斯无条件地属于欧洲的概念。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在这里证明了俄罗斯文化完全属于欧洲文化,因为具有基督教根源,这两种文化都具有三个基本的和相互依存的特点:它们都是个性的文化,都易于理解其他文化,因此——是包罗万象的。最后,欧洲文化和俄罗斯文化都基于个性的创造性的自我表达的自由。因此,利哈乔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指出的“全人类性”,正是俄罗斯人的一个显著特点,它是整体上的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共同基础,正是这样,在最高的程度上,它是俄罗斯文化素有的,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利哈乔夫在与欧洲人争论时,曾多次声称“俄罗斯从来不是东方”。他那戏谑的《宇宙科学院院士的“传记”》已保存在他的文献档案里,其中可以找到他不信任“东方”的悖论解释:“日本战争赋予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一双些许斜视的眼睛/……/,同样也使他有了些许不信任东方的态度。”[2]第1卷(378) 利哈乔夫证明了俄罗斯属于斯堪的纳维亚拜占庭,而不是欧亚大陆,“北—南”轴心对于俄罗斯远比“东—西”轴心更为重要。 利哈乔夫去世并无多年,但历史已经表明,他是正确的,他坚持认为,对俄罗斯和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文明来说,南北之间的对峙的意义,至少不比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对峙的意义逊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无重要的是,他确认并坚持认为俄罗斯具有特殊的禀赋,准备综合和统一这些因素。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和杰出的思想家(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不仅仅只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不必始终如一。例如,在《作为首都的古诺夫哥罗德——圣彼得堡的前身》一文中,可以找到令人惊叹的关于“停靠”在欧洲边上的俄罗斯的一节。利哈乔夫仿佛在与自己辩论,肯定俄罗斯的欧洲实质,他写道:“彼得堡建立的河口就处在海洋和河流的边界上/……/在这里,在靠海的边界上俄罗斯仿佛与欧洲亲密交往,停靠在欧洲边上,创立了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在本质上既不是欧洲,也不是“莫斯科公国”。在这里,俄罗斯“停靠”在欧洲边上后,没有变成欧洲,而且也没有变成“莫斯科公国”。[2]第2卷(129)很难同意那种认为利哈乔夫没有意识到“边界因素”的观点,如果不是在“东方”和“西方”之间,那么无论如何也是在“北方”和“南方”之间,俄罗斯的位置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例如,由于这个原因,它的文化,与“非边境”民族的文化相比,是不可避免的同时既更为“封闭”,又更为“开放”。我认为作为学者和作为艺术家的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对欧亚主义的学说的个别论题给予了应有的评价,但是,显然,作为一个公民,他对欧亚主义理念持不信任态度,认为这些理念对于今天的俄罗斯是危险的,认为减轻其对头脑的影响是他的责任。 利哈乔夫确信,与坚信当代西方文明,同时为自己所有惊人的古老仪式和习俗而感到骄傲的日本类似,俄罗斯必须学会珍爱地保存在其数世纪的历史、信仰、文化和民族性格里形成的一切。作为一个真正的俄罗斯欧洲人,利哈乔夫认为,所幸的是,现在重新意识到自己是欧洲国家,这是返回源头,因为正是它们才既对我们又对其他民族具有不容置疑的价值。 作为对我所提议1994年在普希金之家举行的“东方与西方之间的边境文化:俄罗斯和西班牙”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回应,利哈乔夫所作报告的题目是《文化间的两类边界》,他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关于文化中的“边界”同时具有既分离又统一的意义的论题。利哈乔夫关于文化中边界现象的作用的思考意义巨大。 利哈乔夫总是向对话开放:在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自由主义者与根基派之间、老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过去与未来之间、俄罗斯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进行开放性的对话。毫无疑问,他赋予文化对话以巨大的意义,正是因为他本人总是专注于对话。 在20世纪,唯有利哈乔夫,如我试图展示的,是一位能够在其发展的全部时期,在广泛的世界语境下研究俄罗斯文学,部分地还有俄罗斯民间创作,更为广泛地还有俄罗斯文化,包括绘画和建筑的人。除此之外,在我看来,利哈乔夫还成功地创建了自己的比较文艺学学派,世界语境中的古代俄罗斯文学是其主要的研究对象。与В.М.日尔蒙斯基、Н.И.康拉德、М.П.阿列克谢耶夫学派一样,他的学派有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研究对象、自己的成就,不过,重要的是,有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毫无疑问,这一学派有自己的未来。 ①据神话记载,吉捷日曾依靠祷告而在鞑靼人入侵时获救。有一种说法,它升上了天,而且倒映在入侵之敌葬身的那片湖里;还有一种说法,就像神话中颂扬过的许多城市那样,它被湖水吞没,至今清澈的湖面上古城中的一座座塔楼仍依稀可见。——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