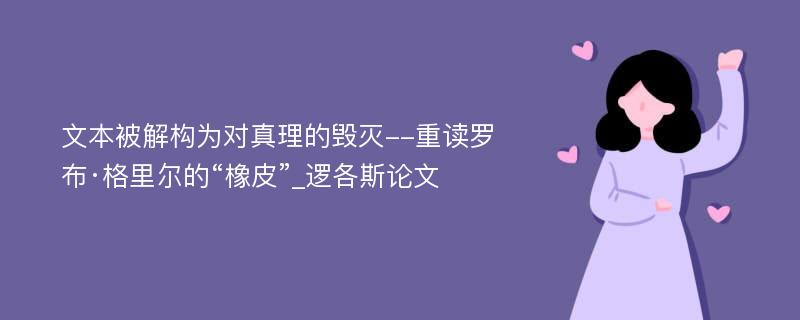
文本在真相的漫灭中解构——重读罗伯-格里耶的《橡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里论文,橡皮论文,真相论文,罗伯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08)03—0061—07
《橡皮》是罗伯-格里耶于1953年发表的处女作。在样书的赠言中,他是这样描述这本书的:“本书涉及一个明确、具体而重要的事件:一个男人的死。这是一个具有侦探性质的事件,就是说有一个凶手、一个侦探、一个受害者,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此简单,因为本书是讲述一个发生于24小时之内的、枪击与死亡之间的故事。”而小说的情节乍一看,似乎也确实如这描述一样引人入胜。一个恐怖组织,正在有计划地刺杀一个对于全国经济和政治都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集团的成员。他们已经成功地杀死了了八个重要人物,都是在晚上七点半钟下手,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一位和内政部长有着密切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杜邦。在杜邦遇刺的消息传出后,一位据说是受内政部长委派的青年侦探瓦拉斯来到了杜邦所在的这个外省小镇,对刺杀事件进行调查。在经过了一天的调查后,瓦拉斯得知大商人马尔萨本来应当在晚上七点多时到杜邦的书房取一份重要文件,但现在却因为害怕临阵脱逃了,便在当晚七点钟来到杜邦的书房查看,同时也想伏击可能会来刺杀本应到来的马尔萨并夺取文件的凶手。不料,杜邦之前根本没有被刺死,而是在遇袭后诈死,由于马尔萨的临阵退缩,他只好自己来取文件,却被埋伏的瓦尔萨当作杀手,在晚上七点半钟时遭误杀身死。
以往人们对于《橡皮》的解读,主要有这样两种主要的着眼点:一种是结合罗伯-格里耶“新小说”的主张,探讨这篇小说所体现的物本观、物本主义;一种是将这篇小说作为罗兰·巴特“零度写作”的一种典范进行探讨,而罗兰·巴特自己也确实曾将格里耶视为“零度写作”的理想代表。但大家却往往没有对格里耶为什么要采用这样一种类似侦探小说的写作方式进行更深一层的探讨,并留意到小说中那个不同于传统侦探小说的被消解“真相”本身就蕴含着格里耶在小说写作方面的思想主张。本文就准备从这被消解的真相入手,对《橡皮》进行一种新的解读。
一 真相·深度·逻各斯
在《橡皮》当中,政治集团、神秘组织、杀手、年轻的侦探,一应俱全,几乎具备了一部惊险刺激的侦探小说的必要元素。读者也就很自然地会期待在经历一番跌宕起伏之后,由侦探揭示出那些隐藏在重重迷雾之后的黑幕、谎言等一切可以通称为真相的东西。
然而,随着情节的展开,读者恐怕要大失所望了,因为整个故事的发展并没有依照典型侦探小说的模式进行。首先是暗杀杜邦的行动根本就没有成功,这就使“探究真相”丧失了最基本的契机——死亡;其次是作为主人公的侦探瓦拉斯,他虽然也在不停地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追踪一切可能的线索,可他的追查行动却总是带给人一种心不在焉、不得要领的感觉,他不断购买橡皮随后又丢掉,和素不相识的路人说着不着边际的话……最重要的是,他的种种活动不仅没有揭露出暗杀活动背后可能隐藏的政治黑幕,反而还在最后误杀了原本已逃过一劫的杜邦,完成了杀手没有完成的使命,从而使得整个事件变得愈发扑朔迷离、难以捉摸;最后,不愿作任何调查、说话总是颠三倒四的警察局长罗伦,反而在最后发现了杜邦诈死的事实,这又对传统的真相揭示模式构成了极大的反讽。
格里耶的其它小说也大都如此,空有一副侦探小说的叙事框架,却留给读者一个不知所云的结局,如《窥视者》《纽约革命计划》《德冉》等。所谓真相,在他的小说中永远都是模糊不清的。格里耶为什么如此偏爱侦探小说的叙事模式,却又总是吝于为读者提供真相呢?这与其取消文学创作中“深度”的主张是密不可分的。在他看来,传统文学创作中“种种文化的外围(心理学、伦理学、形而上学等)自行强加于文本、事物……使它们更可理解、更迎合人心”[1]62。而这些自行强加于文本和事物的正是把人当作世界的中心认为只有人才能作为解释万物尺度的传统人道主义观念。在这种观念背景下,传统文学中才会一直为一种关于“深度”的古老神话所统治,而基于这个神话,作家的作用就在于一层层地挖掘到最隐蔽的底层,用深度的罗网捕获世界,再将其按照自己的价值观书写后交给读者。
相对于这种传统的文学创作,格里耶所倡导的“未来小说”就是要粉碎这个关于深度的神话。“制造出一个更实体、更直观的世界……让事物首先以它们的存在去发生作用,让它们的存在驾临于企图把它们归于任何体系的理论阐述之上”[1]63。因此,他的小说拒绝屈从于一切道德或意识形态目的,也不再打算以文明或人类境况的荒谬性诱饵来唤醒读者的良知。
如果将侦探小说中的“真相”,与他所说的“深度”作一下对比,就不难发现,侦探小说正是包含于传统文学创作之内,又极好地折射着深度写作诸多特征以及创作实质的一种文学体裁。
《橡皮》的故事如果按照典型侦探小说模式写作,瓦拉斯破案的过程就应当是一个寻找真相的过程,而故事推进中出现的所有人物、事件等都应无一例外地是服务于真相最终的揭示,正如传统文学创作中一切都服务于挖掘、展示深度一样。如果是在典型侦探小说中,这部小说最后所揭露出的真相多半是惊天的政治阴谋,或是某些不为人知的仇怨,侦探则通常会在结尾时进行一系列推理,然后踌躇满志地向人们揭示出那些可能的隐秘,而当读者读到这里时,也往往都会感到一种豁然开朗的莫名激动,以及获知真情的巨大愉悦。与此相类,格里耶对于发掘、展示深度行为的描绘正是“把一种令人不安的秘密公诸于世,深入人类激情的深渊,向仿佛是平静的世界发出胜利的消息,描写他亲手触摸到的秘密。于是,读者感到一阵神圣的眩晕,然而这非但不会使他痛苦或反胃,倒反而肯定了他对于世界的统治力量”[1]65。
通过这种对比可以看出,无论是真相之于侦探小说,还是传统人道主义观念之于传统文学创作,实际上都处于一个逻各斯中心的位置。正如德里达所总结的那样,这种写作实际上就是在履行从柏拉图开始就给书写限定的职责:对于逻各斯中心的书写。从而,书写行为本身已变成了一种对写在心灵上的符号的听写,字词的语音或语义的多义功能、个性化和创新都受到极大的限制,一切都要指向那个被视为源头的、唯一确定的逻各斯。因此,实际在传统写作中,全世界只有“一本书”:解释逻各斯的书。深度的挖掘、价值观念的体现无一不是在呈现、解释着那个逻各斯。
同样,真相对于侦探小说中的一切来说,既是起源,又是目的。无论是小说中的侦探还是小说外的读者,都只能在这个结构内根据不断探究或阅读得到的线索,寻至那个早已预先设定的、唯一确定的真相,而根本不可能得到其它。因而,全世界也只有一本侦探小说,那就是揭示逻各斯的影子——真相的侦探小说。
然而,格里耶的《橡皮》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文本不是走向真相的揭露,而是不断趋于漫灭,用支离破碎的线索、相互矛盾的证词、性格模糊的人物不遗余力地消解对应着真相的深度,从而粉碎传统文学创作中的深度神话,进而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以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为思想视角,对《橡皮》进行重读。
二 橡皮·延异
作为小说题目,同时也是文本中反复出现的重要意象,“橡皮”在文本中担当着双重的功能作用。
第一重作用体现在对橡皮的寻找过程上。小说中三次出现主人公瓦拉斯购买橡皮的行为,可每当他买下橡皮时,就会马上意识到这块橡皮并非自己所寻找的,而他对所要寻找的橡皮是这样描述的:“这种橡皮既轻又柔软,脆而易碎,用力压下不会变形,只会变成粉末。这种橡皮不费劲就可以切开,而且剖面光亮平滑,像螺蛳壳一样……这块橡皮的样子是黄色的、立方形的,边上二三厘米厚,角上微呈圆形——也许是磨损了。”[2]136 在现实中显然是不存在这种橡皮的。直到小说的结尾,瓦拉斯也没有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这种橡皮。小说始终没有交待他为何要买这种橡皮,可这显然又不是为了增加荒诞感的闲笔,而更应当是一种功能性的暗示。实际上,这个反复购买橡皮却又每次都不是所需的过程本身,就是在暗示试图从小说中发现唯一确定的真相是几乎不可能的,寻找真相的过程注定要和寻找橡皮一样徒劳无功。
第二重作用体现在橡皮本身的物理功能,以及这种功能在小说中的衍生作用上。现实中橡皮的作用在于涂抹文字、符号并替代以新的书写,可同时又不可避免地留下痕迹。在整个文本中,橡皮的意象反复出现,同时,和涂抹这一功能相关的字词(如污迹、腐烂、模糊、覆盖等)也不时浮现。这对于侦探和读者理清线索、寻找真相都形成了一种阻碍——每当侦探和读者自认为找到了某些有助于揭密的蛛丝马迹时,橡皮就会出现,对线索加以涂抹。这样,橡皮就像一个指示器,在书写的过程中自动地抹去了传统侦探小说所虚构出的连贯性,使读者不能通过逻辑的方式进行思考、推演,真相的揭示也就因而被无限期地推延了。
橡皮在小说中的这两重作用,都与德里达的“延异”(différance)形成了惊人的吻合。从词义上讲,延异同时包括两层含义:空间的差异性和时间的推延性。空间的差异性是指同一性的分裂和同时性的破坏,而时间的推延性则表明一切都是处在暂时存在、不断延迟之中。延异是德里达用新的文字书写割断与话语的联系,切除与逻各斯意指关系这一主张的最主要策略。在德里达看来,文字中没有等级,只有各式各样的能指组合,它只有差异、运动、分延和延搁的作用。而德里达提倡书写的目的,也正在于要用文字的差异性来提倡开放性、边缘性和多义性,以此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带来的封闭性、明晰性和唯一性。
在《橡皮》中,反复购买橡皮却又每次都不是所需,寻找真相却一直茫然无所得的过程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延异。而橡皮(eraser)涂抹的物理功能及其在文中打破连贯性、整一性的作用更是与延异的衍生关键词涂抹(erase)、痕迹(trace)、增补(supplement)不谋而合。在德里达的阐释中,延异包含着一种对在场不断进行自我涂抹的含义,每当意义的呈现趋于所谓的完满之前,就会进行这种涂抹,从而避免成为一种完满的在场与僵化的实体,而每一次涂抹之后,又会在上面用新的书写加以覆盖、增补,并在同时留下逝去符号的痕迹。
德里达认为,在延异的作用下,文本没有整体、中心而只有碎屑。与此相应,在创作《橡皮》时,格里耶也曾表示:“我想讲述一个逐渐自我破碎的故事。”[3] 所以,在小说中,充满了闪回、假想、幻觉、意识流以及时空倒错,使得整个故事显得支离破碎。同时,整部小说的书写更是在延异式的不断自我否定中进行的,无论是在人物的内心活动还是故事情节的进展中。最明显的就是在行文中不断出现“不”“不对”等词。如在瓦拉斯第一次购买橡皮时,一开始描绘说售货员是个年轻姑娘,但马上又说:“不,她不是一个小姑娘……看起来几乎是一个少妇了。”[2]63-64 另外也有不少不明显出现否定词的自我否定,例如杀手格利纳蒂走上杜邦家楼梯准备埋伏时,楼梯是二十一级;刺杀失败逃走时,楼梯却成了二十二级(二十二是塔罗牌的主牌大阿卡那牌的数目,而楼梯墙壁上那幅波那没有向格利纳蒂提及的油画正是主牌中的第十六号牌“落雷之塔”,代表着“情景逆转、意想不到的转变”的含义)。同时,在人物的心理活动中,也存在着这种不断涂抹、否定、修改,比如瓦拉斯一开始时感觉自己儿时似乎来过这个小镇;之后又回忆起是与母亲一起来这个小镇的,似乎是为了遗产的问题探望一位女亲戚;可最后又否定了这一回忆,想起探望的并非女性,而是一个男人,且正是自己的父亲。
就这样,在橡皮延异的作用下,小说空间、逻辑上的同一性、连续性都遭到了难以修复的破坏,侦探小说所要最终揭露的真相由此漫灭不清,真相所映射着的逻各斯也随之被解构得难以存续了。
尽管延异的提出是在1968年,而格里耶的《橡皮》诞生于远早于此的1953年,可“橡皮”这一意象体现出的与延异异曲同工的理念,甚至在文学实践中体现出形象化的说服力也反过来证明了延异并非德里达个人某种异想天开的发明,而是完全符合人类思想发展的某种必然。
除去橡皮的意象,小说还有一点可以从延异的观念进行解读,那就是整个故事都是在时间的推延中进行的。瓦拉斯的表在前一天晚上七点半钟停止走动,杜邦家的黄钟也在前一晚的几乎同一时刻停了下来,而这正是格利纳蒂刺杀杜邦失败的时间。表的停止似乎就像是时间的停止、推延,一直到同样的晚七点半,指针转动一周,又回到起点,瓦拉斯将杜邦“误杀”掉。接下来的一切就如同第一次刺杀如果成功会发生的一样,时间停顿的这24小时里,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同时,时间的这种处理也改变了以往传统小说的单线程时间线索,阻止了因果连贯的结构,有助于文本有效地脱离封闭式的结构,从而使时间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想象的维度,使人能够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组合他所感知的现实的“碎片”[4]73。就像格里耶自己所说的,“只有摧毁那将时间分开的时间,未来才能在时间中重新建构过去”[5]。
三 反复·空缺
小说中与橡皮涂抹功能密切相关的是格里耶作为写作手法的反复和空缺,它们也同样可以德里达的延异理论进行解读。
橡皮的涂抹,往往是为了对相同信息进行反复书写。而格里耶的反复在《橡皮》中,正是表现为相似主题、场景、处境的反复,比如瓦拉斯购买橡皮、杀手格利纳蒂和暗杀团伙头目波那的对话、警察局长罗伦对杜邦自杀情景的假想,都在小说中多次反复出现。
然而正如橡皮涂抹后绝不会重新写上与之前完全相同的内容一样,反复并非简单的重复出现,而是一种包含着差异的反复。如格利纳蒂与波那的对话,竟连续出现了三次反复,虽然同样都是前者向后者汇报任务失败,后者告诉他杜邦已死,可每次反复时在细节上都有着显著的差异。而且,小说中反复的方式也是不尽相同的,有时会出现明显的抵触和矛盾,比如瓦拉斯第一次买的橡皮明明已经落在了罗伦的办公桌上,可下午他再次买了一块橡皮时,却被说成是“跟早上买的那一块放在一起”[2]77。有时又会转入与以前的某些叙述片断有直接关系,但却与正在叙述的事物毫不相干的情景,如格利纳蒂与波那对话的最后一次反复,在谈论暗杀任务的时候,突然转入到对远处屋顶上两个人的揣测和描写上。反复在《橡皮》中所体现出的这种各式各样的差异性,在文本中以类比型的衔接取代了传统的逻辑型衔接,以相似性取代了因果性,从而迫使读者关注文本本身,并进行一种记忆和辨认的活动[4]108。如此一来,正如德里达所说:“一旦文本自我重复,其自我一致性就接纳了某种感觉不到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使我们有效地、严格地,也就是说隐秘地脱离那个封闭体。”[6]528
当然,小说中的这些反复的部分并非是任意的,它其实是符合文本本身的需要的能够在文本中产生作用的反复,否则就无法达到在差异中生成多义性和不确定性的目的。因而,《橡皮》中的反复并不是为了用多次书写补足叙述中的缺失,相反,反复正是用伴随着重叠、模糊而产生的差异消解着传统叙事中时空的整一性,从而破坏故事文本情节的逻辑连续和转换,迫使文本回到其自身,同时,挑战普遍体验中主体的权威,使主体逐渐失去对事态主动权及真相的把握,而主体、真相背后的逻各斯也就自然很难再统治整个文本了。
橡皮涂抹后如果不再对该信息重新书写,而是径直转入其它,就会在文本中形成空缺、省略。《橡皮》中很多情节都呈现为空缺,比如警察局长与诊断杜邦“死亡”的茹亚尔医生之前所谓的“合作”指什么?替暗杀团伙租用邮箱的究竟是不是医生?杜邦手枪中少的一发子弹到了哪里?
而空缺最多的还是与主人公瓦拉斯相关的关键情节:他与骑车人关于天气、勇气的奇怪谈话是否暗藏着玄机?波那究竟要格利纳蒂找到瓦拉斯干什么?瓦拉斯的手枪中为什么也少了一发子弹?瓦拉斯为什么可以收到J.B.(让·波那的简称)给准备杀死另外一个杜邦的凶手安德烈·VS(可能是瓦拉斯的简称)的信?邮局的职员和醉鬼为什么都把瓦拉斯当作第一次谋杀当晚曾在杜邦家附近出现的那个身穿雨衣的神秘人?这些最后都没有解答。而瓦拉斯当晚案发前是否就已经到达小镇,又在做些什么也都呈现为空缺,因为唯一可以证明他到达的确切时间的车票再也找不到了。甚至他的探员身份证上的照片,连他自己都认为不像自己,而其一切与侦探机构相关的叙述又都只是出现在他自己的心理活动及回忆中。因此,瓦拉斯的侦探身份也并不是确定无疑的。
除情节外,这种空缺、省略同样出现在小说中“书写”的行为中,如杜邦遇刺前在纸上写着的“无法避免……”就正是呈空缺状态的。类似的情况甚至同样出现在格里耶文论作品的结尾处:“人们对我说我进行的斗争本身也是一种特别的悲剧的幻想,因为,他们认为企图与悲剧观念进行斗争其实已经就是屈服于它;而我把物件拿来当作避难所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也许他们说对了……也许他们说的不对,因此,在这种情况下……”[7]
格里耶认为,文学作品一旦完整无缺变成某种实体就会成为失去生命力的一潭死水,而有“空缺”的文本才有可能使作品产生旺盛的活力。格里耶的这种空缺,与伊瑟尔的“空白”理论甚为相近。后者认为,空白用来表示存在于文本自始至终的系统之中的一种空位,它“粉碎了文本图式的可联结性,把被文本选择的规范和视野部分引到一个支离破碎、违反事实、对比的或者被压缩了的系列之中,使读者对于‘良好’‘绵延’的任何一种期望都失去意义”[8]。而出于对连贯的期望,读者如想得到一种文本意义就必须调动自己的想象力来填补这些空位。于是,空白实际上打开了一个便于读者进入的空间。而因为文本本身没有提供唯一正确的解读答案,读者的理解又一定是多种多样的,文本意义便由此生成了无限的可能性。比如小说中对于杜邦死因的空缺,瓦拉斯就可以理解为是政治连环谋杀案的一部分,警察局长就可以认为是自杀,而杜邦的女仆则一口咬定是茹亚尔医生害死了东家。而对于关于瓦拉斯的种种空缺,读者也完全可以通过大胆的猜想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最后杀死杜邦可能不是出于正当防卫的误杀,也完全有可能是作为暗杀团伙隐身杀手的他进行的一次掩饰得极好的谋杀,他就是要替格利纳蒂完成任务的人。
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当中有一篇名为Ellipse的文章,这个法语词正是同时具有反复和空缺这两种含义。在他看来,无论是反复还是空缺,其实都指向了对价值观念同一性理念的怀疑。任何语言、符号的意义都与其所处的语境相关,而反复使得符号可以无限次地被多种语境所引用,由此便可能不断地接受新的解释,这样原文语境的权威、不变的价值便就此失去了,根源性不再有据可依,价值的同一性自然也就无从谈起。而在空缺中,价值的同一性早已在空缺带来的未定性和多义性那里遭遇了瓦解,没有任何一种分析方法能宣称自身在文本阐释中是绝对的权威。
因而,与德里达一样,格里耶也试图通过反复和空缺的策略解构逻各斯中心,使文本、书写生成不确定性、多义性,只不过他不是提出理论,而是将反复和空缺实化为文学创作的具体手法而已。
四 对已有文本的再书写
也许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橡皮》的故事其实隐含着一个书写的源头及真相,并且还多次出现对于所书写源头的暗示。比如小说开头引用的索福克勒斯的名言,瓦拉斯曾与母亲来到这里探望自己父亲的回忆,小说中出现过的小孩子领着瞎子的雕刻,明信片上的希腊神庙,警方调查员关于杜邦曾有一个私生子的相关证词等,这些纷繁的线索串接起来都可以使人联想到这个源头。
而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暗示有两个:一是瓦拉斯走在那个迷宫般的环形大道上时,居然能够反复几次都注意到一幅窗帘,窗帘上面“画着两个穿着古装的牧童在树下捧着一个赤裸裸的小孩,让他在喝一只母羊的奶汁”[2]46。二是小说中那个仿佛看透一切的醉鬼反复让别人猜的谜语,虽然每次都没有完整地说完,但仍然可以辨认出那分明就是斯芬克司的谜语:是什么动物早上四条腿,中午两条腿,而晚上三条腿。这一切都在暗示着,小说所在书写的源头正是关于俄狄浦斯的希腊神话。尤其是到了瓦拉斯马上就快要误杀死杜邦时,醉鬼的谜语已变成了:什么动物早上杀父、中午淫母、晚上瞎掉眼睛。由此,小说似乎完全可以解释为是对俄狄浦斯这个本源性故事的一种再书写。
事实上,俄狄浦斯可以说正是侦探小说主人公的原型,他正是通过一系列锲而不舍的调查,最终发掘出那个杀父娶母的可怕真相的,而“凶手”也正是他自己。而格里耶做出的这些暗示,似乎确实可以令人得出这样的结论:瓦拉斯正是杜邦当年和那个身份寒微的女人的私生子,后来他和母亲一起被杜邦抛弃,而瓦拉斯误杀杜邦,正是在重演俄狄浦斯无意中弑父的悲剧,或者根本就是有意报当年的遗弃之恨的。
可如果能够得到一个确定的“真相”,岂非与格里耶的文学主张相悖?类似的,德里达也有一个似乎与其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态度相矛盾的提法:书写永远都是对已有文本的再书写,重复书写实际上就是对于书的源头的书写,也就是一种本源书写[6]527。
但这个让人可能会有所误解的“源头”,在德里达这里其实只是一个占据源头之位的东西,只是“延异”的一个环节而已,它也是一种痕迹,也不过是对其它文本的书写。更原始的是延异、增补,它没有起源,也不是自己的起源,它是对“起源”的悬隔过程。其实,如果能够从源头中读出一种源头来,从中心上读出一个中心来,反而正是无限重复的开始,因为这一主张恰恰体现出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个重要论据:源头、中心既然是整体的源头、中心,那么就应在整体之内;但源头如果还能读出源头,它便不属于整体,整体就应在别处有它的中心,这样便指向了一种他者。
所以,如果把“俄狄浦斯故事的再书写”当作是《橡皮》可以确定的所谓真相,同样是大谬不然的。根据很多人类学家的论证,俄狄浦斯的故事其实也正是对于人类文明、文化中某些更本源东西的再书写,小说由此也陷入了一个无穷悬隔起源的推延中。
而就在那些解读者自认为找到这个“惊人”真相的同时,橡皮又在发挥着它的作用了。之前警察局探员在报告中所写的,许多可以支撑瓦拉斯杀死的是自己父亲的暗示、线索——如看门人听到杜邦与年轻人的大声争吵,年轻人曾与一个陌生人在杜邦家附近激动地比划着威胁性的手势,咖啡店老板说店中来过一个年轻人很可能是杜邦的私生子等——都随着看门人和老板对这些证言的否定而又被重新涂改、再次呈现为不确定。
其实,对比俄狄浦斯和瓦拉斯行为的区别就可以看出那些导向真相和逻各斯的传统写作与《橡皮》的不同之处:前者的活动是揭发式的,是在揭露已发生过的事情(杀父娶母的真相),正如传统写作是要呈现早已预设在终点的逻各斯一样;而后者的行动是生产式的,产生过去没有的事情(杜邦本没有死,瓦拉斯的追查却最终导致其死亡),正如在橡皮延异的作用下,小说已因多义性和不确定性成为了罗兰·巴特式的“可写性文本”,读者的阅读习惯虽然被打破了,但解释能力却大受鼓舞。作品不再是要吸引人、使人放心、说服人或进行论证,而是使人产生焦虑,并且要给它开辟一个广阔的含义空间。所以,读者固然可以为得出瓦拉斯其实是暗藏的杀手、小说是现代版的俄狄浦斯一类的结论而充分地享受“文本的愉悦”“狂喜”,但却要在同时也明白:这永远都不能成为所谓的唯一正确的解读。因为,真相早已漫灭,真正的奥义永远都在延异中。
为什么我们总是想要从侦探小说中获取真相呢?为什么即使我们明明看到了《橡皮》的“反侦探小说”的特性,却还是试图揭示出一个弑父的真相呢?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在这种对真相的欲求背后,其实恰恰隐藏着其他的东西。杜邦的“死”将读者与小说中的瓦拉斯、罗伦、波那、格利纳蒂、茹亚尔等一干侦探和“嫌疑犯”网罗到了故事的中心。读者其实和这些嫌疑犯一样,在内心都有可能希望有人死去——从拉康的观点去分析侦探小说,读者正是要通过阅读来满足毁灭和杀戮的快感,但同时又必须通过侦探,从嫌犯中找出一个凶手,承担其他所有嫌犯和读者的负罪感[9]。这个凶手不过是我们所有人的替罪羊,正如俄狄浦斯也是用来承担所有饱受瘟疫之苦的忒拜人罪过的替罪羊一样。这样一来,我们满足了内心的欲望和快感,又不需要为此负责任,最后还可以拥有获悉一切的全知全能的力量感。所以究竟是谁杀死了杜邦其实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杀死他的人。从这个角度看,这样的“真相”不过是一个永远等待我们根据需要去填补的空位,是我们用来证明自己的认知和掌控世界能力的手段,从而在根本上是一个我们用以罗织自己内心欲望的幻象。而在《橡皮》中,格里耶对于真相的消解,恰恰是在揭露传统侦探小说中“真相”的这种幻象实质,这便使得所有试图从《橡皮》当中获取一个唯一的真相以及其背后隐喻的“深度”和“逻各斯”的行为变得更加可笑。
也许《橡皮》的这种文学创作思路,对于那些一路跪拜,诚心在文学写作及阅读中求索真理、真相的人们来说未免有些残酷。然而,正如同样喜欢用侦探小说模式来消解唯一性的著名意大利学者艾柯在其《玫瑰的名字》中所说的那样:“那些深爱人类的人所肩负的责任,应当是使人们嘲笑真理,使真理变得可笑,因为唯一的真理应在于:学会让我们自己从对真理的狂热之中解脱出来。”[10] 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固守一种封闭的单一思路,在文学的写作和阅读中,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意义,这大概才是罗伯-格里耶们由衷希望见到的事情。
[收稿日期]2008—0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