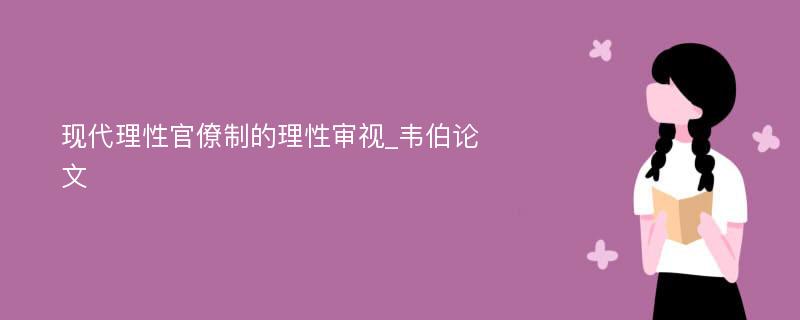
现代理性官僚制的理性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官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化生产方式和法治条件下的社会治理的行政管理体制,理性官僚制自滥觞以来受到了普遍的推崇,成为现代社会经典性和普适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公共管理实践的兴起,这一管理体制在后工业化时代的合理性却受到了广泛的质疑,甚至成为一些人心目中落后和低效率管理模式的代名词。理性官僚制究竟是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成为一种即将被抛弃的管理模式,还是依然具有其现实的合理性?现代社会人们所感受到的公共领域的诸多问题究竟是官僚制的必然产物还是另有其根源?中国行政管理是否有可能超越理性官僚制而直接进入所谓的“后官僚制”行政?这些问题对于正致力于探索适应市场化进程的有效管理体制的中国行政管理,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理性官僚制的历史合理性
现代理性官僚制是一种依照职能和职位对权威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层级制为组织形式,以世俗化、专业化的职业官僚为管理主体,以理性设置的制度规范为运作规则的管理模式。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兴起的理性官僚制与传统的官僚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与现代社会特殊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其一,理性官僚制从法理型权威中获得其合法性的依据,因而它不是一种特权统治。宪政体制对政府职能、权限的厘定,以及民主政治对行政事务的控制,既规定了理性官僚制运作的空间和规则,也赋予了它运作的合法性依据。其二,形式主义的法治秩序规定了理性官僚制运作的抽象性原则。离开普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法律传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其三,市场化、社会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理性官僚制的诞生提供了重要动力。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日趋复杂,社会流动日益增强,需要由政府承担的公共事务的急剧增多,传统的那种因人而异的管理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只有依照形式主义制度规范运作的理性官僚制才能适应公共事务的批量化处理,也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官僚才能有效地承担现代社会复杂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与此同时,也正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才能把官僚作为一种世俗的职业,并以货币薪酬来雇佣职业官僚从事公共行政事务管理。其四,社会结构变迁,特别是从身分到契约的变革,打破了身分、职业的世袭传统,以及人身依附格局,催生出了现代社会以自由契约为基础的具有独立人格的职业官僚。
理性官僚制本质是一种追求形式合理性的管理体制。在这种管理体制中,行为主体的行动受形式化、非人格化,贯穿着理性精神的组织程序和行为规范的支配,体现出一种特殊的“官僚制精神”。所谓“官僚制精神”,实质上就是一种理性精神。这里的理性精神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如规范官僚行为的法律法规、组织程序及契约等等是事先基于效率和形式公正原则合理地制订的;整个官僚体制具有严整的结构和内在逻辑,是体系化的;官僚的行为选择是基于逻辑分析并由理智控制的等等。韦伯区分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合理性,即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在他看来,实质合理性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主要特征,而形式合理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本质特征。形式合理性工具—功效的行为逻辑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科学精神、法制精神与理性精神,它摒弃了传统经验型管理所掺杂的大量人治因素,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管理者的任性专断和感情用事。韦伯认为,正是这样一种非人格化的管理体制适应了现代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发展,显示出了以往其它管理模式无法媲美的管理效率,以致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说它是“实施统治形式上最合理的形式。”(注: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第24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首先,作为一种行政管理体制,理性官僚制的组织形式和行政逻辑所贯穿的形式合理性原则,适应了现代社会对形式平等的追求,体现和保障了人与人之间在法规、制度面前的形式上的平等权利,克服了传统行政管理的特权主义,一切因人而异的专断性,以及“自由的随意专断和恩宠,怀有个人动机的施惠和评价”(注: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第301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等等。在理性官僚制中,行政主体必须根据普遍主义、形式主义的原则,按照统一的标准来对待、处理相关的人和事,“断然拒绝‘特权’和原则上拒绝‘按具体个案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注: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第30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其次,同法理型统治和形式主义法律相适应,现代官僚制行政管理体制一切依照制度规范运作的模式,最大限度地消除了公共权力行使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保证了行政行为的理性化和规范化。在此,行政主体在严格、细致的制度规范的约束下,“没有憎恨和激情,因此也没有‘爱’和‘狂热’”(注: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第250—251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理性官僚制作为美德赞扬的特性是:它成功地“排除一切爱憎和一切纯粹个人的、从根本上说一切非理性的、不可预计性的感觉因素”。(注: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第344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再次,理性官僚制的行为主体是基于自由契约的专业化的职业官员。这一方面构成了对封建世袭制或家臣制的否定,并为职业官僚官员的人格自由和合法权益提供了充分的保障。世袭特权以及对上司的人身依附等现象不复存在,职业精神受到了充分的鼓励。另一方面,理性官僚制运作的基础是专业知识、专家职业,从事行政管理的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官员,这种管理模式充分体现了对知识和技术的重视,有效地促进了实证科学知识在行政管理中的广泛应用,使得行政管理不断向着职业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行政管理的效率。
最后,最重要的是,形式主义、普遍主义原则,专职化、层级化的组织形式,以及权责一致、一切按法律和规则行事等行为逻辑,使理性官僚制形成了适应现代技术、经济和社会生活需要的一种特有的优势,即管理行为的“可预计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生活的高效率,都是建立在行为过程及环境的某种程度的可预见性基础上的。人们只有在能够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相关的事务和社会环境作出起码的理性预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基于功效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公共事务是否具有可预期性,对于人们的行为选择及其效率影响尤为关键。韦伯指出:“现代文化的特性,特别是它的技术—经济的基础,恰恰是要求效果的这种‘可预计性’。充分发展的官僚制在某种特殊意义上,也处于‘不急不燥’的原则支配之下。它的特殊的、受资本主义欢迎的特性,使这种可预计性发展得更为充分,它越是‘脱离人性’,发展就更为充分。”(注: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第297—29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总之,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和高效率的组织工具,以非人格化、制度化的特征否定了家长制下的人治现象,适应了工业社会大生产和行政管理复杂化的客观需要,促进了行政管理由“人治”到法治、由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的历史性转变,在技术上显示出了超乎以往一切管理模式的巨大优越性。正如韦伯所预言的那样,官僚制自诞生以来,已经逐步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组织普遍的结构模式和管理模式。即使是对理性官僚制现实合理性持否定态度的人,也无法否定它所具有的无可质疑的历史合理性。正如阿尔蒙德、小鲍威尔在《当代比较政治学》中所指出的:在现代政治制度里,官僚制机构的作用不可或缺,人们不可能发明一种方法在没有官僚机构提供的组织、分工和专业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工作。(注:参见阿尔蒙德、小鲍威尔主编:《当代比较政治学》,第154—158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
二、新公共管理的挑战:替代性超越抑或调适性完善?
尽管理性官僚制自诞生以来就受到过种种非议,但真正对这种管理体制的组织结构和行为逻辑提出全面质疑的,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新公共管理实践产生的种种行政改革理论模式。美国组织理论家沃伦·本尼斯曾预言:“从六十年代算起的二十至五十年里,人们将目睹并亲自加入官僚制的送葬队伍。”(注:Jay M.Hafritz,Albet C.Hyde:Class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2nd,The Dorsey Press,Chicago,1987,p.325.)1992年,大卫·奥斯本和泰德·盖布勒在《重塑政府》中提出10大新的管理原则,对理性官僚制的现实合理性提出了全面的质疑,认为“工业时代发展起来的官僚体制,专注于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层叠的指挥系统,已不能有效运转;它变得机构臃肿、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它在变化迅速、信息丰富、知识密集的90年代已不能有效运转了。”(注: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第12~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一时间,“重塑政府”、“突破官僚制”、“摒弃官僚制”以及“后官僚制”行政、“企业化政府”之声在公共管理学领域不绝于耳,在实践中则出现了诸如市场模式、参与模式、弹性政府模式和解制型政府模式等“后官僚制”行政的尝试。(注:B.Guy Peters,The Future of Governing:Four Emerging Model,Kansa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6,P19.)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这种否定理性官僚制的思潮在国内行政管理学界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响应。国内学者批评的锋芒除了指向官僚制的组织设计对人的作用的忽视以外,还特别强调“官僚制导致了普遍的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据此,一些学者断言理性官僚制是建立在近代物理学的思维范式上的,是一种机械模式在社会领域中的反映,随着信息科学的出现,它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公共管理的需要。(注:张康之:《“官僚制”的文化省察》,《东疆学刊》2002年第3期。)
新公共管理实践及相关理论思潮对理性官僚制的否定和挑战是全方位的。归纳起来,这种理论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官僚制僵化臃肿的组织结构难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快速变迁。一些理论认为,官僚制以层级节制的结构刚性来维护组织的权威性,以技术性与职业性来体现其效率,使官僚组织演变成了日益脱离社会环境的封闭系统,丧失了对环境变革的适应性。在这种等级制的组织中,只有最上层的管理者才掌握作出决定的足够的信息,它很难适应信息化和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官僚制繁琐陈旧的规章制度和工作程序,也使中下层管理者失去了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和实际操作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创造性,鼓励了盲从和随大流,压制了创新精神。(注:朱国云:《组织理论:历史与流变》,第249—25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2.理性官僚制极端化的形式主义、普遍主义、理性主义的运作逻辑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官僚制犹如一只巨大的铁笼和精密的机器,将人固定于其中,成为官僚制这架庞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或一个螺丝钉。循规蹈矩的官僚只知道服从于铁面无私的工作纪律,只会循规蹈矩地例行公事,并因此而丧失了感情和人性的丰富性。这种行为逻辑同现代社会尊重个人权利,鼓励自主选择,追求自我实现的价值取向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3.理性官僚制专业化、职业化要求所体现的“精英”行政取向同民主政治形成了无法调和的矛盾。民主政治赋予了公民政治主体的地位,但在庞大的官僚行政机器面前,他们依然不过是被动的被统治者和被管制者,“民主悖论”的现象使公民的政治地位与行政处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专业化、职业化的行政管理为官僚体制排斥公民的行政参与提供了方便的借口,普通公民不仅无法参与他们利益息息相关的公共事务,而且也无从了解公共事务复杂的程序及相关的极其丰富的信息,只能成为公共事务的旁观者。
4.官僚制封闭的组织结构实际上使官僚成为某种既得利益群体,其行为取向常常严重偏离公共效用最大化的方向。在这方面,一些学者提出了官僚自主性(bureaucratic discretion)的概念。所谓官僚自主性,是指官僚机构或个人超越其法定的地位和职能,超越政治家的控制,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现象。借助于信息优势,官僚日益脱离或超越了议会和行政领导的控制,已经成为“独立的、准行政、准立法和准司法机构”,并因此而使民主社会演变成了“官僚国家”。(注:袁瑞军:《官僚自主性及其矫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6期。)威廉·尼斯坎宁在1971年出版的《官僚制与代议制政府》中,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职业官僚所追求的目标与官僚所在机构的预算规模正相关,以及政府预算规模与政府权力的大小正相关的假说,(注:William,Niskanen,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Chicago:Aldine-Atherton,1971.)对官僚自主性问题的根源进行了具体论证。此外,委托—代理关系理论、“俘获假说”、“生产无效率假说”、“公共产品供应过剩假说”等等都为批评官僚自利性和官僚制的低效率提供了理论依据。
不能否认,新公共管理实践,以及“后官僚制”行政理论所诟病的理性官僚制的种种弊端,的确在许多组织中相当严重地存在着。但问题在于,这些批评和质疑,是否真正构成了对理性官僚制组织结构和运作逻辑根本性的挑战?社会生活的变迁是否已经使理性官僚制在整体上丧失了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在我们看来,新公共管理与“后官僚制”行政实践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理性官僚制组织结构的基本范式和这一管理模式运作的基本逻辑,它们并不构成对理性官僚制的替代性超越,它们没有也无法确立一种具有足够的经验支持的替代理性官僚制的行政范式,断言理性官僚制时代已经终结为时尚早。
新公共管理实践对理性官僚制的挑战是在西方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展开的。首先是,当代新技术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对企业、政府的组织结构以及行政管理模式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少的确是传统的理性官僚制没有遇到过的。如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信息传递模式,使得理性官僚制的层级结构向网络式结构演变成为必要和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有的社会组织再一味地固守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就有可能难以适应社会生活环境的变迁,抑制组织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的提高。就此而言,新公共管理实践的某些探索对于完善理性官僚制,提高其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对现代社会的适应性,是不乏积极意义的。
其次,新公共管理实践对理性官僚制的挑战,是在现代官僚制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境地,甚至这种管理模式被滥用和推向极端的情况下发生的。例如,政府行政的低效率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根源,就在于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社会不断扩大政府职能和权限,在公共事务中滥用官僚制。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威尔逊所说的:“只有政府小些,官僚主义才会少些”。(注:詹姆斯·Q·威尔逊:《美国官僚政治》,第439及4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当政府权力的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出现政府能力与政府职能的严重不对称,并使传统社会各种自治组织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功能受到极大抑制时,人们对公共事务存在的诸多不满就很容易被引向官僚制本身,而不是官僚制的滥用或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理性官僚制在经历了一两个世纪的发展演变以后,其形式主义、普遍主义的行政管理运作逻辑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境地,在其合理性已经为人们熟视无睹之后,其规范化有余而灵活性相对不足的问题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各种所谓的官僚主义弊端就成为人们批评理性官僚制的重要口实。就此而言,新公共管事实践在西方的兴起,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并非空穴来风。
但问题在于,新公共管理的挑战并没能够动摇现代理性官僚制存在的现实依据,以及这种管理体制的运作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可替代的行政范式。迄今为止,新公共管理实践以及新兴的“后官僚制”行政思潮对理性官僚制的批判,流露出浓厚的后现代主义意味。其对理性官僚制的否定在很大程度上是解构性的而不是建构性的,它们与其说已经宣告了理性官僚制行政的终结,勿宁说是为调适和完善理性官僚制提供了新的机遇。事实上,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一种行政管理思潮形成了足以替代官僚制的成熟的理论范式和经验支持,其多种改革主张更多只是基于官僚制某一弊端而产生的变革冲动,且相互之间往往顾此失彼,矛盾重重。如通过市场化提高政府运作的效率,有可能导致政府行为公正性的缺失;一味地倡导分权可能导致政府部门各行其是,在提高了政府部门的自主性的同时极大地增加政府协调与控制的成本;倡导解制型政府和弹性化政府在提高官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同时,有可能导致官员滥用行政权力;鼓励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订虽然有利于增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础,但也有可能导致决策成本的直线上升,如此等等。
“后官僚制”的种种探索,就其所针对的理性官僚制所存在的弊端而言都有其合理的成份,但这些探索本身可能产生的负面问题却常常为探索者所忽视。在一些情况下,替代思路可能产生的问题比它所致力消除的问题可能还要多。以奥斯本和盖布勒倡导的“顾客导向的政府”为例。期望政府对公众的需求持更为积极的回应性态度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如果这种回应超出了一定限度,可能产生的是公共行政的公正性缺失的严重问题。换言之,这种管理主义取向的公共行政将导致“政府最终对每个分散的个体(即顾客)的短期自我利益作出回应,而不是支持一些通过深思熟虑的过程(公民)公开界定下来的公共利益。”它忽视了“某些向政府寻求服务的人在提出他们的需求方面有更好的策略及技艺。”(注:罗伯特·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第162—16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对于公共行政来说,效率并非压倒一切的价值取向,公共性相比于效率更具有前提性的意义。
再以“企业家政府”为例,有关在政府管理中引入企业家精神和市场机制等种种对策思路,对于降低政府组织结构的僵硬性,解决政府组织存在的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的问题在一定范围内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并非意味着“企业家政府”具有同理性官僚制相比的整体优势,具有了全面取代理性官僚制的现实合理性和可能性,更不意味着政府行政改革只能按照企业工商管理模式来进行。一方面,正如戴维·比瑟姆所指出的,官僚体系并不必然等同于僵化的组织结构,它也可以具有灵活性。(注:戴维·比瑟姆:《科层制》,第46页,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通过引进一些新的机制,增强官僚制的适应性是完全可能的。另一方面,无论企业管理与政府行政管理之间具有多大程度的一致性,但政府行为同企业行为毕竟是两回事,两者的目标、价值取向,以及可能采用的行为手段都有着许多难以超越的界线。如果说把理性官僚制推向极端,以为理性官僚制在各种管理活动上都能取得同样的绩效是一种神话的话,那么,夸大市场化的效果,把“市场化”、“企业化”视为包治政府行政管理百病的灵丹妙药,同样也可能是一种神话。
三、理性官僚制的局限:基于何种视角的反思?
任何一种对现行行政体制的理性反思,都必须建立在合理的参照系统上,建立在对反思对象的性质、功能及其适用范围合理和恰当的理解上。毫无疑问,理性官僚制存在着某些固有的局限性,而新公共管理实践和“后官僚制”的诸种理论思潮对于如何进一步完善现行公共管理体制也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但是,客观地讲,后者对前者的挑战与批判,往往缺乏一种对公共管理体制历史与现实同情性的理解。
首先,我们究竟是应当基于一种理性、现实的态度,还是基于对某种理想化的行政管理模式的浪漫期待,或者基于对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的某种情绪化的感受来反思现代官僚制?坦率地讲,“后官僚制”行政理论对理性官僚制提出的最主要的非难,实际上都没有超出韦伯当年的预言范围之内。韦伯深刻地意识到了理性化进程内在的悖论。尽管他认为理性官僚制是迄今为止最有技术优势和效率优势的行政管理模式,但他对理性官僚制的弊端始终抱有清醒的意识,从不讳言理性官僚制所固有的局限。韦伯甚至充满忧虑地描绘了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可能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悲剧性的后果:“早晚总有一天,世界上充满了齿轮和螺丝式的芸芸众生,他们会紧紧抓住职位,处心积虑,不顾一切地沿着官僚化的等级层次阶梯向上爬。”(注: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第24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韦伯曾经预言,官僚制的发展,最终有可能使政治仅仅成为一种管理实践,而不再是社会状况的创造性体现。因而官僚制统治的人类社会,将可能是一种毫无进步可言的、墨守成规的日常生活的延续。即使是对于效率问题,韦伯也曾提醒人们:“科层体制破坏了人民全部的经济和政治主动性……科层政府压制私有经济活力古已有之。任何科层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都有形成该结果的趋势;我们现在的科层组织同样不可避免。”(注:转引比瑟姆:《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第9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社会往往只能在一种二律背反的困境中作出选择,历史的进步总是伴随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期望实现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完美统一尽管可以理解,但往往却是不现实的。一些学者激烈地批评理性官僚制缺乏人文关怀,缺乏对人的个性价值的尊重。但我们必须看到,理性官僚制否定特权、门第、血统等先赋性因素,坚持形式公正原则,以普遍主义的态度对待行政管理涉及的一切对象,这本身恰恰体现了一种在现代社会至关重要的人文关怀。毫无疑问,理性官僚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其形式主义、理性主义、普遍主义的运作逻辑决定了它不可能给予每个人的个性、情感、价值等非理性因素以充分的尊重,不可能灵活地因人而异地给予每一个人丰富的人文价值关怀。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要求基于人文关怀的实质合理性,按照对象的个性或个案特征去处理公共事务,就某些个案而言的确可能会体现出很浓的人情味或人文关怀,但一旦把这种做法发展成一种管理模式,其结果恰恰可能造成人文关怀的普遍缺失,即各种人情、“关系”的泛滥导致公正秩序的瓦解。
二律背反的困境同样体现在理性官僚制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上。一方面,正如韦伯所分析的那样,官僚制本身就是社会合理化、民主化进程的产物,它对知识化和专业化的要求,以及广泛地从社会普通阶层中选拔公务人员的做法,从根本上否定了身份制和世袭制中的门第、血统、特权观念。与此同时,理性官僚制要求按照抽象的规章进行管理,在一定意义上也否定了传统行政按照长官意志进行管理的做法。这些都具有重要的民主政治意义。但是另一方面,在理性官僚制的发展过程中,其对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注重,以及趋于僵硬化的层级制的组织结构,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公民对公共事务管理的普遍参与。对照官僚制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被滥用于各种公共事务的现实,新公共管理实践提出的放权要求,如将一部分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职能放到社区和各种中介组织之中,要求公民更多地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订过程中来等等,有其现实合理性。但严格地讲,在行政管理中,公民的自主管理和广泛参与毕竟是有限度的。以扩大公民参与为由从根本上否定理性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和运作逻辑是站不住脚的。一是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状态,有序的社会生活都要求有一个权威结构的存在,一定限度内的层级制结构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不可避免的;二是尽管理性官僚制存在进一步扩大公民参与的空间,但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趋势依然是结构越来越复杂,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致。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行政管理对专业化、职业化的要求同过去相比不是更弱了而是更强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共事务的自主管理与广泛参与必然会遇到难以完全突破的限制。
其次,我们究竟是应当联系现代官僚制的社会政治背景,还是孤立地就官僚制本身来反思其可能存在的局限?理性官僚制,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是一种具有效率优势的行政管理的技术装置,其效用的发挥需要有相应的政治制度架构的支撑,因此对现代官僚制的反思不能脱离制约其运作的政治环境。韦伯之所以提出理性官僚制一旦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境地,就可以为任何统治集团服务,同时强调最有效的理性官僚制是与法理型权威相适应的官僚制,根源即在于此。应当看到,现代官僚制所面临的问题有其政治根源,是一定政治结构的产物。肯尼斯·梅尔(Kenneth J.Meier)指出:美国政府的问题不是官僚制的问题,而是治理的问题,关键不在于官僚制的失败,而在于选举性机构的失败。(注:Kenneth J.Meier,“Bureaucracy and democracy:The
ease for more bureaucracy and less democracy”,PAR,May/
Jun,1997(57),p.193—199.)事实上,现在一些被归咎于官僚制的公共领域问题,只有在优化官僚制的政治制度环境,优化政治与行政关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得到真正解决。以腐败问题为例,理想形态的理性官僚制同公共领域的腐败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西方国家恰恰是在理性官僚制得到普遍推广以来,专制时代和产业革命初期那种制度性和普遍性腐败现象才得到了有效遏制;为什么今天恰恰是那些官僚制行政还很不成熟的国家腐败问题最为严重而不是相反。针对尼斯坎宁提出的官僚机构在决策中的自主性问题根源于其对信息的垄断的观点,美国学者布林顿和温特罗布就曾提出,如果议会中政治家能够容易地(低成本地)获取有关公共物品真实生产成本信息的话,官僚的垄断地位就不复存在,将被迫按政治家的意志生产社会理想的而非过剩的产量。尼斯坎宁的结论只有在政治家无法控制官僚对信息的歪曲时才会出现。(注:袁瑞军:《官僚自主性及其矫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6期。)
再次,我们究竟是应当基于一种行政管理体制或行政范式,还是基于特殊情境下的行政行为个案来反思现代官僚制?理性官僚制,其程序化、规范化运作,形式主义和普遍主义的价值取向具有“一刀切”的刚硬性,就某些个案而言,的确可能存在令人反感的官僚主义、低效率之类的问题,显然不如一切依人、依情境为转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任何规制限制的做法更具有灵活性和实质合理性。但也正是这样一种不讲情面的刚性运作规则保证了理性官僚制在整体上的高效率,体现出了理性官僚制的规模效益。相反,缺乏这样一种照章办事,对事不对人的运作刚性,最终恰恰可能造成行政管理在总体上的低效率。迄今为止,新公共管理实践所取得的一些所谓成功经验,都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完成的,如某个小社区的治理经验,基于某一行政主体特殊的行政能力或其丰富社会资本所取得的成效等等。但这一切同整个政治共同体范围内行政管理体制的重建毕竟是两回事。在超越现代官僚制的种种试验还没有取得超时空的突破性成就,“后官僚制”的理论模式还没有取得普遍的经验支持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对这种超越冲动保持理智的审慎态度。
四、理性官僚制之于当下中国的公共行政:规范、趋近抑或超越?
新公共管理实践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行政管理系统中管理主义传统与宪政主义传统之间的内在张力,是管理主义传统对宪政主义传统的一种强有力的反弹。自现代公共管理体系诞生以来,西方的公共管理领域一直存在着宪政主义与管理主义两大思想传统。一般而言,宪政主义传统侧重于公共管理的宪政框架,侧重于强调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与公正性,致力于健全公共管理规范的制度体系。而管理主义传统侧重于公共管理的技术层面,强调公共管理的效率取向以及组织结构的弹性与管理行为的灵活性。两大传统相互支撑、相互制约,较好地维持了西方公共管理在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平衡。在公共管理的宪政制度框架已经趋于定型、成熟,公共管理的制度体系日趋缜密和规范的情况下,以新公共管理实践为代表的管理主义传统的反弹,在不变更整个公共管理的制度结构的前提下,从技术层面探讨消除和缓解公共管理领域日益突出的制度僵化、形式主义、效率低下等问题,当然是不无积极意义的。但是,联系到中国公共管理的现实境遇,我们在借鉴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借鉴其管理主义取向的实践经验时,却必须对中国公共管理的宪政框架,以及公共管理的制度结构问题给予优先的关切,充分注意到中国的公共管理改革,首先是个公共管理的制度结构的确立与完善的问题,而不是技术的移植和创新问题。换言之,相比于新公共管理这种注重技术层面改革的管理主义传统,西方公共管理的宪政主义传统更值得我们借鉴。
当代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在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多种管理体制的混合物。从根源上讲,这一体制与以下几个背景有重要的内在关联。
首先是对苏联集权式官僚体制的借鉴与移植。这一体制同理想型官僚制的最大区别,一是一党政治与官僚行政相结合,官僚体制的运作受党政意志的支配,并由此形成了事实上的二元行政主体格局。二是官僚机构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全面垄断,以及国家权力不受限制的自主运作,使官僚组织的触角得以方便地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形成行政权力对社会生活全面控制的局面。
其次是中国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沿续。韦伯认为,秦始皇以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标志着中国官僚帝国时代的开始。特别是隋唐科举制的发展,中国古代官僚制度达到了人类历史上最接近现代官僚制的古典形态,成为“特别现代的、和平的和官僚体制化的社会最完美的代表。”(注: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第374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但这种官僚制毕竟不是现代那种与法理型权威相对应的理性官僚制,而只能称之为“世袭(或家产)官僚制”、“半官僚体制”。由于中国传统专制政治所固有的专断独裁特征,加上传统宗法文化的影响,古代中国并未真正建立起理性的非人格化的行政管理体系。尽管科举制度本身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出了某种形式合理性的意味,但这一技术进步并没有从根本消除传统官僚制度的非理性特征。严格地讲,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只能称之为人治条件下的特权官僚制。它正如王亚南所指出的那样,“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注: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1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再次是革命战争年代带有浓厚的魅力型权威色彩的行政运作模式的影响。就影响的深入性和广泛性而言,这一行政运作模式一个重要的历史遗产,就是其特有的政治动员机制。所谓政治动员,“就是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的名义下,运用思想舆论和宣传教育等政治社会化手段调动民众对执政者及其决策的认同、支持和配合,从而加强政治体系的施政能量,促进决策的贯彻执行。”(注:胡伟:《政府过程》,第31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这一模式不是把行政管理视为一种世俗化的专门职业,不是立足于保障官僚的世俗权益,借助制度规范来约束官员的行为来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而主要立足于思想改造、思想动员,来激发管理者的献身精神。正如韦伯所言,魅力统治和现代官僚制都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但两者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官僚制“是通过技术手段进行革命的,原则上讲……是‘从外部’进行的,首先对物和制度,然后由此出发对人进行革命化,对人是在改变其对外界的适应条件和可能是提高其对外界适应的可能性的意义上,通过合理的确定目的和手段,进行革命的。与此相反,魅力统治……‘从内部’出发对人进行革命化,并企图依照它自己的革命意愿,来塑造事物和制度。”(注: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第451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行政机构改革与公务员制度建设。按照十六大报告的表述,机构改革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调整政府部门组织结构,实行精兵简政;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完善行政运行机制;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行政体系的法制建设。”这些改革原则和措施,在总体上都可以视为是行政制度结构的调整,其价值取向同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是一致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中国行政制度结构的转型过程还远未完成。建立成熟的现代官僚制,需要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条件的支撑。对照理想形态的理性官僚制,中国在这方面的条件并没有完全具备。举其要者有其四:一是官僚制行政的政治合法性还没有从民主政治制度上得到完全确认,在实际行政过程中由于公民或其代表无法对行政主体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政治监督和控制,由此引发的大量滥用行政管制权力的现象使得基层行政存在相当严重的信用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二是行政体系的运作缺乏现代宪政制度的支撑,行政权力缺乏必要的刚性制衡机制,行政权力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全面渗透的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三是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结构的转型正在展开,职业官僚队伍尚未普遍地形成基于自由契约的独立人格和职业精神。四是受文化历史传统的影响,公民和职业官员都普遍缺乏对体现形式合理性的制度规范的信仰,同现代法治秩序相适应的普遍主义的行为模式尚未确立。
正是由于上述条件的限制,中国在建立现代行政管理体制的过程中,还没能将现代官僚制的理性精神全面灌注到整个行政管理体制和管理行为系统之中。在现实生活中,公共行政还掺杂着大量非理性的因素,在行政结构、行政行为、行政文化诸方面都存在着诸多同理性官僚制形式主义、普遍主义取向格格不入的现象。因此,就当下的中国而言,“官僚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所存在的问题与其说是理性官僚制本身的问题,勿宁说是理性官僚制的欠缺和不成熟造成的。
首先是行政体制层面所存在的非理性因素。由于如何改进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依然是探索中的课题,党政分开还没有形成制度化、法律化的运作规范,目前公共领域两大行政主体并存的格局并没有被完全打破。两者的交叉、重叠,客观上制约了行政组织体系的理性化以及行政运作的规范化。与此同时,即使就行政系统本身而言,职能分化和分工也存在诸多不合理的问题,放权、收权的循环,以及行政机构的频繁调整,说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内部之间,以及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与权力分配还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法律化的制度框架,机构、职能重叠交错现象还司空见惯。
其次是行政运作层面所存在的非理性因素。一是行为内容的非理性,即行政组织往往不是根据事先理性设计和严格限定的职能、权限从事自己的行为,而是承担着大量远远超过其法定权限和能力范围的各种公共性事务。其中最突出的是,目前中国的地方政府还没有从发展型政府的激励机制中摆脱出来,现行的绩效考核体制仍然使得地方政府有着强烈的直接介入经济过程的冲动,而一些最核心的政府职能反而没能真正引起它们的关切。二是行政过程的非理性即人治化运作。从表面上看,各级行政组织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层级化与部门化机制,但实际上行政组织的权力运作过程仍然呈现出浓厚的人格化色彩。服从领导而不是制度依然是普通公务员重要的行为取向。个人权威、职务权威大于法律权威、制度权威,行政行为的效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领导个人的影响力。三是行为取向的非理性,即地方利益与部门利益,以及政府自身的利益,往往导致行政效用目标同整个国家行政体系的效用目标的背离。利益驱动已经成为地方政府行为的一个突出问题。如何在与中央或上级政府的博弈活动中,以及在地方行政管理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成为地方政府政策选择的重要变量,由此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政府行为短期化,以及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等一系列集体非理性的现象。
如果说新公共管理实践针对的是西方现代官僚制规范有余而灵活性相对不足的背景,因而其提出的市场化政府、弹性化政府、解制型政府等改革取向在一定范围内还有其合理性因素的话,那么,中国行政管理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恰恰是灵活性有余而规范性严重不足,刚性制度规范的短缺已经使行政权力运作的随意性远远超出了自由裁量权不当运作的范围。在行政作为与不作为,以及如何作为都存在极大的自由伸缩空间,并没有建立严格的责任机制与监督制约机制,以致行政行为往往缺乏起码的可预期性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解制”,勿宁说是“建制”。
再次是行政文化层面所存在的非理性因素。理性官僚制行政不仅意味一种特殊的组织结构,一种特殊的运作逻辑,而且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行政文化,一种奉行形式主义、普遍主义的“官僚制精神”。相形之下,转型期中国的公共行政还弥漫相当浓厚的传统非理性行政文化气息。
表现之一是行政组织中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人格依附现象。从表面上看各级公务员的身分都有现代自由契约的形式,但受传统家长制遗风的影响,加之公务员的职务晋升,工作业绩考核还缺乏严格的操作规范,主要取决上级领导的旨意,由此客观上决定了各级官员很难完全摆脱对上级组织和上级领导的依附。
表现之二是特殊主义价值取向的广泛盛行。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带有鲜明的特殊主义取向,人们在决定社会行为的态度和行为取舍时,首先考虑的是对方同自己的私人关系。这种特殊主义取向,已经内化在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之中,并形成了某种自我强化的机制,以及对形式主义、普遍主义的行为规范的抗拒心理。时至今日,血缘、地缘、业缘、学缘等人情关系依然是影响公共权力运作的重要变量。
表现之三是制度至上性的信仰,以及忠诚于职业和制度规范的职业精神的阙如。中国传统的价值信仰体系一直偏重于实质合理性,形式合理性的信仰相当淡薄。受其影响,加之人治政治的作用,中国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着相当突出的对人不对事的倾向,各种正式制度往往流于形式,真正制约官员行为的是各种非正式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许多制度安排往往都在行为主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之类的借口中流于形式。“原则”本应是最具有制度刚性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原则上”一词恰恰已经演变成了可以通融的代名词。
概而言之,受现行政治制度框架的制约,在传统型权威与魅力型权威的行政管理模式的长期影响下,转型期的中国行政,无论是在行政体制层面,行政运作层面,还是行政文化层面,都还存在着大量的非理性行政的遗迹。面对这一现实,在探索建立高效率的行政管理模式的过程中,我们没有理由简单地否定现代理性官僚制,更不能不切实际,想当然地试图超越官僚制,直接进入某种所谓的“后官僚制”行政。相反,只有在宪政和法治的政治框架内,按照理性官僚制的逻辑全面改造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中国的行政管理才能最终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由人格化管理到非人格化管理、由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的根本性转变。在这方面,美国学者盖伊·彼得斯的提醒是很有针对性的:“对于体制转换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在追求政府部门最大化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重视建立一个可被预测的属于全民的、正直的韦伯式官僚政府。”(注: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第8页、第2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标签:韦伯论文; 新公共管理论文; 行政管理论文; 经济与社会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行政体制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商务印书馆论文; 经济学论文; 现代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