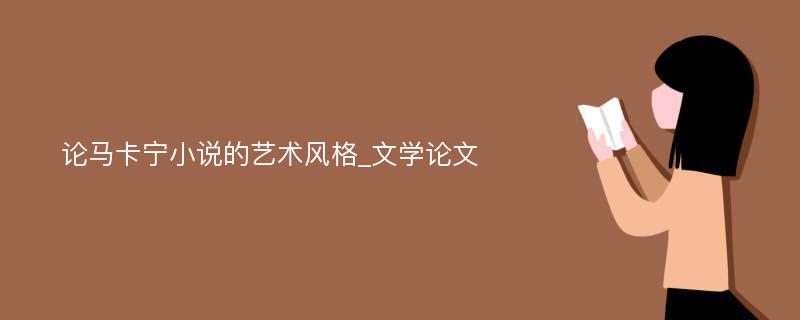
论马卡宁小说创作的艺术风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艺术风格论文,小说论文,论马卡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马卡宁(Владимир Семёнович Макан ин,1937—)是当代俄罗斯文坛最具实力和声望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活动始于60年代中 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作为“40岁一代作家”(注:指苏联70年代后期崛起的一批相当有才华的作家,如马卡宁、克鲁平、阿纳托利·金等 。他们都出生于30年代末40年代初,成名时的年龄是40岁左右,因此把他们称作“40岁一代 作家”。)的重要代表而令人瞩目。苏联解体后,马 卡 宁的创作更加活跃,1993年,他以中篇小说《铺着呢布,中央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摘 取了俄罗斯布克文学奖的桂冠;1998年又成为第10位获得普希金奖的作家。在几十年的创作 历程中,无论经受怎样的毁誉褒贬,马卡宁始终坚持自己的创作理想,远离政治斗争和文学 争论旋涡,以严谨的态度从事写作。本文拟考察马卡宁的主要作品,着重探讨他在艺术上的 大胆探索和特立独行的艺术品格。
纵观马卡宁的创作道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早期、中期、近期的作品有明显的不同, 但它们实质上却又是一脉相承的。从处女作《直线》到90年代末的长篇小说《地下文学,或 者当代英雄》,都真实而鲜明地反映了马卡宁的思想探索轨迹,同时也显示出他在艺术上目 臻成熟又不断求新求变的历程。
一
在早期创作中,马卡宁立足于日常生活,描绘六七十年代苏联社会经历的“安乐化”过程 。这是在战后重建工作结束,物质生活达到温饱甚至富裕之后出现的。马卡宁着力表现在这 种“温饱的考验”中,一些人由于个人意志薄弱以及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蚀,最终放弃正义原 则,随波逐流,成了新一代市侩。马卡宁考察了他们心理蜕变和道德立场模糊乃至丧失的过 程,引发出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深层思考。他的反市侩小说基本上以大都市为背景,描写种 种善恶交织的矛盾人物和平庸世俗的中间人物的日常生活。小说的主人公大多人过中年,激 情不再,现实无情地把他们抛到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逼迫他们作出选择。在描述他们庸俗 化过程的同时,马卡宁揭示了人性的复杂,说明人在庸俗化的过程中善的逐步丧失。因此, 这个时期的作品基本上是写实的,主要表现现实生活中的现实人物。叙述的中心是主人公的 经历,情节的发展由主人公的性格、追求、行为和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决定。小说常常给人以 一种电影画面感,情节发展的进程有时好像是快速转换的电影镜头。马卡宁开始运用隐喻、 象征等手法,即使是在最写实的小说中,也不乏这种手法,如《老村庄的故事》中“老村庄 ”与“都市”相对立,象征着人的纯真而美好的理想。克留恰列夫作为一个都市人时常思念 老村庄,这不是外省人在首都孤立无援的感觉,而是一个淳朴的人在都市化了的人群中的荒 漠感。“老村庄”的存在是克留恰列夫的精神支柱,它的消失象征着克留恰列夫理想的破灭 ,使克留恰列夫最终蜕变为一个现代市侩。《克留恰列夫和阿立姆什金》这篇小说一开始就 是一个带有隐喻性的故事:某人总是幸运,另一个人总是倒霉,于是幸运者向上帝请教这是 什么原因,上帝的解释是幸福太少。而接下去的情节中又渗入了荒诞的成分:克留恰列夫的 幸运总是伴随着阿立姆什金的倒霉。美国文艺批评家理查德·考斯特兰尼茨将所谓荒诞派文 学定义为“通过一连串荒诞不经的(荒谬绝伦的或荒唐可笑的)事件暗示人类存在的极端荒诞 和极端没有意义”。(注:理查德·考斯特兰尼茨《关键在于生活本身毫无意义》,见《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9年。)《克留恰列夫和阿立姆什金》虽然算不上典型的荒诞作品,但的确具 有荒诞色彩。马卡宁采用荒诞的手法不是没有原因的,车祸的惨痛经历,文坛上的不顺(70 年 代马卡宁受到评价常常是毁誉参半,有时甚至成为众矢之的),使马卡宁深感命运不可捉摸 ,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
马卡宁早期还创作了两篇反映自己怎样创作小说的小说,它们是《关于一篇小说的小说》 和《群声》。短篇小说《关于一篇小说的小说》内容非常简单,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爱情故 事(“我”和“我”的邻居阿丽娅的浪漫史)。但小说的结构非常独特,可以说马卡宁进行了 一个全新的试验,以给读者全新的体验和感觉。小说以一个作家回忆自己丢失的一部手稿为 线索,既写了这篇丢失的小说的内容,又写了“我”这个作者创作这篇小说时具体的构思, 回忆完毕,小说也就此结束。马卡宁借此拉开了文本和读者的距离,使读者从作者的视角体 察了一部小说诞生的过程。创作于1977年的中篇小说《群声》在写法上比《关于一篇小说的 小说》走得更远。小说没有一以贯之的情节,没有主人公,作者只是把几个互不相关的人物 的简短经历贯穿其中。
二
从中期创作开始,马卡宁在继续探讨善恶问题的基础上,愈来愈鲜明地提出了人的个性问 题。一些主人公精神陷入空虚和迷茫;另一些主人公想与命运抗争、保持个性独立,可是又 往往造成心理和行为方式的扭曲,成为“怪人”。这些人物虽然不是正面人物,但都不庸俗 ,在他们身上有一种理想的东西,人类值得珍视的东西。马卡宁通过描写他们扭曲的心态、 反常的行为来表现整个社会的苦闷情绪和寻求精神家园的渴望。马卡宁既把他们放置在现实 的 生活背景上,又夸大他们的怪异之处,从而使他的形象获得某种寓意,从哲理高度上揭示人 的个性、精神世界的问题所在。
与早期描写现实生活不同,这一时期马卡宁开始广泛使用夸张、隐喻、象征等手法。这一 特点在《先知》这部小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马卡宁80年代的作品中,《先知》是最具代 表性、同时也是争议最大的一部中篇小说。主人公亚库什金本是一个普通的建筑工人,有一 个平静、幸福的家庭,后因盗窃建筑材料而被判刑。在西伯利亚服刑期间他被原木砸了脑袋 ,从此获得了能够治病的特异功能。出狱以后他开始专门给人治病,居然使几个垂危的病人 起死回生。从此亚库什金被誉为“先知”,他的身边聚拢了大批信徒,他们定期聚会,倾听 亚库什金的宣讲。后来,亚库什金的特异功能突然消失了,治病不再灵验,于是信徒们纷纷 离去。
这部作品引起了评论界的种种猜测和解释,他们各执一词,争论亚库什金这个人物形象以 及作者对他的态度。也有些评论家对作者的模糊立场进行了猛烈攻击。其实,先知是否灵验 ,是否真正存在,并不是作者所关注和要解答的问题,作者主要是借助这个巫师浮沉的故事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今天这个物质丰富、科技发达的社会里,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人在 亚库什金这样的“先知”身上寻找精神上的出路?
在《先知》中有一个具有隐喻意义的细节:亚库什金被原木砸昏过去,被抬往医院。在半 清醒的状态中,他忽然领悟到了真理。“它就像夜空中划过的闪电。当他醒来后,真理已经 不在他的体外,而是栖息在他的身上了。”实际上这象征着他从黑暗的或者蒙昧的意识中觉 醒过来,成为不同于一般人的“先知”。他立即在医院开始了布道式的宣讲:“你们不是工 人、农民,不是服务人员,……”“你们是兄弟和姐妹……”(注:关于《先知》的引文见《马卡宁中篇小说集》,“图书室”出版社,莫斯科,1988年。)他的谈话是对爱的发现,对 人的身份的发现。人在本质上都是平等互爱的存在者。他说出了最直接、最朴素的信仰与真 理——人与人之间是同类,是兄弟姐妹,所以人应当互爱。与其说亚库什金是用自制的药水 治好病人,不如说是通过布道唤起人们心中的信仰。他的精神疗法,能给人以朴素的爱和真 理(信仰),恢复人们的爱心去战胜生活中的“疾病”。
所谓先知就是比别人更早感知事物的人。普通民众沉溺于世俗事物,忘却了生活还需要准 则——往善的方向去努力。马卡宁认为:“……过去我们能够彼此合作,能够感受到人类的 规则,然而现在什么规则也看不到了。这一切又岂能让人熟视无睹呢?”(注:参见利波维茨基《关于山和地穴的荒诞》,载《文学报》,1992年第24期。)先知的意义就是 要提醒人去维护善所需要的社会秩序和生活准则。然而先知往往不被他所处的现实所容忍, 所以亚库什金悲剧性的死象征着先知牺牲自我、警醒后世的先驱精神。
《在天空与山冈相连的地方》是一篇充满隐喻情节的小说,同样引起了评论界不同的阐释 。主人公巴西洛夫是一位功成名就的歌曲作家,但是他一直被一个奇怪的思想所折磨:他对 家乡的人民不再唱歌这件事负有罪责。他的名誉和地位都是在榨干故乡民歌艺术精华的基础 上得来的。他为此痛苦不堪,决定回家乡拯救民歌事业,可是就像命中注定的一样,他的计 划最终破产了。许多评论家都承认,与其说作者是在表现事件,不如说是在象征事件。
小说中的许多情节都富有象征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整个小说就是建立在隐喻基础上的。 在巴西洛夫吸取故乡民歌的精髓、一步步走向事业顶峰时,家乡的民歌却在一点点被人遗忘 。他所体验的不仅仅是面对父老乡亲的愧疚之情,他痛切地意识到:当他逐步接近世人所仰 慕的功名利益的时候,他赖以生存的土壤、他的根本正在逐渐丧失。这其实体现了马卡宁的 一贯思想:被现代物质文明熏陶的都市人却失去了作为人的最淳朴、最本质的品质:善。这 种人性中善的丧失远远比民歌的消亡要更加令人沉重。
小说中经常发生的火灾也有象征意义。小说中的工厂是有规律的火灾的源头。火灾使巴西 洛夫失去了父母和叔叔,村子里许多人都是在火灾中丧生的。工厂是工业社会的必然产物, 它的存在直接与村庄相对立,工厂里“定期发生”的火灾象征着物质文明发达的社会里人们 心灵的一次次失火。
小说中还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情节,就是孩子的声音。夜晚,每当巴西洛夫沉浸在痛苦中的 时候,他都会听到“……在寂静和黑暗中传来高亢清纯的孩子的叫声”。后来在一次火灾中 他想到自己可能会死,这时“代替这种思想的是孩子的叫声”。这种格调贯彻整部小说,在 结尾时再次出现:“那一刻在默默向他靠近,当寂静和黑暗被一声清脆、高亢的童声打破。 ”孩子的声音是纯洁、美好的,这“人之初”的声音,作为光明的象征一次次照亮巴西洛夫 灰 暗的心,鼓舞他不断为拯救民歌、也就是为挽救人类的淳朴之声而努力。
三
进入90年代,马卡宁迸发出旺盛的创作力。在总结七八十年代所思考问题的基础上,他创 作了一系列具有反思性质的小说。一方面,他通过反思人类的历史继续探究善恶问题。另一 方面,他针对80年代提出的个性压抑、精神迷茫的问题,深刻地挖掘社会原因,从而思考理 想社会的问题。在这以前,马卡宁一直关注“人”,试图通过剖析具体的人来探索人性,反 映道德和精神问题。到了90年代,马卡宁开始关注“群体”。作品中愈加频繁地出现了具体 的 社会历史场景,而不是早期创作中展现的一般的个人生活。作家在此背景上思考人类社会的 历史、现在和未来。小说的结构更加复杂,时空进一步扩展,具有了一种恢弘的气度。
由于思考范围不断扩展,马卡宁在艺术上进行了更为大胆的探索和试验,其中最突出的是 引 入幻想和仿写成分。中篇小说《我们的路很长》可以说是马卡宁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 对这个世纪人类的历史和社会行为方式的一次总结和反思。在描写现实世界的同时,作者还 描写了幻想中的未来。在美好的未来,人道主义价值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人类已经善良到连 宰杀牲畜都不能容忍的地步,于是他们发明了人造牛肉。可是当主人公满怀希望来到这里时 ,却发现所谓的人造牛肉是无耻的谎言,这里实际上在秘密生产着恶。于是,无论在真实的 现在,还是在虚幻的未来,恶都依然存在,而且占据优势。善在两个世界里都失败了。小说 透露出马卡宁深刻的悲哀。马卡宁不仅幻想了未来世界中善与恶的较量,而且深刻分析了恶 得以存在和猖狂的根源:那就是人类对恶的熟视无睹、同流合污乃至对恶的掩盖和对伪善的 宣传。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在幻想世界中,人们都渐渐认可了恶的存在,变得麻木甚至加入 了生产恶的行列。没有人起来反抗,没有人维护善,更没有人去拯救善。这里再一次表现了 马卡宁的无奈。
伴随着对善恶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以往在马卡宁创作中一直较为隐晦的一个主题愈益鲜明 地突现在90年代中的作品中,这就是个性问题。作为一个成长于苏联灰色、沉闷的“停滞” 时期的作家,马卡宁深深体验了同时代人所感受到的失望与消沉、无奈与茫然的情绪,也更 加强烈地渴望个性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之中。马卡宁自 己承认:“首先令我关注的是:在群魔稳占上风的环境下个人怎么才能生存?……如果一定 要说目的,那么显现个性就是我的目的。”(注:《“我不为轰动一时的题材所激动”——与马卡宁对话》,见维塔利·阿姆尔斯基《闻 声知人——与俄罗斯作家和诗人的巴黎谈话》,мик出版社,莫斯科,1998年。)在早期创作中,马卡宁塑造了随波逐流、丧失 个性的市侩形象;在中期作用中,他又塑造出一批力图突破平庸与灰色却又无能为力乃至扭 曲 变态的怪人形象;进入90年代,他在深刻挖掘造成人的个性丧失的历史和社会原因的同时, 对人类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思考。在《出入孔》这篇小说中,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两个截然不同 的世界。在地上世界中,一片死寂和黑暗,到处是杀人、掠夺和对弱者的蹂躏,交通断绝, 物品奇缺。最为可怕的是人群以排山倒海之势滚滚而过,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根本无力抵挡 而被裹挟,直至自己都不知身处何方。也就是说,地上世界总是在试图扼杀个性和自由,以 一种貌似严正和强大的力量吞没着渺小的个人,人要么坚持自我,保持独立,要么迫于压力 ,丧失个性。而在地下世界里,灯火通明,物品丰富,人们大摆奢华的宴席,从容不迫地在 咖啡馆里讨论着各种问题。他们用最高雅的词语,谈论着国家和未来。然而,地下世界也有 它的不足,那就是:空气憋闷,氧气匮乏。显然,马卡宁在寻求一种理想的社会存在方式, 但是他没有找到答案。正如《我们的路很长》结尾时人人都点起象征希望的篝火一样,在《 出入孔》结尾时也出现了一个在暮色中唤醒沉睡之人的“好人”。这表明马卡宁仍然对未来 充满希望和信心。
1998年,马卡宁发表了创作生涯中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地下人,或者当代英雄》。从表 面上看,小说采取的是现实主义的描写方法,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小说对俄罗斯文学 史上许多名著进行了仿写。所以有些评论家认为它是“一部写给评论家、文学研究家和注释 者看的小说”,“而不带这些目的的读者未必能从中得到满足。”总之,这“是一部写给非 常专业的圈子看的非常专业的小说。”(注:玛利亚·列米佐娃《黑暗的走廊——沿着弗拉基米尔·马卡宁的下意识旅行》,载《独 立报》,1998年5月20日。)
小说采用了马卡宁惯用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我”是一个年过半百的早已搁笔的作家, 因为没有人承认“我”的作品,所以“我”拒绝写作,拒绝出版。那么“我”何以为生呢? 马卡宁为“我”安排了一个非常奇特的职业:看门。如果谁长期旅游或出差在外,家中无人 看管,“我”就住在谁家,替人照看房屋。因此,“我”就像无业游民一样,到处流浪,接 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物:有知识分子,有流氓醉鬼,有精神病人,有在任何地方都无所适从的 失败者,有高加索摊贩,有苏联解体后暴富的“新俄罗斯人”。无论处在什么样的阶层,这 些人似乎都在精神迷乱、灵魂迷失的边缘痛苦地挣扎。
“我”这个人物身上有许多马卡宁以前所塑造的人物的影子,马卡宁把他放置在不同的境 况 中进行考察,也考察他周围的人。他的名字叫彼得洛维奇,这是俄罗斯最普通、最常见的一 个名字,因此可以推测,他就是小说题目中的“当代英雄”,即我们这个时代中的一个普通 人。这个主人公有许多的缺点、劣迹,正如马卡宁在这部小说的题词中引用的莱蒙托夫的《 当代英雄》中的话:“英雄……是一幅肖像,但不是一个人的肖像,而是我们整整一代人及 其全部发展史上的劣迹所构成的肖像。”他的种种遭遇以及他为之而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原因 都来自他的个性,他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他永不屈服的大写的“我”(在小说中,经常出现大 写的“我”字)。为了维护“我”的尊严,他甚至两次杀人。第一次是彼得洛维奇认为一个 高加索商贩侮辱了他,于是他在一个夜晚约商贩出来,趁其不备用刀子刺入商贩的心脏。第 二次彼得洛维奇与一帮地下艺术家们畅所欲言,大骂那些“为了名声、荣誉和饱食终日而离 开地下的人”,后来他发现有个克格勃分子混入其中,正在秘密录音,于是他又用刀子杀死 了这个密探。
从小说的名称就可以看出,它采用了俄罗斯文学史上两部名著的名称,即《当代英雄》和 《地下室手记》。小说中每章的每一节都设有标题,不少标题乃至情节都是某些名著的仿写 。例如,关于小人物捷捷林的故事情节近似于果戈理的小说《外套》,“第一病室”来自契 诃夫的《第六病室》,“兄弟相会”取自《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兄弟相认”,“维涅基 科特·彼得洛维奇的一天”近似索尔仁尼琴的“伊万·丹尼索维奇的一天”等等。小说中还 有大量民谚和先锋艺术的词语。难怪评论家阿拉·拉蒂宁娜坚持认为这是一部超现实主义小 说 。(注:阿拉·拉蒂宁娜《杀人就如此容易吗?——文学像大病毒》,载《文学报》,1998年第17
期。)总体上说,这是马卡宁进行全面试验的一部作品,是他对自己三十多年创作生涯进行总 结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它标志着马卡宁在继承古典俄罗斯文学风格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终于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四
回顾马卡宁的创作历程,我们可以看到:马卡宁选择了一条孤独的文学之路,一条独立的 文学之路。早在1978年的长篇小说《肖像与周围》中,他就通过人物形象表明了自己的艺术 观:善与恶是同时存在的,因此写出绝对的善人或恶人是不可能的,这是生活的真实,也应 当成为艺术的真实。“文学是人学”,整个文学史就是在努力刻画人的肖像,但文学并不能 完全把“人”刻画出来。因此艺术就是一种苦役,一种永远的探索。
马卡宁主张在同一个人物身上能够听到“群声”的全部复杂的合唱,反对塑造定型、定性 的“铅版”人物。所谓“铅版”是指钝化人的思维的刻板模式和脸谱化的人物,他认为文学 应当塑造多样化的、非重复的人物:“并不是文学臆造了铅版,铅版一直存在,在文学产生 之前就已存在。而且,文学的产生,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同业已存在的铅版共同作用,要么毁 灭它们,要么重建新的。”(注:马卡宁《群声》,见马卡宁《出入孔》小说集,瓦格利物斯出版社,莫斯科,1998
年。)只有这样,文学才是丰富的,才是发展的。从上述观点出发, 马卡宁“以自己全部的创作来反对思维的程式化和艺术上的武断。”(注:马·唐菲里耶夫《良心的考验》,载《星》杂志,1982年第2期。)他塑造了形形色色的 人物,他们都不是绝对的好人或坏人,但他们都各有各的特点,既不彼此重复,也不重复他 人。评论家弗·邦达连科谈到,“对于马卡宁的人物,你无论如何也贴不上标签,他们在本 质上都是胜利者,即使在全盘皆输的情况下”。 (注:弗·邦达连科《希望之时》,载《星》,1986年第8期。)而马卡宁本人也正像他所塑造的人物一样 ,珍视自己的独一无二。无论是在文学受到全面控制的时期,还是苏联解体后对过去大加挞 伐的文学自由的当代,无论是遭受批判还是备受褒扬,他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自己的创作理想 ,实践着自己的创作理论。从马卡宁所走过的创作历程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马卡宁身上 具有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色彩,这就是独立自主的精神和民主自由的思想,这是知识分子身上 最可宝贵的特点,也是他们最为珍视的生存原则。
马卡宁曾经说过:“当前轰动一时的题材不能使我激动。”他的文学之路充满了曲折和艰 辛,他的作品曾屡屡遭到批判,不能在大型文学杂志上发表,马卡宁戏称自己进入了“阵亡 烈士公墓”(注:指以书的形式出版,而不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作品。)。但即使在成为知名作家以后,他依然特立独行,这种对于旧时代的警觉态 度 和始终不变的文学立场源于他深思熟虑的生活立场:“作家应当尽量离大众传播媒体远一些 。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它能使写作的人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使他成为自己的一颗旋钮,一 个齿轮。而作家常常迷惑于此,以为自己是一个什么东西的宣传者,实际上作家应该到适合 自己的地方……作家的声音远远弱于宣传,所以他应当从自我保护的个体感觉来珍惜自己。 ” (注:马卡宁《群声》,见马卡宁《出入孔》小说集,瓦格利物斯出版社,莫斯科,1998
年。)多年来马卡宁拒绝参加任何党派,与文学斗争小心保持着距离,无怪乎亚历山大·格 尼 斯说,马卡宁是侧身挤入苏联文学的。(注:亚历山大·格尼斯《米塔斯的触摸》,载《星》,1997年第4期。)俄罗斯著名评论家娜塔丽娅·伊万诺娃也感叹: “ 马卡宁既不是苏联作家,也不是反苏联作家,他就是他自己,不属于任何范畴,他的这种独 一无二使文学批评界大伤脑筋。”(注:娜塔丽娅·伊万诺娃《马卡宁的机会》,载《旗》杂志,1997年第4期。)
这种竭力维护艺术家及其创作独立性的努力与实践在苏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需要付出代 价 ,有时甚至需要经受苦难。然而,也恰恰是在维护文学独立性的实践中,马卡宁才能真正自 由
地理解和继承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使文学的任务不再是宣传和娱乐,而是理解和探讨人 性本身。马卡宁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体现了作者对人性与生命的理解和探索。甚至可以说, 他的每部作品都是他在不同时期对人性的试验,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物逼入极端状态, 对人性、对人的灵魂进行考问一样。
从处女作算起,马卡宁已经走过了35年的创作历程。他写出了一批风采独具的作品,塑造 了丰富多采的普通人形象,美国评论者玛利亚·列文娜-巴尔克尔说他“要写一部凡人的百 科全书”(注:玛利亚·列文娜-巴尔克尔《主人公的死亡》,载《文学问题》,1995年第5期。
),邦达连科称他是“当代人物形象长廊的缔造者” (注:弗·邦达连科《希望之时》,载《星》,1986年第8期。)。马卡宁曾经把作家的 写作 比作圣徒的活动。他似乎带着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的执著,从不放弃作家的社会责任。从这 里可以看出,马卡宁身上流淌的,乃是历代俄罗斯作家一脉相传的血液。我们尽可以说,马 卡宁是独立不羁的作家,是具有独立艺术风格的作家,但他首先是俄罗斯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