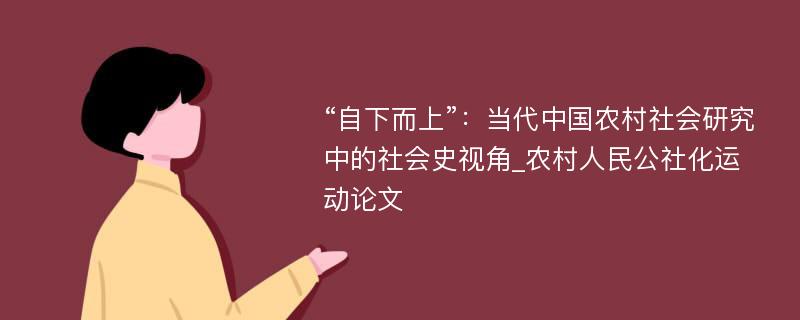
“自下而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社会史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自下而上论文,视角论文,中国农村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2;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9)04-0072-05
近些年来,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已蔚然成风。不同学科因采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判断和结论,但多学科的共同关注无疑会推动研究的深入。稍有遗憾的是,对这样一个重要历史时代的研究,历史学却基本因袭传统的框架,难有突破,这是近年来学界普遍感受到的问题。而以“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来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将有助于丰富我们对新中国历史的认识。
检索多年来对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的研究成果(不包括一般性著述),可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模式。自20世纪40年代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50年代初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撰写形成了一个基本框架。这一框架的基本特点是以重大事件和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为线索,以章节体形式撰写历史。几十年来,以《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党史》命名的数百部著作,更多的是不同类别的诸多教材,大多陈陈相因,难脱此框架。公正地说,这样的历史著述为人们认识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提供了基本的史实,亦曾在革命和建设中起了积极的教育作用。但这些著述大多限于对重大事件和上层路线方针政策的诠释,骨架虽有却缺少血肉。革命史和党史毕竟不能代替全面的完整的历史,除了政治还有经济,除了革命还有生产,除了斗争还有生活,除了中央还有地方,除了领导层决策还有基层百姓的众生相,历史本来就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画卷。
二是海外学者有关人类学、社会学的著述。海外学者对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数量虽有限,但大都是在亲身经历的基础上著书立说,自有其人类学、社会学的特色。迈德尔(Jan Mardal)夫妇1962年即深入陕北柳林地区的一个村庄进行了为时一月有余的田野调查,1965年在美国出版《一个乡村的报告》,1973年又出版《中国:继续的革命》,以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的方式记录了一个普通村庄在党领导下进行革命与生产的真实画面。韩丁和柯鲁克夫妇则以观察员身份直接参加根据地土改,分别成就了《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1]和《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2]两部纪实性作品。1991年美国学者弗里曼(Edward Freidman)等人出版了《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3],这是一部在十余年田野工作基础上多学科专家合撰的社会人类学著作。该书考察的重点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典型——河北衡水地区饶阳县五公村,但理论视觉和基本判断已与先前的成果迥异。未能直接进入内地乡村的一些海外学者则利用口述资料撰写了这方面的著述,代表性的有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生活》[4]等。此类著述最大的特点是在亲身经历或口述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对某一村庄的革命进程进行人类学式的描述,韩丁就觉得自己的作品“无论在风格上或内容上都很像一部记录影片”。[1](pp.4~5)但中国的村庄形形色色、千姿百态,数量极大,而“真实的”是否即是“全面的”?况且,尽管是亲身的经历和大量的田野工作,海外学者的关注点和了解到的面毕竟有限,其到底能做到多大程度“同情的理解”?这些都是后来研究者不断追问的问题。
三是近些年来出现的新著述。美籍华人黄宗智继“过密化”、“内卷化”理论后又从“表达与实践”的角度论述了从土改到“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农村历史,认为中国革命应视为1946-1976年的30年社会结构变迁,正是因表达与实践的距离和这种距离的不断加大才导致了“文革”如此的政治运动[5]。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6]借助自己家乡浙江北部联村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档案资料,试图以“外部冲击—村落传统互动模式”解释人民公社时代农村生活的实践逻辑。阎云翔的《私人社会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7]以自己生活和调查的黑龙江下岬村为个案,细密地讨论了一个普通村庄的个人及情感生活,是一部典型的乡村民族志著作。清华大学郭于华等人则注重对口述资料的搜集与研究,他们对陕北农村妇女在50年代的社会生活进行了相关探讨①。另外,近年来有关专题的论文不断发表。此类著述均以资料见长,或档案,或口述,或田野,或综合,尤其注重理论探讨,值得学界进一步地期待。
笔者此前将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时期推行互助组到20世纪80年代人民公社体制解体统称为“集体化时代”。此间约40年时间(各地不一),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前后相继,一路走来,从历史发展进程而言,这是一个难以分割的时代,更是一个难以忘却的时代。如上所述,几十年来,对“集体化时代”的研究已积累了一批成果,尤其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些新作品,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兴未艾。稍有遗憾的是,历史学科本身对此的研究仍不能尽如人意。
我们不能不承认,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框架更多的是研究上层领导或高层领导的思想与活动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尤其以党为主体的历史事件,甚至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成为党史和革命史的叙事主线,说到底是一条政治史的主线。经济、军事、文化在这种历史研究中只有附带的笔墨,基层农村社会尤其是亿万农民的生存环境、衣食住行、人际交往、精神心理状态、日常生活等,我们了解和研究得仍然十分有限。“自下而上”地研究这个时代的历史,就是要给基层农村和广大农民更多的关注,从农村和农民的角度、从“理解的同情”出发,站在地下看天上,站在地方看中央,上下贯通,左右相连,整体地全面地了解和认识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
从社会史的视角研究“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就是要从农村社会发展变迁的实际出发。1949年新中国成立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可以彪炳史册的事件,亦是重要的历史分期年份,或者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但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从农民的角度来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是一脉相承、前后关联、不可分割的一段历史时期,直到建国后中央召开的有关农业的四次会议仍称之为“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毛泽东更明确地说:“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8]互助组的目的是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道路,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正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转变发展而来,这是一个逻辑的存在,亦是一个历史的存在。与此同理,“文革”后期的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亦是在1958年开始后的人民公社体制内进行,只不过它另有了严重的政治化、运动化的色彩而已。社会史的研究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具体历史时段的划分亦要从它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出发。从“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出发,从农民和农村社会的变迁过程出发,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期间40年时间,就是党带领亿万农民走向和实现集体化的过程。
从“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研究“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就是要在研究上层的同时更多地关注下层农村社会的实态。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各级政府和基层农村社会有无争论,执行得又如何?汇总上来的数字、公布的数字是否真实,基层生产队是否真有“两本账”?除“两报一刊”类的主流话语外是否还有不同的声音,除“一呼百应”外是否还有抵触抱怨的“众声喧哗”?事实上,瞒产私分、小偷小摸、“偷奸耍滑”等无组织的、非系统的、个体的、长期的所谓“无声抵制”在在皆有,高王凌说这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反行为”[9],斯科特(James Scott)称之为“弱者的武器”[10]。在斯科特看来,这样的日常“抵制”才是农民最经常的手段,它是一种相对平静的、日常的、微妙的和间接的表达,地方官员往往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之,这种“去集体化”的过程往往首先从地方开始,从村落开始,而且是从村民开始。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斯科特的说法,正是由于这种日常的、长期的“无声抵制”,才导致人民公社制度在中国农村的解体,解体之后便有了性质不同的联产承包。历史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上层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层面,只有“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才能“取得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11]在高度政治化的“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社会和亿万农民仍有其自身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大势所趋的汹涌波涛底下仍会有潜流或暗流的涌动,全面地完整地看待历史,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诉求,亦是我们更加全面地完整地认识这个时代的基本出发点。
从社会史的视角研究“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需要我们对农村和农民的日常生活给予更多关注。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这些不同时段和事件本身都有不同程度的运动成分,政治化的色彩十分浓厚。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从现有著述中了解更多的是这些运动如何由发动、辩论、推进、高潮,再到另一个高潮,以及有关的会议、方针、路线、政策。农村社会的反应如何,农民的切身感受和日常生活怎样,往往多是轻描淡写或淹没无彰。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出发,农村人口的消长与流迁、耕地水利、婚姻生活或夫妻生活的状态、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的变化、宗族势力的消长、阶级成分划定、职业结构变化、集市贸易、副业生产、服饰的质料式样、食物的多寡与结构及其制作、收入分配及其形式、住房面积和结构、交通工具及利用、日常生活用具(包括家具、农具、照明等)、不同年龄段农村成员的文娱活动、戏曲小调、标语口号、基础教育、卫生医疗、鳏寡抚养、宗教信仰、自然灾害、社会治安、集团冲突、党团妇青民兵组织,以及工作队、巡逻队、斗争会、汇报会、学习班、外调上访等,都应从社会史的角度引起重视并加强研究。已有研究者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先分门别类地研究专题史,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综合地研究总体史,那么,大型的、权威的当代社会史便指日可待了”。[12]笔者不敢奢望那样的当代社会史在短时间可以出现,但这些基本的社会史研究内容,这些农村和农民的日常生活应当是社会史研究的出发点,也应该是全面的完整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的基础。
从“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研究“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还有一个基础的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基层农村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目前,除了各级的官方档案以外,最基层的农村的档案基本处于随意留放和散失的状态。随着近年来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旧房重建或再建不断加快,大批档案散失或干脆被当作废品送到了造纸厂,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已很难见到此类资料,抢救这批档案资料的工作显得十分迫切。然而,数量减少并不等于没有,只要肯下功夫,坚持不懈地到农村去调查搜集,仍可有所收获。近些年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全体师生不避寒暑,栉风沐雨,坚持“走向田野与社会”,广泛搜集散落在全省各地农村的基层档案,到目前为止已搜集到涉及全省各地100余个村的历史档案,总量当在数千万件,内容包括农村总账、分类账、分户账、日记账、工分账、社员往来账、实物收付账、现金收付账、实物明细账等等各类纷繁多样的账册;中央、省、地、市、县、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各级的文件、计划、总结、制度、方案、意见、报告、请示、指示、通知、讲话等各类文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教育、社会方方面面无所不包;大量阶级成分登记表、斗争会和批判会记录、匿名信、告状信、决心书、申请书、判决书、悔过书、契约、日记、笔记等等个人与家庭档案无奇不有;宣传画、宣传册、领袖像、红宝书、红色图书、各地不同时期各种小报、各类票证等也有一些收藏。黄宗智的一篇专题论文中曾说:“关于单个村庄的客观阶级结构的资料相当有限。现存关于每个村庄的阶级成分详细而准确的资料,多是在土改时收集的并在四清中被系统核实过的。然而这些资料并不容易获得”。“直到现在,我们能够掌握的确实可靠的资料只有几十个村庄的数据,这些数据主要来自于解放前完成的人类学实地调查”。[5]我想,黄先生若再来我中心访问(2006年6月初访)一定会修正自己的这一看法。
还要提及的是,目前流行采用口述记录的方法开展农村社会研究,应该说口述史是历史著述的一种重要形式,但在仍有文献资料存世的现时代将历史档案文献和口述结合起来不是更有利于事实的把握和客观的研究吗?
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20多年来,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将历史研究的聚焦点由精英人物和重大事件转移到普通民众和下层社会;将单纯的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自上而下”转换为“自下而上”的视角,从而构建整体的历史,正是社会史研究的魅力所在。遗憾的是,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领域,虽有研究者呼吁从社会史角度开展中国现当代史研究,但有分量的著述依然不多。社会史是一门“问题史学”,“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第三代年鉴派代表勒高夫指出,社会史“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从现时出发来探讨历史问题”。[13]现当代史距我们当今的现实社会最近,现实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与过往不久的中国历史紧密相连,把社会史研究引入中国现当代史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也是社会史研究者应当担负的一份社会责任。
注释:
①代表性的成果有郭玉华的《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标签: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论文; 农业集体化论文; 农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