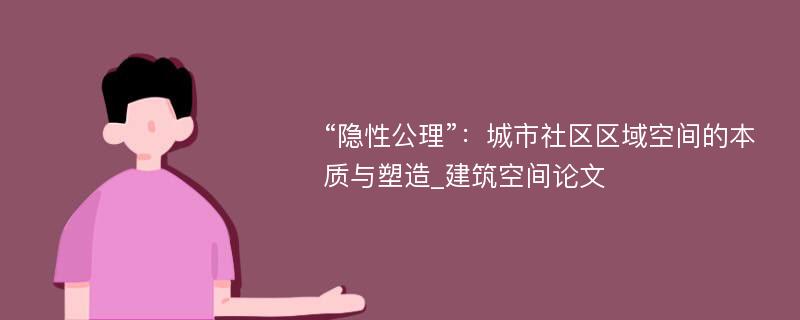
“隐蔽的公理”:城市社区地域空间的性质及其塑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理论文,地域论文,性质论文,城市论文,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2)03-0054-06
在城市化进程中,因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变革而催生的商品房社区不断增多,居民居住形态已发生彻底改变,社区地域空间被不断重塑,同一社区内因地域空间性质差异而带来不同的身份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社区地域空间性质上的差异所带来的新问题[1-3]已远非占主导地位的社区权力架构所能解释。
在当前城市社区研究中,尽管权力的组织结构分析途径依然是一条不可替代的主线、“明线”,但是,权力主体通过提供城市社区地域空间而进行的塑造与控制这一“实体性”途径的研究“暗线”,长期受到忽视。并且随着以房地产为代表的经济力量的兴起,资本已悄悄替代一贯以来的权力主体,成为社区地域空间新的塑造和控制主体。这一“暗线”上主体的转换及这一转换的影响更是少有关注。
基于此,本文着眼于权力与建筑(土地、规划、住宅)空间的关系,历时地分析国家权力通过对社区地域空间(住宅及其规划布局)的供给和塑造,形构社会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以达到控制和管理社区的目标;并且随着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资本替代权力逐渐取得社区塑造和控制的意识形态地位。这一转换改变了城市结构和基层社区的居住形态,给城市社区的治理带来深远影响。
一、建国初期国家权力塑造的“地理政治学”
长期以来,社区作为地域的物理维度是建筑学技术研究的对象,而在城市基层治理研究中缺乏足够的重视。自滕尼斯提出“社区”一词,尽管其定义莫衷一是,但其地域性仍不失为社区的最根本属性。社区的物质载体就是附着在地域上的建筑,所以有学者富有洞见地指出社区是“由建筑结合起来的社会空间”[4],中国的城市社区也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取不同的定义。在本文看来,城市社区主要限于居委会层次的辖区共同体,其中亦包括居住单元、居住小区和居住区,以及传统的街道、里巷、居民大院等次级基层自然社区。
近年来,“空间”的概念也为多个学科广泛使用,其含义也较为丰富。列斐伏尔不仅把空间当成是地理空间和地缘空间,也当成是建筑空间,以及日常生活的制度空间。[5]Castells强调了空间被社会关系所建构、所运作、所实践,并指出所有的“空间理论”是社会的理论。[6]不难发现,空间的社会属性是诸多研究者极为关注的一项内容,而空间原本的自然的、地理的属性则被视为客观的存在而遭到忽视。也因之,我们才屡屡见到“社会空间”、“城市空间”、“文化空间”的提法。本文将地域空间定义为一个实在的物理空间,它包括地理学上的建筑物(住宅)等物质实体。虽然吉登斯提出城墙是权力“集装器”的物理形态[7],Bray也指出“是城墙产生的空间。而非城墙本身,才具有分析性意义”[8]的重要性,然而,是谁产生了城墙,它是如何产生的,这显然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空间不是纯洁的,不是非政治的。赋予内容而获得价值的“容器”这一空间哲学被列斐伏尔称为“隐蔽的公理”[9]44,理应受到更多的研究关注。通过探究建筑形成所依赖的权力规划、意识形态指导及其演变进程,或许才能更清楚建筑被赋予的国家信仰的表达,也才能真正理解建筑“真实地影响并控制着世人的世界观和社会行为方式”[10]170;205的意义。
城市,自新中国建立始,就获得了它在整个国家的独特地位。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11]1421从此,城市担当起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领导角色。新生政权针对当时城市土地所有权呈现出多样形态,对包括官僚资本所有、外国资本家、大地主所有、民族资本所有、城市个体劳动者及城市居民所有的私人所有权城市土地,采取“没收”、“征收”、“征用”、“赎买”等方式,初步实现了土地的部分国有(占不到一半)。1956年始,又通过对城市私有出租房屋的社会主义改造,最终完成了对城市土地私有制的改造。如同建立其权力组织结构一样,新政权以它一贯的革命彻底精神,从整体上基本解决了城市土地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问题,奠定了城市建设的前提和基础,由此掀开了社会主义城市建设高潮。
受制于社会主义短缺经济的根本制约,新政权在建国之初采取了“先生产,后消费”的城市建设规划原则。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只有将城市中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将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11]1428基于城市的生产性质,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必须是全国的大工业基地。波兰领导人贝鲁特曾在一个题为“重建华沙的六年计划”报告中曾明确地说,“人民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用多种办法来恢复首都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12]。以此,首都北京的功能定位,“不仅要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要成为工业、技术和科学的主要基地”[13],要增加工人阶级在首都总人口中的比重[14]。这些都毫无例外地表明了无产阶级政权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改造社会的决心和信心。同时,在意识形态上,由于建国初期我们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与编制原则都基本仿效苏联的做法。这都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住宅规划带来重大影响,无论是“邻里单位”,还是“周边式街坊”。
“邻里单位”(Neighborhood Unit)是19世纪20年代由美国人佩里提出的规划理念,主张以城市干道包围的街区作为集合居住的单位。邻里单位中除了住房之外,还应配建公共服务设施和户外休闲空间,在不穿越城市交通干道的情况下满足儿童、老人日常的就学、外出需要。受民国时期住宅建筑规划的影响,“邻里单位”思想自三年恢复时期起就已经采用,如上海曹阳新村(1951年—1953年)的建设。曹阳新村住宅以行列式布局为主。分弄—坊—区三级布置。每个坊有自己的医疗点、幼儿园、学校,易于到达;区的中心位置建有商店、邮局、电影院以及文化活动中心等,周边配有商业设施。道路分级设置,人车混行。住宅区内道路分级布置,限制外部交通的穿越。内部配备相应的公共设施和绿地,为居民提供必要的生活服务。住宅讲究日照通风,空间秩序井然[1]76。在北京,建于1951年的复兴门外小区也是“邻里单位”规划的代表之作。
正如萨迪奇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新建筑是为了巩固我们的新政权”[10]39。以曹阳新村社区为代表的“邻里单位”住宅建筑,蕴含着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共同生活为前提,组织共享的服务设施和生活空间,并对组成单元进行等级化的管理;同时,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工农之间平等关系的认知,住宅组群分布于绿色背景之下,构成与工业网点紧密关联的工人住宅区,体现了社会主义“新人”在国家的主人翁地位。
随着苏联对中国援助的加大,1953年引进苏联的“街坊型住宅区”(superblock)规划理念。这一规划由若干周边式、双周边式小住宅小街坊组成、内部设置商店、托幼、学校和公共绿地,如北京百万庄住宅区和酒仙桥、三里河住宅区,以及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活区等。这一规划强调在住房群体组合中应用轴线对称的布置方式,突出院落的空间围合和整体形式。这种严谨的布局意在指出,轴线对称构图所产生的均衡感和庄严感,有助于居民——尤其是刚刚当家做主的工人阶级建立信心和尊严。苏联规划者也声称,“街坊型住宅”可以用来抗衡西方理念的“邻里单位”,因为不同于“邻里单位”的隔离于郊区,“街坊型住宅”可称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且它对城市建设来说是最经济的规划[15]。
时隔不久,随着新政权不断强调其工业化的发展重点,以及中国经济的短缺现实,加之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街坊型住宅区”规划思想遭到抛弃。1957年,又从苏联引入“小区”规划理念。
“小区”(Microdistrict)是一个面积在40hm[2]~60hm[2],人口为1万~1.5万居民的大型居住建筑群。服务半径在300米~400米范围的四至五个“小区”构成一个居民区。“小区”的基本空间组织结构与“邻里单位”大体一致。不过,“邻里单位”是以基于安全出行方便生活为出发点,在规模上具有一定的弹性,而“小区”则兼具服务和管理的双重使命,具有明确的等级与规模含义。[1]80
“建筑不仅仅是功能性的满足和审美问题,它已经成为一种治国的艺术。它可以用暗喻的方式表达出一个国家或其领导人的雄心大志。”[10]85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政治运动所引起的住宅区规划理念,可能是对上面这句话作出的最完美的诠释。
全能主义的国家政权在现代化阶段性成就的刺激下,极易繁衍出超越当时时代的激情理念,并以此动员全民奔赴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目标。1958年,中央提出经济建设“超英赶美”的口号,并于8月决定在农村展开“人民公社”运动。此一运动源于满足工业建设对农业资源的巨大需求,同时还被赋予共产主义色彩,成为消灭城乡,通往社会大同、按需分配、平等自由等理想境界的必由之路,将“重生产,轻生活”的发展思路推向极致。
此一时期住宅变化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功能上增加了生产功能。它强调了城市人民公社是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是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政社合一的组织。这与早期“邻里单位”理念强调功能分区和纯化住宅内部功能的原则相互对立。另外,它还强调日常生活的集体化和军事化。城市人民公社要求居民集体劳动、集体生活、居民统一到食堂就餐,各户不再单独设置厨房和餐厅。
在这一运动中,象征秩序和效率的视角符号被广泛采用。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们努力“协同政府的力量影响人们的工作习惯、生活方式、道德行为与价值观”[16],渴望用科学的规划和现代主义美学创造出一目了然的理性秩序。而真实的结果却是,国家权力在基层的进一步介入和对农村生活的控制,而农民物质富足的现代生活希冀落空。激进的空间革命最终给全国带来了一场深刻的现代性乌托邦化破灭的“欲望的教育”[17]。
二、改革时代资本力量配置下的城市地域空间
随着改革时代的到来,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政策,经济体制开启了由传统计划经济的生产模式向市场经济的生产模式的转型,也从根本上要求厘清政府和社会、市场、企业的关系。在这一条件下,单位体制逐渐削弱,计划经济下的单位已经逐步转型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这就直接意味着过去由单位主导集体供给并取得的管理群众日常生活的权力已完全剥离。同时,通过权力关系和企业剩余提取来促进住宅消费供给也已经随体制改革而慢慢消失。城市社区地域空间的塑造动力发生了根本的转换,空间的生产样态也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布局。
当经济规律逐渐上升为住房领域的主导因素,住宅的建设标准、社区的开发模式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运营等都不得不面临市场的竞争和资本的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住宅规划思想不再像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样受国外舶来理念的深刻影响,逐渐独立并趋于理性,并不断由技术层面的修补演变为理论体系的变革,包括“以人为本”的回归,“社区规划”,“可持续发展”等[1]84-85。在具体理念上,社区规划布局、公共绿地与公共服务设施的设置不再拘泥于居住区、小区、组团三级结构,只做总指标控制,灵活合理安排;配套商业设施的布局既要考虑本区居民使用方便,为社会服务,也要考虑经营效益,故由内向型布局向外向型转变;商业服务设施的内容设置不再定得过细。而按市场发展需要由开发商灵活安排,规划审批只掌控基本使用功能和指标总额控制[18]。这些规划理念,尽管均满足和契合改革时代国家“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目标,但是由于住房市场化及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变革所带来的以资本为代表的房地产开发商的强势进入,使得社区地域空间的塑造动力由传统的权力意识形态为资本意识形态所取代。
市场化的联动改革直接促成了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表现在住房分配体制上,由原来的行政手段、福利性质、实物分配制度,转变为货币分配制度;在住房供应体系上,建立了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的、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供应体系,以及以高收入家庭为对象的商品房供应体系这一双轨制的住房供应体系。与住房制度改革相配合的是,城市土地使用制度也经历了从原来无偿、无限期、无流动的土地使用制度转变为有偿、有限期、可流转的土地使用制度的性质转变,并于2001年提出商业房地产开发用地以招标、拍卖方式提供。住房和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直接催生了房地产开发企业及其发展。自此,以“利益至上”价值观为性质的资本及其所建构的意识形态,成为重塑城市社区地域空间的主导性力量,对社区地域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
与权力意识形态对社区地域空间规划理念施加的塑造不同的是,资本意识形态通过对城市土地使用的开发控制,在以“土地/空间效益”为目标的经济开发型模式支配下[19],形成土地级差地租,导致城市社会空间分异,进而实现对传统社会主义社区地域空间的“重创”。
改革时代的城市逐渐抛弃其生产性功能,重新取得了消费性功能的地位,使得城市空间的拓展充满消费主义的生成逻辑[20],并形成了消费空间与生产空间的分化。在这一背景下,受GDP的政绩考核和过度追求城市形象的驱动,由发展型政府推动的城市化进程开始了以房地产商为主导的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和改造运动。在运动中,城市规划对城市空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危旧房改造、绿化、住房容积率、城市功能分区等方面。不过,由于规划主体和开发主体不同,追求目标亦存明显差异,虽然行政规划设立种种限制,但开发“例外”却常常发生[21]。其结果是,一旦开发商启动项目开发,就会常常突破规划限制,造成城市建设均衡布局的破坏,而开发商对城市居住空间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占主导地位。
得益于市场化的住宅开发建设,开发商通过城市内城改造项目,大举拆迁,平整商业用地。在上海,仅1990~2005年的短短15年间,中心城内旧房拆除比例就达58.7%,动迁居民近100万户。同时在内城和近郊新建约1亿平方米的住宅。通过一拆一建,开发资本消灭了旧有城市社区地域空间的传统布局及附着其间的权力塑造积累,割断了社区的社会关联①和邻里交往:相应地建立起以资本逐利逻辑为导向的新的社区地域结构。
资本的本性驱使着新建空间的安排遵循级差地租效益最大化的原则。也就是说,在假设单中心的城市空间里,土地和住房的价格大多随着与城市中心城区距离的增加而减少。这一变化与区位对应的便利性直接相关。越接近城市中心,各种便利条件越集中,土地的价格及房价也就越高,形成单中心圈层式空间地域布置格局。这一区位特征直接决定了城市中心区、城市边缘区、城市郊区的城市总体空间划分,形成了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市中心与郊区呈现出形态上的等级关系[22]。在这种情况下。较富裕的居民阶层进入市区基础条件良好的中、高档商品住宅社区,低收入群体不断因旧城更新改造而被拆迁至地价更低的社区,总的趋势是离市中心越来越远。他们原来居住的社区在房地产资本操作下被中、高档公寓住宅社区所替代,原有的物质空间形态和社会空间形态被一同更新。
资本意识形态所生产的地域空间的这一侵入和演替过程,表现在阶级结构上,就是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阶级分异。在社区地域空间的演进中,中国也出现了类似于西方的“中产阶级化运动”(gentrification)。这一运动指出,在城市化过程中,伴随着城市中心区更新所出现的社会空间的演变,城市中产阶级及以上阶层取代低收入者阶层而进入内城(城市中心区)。相关研究也表明,中产阶级化意味着一个中上阶级家庭迁入贫困工人阶级邻里的过程,并最终取代工人阶级居民,由此改变了邻里的社会特征。[23]伴随着旧城改造,城市中心的物质环境和生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良好的区位条件、完善的基础设施、接近城市服务中心等均能够满足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需要和追求;因而,在利益的驱动下,房地产开发商为了迎合上层阶级的市场需求,往往在环境优越,接近社会服务、休闲设施的地点建造高级住宅社区。在中心城区旧城改造的过程中,房地产商把原有的棚户、简屋推倒建成高档楼盘,使得中心城区由穷人聚居区成为富人聚居区,如北京高价位的豪华住宅,大多集中在CBD和内城。与中产阶级从城市各个地区向城市中心集聚相反的一个进程是,低收入阶层在纯市场原则和土地区位地租的过滤下被迫迁出。这一进一出的阶层地域流动,不是平静自然的演替。强势阶层入驻城市中心,而“小市民”则带着囊中羞涩的无奈逼走市郊。旧城高贵化和低收入居民郊区化的城市规划安排所造成的居住分异,其实质是“强势的资本、权力”和“弱势的民权”空间博弈行为所致。[24]477
值得指出的是,以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利益)型”城市开发从一开始就暴露出旧城改造中的拆迁及安置等诸多重大问题。并不断引发危及社会稳定的拆迁血案。当前,在旧区改造动迁过程中,作为公权力的地方政府,其公共性明显异化,自利性越发加深。公权力已经逐渐为资本所侵蚀而资本化。表现在内城改造中,关切居民根本利益的城市规划“关门决策”,缺乏居民的公共参与和表达,以至于城市规划成为个别官员追求政绩而随意圈地进行“权力造城”的工具。而在居民安置小区的建设上,屡屡出现小区规划不合理,建筑质量低下等恶劣问题,形成动迁居民的利益剥夺现象。由政府负责的保障房建设,也出现挪用资金以及严重质量问题。另一方面,资本的力量正在通过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向城市的公共利益进犯、侵蚀,动迁居民的抗争行动也不断出现。城市开发的空间公平问题正在经受严峻的挑战。
时下,当资本意识形态以它特有的力量渗入并“打造”城市社区地域空间时,我们看到的社区住宅楼盘宣传规划均是以商业利益导向为主,如宣扬海外风情想象的“拉丁风情小镇”、“意式官邸”、“世袭制美式群岛生活圈”等,又如制造炫富迷思的“尊贵”、“都市精英”、“豪门名仕”等,再如策划时髦炒作的“低碳”、“负氧离子”等,以及强调“卖点”的学区、交通、绿地、景致等等。这些商业化宣传口号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地域空间的等级塑造以及相应的贫富分化和对立,使得这些“视角的专制”[9]124显得分外刺目。
三、从权力主宰到资本主导的动力置换:简要的回顾与讨论
新生政权的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进程总是以意识形态为先导,通过组织化力量和对地域空间的控制而展开的。在城市成为政权的行政中心并被赋予生产中心地位之后,体现工人阶级领导地位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意识形态,以铲除剥削政权的根基为信念,对旧有的城市格局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式改造。从“邻里单位”到“街坊式住宅区”、“小区”,再到“人民公社”式住宅,城市社区地域空间受到来自国家意识形态的持续塑造。社区规划和建筑不再仅仅是功能主义的技术手段创造,同时也承担着国家身份、信仰和意志最直白的表达。政权通过引入不同的规划理念,溶入民族自豪感、集体主义、主人翁地位、平等、忠诚等丰富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意涵,以社区住宅的日常方式,实现对“社会主义新人”的人格教化。
在这一动力机制下,城市社区地域空间的结构和性质表现出明显的特征。整体上,社区地域空间呈现与“单位”(work unit)紧密伴生、集聚的结构性特点,且具有平等化趋向。社区地域具有极强的国家动员和行政管控特征,而自主自治性较弱;社区空间内部具有强社区记忆②和社区关联度密织的性状;社区空间的居民阶层均质化分布,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领导”地位;社区日常生活秩序的支配力量来自国家权力。
改革时代的社区地域空间完成了对权力意识形态的动力置换。资本,以它贪婪逐利的凶猛力量,摧枯拉朽,主导了对城市社区地域空间的再造。正统的权力意识形态已经为“发展型政府”所淡化,更者,“发展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已为资本所“捕获”,丧失其公共立场,沦为商业附庸,堕落为逐利型官僚集团。以市民参与为主体、以社会建设为目标的社会开发型模式,因为民权的弱势而被以土地/空间效益为目标的经济开发型模式所取代。社区规划不再有国家意识形态的意志贯彻,而充塞着开发商楼盘销售宣扬异域风格及趋富尊贵的商业化的卖点炒作。住宅取得其交换价值,不动产被动产化,被卷入到金钱和资本交换的洪流中,空间成为稀有物种,疯狂投机成为可能,而社会生活日益堕落[9]133。通过拆迁运动,资本意识形态像最初的权力意识形态一样,再次荡平了城市社区地域空间,取得了社区塑造权;通过开发建设,利用级差地租,不仅重构了社区的地域空间分异,而且重构了空间分异上的阶层分异,出现了“都市的半殖民主义”[9]62。
资本意识形态逻辑下的城市社区地域马赛克(mosaic),呈现出单体均质而整体异质的空间结构[24]452,并且包绕着城市商业/行政中心圈层式展开;社区地域空间具有明显的等级化趋向。由于住宅的获得是基于市场化交易,个人利益得到了强调和重视,社区地域的自主性明显增强③,而国家权力的涉入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剧烈的拆迁运动撕毁了社区刚建立起来的地域传统,整个城市如同一座新城,社区空间内部的社区记忆被撕裂,密织的社区关联被拆解而离散化。社区地域的居民阶层分异明显,由中心向外围呈圈型分布,处于中心的中产阶级取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主导权位。支撑社区日常生活秩序的主导力量由权力转向了财富。
四、结语
在当前的社区研究题域中,无论是宏观的结构分析,抑或中观的制度分析,还是微观的参与式“深描”,均不同程度地视社区地域的物理空间为一个实然存在,并且严重忽视对这一地理存在的性质探析。事实上,如果不从地域空间的基质开始,那就等于漏掉了社区研究中内在天性的一个基本方面。正是这一地域空间,承载着各种力量、情感的交互作用,阐发着社区作为社区的真正意义。因此,历时观察、探究城市社区地域空间的不同塑造力量及其性质的转换,挖出这一“隐蔽的公理”,增补了社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理论不足,为确立社区研究的逻辑起点提出了切实的论证。
注释:
①社会关联指人们在共同活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各样的联系。它侧重社区内人与人之间变动的具体关系,关注社区内的共同行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社区秩序的影响。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02(3):125.
②社区记忆是指:社区历史和传统对社区现实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方式及程度。贺雪峰.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权力结构[J].社会学研究,2001(2):69.
③另一方面,不少业主均是通过按揭贷款购房,过重的房贷压力强化了业主职业上的雇佣依附关系,在压制和削弱社会活跃力的同时,也将这一惰性传递到社区,使社区居民自治文化呈现出脆弱性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