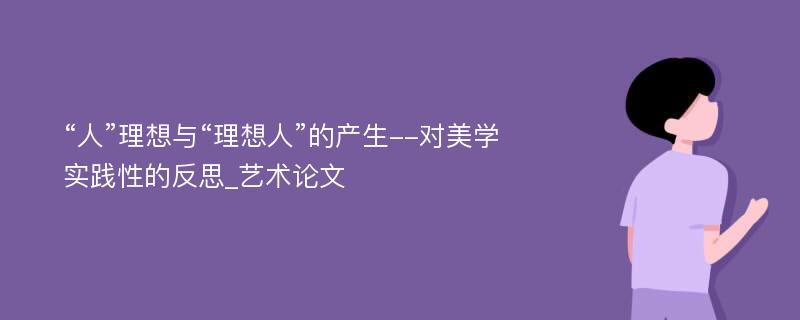
“人”的理想和“理想人”的生产——审美的实践性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0)04-0008-05
审美为什么?——娱情?教化?宣传?迄今为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无非是把审美作为一种安慰剂或者一种辅助性的工具,这些回答或许可以解释审美对个体的意义,却没有把问题上升到“人类”的高度——人类的审美活动为人的发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如果审美活动经得起这样的追问,那么我们就真正把审美作为现实的人类活动与必要的人类活动,而不是生活的点缀来看待。
“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1](P88)问题是,人按照什么样的蓝图改造人,人把人改造成什么样子,也就是问,人的理想是什么?这似乎是个教育学的问题,不,这是一切人文学科的核心的问题——设定人的理想并追索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这关系到的是人的生产及其再生产。
人的生产在其最外在的意义上,是人的繁衍。“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2](P2)种的繁衍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本身是一个社会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人化”是人的繁衍的核心,人的人化不单单是人从出生开始的被社会化的过程,而且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贯通于人的自然繁衍的历史线条中。这一“人化”不单单是人的内在自然的人化,而是人类作为一个族群对自身存在的理想化,尽管这一理想有其时代性,然而这一理想的确立及其实现手段却具有共性,那就是审美。
一、审美在人的生产中的理想性作用
“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P80)把自然的关系留给自然,而生命之生产的社会关系却是我们必须给予控制的。人生产着人,暂且不考虑把人作为商品的生产,把人作为劳动力的生产,这不是生产人,而是否定人,扭曲人,这是需要被抛弃的异化生产。而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产与再生产”,是生产出真正“人化”的“人”,是人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美”作为理想引导着这一生产过程,换句话说,人对人自身的审美理想推动着人的进步。这个审美理想不仅仅是人的外在形态,而是人的整体,是人之为人的理想状态,而人的理想状态既是肉体性的,也是精神性的。
人对于自身的理想性设定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在人类的真正的自由来临之前,即经济与政治上的自由充分实现之前,我们可以想到的理想的人是什么样子?西方人对理想化的人的设定最先见于古希腊。伯利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演说中的一段话,最先给出了关于理想人格的回答:“我们爱好美的东西,但没有因此而至于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没有因此而至于柔弱。我们把财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但没有把它当作可以自己夸耀的东西。至于贫穷,谁也不必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不择手段以避免贫穷。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自己的事务,而且是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自己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这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2](P132)不,这还不是全部,希腊人热爱生活从而热爱身体,他们追求内在心灵的充实并不放弃外在肉体的强健,他们在造型艺术中给出的人体不是人的理想而是人的现实。想一想诗人戏剧家索福克勒斯阿波罗般伟岸而健美的身躯,想一想伯利克利诗人般的气质和政治家的雄辩从一个运动员的身躯中流溢出来,想一想柏拉图以哲学家的深邃隐藏在拳击手般的身躯内,那“内在的充实”与“外在的健”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他们对于理想的人最初的建构,而这也是希腊艺术之“美”的原因。这一“美”呈现在他们的艺术中,成为全民的理想,从而落实在他们的教育中,成为具体的人的成长的目标,希腊人的艺术就是希腊人的理想,也曾成为希腊人的现实。他们的健康的审美观使得他们知道应当向人要求什么,并把人引向什么状态。他们追求内在的充实,而不忘外在的健美。希腊人的艺术使我们知道了什么才是理想的人的形态,什么是畸形。
人们欣赏摇摇摆摆的小脚女人的时候,就希望把女人塑成这个样子,这只是极端地说明审美如何引导着人对自身的塑造,而这只是病态的审美对于人的否定的一个案例。真正重要的是,必须确立对于自然、对于人的属人的审美观。这一审美观应当遵循这样的原则:它必须尊重人的自然生产;它必须受制于人的自由与人的解放;它必须以人的自我肯定为前提。确立这样的审美观就是美学的任务,尽管“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被扭曲过,它被滥用过,它被商品化过;尽管人类的审美趣味千奇百怪,可是作为人对人自身的理想性的设定,美学必须坚守这样的立场:“为人”的审美和“推动人发展”的审美。一切美学思想只有落实到这一点的时候,才是真正“属人”的审美,而不是动物性的或者异化了的审美。这种美学是人的实践的一部分,是人的存在与生存的指引。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学不单单研究审美活动的诸环节,还要确立实践的目的和人的“存在—生存”的理想。
希腊人对于“美”的宗教般的热爱和真正属人的审美观使得他们创造出了堪为人类范型的人的形象,从而也创造了一个美学术语——“希腊人”。对于后世的人来说,“希腊人”不是社会历史的现实,而是社会历史的应当。当我们欣赏着希腊人的艺术,审视着那些“美的”人之时,我们的理想就确立了,而这一理想推动我们去改变现实。在19世纪审美成为推动人的生产的进步力量,并影响20世纪我们对于人的教育。这一过程最先由德国美学家席勒开启。在席勒看来,每一个希腊人都具有独立的个性,他们多方面的性格特征都表现为一种完美的整体。“他们既有丰满的形式,又有丰富的内容;既能从事哲学思考,又能创作艺术;既温柔又充满力量。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想象的青年性和理想的成年性结合成的一种完美的人性。”[3](P49)因此,如何在更高的程度上复现“希腊人”,实现身体与精神两方面和谐发展的完美人性,始终是西方美学史上众多美学家共同追寻的目标,也是审美的人类学意义。“我们可以说,就其天赋和素质而言,在每一个个体的人的身上都具有纯粹理想人的成分,在各种变化中与这种不变的统一体保持和谐,这是他生存的伟大使命。”[3](PP.42—43)审美的任务就在于要不断培植、强化和拓展人身上这种“纯粹理想人的成分”,使现实的人不断上升为理想的人,从而实现人的性格的完整性和人性的完满性,而这一上升不是靠一代人的教育完成的,而是与人的自然繁衍的永不停息的过程相始终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审美为人的生产确立蓝图。
这样审美就不是娱情或者教化意义上的审美,而是人的自我完善,而这一自我完善必将引导人去控制关于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这就是为什么审美与教育,与体育,与生育在19世纪末融合在一起,成为人的生产,人的自我完善的必然过程。
另外一个问题是,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人?“对人的需求必然调节人的生产,正如其他任何商品生产的情况一样”[4](P7)。这首先是一个政治与经济问题,但当社会对人的需要不再是把人当作工具,当作物来看,而是当作“人”来看时,人的理想,特别是对人的审美理想就成了调节人的生产的“对人的需求”,这样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二、审美活动在人的生产中的手段性作用
问题是,“理想性的人”怎么实现?这应当是个社会历史问题,最终是由人的社会生产决定的,但审美活动却在人的理想的每一个阶段起到了推动性作用。它决定着教育的手段与理想,并且引领着人的文化活动,从而指引着人的生产。
希腊人的教育有其强烈的功利性,他们需要合格的战士和公民,而二者在他们的社会中是统一体,这构成了他们关于人的理想,他们以审美的方式实现这一理想,而以艺术的方式强化这一理想,使这一理想成为希腊一切文化活动的指归。“希腊人”是这样被“生产”出来的——与审美相始终的审美教育与审美活动。在当时由私人开办并收取学费的初级文法学校和琴弦学校中,诗歌与音乐都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即使当学生十二三岁升入体操学校,集中进行竞走、跳高、角力、掷铁饼、投标枪等军事与竞技活动的专门训练时,音乐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他们在进行各项体操训练时,常常辅之以箫笛琴弦各种乐器的伴奏。在这些活动中,他们追求身体的美并实现了,所以希腊人把自己的主要时间花在运动场;他们追求内在的充实,所以他们参与各种艺术活动。
审美活动在希腊时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诗歌、音乐、舞蹈、戏剧、体育竞技构成了他们社会生活和文化活动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在雅典,文学和音乐的教育是和公共的宗教节日联系着的。每一年中,这种节日大约有六十次。一些主要的节日不但以游行队伍、体育比赛和竞技,而且还以公众合唱和戏剧表演来庆祝。每一节日都有新的剧本上演,作家们也在热烈竞争之中。”[5](PP.151—152)由于在建筑、雕刻和绘画方面许多的杰作被创造出并呈现出来,雅典变成了一个美术博物馆,而卫城是其中心。
这样一种“审美人”的理想决定着希腊人对自己的要求,并贯彻到他们的文化的一切方面,成为他们关于“人的生产”的“尺度”。这个尺度从现实需求上升为审美理想,并从审美理想成为文化的目的,进而以审美的方式成为现实。
那么审美为什么能够实现对人的生产的指引?这关乎到对人的理解,进而在理解的基础上建构人的理想。19世纪的音乐家理查·瓦格纳给出过一个比美学家席勒更具体的回答。这个回答源自时代对人的理想性设定——“完整的人”,进而回答这个“完整的人”是如何实现的。
完整的人源自时代对人的需要,这一需要首先在席勒审美教育思想中被提取出来,这种完整性就是指理性与感性的统一状态。后来费尔巴哈说“……我要把人,就是说完整无缺的人拥抱在我的怀里”[6](P223),费尔巴哈所说的完整无缺的人被瓦格纳理解为“感性”得到全面发展的人,在瓦格纳的观念中,人首先是感性的人,是感官之感受的综合,所以瓦格纳像费尔巴哈一样把人的感性作为最真实之存在,他认为“第一位的,一切现存的和可以想象有东西的起点和基础,是真正的感性的存在”[7](PP.48—49),认为“真正被了解了的东西,只不过是通过思维成为手摸得到、眼看得见的对象的实实在在而又诉诸感官的存在”[7](P46),所以艺术首先应当是直接诉诸感官的。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人有触觉,听觉,视觉,人有情感,有思想,如果艺术直接诉诸人的感官,那么应当或者说最好是什么感官呢?按照费尔巴哈所说的“完整无缺的人”,瓦格纳认为艺术也应当针对“整体的人”,这样的艺术才是最高的也是未来的艺术,这样一种艺术的榜样是希腊的悲剧。
瓦格纳认为人是肉体的人、情感的人和理智的人的综合,真正的艺术应当把这三者统一起来。瓦格纳把肉体的人理解为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身体来感受的人,从而艺术就可以分为针对眼睛的视觉艺术,针对听觉的听觉艺术,由感官得来的感受必定会在肉体上直接表达出来,这就是舞蹈艺术。这时由情感的人把这些引导向理智的人,就产生了诗——理智的艺术。如果把这些都结合起来,就有了瓦格纳的“整体艺术”。让我们仍举希腊的例子来说明,在希腊悲剧中,有舞台的搭建与布景,这需要雕塑艺术与绘画艺术;有音乐与歌唱,这就是听觉艺术;有演员的形体动作,这就有了舞蹈艺术,而这些都要为悲剧的内容,也就是诗服务,这就是理智的艺术。而这一切会对观众产生一种综合性的影响,会让他们的各种能力结为一个整体,让他们的各种能力得到均衡的发展,并在这种整体感中获得自由感,从而成为健与美的完整的人。正是由于希腊艺术能够实现这个目的,所以,诸种艺术对于希腊人而言是绝对需要。为什么整体人的就是自由的呢?让我们看看瓦格纳的下面这段话:
“人的每一种个别的能力都是一种受到限制的能力;可是他那联合起来的、彼此了解的、彼此互助的,也就是他那彼此相爱的各种能力却是那知足的、不受限制的、一般人性的能力。因此人的每一种艺术性的能力也有它的天然限制:因为人不是只有一种感官而是根本就有多种感官;而一种能力又只能由一种特定的感官导引出来;由于这样一种感官的局限,这一种能力也因此有它的局限。而各种个别感官的界限,也就是它们互相之间的接触点在各点之间互相交流的时候,各点也可以彼此了解。正因为有这样的接触,各点从它导引出来的能力也就能同样彼此了解;它们的局限因此转化为了解;可是能够彼此真正了解的,只有相爱者才行。所谓爱就是:承认别人同时也要认识自己;通过爱的认识是自由,人的各种能力的自由则是——全能。”[7](PP.61—62)
整体的人由于全能而自由,那么相应于这种整体的人,各种艺术就可以通过结为一体而成为自由的艺术,成为共有的、不受限制的艺术本身,这就是瓦格纳所梦想建立的“整体艺术”。它是对所有艺术门类的综合,是为“整体的人”而创造出来的艺术。艺术在这里创造着完整的人,并且使自己成为“完整的艺术”。
瓦格纳的观点是审美主义的鲜明代表,却揭示了我们对于艺术的需要之所以“绝对需要”的原因。黑格尔认为,艺术的最高使命在于“成为认识和表现神圣性、人类的最深刻的趣旨以及心灵的最深广的真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8](P10),而当艺术不再成为这种手段的时候,它就不再是绝对需要了。不,黑格尔错了,人类需要艺术不是为了让它成为神性与真理的舞台,而是对自己的完善与建构,是为自己的生产和再生产。审美过去实现这一使命,现在和将来仍然需要承担这一使命,它是我们完成自我完善基本手段。这就是为什么人类需要审美,人类需要艺术。
三、人的生产的理想性目的:全面发展的人与审美化生存
人们不断的繁衍不仅仅是受本能驱使的自然行为,人的生产同样是社会化的生产,它遵循着进化的原则,而又受到社会理想的制约,人类自我生产的过程,就是人类朝一个理想性目标不断前进的过程。在一个人由于分工而被异化的时代,人的自我生产(繁衍)被一个理想牵引着:人总会赢得自由。而人的社会生产(商品)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动力。那么实现了的人是怎样的?他们如何生存?这又是一个审美问题。
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产生畸形,在异化劳动的时候人类所能设想的最理想的人的形态就是全面发展的人。这个观念体现着现代与未来社会对人的需要,而这一需要将改造人类的教育,改造人类的文化生活,最终推动社会为生产出全面发展的人而准备条件。
“全面发展的人”这一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294)恩格斯在1894年1月9日致卡内帕的信中,应《新世纪》周刊关于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请求,摘下了这句话作为答复,并且说,“除此之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9](P649)。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更明确地把“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作为“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1](P243)。马克思认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10](P130)这是人类的理想,而这个理想的提出源自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历史分析。
马克思关于个人全面发展的理念是在他的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框架内提出来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这样写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这个自由个性的出现,一方面是社会历史问题,另一方面则需要审美去推动,去建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11](P95)因此审美活动实际上是一个生产主体的活动,它可以贯彻到人的繁衍的每一个环节中,从生命体在母体中的育成,到个体所接受的教育与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再到个体的生活方式,再到母体与父体的优化。而就人的社会存在而言,每一个自由个性的出现,都不仅仅是经济与政治的结果,而是审美开化与艺术启迪的结果。没有审美对于人的建构的参与,人类将囿于功利活动而无法形成真正的自由个性,而由自由个性所选择的生活,人类经验与理性所能提供的,都是艺术化的,审美化的生活。
一旦分工被扬弃了,真正自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P85)这就是真正自由的生活,人不再被限制在社会生产的某一个岗位上,人不会再被分工所异化。马克思恩格斯还专门以艺术为例说明:“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中,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艺术家屈从于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的现象无论如何会消失掉,个人局限于某一艺术领域,仅仅当一个画家、雕刻家等等,因而只用他的活动的一种称呼就足以表明他的职业发展的局限性和他对分工的依赖这一现象,也会消失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12](P460)。这就意味着,“完整的人”的生活是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生活,是瓦格纳所说的整体性的生活,是人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与实现了的自然主义。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活动中,只有在审美活动中人类曾经体验过这样的自由,无所拘束的自由。正是这一经验推动着我们对于人的生存的理想状态作出以上的设想。
这个状态曾经是希腊人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是借艺术活动与审美文化实现的;这个状态的理论构想源自艺术家与美学家的理想性设定,而这一设定最终成为整个社会历史的理想。因此,以全部社会力量培育出全面的人、完整的人,这是人类自我生产的理想,而这一理想在人类的审美活动中间接地实现着,并在人类的审美理想中现实地指引着人类实践。
从这个意义上说,审美是人类的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它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它指引着人的生产,指引着人类文化生活的方向,它不给出具体的步骤,但却给出理想与蓝图,审美是人类自我完善与自我进化的社会实践,也是人类存在的理想状态。这就是实践的生存论一存在论视域中审美的超越性意义或者终极意识。
[收稿日期]2009-0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