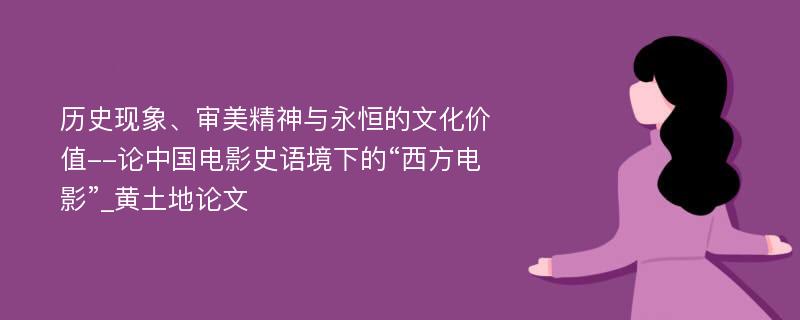
历史现象、美学精神与恒久性文化价值——论影史脉络中的中国“西部电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脉络论文,美学论文,中国论文,性文化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1)02-0023-09
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下,各种文艺思潮纷纷开始涌动。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先生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最早明确提出了拍摄中国“西部电影”的理论倡导。继钟惦棐先生之后,国内诸多学者对西部电影现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众多富于建设性的观点和评价,从而为西部电影的繁荣在理论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伴随钟惦棐先生西部电影理论的提出,西部电影的创作实践随之展开序幕,创作者们也在不断努力寻找着创作的突破口,西部电影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迅速起步,80年代末达到鼎盛、辉煌,创作出《人生》、《黄土地》、《野山》、《老井》、《黄河谣》、《双旗镇刀客》等一批具有西部文化特点的作品,它以其丰富的创作实践取得了作为一个特定片种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电影风格流派的形成发展。作为一种创作美学思想的提出,这些影片充满西部精神和西部意识,具有浓郁的西北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质,以自己现代影像语言的探索和表述,呼应了新时期影像美学的兴起,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的文化符号和形象象征。
一、影像观念的兴起与现代影像语言特征
进入新时期以后的中国电影,对于电影本性的研究不断深入,先是电影纪实性的问题被重点提出,其特征为采用记录手法,还原生活,反对虚假。然而某些影片中艺术元素的发展并不平衡,并表现出相应弱点,“如情节线索不严密,对具体现象不善于进行艺术概括……往往在段落层次上非常精彩,而整体结构却缺乏有机联系,所以对观众没有捶击心扉的力量”,[1]纪实电影的创作得失很快使电影界萌生了新的美学要求,人们不再满足于对现实生活的表层描述,而倾向于以更新的时代意识和审美意识反映生活的本质。
循着这一新的美学倾向,一批追寻民族历史发展轨迹、富有深厚文化意蕴、具有一定哲理意味的影片陆续出现。发轫于此时的中国西部电影在这一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作品《人生》、《黄土地》、《野山》、《黄河在这儿转了一个弯》、《老井》、《黄河谣》、《筏子客》、《双旗镇刀客》等一系列影片,以强烈的视像之美与丰富的表现力呼应和壮大了这一美学思潮。影片在外在形态上保留了情节的框架,但其重心已经转移,创作者无意摹绘生活现象的本相与过程,而更着意于在银幕上呈现意识、情绪以及感受的影像。创作者们紧紧把握电影从外部观看事物的特性,把画面作为表述手段,强调视觉,强调描述,强调表现性动作的展开。在视觉造型上,常常把某个个别特征或部分加以浓缩和突出,实现画面在视觉上的情绪感染力与冲击力,以风格化的描绘开掘出影片的巨大思想涵义、对哲理与历史的思考,从而实现了内容表达与风格化表现的完美统一,使人产生丰富联想。在理论界,逐渐把研究重点从整体性的剧作转向具体的影像范畴研究,对于电影造型语言的系统研究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并且特别强调了影像对于电影本体的意义。电影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双重转向标志着影象观念的崛起。
影片《人生》中导演把黄土地作为主要造型环境来拍摄,把黄土地上的千沟万壑、尘沙暴雨、昏暗的窑洞真实地展现在观众眼前。片中那荒秃的山坡、贫瘠的土地、狭窄的沟壑、古朴的山庄以及栉比的窑舍,强化和凸现了生存其中的人物的情感与性格,命运的内在逻辑性令人深思。在影片《黄土地》中气势雄伟的黄土高原、底蕴深沉的黄河成为全片意义依托的重要依据,时而作为背景,时而作为空镜头,一再出现并贯穿全片。当我们看到影片中那贫瘠的土地,像凝固的波浪一般向天际无尽地舒展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一家三口像泥塑般生息在阴暗的窑洞里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那被鲜红的色彩涂抹着,世世代代在这小路上蜿蜒而行“迎亲”队伍的时候,我们内心就会翻腾起一种激动,我们感觉到了创作者的意绪,这就是象征。
影片《黄土地》一开始就是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的一组长长的叠化镜头。升腾起伏的土地像被赋予了生命,画外传来的脚步声使画面的象征意味得到了加强。在温暖的光色的映衬下,一头牛、三个人组成的小小行列在高高的峁顶缓缓移动,起伏的黄土几乎占满了画面,顶端的地平线上小小的人影在明亮的天空背景上成了剪影。他们溶化在苍天和大地中的身影,已远远超出其在情节中原有的地位。翠巧碾谷时周而复始的碾盘伴上她爹苍凉的声音,就像五千年沧桑历史的和弦咏唱,还有那黑洞洞的窑洞、曲曲弯弯的小路,都已脱离单纯的环境概念。窑洞中昏暗灯光下饱经风霜的老汉,烈日下虔诚跪拜的“脊梁”也不再是传统影片中的人物,一切的一切在新的电影语言体系中都有了新的表意功能。在翠巧洞房段落里,红被子、红枕头和翠巧的红盖头充满了画面,伴随刺耳的开门声,一只粗黑的大手掀开了红盖头,翠巧惊恐的脸向后躲闪,伴随着这一切的是长达半分钟的令人无法忍受的静默。尔后,震耳欲聋的腰鼓阵的乐声冲破画面,明亮的天空下,翻身农民送子参军的腰鼓惊天动地,如黄河的波涛排浪而来,对于观众而言,画面的意象化奇观和修辞化的震惊也随之迎面扑来。
《野山》是西部电影继《黄土地》之后的又一力作。在影片中“山”既是一个重要的背景衬托物,又是影片中重要的表意载体。“这里风光幽静,民风淳厚,有一种纯朴的原生美,老乡们待人诚恳、豪爽……同时,我也强烈感受到一种凝滞、僵死的气氛,令人感到异常沉重,山外面正发生着巨大变化,山里面却还是原始初创时期,历史的车轮在这里转动得实在是太缓慢了……”连绵不绝的野山既是一种雄奇而突兀的自然景观,也是阻碍村里人从落后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文化屏障指称。
认真分析这两部影片,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电影追求画面雄伟、厚重的阳刚之美,给人一种敬畏感和崇高感,它们似乎为中国西部电影的画面定下了基调,即力度之美,凝重的西部精神以及久远历史的沧桑感,似一股激流突然冲出地面,表现出强烈的爆发力和喷薄气势。在此以后的影片如《黄河谣》、《双旗镇刀客》、《筏子客》等,大都步其后尘,十分讲究画面的力度感,并且几乎形成一种程式。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影片《天地英雄》则把这种风格化的表现发挥到了极致。这种风格影响深远,甚至港台拍摄的影片,如《新龙门客栈》、《东邪西毒》等,在画面力度感的渲染上也大做文章。
我们可以重新回到影片《黄土地》中来考察形成这一视觉美感的元素。在景别使用上,影片使用了大量中景、全景和远景镜头,在这些镜头中景物占据着大部分画面,因此,景物的力度感是画面力度感的决定性元素。此外,影片惯用缓慢悠远的摇移镜头展示“天之高远,地之广漠”等博大辽阔、苍凉厚重的自然景观,并以其构成巨大的色块和面,并且线条粗犷,直线多于曲线。比如影片一开始,首先是摄影机以大远景和大全景横摇所摄录的黄土地充溢画面:“落日时分的千沟万壑,庄严地沉默着”,“依旧是庄严而沉默的千沟万壑”。因为“一个民族最初的强悍原是同大气磅礴的自然环境相关的,一个民族最初的文化原是从静默中产生的”。[2]然后我们才看到了顾青像个小黑点似的身影渐渐从纵深处走来。可见,在人与自然的二元构图中,自然比人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同样,中华民族的母亲——黄河也在片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与黄土地相互映照、相互补充。
在此之后出现的影片《老井》,对于影像造型的视觉审美力量与象征表意则有了另一番展现,它力图在叙事中合逻辑地升华,在自然平实中寓深意,在趣味盎然中融进深刻的哲理叙事而得到审美熏陶、心灵震撼与情感的升华。与之前的西部电影创作相比较,其造型意识不再是矫枉过正地以崇拜对待造型,而是把造型紧密地和情节相糅合。“打井”是影片的主要情节线,同时也构成了影片的整体象征,象征着人类与自然的永恒的斗争,象征着民族不屈服的精神。影片的季节从秋到冬的安排,也具有情绪上的整体象征意义。金秋时节,表现老井村年轻人的朝气蓬勃的青春活力,唱戏、调电视、挑水路上的呼喊都发生在这个季节。随着旺泉爹死,旺泉被迫成亲,寒风起了,树木凋零,影片的气氛越来越重,待到旺泉终于屈从、认命、与喜凤结合后,影片转入冰雪覆盖的季节,象征着旺泉个人命运悲剧的开始,而打井的事业也进入了更严峻的阶段。至于具体物体的象征,比如影片中无处不在的“井”,摄影机多次从不同角度拍摄。从上往下拍,井黑洞洞的像个深不可测的深渊;从下往上拍,小小的井口像暗夜中的月亮,透下一缕清冷的光,给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幽深之感。在这里,“井”的象征是感性力量与理性思维的相互扭结,使得情感更具备理性思辨色彩,封闭落后的文化心态与坚韧不拔的民族内在伟力不可分割地统一于一口井中,简约、有限的画面中传递出丰富、深远的传统文化内涵。
影片《黄河谣》中广阔的黄土地旷远而深邃,粗犷的花儿从荒原深处隐隐滚过磅礴大地,牲灵队仿佛从悠悠岁月中踽踽走来,缓缓远去。它们以不同的画面形态,反反复复一再出现,直到随牲灵队走来的当归,最后仍随着它消失在亘古的黄土地上。它们构成了西部电影中壮阔雄浑、苍凉悠远的造型空间。影片中这时所蕴含的不再是悲切,而是一种激情在胸的涌动,以及贫穷困苦中存在的百折不回的顽强抗争。几乎是沿着这一路子继续发展,《双旗镇刀客》的出现将影像造型推上了一个新的巅峰,影片中影像“承担的叙事功能、表意功能不断强化,视觉力量愈加重厚,但这并没有使他‘蹈入’概念隐喻的‘影像怪圈’之中,理性的、思辨的内涵从来没有超越电影影像的感性形式”。影片的开始可以说就是这种影像叙事的典型范例:随着摄像机从右到左的横向移动,一座山峰从左到右移出画面,山峰就像道徐徐拉开的大幕,远方出现了饮马的刀客。摄影机的运动,影像的变化与故事展开完全是同形、同构的。影片中那尽显秦汉遗风的直棂窗、拴马桩的石刻,古代兵营式的圆木栅门,直刺云天的镇旗双杆,那造型独特古朴又不失西部大漠之风的刀客服装等等构成了“双旗镇”这一充满大西北地区风格的造型,它尽融地域之典型、历代之古风、人文之精华、善民之俗情。当我们面对银幕时,那流光溢彩的银幕似梦幻情境,当这些影像还原为它们感性的本体形态时,我们无暇顾及这是人工的造化还是自然的赐予,只能感到心绪间有片刻的波动、瞬间的震颤,而这种感性的力量正是影像最本原的力量。
西部电影中众多的影像造型给予了观众新奇的视觉感受,构成了一道道影像视觉奇观,且同时让观众感受到其中厚重的历史文化蕴涵。进入21世纪,在《天地英雄》、《英雄》等片中先后出现了对于西部地域的表现,它们或部分或局部地选择西部地域背景,以此作为影片的艺术衬托物和商业卖点,或是或多或少地模仿和承袭西部电影中的影像造型与视觉元素,并加入独特的影像想象与个性化表达,使之成为吸引中外电影观众的重要文化因素与心理因素,为新世纪中国电影的成功发展提供了借鉴,在国内外影坛上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水准和市场效应。
二、“西部电影”的文化价值
在西部电影中,电影导演们用现代意识重新观照西部文化,从而获得对神奇的西部世界的真正理解。影片中的文化价值来自于一代最敏感是也最深沉的“思想者”们的文化思考和哲学反思,从而顺应了人类文化发展的需要。与其说是西部电影选择了文化,毋宁说是文化选择了西部电影。当文化价值在西部电影中以独特的审美形态施展其魅力时,它不但与时代同步,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化逻辑和价值体系,大致反映出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一)地域文化的坚守与张扬
在西部电影中,导演们对本民族地域文化的结构和特征显示出极大兴趣,在电影创作过程中,他们对于富有民族特征的地域文化有着一种自觉的诉求,并有意识地选择那种具有深层文化内涵的特殊地域作为整部影片开展的现实空间和潜在文本。
地域文化的存在一方面为电影影像造型提供了自然和人文条件,满足了电影艺术家们进行“文化寻根”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西部那种独特地理环境和民风民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思维上的碰撞,使电影艺术家们进行艺术潮流的突破和更新有了可能。在中国西部这块特殊的地域上,导演们寻找着创作的灵感和题材,以全新的视野、不同的角度实现了对西部传统文化、历史与现实、民族与宗教、社会与人生等的全面解读,这使得他们在地域文化的选择与内在情感的表述上获得了高度的统一。地域文化有效地进入西部电影的创作领域中,最重要的体现是它与人物、性格的血肉联系,与作品的意向、氛围、风格乃至情节的有机统一性。这样,即使是环境描写,导演也可以显示出人物生存境遇的带精神性的象征性,不至于是单一、凝固、游离于作品之外的可有可无的存在,进而成为人物活动有声有色的舞台。影片中黄土高原给人一种厚重而绵延的文化感;黄河水流承载着历史的沧桑与世事的沉浮;戈壁荒原诉说着人生的苍凉和历史的久远;沙漠又有着一种粗犷和力度,地域文化以其特有的方式锻造着西部人的坚韧与执著。
影片《人生》给观众造成巨大震惊,在极具视觉震撼力的影像之外,更加让人难忘的是民俗民情。影片把黄土地和民风民俗作为人物生存的环境,在展示人物的同时展示生活本身,这种地域色彩的凸现与人物内心情感的表述在这片特殊的土地上达到了高度统一。而《黄土地》中故事情节的趋于淡化则加强了地域风情在影片中的表现功能。“环境就是故事,故事如此,完全是因为环境本来如此,黄土地的温暖与贫瘠,与那里生活着的人们的温暖与贫瘠是一样的。其博大与沉寂,其千沟万壑形成的性格上的落差,它的荒凉和希望,它的凝滞与躁动,黄土、黄河、黄土地上的人都是一样的。”[3]293因此才有了如歌哭一般的喜乐,这一切都是合二为一的,难作分别。在《黄土地》把这片土地的风貌发挥到极致以后,《老井》对于这片土地的表现于先前的沉郁中显出一丝亮色。仍然是那块千古不变的土地,我们感受到的似乎更是一种生命的希冀与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之后的《黄河谣》中,黄土地依旧那样贫瘠,但贫瘠之中却是激情在胸的涌动,主人公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的顽强抗争以及百折不回的坚韧,并成了生生不息奔涌的潜流。《双旗镇刀客》中的戈壁沙漠作为主人公孩哥的“用武之地”,它奇绝突兀,有着一种粗犷的力度,为孩哥的单纯与执著提供了一个有声有色的舞台。在这浓厚地域色彩的最深层处是一种文化精神,从艺术发展的角度看,地域文化中最重要的是文化精神,而这种精神是流动的、变化的,既有具体的地域性,亦有一定的开放性。地域文化的确认,需要一个过程,一旦人们开始确认它时,实际上生活又再向前发展了。在现实生活中,在当代题材作品中,需要融入历史感,不要因注视新的生活而忘却历史的根基,历史题材中须注入现代意识,不因题材古远而显得陈旧。历史感与时代感的统一,才会使地域文化既有稳定性,又是丰富多彩,流动变化富有新意的。它以自身特征区别于他人,旧的特征消失了、淡漠了,新的特征又开始形成,并逐渐变得明显。
进入新世纪,再次回顾西部电影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把“地域文化”或者说“地域特色”的追求作为电影创作的一个新支点。即使我们不把地域特色作为刻意追求的目标,但只要我们遵循电影艺术的一般规律,感性的、形象地反映生活,地域特色同样可以得到一种流露。在今天,地域特色的追求也可以向“诗化”、“意象化”的方向去发展,以一种更具有艺术感、情感性的表现,实现与现代人文意识的有机结合,从而有可能成为民族电影的范本,这也许是地域文化在艺术风格上的一种较为理想的境界。因为从国际影视的范围看,它最具有东方色彩与中国意味。
(二)文化反思与文化重建
1984年前后,随着整个社会生活中改革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新时期电影一方面在探求自身道路上继续深入,另一方面则把注意力转向广阔的社会联系。而发轫于此时的中国西部电影作品也显露出新的艺术取向。创作者们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将自己的艺术触角伸向社会深层,去拼搏、去发现,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探寻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剖析受传统濡染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作品中充溢着深邃的人生哲理,跃动着东方人人文思想的火花,显示出强烈的文化自审意识。
从《人生》、《黄土地》开始,文化自审意识在西部电影创作上得到鲜明、突出的显现。落后保守的文化心理积淀同现代化物质进程之间的现实矛盾和冲突成为电影艺术家们在影片中所注重表现的内容,他们内心的忧虑唤起他们对传统文化心理结构进行彻底反省的自觉意识。这种内心的真实感受在影片中以对人、对社会的反思而出现。在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明确的社会责任感的冲击和驱使下,西部电影创作者们在广阔的西部天地里,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把焦点对准民族文化氛围中的人,逐步以高层次的文化审视来探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社会心理,揭示传统心理结构的严谨、嬗变和发展,力图用现代意识和现代观念来剖析民俗灵魂和民族精神,从而站在一种看似超脱、而实际上更为贴近的立场来关注变革中的现实。
影片《人生》的出现,成为早期中国西部电影文化审视与反思的尝试。影片对于人生、对于社会的深刻反思,体现在银幕上即对个人价值及其价值观念的描绘。在《人生》的社会环境——中国广阔的乡村世界中,不仅有其独特且系统的“价值观念”,而且这一价值观念还支配着人们的生活,决定着许许多多人的人生。《人生》所涉及的并非改革开放初期产生的“不正之风”,而是一种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种深入人心的“生存哲学”。在这一意义上,影片在个人的价值及其价值观念层次上超越了所叙述的时代,更超越了所谓“城乡交叉地带”,从而达到了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历史文化深度。
尽管《黄土地》反映的社会背景与《人生》不同,但在表现变革的“情感定势”:即对变革认同和取向的情感状态上却与《人生》极为相似。在影片中,翠巧爹祈雨时那双眼睛与窑洞内呆坐时的混浊无光、麻木冷漠大有不同,那老泪纵横、饱含渴望的样子,与其说是祈雨,不如说是乞命,乞望自己的命运能有所改变,期望古老而多难的中国的命运有所改变。这群光着脊梁的人,朝着一个神秘地方跑去,势不可挡。他们对于命运的改变给予了一种原始的、发自生命本原的渴望。而那逆着人流奔跑的憨憨,抑或是看到了希望,他内心深处所思考的、所渴望的与《人生》中的高加林并无二异,是一种对社会变革强烈的认同和向往,寄寓着创作者们内心对现代意识的呼唤。他们一旦从麻木走向觉醒,从愚昧走向文明,从封闭走向开放,也就必将使自身与黄土地一起获得新生,正因如此,《黄土地》超越了创作主体个人有限情感的外射,而升华出一种社会情感和民族情感的超前意识。它在整个民族文化反思中的开拓意义和在中国西部电影发展中的地位不可低估。
之后,反思潮流在《野山》、《盲流》等影片中进一步推进,在影片中,它们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进程之间的直接搏击,以更有力、更直接的姿态介入到当代社会生活的进程中来。在变革的背景下,禾禾在多次折腾之后,在经济上挥手告别过去的贫困生活,而且在观念上也挣脱了“鸡窝洼意识”的束缚,新的经济意识赋予了他们新的文化观念。至于桂兰,其觉醒是从精神层面开始的,动力源于她的人的意识的觉醒,鸡窝洼的压抑在她心中产生了一种她自己并未意识到其意义的文化冲突。导演颜学恕正是通过这群普通农民复杂的文化心理因素的演变,透视出一种文化转折的意义,而这种转折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西部电影创作已经开始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建构。影片在结尾给了禾禾与桂兰一个圆满的结合,并且使处于“鸡窝洼文化意识”中的人都“团聚”在他们周围。这种结尾不得不归之于导演乐观主义的美好愿望。
1987年是新时期电影发展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文化反思作为一种思潮也达到了“巅峰”状态,中国西部电影在创作中也达到了顶峰,影片《老井》的出现,使得文化反思在实践创作中寻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不但在今天与明天之交的立足点上反思民族文化。且在今天与明天之交的立足点上发展民族文化,反思历史,直面现实,开创未来。”[3]293影片中男主人公旺泉在打井过程中内心生活也曾失去平衡,他曾选择过出走,失败后,不得已留下。它不同于高加林,亦不同于《黄河在这转了一个弯》中的赵大,为了改变现实,他觉得应该去打井,这是在现实环境的刺激和思考之后,带着某种对比、选择所产生的犹豫和彷徨去打井的。这种选择是理智的。在旺泉身上,传统的精神在现实的变革意识引导下显出历史的合理性。这种精神与其说是传统的,还不如说是这个改革的时代唤起和造就的,是人的现代性意识崛起的体现。影片的文化意蕴在于表现变革现实中各种人物如何发挥聪明才智,去创造和建设新文化。人当然要负载历史,承继传统,但人之所以为人正在于人同时以其可贵的创造力去创造历史,创造文化。“老井村文化”塑造了旺泉、巧英、喜凤们,而旺泉、巧英、喜凤们也在以各自的聪明才智多多少少创造着有别于“老井村文化”的新的文化。这也正是《老井》特殊的文化意义之所在。
在《老井》之后,《黄河谣》的文化重建意向更加明显,影片将当归的锲而不舍和百折不挠的优秀品质上升到了一个民族应有的品质。“在时间的流程里,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外在于自己的历史,更不可能脱离自己的历史而走向未来。一个民族要振兴、强盛,只有正视历史,正视现实。”[4]作为这个民族中的一个个体,在思考生命意义与价值的同时,更加意识到的应是一种责任和使命。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文化转型,西部电影在创作方向上发生了很大改变,1990年,导演何平创作完成《双旗镇刀客》,影片中孩哥这个单纯、执著的少年凭借着勇敢与聪慧,在荒漠小镇街上战胜了强大的对手,同时也战胜了自己,在小镇的善与恶、是与非中历练成一个能正视社会、斗量人心、承载重任的青年。影片结尾,孩哥与好妹在如血残阳中纵马离开双旗镇,迎接他们的将是一个崭新的开始,而迎接中国西部电影的必将是等待开拓的新的领域。
(三)尝试与拓展——作为类型片探索的中国西部片的拍摄
从中国西部电影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西部电影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它在逐步走向类型化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叙事结构、人物形象塑造还是主题的挖掘和影像的风格上都体现了鲜明的中国西部电影特色,形成了一些“西部元素”,并在实际创作中不断地进行改进和补充,使中国西部电影走向成熟并形成系列化。从文化比较的视野上来看,中国西部电影一开始就与美国的“西部片”的文化审美取向不同,相比较而言:美国西部片作为一种商业类型“范式”已经定型,而中国“西部片”则是一种非类型化的电影创作。“所谓非类型化,即指中国西部电影从开始产生到成长、发展,都不具备明显的商业性目的和产业化功利目的,而是属于艺术电影类型范畴。如果一定要用‘类型’的角度去审视的话,则可以从地域文化特色和影片生产者的粗线条框架加以勾勒,这类影片大多表现西部地域历史与现实生活,多由西部电影生产厂家创作并拍摄完成。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西部片更应属于风格化、艺术化类型电影。”[5]
对于此,罗艺军先生有着很高的评价:“中国西部片是中国第一个以地域文化资源为内容的类型片,其电影美学价值在于开辟了一条通向尚待开采的文化富矿的通道。”[6]“关于‘中国西部片’的倡导,有两点值得给予充分评价:一是突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因循保守的偏向,在创作上和理论上勇于创新。二是为中国电影发掘深厚的民族文化资源提供一个新视角、一个新境域,从而拓展了中国电影艺术视野,深化了电影民族文化底蕴。”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尽管西部电影从人们的视野中已悄然退出。但西部电影中的一些风格元素、美学趣味已经为后来的中国电影创作所借鉴,溶入到新世纪许多成功影片的血肉之中。但新世纪有着新的电影发展语境,对于西部电影中深刻的人文内涵和独特的民族、地域特色,我们需要借鉴,同时还应加强和注重商业化的运作和包装,制作的影片可以基本上向着两大方向发展:“一个是走艺术电影的道路,较多地借鉴西部电影和同时期电影中的人文传统和内涵,真实地揭示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生意识,靠原创性、地域性、民族性取胜……一条是走商业电影的道路,在保有电影基本的人文内涵的同时,走类型化的生产道路,充分地挖掘和利用中国古老的历史人文资源,靠传奇性、娱乐性、商业性大制作取胜。”[7]
回顾中国西部电影近十年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对于中国电影史和当下电影实践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其文化影响和精神流变延及新世纪的某些电影创作。新世纪以来,《卧虎藏龙》、《英雄》、《刺陵》、《三枪拍案惊奇》、《无人区》、《西风烈》、《决战刹马镇》、《让子弹飞》等,虽形态风格各异,但都有或多或少的西部视觉符号和文化要素。对这些影片的考察研究对今天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的类型建设和文化的国际传播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和实践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