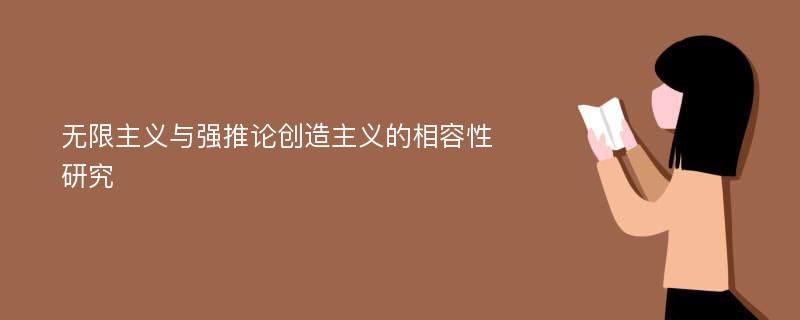
无限主义与强推论创造主义的相容性研究
王 聚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无限主义是当代解决阿格里帕三难问题的一种进路,但学界的一种批评意见认为无限主义无法解释认知辩护的来源问题。面对这一批评,无限主义者主张推论活动本身也具有创造辩护的功能。坚持推论创造主义使得我们可以更准确地理解推论工具主义的内涵,但强推论创造主义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以涂厉(John Turri)为代表的无限主义者或者无法说明为什么信念辩护可以从无到有,或者无法让强推论创造主义与无限主义相容。排除了强推论创造主义,弱推论创造主义或许是无限主义的一个有希望的理论资源。
关键词:无限主义;阿格里帕三难问题;认知辩护;强推论创造主义
① 阿格里帕最初的怀疑论模式有五种:一是普遍分歧,二是无穷倒退,三是视角主义,四是假设,五是循环。
知识的辩护(epistemic justification)问题是当代知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日常情景看来,当一个认知主体相信一个命题,比如厦门大学位于厦门,然后该信念面临来自他人的挑战或者质疑时,该认知主体可以提供自己持有该信念的理由。例如,他可以指出自己曾经到访过位于厦门的厦门大学,或者自己在厦门大学的官网上获得这个信息。通过展现自己持有信念的好的理由,该认知主体彰显了自己的认知责任(epistemic responsibility),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值得称赞的认知主体。不过,针对这样一个日常的图画,古希腊怀疑论者阿格里帕提出了一个挑战,我们可以称之为“阿格里帕三难论证”。①该难题旨在指出,针对任何命题,我们并不能给出基于推论的辩护。我把该难题表述如下:
在良渚文化中,诸多玉器均有兽面纹或神人兽面纹。兽面纹出现得最多,它的基本形制是两只大眼,有一横梁连接,类似眼镜的横梁,横梁中部连一短柱,类鼻,柱下连一横梁。两横梁夹一柱,类工字。工字下有一横梁,较长。此种造型,大致类似兽面。
假设S能对其相信的命题P给出一个基于推论的辩护(inferential justification),那么S只有三种给出理由的方式:
式(12)中:α为显著性水平;Dmin为某方向上目标船到周围船舶的最小距离;f(x)为某方向上周围船舶到目标船最近距离的概率密度分布函数;D为某方向上显著性水平为α时距目标船的距离。
A3:因此,厦门大学在中国。
2. 给出理由R1支持P,给出理由R2支持R1,再给出理由R3支持R2,但给出理由P支持R3。(循环辩护)
3. 给出理由R1支持P,给出理由R2支持R1,但对于某个理由Rn,不再继续提供理由。(任意假设)
这里关注的是基于推论的辩护。我们当然可以承认有些辩护是不基于推论的,例如过程可靠主义(process reliabilism)的辩护观,但是不可否认基于推论的辩护在我们的认知活动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这里给出的三种辩护方式看似都不合理。第一种方式宣称我们的理由链条是无穷的,但直觉上我们倾向于认为一个人无法完成无穷的辩护步骤,所以这种导致无穷倒退的辩护方式是很荒谬的。在第二种方式中,由于某个理由P既在前面推论的结论中出现,又在后面的某个推论中作为前提出现。这实质上是说,一个命题P为其自身辩护,但这样岂不是意味着什么命题都能受到辩护?所以(线性的)循环辩护也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在第三种方式中,理由追问的活动到某个理由止步了,乃是因为对于某个理由Rn我们只是假定它为真,却并不继续提供理由支持。但是针对这样的假定,我们担心其任意性(arbitrariness),即是否假定这样一个前提是合理的。所以,为了避免假定的任意性,我们也不愿意接受第三种方式。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接受上述任何一种方式,并且我们又无法提供除这三种方式以外的新的方式,那么一个归谬论证(reductio ad absurdum)就摆在面前。该论证显而易见地指出,我们无法对自己所相信的命题提供任何基于推论的辩护。或者说,没有一个命题能够被我们辩护地持有。这是一个怀疑论式的结论,所以阿格里帕难题成为了众多学者关心的问题。对于阿格里帕三难问题,学界大致有基础主义、融贯主义和无限主义三种回应思路,我不再赘述前两者。
一、什么是无限主义
一般来说,当辩护者持有的信念被追问后,他可以选择为该信念提供一个辩护理由,以期提高被追问命题的可信度(rational credibility)。针对此,无限主义需要进一步澄清两个问题。首先,为什么问题被提出后我们需要为其寻找新的理由呢?难道不能无视这些提问吗?对此,克莱因认为出于我们的认知责任(epistemic responsibility)一定要回答这些追问。也就是说,由于我们自认为是理性的认知者,希望为自己的认知活动负责,所以就必须要仔细审查自己的信念,通过好的理由之链,以提升被追问命题的理性可信度,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我们的理性和反思精神,我们也才能得到真正的而非动物性的知识,亦即克莱因所谓的与众不同的成人知识(distinctive adult human knowledge)。[1]其次,为什么我们必须把这种“追问-回答”活动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无限主义者认为,既然我们是受到理性精神的指引开始追问和回答,我们为什么要在某个点停下呢?这种止步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理性精神的脆弱,是对探究精神的不彻底的运用,也是违背理性探究活动最开始的初衷的。这里的初衷大致说来就是,对任何信念进行理性考察以至于我们可以有理由地持有它们。
正是受到无穷追问的理性精神启发,克莱因认为真正的认知辩护应该坚持以下的两个原则:
1. 避免独断原则(Principle of Avoiding Arbitrariness,简称PAA):对所有P,如果一个人S拥有一个对P的辩护,那么S就有某个对P的可利用*在这里可利用主要是指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分两个方面:首先它必须是主观地可利用,即其适当地和S的其他思想内容发生关联,不能是孤立的;其次,理由也必须是“客观的”,即理由之间也必须发生关系,不能互不相关。“可利用”为理由序列给出了一定的规定性——无限主义并不是开放给全部理由的。的理由R1,并且S还有对某个理由R1的可利用的理由R2,如此一直不会停止。这就是说,辩护命题P的理由不能是独断的。
2. 避免循环原则(Principle of Avoiding Circularity,简称PAC):对所有P,如果一个人S拥有一个对P的辩护,辩护命题P的理由不能包涵P。[2]
以“两年”活动为抓手 开创新时代国土资源工作新局面 .................................................................................3-1
巷道跨度6.3m,计算模型共取2个,一是首次开挖断面2.3m,后扩挖断面4.0m;二是首次开挖断面4.0m,后扩挖断面2.3m。
无限主义的命题辩护观:当有一系列既不重复又无穷尽的理由支持命题P时,P就获得了(命题)辩护。[3]
无限主义的信念辩护观:S的信念B是获得(信念)辩护的仅当S顺着无穷的理由之路为B提供了足够的理由。[4]
当代知识论里面,一个命题只有受到辩护才可以继而被我们辩护地相信,这当中的额外步骤是我们实际上必须把相信某个命题的理由奠基于辩护命题的理由之上。举例来说,在法庭上,针对命题P琛琛是无辜的,法官J面前有许多相关的证据E,比如人证的不在场证词还有犯罪现场凶器不匹配的指纹等等。假设此时证据E充分地支持命题P,那么可以说此时命题P对于法官J来说是具有充分辩护的。但是,法官可能并没有实际上基于这些好的证据E来相信P,而是基于嫌疑犯琛琛对于尼采哲学的热爱或者琛琛的友善面容。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热衷于什么样的哲学思想或者长相如何,并不构成支持这个人是无辜的证据。所以基于这些“证据”去相信命题P,是缺乏实际的支持力的。在这个案例中,命题P对于法官J来说是(命题)辩护的,但是法官却没有利用这些真正有效的辩护资源。所以即使在该案例中存在命题辩护,法官J也不拥有信念辩护。只有法官J实际上基于证据E去相信命题P,法官相信P才是获得(信念)辩护的。基于上面对命题辩护和信念辩护的区分,我们进一步来看无限主义对两种辩护的讨论。
从克莱因的论述可以看出,一个命题是可以获得完全辩护的,只要它拥有无尽且不重复的理由支持。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一定要实际上完成这个无穷的理由链条从而完成信念辩护。信念辩护在无限主义这里有程度之分,首先只要一个认知者遵循无穷的理由之路开始为自己的信念提供理由支持,那么该认知者的信念就获得辩护了。当然,由于不断的追问出现,该认知者就必须遵循无穷的理由之路提供更多的辩护。无限主义者主张,给出的理由越多,那么辩护的强度就越高。并且,无限主义者纳入了语境的实用要素,即一个人的信念辩护强度只要能满足在具体语境中提问者的追问就足够了,并不需要给出更多的理由或整个的理由链条且这也是原则上不可能完成的事。
以上我回顾了无限主义的基本主张,限于篇幅,我不再赘述无限主义是如何解决阿格里帕难题的,接下来我将转入无限主义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难题。
2.4.1 外周血单核细胞分离 严格按人外周血单核细胞分离试剂盒说明书操作。取15 mL离心管,依次加入总体积与血浆样品等同的试剂A、试剂D(体积比为3∶2),随后加入血浆样品适量,以2 700 r/min离心30 min。吸取细胞层至另一15 mL离心管中,加入清洗液10 mL,混匀,以1 900 r/min离心10 min,弃去上清液,沉淀以清洗液5 mL重悬,以2 700 r/min离心10 min后,用清洗液清洗3次,每次5 mL,弃去上清液,即得外周血单核细胞样品。然后加入RNA提取试剂0.5 mL,于-80℃冻存,备用。
二、无限主义的一个核心困难:辩护从何而来
学界对无限主义的方案有许多批评意见,本文我着重讨论辩护从何而来这个批评,并展现无限主义者的回答思路。*值得一提的是,无限主义的另外一个核心困难是: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一个信念者不能完成无限的辩护步骤。无限主义者对此批评的回应是,信念辩护并不需要完成全部的命题辩护链条,只需要满足语境的需求,提供足够的理由。因为本文主要关注从推论到辩护的关系,因此没有空间进一步讨论这一个困难。这个困难是针对辩护的来源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无限主义是解决阿格里帕三难问题的真正出路的话,那么我们无法解释辩护从何而来。
根据一种主流的观点来看,推理活动只能传递(transfer)辩护,而不能产生辩护。为了行文方便,我把这种观点称作推论工具主义(reasoning instrumentalism):
推论工具主义
推理活动只能把推论前提拥有的认知辩护传递给结论。
为了理解推论的工具主义,我们可以看下面推论。
A1:厦门大学在厦门;
A2:厦门是中国的一座城市;
A3:因此,厦门大学在中国。
B1:厦门大学在上海;
B2:上海是中国的一座城市。
式中:Qw为热水井开采1年所排放的总热量,kJ;Q1为热水井可开采量,取值50 m3/h;Cw为热水平均热容量,取4.1868×103 kJ/(m3·℃);tw为地热水井口出水温度,取65 ℃;t0为地层常温带温度,取15℃。代入相关数据可得:
一般看来,当我们进行推论活动的时候,我们是在进行一个从前提到结论的认知活动。毫无疑问,推论活动是人的一种重要的认知能力,与记忆、感知等其他能力一起构成了人们的认知官能。就知识论的范围来看,我们关心的是,推论活动能产生什么认知价值。在前面我概述了两种对于推理的作用的观点,即推论工具主义和推论创造主义。克莱因想借由“推论产生辩护”这么一个观点来为无限主义进行辩护。但是,有什么好的理由支持推论创造主义呢?在这方面,涂厉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下面我将对此进行细致讨论。
这两个推论的逻辑形式都是有效的,但我相信大部分读者的直觉应该是,虽然两个推论形式有效,但结论A3是被辩护的,B3是缺乏辩护的。究其原因是,结论的辩护与否来自于为结论提供理由的前提是否获得了辩护。因此,如果我对A1持有辩护,那么通过逻辑推论,辩护这个属性可以传递给A3;相反,如果我对B1缺乏辩护,那么即使B1和B3存在有效的推论关系,辩护属性也无法传递给结论。这样看来,如果推论只能传递辩护,无限主义似乎无法解释,作为被传递的辩护属性到底何来。吉内特认为通过推理的辩护可以类比工具价值。[5]当我们说某物有工具价值,就是说某物作为一种方式帮助我们实现某个目的而获得价值。假设学习是实现幸福人生的工具,那么学习自身并没有价值,而只是作为实现幸福人生的工具从而获得了工具价值。也就是说,学习依赖于幸福人生从而获得价值。但是,要使得这样的讨论有意义,我们必须要假设,幸福人生本身是有非工具的价值的,也就是幸福人生不再是作为实现别的目标的工具而拥有价值,否则无论是学习还是幸福人生所获得的价值还要继续追溯到更高层次的目的。那么同样地,如果X从Y那里获得通过推理的辩护,而推理活动本身只是传递Y性质给X的一个工具,那么如果Y本身不具有这种性质,而是又依赖于Z赋予这种性质,我们将无法找到所传递的性质的起点。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那个不依赖于推论活动就获得辩护性质的起点,那么我们无法理解别的信念作为该起点的推论结论是如何获得辩护性质的。丹希把这个想法表述为:
通过推论的辩护只是有条件的辩护;如果A是从B和C推论而出,那么A的辩护依赖于B和C的辩护。但是如果所有的辩护都是在这个意义上是有条件的,那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看作是实际上无条件地辩护的。[6]
为了回应这个难题,克莱因指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推理的工具主义,并且支持某种程度的推论创造主义(reasoning creationism):[7]
推论创造主义
华歆如此功名累世之人,当有一番大才般配。《世说新语》里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明这个人非常有见识:华歆和王朗一起乘船避难,有人想依附他们的船,华歆起先不同意,但是王朗同意了,那人就上了船。后来情势危急,王朗后悔了,要赶那人下船,这时候华歆说:“当初他上的时候我就考虑到了这个情况,但是现在既然叫他来了,怎么能够危急的时候就丢下不管呢?”就一直带着那个人逃难直到脱险。
无限主义者提出这么两条原则,主要是为了避免基础主义和融贯主义的想法,从而彻底贯彻自己的哲学主张。进一步地,遵循命题辩护与信念辩护的区分,克莱因分别定义如下:
推理活动可以产生或扩展辩护。
克莱因强调,我们应该区分两种类型的辩护或担保。一种担保是基于信念拥有某种性质F获得的,例如由一个可靠的过程产生的,或是信念的内容是有关于认知者的当下感觉经验的;另一种担保则是基于理由支持而产生的。[8]克莱因强调,基于第二种担保产生的知识才是值得最高赞赏的知识类型。在我看来,克莱因的大致想法是,像基础主义所认为的那样,第一种担保并不来源于理由,因为针对基础信念并没有任何别的信念可以为之提供理由。这种担保只能来源于信念的因果形成过程或其他使得该信念成为基本信念的条件,那么这类担保和基于理由的担保是具有种类上的差别的,这种差别可以大致说成是理由空间和因果空间的差别。因此,一方面我们很难理解,不是基于理由的担保如何可以通过推论传递;另一方面,我们所看重的那种辩护或担保,既然是体现在理由和理由之间的理性支持关系上,似乎并不能来源于外在于理由支持的东西。因此,即使承认推论关系能传递第一种担保,我们也还没有成功解释我们所关心的第二种担保的来源。所以,克莱因坚持说,推论活动本身能产生担保,所以辩护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也就得到了回应。不可否认,克莱因的回答过于简洁,也忽略了一些重要的细节,而这方面凃厉继续补充了一些有价值的内容,所以下一部分我将借鉴凃厉的理论,讨论推论创造主义是否可行。
三、 推论创造主义的困难与前景
B3:因此,厦门大学在中国。
(一)从推论工具主义到推论创造主义
首先,可以有物-物意义上的传递。比如,拥有房屋产权的张三可以把房屋转卖给李四,从而实现房屋产权所有证的传递。或者,如果张三拥有一件古董,然后卖给李四,那么在此意义上张三的古董传递到了李四的手上。这种物-物意义上的传递有一个重要特征,即这种传递是失去型的。也就是说,当传递活动完成,原本拥有房屋产权或古董的人将不再拥有,转而是买家获得了房屋产权或古董的拥有权。在物-物传递种,只有一个拥有权,通过传递的活动,改变的是拥有权的实际归属人。那么,认知辩护性质的传递能否类比物-物传递呢?我认为这是不能类比的。回顾刚才我们的推论A1-A3:
凃厉认为,如果我们要承认推论可以传递辩护,那么我们也必须承认某种意义上的推论创造主义,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推论工具主义的字面理解。前文提到,主流的观点认为,推论活动仅仅传递辩护,而不创造辩护。为了使得接下来的讨论更加清晰,我建议区分两种意义上的传递。
我们的团队采用这种隧道内游离输尿管方法,结合经典Wertheim手术的输尿管内侧入路法,找到输尿管入膀胱“输尿管末端”的解剖标志点,切除2 cm的膀胱宫颈韧带,ligasure离断子宫神静脉和膀胱下静脉的阴道支,解剖无血管区的膀胱阴道侧间隙(paravesico vaginal space, PVVS;图2),完整向外推移输尿管伴行,位于输尿管下方的盆神经丛;子宫颈主韧带暴露在直视下,切除3 cm宫旁组织。2011年11月11日上述技术成功后,我们在国际手术同行透明监督下,由探索性研究,延推2期注册登记的标准化临床研究。
A1:厦门大学在厦门;
A2:厦门是中国的一座城市;
1. 给出理由R1支持P,给出理由R2支持R1,再给出理由R3支持R2,以此直到无穷。(无穷倒退)
难道在这个推论活动之中,当认知辩护从A1传递到A3的时候,A1就失去了认知辩护吗?假设我对A1的辩护是,我上周去厦门参观了厦门大学,那么难道完成了从A1到A3的推论活动,我就失去了对A1的辩护资源吗?似乎这看起来很不合理,因此类比物-物意义上的传递关系并没有正确地刻画认知辩护的传递关系。
另外,我们有社会担保意义上的传递。试想,有一个在学界很有声望的人李教授,写推荐信说蓉蓉这个人有很强的学术潜力且值得培养。或者试想,学生小明出国留学,有亲戚老王为他提供资金担保。那么我们可以说,蓉蓉从李教授那里获得了一种性质,即被李教授承认的学术能力(而非学术能力),然而这种性质却是依赖于李教授这个人的。也就是说,如果李教授被发现是没有真正的学术能力,只是个弄虚作假的投机分子,那么李教授为蓉蓉做的有关学术能力的推荐或担保也就失去效力了。同样,老王为小明提供资金担保使得小明获得了有资金支持这个性质,但是如果老王本身没有资金支持,或是已经濒临破产,那么这份为小明做的担保也会失去效力。与此类似的担保不仅是有强烈的依赖关系,而且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担保关系不会带来传递方性质的损失。也就是说,作为担保者的李教授和老王,首先并没有因为做出担保和推荐损失了自己所拥有的性质;另一方面他们还因为做出担保和推荐行为传递给了被担保方一些性质。因此,在完成担保和推荐行为以后,李教授并未失去学术能力,而蓉蓉获得了基于李教授的被承认的学术能力;老王没有失去资金支持能力,而小明获得了依赖于老王的资金支持能力。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一开始所理解的辩护性质传递和这里讨论的社会担保很相似,至少比物-物传递模式更相似。
区分两种不同的传递之后,我们要问的是,如果认知辩护传递更类似后者,那么我们就得重新思考推论工具主义是否合理了。因为不可否认的是,如同从A1到A3的推论一样,前提传递给结论一种认知辩护的性质,但这种传递并没有使得前提自身损失这种性质。那么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在推论之前,作为前提的命题拥有辩护Jp,而作为结论的命题并不拥有辩护,但在推论活动结束的时候,作为前提的命题既保持了自身的辩护Jp,又赋予了作为结论的命题一定程度的辩护Jc。因此,进行了推论活动之后的辩护总量Jp+Jc大于推论活动之前的辩护总量Jp,也就是说有额外的辩护产生,那么这些额外的辩护来自哪里呢?似乎一个合理的答案就是,来自于推理活动本身。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能正确描述一开始我们称之为辩护传递的那种观点,我们也不能仅仅认为推论活动是物—物意义上的传递辩护性质,而必须承诺推论活动额外为推论的结论产生了辩护,产生了超出推论前提所有的辩护。因此,我们可以把上述讨论的要点归纳成下面这个论证:
(1) 如果推论工具主义是一种合理的理论,那么推论创造主义就是真的;
MGD患者白内障术后BUT与术前相比有显著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21.042,P<0.001)。而TMH、TMD、TMA、SⅠT、CFS方面术前与术后3个时间点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2) 推论工具主义是一种合理的理论;
(3) 因此,推论创造主义就是真的。[9]
(二)强推论创造主义还是弱推论创造主义
即使我们有好的理由要接受推论创造主义,我们还可以区分其强弱形式,凃厉分别定义如下:
在分析我国南方集体林区的发展现状后,能够从比较科学的角度,掌握林下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影响林下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为经营主体文化程度。一般来说,林下经济活动开展的主体多为林区农户,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其文化程度和学历水平呈现出相对较低的现象。因此,在日后促进林下经济效益发展时,应加强对经营主体文化程度的重视。
强推论创造主义:推理活动可以从无到有创造辩护,也就是说一个辩护程度为0的前提,可以产生一个辩护程度大于0的结论
弱推论创造主义:推理活动可以扩大辩护程度,从一个辩护程度为n的前提,通过推论活动可以获得一个辩护程度为n+m的结论,并且n>0,m>0。[10]
迷宫式密封,迷宫橡胶件内侧装有板簧,在板簧的作用下将密封件压紧在罐壁上进而达到密封作用,每一个密封件下部均有挡堰,克服浮盘上下运动时油品进入到密封内,储运中应用较少。
那么我们应该坚持哪种形式的推论创造主义呢?凃厉认为强推论创造主义是可以被支持的,但我认为他的论证不具有说服力。相反,我主张我们只应该坚持弱推论创造主义。首先来看一下为什么凃厉主张强推论创造主义,试想下面一个情景:
曾经在某个时刻T1,S基于一个坏的理由B相信命题Q。S同时对于B拥有信念辩护,只不过B并不支持Q。因此S的信念Q并不拥有信念辩护。此外,S相信命题G1,它是相信Q的一个好理由;S还相信G2,它是相信G1的一个好理由,并且S有信念Gn,Gn是Gn-1的好理由。只不过在时刻T1,S还没有利用这些好的理由链条来为G1提供辩护。假设在时刻T2,有人问S是否Q是真的,S沉思一会意识到他的理由B并不是好理由。但S并没有放弃Q,而是思索了一下自己有没有别的支持Q的理由,最终他意识到G1是相信Q的理由。[11]
在这个案例中不可否认的是,在时刻T1,S的信念Q并不拥有信念辩护,而到了时刻T2,S的信念Q拥有信念辩护。在T1和T2中使得信念辩护从无到有的关键是S把自己的信念理由从坏的理由B转向了好的理由G1。回顾我们上文对于信念辩护的讨论,一个信念得到辩护当且仅当认知者实际上相信某命题是基于那些辩护该命题的理由之上。这些理由自然而然是好的理由,而不发挥命题辩护作用的理由也就不是相信该命题的好的理由。那么从T1到T2,S的信念Q的根基从坏的理由转变为好的理由,当然提升了Q的信念辩护程度。此外,这种信念辩护程度的提升似乎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提升过程,毕竟S还没有实际上为G1找到任何辩护的理由,而只是完成了G1对Q的信念辩护过程。所以凃厉认为G1的信念辩护程度为0,而Q的信念辩护程度至少大于0,那么一个从G1到Q的推论过程,不就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信念辩护创造过程吗?进一步地,如果我们承认在该情景的末尾,Q的信念辩护程度得到了提升,还是一种从无到有的提升,是否意味着强推论创造主义是对的呢?
我认为凃厉的分析有一个关键漏洞。虽然我承认基于B相信Q并不获得信念辩护,并且基于G1相信Q拥有信念辩护,我也可以假设信念辩护是按照无限主义设想的那样可以被量化考虑且能顺着命题的无穷且不重复的理由链条持续下去。但是是否从G1到Q的推论,是一个从信念辩护程度为0的信念到一个信念辩护程度大于0的信念的推论呢?似乎在涂厉看来,G1还没有实际上基于好的理由之上,因此即使S对它有好的理由,也顶多拥有命题辩护,而不是信念辩护。但我认为,要使得强推理辩护主义行得通,我们必须更细致地分析G1的信念辩护等于0的这种情况。
首先,我们可以问,S是否曾经考虑过G1这个命题的真假。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当然承认G1的信念辩护程度为0是合理的。但是这样一来,S为什么竟然会把一个自己未曾思考过真假的命题放在其推理前提?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认知责任,也与我们大部分的认知实践相冲突的,所以选择这条出路来支持强推论创造主义是很不合理的。
那么假设S曾经思考过G1,此时我们又当区分两种情况,即当时思考G1的真假问题时,S是基于好的理由还是坏的理由的呢?如果S基于好的理由来相信G1,那么理所应当地G1已经拥有了大于0的信念辩护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S以一种潜在的方式保持了对于G1的信念辩护。什么是潜在的信念辩护?我的理解是,当S被要求为自己的信念G1提供理由时,他可以给出支持G1的好的理由。*我认为,潜在的信念辩护与潜在的信念都是正确刻画S知道一个命题的必要条件。假设信念条件和辩护条件是知识的必要条件,那么当S知道G1,S并不需要随时拥有对于G1为真或G1的辩护理由的当下信念,一种合理的看法是,只有S能在被要求的情况下,形成有关G1为真或G1的辩护理由的信念就可以了。关于如何理解知识与潜在信念的关系,参见王聚:《知识论析取主义,蕴涵论题与根据难题》,《自然辩证法通讯》2016年第5期。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看法,毕竟当一个人拥有信念辩护地相信一个命题,只要没有反面的理由出现,我们没有理由要求这个人一直保持该命题是基于某个理由的当下信念。*或许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基础主义的看法,但值得注意的是,基础主义与无限主义的分歧在于,是否一个信念能被无限追问其理由。但是关于信念的理由与信念之间的基于性关系(basing relation)是以当下信念还是潜在信念的方式存在,并不是划分基础主义和无限主义的标致,反而是与两者立场都可以相容的一个额外的理论。这样的要求太严格,以至于我们只有很少的实例。一种更合理的观点是,这个人拥有关于该命题是基于某个理由的潜在信念足矣。潜在信念虽然不同于当下信念,但潜在信念在遇到一定的触发机制时,例如别人的提问或自己的理性追问时,将变成当下信念。[12] 更严格地说,从潜在信念变成当下信念,不仅需要一个触发条件,还要满足无阻碍条件。一个简单的类比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盐有溶解于水的性质(潜在),因此把盐放入水中后,盐就会溶解于水中(性质展现)。但是如果水已经饱和了(阻碍条件),那么这个性质就无法展现出来。同样的道理可以运用在从潜在信念到当下信念转变的情况中。回到我们刚才的分析,即使S在进行从G1到Q的推理时并没有思考G1,但是G1由于曾经被奠基于好的理由之上并且保持着信念辩护程度,那么承认G1的信念辩护程度为0就有问题了。
还有一种情况,假设S曾经思考G1时是基于坏的理由T相信G1为真,岂不是很好地说明了G1的信念辩护等于0吗?我承认基于坏的理由T相信G1并不赋予G1任何信念辩护,但是这样一个选择会与克莱因的无限主义的基本主张不相容。
如果要能恰当地说明强推论创造主义,那么我们必须完整地说S是从G1相信Q且又从T相信G1,而不能只说S从G1相信Q。此时的问题在于,无限主义者坚持,信念辩护应该追随命题辩护的链条,并且达到语境充足的信念辩护程度。假设Q的命题辩护链条是G1支持Q,G2支持G1,那么在何种意义上S跟随了命题辩护链条?我可以用两种方式解读跟随,一种就是S已经基于G1相信了Q;另一种是当S要去相信Q的时候,S会选择G1而不是别的不在该理由链条上的命题。但是在我们讨论的这种情况下,S基于Q相信G1,又基于T(坏的理由)相信Q,很难看出S的信念辩护如何可以说是追随了命题辩护。毕竟,T不在G1的辩护链条之上,否则T就应该是一个好的理由了。此时的关键问题是,无限主义者会如何判断S相信Q的实际理由辩护链条和Q的命题辩护链条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两个链条之间都有从G1到Q这个部分,而不同的是前者有从T到G1这个部分而后者没有。如果无限主义者认为S的信念辩护链条也是追随了命题辩护链条,那么,只要与命题辩护链条的一段重合,无限主义者就需要接受无穷多条不相容的信念辩护的道路。如果拒绝说这种错误的推论方式追随了命题辩护链条,那么最后一种辩护强推论创造主义的道路也就以失败告终。虽然强推论创造主义失败了,但弱推论创造主义是否可行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四、结 论
阿格里帕难题是皮浪主义式怀疑论的一种典型形式,针对这个难题,基础主义者和融贯主义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无限主义作为解决阿格里帕三难问题的一种新进路,旨在消解阿格里帕难题,并且为认知者的理性精神寻找一个新的归宿。在这个目标下,无限主义者面临着解释认知辩护的来源问题。无限主义者非常睿智地注意到,如果我们承认推理活动能够传递辩护,即如果推理工具主义说得通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推理活动本身具有创造辩护的功能。虽然这是一个好的论证策略,但经过对相关思想的细致分析,我认为强推论创造主义并不能自圆其说,即以涂厉为代表的无限主义者无法说明为什么一个信念辩护程度为0的信念可以创造出辩护。虽然强推论创造主义存在严重的问题,但这并不直接意味着推论创造主义本身是有问题的。毕竟推论创造主义有强和弱两个版本,而弱推论创造主义的前景如何还需要进一步探究,或许弱推论创造主义才是无限主义的真正的理论支持。
注释:
[1][3]Peter Klein, “Human knowledge and the infinite progress of reasoning”, Philosophical Studies, 134(1), 2007, p.7, 8.
[2]Peter Klein, “Human Knowledge and the Infinite Regress of Reasons”, in J.Tomber lin, (E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13, 1999, p. 298.
[4][8]Peter Klein. “Infinitism”,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Epistemology. (Ed.) Bernecker, S and Pritchard. 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 252.
[5]Carl Ginet, “Infinitism Is Not the Solution to the Regress Problem”, in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Epistemology. Second Edition. (Ed.) Steup, M Wiley-Blackwell, 2014, p. 290.
[6]Jonathan Dancy,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Epistemology. Oxford: Blackwell, 1985, p.55.
[7][9][10][11]John Turri, “Creative Reasoning”, in Ad infinitum: New Essays on Epistemological Infinitism. (Ed.) Turri,J. and Klein, 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210, 222, 214, 223
[12]王聚: 《知识论析取主义,蕴涵论题与根据难题》,《自然辩证法通讯》2016年第5期。
根据三维实体模型提供的玻璃骨架三维定位数据进行骨架的安装(见图3),安装过程中采用全站仪全程跟踪测量。
商量解决办法,最后得出:为了更方便地量开口向左的角,可在原有工具中再添一圈角度,这样,量角工具便有了内外两圈角度,可以更方便量出开口向左或向右的角的大小。至此,一个现代量角器顺利诞生,此时,组织学生观察、讨论如何用量角器量角,总结出量角四要素:点对中心点,边对“0线边”,看清内外圈,再看另一边。
On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Infinitism and Strong Inferential Creationism
Wang Ju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Infinitism aims to offer a solution to the Aprippa’s trilemma, but it faces the objection that infinitism cannot explain where epistemic justification comes from. Infinitists contend that reasoning alone can create justification, and by holding this thesis, one can have a better grip of what inferential instrumentalism says. However, it is argued that strong inferential creationism is problematic, i.e., the thesis, advocated primarily by John Turri, that reasoning can create justification ex nihilo is implausible. While strong inferential creationism is shown to be dubious, weak inferential creationism might give support to infinitism.
Keywords: Infinitism, Agrippa’s trilemma, epistemic justification, strong inferential creationism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8)01-0165-08
收稿日期:2017-07-12
作者简介:王聚,男,云南昆明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蔡永明]
标签:无限主义论文; 阿格里帕三难问题论文; 认知辩护论文; 强推论创造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