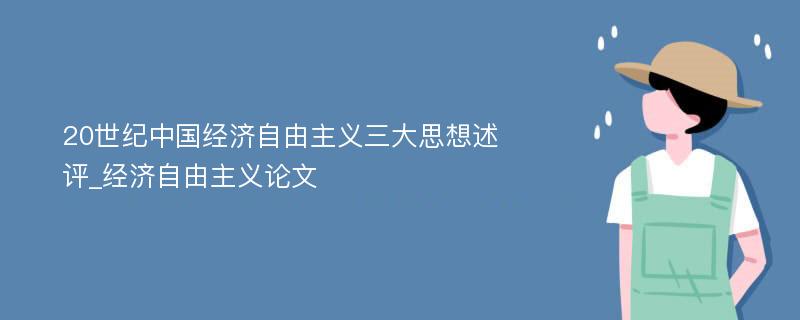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三次经济自由主义思潮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自由主义论文,思潮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230(2007)02-0135-06
作为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现象,经济自由主义吸引了研究者们的注意。现有的考察已涉及到若干时期和人物的自由经济思想。但笔者认为,还存在着整理长期思想演化的必要性。本文试图从经济思潮史的角度,全面考察20世纪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检视三次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演变及其脉络,并以一个中国的视野,把1949年前后在中国台湾出现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纳入到论述框架中。
为便利起见,本文所使用的“经济自由主义”范畴是一个宽泛的、相对的观念集合。凡是主张绝对自由放任的,或是在非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高涨时期倾向私有、民营或市场调节的观点、理论或学说,都可以归于其中。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无意对经济自由主义作任何道德上的判断。类似地,本文将在学理层面上使用“社会激进主义”一词,即它是对现有经济社会体制的批判,对整体建构、剧变、革命等制度变迁方式的认同。
一、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经济自由主义思潮
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和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的破产。在变法图强的口号下,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突然涌来。“戊戌变法”遭到镇压后,经济自由主义出现神学化、激进化趋势,思潮激荡。1905年土地制度论战爆发后,思潮趋于消退。这一时期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理论资源是西方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和中国古代民营经济思想。
(一)1895年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涌来
甲午战败后,洋务派控制和垄断新式工业的政策,遭到了广泛而尖锐的抨击。康有为提出,兴“机器轮舟”之利是富国之大法;官方垄断新式工商业,“徒使洋货流行,而禁吾民制造,是自蹙其国也”。他主张“一付于民”和“纵民为之”[1] (P124)。梁启超也反对与民争利。他尖锐地指出:“挽近之计臣,日日策划筹度者,大率皆与之争也。”[2] (P117)
战前流行的保护贸易思想也遭到了批判。谭嗣同把国际贸易称为“相仁之道”和“两利之道”。他批评了当时保守人士的闭关绝市的主张,认为他们“不自振奋而偏巧于推咎”,而且把保护关税的观点也斥为“西人之旧学”[3] (P45)。梁启超也赞同自由贸易。
严复论证了国家自强与人民经济自由的关系。他指出:“夫所谓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各皆得自由始;欲听其得自由,又必自其各能自治始”[4] (P29)。在他看来,变法的中心内容应当是与民自由。
康、梁、严等人的自由放任主张,在广大思变图强的士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撰写的许多文章引得洛阳纸贵,“自由”、“竞争”成了风行一时的时髦词汇。
(二)戊戌变法失败后经济自由主义的神学化、激进化与自由主义思潮的激荡
1898年“戊戌变法”的被镇压,意味着体制内合法变革可能性的基本丧失。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亡国危机日甚一日。经济自由主义由前一阶段的政策性走向神学化、激进化。神学化和激进化都带有绝对主义色彩。
神学化的主要代表是严复。1902年,他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为经济自由主义提供带有神学色彩的学理支持[5]。他深深折服于斯密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认为英国奇迹般的富强,实系导源于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在严复所作的‘按语’以及其他重要论文中,到处都在宣扬经济自由主义的福音”[6] (P218)。他提出“凡一切可以听民自为者,皆宜任其自由也”[4] (P480)。对于国际贸易问题,他认为“保商权,塞漏卮之说,无所是而全非”[7]。与严复一样,此时期康有为提出的“大同学说”也显露了神学化倾向。
经济自由主义的激进化倾向,集中体现在杨朱的绝对自利主义的流行。当时有相当多的人认同杨朱“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8] (P230)的主张。吊诡的是,可能由于救亡思潮的延续,对于“杨朱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9] (P313)的主张却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绝对自利与绝对利国之间的紧张,暗示了这股自利主义思潮的不稳定性。
(三)1905年土地制度论战的爆发与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逐渐消退
1905年,在保皇党与革命党之间爆发了一场以土地制度问题为中心的论战。论战的实质是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激进主义的交锋。保皇党人的落败,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渐趋消退和社会激进主义影响的扩大。
在论战中,主张土地私有的梁启超颇有新意地提出了个人财产权问题。他认为,人类利己之心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动机,而“一旦剥夺个人之土地所有权,是即将财产所有权中之最重要之部分而剥夺之,而个人勤勉殖富之动机,将减去泰半”。他还很有先见之明地注意到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旦举全国重要之生产事业,悉委诸官吏之手,则官吏之权力必更畸重,人民无施监督之途。”结果将出现“民主专制之恶现象”[10] (P584)。
尽管梁启超等人的言论不无可取之处,但他们选择了一个错误的话题同对手进行论战,不得不以论战的落败而告终。经此一役,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渐趋消退,尽管经济政策愈来愈体现自由放任的精神。1906年,甚至连严复也承认自由贸易主张不是普适的,认为“政之不可以一端论也”[4] (P23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辛亥革命前社会激进主义思潮的日渐高涨。尽管民国初年经济自由主义有了短暂的回潮,但式微之势已成。五四以后,社会激进主义再度勃兴,经济自由主义基本上边缘化了。
二、20世纪中期中国经济自由主义思潮
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和苏联经济建设成就鲜明对比的刺激下,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思潮漫过了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随着苏联计划经济和中国统制经济问题的逐渐暴露,1940年代后期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股经济自由主义思潮。1949年后,这股思潮在中国台湾得到了延续,促进了中国台湾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理论资源是西方新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
(一)1940年代后期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生成
1947年,陈振汉质疑了苏式社会主义公有制,担心生产资料公有将把“根深蒂固的资本家的勤俭美德、进取精神扫地以尽”,使“生产活动归于停滞,整个物质文明寿终正寝”[11]。1948年,他指出苏式计划经济并不是所谓经济民主,而是政府垄断资源配置权的经济专制。吴景超也指出了计划经济中生产要素支配权的少数人专断问题,疑虑少数人滥用其权利,逞其私意来支配生产因素,给大众带来不可胜言的伤害。
1948年,留英归来的蒋硕杰对计划经济作了严厉的富有学理性的批判:(1)生产效率低下。集体计划经济易造成生产事业的官僚化,且“生产因素既然由中央计划当局用配给方法分配于各生产单位,则各生产因素未必能颁于其边际生产力最高之生产机构内”;(2)政治自由匮乏。“生产事业尽属国营,全国的就业人员,除极少数自由职业者外,尽属政府之公务员或雇员。有野心的政府即可利用之以控制全国人事之黜陟。”[12] 尽管不清楚他是否读过哈耶克于1944年在英国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一书,但这些观点与哈耶克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蒋氏主张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即使是国有企业也要遵循竞争原则;在市场与计划的关系上,以自由价格机构为主而以集体计划为辅。在某种程度上,蒋硕杰的自由经济思想代表了其时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最高水平。
同年春,胡适归纳了“极权”国家的经济政策特征。他说:“不论是共产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或农业集合主义,都是政府不容分说,不择手段地强迫推行的一个划一的制度。在极权的国家内,劳工运动已经不存在了……在那里,没有罢工的事件,没有劳工的抗议,唯一的消极抗议——怠工,也被认为是罪大恶极的。”[13]
1947年前后,还有许多学者从维护政治自由的角度,质疑和批判了统治经济和计划经济,尽管他们未必赞同经济自由主义。例如,陈岱孙曾指出:“经济自由日就削弱的趋势不可否认”。“我们所怀疑而关怀的就是政治自由是否会随经济自由之消灭而消失”[14]。
1940年代后期,经济自由主义者摆脱了就经济问题谈经济问题的言说方式,通过引入政治自由话题,实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振衰起弊,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力。面对学术界和舆论界对过度国营化的抨击,国民政府于1948年春颁布了《国营事业配售民营实施办法》,但由于政局的剧变,此办法没有来得及实施就被中止。
(二)二·二八事变与195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台湾的延续
台湾光复祖国后,国民政府在台大规模推行统制经济政策,酿成了民怨[15] (P639),终因台北市专卖局军警检查非专卖香烟严重失当而激起1947年“二·二八事变”。28个台湾省地方团体联名致函国民党中央,强烈要求“废止省营贸易并专卖制度;除国防上必要之重工业暨银行、铁路、电信电话外,一切事业归民营”[16] (P76)。国民党被迫反思其在台推行的统制经济政策。蒋梦麟向蒋介石进言:“关于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应尽量缩小一点。”“凡公营之轻工业,应尽量售予民营。”[17] (P22)白崇禧也提出“极力减少公营企业之范围”[17] (P239)。
国民党退据台岛后,不得不更痛彻地反思其在台湾地区和大陆一再丧失民心的惨重教训。鼎革之际,蒋硕杰、夏道平等一批经济自由主义者渡海赴台,继续传播自由经济思想。1950年代初,“台湾某些圈子里曾谈论过建立指令性经济,但是,这种动议受到了抵制”[18] (P55)。在与国家干预主义者的论争中,市场论者和民营论者占了上风,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大有盖过统治经济思潮之势,并实现了由在野向在朝的转变。受蒋硕杰、邢慕寰等人的影响,1950年代中国台湾经济政策的重要制订人尹仲荣,即主张藏富于民、发展自由市场经济、推动外汇和贸易自由化[19]。胡适在一次题为“从到奴役之路说起”的演讲中,也“公开忏悔”了1949年前自由主义者在抵制统治经济政策上的不作为乃至推波助澜[20] (P170—172)。1950年代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为中国台湾经济的自由化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堪称中国台湾经济奇迹的先声。
三、20世纪晚期中国经济自由主义思潮
鉴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积弊和“文革”带来的乱局,1978年底,务实的领导集团启动了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进程。在此背景下,经济自由主义思潮逐渐生成,在思想论争中几度涨跌,并最终于1992年取得了思想竞争的决定性胜利。1998年后,新自由主义因素不断滋生,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开始了回落和转折。这一时期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理论资源,在其前期是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其后期则是西方新经济自由主义。
(一)198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在大陆的生成与几度涨落
改革开放启动后,一些务实的经济学者提出了带有经济自由主义色彩的主张。例如,卓炯提出,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关键就是要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董辅礽主张,所有制改革是与运行机制改革并重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方面,必须改革所有制的形式和结构。蒋一苇提出了著名的“企业本位论”,主张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企业经营机制[21]。
由于放权让利改革的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在改革初期出现了赤字扩大、通货膨胀等问题,引发了一场从1981年持续到1984年的关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争论。一些人认为经济混乱是削弱计划控制造成的,主张回到计划经济体制。这种观点受到了具有经济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们的抵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基本上被官方所接受。
1988年到1989年间,由于价格双轨制久拖不决,通货膨胀和经济领域腐败现象不断滋长,又引发了一场关于计划和市场的激烈争论,经济学界判然分成了计划和市场两个学派。吴敬琏、董辅礽、高尚全等学者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一度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一部分而遭到批判。
(二)1992年起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再一次高涨
1990年前后经济发展状况的低迷和徘徊,给了经济决策的制定者们很大的压力。保守主义思想的风行,使公众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景产生了疑虑。此时,有一些坚定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继续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1991年,吴敬琏、刘吉瑞明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探索的“结论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体制”[22] (P54)。
1992年春,邓小平到南中国视察,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他以一个政治家的胆魄为关于市场化改革的争鸣一锤定音。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3] (P373)邓小平虽不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但他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务实的宽容,使其最终得以成为1990年代的主流经济思潮。
从1992年起,围绕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结合中国国情,经济自由主义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出版了大量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主题的著作,提出了许多与时俱进、富有创见的政策建议,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三)1998年起新自由主义因素的滋生与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回落
1998年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转折点。亚洲金融危机的波及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导致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指导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的上涨。政府在干预经济运行和发展方面的冲动,压缩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空间。
与此同时,随着接受过西方经济学训练的学者群体逐步走向前台,在试图改革旧有体制的过程中,经济自由主义思潮中回避社会责任的新自由主义因素逐渐滋生。受其影响,放弃政府的经济管制与放弃政府的社会责任的论调并存,导致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出现了很多偏差,引起了公众的质疑,最终引发了一场从2004年夏持续至今的关于改革的公共讨论。在讨论的展开过程中,经济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回落。
耐人寻味的是,在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框架维持不变的情况下,从2003年开始,新自由主义遭到了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在经济发展需要不需要宪政保证这个问题上,经济自由主义学者逐渐站成了结合论与分离论的两行[24]。经济自由主义思潮似乎开始了分流。
四、对20世纪中国三次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评论
20世纪见证了中国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起伏,也见证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曲折。某种意义上,前者是后者的隐喻和象征。的确,“思想的闪电总是走在现实的雷鸣之前”[25] (P163)。在经济近代化迅速推进但依然存在不确定性的今天,对20世纪中国三次经济自由主义思潮作一总结和检讨,既有助于把握其演化规律,更有助于引为镜鉴。
(一)20世纪中国三次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共同特点
1.发生机理上的响应性。三次经济自由主义思潮都是在整个社会体制出现了系统性危机之后才发生的。社会危机暴露了经济问题,迫使人们反思国家干预主义或社会激进主义经济政策。在此意义上,社会现实的乌云总是走在经济思想的闪电之前。
2.目标导向上的工具性。由于发生机理上的响应性,三次经济自由主义思潮都主要是以拯救时局为目标导向的,而不是以逻辑的完善和知识的增进为导向的。在思潮中提出的自由经济思想大都成了“救亡”、“复兴”或“改革”的工具。工具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在其表现形式上,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是政策建议,而不是理论分析。
3.发展动力上的论战性。由于以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为论题,三次经济自由主义思潮都是在与国家干预主义或社会激进主义的论战中高涨或跌落的,而且由于论题的限制,经济自由主义往往受到后两者的夹击。在论战过程中,大众媒体充当了重要的平台。
4.理论资源上的外来性。出于批判的需要特别是论战的需要,在三次经济自由主义思潮中,经济自由主义者主动吸纳了西方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新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或市场社会主义等理论,并将其应用到中国语境中。但在吸纳外来理论资源过程中,也存在着不顾中国情境而盲目搜寻和照搬照抄的情况,为其论战对手提供了攻击的把柄。
(二)三次思潮所显示的20世纪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演化路径
20世纪中国三次经济自由主义思潮,集中显示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演化历程。这一历程有三个重要节点:(1)19世纪末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和戊戌变法被镇压,引起了激进的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发生,但在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赢得广泛的认同;(2)1940年代中期苏联计划经济和中国统制经济问题逐渐暴露,引发了保守的基于政治道德判断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发生。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也以昙花一现告终;(3)分别在1950年代初的中国台湾和1970年代末的大陆,执政党面对危局被迫采纳自由经济思想,引致了强调市场与国家相结合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发生。经济自由主义开始由在野走向在朝,并转变成一种社会思潮。概而言之,在整个20世纪里,在经济思想的生存竞争中,调和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最终胜出。就其实质来看,这是一种发展中心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
20世纪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演化,比之中国古代民营经济思想的演化,体现了某种路径依赖。严清华和杜长征的研究表明:“古代民营经济思想演化历程(尤其是西汉以后)的显著特征,就是在理论主题上从多元化和多样化逐渐收敛到财政中心主义,最终稳定在如何处理国家财政收入—民营经济发展的关系这样一个主题上。”[26] (P286)以司马迁“善因论”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与以贤良、文学“反与民争利论”为代表的保守主义都没有得势,而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出现的以发展民营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的调和主义经济思想,却最终大行其道。20世纪经济自由主义的演化也具有同样的特征。主张绝对自由放任的激进主义和基于政治自由考量的保守主义(同“反与民争利论”一样,也是政治伦理导向的)都没有获得国家权力的认同,调和主义却最终成为主流经济思想,并演变成一种官方学说。
这一演化历程的选择机制,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强化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对经济发展思想主题的限制。如约翰·穆勒所指出的,“在特定时代或国家的特定环境下”,即在“公众过于贫穷没有必要的资金可以支配,或知识过于落后不能判断其结果的价值,或不完全习惯以共同行为作为可能的手段”[27] (978)的场合,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参与经济活动。20世纪中国的情形正是这样。特别地,在外贸主权丧失的情况下,自由贸易主张更是具有先天的局限性。西欧近代经济自由主义的产生,部分地得益于18世纪中期对国际经济自动平衡机制的讨论[28] (P86)。但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已不存在国际平等贸易这样的客观条件。这些因素决定了经济自由主义必须把国家干预纳入其理论视野中,否则不可能成功地影响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