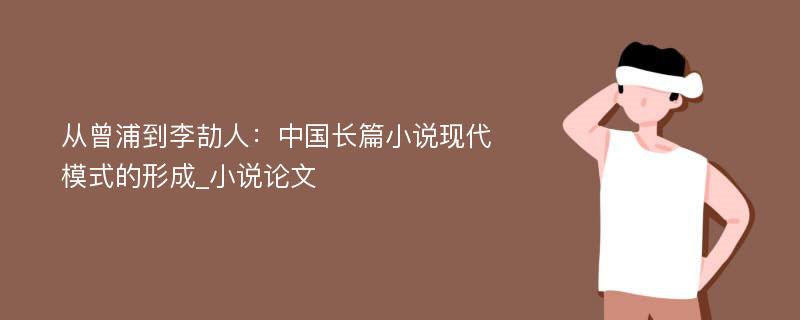
从曾朴到李劼人:中国长篇历史小说现代模式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长篇论文,历史小说论文,模式论文,曾朴到李劼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3)06-0092-07
一
中国历史小说的传统形态有两种:一种是《三国演义》所代表的历史演义体,一种是 《水浒传》所代表的讲史性英雄传奇[1](284页)。演义体小说尊崇正史,以艺术形象再 现正史所叙述的历史“真实”;英雄传奇,则“史”的细节未必可靠,但作者对历史事 件与人物的道德评价,却必定顺乎主流意识形态而“不逾矩”。也就是说,附会正史的 历史观与道德观、主人公必具英雄品格,是传统历史小说最基本的两个元素。
中国历史小说的现代转型,始于曾朴的《孽海花》。《孽海花》的历史叙事,摆脱了 一般历史小说演义正史的模式,它不直接写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而是“避去 正面”,借世俗化的“有趣的琐闻逸事”,“来烘托出大事的背景”[2](128-129页), 展现一种由世俗风情和人的道德生活构成的“风俗史”。其次,它的中心人物,不是历 史上的英雄伟人,也不是具有超人品格的豪杰奇人,而是一些在道德品性、行为方式上 有明显缺陷、不带崇高色彩的“非英雄”。
《孽海花》男女主人公金雯青、傅彩云,其原型是晚清名士洪钧及其出身名妓的妾赛 金花。这两个人物,既属上流社会,却又并非上流的中坚;他们经历了晚清最后几十年 风云变幻的历史,但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他们只是随波逐流、基本不能影响历史进程的 平凡人物(注:关于赛金花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的种种义举,以及她与瓦德西的关系 ,排除民间流传的夸大,也仅仅为小说提供了故事的趣味性和传奇色彩。),不具备任 何道德与价值的理想性。
金雯青虽贵为状元和朝廷高官,但并不是重要的历史人物,甚至在那一段历史中根本 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庸官。他同治5年考取状元,经过大考成为翰林院侍讲,不几年又 得到出使德、俄的美差,其名誉和地位,是靠读死书、撞大运获得的。他本人既缺乏真 知和才干,更缺乏热情与活力。中法战争爆发之际,金雯青与他的一群状元出身的同僚 ,竟不知法国究竟是何许国度。金雯青的生活道路、精神方式,是那个时代平庸而走运 的读书人的代表。面对西学和洋务派吃香的大趋势,他也产生过危机感,可他对西学、 洋务的向往,仅仅是为了在官场更有“出息”。他钻研舆地学,很大程度上是盲目“慕 新”,动力仍然是“功名”。由于无知,他花重金从俄国人手中买的“中俄交界图”, 却是将中国若干领土划到俄国境内的阴谋图。惊人的愚昧无知,闹出了“一纸送出八百 里”的历史笑话。
傅彩云在小说中的地位,颇能显示曾朴历史小说意识的现代特征。她出身风尘,美貌 风流,被金雯青娶为妾后,并不束心收敛做良家妇女。下自贴身男仆,上至德国军官, 甚至旅途邂逅的船主,都成为她卖弄风情、苟且偷欢的对象。以风流美丽的女子做历史 叙事的主角,在《桃花扇》等作品中尽管已有先例,但傅彩云并非李香君。李香君虽是 风尘女,却具有高贵品格,其识大局、明大义、关键时刻代表正义挺身而出的气概与见 识,堪称巾帼英豪。傅彩云的品格,更像中国传统小说中的“红颜祸水”,是一个道德 上有严重缺陷的“坏女人”。这样一种女性,在中国传统小说中,一般是否定性角色, 小说的英雄主角往往藉着对这些淫荡之妇实施无情报复、残酷惩罚而完成其圆满的道德 形象,一般读者或听众也因此得到极大的“审美”满足,《水浒传》中的潘金莲、潘巧 云就是这样。《孽海花》的特出之处在于,曾朴并不从道德上评价傅彩云,而是从人性 的角度刻画这个形象。傅在小说中不但不是“反面”角色,反而有一种逼人的魅力。她 的放荡,既有妓女的天性,更是在特殊环境中对传统男性权威的挑战——“你们看着姨 娘,本不过是个玩意儿,好的时,抱在怀里,放在膝上,宝呀贝呀的捧;一不好,赶出 的,发配的,送人的,道儿多着呢!……我的性情,你该知道;我的出身,你该明白了 ;当初讨我的时候,就没有指望我什么三从四德,三贞九烈,这会儿做出点不如你意的 事情,也没什么稀罕。你要顾着后半世快乐,留个贴心伏伺的人,离不了我,那翻江倒 海,只好凭我去干!要不然,看我伺候你几年的情分,放我一条生路,我不过坏了自己 罢了,没干碍你金大人什么事。这么说,我就不必死,也不犯着死。若说要我改邪归正 ,阿呀!江山可改,本性难移。老实说,只怕你也没有叫我死心塌地守着你的本事呢!” (第二十一回)这哪里是在向丈夫求饶,简直是代表千百年的女性向男性讨伐和报复!金 雯青面对她的放荡和泼辣,除了痛苦,便是无奈,完全没有大丈夫气。金在傅面前如此 窝囊,恰恰在于他无法抵抗傅彩云的美貌和情欲,他惟恐失去这个尤物。《孽海花》的 现代品格,正在于它的“出格”。作者几乎完全摆脱了传统道德观念和传统小说的善恶 评价去塑造人物。金雯青的窝囊、无能,恰恰反映了人性中非理性力量的强大;而傅彩 云惑人的美丽与情欲,她“磊落”的淫荡,都令人想到法国文学从莫利哀到雨果,从巴 尔扎克到福楼拜作品中那些风情万种而又道德越轨的女主人公。
一部没有英雄和失去“道德准绳”的历史小说,对于读惯传统历史小说的人来说,是 会感到不解的。蔡元培承认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却“有不解的一点,就是这部书借傅彩 云作线索,而所描写的傅彩云,除了美貌与色情狂以外,一点没有别的”[3](99页)。 林纾对此书也大加推许,但认为“就彩云定为书中主人翁,误矣”[2](135页)。胡适不 赞同《孽海花》为“一流”(注:1917年胡适与钱玄同讨论中国古典小说,胡适认为《 孽海花》只能算二流。见《新青年》第3卷第4号胡适与陈独秀的通信。),仍然是潜意 识中与蔡、林相似的“士大夫”心态和传统“历史叙述”意识在作崇。
《孽海花》在“小说”和“历史”两方面,为中国历史小说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他 不在史学家的话语中复述,他不是把史学家文字的记载复活为实际的历史,而是为没有 定型的中国近代史创造一种艺术的表述,把历史家还没有来得及记载的实际存在的历史 变成小说。”[1](285页)齐裕焜先生这段话,完全符合《孽海花》的创作实际 ,但有意思的是,这段话,并不是针对曾朴说的,而是对李劼人小说的评价。
在过去十多年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当谈到中国现代长篇历史小说时,人们往往注意到 李劼人的开拓性,而忽略了这个开拓的实际先驱是曾朴(注:最早从“历史小说 ”角度评价李劼人长篇小说现代性开拓价值的,是1987年杨继兴的论文《长篇历 史小说传统模式的突破——论李劼人历史小说的独创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后来的现代历史小说研究多采纳杨文观点。) — —如果说此前的历史小说是对已有定型的中国古代历史艺术地重写或改写,李劼人的历史小说则是为没有定型的中国近代史创造一种艺术的具文。前者的根据是历 史 家的文字的记载,它们的任务是把文字的记载重新复活为实际的历史,实际的生活史 和 精神史,李劼人的根据则是实际的历史,实际的生活史和精神史,作者的任务是 把实际存在的历史变成艺术的具文,变成小说[4](21-22页)。事实上,最早突破传统历 史小说“复活”“历史”模式、用“风俗史”形式再现时代风云、表现历史进程的,是 曾朴的《孽海花》。《孽海花》在历史叙事的意识、历史评价的尺度以及审美观念 上, 都突破了传统中国历史小说或史传文学的模式,体现出与西方现代小说一致的精神 价值 与审美特质。在以西方现代历史小说为参照的中国历史小说现代模式的形成过程中 ,曾 朴是开拓者,而完成者则是李劼人。但五四以来晚清文学在古典与现代之间长期 “失重”的研究状况,以及文学史上形成的以“五四”及革命文学为视点的主流话语, 使这个事实被遮蔽了。
二
没有材料显示李劼人曾经直接受影响于曾朴(注:李劼人中学时便遍读
古今文白小说,晚清新小说也在他的广泛涉猎中。但是,他本人没有专门谈到过曾朴。 参见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李劼人选集》第1卷),李劼人《谈创 作经验》(《李劼人选集》第5卷)等。)。但李劼人与曾朴历史小说渊源 的“同宗”——法国19世纪小说——却使这两位作家在历史小说的审美形态上,有了非 常一致的趋向,呈现出一种客观的传承或延伸。
1894年,曾朴入同文馆学法文。1898年,他结识了福建造船厂厂长陈季同。陈侨居法 国多年,精通法国文学并与伏尔泰等一流作家“常相往还”[5](111页)。在陈季同的指 导下,曾朴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系统学习和钻研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古典派、 浪漫派、自然派、象征派,无一不通。那段时间他几乎“发了文学狂,昼夜不眠,弄成 了一场大病”[2](191页)。曾朴实际是中国近现代最早系统学习西方文学的人,也是最 早、最系统翻译和介绍法国文学的人——“小说林”时代(1905-1908年),他翻译了雨 果的《马哥王后佚史》、《九三年》,译介大仲马;1927年至1935年,在与长子曾虚白 开真美善书店、办《真美善》杂志时,更系统地翻译雨果和法国文学(注:曾朴翻译雨 果剧本、小说、散文数十种。此外,还有左拉的《南丹与奈侬夫人》、莫里哀的《夫人 学堂》、福楼拜的《马笃法谷》及戈蒂耶等人的作品。曾朴还发表过不少法国文学批评 文章。参见曾虚白《曾孟朴先生年谱》、时萌《曾朴与法国文学》(《曾朴研究》第113 -1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等。)。那时,曾朴曾经与胡适讨论过现代文学创作水 平滞后的问题,认为现代作家外国文学修养的匮乏,是新文学难以产生经典的重要原因 [2](211-212页)。因此,他大力倡导译介西方文学。真美善书店和《真美善》杂志,就 是他对这一理念的实践。曾朴对西方文学的了解、对法国文学的修养,比很多五四新文 学作家都强。可惜的是,他的清末名士的“身份”,五四新文学事实上存在的偏见,遮 蔽了这个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奇人。
比较曾朴和李劼人长篇小说的构思过程、审美观念,我们很容易感受到法国文 学的启蒙和滋养,对这两位作家创作形态的形成,意义实在重大。
法国历史小说出现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受英国历史小说作家司各特的影响,法 国浪漫派作家开始了司各特式历史小说的创作(注: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准确说是历史 题材的浪漫传奇,但他被视为欧洲现代历史小说的开山者。),其代表作有大仲马的《 三个火枪手》等。尔后,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把“瓦尔特·司各特和荷马融为一体 ”[6](60页),以恢弘的历史气度和诗的语言,真实再现巴黎15世纪的人情风俗。这部 小说的出现,标志着法国历史小说由浪漫传奇转向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表现。雨果的《 九三年》,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卷帙浩繁的《人间喜剧》,构成法国19世纪 小说一种倾向与传统——以强烈的当代意识与社会政治关怀,“努力忠实地再现过去历 史的某一片断,或现代生活的某一侧面”[6](68页)。法国作家这种对现实的历史关怀 和巨大的表现热忱,甚至导致一种适宜宏大社会历史叙事的特殊文体“大河小说”形成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表示,他的小说将焦点对准当代社会,专门描写被历 史家忘记了的“道德的历史”和“风俗的历史”(注: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 参见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法国浪漫派》第222页;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 》下卷第17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法国现代历史小说由浪漫传奇到现实主义主潮的形成,与法国大革命以来充满变动、 革新的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法国社会进入一个历史大转折时期 ,没落的封建贵族、新兴的资产阶级、大工业产生的无产阶级,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尖 锐矛盾和激烈斗争,将法国社会各阶层都推向命运大搏斗的旋涡中,而社会在各种力量 的较量中发生着急遽变化。法国19世纪作家生存在这样一个“出生入死的时代”,不能 不“惊心怵目于它的奇谲,每一个作家都想写出它的长远意义”,“每一个作家都有一 部伟大的著作象征或总结他们的时代”[7](201页)。这导致一批伟大小说产生:《红与 黑》、《人间喜剧》之后,又有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左拉《卢贡- 马卡尔家族》等。巴尔扎克曾说,法国是历史,他就是它的书记员。这基本上反映着19 世纪法国作家一种主流的文学追求。对照看来,中国晚清以来的历史,也是一个空前大 变动、大转折的时代。“即前清末年而论,大事件不可谓不多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 ,戊戌政变,义和拳变,八国联军,以至民元革命。然而我们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的著 作,更不必说文学作品了。”[8](286-287页)(注: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中 的这段话写于1935年3月28日。)鲁迅去世前,“像样的”的历史小说,只有未完成的《 孽海花》一部,而《孽海花》,又被鲁迅、胡适早定性在“谴责小说”中,被“谴责小 说”的概念所遮蔽。李劼人的《死水微澜》,1936年7月才出版,鲁迅没有来得 及读到,却被当时文坛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强大的主流声音所淹没。即使这两位作家的 作品没有被遮蔽或淹没,晚清以来三十年间仅零星出一两位历史小说作家的事实,也不 能不促使我们反省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追求的某种偏颇与浮躁。所以,探讨曾朴、李劼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就有值得关注的价值。
曾朴谈《孽海花》的创作时说,他的宗旨是要表现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中国充满 巨大变动的三十年来的历史。“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 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 把这些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联系的一些细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 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2](131页)曾朴这 部小说拟定的回目有60回,包括了洋务运动以来至维新变法之后中国的历史。如果这部 小说能够按计划完成,无疑将是一部恢弘的巨制。
曾朴未完成的叙事,若干年后在李劼人的创作中得到继续。只是,历史的延续 ,使李劼人的叙事从更接近他本人历史经验的19世纪末庚子事变前后开始。与曾 朴相似,李劼人历史小说的写作,与法国文学的启蒙直接相关。李劼 人 1919年至1924年留学法国,对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一派小说格外有兴趣,后来翻译过包 括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李劼人译本作《马丹·玻娃利》)在内的若干19世纪法 国小说(注:李劼人翻译的法国文学作品还有福楼拜《萨朗波》、莫泊桑《人心 》、都德《小东西》、卜勒浮斯特《妇人书简》、龚古尔《女郎爱里莎》、德莱士 《文 明人》、维克多·马尔格里特《单身姑娘》、罗曼·罗兰《彼得与露西》、左拉《 梦》 等。)。1925年,李劼人从法国归来伊始,便计划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作 文学 的记录——“以一九一一年即辛亥年的革命为中点,此之前分为三小段,此之后也 分为 三小段”,“打算把几十年来所生活过,所切感过,所体验过”的,“意义非常重 大, 当得起历史转捩点的这一段社会现象,用几部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一段落一段落 地把 它反映出来”[19](3页)。曾、李二人对刚刚过去的社会历史的兴趣,及叙述历史 的方 法,具有惊人的一致。这种一致,根源于他们对法国19世纪小说宏大历史叙事的师 承。
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程,是以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涌入开始的。这个过程使中 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经济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乃至社会用语,都发生了巨 大变化。表现和评价这段历史,必须有超越传统历史叙事的语言才能完成。林纾曾经有 几部叙述晚清大事件的历史小说,如写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的《京华碧血录》(《剑腥 录》)、叙述武昌起义的《金陵秋》等,但是,林纾秉持“良史”立场,采用史汉笔法 ,其语言形式所运载和表现的历史观、道德观,都是合于传统圣经贤传的,这些小说至 多可作史料的参考,根本无力揭示导致历史事件发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根源。曾朴的《 孽海花》,使用的是传统小说的章回体,但由于他对法国文学博大历史情怀与深厚人文 精神的接受,《孽海花》在结构、语言、审美意识上,都突破了传统小说,叙事结构呈 现立体交叉的宏伟形式,人物塑造上体现着文化反省与精英批判的现代立场,这部小说 在传统形式中实现了对传统的颠覆、解构,非英雄、非道德的主人公,第一次成为历史 小说的主角。
三
同样,“风俗史”、“非英雄”及“非道德”的现代历史叙述,在李劼人的长 篇小说中,由于现代白话和口语的娴熟运用,得到比曾朴小说更精彩和成熟的表现。
《死水微澜》中的男女主角,一个是“打流跑滩”、称霸一方的袍哥头子罗歪嘴,一 个是不安贫乐道、最终堕落的女人蔡大嫂。《暴风雨前》的郝又三、武大嫂,分别是无 所事事的公子哥和贫民窟的暗娼,决不能代表社会之善,当然也并不是恶。蔡大嫂出身 于乡下贫民家庭,但倾慕虚荣、繁华,一心想过城里人的生活。她少女时代就发愿:宁 愿给城里的老爷做填房,也不嫁乡下朴实巴交的农民过穷日子。她崇拜可以“走官府, 进衙门”的罗歪嘴,敢面对众人的指戳公然做罗的情人,与罗一起招摇过市。这种行为 ,在道德叙述中,可以称为无耻。但有趣的是,李劼人并不对她及罗歪嘴进行
道德的谴责,他只是将他们作为清末中国社会大变动前夕中国内地乡镇的“风俗”之一 斑来写,甚至,在李劼人的笔下,蔡大嫂与罗歪嘴之间的恋情,竟然具有相当
的合理性;他们不道德的关系,竟然具有强悍野性的美感。罗敢于倚强扶弱,伸张正义 ,引起蔡大嫂的崇拜;罗理解女性、善讨女人欢心,这些都是蔡大嫂的“木头”丈夫望 尘莫及的。在人物塑造上,作者遵循的是人性的尺度和冷静写实的原则,这样,罗、蔡 令人瞠目结舌的畸形爱情,便超越了道德,而成为审美的对象。
这些地方往往使我们感受到,由深厚人文精神支持的法国文学的博大与宽容,给予了 李劼人超越的气度,“道德”的评价在李劼人笔下退隐,人性的真,上
升为艺术的美。罗歪嘴、蔡大嫂,令人想到于连与德瑞那夫人(《红与黑》),爱玛及与 她私通的男性(《包法利夫人》),还有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贵族女性以及围绕在她们裙 下的各色男子。法国小说在描述这些非道德的男女时,其冷静与客观的态度向来是超越 了道德的。它们不是简单地将人物推到道德的法庭进行审判,而是以超越道德评判的眼 光,引导我们思索人物堕落、犯罪的社会与个人的根源。李劼人笔下的罗歪嘴 ,身为袍歌头子,是旧时代与官府关系微妙的“强人”,属于民间霸主。在某些相对稳
定的历史时期,封建帮会除了在民间欺行霸市之外,通常也遵循一种“盗亦有道”的规 矩,且常常有些扶弱济困的善举。从某种角度说,它们扮演着官府管辖之外的维护社会 平衡的角色,代表着民间的意识形态。罗歪嘴的行为,他与洋教徒的冲突,反映着当时 中国社会与西方文化的尖锐对立。官府对他的态度,也生动地揭示了中国政治集团对西 方既怕又恨的心态。李劼人的《死水微澜》,背景是19世纪末,在社会大变动
的前夕,偏僻而富庶的川西乡镇尚处于小国寡民的自足状态,传统社会伦理和秩序还维 持着,但民间与洋教的冲突,已经暗示着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爆发的一刻即将来临。李 劼人追求客观性的姿态,使他能够超越30年代的阶级论语境,真实地刻画蔡、罗 这些善恶交织的人物。
如果说曾朴的《孽海花》对法国历史小说的借鉴,主要在打破传统历史小说的“正史 ”窠臼,使历史叙事“世俗化”,那么,李劼人的“三部曲”,则以更从容的姿 态,将法国历史小说从精神到形态都统统借鉴过来,创作了中国现实主义的“大河小 说 ”。
“大河小说”是19世纪中期以来法国长篇小说的重要体制,由巴尔扎克率先实践,被 众多法国作家钟爱(注: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托 夫》、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等,均属大河小说。)。它的特点是,多卷体,长 篇幅,描写年代长,人物多,背景广阔,容量极大,最适合于历史叙事。巴尔扎克的《 人间喜剧》包括小说近百部,人物数千,通过“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 活”、“政治生活”、“军事生活”、“乡村生活”等各个方面,来进行“风俗研究” ,真实而全面地再现了法国19世纪上半期从大革命失败到1848年资产阶级取得胜利这一 整段时期社会生活的全貌。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完全师承《人间喜剧》,以25 部长篇、一千余人物,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为法国“第二帝国”绘 制出“包罗万象”的历史卷帙。中国现代文学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以多卷体“大河”形 式进行创作的,都是与法国文学关系密切的作家——除了李劼人,还有巴金、茅 盾。巴金在法国待过几年,后来写过很多“三部曲”;茅盾虽然未曾去过法国,却对法 国文学非常熟悉,五四时期大量介绍法国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他的最初创作就是《 蚀 》“三部曲”。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三部曲,也是 师承法国大河小说而创作的多卷体连续小说。这三部曲仅仅是李劼人写作计划中 的一部分,由于社会动荡和作者早逝等原因,他的宏伟写作计划最终没能完成。然而仅 仅是这完成的三部,就充分体现出法国式历史小说的磅礴气势。
李劼人小说蕴含着一种由法国文学的滋养和影响带来的陌生化,发展和完善了 在曾朴小说中已露端倪的现代特征。郭沫若在读到李劼人的三部曲时,“整整
陶醉了四五天。像这样连续的破着整天的工夫来读小说的事情,在我,是二三十年来所 没有的事了。”[10](4页)
值得注意的是,曾朴、李劼人式历史小说的创作,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并没 有形成潮流。1925年,李劼人刚从法国回来,便开始酝酿写中国的“大河小说 ”。但由于生活动荡不安——他在成都大学任过教授,尔后辞职;开过餐馆,又倒闭; 先后在重庆、乐山经营纸厂等实业,耗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直到十年以后,他才集 中时间在三年之内写完《死水微澜》(1935年)、《暴风雨前》(1936年)和《大波》(193 7年)。也就是说,这本该在20年代就出现的小说,推迟到30年代中后期才完成。但是, 李劼人迟到的创作,却仍然是中国现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先行者。因为,五四以
来的二十年中,中国新文学还没有产生过这样一种具有现代精神的宏大的历史叙事(注 :茅盾的小说实际是比较接近法国式“当代史”叙述的,但是,由于他更多采取截取社 会历史进程中的“现在”时刻,并不试图纵向展示历史的历时性,因此一般未被归入历 史小说。)。这不能不令人思索:在传统的演义体历史叙述被抛弃后,历史小说似乎只 有借助一种外来模式才能建立起符合现代观念、表现现代思想和情感的叙述形式。五四 以来中国作家对西方文学的接受和借鉴,更多是注重精神,而忽略艺术的。所以,尽管 法兰西文学是五四新文学力倡的现实主义典范(注:五四时期《新青年》、《小说月报 》等有大量介绍法国19世纪文学的文章,还有法兰西文学专号。茅盾还将法国自然主义 作为新文学首先学习的思潮。),但俄国文学在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法国文学。
四
在创造现代中国历史小说的过程中,曾朴与李劼人,在师法对象、审美选择方 面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二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野中长期被遮蔽的命运,也极为相似 。这种被“遮蔽”,使他们的创作对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影响,注定是有限的。因此, 李劼人之后,并没有形成大河小说式的现代历史小说潮流。但是,他们的创作
及他们参与的法国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仍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中国现代 长篇小说出现了一种关注现实历史进程、以世俗生活一角展开的宏大历史叙事。在这个 过程中,另一位吸吮法国文学养料而成长的长篇小说大家茅盾,其对中国现代小说宏大 叙事的影响,不可忽略。
中国近现代小说作家,只要是在审美倾向上深受法国文学影响的,无论是模仿法国作 家有意创造“历史小说”的,还是并不标榜“历史”二字的,他们的小说,都不约而同 具有对刚刚过去或正在发生的社会历史进程进行刨根究底的兴趣,都不免富有宏大的结 构和“史诗”的气韵。尽管茅盾自我表白他既爱左拉,亦爱托尔斯泰,但他小说“社会 学”式的分析特点、叙事结构的恢弘、细节描写的精雕细刻等,都带有浓厚的法国文学 的痕迹。他并不自称其创作是“历史小说”,因而被研究者归为“社会剖析派”;但他 的小说,从来就是在为中国充满变动的大时代进行形象的记载。他的若干未完成的长篇 小说,从《霜叶红于二月花》到《子夜》,从《蚀》到《虹》,试图通过小说再现和探 讨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变动的历史轨迹,体现出与曾朴、李劼人小说相似的历史叙事特征。不同的是,曾朴、李劼人试图写出《人间喜剧 》、《卢贡-马卡尔家族》式的历时性长轴画卷,而茅盾描绘的只是横切面的“断代史 ”。由于特殊的文化环境,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终没有形成曾朴、李劼人式
的现代历史小说潮流,而茅盾式的宏大叙事——“社会剖析小说”——成为40年代以后 中国长篇小说最常见的模式。从40年代末丁玲、周立波及建国以后土改题材的长篇小说 ,到八九十年代张洁、李国文、路遥、陈忠实等的长篇叙事,大都属于茅盾式的历史叙 事。
当代历史小说既不发达,而且陈旧。无论是姚雪垠的《李自成》,还是二月河的帝王 系列,都基本回复到五四以前传统历史小说叙述豪杰、呈现“正史”的套路上。
收稿日期:2003-07-31
标签:小说论文; 李劼人论文; 法国作家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历史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包法利夫人论文; 读书论文; 死水微澜论文; 孽海花论文; 法国文学论文; 暴风雨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