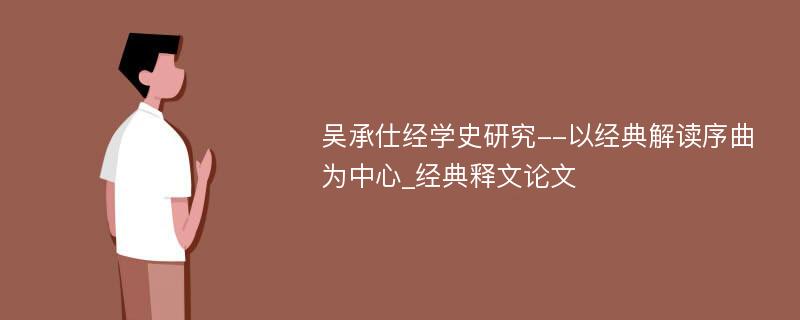
吴承仕的经学史研究——以《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史研究论文,经典论文,中心论文,吴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12)05—0021—09
一、引言
吴承仕(1884—1939),字检斋,安徽歙县昌溪人。父吴恩绶,邑廪生。曾任县知事,后任京师歙县会馆馆长。5岁入仓山源私塾读书。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17岁,考中秀才。翌年赴南京乡试中举人,列第三十九名①。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在保和殿参加举贡会考,被取为第一等第一名,点大理院主事②。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司法部佥事③。1914年章太炎大闹袁世凯的总统府,被囚禁于北京。吴承仕以司法官的身份常往探视,并请教学问,受业章门。次年,将章氏所言录为《菿汉微言》一书④。1919年,为呼应章太炎发起的“亚洲古学会”,在北京大学《国故月刊》发表《王学杂论》,深受章门师徒赞赏。由此渐无意政事而致力于治学著述。
1924年,随着被章太炎称为“洽闻强识,思辨过人”⑤的《经籍旧音辨证》等一批著述问世,吴承仕声名大振。他离开了供职十余年的司法部,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并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各大学讲授《国故概要》、《经学史》、《古籍校读法》、《说文》、《六书条例》、《三礼名物》等课程。
吴承仕的经学造诣极深,著述甚丰。在他短短的20年治学与教学期间,共撰写了《经学通论》、《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国故概要》、《尚书古文辑录》、《尚书今古文说》、《三礼名物略例》、《丧服变除表》、《三礼名物笔记》、《经籍旧音辨证》、《小学要略》、《六书条例》、《说文讲疏》等论著84种⑥。其研究范围涉及经学、诸子、小学、释道、史学、诗文等领域,尤其在经学上的研究成就最大,堪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经学大师。
吴承仕除了以经学家、小学家、教育家闻名于世之外,他还是一位勇于接受新思想,改造旧学,面向社会的学者。自1930年起,他就在同事范文澜那里接触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共产党宣言》。此后又与他的学生,共产党员齐燕铭、张致祥密切来往,阅读大量马列著作,逐步学习和接受社会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新思想的指导下,他一方面从事改造中国大学国学系的课程,一方面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开展对古代经学、文字学的研究,1934年以后,撰写了诸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者对于丧服应认识的几个根本观念》、《从说文研究中所认识的货币形态及其他》等一批论文,并打算循此路径全面展开对三礼名物的新的研究。他的这些成就被后人誉为中国“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学的人”⑦。新思想的召唤和社会运动的激情,促使他创办了一系列宣传抗日救亡、红色思想的杂志,并于1936年秋天加入了共产党。1937年北平沦陷后,他逃难天津。1939年在天津染疾,潜回北平治疗无效,不幸逝世,终年55岁。1940年,延安各界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吴玉章等敬送挽联和花圈。
吴承仕逝去后,由于长期社会动乱,他的著述未能得到很好的保存和整理。20世纪8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在吴先生百年诞辰时曾组织研究活动,并出版《吴承仕文录》及《吴承仕藏章炳麟论学集》等,但仍有他的许多著作至今未能整理面世。今年是北京师范大学建校110周年,为纪念这位北京师大的先贤,特撰此小文,对吴承仕以《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以下简称《疏证》)为代表的经学史研究作一粗浅的阐述,企求认识其经学成就于万一,并就教于方家。
二、《疏证》的编撰背景与特点
《疏证》初版于1933年9月,是中国大学国学系丛书中的一部名著。从完成和出版的时间来看,应是吴承仕的经学研究比较成熟的时期。吴氏作为章太炎的入室弟子,学问和声望与章氏大弟子黄侃齐名,20世纪30年代曾以“南黄北吴”并称。章太炎在他晚年所写的《新出三体石经考证》中,其他人的论述皆未提及,唯独引用黄、吴之说,并曾专门致信吴承仕曰:“仆于《石经》古文所不解者数事,得君发明,此一事涣然若冰解矣。”⑧可见他在老师心目中独特的地位。
在吴承仕治学诸领域中,经学成就是最可称道的。然而考察他早期的研究成果却是颇专注于诸子和小学。诸如,1921年撰成《经籍旧音序录》,1922年撰成《通语释词》,1923年撰成《经籍旧音辨证》,以上都属小学类;1923年校《盐铁论》,1924年撰成《淮南旧注校理》,同时又着手《论衡校释》,以上则属诸子学研究⑨。1924年8月9日,章太炎在得知吴承仕的治学近况以后,去信对吴氏的治学方向加以指导,函曰:
大著近想更富,既有《淮南》旧注校理,又勘《论衡》,功亦勤矣。……足下于学术既能缜密严理,所得已多,异时望更为其大者。佛典已多解辨之人,史学则非君素业,以此精力,进而治经,所得必大。……次则宋明理学,得精心人为之,参考同异,若者为摭拾内典,若者为窃取古义,若者为其自说,此亦足下所能为。昔梨洲、谢山不知古训;芸台、兰甫又多皮相之谈,而亦不知佛说。非足下,谁定之?⑩
信中对吴氏治学颇加赞赏,然而又及时点拨指示其“更为其大”、“所得必大”者。这就是先治宋以前经学,再治宋明理学。从广义上讲,后者也仍是经学的范围。恩师的谆谆教诲和寄予厚望,犹如黑夜明灯,照亮了吴氏治学的方向,促使素有经学修养的吴承仕及时地警醒。从此后他的研究对象和著述成果,可以看出他转向经学研究的明显迹象。先是《尚书》学的研究,此后的三礼名物、《春秋》学研究等。经过近十年的积累,为撰写《疏证》一书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因此,章太炎的指导是他撰著《疏证》的重要契机。
吴氏曰:“愚为《序录疏证》,本欲略明经典源流,为学校讲疏之用。”(11)故《疏证》的编撰还与吴承仕入主中国大学国学系后,振兴国学系,改造课程设置,讲授经学史的教学实践有关。中国大学是一所私立学校,经费紧张,聘请不到著名的教授,其国学系因此而惨淡经营,课程开设简陋,被人另眼相看。吴承仕自1926年出任国学系主任后,开展了新的课程设置的改革,编制了正式的教学大纲。大纲把大学四年的课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打基础的阶段,着重于博,丰富学生的知识;第二阶段为提高的阶段,着重于精,以求发展学生的专长。后来他在《本系的检讨与展望》一文中回顾说:“当初我们在这里上课,每点钟两块半钱”;“度着那种艰苦的生活,我们也没有灰心,只知道在客观的条件下,渐渐的改变我们的课目,充实我们的内容,企图本系的发展。”(12)吴承仕倡导的改革,为国学系带来了生机,而他在应付繁忙公务外,也身体力行,亲自讲授多门国学课程,其中《经典释文序录》一课就是系统讲述经学史,拓展学生知识面的重要课程。吴承仕选择疏证和讲授《经典释文序录》是有缘由的。首先,清亡之后,新学滋漫,经学衰微。清世流行的经学余韵重在小学,以小学论经,或以经师为主,或以典籍为中心,未能系统阐述各时代经学之意义及历代之变迁。清季虽有皮锡瑞以会通眼光撰述的《经学历史》,然过于简略,又未能充分吸收清代经学考证的成果,特别是未能利用清中叶以降新出现的经学新史料,如从敦煌和日本发现的唐残卷郑玄《论语注》、从日本发现的皇侃《论语义疏》等等。此外,皮锡瑞《经学历史》中明显的今文经学倾向也颇令人诟病。正如章太炎后来给吴承仕的信中所说的:“仆每念近世学校中能理小学者多有,能说经者绝少。然有之,大氐依傍今文,指鹿为马,然尚不可骤得。”因此,他对吴承仕研究和宣讲经学史大为赞赏,认为“此之一线,固不可令绝也”(13)。
如何撰写符合时代需求的经学史新著呢?吴承仕以南朝末年陆德明所撰的《经典释文序录》作为灌注新义的最佳选本。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为《周易》以下12种儒家经典及《老子》、《庄子》共14部经典注释音义。全书采集广博,音义兼解,为后世治经者所宗。其卷一《序录》记录了唐以前经学发展沿革的基本线索,记录了除《孟子》之外的12部经书的产生、授受源流及相关的经师、典籍,不啻一部简明的唐前经学史。
《疏证》以陆氏《经典释文序录》为基础,采用古文经学家治经的方法。在书中详征博引,阐述了群经兴衰及经学史变迁,考证了主要人物和典籍,论断精辟。《疏证》的撰述有以下特点:其一,详加校勘,吸收了《经典释文》通志堂本、宋本的优点及卢文弨等清人的一些校勘成果。这些成果在《疏证》行文中时有提及。其二,以章句之法,将《序录》原文按文意分段疏解,疏解首句常点明原文段意。吴氏在《序录·条例》的题解中曰,“此文自述著述体例……相其文势,自分章段。今本皆随行直下,总为一篇”。“兹就其文义,析为数章,略加笺记”(14)。于是将《序录·条例》分为数段,第一段的疏证文首句曰“此明本书与旧作不同”;第二段的疏证文首句曰“此明五经大义世有常宗,不须具说”;以下皆类此。综观全书,这种章句之例则常用在注解长段正文的疏证之中。其三,用考史源之法。陆氏《序录》多本《汉书·艺文志》、前四史传记及旧家诸说。《疏证》追踪史源,或明《序录》言之有据,或加以补充辨证,以明是非曲直。如《序录·注解传述人》“周易”首段之后,《疏证》曰:“自‘伏羲氏’至‘画八卦’,约《下系》‘九事’章文,《艺文志》‘易类’亦引之。”(15)指出《序录》此段叙述,裁自《周易·系辞下》的内容,与《汉书·艺文志》易类小序所述相似,以明其来有自。其四,疏解考证之法,此为全书主要形式。《序录》以“注解传述人”为阐释14部经典产生、授受源流的主体。每部经典为一单元,前为序论,叙述各经渊源、产生、授受、流变,其中兼述历代经师行迹及典籍流传;后为目录,记传注各部经典的作者、书名、卷数。吴氏《疏证》针对不同内容采用不同方法。对于序论,则以疏通源流,考证史实为主;对于目录,则以考证作者行状、典籍真伪、注解书名异同、卷帙分合为主。其五,论断。徐复观认为经学史著作“有传承而无思想,等于有形骸而无血肉”(16);“只言人的传承,而不言传承者对经学把握的意义”,则“经学成为缺乏生命的化石”(17)。《疏证》则既言传承,又有论断,从而突破了以往古文经学家治经学史的局限。书中有许多论断,如《尚书》学史中论清人丁晏《尚书余论》辨伪孔传形成的意义(18);《诗经》学史论小毛公在毛诗传授中的作用(19);《论语》学史中论后出皇侃《论语义疏》本的校勘价值(20),等等。或纠前人之误,或申自得之见,从而凸显了《疏证》的学术品位。
这里还要提出的是,《疏证》出版之后,吴氏在讲授过程仍不断对此书作大量的批注,加以补充,反映出他严谨的治学精神。《疏证》以其详博的材料,深入的论述和独具特色的编撰方式,为人所称道。其值得讨论的学术价值,归结为荦荦大端者有二,一是对经学史的梳理,二是对经学史的考订。
三、《疏证》对经学史的梳理
章学诚在谈到校雠群书、条理学术时认为:“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21)吴承仕的《疏证》在经学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之一,则表现在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旨,梳理了古代经学史的先后次第及渊源流变。
(一)对诸经次第的条理辨析
诸经次第的排列,或反映诸经产生的先后,或反映人们接受的次序,从中亦可看出各经在经学史上所处的地位。所以陆德明在《序录》中专设《次第》一章给予阐述,认为五经六籍“不相沿袭,岂无后先?所以次第互有不同”。吴氏《疏证》在《序录·次第》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衍为三个层面:一是六经次序;二是十三经中相关经典的次第,如三礼、《春秋》三传;三是单经中不同注家的先后,如《诗经》鲁、齐、韩三家。这是《疏证》辨析诸经次第意义的新发展。
其一,关于六经次第。六经次第,汉前与汉后排列明显不同。《序录·次第》曰:“如《礼记·经解》之说,以《诗》为首;《七略》、《艺文志》所记,用《易》居前……今欲以著述早晚,经义总别,以成次第,出之如左。”陆氏述六经次第比较简略。但他提出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以著述早晚排六经次序。《疏证》进一步注解了《序录》的观点,指出“《经解》以《诗》、《书》、《乐》、《易》、《礼》、《春秋》为次”;《七略》、《汉书·艺文志》“首《易》,次《书》,次《诗》,次《礼》、《乐》、《春秋》”,基本上沿袭了《序录》的看法。其略有发挥者,引郑玄《三礼目录》之说,指出《礼记·经解》中“六经次第,则随意为之,不关本篇弘指”,认为《序录》的六经排序与《七略》、《汉书·艺文志》相同,“或刘、班亦以著述早晚为次,亦未可知”(22)。平心而论,在六经次第的问题上,《疏证》因当时经学研究的沉闷空气所限,因循为多,发明甚少。时至今日,有关六经次第的认识可以逐渐明晰了。汉前关于六经次序,不仅《礼记·经解》如此说,《庄子·天运》也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23)《诗》、《书》、《礼》、《乐》列在前,因其较早成为西周官学。《礼记·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其排列顺序大概因贵族子弟的接受程度而先易后难有关。《易》因占筮问天之具,为王室所秘,不列于学官;《春秋》乃孔子所修。故《易》与《春秋》为儒生所研习,应在孔子之后了。至于汉代对六经的排列,当与汉代《易》学的地位逐步提升有关。到刘向、刘歆父子时,《汉书·楚元王传》曰:“歆及向始皆治《易》。”(24)姜广辉等人从刘向著述及《汉书·律历志》收录的刘歆《钟律书》、《三统历》、《三统历谱》之中,分析了向歆父子重《易》的思想,指出因此《七略》、《汉书·艺文志》要以《易》为首(25)。《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大序在分析其他五经的意义之后,说:“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26)可见,二刘、班固以重视程度列《周易》为首的六经次第,其次第先后只是偶与著述早晚相合而已。
其二,关于三礼、《春秋》三传次序。此处《疏证》有较多发明。《序录·次第》曰:“三礼次第,《周礼》为本,《仪礼》为末,先后可见。”即以三礼次序为:《周礼》、《仪礼》、《礼记》。《疏证》首先分析陆氏之说源于郑玄注《礼记·礼器》“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一句。郑注以“经礼”为“《周礼》”,“曲礼”为“事礼”,即《仪礼》。孔颖达《礼记正义》又秉承郑、陆之意曰:“《周礼》为本,圣人体之;《仪礼》为末,贤人履之。”接着《疏证》证以反例,指出西晋臣瓒注《汉书·艺文志》曰“礼经三百,谓冠、婚、吉、凶”,乃以《仪礼》为礼经。朱熹作《仪礼经传通释》更倡其义,“自尔更无崇信郑义者矣”。最后论断曰:“自周讫汉,盖以十七篇为《礼》之正经;《周礼》本名《周官》,二戴自为传记,并非正经之比。”(27)由此定三礼次序为《仪礼》、《周礼》、《礼记》,实为允当。
论《春秋》三传次序时,《疏证》虽无明确的论断,但也提出可供辨证的意见。《序录·次第》按通常的看法,述三传次第曰:“左丘明受之于仲尼,公羊高受之于子夏,谷梁赤乃后代传闻。三传次第自显。”《疏证》在引述《汉书·艺文志》、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疏解三传次第之说后,又引桓谭《新论》、《礼记·王制》正义所引郑玄驳何休等异说以为参证,曰:“此三传后先之次,而桓谭、郑玄皆以公羊在谷梁后,疑就著竹帛史言之。”(28)则认同郑玄“谷梁近孔子,公羊当六国之世”的说法,认为《序录》言《公羊》在《谷梁》之先,大概以成书的时代而论。
其三,关于《诗经》鲁、齐、韩三家。《序录·次第》引《汉书·艺文志》,指出“鲁最为近之”,齐、韩诗则“咸非其本义”。《疏证》又辨析齐、韩二家何者稍近,曰:“窃谓齐学之五际六情,本与《易》阴阳、《春秋》灾异相次,犹焦延寿之独得隐士之说也,则齐学实为巨异。”(29)于此有进一步的发明,条列出鲁、韩、齐三家与《诗》义由近到远的次序。
(二)对诸经之学源流演变的论述
阐述诸经之学的源流、演变及不同流派之消长,揭示诸经之学在各个时代所取得的成就和认识意义,是《疏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要旨。书中对各经学术发展史多有阐述,或详或略,可归为三端。
其一,对各经学术发展脉络的把握。以《尚书》学为例,自西晋起,统治《尚书》学千余年的伪古文《尚书》在清代既已成定谳。那么,今文《尚书》学短暂的发展史就显得尤为重要。《疏证》从五个方面归纳了“今文《尚书》之传始于伏生,盛于三家,歇于永嘉之乱”的历史。其中尤可注意者:一是点明伏生有《大传》四十一篇、郑玄所注以及西汉三家遗说的重要性,今存清人辑本,“固治《尚书》者所宜取资也”。二是阐述今文《尚书》学在西汉最为兴盛。欧阳氏、大夏侯、小夏侯三家皆有本经、有章句。三家传授又有九人,各为名家。今文《尚书》立于学官,宣帝时石渠之论则有《尚书》博士的《议奏》四十二篇。而在东汉,今文《尚书》学则流于平淡。至永嘉乃衰灭以尽。三是指出今文《尚书》学的支流。即有夏侯始昌、夏侯胜、刘向父子等的《洪范》五行推验灾异一脉(30)。
其二,对不同经学流派消长的分析。各经源流,派有所分,流派消长是学脉走向的具体表现,故不可不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易》学发展变化的重要阶段。王弼吸取玄学思想,以义理阐发《易》学,与郑玄《易》学为代表的旧学相左,形成势头强劲的新流派。《疏证》分析了两家流派的消长。先是魏晋之际,玄学大行,东晋中兴,只置王氏《易》学。至南北朝时期,因“陆澄、王俭等皆谓玄、儒不可偏废;请置郑氏”,故二家并立。此后二派互为角逐,“大抵北朝用郑,南学宗王,至隋则王注盛行,郑学浸微”。最后因唐孔颖达《五经正义》选用了王弼、韩康伯注,而郑学衰竭矣(31)。
其三,揭示学术之流变。学术发展因时而异,在变化中推演。《疏证》注意了经学史的流变,因而能够表阐不同时代的发展特征。仍以《易》学为例,西汉时期,京房《易》学的出现是一转折。《疏证》引《汉书·儒林传》曰:“成帝时,刘向考《易》说,以为诸家《易》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义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经分析京氏《易》授受源流,《疏证》作出结论说:“然则灾变之书、隐士之说,要非田生、杨、丁之旧可知也。”(32)《易》学在东汉末郑玄时又有一变。郑玄综合今古文《易》学,约之以《周礼》,于是郑氏《易》学一时风行。纵观汉至六朝《易》学的历史,《疏证》总结为三变:“盖孟、京《易》行而施、梁丘衰;郑、王《易》行而孟、京衰;王氏大行而郑氏衰。术数之学绌于玄言,于此可以观世变矣。”(33)
(三)对经籍流传的阐释
经学典籍是经学学术与思想的载体。因此阐述经籍产生与流传的过程,是分析经学史发展状况的重要内容。《疏证》对经学典籍流传的阐释,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环节。
一是追索经书名称的由来。经书名称的由来和确定,反映出人们对经典认识的程度。《疏证》论“尚书”之名的出现,条列了各种说法。如马融以为乃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王充《论衡·正说》以为乃上古帝王之书;伪孔序以上古之书乃谓“尚书”;郑玄则认为“尚”字乃孔子所加;孔颖达《正义》则以为乃伏生所加,众说纷纭。《疏证》经过一番比较,较为认同“尚书”乃上古之书的含义,并指出此名约产生于汉初。《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之言,已有《尚书》之称(34)。至于“毛诗”之名,则据《汉书》、《后汉书》等史料,指出毛亨作《诗诂训传》时,尚无“毛诗”之名。延至毛苌传《诗》之时,始题曰《毛诗》(35),从而说明了小毛公在传播《诗经》学上的作用。
二是分析经书内容的来源。《礼记》本为孔子门生所闻所记,内容庞杂,后人又多有损益,至汉代方形成大小戴二家《礼记》。然二戴《礼记》内容又多不相同,其源流所自,说法很多。《疏证》综核众说,断以己意,分析了二戴《礼记》内容的来源:一为礼家之记,二为乐家之《乐记》,三为《论语》家之《孔子三朝记》,四为《尚书》家之《周书》,五为诸子中之儒家,六为道家,七为杂家,八为汉人著作,九为《逸礼》(36)。这些分析为经学研究者深入认识《礼记》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三是讨论经书的流传。《周礼》的产生流传,《序录》以寥寥数语一笔带过。《疏证》爬梳史料,详细地阐论了《周礼》的产生、发现及流传之隐显。首先,《疏证》以马融《周官注》辑本为据,认为《周官》六篇乃周代史官所著。其次,指出秦始皇焚书后《周官·冬官》已亡,时人以《考工记》补之。并引郑玄《三礼目录》、《六艺论》之言,以证《冬官》乃为汉前所补。《周官》在壁中发现时已有六篇,批驳汉时才补《考工记》或汉时才使博士做《考工记》补之的说法。再次,述汉初得《周官》,成帝时刘向父子著录,王莽及东汉章帝时立于学官,此后传授渐盛的过程。驳何休等人以为《周官》乃伪书之论(37)。《周礼》的产生历来各有说法,至今也仍存在争议。然吴承仕综汇史料,详述其流传历史,亦成贡献于经学史的一家之言。
四是辨析典籍传承中误传伪托的原因。厘清经学典籍流程中误植或伪托,辨析其缘由,亦是经学史中正本清源的重要工作。以《易》学中京房的著述而言,其误传和伪托的现象就比较突出。仅以《隋书·经籍志》为例,其经部、子部著录的京房《易》著多达25种,然而绝大多数为误传或伪托。《疏证》分析其根源,一为弟子述师说而冒用师名;二为术数占验之书多依托;三为用京房之法推论而假称京房之名,如《晋灾异》一书;四为后人所作,传承者误认为京房之书,五为本署京房之名而有异议者(38)。
综上所述,《疏证》以其详博的征引和简明的论断,从几个方面梳理了唐前经学史的脉络。从把握各时代学人对经学内涵认知状况的角度,部分地达到了“把时代各人物所了解的经学的意义,作郑重的申述”(39)的目的。
四、《疏证》对经学史的考辨
章太炎曾与人评论两个得意弟子黄侃、吴承仕的治学风格,他说:“检斋文不如季刚,而为学笃实过之。”(40)《疏证》对于唐前经学史上相关史实的缜密考证,纠正了包括陆氏《序录》在内的许多著述的谬误,为经学史研究提供了正确的依据,也反映出吴承仕扎实、精审的治学功夫。
(一)考《经典释文序录》史源
根寻史源是治史的优良传统。陈垣曾发明史源学,他认为:“读史必须观其语之所自出。”对于历史记载,“非逐一根寻其出处,不易知其用功之密,亦无由知其致误之源。”(41)吴氏《疏证》对《序录》的疏解,即特别注意《序录》叙述的依据和根源,常以“此约”何处文、“此据”何处文的方式,说明《序录》所本。这样做,一是为了根据《序录》的史源,充分展开史料,以便疏解《序录》文意;二是为了找出《序录》的原始根依,以便稽考史实,辨明正误。比如,《序录·注解传述人》“尚书”部分,陆氏述汉兴以来今文《尚书》授受源流,曰“伏生失其本经”。《疏证》考其史源,乃出自伪孔《尚书序》“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云云。《疏证》论证此乃作伪者妄自称大,诋毁今文《尚书》,“失其本经”言过其实,因据《汉书》所载,只是有所残缺。进而指出陆氏受伪孔序之惑,采信“失其本经”之说,有失偏颇(42)。
又如《序录·注解传述人》的“三礼”部分,叙说礼之义用。《序录》曰:“礼教之设,其源远哉!”《疏证》考其史源,以为若依《礼记·礼运》之说,“礼必本于太一”,则礼生于天地未分之前,未免过于玄远而不实。不如依《荀子·礼论》关于先王为养民治民而制礼之说,方为“掸本之论,贤于《礼运》远矣”(43)。通过史源的疏解,更为合理地阐明了礼教的起源。
(二)考典籍状况
首先是考订《序录》文字。《经典释文》流传至清,已有多家校正,其中尤以卢文昭《经典释文》考证为胜。《疏证》已吸收了卢氏《序录考证》的成果。然又有新的补充、考异。如《序录·注解传述人》中谈到《易》传“十翼”,陆氏自注“解见余所撰□□”,注文有阙。卢文弨曰:“《隋志》:《周易大义》二卷,陆德明撰。当即指此书。”但是《疏证》认为《旧唐书·陆德明传》称陆氏“撰《易疏》二十卷”,究竟阙文所指何书还不能断定(44)。
此后,《序录》又述施雠传《易》源流,曰:“后汉刘昆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其子轶。”《疏证》引《后汉书·刘昆传》“子轶传昆业,门徒亦盛”,认为:“《序录》‘其子轶’上疑夺‘传’、‘授’等字。”(45)
《序录·注解传述人》著录《易》类典籍,在“宋衷《注》九卷”下注:“字仲子,南阳章陵人,后汉荆州五等从事。”《疏证》查《隋书·经籍志》,“五等”作“五业”。然孰正孰误,前儒卢文弨等不能定是非。《疏证》以理校之,以《三国志》注引《魏略》“乐详少好学,五业并受”为证,认为五业乃五经之业,“等”应是“业”字形近之讹(46)。
其次,《疏证》注意考典籍卷帙。如《序录》、《隋志》、《旧唐书·经籍志》皆记载孟喜有《易章句》十卷,而《汉书·艺文志》记孟氏《章句》仅有二篇,何以后代卷帙反盈于前代。《疏证》认为“疑后世述《孟易》者缀缉为之,非《汉志》之旧”(47)。
复次,考典籍之伪托。《疏证》考古文《尚书》之伪是本书辨伪之大宗。从古文《尚书》兴起,到传承人物,具体篇章,层层考辨,篇幅较多。仅以考证古文《尚书》兴起而言,《序录》述此,多依《汉书·艺文志》,然又有附会和演绎。《疏证》从几个方面进行考证:一是辨析鲁恭王坏旧壁得书的时间。《汉志》曰“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疏证》认为“恭王卒于元光四年,不得至武帝末”,《汉志》说乃传闻之误。二是辨古文《尚书》的卷帙,指出后来伪造的古文《尚书》乃弥合篇卷数,以合《汉志》的记载,以假乱真。三是辨《序录》所言“安国又受诏为古文《尚书》传”,注引《汉书·艺文志》云“安国献《尚书》传”;指出此乃陆氏附会之说。《汉书》只言安国献书,并无孔安国作传的记载(48)。
除上述之外,《疏证》还有多处辨伪。如指出北宋《崇文总目》记载《子夏易传》十卷,已非《序录》著录的《子夏易传》三卷,乃唐末张弧伪作;今世流传的《子夏易传》又与张弧的伪书不同,已是伪上加伪了(49)。在辨析《诗经》学典籍时,则指出明朝嘉靖间丰坊伪造的《子贡诗传》一卷、《申公诗说》一卷(50)。
(三)考经学人物
首先是考证经学典籍的作者。经籍的作者是经学史上的重要座标,只有真实地认识作者,才能准确地理解经籍的内容和思想。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51)但是由于记载的混乱和流传过程中有意无意的误植,经籍作者的混淆常给经学史研究带来障碍。《疏证》对此也有不少考证,比如《诗经》有大小序,历来认为乃子夏、毛公所作。然而因《后汉书·卫宏传》记载的模糊,使后人以为卫宏也是《诗序》的作者之一。卫宏,字敬仲,东汉人。《隋书·经籍志》就说:“《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敬仲又加润益。”《疏证》认为郑玄与卫宏相隔仅百年,而郑玄作《诗笺》、《诗谱》却从未提及卫宏作《诗序》之事。因此《诗序》与卫宏了无关涉。卫宏所作之序,乃自己《诗》学著述的自序(52)。又如《春秋谷梁传》作者之名,历来记载混乱。桓谭、蔡邕、应劭说“名赤”,《论衡》作“真”,《七录》说“名傲”,颜师古注“名喜”,杨士勋疏作“淑”,因此有人认为《谷梁传》乃前后数人相承而作。皮锡瑞就说:“一人岂有四名,抑如公羊之祖孙父子相传,非一人乎?”(53)吴氏在《疏证》中以小学之法证之,指出:“赤、俶、淑、寘、喜五文声转通作,故字异而人同。”(54)即五字因声转而相通,皆指谷梁子一人。
其次,考经学人物的行迹。《疏证》开篇即以四证考陆德明撰著《经典释文》的时间。《经典释文》撰于何时,史无明载,陆德明只是在自序中提到其撰作的时间在“癸卯之岁”,而陆氏却是身历陈、隋、唐三朝的人物。历代学者根据新旧《唐书》本传及其他史料,推断出“癸卯之岁”的两个年代。李焘、桂馥等定为唐贞观十七年(643),钱大昕、丁杰等定为陈至德元年(583),孰是孰非,久未论断。《疏证》从陆德明在世的大致年限、在唐以前两为学官的经历、书中多引南朝人著述的情况、在唐初的学术地位等四方面,力证《经典释文》应著于陈末的至德元年(55)。至此,吴氏的裁断便成不刊之论。除此之外,《疏证》书中关于人物行迹的考证还有不少纠谬之功。如《序录·注解传述人》在序论《春秋》三传的最后,述三传之学兴衰过程。其曰:“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上《左氏》,乃立于学官。”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也秉承其辞。《疏证》指出,郑兴之子郑众卒于和帝之前的章帝建初八年,而郑兴卒年则更早。此外,和帝崩于元兴元年,历史上也无元兴十一年之号,故《序录》所言乃“错谬已甚”(56)。
(四)考典章制度
经学史的发展恒与历代典章制度相关。因而《疏证》对经学史上涉及的相关制度也有一些考证,这里略举二例,以明其考证所及范围。一是考“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此乃《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在春秋类小序中所言,流传日久,历来为论古代史官制度者所本。《序录·注解传述人》在“尚书”部分曰:“《书》者,本王之号令,右史所记。”号令本属言辞,《序录》所述与《汉志》相反。《疏证》引《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一句,又参证《礼记正义》所引北齐熊安生对《玉藻》的疏文,认为《左传》、《周礼》所记历史事实,足证《汉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乃传闻之误(57)。二是考学官制度。《序录》记《礼》学立于学官始末曰:“后汉,三礼皆立博士。”《疏证》批驳此说,指出“三礼”名称至东汉末郑玄时才有,《序录》所云,“似谓《礼记》亦立学官矣,说误。”(58)
五、余论
吴承仕完成《疏证》之前,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纵观《疏证》全书的具体内容,他采用的仍是传统的、最熟悉的古文经学疏通考证之法,亦可见他撰著此书的谨慎。不过吴氏虽用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来做经学史研究,但他并不墨守古文经学派的观点,而是实事求是地吸取了历代至清末各家各派经学研究的成果,以令人信服的疏证,使该书成为一部独具特色的经学史名著。当然,吴氏治学虽笃实精密,但《疏证》也有智者之失。此书面世后,吴氏自己多次增加批注补充,但仍存一些疏误。他的学生任化远教授曾作校证,其显著成果已为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最新点校本所吸收。任氏的校正主要是《疏证》在引用《隋志》、两《唐志》时,出现的书名或卷数之误,这可能是吴氏当时引证时的疏忽,也可能是所用版本不精。此外,可能还存在一些小疵,如卷首疏证《经典释文》自序,考证此书撰著年代时,引《旧唐书·陆德明传》“陈太建中,太子征四方名儒,讲于承德殿”(59)。今查中华书局本新旧《唐书》,“承德殿”皆作“承光殿”。这些自然是瑕不掩瑜的。
总括《疏证》的学术价值,有几点是值得重视的。一是汇集古代特别是宋以前的大量史料,详细疏解《序录》对唐前经学史的叙述,丰富了这一阶段经学史的内容。二是综核众说,断以己见,多方面地梳理了唐前经学史的脉络。三是阐幽释微,考证精审,纠正了《序录》及多家论著在经学史上的谬误,为后人的经学史研究铺平了道路。
上述《疏证》的成就,只是吴承仕在经学史上贡献的突出者。除此之外,他的经学史研究著述,还有《经学通论》讲义六篇,《经典释文引用书目及众说考》手稿,《经学受授废兴略谱》残稿,《治尚书四术》手稿及已发表的《尚书今古文说》,等等。这些成果,容俟他日再作继续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