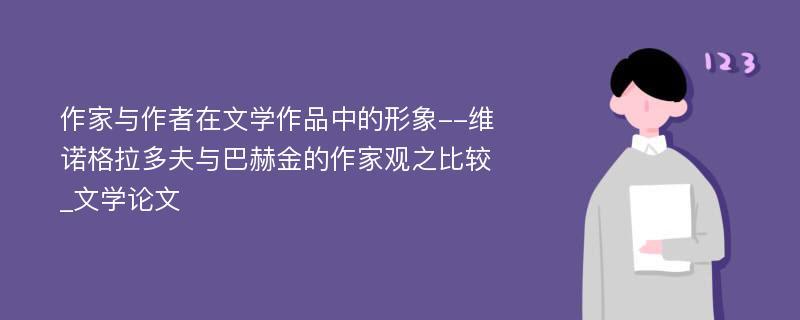
文学作品中的作者与作者形象——试比较维诺格拉多夫和巴赫金的作者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者论文,巴赫论文,文学作品论文,格拉论文,多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从一个角度看一块山石,它的形状可能像一只猴子,再走过几步回头看,这块山石可能就是一头狮子的模样。那么,究竟是猴子还是狮子更接近山石本来的形状呢?同样的道理,在作者这个问题上,究竟是巴赫金还是维诺格拉多夫更胜一筹,我们不可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原因不仅仅在于我们本身在学术水平上与两位大师之间的巨大差距。更重要的是,比较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此。同一块山石,从不同角度看,形状就不同,如果我们从更多的角度来对它进行观察,再对多种观察结果进行分析比较,显然得出的结论会更接近石头本来的形状。我们认为,巴赫金和维诺格拉多夫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角度是非常完美的互补,如果能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作者在艺术文本中的存在问题,通过作品独特的修辞特征展现作者与叙述者、主人公之间独特的涵义关系,无疑有益于更深刻地理解作品的主旨。当然,一定还可以有其他的研究视角。各种角度互相补充,互相深化,最终实现对作品思想和艺术的全面完整的理解。
作为文本和审美活动的主体,作者于文学创作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文学作品是作者思想的载体,而表现作品思想的艺术手法亦体现着作者的独运匠心。因此,作者问题一直都是文学研究所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之一。尽管这个领域的研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但时至今日,作者问题似乎成了一个理论上的悖论:一方面文艺学家们以作家创作过程的亲身体验告诉我们,作者在他所创造出来的艺术世界里几乎没有丝毫权利,在创作行为中无力控制局面,主人公总能成功地摆脱他的控制。另一方面,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不容忽视,即作品中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属于作者。作者的态度和情志,左右着内容的取舍,也决定着形式的选择。由此可见,作者问题的核心是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俄国著名语言学家维诺格拉多夫从文学修辞学入手,与之同时代的著名文艺学家巴赫金则从哲学美学和审美创作论入手,都深入探讨了作者在作品中通过自己的立场态度统摄全局的复杂情形。
维诺格拉多夫认为,对于文学作品研究而言,重要的不是现实中的作者其人,也并非现实中作者其人的个性、经历和思想投射到作品中的影子,而是作品中潜移默化存在的作者,换言之,是化解于作品、体现于文本中的作者。他为此创造了一个重要概念:作者形象。这一概念的实质正是一种平衡:作品中的一切既属于作者,又不属于作者。对作者问题的关注也贯穿巴赫金学术生涯的始终。从早年的《行为哲学》,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长篇小说的话语》,作者的责任、作者的功能、作者与主人公的审美关系等问题一直是他思考的焦点,可以说,也是他著名的对话理论的文学渊源。巴赫金从审美的创作论出发,令人信服地证明,作品中不可能没有作者存在,但这一存在并非指的是生活中的作者其人,而是作为创造者的作者的立场和功能。作为审美主体的作者,在作品中起着统摄全局的核心作用。两位大师共同的结论是:作者的立场和态度问题,是理解作品整体结构的钥匙。维诺格拉多夫和巴赫金都是在大量学术实践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维氏一生中研究了许多作家的语言和风格,揭示出他们的作者形象;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建构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精辟的分析和理解之上。他们的理论因此更加令人信服。因此,在他们之后,作为生活中人的作者和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作为创作者的作者其人不可等同这一思想,已经普遍为广大研究者所接受。当然,两位学者的切入角度不同,考察重点不同,对问题本身的理解也多有不同之处。两位学者在各自的著作和文章中,都发表了对对方观点的看法,其中也不乏争论。而这场半个世纪以前的争论在今天看来,仍然颇具现实意义。
“作者形象”这一概念是维诺格拉多夫的独创。它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的。作为语言学家的维诺格拉多夫,一向十分关注文学语言,自然,文学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作家个人的语言风格一直都是他研究的重点。为此,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维氏几乎研究了俄国文学史中所有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他对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叶赛宁、阿赫玛托娃等人的研究至今堪称经典。正是在对作品的研究中,维氏发现,一部作品最重要的是风格,而风格的核心是作者形象。他创造的这个概念,如他本人的阐释:“作者形象——这不是简单的言语主体,甚至在文学作品的结构中,通常并不提到它。‘作者形象’——这是一部作品真谛的集中体现。它囊括了人物语言的整个体系,以及人物语言同作品中叙事者、讲述者(一人或更多)的相互关系;它通过叙事者、讲述者而成为整个作品思想和修辞的焦点,作品整体的核心。”[1](252)可见,维诺格拉多夫首先是从语言学的视角提出作者问题。他所关注的是作品的语言——个人具体的、个性化的语言,而不是作品之外那个现实生活中的作家。每个优秀的作家都创造出属于他个人的一种独特的民族语形式,“作者形象”这一概念就是这种独特民族语形式的定义。所以,作者形象之于维诺格拉多夫,实际上是话语主体的形象,是将作者与他的创造物——作品联系在一起的一种修辞特色。维氏正是从话语的主体出发,通过对大量名著的精辟分析,揭示出作者形象在俄罗斯文学中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展现了这一范畴的普遍性和阐释力。这一概念成为维氏文学语言研究中最重要、最主要的范畴。作为文学作品的核心,作者形象传达出作者对文本中所讲述事件的态度,同时,作为作品主导因素的作者形象的建构,又与作者通过文本表现出的对读者的态度相关联。作者形象直接或者间接地反映在作品中,并贯穿作品始终,体现于布局谋篇、情节架构、文体风格等各个方面。并且似乎以此来表达对所讲述事件的接受和评价。关于这一概念,我国著名学者白春仁教授和王加兴教授都有非常精辟的阐释。“作者形象是一个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综合范畴,简单地说是作者对所写世界的评价态度和作者对民族语的态度。”[2](3)“它是贯穿在作品中的一种立场和观念,具体说是对作品艺术世界的评价态度和对语言艺术的取舍态度……这个‘作者形象’又不是空泛的假设,而必须落实在文本上,有具体实质的表现可以捕捉,可以指证。”[1](3)所以,作者形象是作品创作理念的唯一承载者,是对作品中所包含的世界的一种立场。作者并不直接进入文本,他总是通过一些主观或非主观的形式在作品中反映出来。对于作者的理解,来源于对这些形式,以及对这些形式的选择和组合的过程中。
巴赫金对“作者形象”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将作者的因素定义为“形象”,即意味着它与主人公形象同处一个层次。而在他看来,作者在作品中的表现形式与主人公完全不同。“形象”、“主人公”这两个概念对巴赫金而言是从外部审美的结果,是一种完成和结束。而作者不可能自己结束自己。作者不可能以具有一定外貌和精神的形象的方式出现在作品中。巴赫金区分第一性的作者(不是创造出来的)和第二性的作者(由第一性作者创造的作者形象),认为第一性作者不可能是形象,它回避任何形象的表现。他指出,“真正的作者不可能是形象,因为他是作品中任何形象、整个形象世界的创造者。因此,所谓的作者形象只能是该作品诸多形象的一员(诚然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形象)。”[3](378)这实际上有力支持了维诺格拉多夫反复强调的生活中的作者其人和作为文学作品创造者的作者形象的区别。因此,尽管巴赫金对维氏的这一概念始终持不赞同的态度,但是说巴赫金反对“作者形象”的概念本身,不如说他反对的是这一术语的提法。他与维诺格拉多夫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不赞同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作者问题,反对后者将作者的形象和人物的形象之间的区别仅仅归结为语言和风格的不同,从纯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巴赫金本人关于作者问题的思想,在他很多重要著作中都有阐述,而直接表示对“作者形象”的意见,主要集中在《文本问题》、《人文科学方法论》、《1970年-1971年笔记》等文章和笔记中。巴赫金本人所重视的,是作者和主人公之间“超语言学”的相互关系,即所谓的涵义关系——对话关系。作者的言语和人物的言语,也不是纯粹语言学意义上的关系,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涵义层面,在文学作品中相互交错在一起,之间可以有对话关系。作者正是在这一对话中采取立场,而这一对话的结果,决定了作品最终的统一性,决定了其最后的涵义立场。可见,巴赫金是从哲学美学的角度入手,将作者作为文学作品中与主人公和其他人物并存的一种声音(立场)来研究。
研究文学文本中作者的存在形态,维诺格拉多夫和巴赫金不约而同都将目光转向俄国文学的宝贵传统——故事体小说(cka3,或译讲述体)。而他们之间在理论上针锋相对的碰撞,也正在这里反映得最为突出。
故事体是以讲述人言语结构为主体的一种文学样式,俄国文学史上许多大作家都曾使用过这种形式进行创作,如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左琴科、列斯科夫等。故事体中作者假托一个讲述人来建构叙事结构,讲述人是沟通作者、主人公和作品艺术世界的中介。维诺格拉多夫认为,讲述体是作家将自己的社会生活立场转移到文学中的结果。作品中的讲述人是作者的“面具”,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作家“面具”,因而讲述者可能有十分不同的语言风格。然而,这并不代表他们可以享有如巴赫金所言的与作者“平起平坐”的权利。讲述人归根到底是作者的言语产物。作者包容了这些面孔和这些声音,把它们统统“拥进自己的怀抱”,而自己以讽刺的态度凌驾其上。由此可知,维诺格拉多夫所创造的作者形象理论,正是要找到一个能将作品聚合为一个主体意识控制之下的东西。认为是这个统一的整体组织起语言意识和其他的一切。他定义的作者形象,是“作品所有言语结构的最高形式的联结,是联结由作者派生出的诸多讲述人形象的思想和修辞核心”[4](226)。作为语言学家的维诺格拉多夫,以修辞分析为切入点,最终达到对作品整体涵义的理解。他并不否认,故事体这种“故事性”的特点不仅在于话语结构,更在于文学的思想涵义,但他认为,这个涵义并不表现在“他人”(巴赫金语)身上,而是反映于作者自身。
在巴赫金看来,维诺格拉多夫所讲的这一切,这些“面具”、“声音”和“言语结构”,恰恰是“对话”关系在作品中的切实体现。对巴赫金而言,故事体小说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对话,不同的声音代表的是不同的立场,整个作品就是各种立场和思想交锋的结果。巴赫金认为,维诺格拉多夫以极为丰富的材料揭示出艺术散文原则上的多语、多风格现象,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复杂的作者立场,但散文中复杂的杂语问题,即各种社会语层、群体风格、职业行话等的复杂组合,是传统修辞学所无法完全解释的。只有从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对话关系入手,才能深入到问题最终的实质。正如巴赫金不能认可维诺格拉多夫的作者“独白”一样,维氏也从不承认巴赫金的“对话”具有那种超乎一切之上的地位,尽管他本人也十分敏锐地感觉到话语中存在这种对话性。他指出,巴赫金特别深刻地提出了主人公和作者方面各种不同话语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他们的思想还有相近之处。但他认为,在具体的话语中,这种对话性还是以独白的形式表现出来,包含在主体的“独白”意识之中。巴赫金认为,维诺格拉多夫对对话思想的评价不足,说明维氏的理论和分析实践存在不足。他承认维氏对《同貌人》的分析细致入微、令人信服,而且结论是正确的。指出的唯一不足就是,维诺格拉多夫不理解小说的“对话性”,认为维氏对各种话语风格之间对话关系的意义重视不够。
维诺格拉多夫提出,文学作品的核心是“作者形象”,它集中反映了作者、讲述者及其主人公的全部话语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且透过这种关系成为思想、修辞的核心。巴赫金则认为,“自己的”与“他人的”问题是确定这两者之间对话平衡的问题。而这种平衡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作者与主人公、与现实生活中的作家之间对话的思想。我们今天看来,一个强调“对话”,一个强调“独白”,这两种思想看似针锋相对,实质上并不矛盾,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同是文学作品中的作者问题,但两位大师的切入点不同:维诺格拉多夫是从文学修辞学的视角,而巴赫金是从哲学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