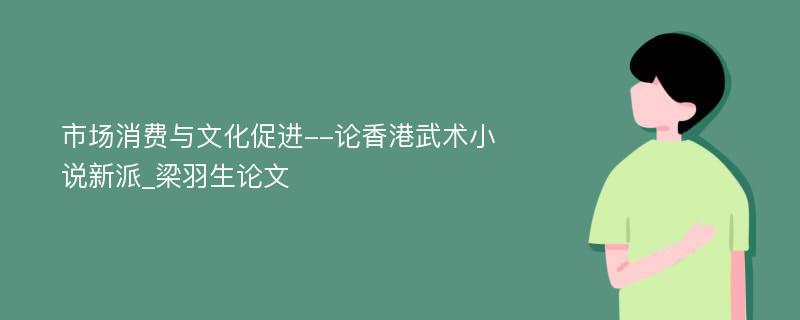
市场消费与文化提升——论香港新派武侠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新派论文,武侠小说论文,文化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新派武侠小说,学界毁誉不一。本文试图从香港文化语境的角度阐释新派武侠小说的品格:1949年以后,香港继承发展了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商业性既激发了新派武侠小说的产生,也制约了它的内容风格;中西方文化交汇的独特文化语境又衍生了金庸、梁羽生的现代观念,他们对于农民起义的不同观点,对于“夷夏之辨”辨析、对于伐恶复仇的探讨,对于人性的新的挖掘,都是他们对于旧派武侠小说的进一步的文化提升。
一
新派武侠小说是中国通俗文学的一个登峰造极的发展。据说,在世界各地,凡有汉人的地方就有新派武侠小说,它已经成为了富有象征意义的中国文化文本,这可说是香港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个独特贡献。
新派武侠小说不产生于大陆、台湾,而独独产生于50年代初中期的香港,并非偶然所致,它是香港特定都市环境的产物。
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形式,中国武侠小说始自汉代,唐宋明清绵延不绝,可谓源远流长。本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武侠小说被视为鸳鸯蝴蝶派的一支而受到了新文学工作者的猛烈抨击,但武侠小说并未因此消失,相反,民国武侠小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二三十年代有“南向(恺然)北赵(焕亭)”并驰,后又有“北派四大家”——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王度庐称雄,还有采撷众长、被后世誉为“新派武侠小说之祖”的朱贞木。最具影响的作品前期是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1922年开始在杂志上连载,历时六年多,轰动一时;后期当属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这部小说自30年代末开始一面在杂志上连载,一面出单行本,直到1949年,小说出了55集350万字, 还尚未完成。民国武侠小说的空前繁荣,曾令新文学家们惊叹不已,茅盾就曾撰文描述过上海市民观看由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而成的电影《火烧红莲寺》时的如痴如醉的狂热情景。
这种局面至1949年大陆解放戛然中断。文学工作者无可奈何的事由政权执行起来则轻而易举。新中国禁绝武侠小说。1949—1957年间,虽无新的武侠小说的问世,但还有诸如《三侠五义》等旧武侠小说的重印。1957年之后,一直到1980年,大陆竟没有出版过一本正而八经的武侠小说。那些解放前声名显赫的武打小说家,被迫转变了题材和风格。还珠楼主解放后在广州连载过《游侠郭解》,也是写的侠士,却是严肃的历史小说,不似出自奇幻绝伦的《蜀山剑侠传》的作者之手。曾以《十二金钱镖》名噪京津的白羽50年代曾在香港报纸上连载《绿林豪杰传》,但这部描写农民起义、夹以武打的小说也无法称为武侠小说,听一听作者之言,我们就知道何以如此呢?“写武侠小说,还要有进步意义,有阶级斗争,这样的书太难写了。我这一辈子,写了几十部书,水平怎样,我不敢说,但皆是我随心所欲之作,只有这一部,却是在教师的指挥下写的,于是变成了非驴非马的四不像!”(注:梁守中:《武侠小说话古今》,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港]1992年第1版。)
无独有偶,1949年之后海峡对岸的台湾对武侠小说也毫不容情。50年代初,台湾当局以戒严法的名义查禁一切“有碍民心士气”的作品,武侠小说包括在内;50年代末,台湾当局又以“暴雨专案”全面取缔包括大陆、香港出版的新旧武侠小说,计有500多部。 台湾对于金庸小说的查禁直至1979年才解冻,时间竟与大陆相仿佛。尽管台湾方面的武侠小说创作并未中断,于六七十年代还掀起了程度不同的高潮,但台湾当局对于武侠小说的查禁仍然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台湾学者叶洪生认为其后遗症有三:“一,斩断武侠小说传统脐带,致使60年代以降有志于武侠创作的文艺青年无法全面继承前人‘遗产’;只能自行摸索或仅靠有限几部老书为范本参考。故在众多武侠作者中,名家虽颇不乏人,但庸劣之作更为充斥,造成若干不良影响。二,基于政治禁忌,大多数武侠作者皆避免以历史兴亡为创作背景;甚至为求省事,干脆将时代背景全部抛开,而相偕进入一个‘不知今夕为何夕’的迷离幻境。于是在此浪漫的‘成人童话’世界里,若辈专写江湖恩怨、纷争、情仇,并以寻宝(包含武学秘籍)与图谋武林霸业为两大主题。三,由于以上的偏枯发展,致使台湾武侠小说大半陈陈相因,难以突破创新;即或偶有佳作妙构,亦可遇不可求。其中惟一的例外是古龙(本名熊耀华),但他的‘新派’作品在独领十年风骚后,却促使武侠小说陷入一个‘为新而新,为变而变’的绝境。至于晚近出现的‘超新派’或‘现代派’武侠小说则不知所云,更毋论矣。”(注:林耀德:《当代台湾武侠小说的成人童话世界》,《流行天下——当代台湾通俗文学论》,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版。)
与大陆、台湾相比,1949年之后香港的文化环境比较宽松。作为一个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英属殖民地,相对来说,香港在意识形态上不具有严格的规定性。这里左“右”派文学并存,对于武侠小说的存在也毫不在意,更毋谈禁绝。相互隔绝的大陆与台湾的文学作品在香港倒能畅通无阻,海峡两岸对于彼此文学的了解往往还得通过香港这块风水宝地。1949年之后不容于大陆与台湾的本世纪上半叶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唯在香港继续流行。此前武侠小说的传统、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意识,再加上面向西方的社会环境,香港的这一种得天独厚的开放性,使其成为50年代初衔接本世纪上半叶武侠小说的唯一可能的地方。
可能还仅仅是可能,这只是一种外因,它的实现还须有内因,这一种内因在香港恰恰存在着——那就是其商业化的都市环境。香港是一个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规律支配社会,政府较少干预。与经济上的“消极不干预”相应,港英当局在文化上采取的是“消极不扶持”的态度。正是这种放任自流的政策,导致了香港意识形态的疏松与文化上的多元。代替了政治上的苛求的是商业上的严峻,在香港,作为一种商业运作的报刊,虽然较少受到政治的限制,但却受商品规律的支配。报刊如不能获利,就无法生存,香港的报刊因经营不善而自生自灭者众多,这也是香港报刊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报刊经营者的所思所想是如何投合读者的趣味,增加销量,连载武侠小说吸引读者正是出自这一需求而出现的。
香港新派武侠小说即是缘此而生。1952年,香港武术界太极门与白鹤门发生争执,他们先在报纸上互相攻讦,后又约定在澳门新花园擂台比武,这件事轰动了整个香港,当地的报刊自然不肯放过对这场比赛的报导渲染。《今晚报》的编者借题发挥,向读者预告从比赛的第二天起将有精彩的武侠小说连载满足读者,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第一部作品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就这样匆匆问世了。这一经营策略果然有效,小说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报纸的销量自然也大增。金庸在自己的《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名声大噪后,自己独立创办《明报》,以自己的武侠小说吸引读者,制造市场。金庸在《明报》连载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是《神雕侠侣》,在《射雕英雄传》的盛名之下再写这部续集实非易事,但事关《明报》的兴衰,金庸不能不分外注意。在金庸的精心操作下,《神雕侠侣》大获成功,赢得了读者的欢迎,《明报》也由此打开了销路。金庸后来在谈到他的武侠小说时,表示最喜欢这部《神雕侠侣》,这种喜欢恐怕不完全是基于艺术上的原因,其中分明包含了他的事业成功的喜悦。
梁羽生、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创作事实上首先是一种商业行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形态也就不能不受到商业性的规定。研究新派武侠小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视角,但从目下对新派武侠小说的研究来看,这一点似乎并未引起重视。
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形式是报纸连载,这就要求作者赶时间、抢速度,到时候就一定要交出作品,不容迟疑。在这种作者没有余裕精雕细琢的情况下,小说中出现草率之处势在难免。新派武侠小说中事理逻辑上的错漏颇不缺乏,这一点已有不少人指出过,如金庸的朋友许希哲先生曾专门发表了《忙里偷闲话武侠——读金庸的“天龙八部”与“倚天屠龙记”随笔》一文,(注:三毛等:《金庸百家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指出了《天龙八部》与《倚天屠龙记》两部小说情节上的多处错误。金庸曾多次谈到,他的小说自报刊连载到出版以致重印,修订之处很多,“约略估计,原书的十分之六七的句子都已改过了,原书的脱漏粗疏之处,大致已作了一些改正。”(注:金庸:《雪山飞狐·后记》,三联书店(港)1994年5月第1版。)“现在修改校订后重印,几乎每一句子都曾改过。甚至第三次校样还是给改的一塌糊涂。”(注:金庸:《书剑恩仇录·后记》,三联书店(港)1994 年5月第1版。 )这一方面说明了金庸的认真负责——事后能够重新校订自己的作品,这在香港实属少见,多数人连重读自己作品的时间都没有,但另一方面又说明了这些小说在当初发表时是如何的草率。
这些是商业性写作最表层的弊病,仅仅如此也就罢了,因为表面上的错漏是可以事后修订的。严重的是,商业性的影响已经渗透进了小说的整体风格之中,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并加以追究了。
作为一种商品,小说如想得到读者的喜爱,就必须投合读者的口味,这是小说或报刊能得以销售获利的前题,由此而言,商业性写作的实质问题是作者对于读者趣味的迎合。如前所说,报刊上连载的武侠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商业策略,为了使小说更好看,新派武侠小说又有不少自觉不自觉的迎合读者之处,这些都对作品的风格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约略谈谈。
女性的点缀 在中国古代武侠小说史上,女性是没有地位的。刘若愚先生在比较中西之侠的区别时曾谈及这一问题:“西方骑士总表现出殷勤的爱情,理想的骑士同时就是完美的情人;中国侠客则大多数对女性淡漠无情,认为爱恋女人非男子汉所为。”中国的侠客排斥女性,“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结义都发生在同性之间。这种局面至晚清“英雄儿女型”小说而被打破,但在此类小说中,男侠、女侠都是严守封建礼法的。在民国武侠小说中,我们仍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等小说对情欲都抱着一种“万恶淫为首”的敌视态度,正面人物一个个守身如玉,把持甚严,反面人物则多淫邪之徒,动辄以色相引诱对手,真正的英雄多能不为美色所动,经得住考验。
在新派武侠小说中,女性大量涌入,男女之情蔚为大观。应该说,新派武侠小说中女性追求的爱情带有现代性爱的性质,如小龙女与杨过为了爱情勇于反抗一切封建礼法,此类情景是常常为人称道的。但远而观之我们会发现新派武侠小说中的女性缺乏现代女性所应有的最基本的意识——独立感。
新派武侠小说中的女性都是专为男子而设立的,她们本身并没有什么独立的事业,从出现之日起,她们的使命就是等待或追求爱情,寻求终身依托。在小说中,男侠可以闯荡江湖,施展抱负,女性则无论武功高低,都只能作为男子或远或近的点缀而存在,她们围绕着男子制造出一朵朵花絮。新派武侠小说中三角恋爱比比皆是,金庸小说的男主人公的周围更是围绕着一大群女性,如张无忌周围有小昭、殷离、周芷若、赵敏等,杨过周围有小龙女、陆无双、程英、公孙萼等人,集大成者的韦小宝竟有七位夫人,花簇锦绣一片。新派武侠小说中男女的这种不平等的位置,反映出作者令人吃惊的落后的妇女观。金庸、梁羽生极富现代意识,何以一落入这个问题思想就如此陈腐不堪呢?笔者以为,除了封建男权思想的根深蒂固外,商业性的影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新派武侠小说中大量引进女性,本身就缘于一种商业目的,她们是被作为制造三角、多角恋爱的“味精”放进小说的。女子的多情陪衬、一男而多女,更能合乎市民读者、尤其是男性读者的心理兴趣,于是女性自身的独立地位就只得牺牲了。新派武侠小说对于市民低级趣味的庸俗迎合,不能不令人感到可悲。如果说,旧小说对于妇女的蔑视反映出封建道德的陈腐,新派武侠小说对于女性的“重视”则折射出商业观念的铜臭。
“搞笑”的穿插 相对来说,读金庸的小说比之读梁羽生更为轻松,原因是金庸长于设计一些幽默轻松的情节,使打斗有时变得趣味横生。如他的小说中常有洪七公、周伯通、桃谷六仙一类武功高超、但性格天真烂漫的人物,他们的令人忍俊不禁的言行,常使情节变得出人意外。读者在为剑拔弩张的打斗而感到惊心动魄时,能够舒缓下来,轻松一笑。这样的设计是好的,它成功地调节了小说的节奏。但金庸有时为逗乐而逗乐,制造一些庸俗低级的噱头,这就成为了“搞笑”——看过香港电视剧的人想必熟悉那些哗众取宠的镜头。
金庸小说的“搞笑”之处很多,尤为《鹿鼎记》为甚。这里姑且举一个手边的《笑傲江湖》的例子加以说明:美貌的小尼姑仪琳在身陷于淫贼田伯光之手、为令狐冲所救后,当着武林各派向师傅定逸师太转述这一情景:
……我说:“快让开罢,你知不知道我师父是很厉害的?她老人家见到你这样无礼,说不定把你两条腿也打断了。”他说:“你要打断我两条腿,我就让你打。你师父嘛,她这样老,我可没胃口。”……定逸喝道:“胡闹!这些疯话,你也记在心里。”
众人无不忍俊不禁,只是碍着定逸师太,谁也不敢露出半点笑容,人人苦苦忍住。
仪琳道:“他是这样说的啊。”定逸道:“好啦,这些疯话,无关要紧,不用提了,你只说怎么撞到华山派的令孤冲。”
仪琳道:“是。那个人又说了许多话,只是不让我出去,说我……我生得好看,要我陪他睡……”定逸喝道:“住嘴!小孩子家口没遮拦,这些话也说得的?”仪琳道:“是他说的,我可没答应啊,也没陪他睡觉……”定逸喝声更响“住口!”
便在此时,抬着罗人杰尸身进来的那名青城派弟子再也忍耐不住,终于哈的一声笑了出来。
仪琳接着转述令狐冲如何营救她的经过。令狐冲见田伯光坐着打功夫高超,提出要坐着与他一决胜负,谁先站起来谁认输,输者第一要拜小尼姑为师,第二要“举刀一挥,自己做了太监”,仪琳不解此语,问师傅:“师傅,不知道什么叫举刀一挥,做了太监?”引得众人大笑。田伯光问令狐冲何以能有把握取胜,令狐冲回答他自创了一套“臭不可闻的茅厕剑法”,田伯光纳闷剑法何以能“臭不可闻”,令狐冲解释道:“不瞒田兄说,我每天早晨出恭,坐在茅厕之中,到处苍蝇飞来飞去,好生讨厌,于是我便提起剑来击刺苍蝇,初时刺之不中,久而久之,熟能生巧,出剑便刺到苍蝇,渐渐意与神会,从这些击刺苍蝇的剑招之中,悟出一套剑法来。使这套剑法之时,一直坐着出恭,岂不是臭气有点难闻么?”田伯光大怒:“你当我是茅厕中的苍蝇?”比赛一开始,令狐冲便叫仪琳走开,田伯光这才发现上当,他此时如站起来就算输了。
这是两段明显带有“搞笑”色彩的文字。让仪琳向老尼姑转述淫贼及令狐冲的粗话,这本身就是一种尴尬,偏偏仪琳又年少无知,公然向师傅提出一些自己不解的猥亵之事,更令人喷饭。以猥亵为乐,这正是香港电视剧最常用的搞笑方式,迎合了低级的市井趣味,金庸先生在此竟未能免俗。小说中适当的幽默、逗乐原是一种长处,金庸的所谓“臭不可闻的茅厕剑法”之类,却未免太过于胡编乱造,趣味实在不高。以金庸先生之学识,原当不至如此,笔者只能将此看作是他对于市民读者趣味的迁就。
二
通俗小说的确受制于商业性而有着诸多局限,从上面所谈的新派武侠小说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商业性机制下的通俗小说并非一定就是毫无文化品味的商品,这取决于作者自身。作者的素质与才华,再加诸于历史所提供的际遇,有时能使通俗作品超越而出,成为意蕴深刻的文学精品,这一点香港新派武侠小说同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50年代的香港不但具备延续武侠小说的都市商业环境,而且还具备使得武侠小说发扬光大的外部条件:金庸、梁羽生俱是40年代末才从大陆去香港的,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成为了他们当然的思想资源,这使得他们获得了一种批判旧派武侠小说的高度;与大陆、台湾比较,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离中国文化较远,而与西方文化较近,这一特殊语境又使得金庸、梁羽生不太拘于中国文化,而能够有自己的创造,以至于对中国新旧文化传统作出反思。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成就,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语境中产生的。
谈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成就,首先要提本世纪上半叶的民国武侠小说。因为大陆的禁绝,如笔者这样在1949年之后出生的人无缘接触到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能见到的充其量只有《三侠五义》等几本晚清武侠公案小说,所以当我们在新时期初次读到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时候便大为惊叹。现在返回头去重读民国时期一些名家如“南向北赵”、“北派四大家”的作品,才发现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成就实非凭空而来,其中存在着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民国武侠小说后期如还珠楼主、朱贞木的作品与香港新派武侠小说在风格上已经逼近。
金庸、梁羽生在年青时代就阅读过大量的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两人在《大公报》同事时还经常在一起讨论还珠楼主等人的作品。梁羽生原名陈文统,因为钦佩白羽的小说而取笔名为梁羽生。金庸、梁羽生的小说创作直接向民国时期武侠小说借鉴的地方颇为不少,且举一例:朱贞木有一部小说名为《罗刹夫人》,其中关于大理境内“天龙八部”的种种传说,显然启发了金庸《天龙八部》的构思;而其中罗刹夫人的形象又显然是梁羽生《白发魔女传》中玉罗刹的原型,罗刹夫人自小由母猿奶大后遇高人而学得一身武功,玉罗刹由母狼养大,后来也是遇高人而成就了一身武功,情节颇为相似。这些都表明香港新派武侠小说是从民国武侠小说脱胎而来,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承传关系。无怪乎古龙将金庸与还珠楼主及朱贞木、王度庐并称为本世纪武侠小说的三个阶段。
以《史记》中的《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为标志,中国传统武侠小说原有“盗侠”与“官侠”两条线索,前者反抗官府,后者拥护官府。到了《水浒传》标榜“忠义”后,“盗侠”渐隐而“官侠”大盛,直至清末《施公案》、《三侠五义》等武侠公案小说而达到高潮。在这些武侠小说中,作者站在正统“官家”的立场上,对农民起义持敌视态度,侠客的业迹便是替青天大老爷除恶缉盗。及至民国武侠小说,这种陈旧的封建观念竟未有多少改观。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朱贞木的《罗刹夫人》等众多小说都程度不同地涉及到了苗民起义、白莲教起义、义和团运动等,各书描写的内容不尽相同,但所持立场却惊人地一致——都将其作为“匪乱”而加以咒骂,称其为“白莲余孽”、“苗匪”、“拳匪”等等,歌颂官府侠士对起义军的镇压。赵焕亭的《精忠奇侠传·自序》云:“取有清乾嘉间苗乱、回乱、教匪乱各事迹,以两杨候、刘方伯为之干,而附以当时草泽之奇人剑客。事非无稽,言皆有物;更出以纾徐卓荦之笔,使书中之人须眉跃跃;而于劝惩之旨,尤三致意焉。”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小说的构思是以“奇人剑客”配合官兵平定匪乱,而主旨是籍此劝惩世人精忠报国,这实在未脱《三侠五义》等小说的巢臼。民国武侠小说虽然写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但在思想上仍与旧小说无多大区别,无怪乎受到了新文学工作者的批判。
这一情况在香港新派武侠小说中有了改观。新派武侠小说的第一部作品《龙虎斗京华》正是描写清末义和团运动的,小说所持的立场态度与旧小说已截然不同。义和团原是白莲教别派八卦教的一支,在清末发展壮大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清反帝运动。小说对这一场群众革命进行了正面的描写,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而对利用、出卖义和团的清政府予以了谴责,对义和团内部寄幻想于清政府的倾向也予以了批判。《龙虎斗京华》对待农民起义的崭新的态度,为日后新派武侠小说奠定了格调。梁羽生、金庸后来的多数小说都以历史为背景,牵涉到农民起义,作者均能站在一种进步的立场上看待这一问题。
新派武侠小说对于历史的新认识,来自于五四新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这一点在《龙虎斗京华》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书中的主人公娄无畏的是“匕首会”的成员,专以暗杀手段对抗清政府,但暗杀反给民众带来了更大的牺牲,这使他感到苦闷。在“云中奇”的指点下,他有了醒悟。云中奇以“蚂蚁斗白狼”的现象启示他看到群众的力量,他说:“凭几个人的武功本领,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推翻一个根深蒂固的皇朝。”“一只蚂蚁只消一只指头,稍微用一点力就可捺死。但一大群蚂蚁可就有这么大的威胁,蚂蚁合群起来,已有这么厉害,何况万物之灵的人?”娄无畏后来终于投入到义和团的革命斗争中去了。梁羽生在此运用的“个人——集体”模式,是左翼文学的典型套路。梁羽生、金庸40年代末期迁港,在大陆时均深受新文学的熏陶,正是这种熏陶使他们获得了一种有别于旧小说的新的眼光。
新派武侠小说并没有停留于此,现代香港的独特语境,使得梁羽生、金庸能够进一步脱离左翼文学的模式而走得更远。
“苗匪”、“回乱”这些称呼中潜含着另一个问题——即汉族正统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征讨异族、反清复明,这是武侠小说的常见内容,这些小说严守“夷夏之辨”,不能以平等的眼光对少数民族。这种汉族正统的思想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迎合了汉族读者的社会心理,根深蒂固而难以改变。香港新派武侠小说一开始也未能脱俗,梁羽生的处女作《龙虎斗京华》中的义和团、金庸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中的红花会,其宗旨均是“反清复明”,小说中侠士宁要汉族的昏君,也不能容忍异族的统治。
百年来的殖民统治,使得香港较之于大陆、台湾而显得民族意识相对薄弱,但这反倒给小说家提供了一个跳出情绪化的民族主义怪圈的机会。60年代以后,金庸开始逐步意识到这一问题。在作于1965年的《天龙八部》中,他对民族主义的问题予以了重新审视。关于历史上宋辽间的战争,我们的教科书常站在汉族的立场上谴责辽国的侵略。从《天龙八部》中宋辽间的“打草谷”来看,双方统治者互有侵扰,而真正的受害者是双方的老百姓。《天龙八部》的主人公乔峰是长于汉族的契丹人,民族冲突、文化分歧使他这一特殊身份的人饱受困惑,“大师是汉人,只道汉为明,契丹为暗。我契丹人却说大辽为明,大宋为暗。”到底孰明孰暗?民族之别果然能代替是非之别吗?
到了《鹿鼎记》,金庸对这个问题已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鹿鼎记》也写了天地会的反清复明,但与《书剑恩仇录》的态度已大大不同。《鹿鼎记》一方面描写了天地会所扶持的明朝朱家的腐败,另一方面又揭示了清代康熙当政的清明。书中康熙有言:“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在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在朱皇帝的统治下,日子会比今日好些吗?”从书中的内容看,作者的感情倾向显然在康熙一边。判断统治者的标准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进步,而不应是种族的类别,金庸显然已从传统的汉族主义的执迷不悟中超越而出了。金庸曾回忆“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注:《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三联书店(港)1994年5月第1版。)
对于武侠小说最基本的伐恶复仇观念,新派武侠小说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武侠小说中,反面人物被杀死,通常的处理方式是认为‘该死’,不再多加理会。”金庸的考虑复杂了一些,他感到现实生活中的情形远非如此,《雪山飞狐·后记》有云:“本书写商老太这个人物,企图表示:反面人物被杀死,他的亲人却不认为他该死,仍然崇拜他,深深地爱他,至老不减,至死不变,对人的死亡永远感到悲伤,对害死他的人永远强烈憎恨。”读了新派武侠小说,不但是反面人物的亲人,我们普通读者对此也有了狐疑。《倚天屠龙记》中的灭绝师太自居名门正派,嫉恶如仇,她无情诛杀恶人,不择手段,但善恶与否却全凭她自己的主观判断,这不免让我们想到下列问题:一,被诛之人是否确属该死,其中是非曲折有时颇难断定;二,对于恶人是否只有杀戮这一个方法,杀戮无疑又造成了新的仇恨。被诛之人的亲人必要替死人报仇,这样就会引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杀戮,金庸、梁羽生由此对通常大快人心的复仇观念也发生了疑问。梁羽生《大唐游侠记》中的铁摩勒在遇到复仇之人、得知自己的义父也害过人命之后,不禁毛骨悚然:“我为了义父待我之恩,无时无刻不想为他报仇,却原来我的义父也曾害过许多人命,若然似这等冤冤相报,何时得了?”金庸的《雪山飞狐》中,胡苗范田四家子孙怨怨相报,不得善终,苗人凤干脆立下了一条家训,自他之后的苗门子孙不许学武,他也不收一个弟子,试图以此来一笔勾销这百余年来的冤孽。梁羽生、金庸对于伐恶复仇这一古老观念的质疑,无疑是武侠小说史上的一次革命。
这一次革命无疑是香港文化语境的产物,彼时大陆正在紧抓“阶级斗争”,而台湾正在叫嚣“反攻大陆”,对于暴力革命的反思只能出现于没有硝烟味的现代香港社会。
在对于人物的表现上,新派武侠小说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金庸、梁羽生的笔下都呈现了不少广为人知的成功的人物形象,如梁羽生笔下的凌未风、张丹枫、白发魔女,金庸笔下的洪七公、杨过、乔峰、韦小宝等。在谈到塑造人物时,梁羽生曾作出具体解释:“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干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同时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腐败和暴虐,就是所谓的时代精神和典型性。”(注:冯立三:《与香港作家一席谈》;梁守中:《武侠小说话古今》,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港]1992年第1版。)善恶分明、邪不压正,这样人物形象是突出了, 但有时却难免概念化。从梁羽生对时代精神和典型性的解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受到了大陆文艺思想的影响,我们前文谈到的《龙虎斗京华》情节的左翼模式也说明了这一点。
比较而言,金庸在人性刻画上有较大的突破。他感到现实中不可能有纯粹的英雄或坏蛋,人性自有其奥妙所在。他说:“人的性格很复杂。平常所说的人性、民族性、阶级性、好人、坏人,等等,都是极笼统的说。”“人的性格却每个人都不同,这就是所谓个性。”(注:金庸:《韦小宝这家伙》, 桂冠工作室主创《金庸评传》,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看得出金庸与梁羽生不同, 他对大陆的关于阶级性、典型等思想没有完全盲从,而是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在《神雕侠侣》之后,金庸开始探索在小说中写出人性的复杂性。金庸笔下比较有生命力的人物多数并非大善大恶的侠客或恶棍,而是邪正集于一身的活生生的人,如杨过、韦小宝等。他们立身行事,并不恪守什么道德戒律,而是完全出诸个人的自然性情,既做好事也做坏事,让人既爱又恨,无法将其概念化地贴标签归类。在六七十年代大陆谈人性色变的时候,金庸居然在孜孜于人性的探索,于小说中表现出了人性的深度,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人们常称新派武侠小说的最高境界在于其文化意识——即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笔者感到这一说法颇为模糊。新派武侠小说中大量出现了中国古代诗词曲赋、琴棋书画等知识,体现出入世行侠、以柔克刚、四大皆空等儒墨道佛观念,这是令人称道的。但仅仅指出这一点还远远不够,旧派武侠小说同样也体现出了中国文化精神,甚至还更为浓郁,只不过它体现的是忠孝节义、因果报应等中国旧文化的精神。新派武侠小说的精髓应在于它立足于香港文化语境而对中国文化作出的变革——譬如前文所提到的对于农民起义的新视角、对于“夷夏之辨”的辨析、对于伐恶复仇的探讨,对于人性的新的挖掘等等,这是我们不能不分辨清楚的。
标签:梁羽生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龙虎斗京华论文; 江湖奇侠传论文; 蜀山剑侠传论文; 金庸论文; 天龙八部论文; 读书论文; 大陆文化论文; 书剑恩仇录论文; 三侠五义论文; 明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