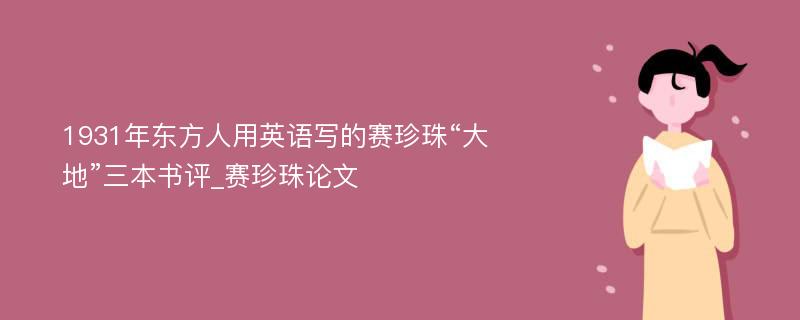
1931年东方人用英文撰写的关于赛珍珠《大地》的三篇书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方人论文,英文论文,书评论文,三篇论文,大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反映中国农民生活的史诗
——评赛珍珠的《大地》(注:该文原载北京英文《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 ScienceReview)杂志1931年第3期第448—453页,系为《大地》书评, 作者所依据的版本是London,Methuen,1931年版,全书339页。文章末尾的作者姓名后署有:国立清华大学。——译者注)
[中国]叶公超
当听说一部描写中国的小说出自一位西方人之手的时候,能够阅读英文的中国人心里明白,假如他不得不信的话,那他也只是将信将疑,从阅读此类作品的经验看,他可以料想到,在众多的角色中不难找到这样的人物形象:首先,是一位达官贵人,他相貌威严、不苟言笑,是一位大阴谋家,当然如果作者高兴的话,他还应该是一位儒士。其次,是一个妇人,常常是逆来顺受、注定要倒霉的东方女性,她寡言少语、唯命是从。她冷若冰霜的美貌面对私情与罪恶也只能听天由命。再次,犹如只有中国人似乎难以使故事情节发展下去一般,小说一定还要加上外国人,诸如:美国商人、中国通、失望的传教士以及寻欢作乐的水手等。另外,我们懂得英文的中国人还能预期:这篇故事充满神秘色彩,配以慢条斯理而又富于浪漫色彩的背景,还有数不清的会意的微笑与点头称是。而且,尽管人物活动的场景肮脏不堪,但从中国人口中说出的古代的警言妙句却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的作品已经多的数不胜数,就连最敏感的中国人对此也已见怪不怪了。所以,当一位西方人无论是将中国旧有的美德过分理想化,还是用其他一些什么人物以取代实际生存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中国人对此除了付之一笑,还能怎么样呢?
然而,赛珍珠在《大地》中所写的某些东西却与众不同——如果我们对此给以充分理解的话,它们是我们必须认真接受的;因为我们在一页页翻看这本书的时候,它迫使我们去思考我们自身的许多问题。赛珍珠忠实地刻划了中国人在中国背景下的生活,她完全了解他们的思想与感情。一个外国小说家没有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之中,而是深入地描写了我们昏暗的现实社会的底层,这是唯一的一次。《大地》是这块国土的史诗,并且将作为史诗铭记在许许多多阅读过它的人们的心中。小说中的主人公、安徽一位贫穷的农民王龙,从城里的黄家大院领回了一个女佣阿兰为妻。此后他们就与王龙的父亲一起在农村过着俭朴的生活。由于连年丰收,家境逐渐富裕起来,王龙有了更多的土地,妻子给他生了几个孩子。不久遇上持续不断的干旱,从此家道衰落,一贫如洗,最后被迫离乡背井搭乘“火车”去向一个南方的城市,希望在那里干些体力活得以生存。他们在南方城市的生活构成了本书最重要的一章。王龙在这里最初是拉人力车,当有可能被强争入伍的危险时,他改为夜间给人家托运装满箱子的货车。每天夜里他在漆黑的街道上用力拉着绳索,痛苦的呻吟着,赤身露体、汗流夹背,赤脚踏在大鹅卵石上,石块潮湿粘滑就像潮湿的黑夜一般。当他在这样卖命的时候,他的妻子儿女、年迈的父亲则在街上向行人乞讨。他们就这样在低陋、蒲席搭成的房中勉强维持生计。但城市并没有真正吸引王龙的东西;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回到家乡,踏上与自己血肉交融、属于他自己的土地上。于是,仿佛他的祈祷得到了回应,他们邻近的一家大户遭到了抢劫。王龙不知道事件是怎么发生的,也不认得那个鼓动民众抢劫的勇敢的人。他只记得自己的邻居有一天曾经对他说:“情况往往是这样的,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当时他太累了,也就没有去多考虑这话的含义。现在,还没有来得及去想,他和妻子就被人流卷入了那扇大门。在人流中,他们的脚甚至无法落地。人们就象饥饿难耐、愤怨不已的野兽狂叫不停,宽大的院落到处是嚎叫与跑动的人们。随着喧闹的人群,王龙和妻子也开始洗劫财物。当他们带着掠来的财物回去以后,王龙惊魂未定地说:“我们回到田地去——明天我们就回到田地去!”一旦回归到自己的田地上,王龙辛勤劳作、阿兰忙于家务,王家又开始连年获得了丰产。伴随着每季在谷物市场上得到的收入越来越多,王龙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土地,最终因为丰产,他变得越来越富有。不久,王龙开始感到拥有财富带来的快感,他纳了妾,送自己的大儿子去读书,要他作有学问的人,让二儿子去谷物市场当学徒,买下了黄家大院。他现在养尊处优,把管理权交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年老将至,他仍心系土地。有一天他无意中听到二儿子正慢条斯理地跟他哥哥说:“这块地我们把它卖了,得的钱我们两人平分……”老人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颤抖着声音喝断他们:“败家子呀,——要卖地?谁卖地,谁家就到了末日。”儿子们多方劝慰才把他扶到床上,并且保证不卖地了。但背着老人,孩子们相视而笑。
合上小说,读者首先回想到的自然会是王龙,想到他对土地的挚爱、对人性“善”的无言的忠诚。哪怕是抢劫也未能在他心中留下悔恨的痕迹,只要它能帮助他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就王龙自己简单的想法来看,一个人财富的锐减往往源于离开了土地,因为是土地、也只有土地才使他一度获得了众多的金银财宝。当然,还要托“老天爷”的福。如果告诉他其它的发财之道,他一定不会信的。在他与土地的关系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对自己的劳动成果引以自豪的、独特的农民,而且,我们还见出一个果敢之人的品性,他对土地的占有欲被描述得无以复加。在原始社会,正是土地,给了人类最初的占有欲与现实感。作为中国农民,王龙在这块土地上显然比他的大多数同胞们过得好。事实上,假如不是因为他抢劫得来的金子,人们会同作者争辩:如果仅仅是靠诚实的农耕,今天的农民是否能够像王龙一样变的富有呢?中国的农民要抵御连年的国内战争与大自然的无情打击,因而往往是智穷计尽、不知所措。如果他能够略有丰收、可以维持自家的生计,那他就会被认为是运气不错,更不要提像王龙那样的兴旺发达了。然而,大自然的变幻不定——水灾、旱灾与蝗虫灾害——甚至远不及国内的战争以及军阀们征收的高额的土地税带来的危害大,这一点,赛珍珠在小说中没有提及。主要因为战争与税收,才使安徽、山东、河南、河北这些省份的大部分土地所有者在最近几年里,只要可能,就出售土地。在山东的某些地方土匪横行,税收高的令人无法承受,以致于没有人敢拥有几亩土地,大地主要么使用假名把土地出租给佃户,要么干脆让土地就此荒芜下去,哪怕是肥沃的土地,也只能如此。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几乎很难听到富足的农民了,即使听说了也差不多会认为是怪事。如果今天的中国农民正在远离他们的土地,那是因为土地没有收益,或者说还没有能够收益到以维持他们的生计,而不是因为——像作者所认为的那样——城市生活更具吸引力、这个国家的人口在向城市流动。在美国是这样一种情景。当然,这一天也会到来的,那时中国也会使她的农村城市化,从而缩小城市与乡村生活之间的社会差别。但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还没有搅得我们寝食不安。当务之急则是提高我们农作的方式与普及农村教育。
回过头再来看小说,作者几点有关中国的知识似乎还有必要加以修正。例如,大户人家的女佣通常受到的待遇比作者所描述的要好。在有些家庭,女佣的地位与养女的地位相仿,是其女主人的总管与知己。《红楼梦》中的女佣们就是如此,尤其在南方的一些省份更是这样。因此,阿兰的终身大事似乎操办的过于简单了,令人难以置信。在作者所描写的这户大家,一个女佣的婚礼至少要举行某种典礼,虽然可能是非常简单的。小说中有关厨房中的女佣的描写似乎也是个疑点,除非主厨是个女人,而这在大户人家并不常见,也许还会有人问,有没有聪明的农民会让自己的儿子去娶一个大户人家的女佣呢?除非她们天生头脑灵光、运气不错而被主人纳作妾,否则女佣们通常都是嫁给男仆、小商贩这类人的。还有作者对妓院的描写乃匪夷所思。这类事情今日依旧存在,但都在非常雅致、高级的地方,因为在中国,它不仅仅是普通的卖淫场所。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瑕疵,这本小说还是应该引起中国人更大的兴趣与关注。在中国的小说中,农民心理研究至今还是个鲜为人知的主题。中国农民生活在自己独自的环境中,对此,有关他们的文学作品至今还没有给以恰如其分的表现。所以,对中国的读者来说,《大地》至少可以被喻为是:照亮了农民昏暗生活的一个侧面。
(二)合情合理地看待中国
——评赛珍珠的《大地》(注:该文原载《太平洋时事》 (Pacific Affairs)杂志1931年第4卷第10期第914—915页。系《大地》的书评。作者所依据的版本为纽约:约翰·戴出版公司,1930年版。文章发表时作者署名为Sophia Chen Zen。——译者注)
[中国]陈衡哲
外国人笔下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态度,其每一种都反映出外国心理演变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待中国人民与中国文化的看法。第一种态度是误解与蔑视。认为中国乃异教之地,仍处于半文明时代。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在艺术上被描写成一片黑暗,同时通过那些对中国文化似通非通的诠释者们的演讲,这一点也得到了公开的宣扬。第二种态度是对第一种态度的反驳。由于急欲要纠正后者的错误,并且以超乎想象的热情将中国人理想化,这些作家可能给予了中国她自身难以承受的、过高的赞誉之辞。
然而,中国既非恶魔之地,也不是天使之国。她有着普普通通的民众,有欢笑,也有眼泪;有爱,也有恨,同地球上的人类别无二致。这就是目前在作品中显露的对中国这个持久热门话题的态度。这是唯一合情合理的科学态度,它有助于国与国之间的理解和沟通。而最能展现、同时也最忠实地反映了这种态度的作品,无疑当属赛珍珠的小说《大地》了。
但赛珍珠远不仅仅是展示了一种态度,她有自己实质性的内容,那就是她熟知中国下层百姓的生活,而这源于她对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致入微地体察。其中的一些观察惊人的准确,令人信服,如:妯娌之间的争吵;叔叔的自私自利以及王龙在城市中经历的磨难等。然而还有其它一些场景,如:那位地主婆在大厅当着一个陌生农民的面抽雅片烟;像荷花这类歌女出身的姑娘居然心甘情愿跟自己的农民丈夫住在乡下的茅舍中,让人情不自禁地怀疑赛珍珠有关中国生活的知识完全是她自己想象出来的。但总的来看,赛珍珠书中的观察不仅仅是逼真的、人们所熟知的,而且显示出了深切的同情与深深的理解。
很可惜,赛珍珠的本旨也仅限于观察。尽管她深怀同情之心,但在一位中国人看来却只会感到:《大地》的作者终究是个外国人,毕竟没有融入中国人之中,她同中国人的关系也仅限于小姐与阿妈、学生与家庭教师而已,不可能有心智之间的密切联系,而这是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与中国人自由自在和坦诚相见的交往才能达到的境界。尽管赛珍珠曾长期居住在中国,但她似乎忠实地坚持了自己日耳曼人的传统:永远置身于自己所描写的国家之外,决不融入其中。这种置身其外的结果是:《大地》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类型,而非个人。
对人物缺乏个性的描绘、过于专注情节的发展以期符合预期的格调无疑是阻碍《大地》成为一部伟大小说的两大因素。凡是熟知中国社会生活的人,都会感到黄家与王家两大家族的图解式的兴衰、时来运转的轮回所带有的人为因素。他们太像一种道德类型了,让人难以相信他们的生活是一种有机的社会生活,而有机的社会生活有着更多的、更为复杂的因素,而决不仅仅只有两个家庭!
以上评述了该书的优缺点,现在,笔者要向《大地》的作者表示祝贺:一来因为她深怀同情之心地描绘了中国农民的生活以及他的家庭;二来因为她创作了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读者会发现你很难不把它一气读完。小说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色,只能源于一种忠实的创作意图、对人物持有真正的同情之心、脱离了做作的文风与腔调的束缚,以及作者沉浸于创作之时所有的真正的喜悦。
(三)中国决非如此
——评赛珍珠的《大地》(注:该文原载美国《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1931年7月1日第185—186页。原系评介《大地》与《阿桂的悲剧,及其它当代中国故事》(The Tragedy of Ah
Qui,and other modern Chinese stories)的书评。《大地》所依据的版本为纽约:约翰·戴出版公司。《新共和》杂志的编辑在文章后面加了编者按。在该杂志后面的“作者简介”中,对康永熙的介绍如下:
康永熙,纽约大学英语系讲师,《东方诗歌》的译者。他最近出版了一部小说,名为《绿草屋顶》,其背景为他的出生地朝鲜。目前他正在创作一部有关东方学生在美国情景的小说。)
——译者注
[朝鲜]康永熙
王龙,一位穷苦农民的儿子,需要个老婆,这并非因为他是个准备虔诚地遵奉祖先的中国人,反倒像个西方人那样,因为他渴望爱情、希冀获得好运。他走进地主大院,然后得到了一个奴隶……就这么简单!将一个女人带回家,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长者指点,就这么度过了新婚之夜,你得承认,这未免也太原始野蛮了吧。这哪里是结婚嘛。作者无非是在暗示,中国还没有婚嫁的体面礼仪而已。
这对夫妻是《大地》中的主人公,他们的生活飘浮不定:经受过饥荒:流落到南方,在江苏一带靠乞讨为生;遭遇了革命,虽然他们不理解,但革命却使王龙发了意外之财;他们因此得以回到了家乡。同样出于爱情与希求好运,他带回家一位“妓女”,纳她为妾,这使得他的原配妻子痛苦不堪,因为她一样渴慕爱情与好运。作为一个女人——女人这个词在赛珍珠的笔下等同于“奴隶”——阿兰除了死掉之外别无选择。她确确实实死了,“像男人头一般大的一颗石头压在她的心上、心乱如麻”,就这样一命呜呼了。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作者把她描绘成一位贤妻良母:忠贞不渝、具有牺牲精神、颇有生育能力。赛珍珠笔下的王龙耽于声色、冷酷无情,虽然她称他为“心底善良”。用马塞尔·普鲁斯特在书前的话说就是,作者在暗示:小说没有任何寓意。而王龙无疑要比阿兰得到了更多的爱与好运。
对一位西方读者来说,小说一定感人肺俯。不过,有一个障碍,浪漫的爱情是心理上的一个虚假中心,它被置于典型的东方男人或女人的身上,但东方人完全生长在一种传统的束缚之中,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尽管对西方的妇女来说,浪漫的爱情是其第二天性——要知道这是千年的文化传统使然——但对一个旧式的中国妻子来说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事。如果一切以浪漫的爱情为中心,那么,儒家的社会无疑会堕落成一座滑稽的地狱。仔细想想:一个男人带走了一个相貌丑陋的女人(因此她一定是个处女);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儿子呆在自己小老婆的闺房中成了自己的对手;他劝慰了企图在父亲眼皮底下强奸屋主的女儿的堂兄弟;他最终在自己小儿子嫉妒而仇恨的目光中,把自己家中最年轻的女佣占为己有。在儒家传统的社会中,所有这些情节都令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设想一下:一个男人把自己家的女佣拉到了自己的床上,在这一点上,人们有着巨大的思想压力,乃至在未来的几百年里,羞辱感都会伴随着他的整个家族而阴魂不散。一旦这样的事实公之于众,儿子们甚至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自杀来洗刷耻辱。而且在中国,一个女人在结婚之前始终是处女之身。女人们,是的,甚至包括女佣们,都对这个问题讳莫如深。如果她们的贞洁受到怀疑,她们很可能自杀以维护自己的声誉。(参见《阿桂的悲剧》第62页,就是女佣在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由于赛珍珠不了解儒家的男女有别及其各自领域的含义,所以,她就像某些根本不了解骑士制度的渊源与基督教体制的人一样,却非要苦思冥想地去创作一部欧洲中世纪的故事。除了次要的细节之外,她所有重要的描述都毫无正确性可言。总的来讲,中国人的成长靠的是礼节,或者是“礼”,这个词最好还是用黑格尔的“道德”(Sittlichkeit)来翻译为妙。为人处事的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一位孕妇就不大可能吃一些尚未切好的面包。……作者在过多的生养孩子问题上颇费笔墨,但她的描写夸大其词。虽然计划生育在远东尚不为人所知,但自我节制生育则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基本原则。赛珍珠笔下的人物,说话像西方人,言辞激烈、不讲“道德”,却保留了西方人唯一的一种美德:坦率,而坦率对传统的东方人而言则是令人深恶痛绝的。另外,小说中出现了一个大的时代错误:王龙出场时是一位农民,后来却成了封建贵族中的一员。这种事情可能更容易发生在英格兰而不是中国。在中国,每个家庭祖祖辈辈都属于同一个阶层,假如人们期望飞黄腾达,那也只能仰仗礼式与学问。
《大地》尽管缺少幽默成分、没有深厚的史诗般的激情,但它依然显示了娴熟的技巧与广泛意义上的艺术的真实性。正因为如此,我们会发觉小说趋向于混乱而不是清晰,这不免令人感到沮丧。小说对东、西方二者不言而喻的比较,对东方来说是不公平的。对一些受过教育的东方人而言,基督教在展示个人以及社会对个人极为关注方面显然优于儒教。但是,因为我自己也算是受过东方文明熏陶之人,因此,我不愿过于激烈地表述自己的观点,说:赛珍珠这位传教士的女儿,从她的小说一开始就拒绝承认有儒教这样一种文化——或许因为她确信:人与人之间只有涉及到爱情、好运与灵魂慰藉才是、也才能够促成婚姻。
与《大地》相比较,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由中国人写的故事集(先由中文翻译成法文,然后又从法文翻译成英文)更见其意味深长之处。读《阿桂的悲剧》时,只有意识到当代中国人所引发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你才知道小说并不完美,甚至令人难以置信,更谈不上壮观了。由于受到了胡适之流的蛊惑,这些作家成为了新思想、新艺术形式的实践者和皈依者。使用口语化的方言——即白话——他们在模仿西方的复杂性。他们被迫与古典主义和儒家的人道主义论战,并且开始狂热地、大规模地宣扬浪漫的个人主义,好象人们急不可待地在西方寻求避难所一般。然而,他们将会如何改变、如何诠释这正在消亡的西方浪漫主义,人们还要拭目以待。
我们认为,康先生对作为一部小说的《大地》有失公允。他对自己所称的儒家社会的虚假图画所表示的义愤完全忽视了叙述的文学性。在过去的一个季节里所出版的大量的文学作品,《大地》是引起人们极大兴趣且持久不衰、为数极少的几部作品之一。但也正由于此——因为故事情节如此简单明了、感人至深,所以没有人怀疑其描述的准确性——《大地》理应从一个熟知中国人生活准则的东方人的角度来加以讨论。——《新共和》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