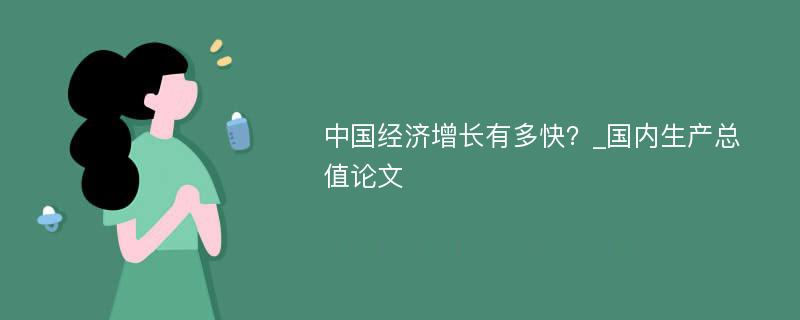
中国经济增长究竟有多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有多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9.5%。增长的速度如此之快,而且持续的时间如此之长,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尽管中国经济也面临着诸如失业下岗增多和收入差距扩大等一系列问题,但其增长的高速、健康、稳定性质毋庸置疑。但是,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如此高的增长速度,的确是世所罕见。很多人尤其是国际上的专家学者,对此形成了怀疑的态度,并且发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探讨高潮。因此,有必要认真探讨这个问题,以正视听。
一、中国经济增长成绩
1978-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5%。一些年份的增长率极高,在15%上下,增长率最低的年份为1990年,略低于5%。沿海省份实现了超过10%的增长速度。物价指数的年增长率大多数在10%以下,只有个别年份在15%以上。1997年以来,物价指数的增长率一直为负值。总体来说,中国在改革开放的20余年中,在没有恶性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多数国家未能做到的。
经济增长不仅仅是数量的增长,还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1978-2000年,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增长率分别为4.7%、 11.4%和 10.3%,三种产业的增长率都较快,但相比起来,第一产业的增长率最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增长率较高,都超过了10%。正是由于斯密—配第—克拉克法则或农业份额相对下降规律的作用,使得不同产业的增长速度不尽相同,即农业增长相对慢,第二产业增长快,而第三产业有越来越增强的趋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的产值份额及就业份额下降,是一个古老的经济规律。几乎所有的社会在从不发达到发达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相应于这个趋势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
我们来比较一下不同国家在相类似的增长时期中,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英国58年(1780-1838),美国47年(1839-1886),日本34年(1885-1919),韩国11年(1966-1977),而中国只用了9年(1978-1987),紧接着又在1987-1996年的9年中再次翻番。中国的人均收入翻番所用的时间之少,是其它国家无法比拟的。
二、对中国增长速度的怀疑观点
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绩效受到国内外一些研究者的质疑。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Thomas G.Rawski)在英文刊物《中国经济评论》2001年12月号上发表专门讨论中国近年来GDP统计数据可靠性问题的文章,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对中国GDP增长率从而对中国统计数据的质疑,包括下列一些证据。
首先是国家统计局发表的各种指标数据的不一致。
其次是对于统计数据的“假报和浮夸风”。
再次是利用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诸如交通运输、货物周转量等指标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作出不同于官方统计的替代估计。
最后,由于多数人认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很高,近年来世界经济普遍遭遇到的困难以及出口形势的恶化,都会很自然地制约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因而,目前国家统计局报告的GDP增长率数字被认为是不可靠的。
三、对怀疑论的解析
我们并不否认,在这些研究的论据中,也存在一些合理之处。但是,用一些变量(如交通客运量、全社会货物周转量、就业增长、能源消耗等)的数据去推测另一些变量(如 GDP增长),却是有条件的,是值得更加深入探讨的问题。忽略经济变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或者把某些时期的经验关系应用到变化了的条件下,其结论有着很大的风险。本文将着重于解释这些关系可能的变化,从而对怀疑论提出怀疑。
由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部门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增长方式或模式也必然发生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长已呈现出产业结构调整的明显迹象,即传统的经济增长主体部分即工农业的产值比重逐渐下降,贡献率缩小,相应地,第三产业贡献率稳步增长。这就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能源消耗的特征也会发生变化。众所周知,第三产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能源消耗是很低的。中国的改革一直在进行,在改革的过程中,劳动力、土地和能源的使用效率都会提高。因此,用以往的增长模式套用解释当前的经济增长特征,或多或少已经不合适。
另外,从各种经济成分对GDP的贡献看,改革之初,国有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超过80%。目前,国有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贡献已经非常小,城乡个体和其它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近2/3。我们知道,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规模较大,受政府的限制较多,它们大多被要求生产能源消耗多的产品。而城乡个体、外国独资、中外合资等新型的经济成分从事的大多是消费品的生产,而且大多为劳动密集型,能源消耗低。因此,这种新型的经济成分构成必然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式,包括能源消耗模式。
我们用旅客周转量作为交通客运规模的指标,可以发现,交通客运的增长十分迅速。如果设定在经济增长与交通客运之间有一个正相关关系的话,由此我们看不到任何经济衰退的迹象。
针对罗斯基的估计方法,我们进一步观察民航客运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两者为正相关关系。即国内生产总值越高,民航的客运规模也就越大。第二,民航客运增长率的波动比国内生产总值的波动大得多,即民航客运增长率对GDP的增长率具有较大的弹性。在这种情况下,用民航增长率来表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显然不合适。
就业增长的确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两者之间应该具有紧密的联系。同时,城镇正规就业的确具有下降的趋势。然而,中国城乡就业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城镇就业已经不再能够单独解释整个经济的就业状况。其次,城乡就业的结构越来越多元化,而所谓的正规就业并不能作为整体就业的代表。从就业增长的所有制结构消长看,1978-1997年,城镇国有和城镇集体经济的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在稳定中略有增长,1997年以后,这一比重急剧下降。而城镇其它和农村非农经济的从业人员比重自1978年以来一直在迅速增长,目前已占从业人员总数的 2/3以上。这种就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为保持中国从业人员总数不断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了观察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我们可以从城镇的单位内就业与单位外就业之间的消长变化看。总体来看,单位的城镇从业人员数自1978年以来在逐渐下降,而单位外的从业人员数在增长。为了观察近年来两类就业变化趋势,我们对2001年数据进行了一点调整,以便与1996年以来的数据一致。到2001年,非正规就业与单位就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几乎平分秋色。城镇的非正规就业大幅度增长,农村的非农产业就业越来越重要,所以,总体的就业趋势还是增长的。城镇正规就业越来越不代表与中国经济增长同步发生的就业增长。更高的增长率应该伴随着更高的就业。中国的就业总体趋势的确是增长的,只是城镇正规就业在减少。
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巨大的地区差距。然而,地区差距的存在并不能否定中国经济增长的成绩。事实上,一方面中国经济的重心在东南沿海地区,这部分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完全可以抵消掉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影响。在1998-2000年平均的GDP年增长率中,东部地区的贡献率为58.7%,中部地区为25.9%,西部地区17.3%。另一方面,按照国际标准,中西部地区的增长也是相当高的。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并不像人们感觉的那么大,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仍然是国内需求。国际贸易状况的变化波动,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因为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很低,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应该太大。
四、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依旧
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因素分解分析可以看出,物质资本积累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而中国物质资本积累的潜力不会耗竭。从固定资产投资看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有多种来源。80年代以来,国家预算的固定资产投资数额一直很小,而且几乎没有增长;国内贷款和自筹的其它固定资产投资数额都在迅速增长,而且这两方面的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绝大部分;利用外资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在增长,但幅度不是很大,而且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很低。1979-2000年,外资累计为5190亿美元。西方人认为,中国的繁荣是靠外资支撑的。但从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看,外资的重要程度并不是那么高。中国多样化的物质资本积累来源可以保障资本的供给。
劳动力数量是否会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呢?从人口数量和结构预测看,2010年以前,劳动年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会持续提高,2020年以前,这个比例将保持很高。2020年以后,这一比例会下降,但降幅很小,本世纪内会基本保持在55%上下。因此,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会在长期内保持一个很大的绝对数量。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尽管一直在上升,但到2020年也刚刚超过10%,因此,老龄人口的负担也不是承受不起的。可见,今后20年中国仍然可以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发挥比较优势。
人力资本积累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是巨大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的引擎。改革以来,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很快,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逐年递增,而且在东中西三类地区都迅速增加,保证了经济增长的后续力。
劳动力转移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可以大幅度提高配置效率。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劳动力转移会一直持续下去。因此,劳动力转移将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提供持续的源泉。目前,中国仍然有1.5~2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大量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预期城市化水平将有一个迅速的提高。
在分解出劳动力转移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之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意味着仍然有巨大的提高潜力。经济活动中技术效率的提高,依靠两个动力。第一是非国有经济的扩大。以往的经验研究证明,非国有经济比国有经济的生产率高很多。所以,非国有经济比重的扩大就会提高经济整体的生产率。第二是在非国有经济发展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竞争加强的压力下,国有企业为加强自身的竞争能力,本身也在改革,从而提高生产率。
五、总结
本文并不试图系统回应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GDP统计的怀疑与批评,也无意掩饰中国统计中存在的问题,而仅仅尝试通过对中国经济的长期观察,表达以下几点看法:(1)中国经济自改革以来的持续、快速增长业绩是不容怀疑的;(2)许多用来证明中国经济增长数字不真实的方法,可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3)过去20余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不会耗竭,仍将支撑今后的高速增长。此外,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统计应该进一步提高其科学性、透明性,以避免出现不必要的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