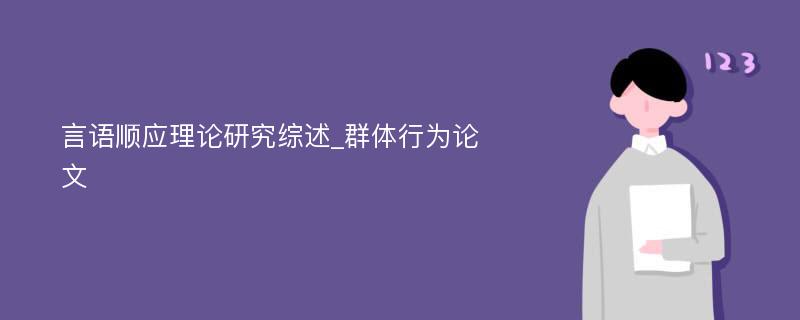
言语适应理论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理论研究论文,言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397(2001)02-0057-08
一 引言
言语适应指说话者改变或掩饰自己的身份以期更被受话人接受的一种努力(柴尔斯等,1997)[11]。作为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理论之一,言语适应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SAT)从70年代初由柴氏等人提出来,发展到今天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了。它最初作为社会心理学理论模式提出来主要用于解释人们在交际过程中的心理动机,但今天其影响已大大超越了原有的理论目标,被广泛用于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话语分析、(第二)语言习得和交际学研究。本文将综述这一发展过程和有待研究的问题。
二 言语适应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2.1 理论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可说是理论的建立时期。柴氏、泰勒和鲍里斯(Giles,Taylor,Bourhis)(1973),因不满足于欧文·特立浦(Ervin-Tripp)(1964)、海姆斯(Hymes)(1967)、桑苛夫,(Sankoff)(1971)等对语码变化、社会交际中言语的多样性所作的分类和描写(尽管柴氏等高度评价了欧氏等的贡献),认为有必要提出某种理论来解释言语交际中的言语多样性问题。柴氏和波维斯兰德(Powesland)(1975)等提出了言语适应理论,但最初完全是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模式。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心理学中的相似吸引原则、社会交换原则、归因原则和群体特征原则。相似吸引原则指在交际中说话人(addresser)的话语与受话人(addressee)的话语越相似,对受话人越具吸引力、越容易理解。社会交换原则指说话人在采取某一会话策略时权衡利弊得失,希望利大于弊,因为言语趋同有可能使说话人的社会身份特征受到威胁和损失。归因原则指人们对他人的言语行为一般都要追究其动机和原因。群体特征指当交谈的双方分属两个不同的群体或社团时,说话人更多的是被视为其群体的代表,或者说具有类典型性(protypicality)。
言语适应理论主要用于解释言语风格变化中的言语趋同(convergence)、言语趋异(divergence)和语言保持(language maintenance)等交际策略的心理动机和情感因素等的影响。言语趋同指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交际一方改变自己原有的言语习惯或语体,以更接近说话对象的言语或语体。它可表现在发音、语速、停顿、语码等方面。一般来说,言语趋同追求的是获得对方的赞同、接受、喜欢或好感,增进理解和交际效果以及相互间的吸引力等。应该指出,它们往往是相互作用,同时存在。言语趋异指交际中的一方使自己的言语或语体变得与说话对象的言语或语体不同。言语趋异主要是为了保持说话人自己的社会身份特征和群体特征。言语保持指未作出任何改变,也就是说没有趋同。Giles将它视为言语趋异的次类(subtype)。
2.2 理论发展的特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理论的实践和发展时期。进入80年代以后,许多社会语言学家运用言语适应理论对以移民区和双语或多语区为主的言语运用中的多样性进行了大量深入和富有成效的调查,硕果累累。除了柴氏本人的大量系列研究成果以外,主要的还有柯普兰德(Coupland)的系列研究成果,克劳斯(Krauss),斯特里特(Street),毕贝(Beebe),鲍里斯,布拉戴克(Bradac),加洛伊斯(Gallois),卡兰(Callan),库尔马斯(Coulmas),贝特(Burt),司各腾(Scotton),贝格(Berg),梅尔霍夫(Meyerhoff)等人也出版了不少著作,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在此,限于篇幅,不可能一一细举。另外,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杂志于1988年的3/4期出了专号,集中刊出了十几篇论文。综观其二十多年的发展,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2.2.1 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如前所述,适应理论提出之初,它只是一个社会心理模式(柯普兰德,1995)[7],主要属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畴。重点研究的是微观领域中诸如风格变化和语码选择时的动机、认知与群体忠诚(group loyalties),以弥补传统社会语言学中注重规范和规则的社会功能解释的不足。研究者们如柴氏(1975,1976)等主要研究了相似吸引原则和归因原则。相似吸引原则是适应理论的实质。言语适应的过程以此为原则,表明个体希望获得社会的承认。斯马德(Simard)、泰勒和柴氏(1976)根据海德(Heider)的归因理论三因素(能力、努力程度和外部压力)提出了适应理论修改模型。该模型认为,适应的有效性应从说话人评估和相互适应两方面来考察(柴尔斯等,1997)。初期的适应理论只是一组预测听话人对诸如言语趋同、言语趋异、语言保持等言语策略的社会评估的假设(柯普兰德、柴尔斯,1988),因而注重内在因素的研究。柯氏(1988)认为在研究言语适应时,除了研究言语趋同、言语趋异、语言保持和言语互补等会话策略外,还应研究说话者的语言能力、对会话需要的注意程度和角色关系的处理。柯氏和柴氏(1988)[8]概括说,除了研究由言语趋同、言语趋异和语言保持构成的近似(approximation)策略以外,还应包括可理解策略(把话语清楚明白地表达出来)和人际控制策略(给说话者合适的角色选择权)。这一概括把语言的和非语言的所有交际行为都纳入了适应理论的研究范围。
80年代以来的另一个发展是区分了主观适应和客观适应。主观适应比客观适应更重要,更起作用。这种区分很有必要,因为与语言选择和语言变化的客观事实相比,交际策略的主动性和社会评估更与我们对社会言语行为的感受和信念直接相关。同时,主、客观适应的区分也促进了对交际策略的大量研究。
但是研究者们发现只研究内部因素并不能充分解释风格和语码变化的原因。于是,他们把研究的目光转向了外部因素。
耶格尔·德洛尔(Yaeger-Dror)(1988)[18]在深化和拓展柴氏(1977)提出的影响群体力量(group vitality)的三个因素——移民分布(demograph)、机构支持、和社会地位——的基础上,研究了群体力量对言语趋同的影响并提出了以下三个影响因素:地理与历史因素、社会地位和语言学背景。地理历史因素包括原来生活的地理环境、移民分布、机构支持。移民分布因素包括移民的数量、出生率、婚姻模式、居住时间等;机构支持因素包括学校、媒体、商业和政府机构的支持等。社会地位或称社会结构因素,包括经济、政治因素和母语的地位。语言学背景指官方或学术机构对语言使用的规范。耶氏的研究结果表明,当某一群体的力量小时,其语言必然朝居主导地位的语言规范趋同,反之亦然。不可忽略的是,与移入国文化(host culture)接触越多,趋同越多。
波伊德(Boyd)(1987)作了类似的研究,并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了影响群体力量的三个因素:历史的、地理的和态度的。他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移民群在母文化(home culture)背景下的社会和语言环境与群体力量具有内在联系。从地理的角度看,原籍国(地区)和移入国(地区)之间的距离、与居住点的融入程度和自给自足与否都产生一定的影响。对移民群和移民原社区持群内还是群外态度的影响自不待言。
基内西(Genesee)和鲍里斯(1988)[10]研究了影响受话者对语码选择变化的反应的四个相互作用的因素:情景语言规范、言语适应、群内偏爱(ingroup favouritism)和社会结构因素。他们的调查和研究表明,在某些情况下,语码变化或言语趋同是社会规范的‘要求。比如,售货员与顾客之间的对话,其社会规范的要求是“顾客语言总是对的”,如果售货员不向顾客的言语趋同,对他的评估就会降低。反之亦然。将人们划分为“我们”和“他们”会诱发对群外成员的偏见和歧视、对群内成员的偏爱。这会导致对群内典型成员的语言的喜爱和偏爱使用群内语言。如前所述,社会机构因素影响群体力量。
2.2.2 学科单一性到学科交叉性。如柯氏(1995)[7]所指出的那样,言语适应理论最初只是研究言语风格变化的社会心理模型,属于社会心理学研究范畴。但是,随着理论的发展和社会语言学家越来越多的关注,学科的交叉便不可避免。目前,它已成为了由社会学、社会语言学、和社会心理学交叉而成的一种交际理论。
语言使用是个动态过程。而传统的社会语言学以规范人们进行交际的社会语言规范和规则来解释语码变化。其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忽略了会话者的动机和认知等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基内西、鲍里斯,1988)[10]。社会心理学研究在缺乏人际适应过程相互作用时使用的语言策略。那么,社会语言学与社会心理学相结合能解释社会语言规范被遵守和被违背是说话者的动机、认知和情感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问题。在这方面,鲍氏(1979,1985),基氏和鲍氏(1982),波尔(Ball)(1984)等人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和贡献(可从研究领域的扩大中看出来)。
由于言语趋同、言语趋异和语言保持被视为言语互动交际策略,交际学理论和言语适应理论获得了共同的理论目标和研究对象。言语适应理论超越了初期作为社会心理模式的预测功能,而成为了情景性互动交际通用模式(a generalised model of situated 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柯普兰德、柴尔斯,1988)[8]。柴氏等在1987和1991年改称为“交际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CAT)。在此基础上,加洛伊斯和卡兰(1988)[9]研究了说话者的类典型性与地位和同等关系(solidarity)的预测评估关系,并得出了如下研究结果:(1)适应指数比实际的非言语行为更能预测说话者的同等关系等级;(2)CAT对互动交际行为的评估更倾向于使用相对标准而非绝对标准;(3)被评为同等关系等级高的说话者不一定要表现最典型的行为,而是遵守准则;(4)以类典型说话者的行为为评估依据表明受话者的期望可以违背,效果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出乎意料的违背行为只要是遵守友好和礼貌规范的都会获得积极的评估;(5)CAT认为,虽然言语趋同的目的是寻求赞同和表达同等关系,但言语趋异是为了否认同等关系,表明差异或优越性;(6)最能预测对说话者地位的评估的是说话者的说话行为,如语速。
2.2.3 由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早期的言语适应理论研究试图制定一组准则来预测:什么条件下言语趋同、言语趋异和语言保持会发生、它们的相互关系和评估效果(柯普兰德,1995)[7]。因而,言语适应理论的研究最初具有明显的经验主义传统。这种静态的研究方法受到以下两方面的影响而发生了改变。一是其理论自身的发展。2.2.1和2.2.2能充分说明这一点。越来越多的实际研究表明说话人的言语变化不但受内部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外部因素(如社会身份、群体力量)和情景因素(如情景规范)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所以,越来越不可能通过对情景的拟构(situational configuration)预测出具体的适应过程和结果。换句话说,理论自身的发展要求改变以往的对语言和社会情景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以便能洞悉出特定的言语变化时的局部的社会心理过程(ibid.)。二是社会心理学本身一直在反省自己的认识论基础。包括柴氏、柯氏,波特(Potter)等在内的适应理论学者们和许多社会心理学研究人员对一直统治着社会心理学的经验主义假设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不仅仅是作定量研究,还可作定性研究;在研究语言和情景时要更加重视推理的方法。
由于言语适应理论越来越重视言语交际中的动态过程和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研究,言语适应理论模型由预测性模型发展成为了解释性模型(interpretive)。
三 适应理论的研究范畴
3.1 宏观适应研究与微观适应研究。
从研究的范畴来看,适应研究可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宏观研究的主要是方言的变化、语言变化、语言现代化和语言发展等问题。库尔马斯(1989)主编的《语言适应》(Language Adaptation)[6]一书中的大部分论文论述了语言适应过程中的一些宏观问题,其中以他自己的论文作为首篇,进行了理论上的高度概括。他认为适应是个过程,不局限于某一个时代。因为语言反映语言社区的社会现实,因此,语言不但要能满足特定的交际需要,还必须能胜任语言交际中的所有需要。即语言这个符号系统必须能充分履行某一语言社区的各种交际功能。世界上的语言千差万别在于它们的语言使用的方式和履行的交际功能的不同。所以当由于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语言突然被赋予新的任务时,语言会突然显得力不从心,不能履行其应该承担的功能。这种社会的发展和语言变化的不同步性要求语言必须不断地适应新的交际要求,满足新的社会需要,否则一种语言就有可能消亡或被取代。任何语言都必然经历不断适应的过程。适应得越好的语言就越有可能成为越重要的语言,如英语、德语和日语等。它们完全适应现代教育、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和管理等现代交际的需要。发展中国家的语言现在需要适应,是因为它们还不能满足这些需要。就整体而言,宏观上的语言适应是个逐渐的、连续的、悄然的(unnoticed)过程,由客观因素催化产生。但是在出现语言危机时,主观干预是必要的。此时,语言适应成为了政治目的。如为了保持语言的统一性、准确性、高雅性和纯洁性。充分适应是动态的,具有潜在的可变性。语言适应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语言社区的意志。
在个案研究方面,除了《语言适应》中介绍的以外,还有普林斯(Prince)(1988),耶氏(1988)[18],贝格(1988)[16]等人运用适应理论对方言变化的研究。
微观研究主要是具体的言语交际中的风格变化和语言选择等。在言语交际中,言语趋同除了能获得前面提到的效果以外,还能达到适应对方的言语习惯和社会权威[12]、或改变说话双方业已存在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司各腾,1988)[5]的目的。语码选择(转换)是微观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柴氏等人认为,作为言语趋同的语码转换是为了获得赞同等。对此,贝特和司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贝特(1994)[5]认为,言语趋同的效果是模糊的,有时获得赞同,有时却获得反感;言语趋同并不总是被视为是适应;过分的趋同还会被受话人视为一种威胁。司氏(1988)[15]虽然同意言语适应理论模型和标记理论模型有许多相似之处并接受它,但他运用标记模型(markedness model:MM)对语码转换作出了大不相同的解释。他认为,语码代表着一组权利和义务(rights and obligations:RO sets)。说话人通过使用有标记的语码(即语码转换)来向受话人表示这种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改变,暗示自己的多重身份,获取交际权势(interactional power)。这是以说话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受话人为中心。
3.2 短时适应和长时适应。
短时适应指在某一特定的交际场合,说话人根据受话人的情况对自己的言语(包括用词、语速、语法和语音等)所进行的临时调整,说话人可根据不同的目的采用言语趋同、言语趋异或语言保持(不改变自己的言语习惯)不同的策略。短时适应一般属于微观研究。长时适应指一个人移居到另一个地区或国家后为达到融入其中的目的,有意识地或不知不觉地使自己的口音向新地区的口音靠拢,或者学会新地区的口音、方言或语言。严格说来,长时适应发生在群体间的互动交际中,属于宏观研究的范围。
对长时适应具有充分解释力的理论是人种语言学身份理论(Ethnolinguistic Identity Theory:ELIT)。ELIT已被发展为SAT的一部分,用以解释群际间的适应过程。ELIT认为,说话者的社会与个人身份影响其语言态度,其语言态度又反过来影响其对另一语言群体的交际行为是采取言语趋同还是言语趋异的倾向。而且,语言态度还影响说话人对群内成员和群外成员的习惯性取向(habitual orientations)。加洛伊斯与卡兰(1988)[12]和贝格(1988)[16]在这方面运用ELIT做了比较独到的深入的实证研究。
长时适应中的言语趋同的目标一般是新语言社区的交际规范和具有代表性的类典型成员(prototypicality of a person)所使用的语言。规范或称社会规则构成人们在各种场合的行为规则的共同期望(shared expectations)。在实际的交际中,人们在遵守规范时具有弹性。类典型成员是能最大限度地缩小(most minimises)群内成员间的差异、最大限度地扩大(maximises)与群外成员的差异的成员。类典型成员提供了一个考察社会影响过程的锚点(anchor point)。群内保持一致的压力导致在态度和行为方面朝最具类典型性的成员的言语趋同。值得注意的是,当两个语言群体拥有相似的规范时,最遵守规范的不一定是最具类典型性的成员。
在长时适应研究中,方言变化是个重要的课题。虽然从原则上讲,方言变化与适应并不一定具有必然的联系。但是特鲁吉尔(Trudgill)(1986)和普林斯(1988)[14]的研究表明,适应事实上是方言变化的内在动力。方言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说话者不必与操目标方言者发生任何互动交际就可以经历方言变化。即无须一个适应对象共同在场。普氏的研究对象(一位移民歌唱家)的方言变化还具有外语学习中的中介语的变化特征,即她的适应后的个人方言(idiolect)既不像她原来的方言(D1),也不像目标方言(D2),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种方言(D3)。此研究成果对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四 适应的本质特征
如前所述,适应理论研究的是作为交际策略的言语趋同、言语趋异和语言保持背后的心理动机和认知过程与听话人对说话人的言语输出的评价,也就是研究言语交际中说话双方的心理机制,因而具有以下三个本质特征。
4.1 主观性。
适应的主观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对言语趋同、言语趋异和语言保持的评估与受话人的主观体验紧密相关。布拉戴克、穆拉克(Mulac)和豪斯(House)(1988)[4]的研究表明,言语交际中的地位和能力的评估等级并不与词汇的多样化正相关,而是与受话人是否感觉说话人是向上或向下言语趋同或言语趋异相关。向下言语趋同和向上言语趋异都获得了更高的评估等级。对交际中的一致性的评估等级与听话人感受得到的说话人的努力相关。说话人不但对自己,而且对说话对象和交际情景也不断地作出主观性评估。
适应的程度、话语的组织和构成原则、交际中的社会权势关系的建立和操作以及认知结构都受意识(ideology)的影响[1]。
感知的群体力量与感知的群体边界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人们认为群体边界难以逾越并感觉群体力量小时,会竭力保持自己的语言。相反,当人们认为群体力量大时,会感觉群体内的边界松散和开放(贝格,1988)[16]。语言群体认同他们自己的言语和行为的程度取决于主观感觉的群体力量,而不是对群体力量的客观评估标准。[18]
4.2 非对称性。
由于言语和会话风格中的许多因素随情景的变化而变化,会话双方可能改变不同的绝对量(absolute amounts),因而适应不必对称。毕勒斯、克劳斯(1988)(Bilous & Krauss)认为[3],在某一情景中的适应方向和对称性首先取决于交际双方关系的性质。正因为如此,适应的过程中会出现过分适应(overaccommodation)和适应不足(underaccommodation)。由于适应不是单向性的而是多向性的,所以当说话者的话语超越了当时情景下的最大值时(optimallevel),或者说“合适的”或“很协调的”行为标准时,会产生过分适应。如家庭护理人员对年迈者的保姆式语言(baby-talking),庇护式语言(patronising talk)和卑谦式语言(demeaning talk)。适应不足指傲慢的说话方式或回避说话,也可指不给受话人在互动交际中足够的权利和空间。这表明没有足够的参与或关怀(柯普兰德,1995)[7]。但应区分过分适应和过度适应(hyperaccommodation)。过度适应指在使用某一变项时超出了目标语中使用的频率,过度适应可由认知显度解释(耶格尔·德洛尔,1991)[17]。
4.3 以受话者为中心。
如前所述,言语适应理论认为,说话人的言语趋同或言语趋异是以受话人的言语特征为目标的。柯氏和柴氏(1988)说,言语适应理论十分重视以受话者为焦点是受到了贝尔(Bell)(1984)[2]的“听众设计”(audience design)的启发。风格和语码的选择是基于听众与说话人的由近到远的关系作出的。交际中对语式和语场的选择和研究也是处于优先考虑受众的结果(recipiency considerations)。他们还认为,以受话人为中心可大大地扩展适应理论对社会语言策略的研究范围;可以将交际性适应全部看成是以受话人为取向的话语策略,说话人由此可将自己的话语去适应受话人的特点。贝尔(1984)认为,在语言变化的各层面上,人们主要是回应他人。说话人为其听众设计自己的言语风格。在场景、话题和参与者这三个影响语码选择和风格变化的因素中,对话者(interlocutor)更具决定性效果。柯氏等人认为,说话者的言语变化更多的是因为受话人的改变,而不是话题的改变。桑柯夫(1980)也认为对话者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约瑟夫(Youssef)(1993)的研究表明其它因素也具决定性作用)。列维(Levin)和林(Lin)(1988)[12]的研究不但证实了贝尔的观点,而且还发现说话人从表面看是向受话人的言语风格趋同,其真正目的是顺应受话人的地位和社会权威而不是他们的实际言语。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顺应群体范式(stereotypes of groups)。
五 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言语适应理论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变化,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广泛的应用研究使其学科交叉性日益突显,随之也开拓出更多新的研究课题:群际接触与群体力量的关系,身份范畴对言语适应的影响,标记性与交际权势的关系,社会身份和交际规范对言语适应的影响,临时适应中的言语变化与长时适应中的个人方言、群体方言以及语言变化的关系,建立长时适应理论模型还应研究哪些机制和过程,确定类典型成员的标准是什么、何时确定、怎样确定,怎样才能充分解释不同情景下的适应策略背后的相互交织的复杂动机,怎样确定某一特定的言语变化是规范要求的结果还是适应的结果,言语适应理论的合理使用范围和与其它理论模型的合适结合点等等。
研究言语适应理论的方向应是将它与别的学科交叉起来。维索尔伦(Verschueren)(1999)的《语用学新论》作出了很有意义的成功尝试。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一批交叉研究的成果。
[收稿日期]2000年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