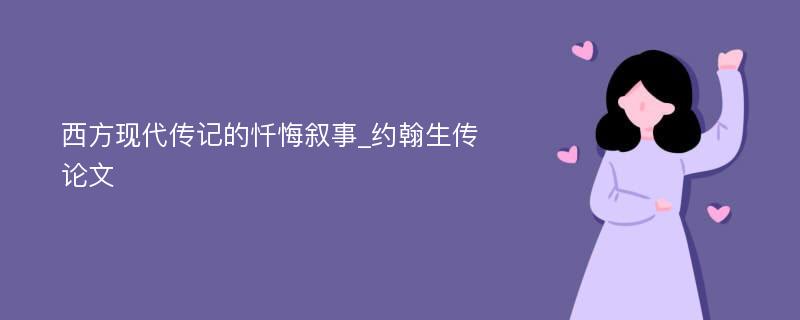
西方现代传记的忏悔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09)01-0043-06
作为普遍的情感体验形式,愧疚感、罪恶感在西方人性的发展中有长久的历史,① 古代西方传记对此虽有所表现,但并不多见,并且传记家一般是在传主做出极端残酷的行为(如杀人、弑亲等)时才会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也很少有深度的解释。普鲁塔克对亚历山大在狂怒之下杀死好友克雷塔斯之后的愧疚和悲痛的描述,以及塔西陀、苏维托尼乌斯在各自的作品中对尼禄在弑母之后的恐惧和罪恶感的叙述都是如此。即便是被称为西方“最早探索人物行为的无意识动因”[1]的罗马传记家阿里安,对传主的忏悔意识也主要是通过对传主语言和动作的描写加以表现。[2]文艺复兴时期托马斯·莫尔的《理查三世传》中,对传主杀人后的愧疚和恐惧有了非常生动的描述,但仍谈不上解释。这一特征一直到18世纪末鲍斯威尔的经典之作《约翰生传》都没有大的改变。在精神分析理论影响下,西方现代传记对传主的愧疚感和忏悔意识有一种更为敏锐的关注和更深入的解释,这已经不同于古代及近代传记作品对传主愧疚感和忏悔行为的单纯描绘和记录,而将笔触探入到传主的意识深处乃至无意识层面。本文主要从精神分析理论对现代传记的启示这一角度切入,对现代传记的“忏悔叙事”及其意义进行评述和探讨。本文所谓“忏悔叙事”,主要包括现代传记作品对传主的忏悔行为的“再叙述”,以及对于传主的愧疚感或罪感的探索和深度解释。
一、追踪“严酷的良知”
1784年,约翰生博士最后一次来到了他的家乡利希菲尔德,他向当地的牧师亨利·怀特忏悔了早年对父亲的一次“不孝”行为。克利福德的《青年约翰生传》和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中都处理了传主晚年这一重要事件,但其处理方式却很不相同。鲍斯威尔采用的是“实录”:
亨利·怀特是一个年轻的教士,约翰生跟他已经很熟识了,所以谈起话来也比较随便。他提到,亨利不能在一般意义上批评他是一个不孝顺的儿子。他说,“的确,是有这么一次,我不听话;我拒绝替父亲去乌托塞特市场。拒绝的原因由于我的骄傲,想起这件事是令人痛苦的。几年之前我渴望弥补这一过失;我在一个很坏的天气里去了乌托塞特,在雨中光着头站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父亲的货摊就曾在那里。我悔恨地站着,希望忏悔能够补偿我的过失。”[3]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动人的场景,但在鲍斯威尔的作品中,这却是对于约翰生的一个自传事实的单纯叙述,没有任何解释。约翰生何以对别人批评他是一个“不孝顺的儿子”如此敏感?一次简单的“拒绝”何以能够引发如此深远的内疚?鲍斯威尔语焉不详。
克利福德评论说,鲍斯威尔“所使用的仍是经验性的方法,依靠的是证据的长久累积,只是偶尔才出现稍纵即逝的阐释性片断”。[4]他在其《青年约翰生》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重新叙述。他将约翰生对父亲的一次拒绝看作他青年时代中“最著名的一件事”,[5]135并将鲍斯威尔作品中的“自传事实”转换成为一件“传记事实”,用“严酷的良知”对约翰生的忏悔行为进行了解释:
有一天,迈克尔(约翰生的父亲)病倒在床上,他让大儿子替他去乌托塞特市场去照看一下在那里的货摊。出于骄傲,萨姆拒绝了,在露天市场上卖东西对他这个牛津大学的大学生来说似乎是有失尊严的事情。他对父亲的请求置之不理,这一事件就这样结束了。但他严酷的良知从没有让他忘记这件事;对父亲的拒绝在他心灵深处地引发了长久的内疚感。最终,50年后,他感到了一种要对这一忤逆行为进行赎罪的极其强烈的愿望。一天,他离开利希菲尔德的朋友们,走到乌托塞特露天市场他父亲的货摊曾在的地方,光着头,“站立在旁观者的讥笑与糟糕的天气之中”。[5]135
约翰生的父亲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6周后就去世了,克利福德认为,这在约翰生心中很可能造成了一种因果关系的幻觉,从而“强化了上述行为的不孝性质”及伴随产生的内疚感。[5]135“良知”的残酷性在弗洛伊德之前由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麦克白》、《罪与罚》及《卡拉马佐夫兄弟》等文学作品中作过惊心动魄的描绘,勇敢地“站立在旁观者的讥笑与糟糕的天气之中”的约翰生,尤其让人联想起在良知的追击下扑倒在于草市场的空地上亲吻大地的拉斯柯尼科夫,在那里同样有旁观者的“冷言冷语”和阵阵轻蔑的“笑声”。[6]弗洛伊德则首次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良知”进行了系统性的探讨。“良知”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里属于超我的范畴,或者说是超我的一个性质:“超我支配自我会更严格——以良心的形式或可能以无意识的形式。……超我这种统治权力的源泉带有强迫特点的专制命令形式”。[7]183他不仅指出了超我具有无意识般强大的“非理性”力量,而且他更进一步将超我的起源追溯到个体以俄狄浦斯情境为核心的与父母尤其是与父亲的错综复杂的认同关系。他指出,我们在超我中所具有的那个高级本性是“我们与父母关系的代表”,超我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7]184-185
克利福德正是从约翰生与父亲之间复杂的认同关系这一角度来解释传主旷日持久的、历经数十年而不衰的内疚感的。他虽然并没有套用精神分析的理论来解释约翰生父子之间的关系,但他确实对二者关系的复杂性给予了很多关注。克利福德指出,由于父子两人年龄相差过大,迈克尔性格忧郁,沉默寡言,并且常常不在家,约翰生对父亲没有怀有多少亲密的情感。此外,作为一个中年得子的父亲,迈克尔过于炫耀他那早慧的儿子,这也增加了他对父亲的厌烦。约翰生甚至“常常逃到树上去……以逃避在客人面前卖弄才华的场面”。[5]21但另一方面,克利福德认为,约翰生在无意识里或者内心深处又认同于他的父亲,后者实际上成为他在此后人生中克服自身弱点的一个反面镜像,在他暴发忧郁症的最令人绝望的时刻,父亲为他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力量”,从而使他免于沉沦。正是由于建立在这样一种对于约翰生看待父亲的一种既排斥又认同的暧昧态度的深度解说的基础上,克利福德对约翰生的忏悔行为的解释才获得了更为充分的说服力:他的“不孝”行为出于对父亲表面情感上的排斥,而与父亲的一种深度认同和理解则强化了他的愧疚感,使得他对早年的行为怀有一种特殊的敏感。
二、从“沉默”中理解罪感
弗洛伊德还指出了一种所谓“沉默的罪感”。弗洛伊德说,这种罪恶感“是沉默的;它没有告诉他他是有罪的”,而这个人也并没有意识到“有罪”,因而面对这一罪过他常常保持“沉默”,而这恰是罪恶感和内疚感表现出的“症状”。[7]200这启发了传记家在传主的“沉默”和“空白”之处发掘其深藏的愧疚。在克利福德看来,约翰生极富道德良知,极易产生内疚感,他几乎常常感到愧疚,感到需要忏悔,而其原因有时他并没有意识到。比如,约翰生对自己早夭的也是唯一的弟弟就基本保持了奇怪的沉默,克利福德认为,这就是一种“沉默的罪感”。
约翰生的弟弟纳萨尼尔·约翰生在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中几乎是一个空白。② 约翰生曾经向斯雷尔夫人提到,在童年时期他和弟弟成为“争夺母爱的竞争对手”,克利福德据此猜测,兄弟之间早年可能存在的充满嫉妒的争执,以及为争夺母爱而产生的矛盾或许形成了约翰生最初的创伤性记忆,而这种记忆中的伤害则很可能在后来的岁月中导致了在意识层面难以辨别的复杂反应。
克利福德结合纳萨尼尔不幸的一生对约翰生的愧疚感作了更细致的考察。和萨缪尔·约翰生相比,纳萨尼尔的一生要暗淡的多。他中学辍学之后就在父亲的书店里帮忙照顾生意,其间在书店的生意中做了一件有失诚信的事,引发了家庭内部的一些争吵。纳萨尼尔一时陷入困境,他对自己的哥哥萨缪尔·约翰生怀有十分矛盾的期待,一方面,他模糊地感觉到哥哥对自己其实“不怀好意”,在给母亲的信中他写道:“至于我哥哥的帮助,我几乎没有理由去指望,而正是由于他的意见,你才不愿让我到斯图尔桥镇去。”另一方面,他仍然抱着一丝幻想,希望哥哥能够帮助他,在斯图尔桥镇帮他找些事做:“如果我的哥哥确实能为我做些什么,我对他将十分感激……”[5]166-167但显然约翰生并没有为弟弟“做些什么”。传记家指出,童年的创伤性记忆在此发挥了影响,此外,他还有许多现实的考虑:约翰生自己在那儿有很好的发展前景,而他实在“不愿意让那个声誉不怎么好的纳萨尼尔——他必定怀疑弟弟希望来揩那些富裕朋友的油——来危及这一前景”。[5]167
这一自私的考虑最终导致了严重后果。不久纳萨尼尔就到萨默塞特一个叫做弗洛姆的地方闯荡谋生,于1737年3月5日死在了利希菲尔德的老家。克利福德指出,“纳萨尼尔之死是约翰生一生中最令人困惑的事件之一。”[5]171因为同年3月2日,约翰生和他的学生加雷克从利希菲尔德出发赴伦敦,此时尚在途中。克利福德问道:“那个年轻人必定是在萨姆出发后不久——几个小时,或至多一两天——死去的。如果他唯一的弟弟就要死了,约翰生是否还能够快快乐乐地踏上去伦敦的征程呢?”[5]172无论如何,弟弟的死给约翰生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创伤:“这一死讯对约翰生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打击。这是他少年时代的伙伴,而他很少以基督徒的宽大胸怀对待他。这是他唯一的弟弟,但他曾自私地堵死了他可能在斯图尔桥镇生活的机会。然而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弥补自己对待弟弟的那种残酷行为了。很可能这一深深的悔恨和内疚之情常常伴随着约翰生,即使在表面上他没有什么表示。他或许还梦到过纳萨尼尔,但甚至在他最亲密的朋友面前都避免提起他。”[5]172
三、抚慰“留连不去的创伤”
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权威传记作者艾德尔指出,一个优秀的传记家要探索其传主的核心情感,“一个研究传主情感中的决定性因素的传记家,要比那些仅仅展示出传主所表达出来的冲动与渴望……的传记家更接近真实。”[8]17而在艾德尔看来,詹姆斯的内心深处的核心情感正是罪感和内疚。他将亨利·詹姆斯与弗洛伊德、普鲁斯特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几乎同时都踏上了一个通向内部世界的旅程,而那是一个“不断后退的深渊”。他特别指出,在这一方面,詹姆斯是最没有自觉意识的,他主要是“将艺术用作对存在于内心深处留连不去的创伤进行净化的一种方式”。[8]19-20从这些观点出发,传记家探索了詹姆斯对女作家康斯坦丝·芬尼莫尔·伍尔森所怀有的内疚。
芬尼莫尔是美国小说家库柏的后裔。由于父亲早死,她长期陪伴母亲,在母亲死后,年近40的她独身一人生活。她一只耳朵有些聋,性格有些忧郁。詹姆斯的小说对她有很大的吸引力。她在1880年见到了詹姆斯,从此开始了延续14年之久的友谊。据艾德尔考证,芬尼莫尔显然爱上了詹姆斯,而小说家并没有明确态度。但由于芬尼莫尔很有个性魅力,并且崇拜他,这都可能使詹姆斯对她表现出了比一般朋友更多的兴趣。他们在同一个城市生活过三年时间,有时也一起去看戏、旅游。1886年芬尼莫尔去意大利,詹姆斯承诺以后每年去看望她一次。但1893年圣诞节前夕,芬尼莫尔开始流露出弃世情绪,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感到,在来生里,这些神秘和惶惑都会展开,变得清楚。……但你无论何时听说我已离开,我都要你知道我的结局是平静的,甚至在解脱的时候是快乐的……”[9]73 1894年初芬尼莫尔最终自杀身亡。
精神分析揭示出,“许多看似偶然、毫无意义的行为,以及许多被简单地归之为‘自由意志的举动’,实际上是人们没有意识到的隐秘而矛盾的愿望所驱使的。”[10]在艾德尔看来,亨利·詹姆斯的情况正是如此。在惊悉朋友的死讯时,詹姆斯原准备立即赶往意大利参加葬礼,但当他知道了芬尼莫尔那种暴烈的死亡方式时,他改变了主意。艾德尔认为正是在这里,在这一“症状性”的决定中,暴露了詹姆斯的内心所经受的真正“创伤”:
尽管难以猜测詹姆斯作出这一决定的动机,这一点依然是清楚的:当他以为芬尼莫尔小姐是出于自然原因而死去时,他本来是决定去罗马的。从他知道她是自杀的那一刻起,他就觉得自己病倒了,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不仅仅是被悲伤,以及如他所说,惊骇与怜悯,而且还有——如他后来透露及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感情:他觉得自己应该为她最后的行为负有某种责任。[9]78
当刚刚发生的事情的残酷性还飘荡在空气中时,亨利·詹姆斯觉得自己不能去意大利经受折磨。艾德尔进一步指出,他的决定显然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芬尼莫尔小姐那残忍的、暴烈的、十足恐怖的、神秘的、似乎是疯狂的最后一幕深深地刺伤了他……他现在需要一个庇护所,来抵挡他深深的受伤和愧疚”。[9]79
詹姆斯通过将她看成一个病人来解释她的非理性行为,以此来减轻自己的内心的不安。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一再强调:芬尼莫尔小姐是“慢性忧郁症的牺牲者,这种困扰在病中突然发展成为自杀冲动”,或者是她有“心理方面的疾病”。[9]73但这无非是他掩饰自己真实感受的一种无意识策略。显然,詹姆斯从“芬尼莫尔是一个严重的病人,所以她不能为其行为负全部责任”这样的想法中获取了安慰。艾德尔认为,尽管无法确证詹姆斯的真实想法以及他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了罪过,但他一遍遍地重复着“对她的友谊中有一半是忧虑”,这表明他在和芬尼莫尔的关系中发现了某种使他忧虑不安的因素。[9]81
艾德尔用詹姆斯写于这一时期的一个短篇小说《死者的祭坛》(The Altar of the Dead)更为深入地解析了芬尼莫尔之死对他造成的“暗伤”,在他看来,詹姆斯正是用他的作品来治疗这一内心创伤的,这一作品是他特殊形式的“忏悔”。
《死者的祭坛》是一篇具有浓厚的象征主义意味的故事,其主题是生者和死者之间的宇宙性联系。男主人公斯坦瑟姆为每一个死者点燃一根蜡烛,但却将一个曾经使自己遭受冤屈的朋友阿克顿·哈古排除在外。他已经原谅了他,但还不能与其彻底和解。后来斯坦瑟姆发现另有一个女人也在他的祭坛上做礼拜,她只为那个被他排除在外的人点燃了蜡烛。斯坦瑟姆恐惧地意识到,“她实际上才是圣坛的女祭祀”。他的圣坛被剥夺了,于是就在圣坛前死去了。
艾德尔认为这一故事应从宗教的角度来理解。《圣经》中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们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这样,这一故事就应被理解成为詹姆斯试图消解由他和芬尼莫尔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怨恨和内疚的一种努力。艾德尔指出,芬尼莫尔的行为肯定在亨利那里引发了一种被出卖感,他觉得那是对他心灵圣坛的一种亵渎。芬尼莫尔以某种方式让他感觉到她在向他提出某种他还没有准备好的要求,而最后她竟以这种残酷的方式表现了自己的哀怨,“他的圣坛被她的鲜血溅污了”。[9]97芬尼莫尔以这种专横的方式切断了她与亨利之间的联系,而小说家却只能利用其艺术进行自我治疗:“在他的故事中主人公死去了,在生活中詹姆斯却活了下来,同时存留下来的还有一种阴暗的疼痛,一个无法解决的、没有回答的谜。”[9]100
四、忏悔叙事的意义
可以看到,精神分析方法为现代传记对传主愧疚感的处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现代传记的忏悔叙事也使得传记家“同时成为精神分析家和倾听忏悔并予以解脱的神父”。[11]事实上,如果我们稍微深入考察一下精神分析尤其是弗洛伊德的经典理论,就会发现在其底层正流淌着一股“愧疚”与“负罪”的情感潜流。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阶段”(1895-1899)被看作整个精神分析学科得以发展的“母源”(matrix),而其主要内容就是对负罪感的揭示。弗洛伊德在被称为“梦的标本”的“爱玛”一梦中表露出他对病人、同事等怀有的罪恶感,而父亲的去世则使他意识到自己对父亲的敌意(由此他才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结”假说),此外他还分析出对与自己同龄的侄女(他同父异母哥哥的女儿)的虐待狂倾向以及谋杀兄弟亚历山大的欲望等等。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精神分析从一开始就是从一种沉重的愧疚感中诞生出来的,它的治疗任务也可以被看作通过若干复杂的“叙事行为”让病人有勇气面对自我深层的冲突,从而在某种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与自我的和解。这与现代传记对传主愧疚感的处理有着相近的旨趣。
现代传记的忏悔叙事因此具有了重要的认识价值。一般认为,诸如内疚和罪感这样的深层体验只有本人才能够把握和理解,自传作者在这方面似乎具有先天的优势,甚至拥有“专利权”。但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罪恶感的大部分恰恰是无意识的,一个人“既比他所相信的更无道德,也比他所知道的更道德”,人的本性“无论善、恶,都有一个比它所自以为的范围——即他的自我通过意识知觉所知道的范围远为广泛的范围”。[7]202自传作者由于更多地考虑到自我形象塑造和身份认同的理想化,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来面对自我的真实。而传记家因为站在一个比其传主更为客观的角度,因而有可能比传主本人知道得更多,能更好地“认识你自己”,如艾德尔所说,“传记必须放弃赞成自传”。[8]56
像《青年约翰生》与《亨利·詹姆斯》这样的传记作品对传主内疚和罪感的处理具有一种震撼读者心灵的力量,这除了和精神分析理论所带来的启发有关之外,更和传记家对于复杂人性的深入体察以及人性向善的深刻信念紧密相关。由于在某种意义上,“忏悔”可以看作忏悔者与自身之“罪”之间的“对话”,是忏悔者对自身之罪进行理解(至少是“感知”)并力图与之和解的一种行为或努力,因此,“愧疚感”或“罪感”(guilty)本身就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忏悔以及忏悔叙事的动力因素;而在更高的叙述层面上,由于现代传记家将传主的这一罪感看作人性更深层的“真实”,并相信有能力对其“忏悔”进行再叙述,因而现代传记的忏悔叙事也可以看作是现代传记家与人性真实的深度对话。这也正如杨正润所说:“忏悔话语中都包含着价值准则和道德判断,包括自我批判的成分;但是对任何忏悔来说最重要的是说出事实真相。”[12]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讲,在传主无法或没有勇气“说出事实真相”的地方,通过传记家的揭示,读者会有一种如艾德尔所说的“更接近真理的感觉”,一种“深层真实被触及时所获得的情感满足”。[8]60-61可以认为,这种建立在对人性进行更深入理解基础上的忏悔叙事正体现了现代传记的一种更为隐蔽的伦理追求。[13]
但现代传记对愧疚感的深度探索也有一定的局限。对传主而言,严格地说,除非经过他人的揭示与分析或者经过自我的反思,愧疚都可以说是不存在的;由于传记家所面对的对象大多已不在世,传记家对其愧疚感进行深度探索的可能性就只能建立在传主本人所留下的有关传记材料及其反省倾向这一脆弱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对传主的人格整体特征进行判断是对其进行深度探索的一个重要前提(这也正是克利福德与艾德尔一再强调其传主具有强烈的道德反省倾向的原因),但传记家作出此类论断往往是冒一定风险的,因为这毕竟仍是关于人性的某种想象和预设。
收稿日期:2008-10-25
注释:
① 按照弗洛伊德在《图腾与塔布》中的看法,原始人对弑父行为的愧疚感是人类文明、道德和宗教的起源,在此意义上,愧疚感和忏悔意识跟人类文明、道德和宗教是同时产生的。
② 鲍斯威尔只在两处顺便提及了弟弟纳萨尼尔,一次是开头:约翰生夫妇共生有两个孩子,一个是约翰生,另一个是“纳萨尼尔,死于25岁”。另一次提到纳萨尼尔曾接替其父亲的生意。参看James Boswell.The life of Johnson,vol.1,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00,第9页,第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