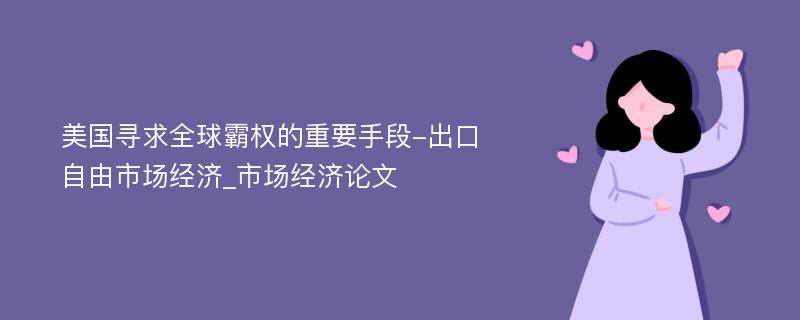
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重要手段输出自由市场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霸权论文,美国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手段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美国总统,无论是布什,抑或是克林顿,都把输出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使命,而其中,输出自由市场经济这种美国价值观则是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重要手段。美国的媒体卖力地兜售这种价值观,使之传遍四方,广闻三界。其目的是特别指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使之经济私有化,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利益多元化”,进而实行“多党竞争制”和全面“西化”,使之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纳入美国的轨道。然而专注地以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的里根经济学及其实践,在美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高失业率、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失序等社会流弊。美国自身犹如此,遑论输出这种价值观!美国输出自由市场经济,其中包括自由贸易,然而美国政府在自由贸易方面则采取双重标准,对其他国家是迫使其开放市场,而自身则实行私己的贸易保护主义。现今即使一些西方国家对自由市场经济也不愿苟同,在谈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及其效果时,也开始语带几分悲凉之感。对于美国输出自由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也需要了解其文化和政治意蕴,才识得个中玄机。
美国输出自由市场 经济的文化和政治意蕴
前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结束,使得经济力量相对更重要了。一些美国学者鼓吹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欢呼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已向私人资本的渗透敞开了国门,宣称为了成功地把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纳入资本主义范围,美国需负起政治领导和经济领导的责任。1993年1月,克林顿首次谈及美国对外政策时, 把“在国外促进民主和市场经济”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支柱之一。同年3月, 克林顿政府提出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对外关系新战略是“扩大全世界市场民主国家的自由大家庭”。为此,其中一个政策思想是“加强对苏联、东欧和其他前共产党国家的支持,”使其“扩大民主和市场经济”,从而“把以前有威胁性的国家转变为经济和外交伙伴。”同年9月, 克林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将美国对外战略概括为“民主的扩大”。这一对外战略一直延续至今。何为“民主的扩大”呢?新奥尔良大学历史学教授和艾森豪威尔中心主任道格拉斯·布林克利在《外交政策》1997年春季号上发表题为《民主的扩大:克林顿主义》中披露,“民主的扩大”是扩大世界上的市场民主制的自由社会的战略”,其内容有四点:其一是“加强市场民主制社会”;其二是“在可能的地方培植和巩固新的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其三是“反击侵略和支持敌视民主的国家的自由化”;四是“在人道主义最关切的地区,帮助民主和市场经济扎根。”文章称,“民主的扩大”的对外战略“设想在共产主义的命令经济崩溃的地方,自由经济会最终兴起和兴旺”。文章指出,“民主的扩大的观念是以经济为中心。据信,只有存在自由消费的中产阶级的国家,才能成为民主的国家,并接受西方的价值观。”“民主的扩大的概念来自地缘经济学。”“民主的扩大是意指通过传播地缘经济学的福音来扩大民主。”1997年2月4日,克林顿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强调“我们现在需要得到授权,使我们在维护我们价值观的同时,达成对我们的商品和服务开放的新的贸易协议。”“通过扩大贸易,我们可以推进世界各地的自由和民主事业。拉丁美洲是说明这一真理的再好不过的例子。在那里,民主与开放的市场如今正在共同发展。”他们摆出一付匡济天下的姿态,然而他们说得言尽辞枯,无非一句话:输出美国的价值观——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
美国鼓吹自由市场经济有其特殊的文化和政治意蕴。美国历来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包括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贸易。20世纪初“进步主义时期”的改革和30年代罗斯福的“新政”,不啻等于帮助美国大资产阶级实现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合理化,帮助大资产阶级摆脱困境。这是有案可稽的。美国前总统柯立芝有句名言:“美国的事务就是企业。”在美国,企业的利益是至上的。美国政府历来把美国企业的利益放在首位,把美国企业的利益看作是美国的利益,把美国企业的繁荣看作美国的繁荣。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总是被宣扬为美国的民主、自由、繁荣和进步的象征。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美国资本主义被视为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而不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则被谴责为“专制”。美国自诩自由市场经济创造了机会的平等,保障了民权和政治权利,保证了持续不断的进步。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实质上是“私有化”,它所信奉的和宪法规范的最高个人权利是财产权。在美国,当资产者的财产权与人民的个人权利发生冲突时,财产权则被置于首位,并不惜牺牲其他的个人权利。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工业事故频仍的原因。爱德华·格林伯格在《美国政治制度》一书中引证确凿证据,披露美国矿工的事故死亡率是英国的4倍,是荷兰的6倍。本世纪中,美国煤矿矿工平均每月约有100人死于事故。在工业部门,每年平均有500多万美国人受工伤,40多万人罹患职业病,10万多人死于职业病。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标榜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体现了众多的“自由”和“选择”,然而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把美国人塑造成处处以个人为中心的个性,也造成了美国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心态。他们努力寻求获得更多的自由和选择,但他们又是待价而沽的商品,而随时可能被他人所代替,因此时刻处于焦虑之中。与此同时他们把与他们同等地位或低于他们地位的人视为潜在的敌人,从而陷于孤独。这是美国白人男子强烈地歧视穷人、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妇女的根本原因。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成为美国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1997年的新移民法的目的正是限制外来竞争者。美国自由市场经济被吹嘘为美国自由、平等的象征,然而它却又真正是美国人钟情于不平等的心态的基础。从历史上看,美国没有西欧和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的传统,也没有强大的工会,没有工党,社会福利事业远远逊于西欧和北欧国家。
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伸。美国企业至上也是美国对外战略的原则,因此力图在全世界,特别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传播和促进自由市场经济,其实质是推动这些国家实行自由企业制度,实行私有化,不断扩大私人经济力量,并在市场自由化和强大私人经济力量的基础上培育和建立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政治。美国学者理查德·范伯格在《过激的地区:第三世界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挑战》一书中写道:美国政府力求推动第三世界国家采取“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和制衡制度,”美国“民主党政府倾向于主张,强大的私人企业是自由民主制的先决条件。”
美国输出自由市场经济是因为自由市场经济关注的基本问题是政府不要干预资产者在市场聚敛财富,正如里根总统时期的财长里甘于1981年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席会议上所言:“市场机制和个人努力以及政府的障碍减少到最小程度,这些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其中奥妙何在呢?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藤在1997年5月28日《纽约时报》撰文, 宣称美国公司“愈来愈成为体现美国价值观和影响的旗手。”“商业外交应该成为我们对外政策的主要优势,因为自由贸易为我国商人与外国商人建立联系。这种联系能够造成扩大民主的压力,促使外国政府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这样,在推动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私有化和扩大私人经济力量的基础上,形成“利益多元化”,进而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竞争制度”,移植或仿效美国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最终达到克林顿希冀的实现美国为领导的“全世界市场民主国家的自由大家庭。”
克林顿政府对于在输出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方面所取得的业绩是颇为得意的。1996年10月,克林顿在底特律的竞选集会上讲:“由于我们的帮助,欧洲的新兴的自由国家的改革力量奠定了民主的基础。我们帮助它们发展有成效的市场经济。现在正由援助转向贸易和投资。”1997年6月底,克林顿在荷兰海牙参加纪念“马歇尔计划”50 周年活动时,建议同西方发达国家一道,提出新“马歇尔计划”。法新社立即给予揭露,指出克林顿“一揽子援助建议”是“旨在实现美国政府早就想实现的长远目标,即加强西欧同东欧新出现的民主国家的贸易关系,希望能借此将这些新的民主国家更加牢固地控制在西方手中。”诚哉斯言。道格拉斯·布林克利发表在《外交政策》1997年春季号上的上述文章兴高采烈地写道:“克林顿政府自1993年以来以双边援助的方式给予叶利钦政府43亿美元援助。这种以‘民主的扩大’的精神进行的援助有利于推动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其最终结果是现在俄罗斯由私营企业生产的产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自克林顿入主白宫以来, 美俄贸易上升65%。与此同时,由于‘民主的扩大’, 美国成为俄罗斯的最大投资者。美国进出口银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以及贸易和开发署支持同莫斯科的商业成交,价值在40亿美元以上。这种全球性的自由市场的扩大以及俄罗斯1995年的议会选举和1996年的总统竞选,表明民主已最终在那里扎根。”
克林顿政府欣喜于其在东欧和俄罗斯的作为之余,眼睛也盯着中国。美国财长罗伯特·鲁宾于1997年6月5日在美中全国贸易委员会发表的讲话中,在谈及美国的经济战略时,强调美国对华的战略目标之一是“帮助中国在建立更加面向市场的经济方面取得成功。”这里,美国的“民主的扩大”的对外战略依稀可辨。
美国自由市场经济 在国内造成的流弊
80年代,自由市场经济盛行于美国。而此前,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作和“新右派”学者的论著为之奠定了理论基础,而被称为“自由市场右翼”的经济顾问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转化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导向。这种理论批评二战后中央政府权力的扩大和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使资产者颇有微词,批评凯恩斯主义不能解决70年代的“滞胀”危机;它信仰自由市场经济形式的社会组织的优越性胜过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的社会组织形式,能提高经济效率和所谓能保障个人自由;它阐述了国营私有化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思想;它称誉自由市场经济最能使人们保持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人们会有更多的自由和选择以及个人消费的快乐,把任何人的贫困归咎于他们自身的无能,并以此转移人民大众对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注意力;它强调财产所有者的主权作用,资产者在人们按广告文化设定的消费导向来实现自己梦想过程中,攫取最大利润,而这又是以所谓“市场自由”“个人权利”等美丽语言加以粉饰的。
对于里根时期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后果,美国学者埃玛·罗斯柴尔德作了整体性的概括。他在1988年6月30 日《纽约书评》上发表的《真正的里根经济》一文中写道:“真正的里根经济,是同他的政府拟创造的保守主义牧歌,是实际上正相反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法律和社会研究中心的埃利奥特,柯里教授在《自由市场政策、不平等和社会措施》一文中称,里根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特点是,“在经济速增的过程中扩大了贫困。表面的‘繁荣’也伴随着忧郁的眼泪。”
英国伊恩·泰勒在他主编的《自由市场政策的社会影响》一书中披露,在80年代初至1986年,美国失业率达9.5%。自由市场经济政策造成贫富进一步分化,这是因为里根政府为了扩大私人市场,系统地削减了整体上有利于低收入美国人的政府开支,也是由于里根政府的就业政策是依靠私人市场,减少公共就业,鼓励扩大低工资就业和降低最低工资的实值。在80年代,美国低于贫困线的工资的职业发展速度两倍于高工资职业。1989年,在美国,5名穷人中有2人,其收入低于官方贫困线的50%以下。而“脱离贫穷的可能性”, 即穷人在第二年脱贫的机会急剧下降。F.M.哈里斯等人主编的《平静的骚乱:美国的种族和贫穷》一书指出:“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使贫穷加深,以致脱贫变得更为艰难。”在1979年至1985年期间,操西班牙语儿童的贫困率增长43%,甚至白人儿童中的贫困率也增长35%。1970年至1987年期间,占人口5%的最穷者,个人实际收入下降10%,而占人口5%的最富者,实际收入增长16%。若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在家庭贫困率方面,瑞士和瑞典约为4%,西德和挪威6—7%,加拿大和英国8%,而美国高达14%。在贫困减少率方面,瑞典为58%,挪威47%,而美国仅为17%。美国学者J.K.加尔布雷斯在《周末卫报》1989年第2 期上撰文写道:“我们美国的穷人仍然贫穷。这归因于这一类的人数的大量增加,收入的更大份额进入富人的腰包。在我们大城市的中心区的生活和条件,若用审慎挑选的字眼来说,是低劣得不像话。住房糟糕,并愈来愈糟。我们许多公民甚至没有栖身之处,他们的收入近于饥饿水平。学校也糟。青年人和老年人常靠犯罪为生,以吸毒来暂时逃脱失望。”
80年代兴起房地产热,但新建住房不是以购买第一住房的家庭为主要对象,而是以已有住房的人为主。富人往往狡兔三窟。房价的上涨和收入的下降,增加了无住房者的人数。美国众议院的儿童、青年和家庭特别委员会披露,“无节制的自由市场的影响,使许多人不可能购买普通住房。”廉价出租的房屋也少了。需要租赁这类住房的家庭数与可提供的这类住房的数量之间的差距增长120%。
自由市场经济造成美国穷人就医难。联邦支付的给穷人提供的三种保健,即妇婴保健、社区卫生中心和流动卫生中心等下降32%。 在自由市场经济机制下,医院采取了“钱袋诊断”,为赚钱而治病。例如在芝加哥,被遗弃的病人由1980年的1300人增至1984年的5600人。90年代初,每年约有25万病人因经济原因而被赶出医院。
里根和布什时期,经济有所增长,但美国却成了一个破碎的国家,社会动乱频仍,渲泄长年遭到剥夺的积忿。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损害了公共福祉,给普通美国人,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带来了灾难。不少美国学者纷纷指出,不能过份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市场作用,而削弱政府的社会责任,特别是不应忽视公共事业和保护所有公民的社会和个人的权利。然而为什么美国极力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输出自由市场经济呢?为了诱骗,必然夸大自由市场经济的功能,而舆论的功效取决于舆论背后的各种实力的较量。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体现的是私人企业至上,正是美国的大资产阶级在背后推波助澜。输出自由市场经济价值观,实质上是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重要手段。
自由市场经济沉疴难愈
8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遇到战略上和政治上的困难。时至今日,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已开始陷于落叶哀蝉的境地。公众舆论明显地表现出强烈地造成国家关注公共交通和卫生事业,严格管理私人企业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要求改变纯粹个人主义的政治。而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如日本和德国,早就不赞成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而实行经济的和社会的组合主义,把整个社会置于国家的领导之下。1997年在大选中取胜的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在谈及施政方针时,都表示要有所改弦易辙。托尼·布莱尔在竞选中即提出“新工党、新政策”的口号,认为有活力的经济既不能由国家单独控制,也不能死守“市场经济”的教条,而应建立在政府为企业、雇主与雇员、国营与私营三个良好的伙伴关系基础上。”一些专家学者也对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实践进行抨击。联合国贸发会议总干事鲁本斯·里库佩罗于1997年7月初警告说, “让世界经济在一个放任自流的自由市场中发展将会扩大贫富差距,并造成使改革毁于一旦的全球性强烈反响。 ”欧洲复兴和开发银行前行长雅克·阿塔利在《外交政策》1997年夏季号刊登了题为《西方文明的冲突——市场与民主的局限性)的文章,指出“美国外交的主要使命看来就是输出这些价值观(指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至少对美国有利就这样做。”“这两种价值观本身事实上并不能支撑任何文明。”除非美国“开始承认市场经济和民主的不足之处,否则西方文明必将逐渐没落,最终将自我毁灭。”他进而指出,“民主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有着三个根本缺陷,其一,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指导原则不能普遍用于西方社会;其二,这两套原则常常互相抵牾,相互对立较之相得益彰的可能性更大;其三,它们自身包孕着毁灭的种子。”“市场经济剥夺了一部分人的满足自身基本经济需要的能力,与此同时也就削弱了他们行使完全的政治权力的能力。”阿塔利也历数了自由市场经济造成的其他各种弊病,他尖锐地警告说,“不要一味得意地自吹价值观的全球化。实际上这些价值观即使在我们社会的运用范围也是有限的。”
美国输出自由市场经济的同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这更加明显地暴露了美国政府在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方面翻云覆雨的霸权主义特性。按自由贸易理论原则,贸易的流向应基于比价,而非为达到双方平衡而流入这个或那个渠道,因此应排除商品和资本流动的人为障碍,让人们在最便宜的国外市场上购买,并且在利润最大的地方销售。克林顿的“民主的扩大”的对外战略的中心是自由贸易。美国商业部负责国际贸易的副部长斯图尔特·艾琴斯泰特说,“在冷战中是‘遏制’,现今是扩大民主的范围,这都是涉及扩大进入市场的机会。”然而克林顿政府的对外贸易的主导原则却是创造出口顺差。这理所当然地遭到谴责。1997年2月, 联合国贸发会议总干事里库佩罗“指责大国敦促发展中国家开放经济,自己却坚决防止它们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如果设想,市场力量一定会被赋予毫无约束的自由支配权,那就大错特错了。”欧盟负责大西洋两岸关系的委员布里坦于1997年7月29日在其年度报告中, 批评美国的贸易霸权主义行为,指出“美国某些做法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仍然是相违背的,甚至是保护主义的,”“美国对古巴、伊朗和利比亚使用治外法权影响了欧洲一些公司的利益。”
美国在举世谴责声中会不会改弦易辙呢?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不减昔日的煊赫声势。当西方七国和俄罗斯的首脑在美国丹佛聚会时,克林顿声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已证明是“经济管理的最佳模式。”可以想见,克林顿政府不会另谋良策,会继续把输出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