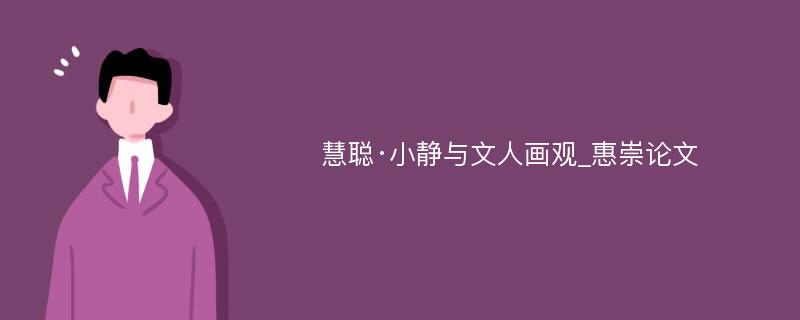
惠崇小景及其文人画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人论文,观念论文,惠崇小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景”作为古代绘画的画科之一,因为画家人数和绘画数量都比较少的缘故,被附入《宣和画谱》十门之末的“墨竹门”之后。虽然是附录性质,却表明了这一画科在北宋的地位。推究“小景”的来历,在宋人的心目当中,与“惠崇小景”是分不开的。惠崇是一代诗僧,多写“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诗意澄净清幽,被认为是北宋诗僧中最杰出的。又工画,“善为寒汀远渚,萧洒虚旷之象,人所难到也”,得到王安石、苏东坡等大文豪的好评。以诗入画,以画入诗,人所难到,因而得以专设称为“惠崇小景”。此名最先见于欧阳修《诗话》,“世谓‘惠崇小景者’是也”①。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宣和画谱》虽然把小景画名流的赵大年、梁师闵列入其中,却没有记录惠崇其人②。赵、梁二人都有可信的作品传世,参照这些作品,并结合惠崇的诗歌绘画,可以了解“小景”的艺术特色,同时还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北宋后期文人画美学观念发展的态势。
一
惠崇是文学史上有名的宋代九僧之一。九僧以唐韵十足、风神秀朗著称,历代认为惠崇在九僧之中名数第一。和尚们逃禅于诗,以诗歌作佛事,是禅宗兴起之后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自唐代禅宗分成南北两宗以来,以慧能为中心的南派独盛,文人士大夫或多或少地受到南禅的影响,在诗歌中渐渐表现出禅境、禅趣和禅悦。僧人们也渐渐地步入诗坛,典型的如寒山、拾得、齐己以及后来的宋初九僧等,他们以平凡的景物为诗材,辞藻清新,在诗中表现禅悦,以诗作佛事,以诗把他们向往的禅悦表现出来,而且作为诗的艺术性也越来越强,诗味悠长,澄清高逸,渐渐引起文人士大夫的重视,得到好评。诗的美与禅的趣,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金代元好问在《答俊书记学诗》中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歌切宝刀。”③ 元人方回云:“释氏之炽于中国久矣,士大夫靡然从之,适其居,友其徒,或乐其说,且深好之而研其所谓学,此一流也。……诗家者流,又能精述其趣味之奥。”④ 这些评价,无论对好禅的诗人,或是好诗的禅僧来说都是切合的。这一类的诗,在诗意禅趣上,大抵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澄清高蹈的志趣,二是追求清幽冷寂的心境,总体来讲,表现出一种关注自我而不暇旁顾的个人抒情写意。惠崇的诗,恰好表现出这两个特点。
他的诗,《宋史》著录有诗三卷⑤,《文献通考》著录有《惠崇集》十卷⑥、《惠崇句图》一卷⑦。其得意之作,如《湘山野录》卷中有:“莱公一日延诗僧崇于池亭,探阄分题,丞相得池上柳青字韵,崇得池上鹭明字韵。崇默绕池径,驰心于杳冥以搜之,自午及晡,忽以二指点空微笑曰:‘已得之,已得之,此篇功在明字。凡五押之,俱不倒,方今得之。’”⑧ 欣然自喜之态,溢于言表。这首诗是:“雨绝方塘溢,迟徊不复惊。曝翎沙日暖,引步岛风清。照水千寻迥,栖烟一点明。主人池上凤,见尔忆蓬瀛。”《六一诗话》不仅摘录了惠崇脍炙人口的联语,还说到了惠崇作诗的题材特点,有这么一则趣闻:“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余少时闻人多称其一曰惠崇,余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记其诗有云:‘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又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其佳句多类此。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谓九僧者矣。是可叹也。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辞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⑨
惠崇的佳句不止六一居士所引的两联,但仅此一诗两联,已经可以想见宋人称其“于近代释子中为杰出”⑩,并非虚妄之评。惠崇的诗才与其他诸僧一样,都是“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在平凡习常的景色当中发现了禅趣诗意,故而历代诗评常提到他继承着陶渊明、王摩诘等大诗人的传统。中国传统的艺术家都追求心灵的自由流动,在大自然的树石花鸟之中寄托着艺术的最高理想,并给了艺术家无穷的灵感。由此,许多中国艺术家把自然作为艺术的对象,就不足为怪了。许多艺术杰作都是写山水、花鸟、树木、竹枝,仿佛可以看见一人,在山脚下,在溪水边,静坐沉醉在天地的大美之中,从中领会超越于自然和人生之上的妙道。惠崇的诗,不正是如此吗?
二
郭若虚撰写的《图画见闻志》(约元丰初年成书)(11),仅在卷四有两次提到“小景”。其中一处说:“建阳僧慧崇(即惠崇)工画鹅雁鹭鸶。尤工小景,善为寒汀远渚,萧洒虚旷之象,人所难到也。”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四:“僧惠崇善为寒汀烟渚萧洒虚旷之状,世谓‘惠崇小景’。画家多喜之。故鲁直诗云:‘惠崇笔下开江面,万里晴波向落晖。梅影横斜人不见,鸳鸯相对浴红衣。’东坡诗云:‘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舒王诗云:‘画史纷纷何足数,惠崇晚出吾最许。沙平水淡西江浦,凫雁静立将俦侣。’皆谓其工小景也。”
著录中的惠崇绘画较多,现在只有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的一幅长卷被认为较多地体现了惠崇的绘画特色。《溪山春晓图》,绢本设色,24.5×185.5厘米。卷首有李兆蕃“溪山春晓图”五字。画江南平远景色,不太高的山坡上桃红柳绿,桃花的红色融在墨色之中,淡淡的呈现出清丽的春天暖意。山坡之间有清泉叮咚而过,有两群鸭子在嬉戏,仿佛就是东坡看到的那幅“春江水暖鸭先知”。水禽翔集,桃柳人家,不愧为溪山春晓之称。本幅有乾隆诗题,一口气写了三首诗。其一:“馥馥兰芬炉地陈,溪山动植共熙春。摩挲七百余年物,润手桃花带露新。”其二:“禅宗南北画还同,六度中禅属惠崇。奇迹千秋贵得所,真诠拈出是思翁。”其三:“个僧工画又工诗,妙构溪山春晓时。若识本来无一物,淡皴浓抹更奚为。”(12) 第三首诗点出了惠崇工诗工画的特点,化有慧能的悟道偈语,说惠崇既然理解了“菩萨本无树,明镜亦非台”,那么,淡皴浓抹都是妨碍他以笔墨作佛事。第二首则来自董其昌跋语,董跋曰:“五代时僧惠崇与宋初僧巨然,皆工画山水。巨然画,米元章称其平淡天真;惠崇以右丞为师,又以精巧胜。江南春卷为最佳。一似六度中禅,一似西来禅,皆画家之神品也。”(13)
惠崇善诗善画,一身兼诗人与画家两任。他的画,据郭若虚说:“工画鹅雁鹭鸶”,与他的诗题相似。所画重在“寒汀烟渚萧洒虚旷之状”,与他的诗表现出的情趣是一致的。如果忽略表现形式的差异,他的诗与他的画完全可能相通,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画即是诗,诗即是画。苏东坡说王摩诘“画中有诗”,出于追慕的要多于历史的真实,而切切实实地将“画中有诗”发展到成熟的是北宋中期前后,是在惠崇的画笔下实现的。他的画被称为“惠崇小景”,与他作为诗人的文学修养是分不开的,这无疑是对他绘画成就的肯定。尤其是王安石,“画史纷纷何足数,惠崇晚出吾最许”,将惠崇与寻常画史对举,足证王荆公看重他的诗意禅趣。
自此以后,“小景”之名与惠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众多的文人墨客中传颂着,也被作为绘画的专门一科载入《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等画学文献,成为凝固的历史。
三
北宋在武力上自然不及汉唐,而在文化上却足以与之鼎足,但其文化的特点不一样。北宋更多的趋于内省,从中寻找个人诗意化的生存。即使是通常觉得是板着面孔说教的理学也在教人寻孔颜之所乐,仅是这一个“乐”字,就足以显现诗意化的文化特质了。诗意化的生存,也就是文学化的生存,不仅理学如此,绘画也是如此,对绘画的诗意化要求,宋人分成两步完成了向文人诗意化的转变。一是借助文学的灵感绘画,一是以文学的审美品评绘画;前者是立足于创作层面,后者是着眼于品评层面的。前者以郭熙为代表,《林泉高致·画意》:“佳句好意亦看不出,幽情美趣亦想不成,即画之,生意亦岂易有?”“古人清篇秀句,有发于佳思而可画者”云云(14),以诗意通于画意。在宋徽宗的皇家美术学院(古称“画学”)进行的考核,以诗为题作画,与郭熙有承续的关系。后者以苏东坡为代表,“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这里是论画而不是创作绘画,但东坡以后终究要发展到“作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这一步的。苏东坡又说王摩诘的《蓝田烟雨图》:“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曰:‘蓝溪白石出,玉山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此摩诘之诗也。”(15) 这仍然是一种欣赏口味的眼光。
综合郭苏二家之言,能入画的诗,需要满足这样的条件:一、幽情美趣;二、清篇秀句,有发于佳思而可画者;三、天工与清新。即使是王维的诗也不完全符合这样的要求,试问“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如何画得出?虽不能画出,恰恰是这首诗的灵魂,是诗中之诗。仅仅画出前两句,虽是好景,却不是好画。而惠崇的诗显然就不一样了,“指咏风景,影似百物”,像他自己很得意的“照水千寻迥,栖烟一点明”,全是景物,情在景中,人在景后,如同王国维所说的,是一番有我之境,水是我,烟是我,有水便有我,有烟便有我,水能入画,烟能入画,我岂不已隐隐然在其中了吗?虽然惠崇的诗和画之间仍有难以逾越的障碍,但已经相当接近了。正因为如此,《宋稗类钞》卷二十才这样评述说:“僧崇人知其绘事精妙超凡,不知诗句亦清远,有冰雪松霞之韵。尝作《句图》,书其所最得意,如‘岭暮春猿急,江寒白鸟稀’,‘掩门青桂老,出定白髭长’,‘鸟归杉堕雪,僧定石沉云’,‘空潭闻鹿饮,疏树见僧行’,‘磬断虫声出,峰回鹤影沉’,‘繁霜衣上积,残月马前低’,‘移家临丑石,租地得灵泉’,‘残月楚山晓,孤烟江庙春’,‘松风吹发乱,岩溜溅棋寒’,‘云残僧扫石,风动鹤归松’,‘禽寒时动竹,露重忽翻荷’,‘野人传相鹤,山吏学弹琴’,‘地遥群马小,天阔一雕平’”。(16) 皆亲切如画,一如他的老友林和靖之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清冷静穆,如诗如画,如画如诗,又不着诗画痕迹,自有一种别趣。与惠崇的画比较起来,没有惠崇这样的诗,便不能有小景画,没有惠崇的小景画,也不能有这样的诗,诗画融为一体,已密不可分了。
“惠崇小景画”之名确立后,惠崇风格的诗也可以称之为“惠崇小景诗”了,影响很大。把惠崇作为小景的代表人物,并不局限于绘画领域,比如高似孙所著的地理学著作《剡录》就这样说:“莲:剡少陂隰,莲芰非利。钱昭度《剡溪诗》:‘到处杨柳色,几家荷叶风’。尚言此也。择璘《荷花诗》:‘双双白鹭坠青空,飞入花汀杂翠红,烟火一篷渔舍晚,归时荡漾小舡风。’全似惠崇、大年小景。”(17) 这也正表明了他们的诗和画是相通的,小景画便是小景诗,小景诗便是小景画,诗画合一,画诗一体的。如果说高似孙用画论作诗论,这也未尝不可。
这样的诗人画出来的画是那样合乎文人画的基本理想,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宣和画谱》才把小景画与墨竹画合在一起加以论述:“绘事之求形似,舍丹青朱黄铅粉则失之,是岂知画之贵乎有笔,不在夫丹青朱黄铅粉之工也。故有以淡墨挥扫,整整斜斜,不专于形似,而独得于象外者,往往不出于画史,而多出于词人墨卿之所作。盖胸中所得,固已吞云梦之八九,而文章翰墨形容所不逮,故一寄于毫楮,则拂云而寒,傲雪而玉立,与夫招月吟风之状,虽执热使人亟挟纩也。至于布景致思,不盈咫尺,而万里可论,则又岂俗工所能到哉?画墨竹与夫小景,自五代至本朝才得十二人,而五代独得李颇,本朝魏端献王、士人文同辈,故知不以着色而专求形似者,世罕其人。”(18)
墨竹画以文同为代表,正如苏东坡反复表彰的那样,承载着文人的理想。惠崇的小景画也一样。然而,这篇叙论不谈论墨竹和小景这两门画科本身如何如何,而是通篇谈论词人墨卿作画,“不专于形似而独得于象外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词人墨卿的文章,“胸中所得”,高于普通画史。当时的绘画情形,尤其是宋徽宗时期的花鸟画特别发达,从花鸟画的情形来看,都是五彩精妍、以形似胜气韵的。墨竹和小景这两科却不是这样,他们求形似却重于“有笔”而不是“丹青朱黄铅粉”,以“有笔”与“得于象外”作为他们追求的目标。
按我们的理解,《宣和画谱》之所以这样,恐怕只能因为编纂这部书的人早已认同了文人画的基本理念。事实上,《宣和画谱》引用了苏、黄等人的许多论画语,而将其改头换面,不愿直接称名罢了。
四
回到惠崇小景画,让我们再度细细地品读《溪山春晓图》,既有水渚平滩,又有水禽活动。诸大家评述惠崇的小景画,也包括着这样的两类基本素材,万变不离其宗。《宣和画谱》是按绘画题材把作品分成十大门类的,第一是道释,第六是山水,第八是花鸟,都有相应的固定的绘画题材,倘若不是接受文人士大夫的绘画观念,墨竹完全可以并入花鸟,小景也完全可以并入山水,又何必非得单列呢?属于这一画科的画家,有这样的特点:第一,都是游戏翰墨的文人士大夫,非寻常画史可比。第二,凡作小景,滩渚和禽鸟都占有特出的位置。根据这两点,我们来考察赵大年和梁师闵。《宣和画谱》在墨竹附小景这一门里共著录了十二位画家,其中,擅长小景的有赵大年和梁师闵两人,他们都有作品存世。
赵令穰,字大年,“生长宫邸,处富贵绮纨间,而能游心经史,戏弄翰墨,尤得意于丹青之妙。至于画陂湖林樾,烟云凫雁之趣,荒远闲暇,亦自有得意处,然所写特于京城外坡坂汀渚之景耳。”这里提到的“游心经史,戏弄翰墨”云云,正是表明他在诗文书法方面的修养。他的画现存有一卷《湖庄清夏图》,绢本淡设色,19.1×161.3厘米,现藏于波士顿美术馆,卷尾自识“元符庚辰(1100年),大年笔”并押“大年图书”朱文印。所画正是“陂湖林樾,烟云凫雁之趣”。画面以当中的湖水为分割,湖岸垂柳依依,雾霭弥漫,湖庄静幽,其间点缀有荷花、小鸟,趣味盎然,优美平淡,甚至带有一丝凄幻幽迷的感伤。画法自成一家,笔法柔润,墨气滋润,柳叶用笔来回反复挥扫,随意而不狂放,温柔却又自然。画中坡岸、汀渚、树木都是浑朴有情,内秀外雅,悠闲意度中见自然和漫,表现出天工清新的诗意。难怪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称之为“超轶绝尘”,并说是元代倪瓒的先驱。另一件作品《江村秋晓图》画的也是汀渚小景,一群大雁从冰滩芦丛中惊飞而起,引颈向空,水渚村庄,雾带绕林,颇似《湖庄清夏图》,而显得更为荒率。这两件作品与《溪山春晓图》有明显的联系,表现他们在绘画审美方面有相通之处。
梁师闵,字循。其父梁和“尝以诗书,师闵略通大意,能诗什”。其后梁和“因其好工诗书,乃令学丹青,下笔遂如素习。长于花竹羽毛等物,取法江南人。精致而不疏,谨严而不放”。这里对梁师闵还不十分推重,认为方兴未艾,过于拘谨了。他的作品现存一卷《芦汀密雪图卷》,绢本设色,26.5×145.8厘米,故宫博物院藏。画幅尾部有“芦汀密雪,臣梁师闵画”自署款。此画作雪中湖景,能于凛冽中表现出温暖的情感。湖塘汀渚造型静穆,晕染也很温厚。近处画倩枝筱竹,落笔特别轻柔,枝干婀娜多姿。远处寒芦霜蓼,雪霰霏微,景致清淡秀雅,用笔铺摇闲绵。渚头的卧雁,湖中的鸳鸯,相偕相随,造意备极生动。在这里,作者的神思和笔墨修养都表现得十分突出。
除了赵大年、梁师闵之外,还有赵士雷的一卷《湘乡小景图》也属于小景画。赵士雷“有诗人思致,至其绝胜佳处,往往形容之所不及。盖胸次洗尽绮纨之习,故幽寻雅趣,落笔便与画工背驰。”(19)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湘乡小景图》,43.2×233.5厘米,是赵士雷唯一的传世作品。画幅前隔水有徽宗“宗室士雷湘乡小景”瘦金书题签,归入小景的范畴,可以说是徽宗皇帝钦定的。此图前景作松柏女萝,摇姿回墉,后景是溪柳匝岸,飘垂弄阴,一派仲夏气象。滩边菖蒲丛生,湖中则白鹭、野凫等水鸟,三五成群,有的嬉戏相逐,沉浮觅食,有的交颈憩息,修羽舔翅。翔则掠水,落则惊波。树头上鹧鸪交鸣。画面活泼有趣,意境恬淡朴实,富有诗人思致。
有一件定为徽宗画院之作的《人物画页》,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绢本设色,29×27.8厘米,图中人物背后的屏风,所画正是与梁师闵《芦汀密雪图》相似的汀渚水鸟,表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对这类小景画的倾慕。(20)
梁师闵传记里所说的“取法江南人”,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北宋末年的画坛,渐渐地从山水三大家关仝、李成、范宽和花鸟画宗黄筌等人转向于江南风情,像崔白取法于江南的徐熙,米芾推重江南的董源等,梁师闵自不能例外。值得注意的是,小景画的创始人惠崇,有说是淮南人的(《宋稗类抄》),有说是建阳人的(《图画见闻志》),有说是“楚僧”的(《青箱杂记》、《类说》),然其人载入《湖湘故事》(《说郛》卷三十下摘抄),则以楚僧为近是。要之,惠崇主要生活于南方山水林樾间应当是合乎实情的。江南文化渐渐浸入北宋文化的主流,源于惠崇小景画是山水画的别一格致,它表现湖山田园生活所特有的朴素宁静的情趣,不像全景山水那样端严凛深,似更平易,更富有诗的意境。我们现在知道专擅此格的画家不多,能见到作品的更少,惠崇开其端绪,赵令穰、梁师闵和赵士雷等数人承其后,北宋仅此数人而已。小景画在北宋后期得到重视,是文人画观念展开的一个侧面。小景画就题材而言,多画汀渚水鸟;就意趣而言,多写澄净清幽。小景画与尺幅大小并没有多大的联系,像前举赵士雷的《湘乡小景图卷》,长两米有余,可谓高头大卷,绝不能称之为小幅。后世书画家有一种说法,把小景与小幅等同起来。但这并不是宋人所说的小景画,更不属于“惠崇小景”的范畴。(21)
注释:
① 《宋稗类钞》卷二十引《欧阳文忠公诗话》,四库全书本。按《诗话》版本较多,此本引惠崇事实较多。
②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五《惠崇小景》:“惠崇作画,荆国王文公屡褒奖之,京、卞作《宣和谱》坚黜之,何耶?”——袁桷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③ 金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十四,四部丛刊本。
④ 元方回《瀛奎律髓》卷四十七。
⑤ 《宋史》卷二百八《艺文志》第一百六十一。
⑥ 《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五:“陈氏曰:淮南僧惠崇撰与潘阆同时,在九僧之数,亦善画。”
⑦ 《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九:“陈氏曰僧惠崇所作。”按,所谓“句图”,《说郛》卷八十二上引刘《贡父诗话》云:“人多取佳句为句图,特小巧美丽可喜,皆指咏风景,影似百物者尔,不得见雄材远思之人也。若此等句,其含蓄深远,殆不可模仿。”
⑧ 宋僧文莹《湘山野录》,四库全书本。
⑨ 欧阳修《六一诗话》,历代诗话本。
⑩ 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九、《说郛》卷三十下引陶岳《湖湘故事》、宋江少虞《事实类苑》卷三十六等。
(11) 《图画见闻志》,四部丛刊本。成书时间据阮璞考定,说载《画学丛证》,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7月版。
(12) 又载《御制诗集》二集卷七十五。
(13) 《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三十一《明董思白画旨》。
(14) 郭熙著、郭思编《林泉高致集》,四库全书本。按,此书通常省称为“林泉高致”。
(15) 苏东坡《东坡题跋》,丛书集成初编本。
(16) 清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二十。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卷三节录。
(17) 高似孙《剡录》卷十。
(18) 《宣和画谱》卷二十《墨竹叙论》。
(19) 《宣和画谱》卷十六《花鸟》二。按,赵士雷名下的作品有51件,其名称有“春岸初花图”、“桃溪鸥鹭图”、“春江落雁图”、“春晴双鹭图”、“暖水戏鹅图”、“春江小景图”等。看来,赵士雷擅长的是“小景”,不应列入花鸟门。
(20) 林柏亭、蔡玫芬《宋人〈人物〉》,见台北故宫博物院编《故宫文物月刊》,总第150期。
(21) 阮璞《释小景》,载《画学丛证》,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7月版。
标签:惠崇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文人画论文; 图画见闻志论文; 宋朝论文; 读书论文; 宣和画谱论文; 说郛论文; 宋稗类钞论文; 文献通考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