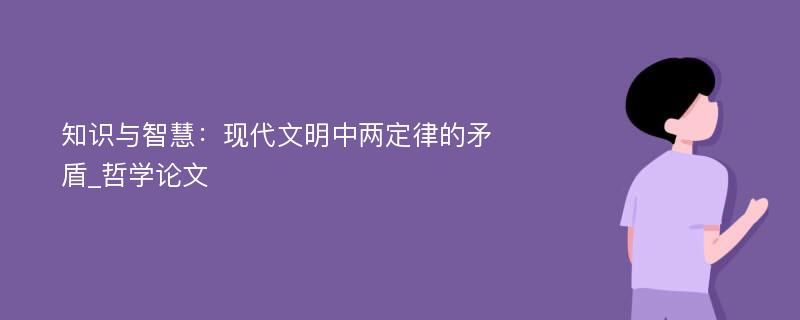
知识与智慧:现代文明中的二律背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智慧论文,知识论文,二律背反论文,文明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198(2000)03—0012—06
人们常说,我们正处于“知识爆炸”的时代;不久前,人们又开始兴奋地谈论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这无非是说,知识分支越来越多,每个知识分支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知识更新越来越快,知识在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知识创新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知识通过产权界定可以买卖,等等。但现代人有个严重的缺陷:知识有余,智慧不足。那么,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智慧?知识与智慧之间的区别何在?
知识就是人类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是对具体事物之因果联系或具体事物之内部结构的描述说明。知识亦是种种能指示我们进行物质操作和社会操作(包括金融、商业操作)的信息和方法。所谓知识创新主要是指信息收集和方法创新。有了关于特定事物的知识,我们就可以改造、控制该事物。所以,有了知识,我们就知道如何进行种种操作,就既可以让自然物为我们所用,亦可以通过社会协作而达到特定目的。一般来讲,知识是通过分析的方法获致的,主要是由科学与工程技术提供的。但广义的知识也包括对前人知识和思想的了解,这种知识又特别表现为博学之士对前人思想表述的记忆,如记住柏拉图《理想国》第五卷说了什么,《老子·十三章》是怎么表述的(包括如何遣词造句)。
智慧则是在知识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人对世界与人生的博大圆融的理解。智慧是抽象的,但又直接关乎人的生活整体;智慧是高度综合性的,而不是对具体事物及其演变过程的精确说明。智慧涵盖着对无限的理解,但智慧所涵盖的对无限的理解不同于数学对无限的描述。数学所说明的无限是纯形式的无限,而智慧所涵盖的无限是本体的无限,是有限的人类应对之心存敬畏的无限。与纯理性的知识相比,智慧之综合不仅体现为概念的综合,而且体现为思想与实践的合一,体现为理性、情感和意志的统一。智慧能用语言表达,但更多地体现于主体的行为选择和处世态度,或体现为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境界(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388—392.)。智慧用语言表述出来似乎是“元话语”,但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虽为“元话语”却并不表述大智慧。大智慧更像老子、庄子、苏格拉底和海德格尔所表达的微言大义。有大智慧的哲人常会觉得囿于逻辑和语法有碍于表达大智慧,所以海德格尔所表达的大智慧极其晦涩难懂,并被分析哲学家们斥之为“无意义的胡说”。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大智慧,有时体现为后现代主义者们所十分厌恶的“宏大叙事”或“宏大话语”,故常被那些认为“平平淡淡就是真”的学者斥为大而无当。若认为只有能指示我们进行物质操作和社会操作的知识才有用,那么智慧就没有什么用。但智慧的作用不在于指导操作,而在于指导人们的价值取舍,指导人类的努力方向。
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把握知识与智慧之间的区别。
一、科学与哲学
知识是由科学所提供的,科学基本上也只能提供知识。现代工程技术是最具有可操作性的知识。有些酷爱科学真理的人强调科学不同于工程技术,但无论从科学技术史上看,还是从科技之实际运作上看,都否认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工程技术是由科学派生出来的,没有现代科学,就没有现代技术。智慧则主要是由哲学提供的。当然并非所有哲学皆提供智慧,20世纪上半叶的英美分析哲学,基本上不提供智慧,因为分析哲学自觉地充当科学的附庸,只做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方面的“细活”(注:Cf.Peter Winch.The Idea of Social Science 〔 M 〕.Routledge & Kegan Paul,London,1958.P.5.),而不屑于“大而无当”的“宏大叙事”。宗教、文学和艺术也提供智慧,但宗教由于过分强调信仰、避免怀疑,便不具有哲学的空灵;文学和艺术的表现形式灵活多样,且不局限于语言文字,从而可补充哲学之不足,但它们对智慧之追求远没有如哲学那样穷根究极的执着。
科学研究的方法亦被称之为“自然的方法”(注:Cf.Arthur C.Danto.Naturalism〔A〕.in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C〕,Vol.5 and 6.448—449.)。其基本特征有二:一是特重经验实证,即科学上被接受的假说必须先经过观察或实验的验证,亦即仅当一个假说能得到“经验事实”的归纳支持,才会被科学共同体所接受;二是特重逻辑论证,能整合成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是一个理论可被称之为科学理论的必要条件。科学方法的这两个特征,决定了科学不会“空谈性命”,不会大而无当地“坐而论道”。科学决不去谈论“无限存在”,因为述说“无限”或“存在”的命题,无法与经验事实取得直接、明晰的逻辑联系。科学之优点在于它的实证方法,科学之短处亦在于它的实证方法。就其优点而言,科学提供最具有可操作性或最有用的知识;就其短处而言,科学不可能直接为人类提供大智慧,因为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的大智慧必须涵盖对“无限”与“存在”的理解。
传统哲学则以“爱智慧”为其根本特征,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就以理解“无限”与“存在”为己任。20世纪上半叶逻辑实证主义之拒斥形而上学(注:Cf.Alfred Jules Ayer.Language,Truth and Logic〔M〕.Dover Publications,Inc.,New York,1952.33—45.),实在是哲学的堕落,因为它试图把哲学归结为逻辑学和语言学,使哲学完全从属于科学,使哲学完全放弃对“无限”和“存在”的追问。但哲学若放弃了对“无限”与“存在”的追问,就决不可能达到其应有的彻底性。值得庆幸的是,逻辑实证主义之“拒斥形而上学”运动已成为过去,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形而上学在英美也正走向复兴。
当然,哲学不可漠视、轻视科学的成果。智慧与知识的区分也是相对的,智慧必须建立在知识之上。哲学须以尊重科学、直面现实的态度,再加上穷根究极地追问“无限”与“存在”的执着,才能达到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大智慧。哲学像科学一样重视逻辑论证(这是哲学不同于宗教的地方),但不像科学那样重视实证,即哲学不要求自己的每一个论断都能取得经验事实的直接归纳支持。然而,哲学具有比科学更加彻底的理性精神。没有哲学彻底的理性精神,人类就达不到对无限存在的理解。例如,科学认为我们居住的宇宙是有限无界的,它有诞生的起点,它诞生于150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它仍在膨胀。 科学家们之所以能接受这一学说,就因为它受到了天文观察事实(即经验事实)的归纳支持。但科学家们不能接受宇宙无限论。科学不愿对产生于“大爆炸”的宇宙之外的存在有所断言,因为关于无限存在的议论无法直接得到经验事实的归纳支持。然而,从纯粹理性的角度看,断言惟与可观察现象有逻辑联系的东西才存在,与断言惟人类看得见的东西才存在是同等荒谬的。从纯理性的角度看,我们不能认为科学所描述的宇宙就是仅有的宇宙。维特根斯坦曾很重视区分什么是“可以言说的”与什么是“不可言说的”。在他看来,可以言说的“真命题之总和便是自然科学之全体( the whole of natural
science )”(注: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 -
Philosophicus 〔 M 〕.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97.P.25.)。 他认为“对不可言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注: LudwigWittgenstein,Tractatus Logico - Philosophicus 〔M〕.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97.P.74.), 并说正确的哲学方法就是除了可以言说的东西而外,什么也别说,而可以言说的东西就是自然科学命题,所以哲学所应说的恰是与哲学无任何关系的东西(注:Ludwig Wittgenstein,Tractatus Logico - Philosophicus 〔M〕.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1997.P.73—74.)。这显然是个矛盾。 但维特根斯坦能体认到:“确实存在不可言说的东西。它们自己显现自己。它们是神秘的”(注: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
- Philosophicus 〔M〕.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97.P.73.)。而且对他来说,“这种神秘的感觉具有最高的重要性”(注:〔美〕M.K.穆尼茨著,吴牟人等译,当代分析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257.)。可见,在维特根斯坦看来, 能在我们的精神过程中触及“神秘的”、“不可言说的”东西是具有最高重要性的事情。科学诚然把“可以言说的东西”讲得最清楚,但科学并未触及“具有最高重要性”的东西。我们也不能认为,只有可以言说的东西才存在,不可言说的东西皆不存在。在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引申:断言惟“可以言说的东西”才存在,“不可言说的东西”一概不存在,也与断言只有人类看得见的东西才存在同等荒谬。
哲学的任务就在于从现实出发去理解无限存在。哲学的使命不是跟着科学去说可以言说的东西,而是努力在可以言说的东西的基础上,努力用语言形式去理解不可言说的、神秘的东西。若能如此理解哲学的使命,就不会陷入维特根斯坦的矛盾境地。依笔者之见,对人类生存具有“最高重要性”的、“神秘的东西”便是无限存在。人类必须通过哲学而达到对无限存在的理解,其生存才有了根。人类意识仅当达到对无限存在的理解时,才会对世界有所敬畏,从而才既不致因过分张狂而自毁,又不致因陷入虚无而自卑。不甘于做科学之附庸的哲学,可以用理性论证的方式达到对无限存在的理解,从而达到人类安然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大智慧。
二、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
智慧关乎价值合理性,知识则只关乎工具合理性。
价值合理性植根于人们的宗教或哲学信仰,是关于人生根本选择和文明根本走向的合理性。就个人选择而言,价值合理性涉及视何种价值为最高价值,即视何物为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一个人一旦认定某种价值是最值得重视的,他的生活就是以对这种价值的追求为根本意义。价值合理性植根于信仰,一个信仰坚定的人可以为自己所认定的最高价值献出一切,包括他自己的生命。例如,谭嗣同在“戊戌维新”失败后能逃而不逃,自愿为中国的变法图强献出生命,就与他的信仰和价值观密切相关。就一个民族或一种文明而言,价值合理性关系到民族或文明的根本发展方向,有大智慧的人,其人生抉择才具有价值合理性;在有大智慧的人能较有效地影响公众或有决策权的国度,其文明发展才会具有价值合理性。
工具合理性则指为实现一个明确的目的而对方法、手段的设计和选择。有了一个明确的目的,对实现该目的的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或手段的设计、算计和选择,便是工具合理性的典型表现。一个人有足够多的知识,才能保证其行动的工具合理性。科学技术是人类行为工具合理性的保障。现代人对科技的崇拜和重视,正表明现代人极重视工具合理性。
在极重工具合理性而不重价值合理性的现代社会,金钱已成为万能的“一般等价物”或价值标志。但用金钱只能买到工具和方法(如种种工程设计和电脑软件),而决不可能买到圆满人生必不可少的精神价值。
三、道德与理智
苏格拉底曾说,“知识就是德性”,但他那时的知识概念不同于今天的知识概念。那时,知识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分化为如此繁多的专门化分支,知识都总括在哲学的门下,知识是关于人生的综合性信念(注:〔美〕梯利著,葛力译.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50,58.)。可见,那时的知识就是智慧。苏格拉底所说的知识, 主要是一种指导人生的艺术,是实践性的知识,亦即对人生、社会和世界的正确理解和对道德的正确理解(注:〔美〕梯利著,葛力译.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50,58.)。正因为如此,知识才是德性。但从苏格拉底的“知识就是德性”,到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再到今天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就是金钱”,知识越来越为科学技术所专用,越来越成为纯粹工具合理性的化身,越来越与人的德性和品格相脱离,即知识越来越成为纯粹理智性的算计和操作性的工程技术。
培根被恩格斯称为“近代科学的始祖”,其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特征。经过文艺复兴之后,现代科学已悄然兴起。科学以把握具体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或事物内在的因果联系为己任。把握了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即有了知识),就可以干预、控制事物的变化过程,使事物以有利于人类的方式演变。有了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就可以开采自然物,利用自然物(能源和原料),制造出种种物品,就可控制和征服自然。所以,“知识就是力量”。求知就是追求力量,而不是追求德性。自培根以后,在“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口号的鼓舞下,西方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今天的科技正加速进步。
到了20世纪90年代,“知识经济时代”业已来临。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知识产权的界定,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知识就是金钱”。如果说牛顿时代的科学家们把“科学当作一种天职”,那么,今天的知识发现者和技术创新者们都很自觉地服务于商业。他们再没有牛顿那样的追求真理的执着,也没有爱因斯坦那种献身于纯科学的宗教式的热忱,追逐金钱就是他们创新的心理动因。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与德性不仅已完全脱离,而且可能成反比。在苏格拉底看来,有知识的人必然有德性,但今天,有知识的人完全可以没有德性。
可见,由“知识就是德性”,到“知识就是力量”,再到“知识就是金钱”,代表着人类文明演变的一条线索,这是由重智慧、重德性到重知识、重理智的演变线索。德性日益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而理智日益被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今天,你若说某人没有德性,他大抵不会气恼,但你若说他智商低,他一定会十分气恼。重智轻德是整个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在现代世界,几乎人人都在用智逐利。
四、关于知识与智慧矛盾的哲学反思
本文无意于“制造”新的二元对立。相反,笔者认为智慧与知识、哲学与科学、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以及德性与理智的区分都只是相对的,而且每一对范畴彼此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智慧以知识为基础,无知识的人无从有智慧,但智慧又超越了知识。哲学必须认真吸取科学所取得的成果,哲学所表述的世界观不能完全置科学所描述的世界图景于不顾。但哲学决不应该做科学的附庸,不应该只跟着科学去说“可以言说的东西”。哲学对人生与人类文明有着科学所无法取代的启发与指导作用。今天,许多人都在谈论“全球化”趋势,人类在经济活动方面的全球合作已经很有成效,人类文明的演化越来越具有整体性。在人类文明越来越具有整体性的时代,要不要一种真正高明的思想的指导,这是当代人必须思考的问题。自由主义主张只谋求政治层面的统一,而在根本信仰方面应任由不同个人自由选择(注: Cf. John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6.)。自由主义反对思想精英对社会生活的领导,认为不同个人在利己心驱使下的努力,经市场协调即可推动社会的进步(注:〔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5.)。故文化精英和思想精英们不应用自己的思想去过分干预大众的价值取向。社会可自然而然地达到和谐,实现进步。这种思想在破除封建专制、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曾起过巨大的解放作用。但时至今日,我们应反思它的局限性,反思它对人类文明的误导。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穿衣吃饭问题才是人类最重要的事情。人没有饭吃会饿死,冬天没有衣服穿会冻死,这是个硬道理。有思想和远见卓识的人也许生活质量高一些,因为未得到满足的苏格拉底要比得到满足的猪快乐(注:Cf.Archie J.Bahm.Why Be Moral?〔M〕.World Books,Albuquerque,1992.65.)。 但没有多少人认为思想和远见卓识是人生的必要条件,简言之,没有饭吃人会死,但没有思想和远见卓识人不会死。还有人把这一观点加以引申:思想和远见卓识不仅不是个人生活的必要条件,也不是人类文明的必要条件。即一个民族只要有高水平的经济和科技,就是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不必有高水平的哲学、高水平的思想。说“没有哲学的民族就如没有神龛的教堂”,只是哲学家的自吹自擂。但今天我们若认真反思人类文明近500年来的演化历程, 就当领悟:哲学家不是自吹自擂,人类文明不能没有大智慧的指引。
与古人对比,再反思今日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全球性危机的根源,我们应当认识到:现代人知识太多而智慧太少,或说现代人有太多的“小聪明”,而没有什么大智慧。现代人把宗教、哲学都挤到边缘,惟经济和科技居于中心;现代人只重工具合理性而不重价值合理性;现代人只重智巧,只工于算计、巧于投机,而不重德性,不重品格。人类在现代科技知识的武装之下,在全球化市场的协调之下,拥有巨大的整体力量。这是空前强大的整体力量,它足以彻底破坏地球的生态平衡,足以使地球变得不可居住。但人类文明缺乏真正远见卓识的指引,人类没有正确指导自己如何使用强大力量的智慧。正如阿尔·戈尔所描述的,人类已僭取了自然和上帝的权力,但又没有上帝那样的智慧(注:Al Gore.Earth in the Balance,Ecology and the Human Spirit〔M 〕 .A Plume Book,New York,1993.240.)。这使人类的处境特别危险,就像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拿起一把子弹上了膛的手枪。
人类文明虽已呈现出整体化趋势,但真正有效的全球性合作只是经济领域的合作。全球化的、整体性的人类文明需要真正远见卓识的指引,需要大智慧的指引。
至此,我们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智慧与思想即使不是个人生存的必要条件,也是确保人类文明安然生存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之所以这样,就因为人类知识发展已使人类强大到极易自毁的程度。在资本主义文明框架内,人类“跟着感觉走”,“自然而然”地发现和积累了许多知识,人类运用自己的知识能控制和征服许多自然物。这便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宣称人即上帝,人类可征服自然,有科技之剑在手,人类将无往而不胜。殊不知人类所能控制和征服的只是有限的自然物,而不是无限的自然。但由于现代人知识有余,智慧不足,只有发达的科技,缺乏高明的哲学,所以在他们的眼中,只有自然物而没有自然,或说他们把有限的自然物误当作自然。他们因为人类成功地征服了一些自然物,便以为人类可以征服自然(注:关于自然与自然物的区分,详见拙文.论自然的主体性和人的主体性〔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2).)。正是这种错觉才使人类在生态危机中愈陷愈深。 人类已不能再一味“跟着感觉走”了,人类文明急需思想和智慧的指引。没有饭吃人会死,没有大智慧人类会灭亡。经由追求大智慧的哲学,我们才能理解那“不可言说的”、“神秘的”、无限的大自然,才能破除“人即上帝”的迷信,才能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眼界。仅当人类放弃了“人即上帝”的狂妄信念之后,才可能脚踏实地地行走在大地上;仅当人类体认到无限大自然的奥妙无穷(不是把握了大自然的一切奥秘),才会对超越于人类之上的存在有所敬畏;也仅当人类对无限存在有所敬畏时,人类生存才有其根。有根的生存才是安全的生存。
〔收稿日期〕2000—0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