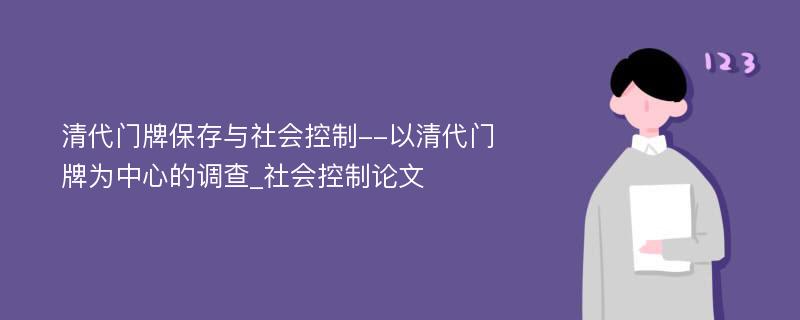
门牌保甲与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以清代门牌原件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门牌论文,清代论文,保甲论文,原件论文,基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有很多微观的要素在士民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充当了他们认知自我与社会的标尺和参照物。门牌①就是微观要素之一,在宋元以来的基层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现存史籍中,关于宋代之前门牌的记载语焉不详,已经很难还原出当时门牌的具体形制。但自宋元以来,作为控制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出现的门牌,不仅在史书中留下了相当丰富的记载,而且还保留下了相当多的实物原件。这些记载和原件为探讨宋元以来门牌功能的演变,特别是清代门牌保甲制度的确立及其对基层社会的影响,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近年来,《徽州千年契约文书》②、《田藏契约文书粹编》③以及《古代乡约及乡治法律文献十种》④等文书史料的陆续结集出版,为通过门牌原件研究清代门牌保甲制度提供了便利。学者们已经关注到了门牌原件,并尝试通过这些文书去解读晚清(特别是太平天国时期)和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⑤但学界对于清代门牌保甲制度的发展脉络及其所体现的基层社会控制理念的梳理仍不够系统,留下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本文将结合《大清会典事例》、《户部则例》等官方史料及《福惠全书》、《保甲书》等政书文献,通过解读《田藏契约文书粹编》中所刊布的清代门牌原件,来探讨清代门牌保甲制度与基层社会控制的相关问题。
一、清代门牌保甲制度的确立与完善
1.北宋以来保甲制度的发展
在清代以前,保甲制度的发展实际上经历了由“里甲制”向“牌甲制”的转变,而具有稽查人户功能的门牌在这一制度转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想要了解清代门牌保甲制度的起源,必须从北宋以来保甲制度的逐步推行开始考察。
“保甲”作为一种制度的名称正式出现于北宋⑥。王安石在变法中有实施“保甲法”的规定,主要希望以此寓兵于农,强兵减费,同时也有加强地方社会控制的考虑。当时的具体规定是:“十家为保,有保长。五十家为大保,有大保长。十大保为都保,有都保正、副。……逃移、死绝,同保不及五家,并他保。有自外人保者,收为同保,户数足则附之,俟及十家,则别为保。置牌以书其户数、姓名。”保甲法以人户为基本单位,平日“授之弓弩,教之战阵。每一大保,夜输五人警盗。凡告捕所获,以赏格从事。同保犯强盗、杀人、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蓄蛊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⑦通过各保间的联防,配以乡约,来强化社会控制。
虽然在北宋王安石推行的保甲法中,已经有“置牌以书其户数、姓名”的规定,但根据相关记载,当时置牌以“保”为单位,目的在于明确每保中的户数和每户中当出的丁壮名额。关于当时保牌的具体形制,史籍语焉不详,更没有关于悬挂门牌的详细记载。
目前发现最早的关于使用门牌的记载,可以在元代欧洲人马可波罗的行纪中找到。《马可波罗行纪》卷二中提到:“尚有一事须言及者,此城(杭州)市民及其他一切居民皆书其名、其妻名、其子女名、其奴婢名以及居住家内诸人之名于门上,牲畜之数并开列焉。此家若有一人死则除其名,若有一儿生则增其名,由是城中人数,大汗皆得知之。蛮子、契丹两地皆如是也。一切外国商贾之居留此种地域者,以书其名及其别号,与夫入居之月1日,暨离去之时期,大汗由是获知其境内来往之人数,此诚谨慎贤明之政也。”⑧依据马可波罗的记载似乎可以推论出,在宋元时期,以杭州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城市里已经出现了以社会控制为目的的门牌(法国学者谢和耐也引此条记载来说明宋元时期的中国城市中的户口控制⑨),但是,这只是一条孤证,目前并没有充分的史料可以佐证当时的保甲体系已经推及于每家每户的门牌上。南宋时期记载杭州情况最为详尽的《梦粱录》、《武林旧事》等著作中,也都没有与门牌相关的记载。事实上,相比保甲控制为目的的门牌制度,元朝政府更为重视的是管理户籍、赋役的里社、里甲制。⑩
明朝初期,政府建立了黄册和鱼鳞图册两种制度,并要求户部设置户贴来登记人口,来配合以征收赋税为目的的里甲制度的推行。直到明朝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及“一条鞭法”等赋税改革的推行,里甲制度才逐渐被以维护地方秩序为主要职能的保甲制取代。地方行政稽查的实际需要,促使地方官员制定出各种不同的保甲法令。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王守仁所推行的“十家牌法”。
据记载,王守仁巡抚江西时,“行十家牌法,曰:‘凡置十家牌,须先将各家门面小牌挨审的实,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为某官吏、或生员、或当差役,习某技艺,作某生理,或过某房、出赘,或有某残疾,及户籍田粮等项。俱要逐一查审的实。十家编排既定,照式造册一本,留县以备查考。及遇勾摄及差调等项,按册处分,更无躲闪脱漏,一县之事如指诸掌。’”(11)史料中还保留着当时他推行门牌保甲的详细规定,包括户主从事的职业、户内的男丁和妇女的人数、屋面的间数以及留住客人的情况,都需要在悬挂的门牌中写明。(12)
王守仁推行的“十家牌法”详细规定了人户门牌的内容以及十家牌的使用方式,正是清代所推行的“牌甲法”的雏形。此后,门牌上附加的信息越来越多,不仅仅作为区分人户的标志,更多地承担了治安、教化的作用。
2.清前期门牌保甲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行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推行保甲制度最为有力的朝代。清代前期,政府对于门牌保甲制度的推行与完善,体现出了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的高度重视。
清朝保甲制度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自顺治元年至康熙四十六年,为保甲法之草创;自康熙四十七年至乾隆二十二年,为保甲法之确立;自乾隆三十七年以后,保甲法逐渐废弛。(13)
入关以后,清朝继承了明朝的里甲制度,作为征收赋役的行政基础。后来,又逐渐采用了宋朝的保甲法和乡约制度,以加强社会控制。(14)顺治初年初行保甲,各省对于牌、甲、里、保等名称建置不一,常常混淆。(15)总体上看,当时主要推行的制度还是属于里甲制的范围,以赋役册和户籍的编审为主。作为清代保甲制度初期形式的总甲法,仅仅是防范汉人复明运动的应急措施。可以说,这一时段里甲制度与保甲制度同时并行,保甲制度仅仅作为里甲制度的一种辅助和补充。(16)
到了康熙四十七年,朝廷申行保甲法,从此以后清朝保甲制度开始走上正轨。历经雍正、乾隆两朝的整顿,以门牌制度作为基础的保甲体系有了全面的推行。值得注意的是,在雍正时期,由于丁银摊入地亩,赋役册的制定和编审逐渐废弛,“从此以还,言户口者,惟保甲之是赖”(17)。这表明清朝继承明制而采用的里甲制度基本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其编审户籍、核定赋役的社会功能,逐渐被并入保甲制度中。此后,保甲制度成为了清朝全力推行的地方行政制度。
乾隆二十二年,颁布上谕,详细规定了保甲的推行方法和悬挂门牌的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18)这标志着门牌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二、清代门牌保甲制度的相关规定及其基层社会控制理念
在清代的保甲体系中,保甲登记的户册称为“保甲册”,而“保甲册之基本,在于门牌”(19)。由此可见当时门牌对于保甲制度和户籍管理的重要作用。而门牌制度代替了以往的五年(或十年)编审户籍的制度,也是清代保甲制度的新变化。本部分讨论的正是在乾隆二十二年之后逐步完善、并系统推行的门牌保甲及其反映出的基层社会控制理念。
1.清代政府推行门牌制度的相关规定
通过乾隆二十二年颁布的上谕(与《户部则例》条目基本相同)以及当时官吏所作政书的记载,可以大致了解清代保甲制度着力推行时期的基本规定。
当时在全国各省州县中,以顺天府五城所属村庄及直省各州县城市乡村规定最为详细。按规定,“每户由该地方官岁给门牌,书家长姓名、生业,附注丁男名数。出注所住,入稽所来,有不遵照编挂者治罪。十户为牌,立牌长;十牌为甲,立甲长;十甲为保,立保长,限年更代,以均劳逸。”(20)这是推行门牌制度的官方法令。
关于门牌与循环册如何使用,在《钦定大清会典》等官方文书中记载并不详细。但清人叶佩荪在《保甲事宜稿》中对配合门牌保甲使用的循环册进行了十分详细的介绍。其“缮造之法”为:“期于某日,里长同所举甲长至县,该县当堂发给空白循环册二百页,空白门牌一百张,俱交甲长收领,谕令持归各里。按一甲百户中分作每十家一牌,各举晓事牌长一人,每牌长交与空白册二十页,门牌十张,令其将本牌人户姓名、丁口、年岁等项于空白册牌内详悉填注。倘有隐匿遗漏,惟甲牌长是问。”填好各项内容后,牌长将册牌汇交甲长,甲长合十牌之册挨次分订循环二本,再由里长携带这些牌册至县衙交给知县,知县则将循册存署,环册及门牌星夜用印毕。“次日,合集里长,当堂将环册及门牌交里长带回分交甲长,令甲长以门牌交牌长发各户,用木板悬挂。环册存于甲长处,以便改注倒换。”(21)当时地方政府对门牌与循环册施行的具体规定,由此可窥一斑。
关于牌长(头)所管理的事务。清人黄六鸿在《福惠全书》中讨论了保甲稽查的方式,按规定每十家长每日准备好稽查簿册,日暮执册挨户清点人数,询问家内情况,如:户主有无外出、有无外人留宿等。“若连宿不去,或常有人往来,语音不对、面生可疑,即细加盘诘,并讯邻佑,不能明晰,则拘留其人,报知保正。”(22)而《刑部条例》则规定:“牌头所管内,有为盗之人,虽不知情而失察,坐以不应轻律,笞四十。甲长、保正递减科罪。”(23)由此类记载,即可知当时法律规定对于牌长等地方管理人员要求相当严格。
2.清代门牌的基本形制
门牌的基本形制在清人黄六鸿所著的《福惠全书》中有详细的记载,除此以外,清人王凤生《越中从政录·保甲事宜》(24)和《田藏契约文书粹编》中还收录了当时通行的门牌样式。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清朝门牌制度的基本情况:
首先,印发的门牌名称基本上使用“烟户门牌”或“某(州)县门牌”的字样。由于烟户(25)是清代各类人户的统称,所以“烟户门牌”也成为最主要的门牌名称。
其次,门牌上都需要写明人户的情况,特别强调户主的个人情况及人口数量。门牌上需要写明户主所处地区、所属保甲(如《田藏契约文书粹编》所收录“张大舍烟户门牌”中所记录的“江苏苏州府昭文县东二场廿七都廿二啚”)、户主年龄以及所从事的职业(所营生理),还要写明本户内不同年龄的人口(分为男丁、妇女、幼童、幼女等)、亲戚,有的门牌还需要详细写明户主的相貌(如“身”、“面”、“鬚”等待填项)。与以往里甲制中的赋役册不同,门牌所登记的内容不再以“家”或“户”作为统计对象,而是以“人”作为统计对象(26)。这与保甲、里甲制度的发展及摊丁入亩的情况有关。
第三,有的门牌后还附有“民间易犯严例”等法令条文。这些法令条文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除了与宋朝以来流行的乡约有着类似的教化功能外,还具有进一步的警诫意味。通过“张大舍烟户门牌”等文本内容,可以探讨不同时期政府在社会控制中的规定和措施。
此外,配合门牌使用的两种工具也需要加以说明。
梨木板。在《福惠全书》卷二十一所列“烟户门牌”样式的旁边,黄六鸿注明:“用梨木板将前示谕,并后年月、一行保长等一定字样刊刻端楷,用坚白棉纸印刷明白,照格将本户同居丁口,填注整齐,该甲保查对无差,汇送印发。”(27)又叶佩荪《保甲事宜稿》中提到,“令甲长以门牌交牌长发各户,用木板悬挂。”(28)叶世倬《清查保甲说》提到,“凡门牌须用板实贴悬挂门首,不过欲使一户中同食同处之人可以一目了然。”(29)王凤生也提到,“甲长将门牌率同牌长分给各户,用木板裱糊,悬挂门首。”(30)可见当时一般人户按规定需要将门牌填写明确后用木牌裱糊悬挂于门首。但是,据瞿同祖推论,“这些门牌常常只能在州县官衙所在治城住户门上才能看到”(31)。依此说法,当时的政府法令规定与现实运作还是存在着很大差别的。
木戳。在《越中从政录·保甲事宜》中“门牌”样式之后,王凤生注明“另刻一木戳,写‘保甲一切牌册纸张俱系本县捐给,倘有书役、地保借端需索分文,立挐重究’字样,用红色印盖于首二行之下。其零户用木戳刻‘双身零户’四大字,另户用木戳刻‘另户’二大字,俱用红印色盖于该户门牌之首以示区别。”所谓“零户”是指畸零之户,而“另户”则主要指官府为区别贱民、曾经犯罪的人户(还包括寄居、鳏寡的“只身另户”)与普通人户而专设的特殊人户。(32)但在现存的门牌原件中,并未发现此类木戳的印记,可能是此种规定是地方施行的法令。
3.从门牌原件看清代的基层社会控制理念
《田藏契约文书粹编》收录了多件清代门牌原件的图片,其中最为详细的是“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张大舍烟户门牌”(33)。这份门牌不仅具备了清代门牌所共有的基本内容,而且附带的一份“民间易犯严例”,有15条详细规定。结合这份门牌原件文本进行分析,可以了解清代门牌在基层社会控制体系中的作用和意义。
首先,通过悬挂门牌,社会各阶层对于所属群体的不同地位有了认知。
悬挂门牌可能是清代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但从社会控制层面看,门牌的具体规定体现着政府对不同人群的定义。例如:门牌中需要填写的“生理”一项,就是政府考察人户所属阶层的重要依据。这种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区别,也对不同的人群产生社会暗示,进而影响着他们对自我形象的认知。(34)
一方面,地方士绅阶层在悬挂门牌方面拥有特权,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群体认同。在清代的门牌保甲制度中,乡绅阶层的特权是值得重视的。(35)在《福惠全书》中,黄六鸿提到了地方士绅的两点特权:一、“凡十家长、保正长俱选之庶民,不及青衿、衙役,以青衿有妨肄业,衙役善作奸也。”(36)即因为举业的关系,免除了地方士子应服差役;二、“其乡绅、举贡监、文武生员在本甲居住者,不必编入十家之内,以不便悬门牌。令十甲长稽查,惟将一户系其乡绅某举贡监衿,开明姓讳、籍贯、官职,附编本甲十家之后,城乡俱同。”(37)此项规定表明,虽然政府有“绅衿之家,与齐民一体编列”(38)的法令,但是有些地方还是免除了地方士绅悬挂门牌的义务,以明确其与普通人户的区别。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地方士绅的身份介于政府管理者与普通民众之间。以方大湜等清代官吏的文献记载,(39)结合萧一山、张哲郎对乡约制度的发展以及地方士绅参与城乡自治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地方士绅阶层对于自我形象的认知。
另一方面,门牌制度的规定中也反映出普通民众与特殊人户的区别和隔阂。在《福惠全书》、《保甲书》等政书中,不仅有关于地方士绅特权的记载,还有很多关于贱户、另户及流丐的记载。如王凤生记载:“至于该坊之贼盗、窝家、娼赌、匪徒等户,则令甲邻自相排挤,剔为另户。各坊另立一册,交地保收管,季终随同乡耆赴县倒换。”又云:“查验土著乞丐,酌令数坊设一丐头,将所管乞丐造册存查,各在各坊乞讨,勿许越境。其外邑新来之丐,饬令丐头随时举报,官给口粮,即行遞籍。凡此皆不列入保甲之内。”(40)上文所提到的用以区别“另户”的木戳,也有与此相同的用意。由此可见,在清代地方行政管理过程中,地方政府不仅通过不同的保甲册区别人户类型,也通过“令甲邻自相排挤”及“饬令(土著)丐头随时举报(流丐)”等种种方式,试图人为地强化不同社会群体的自我认同意识,并借此来控制社会流动,剔除城乡中不稳定的因素,维持社会正常的秩序。
其次,门牌与基层社会控制的实际推行密切相关。
作为清代保甲体系的基础,门牌本身所包含的意义更多地指向了社会控制。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门牌的内容逐渐增多,其负载的社会功能也越来越复杂。其中,除了保甲本身“相保相救”的宗旨之外,教化与申诫也是门牌重要的社会功能。
一方面,门牌分担了乡约的一部分教化功能。乡约制度始盛于宋,其立意可归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后来,南宋朱熹、明代方孝孺、王守仁、吕坤等对乡约制度都有过修改和补充。(41)特别是王守仁在平定叛乱和抚治江西时,不仅大力推广乡约制,而且尝试推行“十家牌法”与之配合。乡约制度本为团结和约束地方民众,实际上是一种追求以士绅为首的地方自治的努力。其中“德业相劝”的主要目的在于教化,而“过失相规”则不仅有教化督导的意味,还隐含着申诫的深层含义。通过“张大舍烟户门牌”中“窝赌窝娼”、“聚众不法”等条目对邻右行为的相关规定,可以了解清代门牌实际分担了乡约一部分的教化功能。
另一方面,门牌中附加的内容反映了不同时期基层政府社会控制的指向。“张大舍烟户门牌”上附有详细的“民间易犯严例”,按类型包括:窝藏类、造假私铸类、妖言邪教类、闹事扰民类、犯奸类、教唆类、私藏禁书类以及私宰耕牛罪等。比对不同时期门牌附加信息的区别,研究者可以进一步了解清代不同时期基层社会控制的重点。例如:由其中“妄立教民,□□吃素、夜聚晓散军民人等,不问来历窝藏接引者充军,里长人等一并治罪,被惑被骗之人,亦分别杖徒”一条,可知在嘉庆二十二年左右,被目为“吃菜事魔”的白莲教叛乱虽然已被镇压下去,但在广阔的基层社会中,民间秘密宗教、结社仍然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政府需要时刻防范。(42)
此外,门牌原件还为研究清代地方宗族、财产继承、社会性别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史料。
在“张大舍烟户门牌”的户主情况一栏之后,有关于家中男丁及幼童的统计。后面的“同居异姓”一栏,是针对暂居家中的朋友、亲戚(例如女婿、外甥等)而设置的。通过一张详细填注的门牌,邻里可以一目了然地了解到该人户的家庭构成和亲属关系。在清代里甲制和赋役管理衰落的背景下,这种公之于众的门牌能够提供户籍的基本情况。这一方面是为了方便政府的赋役统计,另一方面也是为人户的继承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关于门牌中反映出来的性别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行政统计中,男女性别的区分是非常明确的。很多情况下,妇女和童幼都不算在正式统计之内。在《户部则例》关于门牌制度的记载中,笔者也发现了这种现象。在这份与乾隆二十二年诏谕内容大致相同的记载中,提到顺天府五城所属村庄“由该管地方官岁给门牌,书家长姓名、生业,附注男丁名数”,下面有双行夹注写明“不及妇女”(43)。虽然在现在所见的门牌中基本都有记载家庭内妇女人数的栏目,但是,政策条文方面的对于妇女的不同规定,仍然值得研究者重视。
在“张大舍烟户门牌”的“民间易犯严例”内容中,还有“强奸轮奸”、“抢拐妇女”两条,实际上是对妇女权益的保护性法令。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关于逼迫守志孀妇再嫁行为的处理规定,是研究该时期政府对守节行为态度的直接资料。(44)
三、清中后期门牌保甲制度的衰变
1.清代中期门牌制度的实际推行情况
清代的门牌制度旨在完善地方保甲体系,加强社会控制。但是,根据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行政命令实施的通常情况,一种法令的颁布与实施过程中的具体运作,实际上会有很大的差别,而门牌制度在实际运作中的情况也是如此。通过清代中期政书文献及门牌原件中反映的情况,可以大致了解当时门牌制度的实际推行情况。
首先,清代门牌的基本推行范围、时间及影响。
通过《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及《户部则例》可以大致了解门牌制度在清代的推行范围。雍正十一年,门牌制即在福建推行。乾隆十一年,督令“直省督抚将现行保甲门牌册籍,实力稽查”(45)。到了乾隆二十二年,颁布上谕,正式在顺天府五城及直省各州县中推行。此后,政府陆续颁布了有关旗民、屯居汉军旗人、客民、寺观、外来流丐以及山居棚民等各类人户的不同规定,并针对云南、贵州、吉林、广东等沿边省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从地区范围上看,除新疆、西藏等地区情况不明外,门牌基本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从时间范围上看,从雍正时期开始有系统的门牌制度记载,直至清末光绪时期,门牌制度仍在地方推行。《田藏契约文书粹编》所收录的门牌原件图片中包括从清雍正到光绪各朝的门牌,其所属省份也涉及今天山东、山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可以作为佐证。
虽然有证据表明,在全国的大多数地区曾经推行过门牌保甲制度。但是,研究者仍需要审慎地讨论门牌制度对清代实际行政运作的影响。正如瞿同祖、萧公权等学者对保甲制度的考察表明,清代地方的保甲制度并未真正成为一项严格执行的制度。在咸丰、同治时期,太平天国运动的威胁曾经迫使曾国藩等清朝大员重视保甲,严厉推行,当时的保甲制只是临时服务于政府平定叛乱和加强治安的目的,使叛乱者及其余党无处容身。(46)同样,门牌制度的情况也与此相似,虽然律令和门牌的烟户条例里有着种种严格的规定,但是实际上可能仅仅在有限的地域(如瞿氏所提到的“州县官衙所在治城”等)、有限的时间(如乾隆二十二年前后、太平天国叛乱前后),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其次,门牌制度下出现的需索与舞弊情况。
在清代,胥吏的舞弊现象是令地方循吏们颇感棘手的事情。瞿同祖曾在《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地方政府与胥吏间复杂的关系。门牌制度是通行于地方、关系民生的一项重要制度。这一制度的推行,也很难摆脱胥吏(特别是书吏)的影响。方大湜曾愤慨地指出“发门牌须防需索”:“查保甲发门牌须严防需索。光绪元年,湖北鹤峰州牧某饬保正散发门牌,每张索钱一千文。阖州百姓无不怨恨本官。嗣后一切公事,无不与本官相龃龉,卒以不洽舆情上登白简。其实所索之钱者,皆系门丁、书差瓜分,本官并未染指也。因案:勒索已经不可,然尚系一人之事,一家之事,未必人人怨恨,家家怨恨。散发门牌系阖邑之事,按户勒索,则人人怨恨,家家怨恨矣!门丁、书差惟利是视,必不为本官声名计,本官奈何不自为计耶?”(47)在王凤生等人的记载中,也可以找到针对散发门牌时胥吏舞弊指定的法令。可见当时门牌制度中书吏舞弊的情况时有发生。
2.太平天国叛乱与清代后期门牌保甲制度的演变
自嘉庆以后,清代地方社会不断爆发各种规模的叛乱。继川楚教乱之后,太平天国又攻占了长江中下游的大片区域。
太平天国政权也曾经在占领区推行过门牌制度。但是,太平天国的军事化组织和地方士绅的抵制,导致太平天国的门牌制度出现了很多弊端。一方面,太平天国早期的门牌十分简陋,很多只是发给服从控制的人户的“良民证”(48),其社会控制功能并不完备;另一方面,据当时文人记载:“贼(太平军)谓有门牌者为天朝百姓,长毛遂不来打先锋之说,其实皆欺人以敛财耳。”(49)可见早期门牌难免需索的弊端;此外,太平天国推行的门牌制度在推行中也存在着地区和城乡间的差异。(50)
基层社会中的社会流动的增强和地方叛乱的频发,使得政府在加强门牌保甲的同时,积极推行团练与之相配合。自嘉庆朝镇压川楚白莲教以后,地方的团练不断增强,成为了继门牌制度之后清代保甲又一新的变化。太平天国叛乱中,八旗、绿营兵的作战能力很差,于是政府更加依仗各地方官绅兴办的团练。此后,门牌制度虽然仍旧推行,但是形制越来越简单,作用也不如推行初期。门牌保甲逐渐成为了团练制度的附庸。
到了清末民初时期,地方自治运动兴起,门牌制度与闾邻制和新县制相结合,出现了新的变化。最终,清代体制完备的门牌保甲制度在民族战争和政权交替中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视线。
结语
从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来看,从清朝入关后的社会流动控制,到中期兼备了户籍制度的功能,再到晚期逐渐成为地方团练附庸,门牌实际上反映了政府控制能力与地方自治力量间此消彼长的变化。同时,从门牌保甲制度的立意及其政策规定来看,清代地方民众的生活及邻里间的关系与朝夕悬于门首的门牌密切相关。正如同市镇上的更楼、村落中的水井和告示牌等公共设施一样,都是考察基层社会日常生活的重要参照物。
由于目前所能见到的门牌原件在数量上尚属冰山一角,因此,随着文书、实物文献的不断整理刊布和对地方乡邦文献的系统解读,对于门牌制度及其实际推行情况的研究可能会出现新的进展。以门牌等实物文献为中心考察不同时代的制度变迁,仍然是一个极具吸引力并需要继续讨论的课题。
注释:
①《中国古代生活辞典》中“门牌”一条有基本的定义:“清代用保甲法编制户口,维持治安,防止人民反抗,乾隆时更加严厉。不论城乡,每十户为一牌,立一牌头;十牌为一甲,立一甲长;十甲为一保,立一保正。其户籍曰保甲册,其基本在于门牌。每户给印信纸牌一张,上写户主姓名,丁男口数,外出注明所往,人则注其所来,月底令保正出具无事甘结,报官备查。门牌揭于每户门上,以便勾稽人口动静。”(何本方等主编:《中国古代生活辞典》,沈阳:沈阳出版社,2003年,第112页)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从性质上讲“门牌”不同于今日的地址号牌,实际上是明清时期广泛采用的一种下行公文和户籍凭证。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整理:《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
③田涛、[美]宋格文(Hugh T.Scogin,Jr.)、郑秦编著:《田藏契约文书粹编》,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④一凡藏书馆文献编委会编:《古代乡约及乡治法律文献十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⑤例如:方荣、杨兴茂:《清代公文“易知由单”和“门牌”》,《档案》1997年增刊,第37-38页;邵凤芝:《一件太平天国的门牌》,《文物春秋》2005年第6期,第70-72页;谢进如:《甲牌制下门牌制度述论(1927-1933年)》,《宿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8-11页及《闾邻制下门牌制度述论(1928-1934年)》,《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93-98页。此外,梁治平在为《田藏契约文书粹编》所作的书评中也敏锐地指出了其中收录的大量门牌文书在考察清代地方社会方面的重要意义(《故纸中的法律与社会》,《北大法律评论》2003年第5卷第2辑,第551-555页)。
⑥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民国丛书》第四编第2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115页。
⑦[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37“王安石变法”,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46页。
⑧[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第二卷“蛮子国都行在城”,冯承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⑨[法]谢和耐(Jacques Gernet):《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刘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⑩江士杰:《里甲制度考略》,“民国丛书”第四编第23册,第四章。
(11)[清]陆曾禹:《严保甲》,[清]徐栋辑:《保甲书》卷4,《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5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48页。
(12)详见[明]王守仁撰、陈龙正辑:《十家牌法》,一凡藏书馆文献编委会编:《古代乡约及乡治法律文献十种》第一册,第129-161页。
(13)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09页。
(14)张哲郎:《乡遂遗规——村社的结构》,杜正胜主编:《吾土与吾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第191-226页。
(15)《清史稿·食货一》记载“世祖入关,有编置户口牌甲之令”。
(16)关于当时里甲制与保甲制的区别,萧一山先生曾经围绕着两种户籍的不同进行讨论,而张哲郎则认为二者是清代并行的两种制度。萧公权也从法律、功能等方面讨论里甲与保甲系统的差异(参见Kung-Chuan Hsiao,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pp.33-36)。
(17)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371页。
(18)[清]崑冈等修:《钦定大清会典》卷17,《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94册,第164-165页。
(19)[清]崑冈等修:《钦定大清会典》卷17,第164-165页。
(20)[清]崑冈等修:《钦定大清会典》卷17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58。另:清人徐栋所编《保甲书》卷1中所收录的《户部则例》中的规定也基本与此相同。
(21)[清]叶佩荪:《保甲事宜稿》,《保甲书》卷2,第70页。
(22)[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卷21,《四库未收书辑刊》第3辑第1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45页。
(23)[清]徐栋辑:《刑部条例》,《保甲书》卷1,第67页。
(24)[清]王凤生:《越中从政录·保甲事宜》,《保甲书》卷2,第88页。
(25)“烟户”是清代对人户的统称。《钦定大清会典》卷17中提到:“各省诸色人户,有司察其数而岁报于部,日烟户。”其下分为民户、军户、灶户、渔户、回户、番户、羌户、苗户、黎户、夷户等。而所谓的“烟户门牌”即是政府颁发给一股人户的门牌。
(26)[清]叶世倬《清查保甲说》中有“门牌所重,在稽查一户之人”的说法,见《保甲书》卷2,第75页。
(27)[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卷21《烟户门牌式》,第244页。
(28)[清]叶佩荪:《保甲事宜稿》,第70页。
(29)[清]叶世倬:《清查保甲说》,第74页。
(30)[清]王凤生:《越中从政录·保甲事宜》,第79页。
(31)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56页。
(32)[清]王凤生:《越中从政录·保甲事宜》,第82页。
(33)田涛等编著:《田藏契约文书粹编》,第44页图,第41-42页释文。
(34)(美)E·A·罗斯:《社会控制》,秦志勇、毛永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12-125页。
(35)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第257页。
(36)[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卷21,第243页。
(37)[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卷21,第243页。
(38)《清史稿·食货一》。
(39)[清]方大湜:《平平言》卷4,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十三年常德府署刊本。
(40)[清]王凤生:《越中从政录·保甲事宜》,第78页。
(41)关于乡约的论述,可参考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三章及张哲郎《乡遂遗规——村社的结构》。
(42)关于白莲教及其叛乱的研究,可以参考[美]韩书瑞(Susan Naquin):《中华帝国后期白莲教的传播》(《清史译丛》第4辑,陈仲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一文,以及[美]孔飞力(Philip A.Kuhn):《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43)《户部则例》,《保甲书》卷1,第63页。
(44)关于清代孀妇守节问题的研究,可以参考[美]曼素恩(Susan Mann):《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定宜庄、颜宜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二章。
(45)[清]崑冈等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58。
(46)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第254页。
(47)[清]方大湜:《平平言》卷4。
(48)太平天国早期门牌式样可参考罗尔纲所辑录的门牌原件,见罗尔纲:《太平天国文物图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五章“社会组织”的甲部“门牌”。
(49)[清]沈梓:《避寇日记》卷1,“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六日”条,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值得注意的是,在《简辑》中《金陵纪事》、《皖樵纪实》、《自怡日记》等当时江南地区文人的笔记中,都有太平军借门牌索要钱财的记载。
(50)罗尔纲:《太平天国文物图释》第五章“社会组织”的甲部“门牌”;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简氏猛进书屋,1958年,第八篇“乡治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