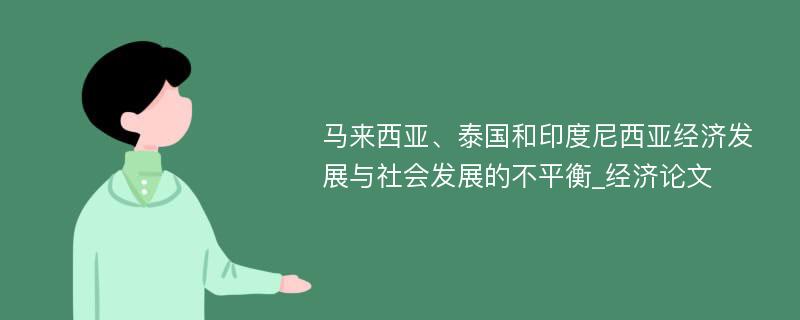
马、泰、印尼三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失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尼论文,社会发展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发展指标涉及人口、教育、福利、卫生、安全等诸多方面,它实质上反映的是经济增长的成果分配状况。因此,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关系。由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历来被看作是相互制约、相互矛盾的,因此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赶超世界先进国家,加速工业化战略的实现,在处理二者关系时便过于偏向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公平,出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现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三国即是如此。
一、人口素质的改善及生活质量的提高与经济发展速度不同步
继“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之后,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三国也在经济上取得了快速发展。1980-1990年,三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5.5%,超过世界经济的增长率3.2%,成为充满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的新兴国家。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三国的社会发展也取得一定的成就。如在人口的生活质量方面,以国际上常采用的生活质量指数体系的三项指标考察,三国的婴儿死亡率不断下降,平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均有很大的提高。然而,如果我们将三国的社会发展成就与其经济增长速度联系起来考察,不难发现,三国的社会发展明显呈滞后状态。
首先,我们从三国的人均GDP和HDI(Hnman Development Index,人类发展指标,包括预期寿命、教育状况和人均GDP)得分在世界上的排名来考察。通过对世界上174个国家人均GDP和HDI得分排名,结果发现三国的HDI得分排名均落后于其人均GDP的排名。如泰国的人均GDP排名第55,而其HDI得分排名为58;马来西亚人均GDP排名45位,HDI得分排名59位;印尼人均GDP排名99位,HDI得分排名为104位。[1](P61)HDI得分排名的落后说明三国人口的生活质量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同步的,即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落后于其经济发展速度。
表1 三国政府的各项开支占总开支的百分比[4]
国防和经济卫生和教育 住房、舒适、社会安全与福利
19721990
1972 1990 1972 1990
印尼49.135.48.8 10.4
0.9 1.5
马来西亚32.729.2
30.2 18.7
4.4 5.5
泰国45.839.4
23.6 26.9
7.0 5.8
(资料来源:Johannes Dragsbaek Schmidt,The challenge From South East Asia:social forces between equity and growth.In Chris Dixon and David W.Smith(eds.),Uneven Development in South East Asia,England: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1997.29.)
其次,从人口素质的改善与经济发展要求来看。尽管三国人口的识字率大为提高,初等教育基本普及,可是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仍然是比较落后的,这与其工业化发展速度极为不协调。1988年统计表明,当年泰国需要工程师和中专、大专程度的技术员7000人,而同期各院校只能培养2700人,其中特别缺乏电力、电子、电讯、交通、计算机和工业方面的工程师。泰国每10万人中只有约17名科学家和工程师。马来西亚也有类似情况。据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在20世纪90年代发布的世界国际竞争国评价报告,在参评的46个国家和地区中,马来西亚的科技开发要素世界排名居第29位,国民素质要素世界排名居第35位,二者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马来西亚从事科技开发的人员占国民总数的比例则排在倒数第2位。[2]在1997年底,马来西亚劳动市场约800万人中只有11.5%的劳工拥有大专学历,每10万人中只有40名科技人员。这种状况与马来西亚长期忽视高等教育密切相关。印尼的教育发展则更为落后。在印尼,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师资十分缺乏,如全印尼高等院校工程教师只有2000人左右,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人口素质提高缓慢致使三国缺乏大量工程技术人员、中高级管理人才和熟练工人,这与其经济发展要求远远不相适应。
造成三国人口素质与生活质量提高缓慢的原因在于三国政府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指导思想上,都将实现经济增长放在头等地位,从而忽视了教育、卫生等其它方面。如表1所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印尼、泰国在教育卫生方面的开支占总开支的百分比仅有较小的增长,而马来西亚不仅没升,反而下降了许多。三国在国防和经济方面的开支远远高于教育卫生开支。1990-1995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上中等收入国家的马来西亚和下中等收入国家的泰国、印尼,三国医疗卫生的公共开支占其GDP的百分比分别是1.4、1.4和0.7,而同期上中等收入国家和下中等收入国家医疗卫生的公共开支占GDP的百分比平均是3.3和2.5。[3](P202-203)
人口素质的提高缓慢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是显然易见的。受教育水平和科技力量的限制,三国普遍面临产业升级的困难。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这种状况显然成为三国工业化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二、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未能随经济发展而得以健全与提高
社会保障(也称社会安全)和社会福利两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界定。但不管二者概念如何界定,其基本功能是一致的,即保障国民基本生活需求和提高全体国民生活质量。社会保障是否健全、社会福利水平的高低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在马、泰、印尼三国,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发展速度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三国在国民经济的再分配中,把较少的份额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在1972-1990年的18年间,三国用于住房、舒适、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的开支,马来西亚仅增加1.1个百分点,印尼增加0.6个百分点,而泰国则下降了1.2个百分点(见表1),分别达到5.5%、1.5%和5.8%的水平,这一比例明显地低于其他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16.2%(1985年数字),也低于大多数拉美国家和南亚国家的水平。[4]在90年代,三国均制定了五年计划,政府投资较高地集中在基础设施和环境上,除了泰国,其他两个国家均未提到增加福利方面的开支。
表2 1987-1989年间三国未被社会保障制度涵盖的人口组成和比例的粗略估计
工薪者自营业者 家庭工人失业者年份
印尼 13.7
41.9 29.62.8 1988
马来西亚 24.9
22.6 12.36.0 1987
泰国 17.8
29.6 34.37.9 1988
(资料来源:Johannes Dragsbaek Schmidt,The challenge From South East Asia:social forces between equity and growth.In Chris Dixon and David W.Smith(eds.),Uneven Development in South East Asia,England: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1997.30.)
由于政府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方面投入偏低,因此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很低。如表2所示,三国中只有一部分劳动力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而且大多是政府的雇员或城市人口,广大的农村人口几乎未能享受。
三国“高增长、低福利”的政策还集中体现在劳动立法上。由于政府的导向是实现工业化战略、促进经济增长,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吸引外资,政府的一些劳动立法不是保护劳工的权益和福利,而是压低工人工资,削弱劳工组织的力量。
马来西亚于1967、1969年两次修改《劳资关系法》,工人的工作日被延长,假日被缩短,工会力量被削弱,罢工权遭限制。1971年,政府下令禁止工会领导人在政党中担任职务,禁止工会保留“政治基金”,同时进一步限制罢工权,不再要求雇主解释开除员工的理由。马来西亚从未有过关于最低工资的立法。在90年代以前,马来西亚的劳动力成本一直偏低。1986年出台的马来西亚《工业总体规划》中对本国与其他国家在半导体和电子元件中的劳动力成本及生产力作了比较。结果发现,马来西亚工人的平均报酬只有美国工人的11.7%、日本工人的19.0%、新加坡的42.0%及南韩的71.0%。但是,平均每个马来西亚工人所增加的价值却是美国平均水平的18.2%、日本的24.0%、新加坡的56%及南韩的31%。[5]在印尼,政府也没有强制实行最低工资标准。一个女工每周工作60小时,每月仅得80美元的工资,这几乎只是一双鞋的价值。在泰国,工会尽管很普遍,但时常遭到政府的限制和取缔。1990年,泰国有700个工会,拥有30万个会员,但在1991年遭国家取消后,仅存645个工会和16万个会员。特别是在相当多的日资企业中,从1985年起,这里实行了一系列削弱劳工组织的措施,如开除工会领袖,设立亲公司的第二工会,雇佣临时工人破坏罢工,用更坏的条件来回应工会的工资要求等。[6]工会的削弱使得劳工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福利无从提高。由此可见,由于政府的劳动立法的限制,尽管三国经济出现快速发展,但工人的权益和福利并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提高。在1960-1990年间,三国经济发展速度平均达到5%以上,而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只是GNP增长速度的一半。
社会保障是否健全、社会福利的高低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开支一直被认为是非生产性的,与市场经济原则相对立的,而对它的经济意义少有认识。实际上,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只有劳动者收入、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水平得到提高,他们才有可能成为具有一定购买力的消费者,而内需旺盛能够弥补以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脆弱性,使之尽量减少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动荡影响。另外,建立一套保证国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系统也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定,缓解社会冲突,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20世纪90年代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三国轻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危害性。在这场危机中,三国依赖国际市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大量工人和管理者因失业陷入绝对贫困之中,社会动荡不安。
三、消除贫困的成就与经济发展速度不相协调
自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尽管马、泰、印尼三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与其经济发展速度相比,明显呈落后状态。
第一,绝对贫困的人数仍有相当大的比例,消除贫困的步伐相对缓慢。据《世界发展报告》数据表明,处于国家贫困线下的人口在马来西亚有15.5%(1989年),泰国有13.1%(1992年),印尼有15.1%(1990年);处于最低国际贫困线(每人一天一美元)下的人口在马来西亚有4.3%(1995年),印尼有7.7%(1996年),泰国小于2%(1992年)。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大部分国家相比,三国的贫困率相对较高。[3](P196-197)特别是马来西亚,90年代其人均GNP已超过3000美元,在这样一个较为富裕的国家尚存在着这样比例的绝对贫困人数,显然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协调。
第二,贫富悬殊没有得到明显改变,相对贫困现象依然严重。据印尼中央统计局资料,印尼1978年富人占全国人口的20%,却占有45.34%的国民收入,而占全国人口40%的穷人,只占.18.12%的国民收入。到1990年,占20%的富人占有40%的国民收入,而占40%的穷人占有国民收入上升至21.3%,只增加了3.1%。[7]可见在七八十年代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印尼的贫富悬殊现象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变。在泰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没有缩小贫富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根据泰国发展研究所的调查,1976-1986年,占人口20%的高收入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从49.3%上升到55.6%,而占人口20%的低收入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则从6%下降到4.5%。[8]马来西亚虽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有所缩小,但情况仍不容太乐观,1989年,马来西亚最高收入的1/5家庭与最低收入的1/5家庭的收入之比为11.7:1,大大超过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9]贫富悬殊问题一直是影响三国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造成消除贫困步伐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三国政府对“公平分配”的忽视。这在三国的一些资源大省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在马来西亚,丁加奴的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可它却是全国第二大贫困州,在1987年,其贫困率高达36%,而同年吉隆坡联邦直辖区贫困率只有5.2%。又如在印尼,1985年,人均GDP位于全国前6名的地区依次为东加里曼丹、廖内、亚齐、雅加达、南苏门答腊、伊里安查雅,可其人均月消费支出的排名却大相径庭,雅加达为全国第一,东加里曼丹排名第5,廖内第4,亚齐第6,南苏门答腊第7,伊里安查雅第22。[1](P64)由此可见,一些人均GDP较高的地区,其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并非同样较高,有些地区甚至十分贫困。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央与地方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均。人均GDP排名在前的大多是资源大省或首都附近地区,如马来西亚的丁加奴盛产石油,印尼的东加里曼丹、廖内、亚齐、伊里安查亚等地盛产石油、天然气、铜、金、木材等。自然资源的开发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可其中大头为中央政府所得,当地受益甚少。据统计,印尼中央政府控制着全国85%的油税,70%的天然税,资源丰富的亚齐每年所得拨款仅占印尼国内生产总值的2.9%,伊里安查亚占1.6%,廖内占4.7%。[10]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利益分配不公使得一些资源大省沦为贫困省,印尼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此起彼伏与此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马、泰、印尼三国在20世纪70-9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三国政府“经济增长第一”的指导思想所致。尽管这种“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公平”的政策带来了一段时间的经济快速发展,但从长远来看,这种经济增长是没有后劲的。因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真正实现工业化,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必须出现这样一批人,通过他们使引进的以科学技术为中心的原来属于外来文明的产业文明诸要素内化于本国社会,这就是掌握现代技术的技术人员,具有一定资本、事业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实业家,具有熟练能力的工人和具有购买力、作为买主而出现在市场上的消费者等等。”[11]而人口素质不高、社会福利低下和消除贫困步伐缓慢都将制约着这样一批人的出现。没有这样一批人,仅仅依靠劳动力和投资的增加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是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的。社会发展的滞后对社会稳定也是一个威胁,并最终影响经济发展的环境。因此,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兼顾社会发展。另外,发展经济本身不是一个国家的目标,而是使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一种手段。若是为了经济增长而增长,忽视了以人为中心的全面、公平的发展,显然不符合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