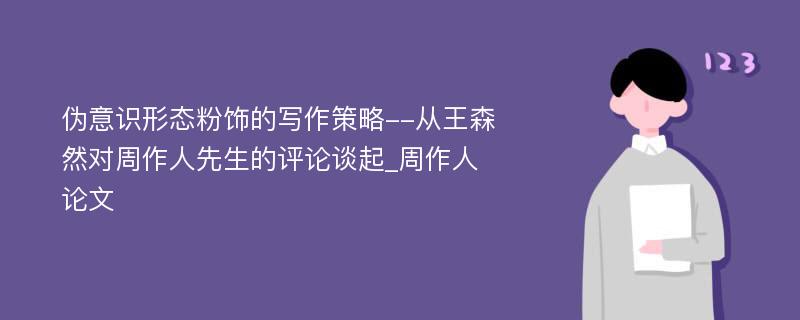
粉饰逆伪意识形态的书写策略——从王森然的《周作人先生评传》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森然论文,评传论文,意识形态论文,策略论文,周作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内最早的周作人传记
国内最早的周作人传记是王森然1944年发表于北平《华北新报》的《周作人先生评传》,该传记在5月24、26、27、28、30、31日,6月2、3、4日,分九次连载,共1万4千余字。这篇传记一直鲜为人知,更遑论细致研究,主要原因在于这篇传记从未被收入王森然的两部评传合集,还有众所周知的政治因素,等等。
从《周作人先生评传》的叙述中可明显看出本篇评传完成于沦陷时期,具体写作时间是1944年。这里需要对刊载《周作人先生评传》的《华北新报》的基本情况作一简要介绍。1943年初,为配合日本“大东亚战争”,汪伪政府向英美宣战,将沦陷区引入“战时体制”。1943年6月汪伪最高国防会议通过《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规定了战时文化宣传的基本方针,即“动员文化宣传之总力,担负大东亚战争中文化战思想战之任务”①。1943年底汪伪国民政府确立战时文化宣传体制,随即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自1944年5月起开始实行“新闻新体制”,其中就包括成立华北报道协会,以及整合华北各地多家日伪重要报纸创办《华北新报》,该报于1944年5月1日创刊,在华北各地设多家分社,社长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局长管翼贤担任,实由日本军部控制,是抗战后期华北日伪当局最重要的机关报,被称为“代表华北惟一国策的新闻纸”②。《华北新报》创刊伊始,汪伪政府、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主要政要,以及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日本驻华特命全权公使盐泽清宣等日方军政与情报部门重要官员都纷纷发来祝辞,显示出《华北新报》作为日伪思想战、宣传战阵地的显要地位。
作为《周作人先生评传》传主的周作人,在日伪政权的思想战、宣传战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在《华北新报》中的身份也非同一般。身为汪伪政府和伪华北政权中最高级的“特任级”高官的周作人,在《华北新报》创刊及华北报道协会成立伊始,即兼任《华北新报》理事与华北报道协会理事。在《华北新报》创刊号上,于第一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前任委员长王克敏的大幅题词“一新壁垒贡献战争”与汪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陈公博的祝辞等旁边,就以显著篇幅刊登了《创造新闻新体制③ 华北新报今日创刊 周作人钱稻孙管社长对谈感想》(对谈于5月2日第2期连载刊完,题为《抱定报道报国决心 积极完成华北宣传战 周作人钱稻孙管社长对谈感想》),周作人在对谈中以政府高官的权威口吻宣称,“最近中共重庆之扰乱工作及一部分人的不法营利举动,而使社会民众的生活,失去了原有的姿态,固然这是由于战争所受的影响,但是在参战下的中国人,要忍耐一时的艰苦,协力战争,并且在生活上及其他事情,须要自己来加以矫正,我以为这也就是《华北新报》所负的时代上的义务”④。这明显是为日伪“国策”献计,攻击抗日政权,号召中国民众协力日本侵略战争。
汪伪意识形态构造中的周作人形象塑造
登载在《华北新报》上的《周作人先生评传》,与国内外大多数的周作人传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落水后的周作人表示支持。在该评传中,王森然不仅充分褒扬周作人的伪职身份,而且处处显现出为新朝元老功臣塑像的自觉意识。在当时的背景下,捧扬贰臣、为其树塑金身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即便是在沦陷区,与日协力也是有悖于正常伦理观念的,同时鼓吹附逆者更会使自身名节受损。王森然对此应该十分清楚,但他又试图越过这一底线,配合新朝的意识形态工作,并以吹嘘伪职高官作为登龙之捷径。于是如何做到不露痕迹地既吹捧伪高官在新朝的崇高身份与光辉功业,不致暴露他们丧失人格、为虎作伥、替日本侵略奔走呼号的本质,同时又能实现王森然依附投靠的意图,这就成为王森然传记写作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经过长时间探索,王森然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并在《周作人先生评传》中相当成功地打造出新朝显贵周作人的“完美”形象。
当然在此之前王森然也曾有过失败的尝试,例如1941年他为新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傅增湘所撰《傅增湘先生评传》便属此类作品。这篇传记为了塑造手握重器的伪职高官傅增湘的“光辉形象”,王森然赞颂傅增湘出任伪职,“二十七年任东亚文化协会副会长,三十年改任正会长”⑤,并全文引用傅增湘自撰《藏园居士七十自述》(1941),其中傅增湘就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伪政府官员附逆落水大肆吹嘘,而王森然则高度评价傅增湘为伪政权创造的功业,甚至“私撰”六篇寿联,颂扬这位伪政府高官“合文学政治为一家”、“国赖长君掌文化”、“学问贯天人,立德立功立言,均能不朽”。⑥应该说,王森然塑造的傅增湘形象堪称忠实的写实画像,可是在沦陷区的特殊背景下,这样直接地通过表现与日协力活动来塑造伪高官形象,并且将自己的态度公然表露的做法,其效果恰与王森然的写作意图南辕北辙。因为通过这篇传记,呈现的是汉奸傅增湘的形象,王森然吹捧新朝、攀附汉奸的事实也铁案如山,《傅增湘先生评传》反倒成为不折不扣的新朝《贰臣传》,以及王森然卖身投靠的证词,惹人反感憎恶。当然这篇传记的失败,不是因为王森然不够机敏,而是他登龙之心太过急切,未能及时调整以往简单吹嘘的传记写作套路。这个失败使王森然意识到在沦陷区此种做法显然行不通了,即便他想捧扬贰臣、树塑金身,也必须改弦易张。于是他着力再拓新途,在沦陷区连续撰写并发表了大批传记,进行多方实验,最终《周作人先生评传》成为这一系列实验的集大成之作。
《周作人先生评传》探索的成功,除了王森然个人数年努力的摸索外,更直接受益于当时日伪政权主流观念潮流的影响。自日本开始谋划建立伪政权之日起,如何将与入侵者的合作进行合理化表述,并进行新的意识形态构造,成为附逆中国人的一项重要工作。构造这种意识形态较为困难,既要有为迎合日本人的侵略理论而进行的新的阐释,又要有附逆者自己较为独立的理论思考,同时还要为自身行为的正当性百般辩解,表现出为保国保种、殚精竭虑、敢于担当的崇高精神,总括而言,就是要构造一种诡辩式的话语。这种所谓“合理性”表述具有多种形态,其中为新朝的代表性人物塑像就是一种重要的形式,因此沦陷区兴起一种新的风尚,出现了关于伪政权衮衮诸公的大量访谈、传记、自述类作品,此外日本驻华各界重要人士亦皆有像传。在新朝元老们看来,国土沦丧、傀儡政权成立绝非国耻,而是另一个崭新中国的开端,他们正是开国的凌烟功臣,因此当时形象塑造工作的一个核心,便是塑造“新中华”的伟人。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伪政权对“新中华”看法有较大差异,其中作为汪伪政府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特任级”高官,始终亲附汪精卫的周作人发表的关于“新中华”的建言,与南京汪伪政权的舆论主调大亚洲主义完全一致。在包括周作人在内的汪伪政府高官们的自我表白中,他们始终坚持这样一种信念——自己绝非入侵者在政治及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傀儡或代言人,自己的人格、理想及追求是始终如一的。甚至有些人坚称自己始终如一忠于革命,是孙中山先生理想的传人,真正的革命道统与政统的正统继承者。更有甚者,还自诩是始终如一的道德家、思想家、文学家,是中华传统文明或新文化的道统、学统及文统的纯正代表。诸如此类言论正是他们建构“合理化”意识形态的重要立足点。
汪伪政府高官们的这种言说逻辑,在沦陷区颇为盛行,深刻影响舆论界的取向,特别是启发了那些愿意靠近新朝,有所谋获之辈,他们以更为巧妙的方式向新朝示好,盼望能分一杯羹,王森然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当他体察到汪伪政界“新中华”伟人形象塑造的急切心理需求,并心领神会此种形象塑造的奥妙后,便将自己的传记写作融入“新中华”伟人形象塑造的潮流中。在《周作人先生评传》中,王森然运用高超的手法,塑造了周作人新朝股肱的“完美”形象,同时又掩饰了他热衷依附投靠汪伪、参与伪政权意识形态建构的意图。
为实现这一目的,王森然一方面在周作人的道德家、思想家、文学家形象塑造上颇费笔墨,另一方面则着力打造周作人作为革命前驱的不凡身姿。该篇传记所使用的材料,皆来自1934年编集的评论合辑《周作人论》(该书主要汇集抗战前30年代周作人声誉达到顶峰时的各类评论),王森然基本上专截取该著中高度赞誉、捧扬周作人文学、思想及人生气象等的文字,即使偶尔截取批评周作人的文字,他也将此作为肯定的意见,或进行修改。在对所有材料进行有意识地重新处理、组合之后,王森然便使用这些已经发生质变的材料编著传记,力图借此完全概括周作人的思想、人格,以及理想追求。这种写作方式,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当今中国存在一个始终如一的周作人,他从进入思想、文学界始,直到成为伪政府高官,思想、人格、理想追求等都是一以贯之的,基本未发生变化,仅有略微的调整;而且评传主体以引文连缀编撰,又会造成一以贯之的周作人形象是客观的存在物的错觉。但历史上一生始终如一,并具有一以贯之思想、人格等的人物基本是不存在的,更遑论像周作人这样思想观念、人生选择不断发生变化的复杂人物。就在40年代初,周作人投身伪政权,在思想、行为等很多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可以说,从其附逆的那一刻开始,先前的那些评价大多已不再适用于他,就连沦陷区的多数文人也都无法认同,实际上当时很多严厉的批评者已明确把周作人一分为二,认为作为严肃思想者的周作人已经死去,剩下的不过是一个不知丑的老人在荒唐表演罢了。对于这些,身处沦陷区的王森然应是心知肚明,但他避而不谈周作人一生多次思想变化问题,反而将30年代的部分周作人论“去历史化”,打造并不真实的始终如一的周作人整体形象,实在是别具用心。⑦王森然这样做,就是为了说明作为伪政权高官的周作人并没有变化,他仍是那位被30年代部分中外人士所敬仰的,在学问修识、道德品格、国族关怀、人生境界等方面都令人高山仰止的知堂先生。从这样的判断出发,人们自然会得出结论:周作人在40年代的选择,并不代表其思想、行为出现断裂,而是其思想正常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以说,让世人对周作人形成如是的认识,正是王森然花气力剪贴拼凑的真实意图。
通过对以往材料的组构,一位始终如一的道德家、思想家、文学家,而且集中华传统文明与新文化的道统、学统及文统于一身的新周作人形象跃然纸上。⑧但王森然更为关注的,是如何将作为“新中华”政治明星的周作人打造成自辛亥革命以来一贯正确的革命政治家。对于周作人在“新中华”的政治活动,王森然在《出任教署督办》一节中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该节描述自“七·七”事变后,周作人从参加东亚文化协议会,担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到出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整个过程,并引述周作人回答记者关于华北教育施政方针的询问,还简要介绍了周作人在沦陷区的核心理念“中国固有的国民思想”观,王森然对于周作人这段政治经历的陈述口吻相当敬重,同时也极为尊重所提及的其他伪政府首脑,不过这部分总体上未作个人价值判断,但在其他部分,他则通过完全篡改许杰《周作人论》一段话的原意,较为明确地表达出对“新中华”高官周作人的欣赏及尊崇,“周作人先生虽然作教育督办的大官,并不是一个利禄熏心的读书人,他是一个具有清高的风度的士大夫,因此,他不得不走入这两条路了,得志则与民由之,兼善天下;不得志发牢骚,读奇书,喝苦茶,独善其身”,明显表现出这样的含义,即周作人一直以来都怀有坚实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但由于政见与当局不合,所以未有机会施展,而到了“新中华”,他的政治理想与新政府衮衮诸公完全投合,这才步入仕途,实现自己坚守多年、始终如一的光辉理想。
对于周作人的这种政治性定位,完全是战争时期才出现的,主要来自于政治明星周作人的各种自我表述,此类表述,是出于包括周作人在内的伪府高官标榜承续孙中山革命政统的需要。当然由于这种表述的虚假与诡辩本质,导致伪府高官们在做自我辩护时,总是底气不足,而且也很难将他们表述中的逻辑漏洞、事实错误等填补得天衣无缝,这就成为一块心病,我们从他们那喋喋不休的自我辩解中便能看出他们心底的虚弱。对此,已在沦陷区混迹多年的王森然自然了如指掌,于是他便力图在传记写作中解决这一技术难题,创造出独特的写作修辞术。
首先,王森然肯定周作人一贯的革命性,他借用了20年代末著名女兵作家谢冰莹(笔名碧云)对周作人的评价,国民革命的信奉者谢冰莹十分敏感地注意到周作人对于革命的态度,在“革命文学”论者及国民党人批评周作人“非革命性”的声浪中,她却着力强调周作人并不单纯是一个学者,他“始终同情革命,拥护革命”。不过由于王森然对这些历史性判断都做了“去历史化”的处理或有意改造,因此不必追究谢冰莹所说的“革命”具体所指,我们所需要了解的是,王森然笔下的周作人始终一贯的革命观念究竟指的是什么。
在《周作人先生评传》中王森然标举出周作人始终一贯的革命观是民族主义观念。民族主义观,在周作人一生的思想变迁中曾多次出现,形态亦有较大差异,但王森然所要塑造的是一个始终一贯的周作人民族主义观,对此王森然是通过描绘周作人政治生活的历程来完成的。在《周作人先生评传》中,为了构造出一条完整的周作人政治生活持续发展的脉络,王森然改造了许杰《周作人论》的一个部分,又新增添了一节,在重新改造组合过的《人的文学以后提倡民族文学》《民国十六年以后主张闭户读书》《出任教署督办》三部分中,王森然首先论及周作人的民族主义观,随后谈到他的“得志兼善天下”、“不得志独善其身”的两种人生道路的选择,最后说明由于二三十年代的社会乱局,周作人选择了独善其身,直至新朝才终于出山,最终实现他的民族主义的理想。这部分内容正是围绕着周作人始终一贯的政治见解“民族主义”这一点来构造的。当然《周作人先生评传》中引述的是许杰对1925年前后周作人的民族主义观的分析,其中许杰引用了周作人《元旦试笔》中对此观念的阐释,但周作人1925年的阐释,与其沦陷时期的观念不能等同。按,1925年周作人在《元旦试笔》中原本是这样阐释自己新的民族主义观的:“我的思想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我当初和钱玄同先生一样,最早是尊王攘夷的思想……后来读了《新民丛报》《民报》《革命军》《新广东》之类,一变而为排满(以及复古),坚持民族主义者计有十年之久,到了民国元年这才软化。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去年春间收小范围,修改为亚洲主义,及清室废号迁宫以后,遗老遗少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诡计阴谋至今未已,我于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觉得民国根基还未稳固,现在须得实事求是,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我不相信因为是国家所以当爱,如那些宗教的爱国家所提倡,但为个人的生存起见主张民族主义却是正当,而且与更‘高尚’的别的主义也不相冲突。”⑨王森然却将“日英帝国”改为“美英帝国”,一字之差,天壤之别,立刻使这一文本符合了汪伪政权的政治宣言,这便将周作人1925年的言论改造成了沦陷区的主流意识形态,并让人感到这就是周作人始终一贯的政治观。
汪伪政权为迎合服务于“大东亚战争”及“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大亚洲主义”观念,提出“大亚洲主义”本是中国固有观念,孙中山最早大力倡导,而汪伪集团诸公正是这一理想的唯一正统继承者。汪伪“大亚洲主义”观念的理论核心,是宣称要在日本带领、提携之下,东亚内部团结一致,反对以美英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殖民统治,争取东亚的独立解放。身为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在多次讲话中都反复重申这些理念,他首先阐明“大亚洲主义”是东亚解放运动的思想根据,⑩并指出“本来大亚细亚主义原是中国旧有的思想,远在四五十年前中国知识阶级恐惧西洋各国的侵略,主张学日本变法自强,联合日本,共保东亚,后来孙中山先生提出大亚细亚主义,即由于此,其根基是颇深远的”(11),他还着重强调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的核心理念,“东亚多少年来的纠纷是怎么起来的?中日事变又是怎么起来的?那都是英美从中拨弄,才生出来这个局面……东亚民族受英美的胁迫,时间已经很久,从来也只有忍受,自从中日事变以来,我东亚已结成一环,共存共荣,以建设新秩序,以期解脱英美的羁绊”(12)。而在汪伪政权的“大亚洲主义”理念构造中,也包括“民族主义”部分,如汪精卫在《光明的方向》(1943)中明确宣称,“民族主义,应该以大亚洲主义为核心,中国自己想得到独立自主,同时亚洲有许多民族,也想得到独立自主,以大亚洲主义,互相团结,共同协力……方才能将压制剥夺亚洲诸民族使不能得到独立自主的共同敌人英美帝国主义者打倒”,同时汪精卫还多次申明这正是孙中山的重要理念。(13)周作人在多次讲话中也反复强调这一观念,比如他说,“凡是东亚人民,应当谁都明白,别一民族的衰亡,决不会是自族的利益,大家须得相互扶助,共寻生路,才是正当的办法。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大亚细亚主义,也就是这个意思”(14),并提出“在东亚解放中求中国民族的生存”等。(15)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王森然通过改写文本的方式,使战争时期周作人的基本政治理念与汪伪政权一致,更重要的是,向社会宣称周作人早在十多年前就提出了这一观念,那么他始终都是孙中山先生的忠诚信徒(实际上是当下侵略者及汪精卫的忠实信徒),也是“新中华”先知先觉的忠实同志。不仅如此,该评传还不露痕迹地把早年周作人曾经反日的历史抹除得一干二净,(16)塑造出一位自民国以来始终深晓东亚解放的根本,而与作为亚洲领袖的日本情深义重的革命前驱,正如周作人在这一时期反复标榜的那样。这一改写的最关键之处,在于通过篡改历史文本,同时也改造了整个民国史的叙述,仿佛历史的真相就如汪精卫等人所叙述的那样,因此他们现在的言论以及所作所为自然顺理成章,甚至极富光彩,而绝非附逆丑行。应该说,整个的叙述链条非常圆满,极具欺骗性,(甚至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还有些人陷入汪伪以篡改民国史构造的意识形态圈套,并借此替他们翻案)这正是汪伪政权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叙述策略,王森然显然参透其中三昧,才锻造出如此纯熟的笔法。
通过篡改民国史的方式,王森然自然而然赋予周作人等汪伪政要所建政权的正统性,但这种修辞术并非万灵丹,因为在沦陷区,有些问题很难用这种方式做出圆满解释。比如汪伪政权核心人物的一些关键性言行,明显是迎合日本意识形态的荒谬表演,不仅很难与以往民国历史拉上关系,而且一以贯之的革命性也不知从何说起,这是很难让普通人信服的。因此对于这些荒唐表现,如果仍旧像吹捧傅增湘时那样,实话实说、就事论事地直接捧扬,结果反而会暴露出被吹捧者及吹捧者双方的丑陋、龌龊。王森然在塑造周作人形象时又遇到同样问题,他也亟待处理周作人类似的言行,探索出恰切的写作方式,既能充分阐释周作人思想行为与汪伪政权的一致性,又不暴露出周作人对日本侵略国策及汪伪政权思想战的过于热衷、主动配合的原形。王森然最终采取了不露痕迹、微言大义、暗度陈仓的手法,即表面上只是在客观描述,但又让传主周作人及其他伪政府人员能够确切、清晰地领会到王森然所要表达的信息,他主要突出了两个方面:
一方面,王森然重点突出周作人在汪伪意识形态建构中的重要贡献,即周作人在大肆宣扬“大亚洲主义”的同时,对汪伪主流意识形态做出了个人新的阐释,提出著名的“中国固有的国民思想”命题。周作人做出这种新的理论阐发,正是为迎合汪伪集团意识形态建构的需要,因为汪伪集团认为,仅仅迎合日本的战略观念大力宣扬日本“大亚洲主义”是远远不够的,新政权还必须根据自身的需要,创造出自己的“大亚洲主义”理论系统。对周作人在思想战中的这一重要活动,王森然并未明确点明,只是在叙述周作人政治生活历程的结尾处,轻描淡写地加上了这样一句话,“周先生在第三届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的精神讲话:我个人多少年以来想出来的一点问题,就是中国固有国民思想,究竟是什么?它的优点与劣点在哪里?颇见重于一时。文长不俱录”(17)。这样做,是在向日方及汪伪集团说明周作人在思想战中的地位与贡献,同时也是潜在地声援“反动老作家”事件中周作人的一方,既然周作人本来是为日伪政权献策,就不该受到他们的误解与抨击。
另一方面,关于周作人反共的坚定立场。在汪伪自诩的革命观当中,最为核心的一项内容就是反共,汪伪政要们为了迎合日本提出的“共同防共”的口号,从中国革命及中日关系发展历程等角度解析了反共的必要性与意义,基本是对日本提出的一套逻辑的阐述。作为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在各类讲话中反复重申这些观点,并积极为反共、灭共献策。(18)不过历史上周作人并没有反共的经历,而且战前他对共产思想及信奉共产主义的党派还有一定的同情,因此在沦陷区政府诸公看来,周作人反共立场还不坚定,所以王森然感到非常有必要着重强调周作人对日伪政权核心价值体系的忠诚。王森然对此问题的处理手段愈加高明,他并未反复渲染周作人的反共主张,而是从周作人刺杀事件着手,只轻易点染,便境界全出。关于周作人的刺杀事件,王森然做出了这样的表述,“先生……二十八年一月一度为共党分子刺客所袭击,幸吉人天相,安然无事”。王森然这种说法基本来自于日本方面。
按,刺杀事件发生后,日本重要舆论机关都曾较为密集地连续报道事件后的相关动态,并有意引导舆论方向,如刺杀事件后第三天,1939年1月4日日本《読売新聞朝刊》1面登载短讯《周作人氏狙击共产分子的恐怖行动》(「周作人氏狙擊共產分子のテロ」),不过文中尚未提及刺杀者身份,而到3月5日《読売新聞夕刊》1面的新闻稿《味噌汁的味道 周作人的新出发》(「味噌汁の匂ひ周作人の新しき出發」)中则明确指出,周作人是被诈称天津中日学校学生的共产分子所狙击。当时日本方面坚称此事乃共产分子所为,显然是别有用意的。查阅1939年1月4日日本《読売新聞朝刊》1面,新闻主题是《汪永久除名 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汪を永久に除名 國民黨中央會議決定」),报道了因汪精卫出逃,并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联合声明,国民党中央将其永久除名,并宣布逮捕令的新闻。日方对此事的评述,完全采用汪精卫派机关报《南华日报》的论调,新闻标题为《大改组要求 共产党策谋愈加露骨》(「大改組要求共產黨策謀愈ょ露骨」),对此事件进行歪曲解读,宣称国民党中央对汪精卫的处分完全是出于共产党方面的胁迫,共产党欲借此机会彻底清扫国民党内“反共主和”的力量,从党务、政务、军事等诸方面改组国民政府,企图使其成为第三国际指挥下的完全的赤色傀儡政权。而短讯《周作人氏狙击 共产分子的恐怖行动》正是此大的新闻主题下的一则新闻,虽称刺杀乃共产党所为并无实据,但日方这样讲,明显是要将周作人刺杀事件纳入到此段时间紧锣密鼓的反共宣传中,而这样做的结果,自然而然就将被刺后迅速与日伪政权合作的周作人,塑造成为“反共主和”的英雄,这当然正是日方所希望树立起来的周作人像。不过将周作人刺杀事件归于共产党的说法,主要出现在本轮宣传战中,随着宣传攻势减弱,这种说法就很少出现了,当1941年4月2日《読売新聞朝刊》1面《风尘录》(「風麈錄」)中重提暗杀事件时,已将暗杀者归于重庆方面了,这也是后来沦陷区及日本国内的普遍看法。但是在时过境迁的1944年5月,王森然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居然又选择了此前关于暗杀者身份的不确解释,这不能不说其用心良苦。《周作人先生评传》为迎合五年前日方的宣传论调,将日方塑造的周作人像完全接受过来,极力在日伪政权最为重要的舆论机关树起一尊“反共英雄”周作人的“丰碑”。(19)
从以上两方面分析可以看到,此时王森然的手法已相当纯熟,仅仅几句看似随意、不露痕迹的点染,就把周作人在汪伪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贡献,以及在思想战、宣传战中的重要地位,全都和盘托出了。我们说的这些特点正是人们在看待沦陷区中的周作人时容易忽略的一面,而王森然在传记中着意加以强调,可见他对沦陷区意识形态建构问题与伪高官周作人在其中的关键性地位,都有着极为敏锐的嗅觉与深入的体察。
综观全文,王森然成功地完成了高难度的工作,实现了其预想目标,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他塑造出一位完全符合日本侵略者及汪伪政权意识形态要求的伟人形象,这位伟人自辛亥革命以来,就是一以贯之的伟大文学家、思想家、道德家,同时是一位始终顺应时代潮流、矢志不移的革命先锋,在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中他居功至伟,尤其在当前的革命事业中勇担国难,成为大亚洲主义的重要理论家、反共的勇猛斗士。应该说,这一对作为新朝股肱的周作人像最为全面综合的塑造,堪称沦陷区最有代表性、最具特色的周作人像。另一方面,王森然也同时探索出沦陷区意识形态建构的新的写作方式、逻辑方式及语言方式,甚至可以说锻造出一种“诗学”,并将此利器落实于传记写作中,以《周作人先生评传》成就最高。该传记貌似客观叙述,实则采用了“去历史化”手法,偷梁换柱、篡改历史文本、暗度陈仓等,在进行汪伪意识形态建构、吹捧新朝股肱光辉功业的同时,又不显露伪官丧失人格、为虎作伥、为日本侵略奔走呼号的本质,完全可以看做是汪伪意识形态写作的一项标志性成果。而这部蕴涵着如此丰富历史信息的沦陷区代表性作品,其后也隐藏着沦陷区部分知识分子特殊的精神史。
王森然的这一文学行为当然是有功利预期的:通过编著《周作人先生评传》,他明确地向汪伪政权表达了“咸与维新”的姿态与愿望,并向身居高位的周作人表示了充分的敬仰,这在其他几篇传记中也有同样表现。(20)但不幸的是,王森然最终未能得到传主的接纳,据与周作人密切往来的张中行回忆,“三十年代前后北京有一位王君,大概是个教师吧,学齐白石,也画也刻,粗制滥造,装腔弄势,有人拿他的作品请周评论,周说:‘我看他还是先念点书吧’”(21),很明显,周作人认为王森然学识鄙陋,拒绝为其作品发表评论,并对其人作出了较苛刻的评判,周作人如此的态度自然使王森然的一切希望化为泡影。随着抗战结束,周作人的地位一落千丈,此时已无攀附之必要,因此在王森然建国后的口述历史创作中就极少再提及周作人,(22)而这恰与他笔下及口述历史中鲁迅形象的变化形成鲜明对比——建国前的王森然甚至可以不时调侃鲁迅,(23)建国后的他却在其笔下与口头创作中视鲁迅为其人生、文学,乃至革命道路的启蒙导师、引路人等等,而王森然所编造的这些故事也为其耄耋之年赚得很多荣光,不过这些已超出本文论述范围了。
注释:
①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 傀儡组织》(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版,第942页。
②关于《华北新报》及华北沦陷区新闻统制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其大致情况参见程曼丽著《华北地区最后一份汉奸报纸——〈华北新报〉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3期;郭贵儒著《日伪在华北沦陷区新闻统制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③周作人这段谈话刊载于1944年5月2日北平《华北新报》第2期。
④1940年11月汤尔和死后,东洋文化协议会会长一职曾由副会长傅增湘暂时代理,1941年10月周作人接任后,傅增湘仍做副会长。
⑤王森然:《傅增湘先生评传》,《新东方杂志》1941年第2卷第7期。
⑥实际上以往的周作人评论基本都是历史性的叙述与评论,且各种评论对于周作人的认识也有相当大的差距,从不存在一个凝固、确定的周作人像,而王森然《周作人先生评传》则塑造了首个毫无历史感的凝固的周作人像,而新时期以来诸多周作人像也都存在此弊病。
⑦在王森然用旧材料构造出的新表述中,周作人既是新文学的开创人之一与首脑人物,而且珍视传统文化,王森然特别强调后一部分,即“先生慕恋旧社会”,并将以许杰为代表的,30年代左翼思想家对周作人中年以来思想逐渐落伍,慕恋封建社会、封建文化的严厉批判,转变为充分的肯定,如把许杰《周作人论》原文中的“封建社会”,替换成在沦陷区受到政界、文化界高度褒扬的“中国旧社会”及“中国旧文化”等。
⑧开明(周作人):《元旦试笔》,《语丝》周刊1925年1月12日第9期。
⑨(14)周作人:《树立中心思想——在第四届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精神讲话——》,《教育时报》1942年9月1日第8期。
⑩周作人:《东亚解放之证明》,《教育时报》1942年3月1日第5期(大东亚建设特辑号)。
(11)周作人:《日美英战争的意义与青年的责任——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广播讲演——》,《教育时报》1942年1月1日第4期。
(12)此处脱落一“得”字。
(13)汪精卫:《光明的方向——汪主席对上海各大学及高中青年团训话——》,《中日文化》月刊1943年第3卷第11、12合期。另请参考汪精卫《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总理孙先生诞辰纪念作——》,《中央导报》1940年第1卷第15期。
(15)周作人:《齐一意志·发挥力量——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成立大会开会词》,《中国公论》1942年第8卷第4期。
(16)沦陷时期的王森然在传记写作中不止一次抹除传主反日历史,如王森然《蔡元培先生评传》(《公议》半月刊第2卷第6期,第3卷第1、2、3、4、新年号各期,第4卷第1、2期)的四分之三部分皆抄自贾逸君编《中华民国名人传》的“蔡元培”辞条(北平文化学社1933年初版),而王森然单将“蔡元培”辞条的末句去掉,而这一句正是含有反日内容的,“九月,日本无理占我辽、吉,(蔡元培——论者加)遂与张继、陈铭枢偕赴广东,磋商统一问题”,王森然如此做,其用心昭然若揭。
(17)周作人所作这一讲话即为《中国的国民思想——在第三届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精神讲话——》,《教育时报》1941年9月1日第2期。
(18)关于周作人的反共言论,可参见其以下讲话《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周督办广播演讲》,《教育时报》1941年9月1日第2期;《树立中心思想——在第四届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精神讲话——》,《教育时报》1942年9月1日第8期;《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展开》《举办农事教育人员讲习班的意义——在第一届华北农事教育人员暑期讲习班训词——》,《教育时报》1942年11月1日第9期;《齐一意志·发挥力量——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成立大会开会词》,《中国公论》1942年第8卷第4期等。
(19)关于刺杀周作人事件,90年代以来成为学术界与社会舆论争讼不已的热门话题,在各种细节问题上说法纷纭,其中关于刺杀者身份认定问题,现在的研究者们都在集中揭示刺杀者的真实身份,而很少去考察刺杀发生之后当时中日各派力量是如何解释此事的,比如,现在很多学者都习惯征引战后周作人为自我粉饰而将一切责任推给日方的说法,却很少去考察周作人在事件发生后的明确解释;另外,现在非常流行的关于军统控制的“锄奸团”暗杀周作人的多种说法,皆为战后当事者的回忆,也非当时的看法。关于刺杀发生后当时中日各派力量对此事件的解释,仅有钱理群、木山英雄等少数研究者做了零星的研究,考证出当时日方的一种说法,即认定是重庆方面所为,此外没有其他相关的研究。因此关于刺杀周作人事件的相关问题还需进一步深入考察研究。
(20)请参照《刘半农先生评传》(《中国公论》1941年第5卷第1、2、3期)、《钱玄同先生评传》(《中国公论》1941年第5卷第4、5期)、《徐志摩先生评传》(《中国公论》1941年第5卷第6期,第6卷第1、2期)。
(21)张中行:《苦雨斋一二》,《负暄琐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
(22)王森然在建国后很少提到周作人,迄今笔者所能见到的,只有王森然在70年代讲述自己为周氏兄弟拉架的奇闻时提到周作人,见郭慕岳著《关于王森然》,《粤海风》2005年第5期,以及王森然告诉刘海粟关于1923年周作人等名教授掩护他逃脱曹锟通缉的故事,见刘海粟著《王森然传略》,《晋阳学刊》1989第1期。
(23)请参照王森然编著《周树人先生评传》,见《近代二十家评传》,北平杏岩书屋1934年版,以及《鲁迅先生评传》,《中国公论》1941年12月1日、1942年1月1日、1942年2月1日第6卷第3、4、5期。
标签:周作人论文; 王森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民族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