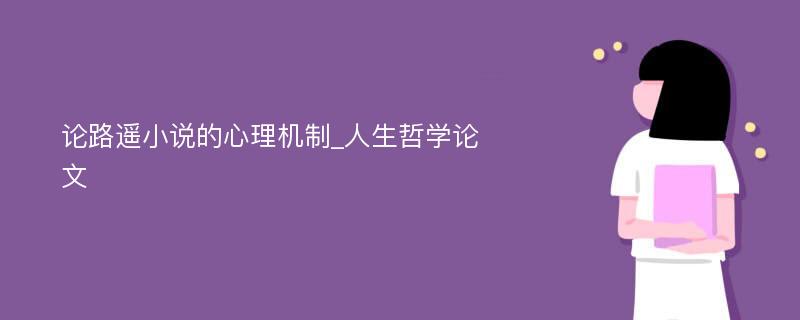
论路遥小说创作的心理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制论文,路遥论文,心理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时期我国整个作家群落中,陕西作家群确实以其独特的文化资源和创作灵性在文坛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里,历史主义的史诗意识,道德主义的生活追求和神秘主义的文化倾向在新时期许多作家的文学创作中都有着或隐或显的普遍体现,这也许是源远流长的古老、厚重、博大的周秦汉唐文化遗绪深深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构心理中的独特方面之一吧。毫无疑问,诞生并生活在这片钟灵土地上的作家,从建国以来的柳青、杜鹏程等到新时期的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也无疑深受其影响。在他们身上,那种恢宏壮阔的诗学气象和沉重压抑的精神苦难在其天人相生相克的深厚文化哲学意蕴背后,显示出一种张驰有度、伸缩自如的审美诗学机制。而具体在路遥身上,一方面,他确实显示了这种追求真、善、美相互统一的共同价值观;另一方面,在其紧紧围绕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社会结构的切入点上,又体现了自己独特的心理和精神世界。
(一)
肖云儒曾这样说:“我感到,纠缠在路遥心中的大痛苦主要是两点:第一,历史发展性的规律和个人文化心理、伦理感情之间的冲突痛苦着他。……第二是精神劳动所需要的漫长的孤独和他强烈的参与意识之间的冲突造成的痛苦。”也就是说,“一个路遥要求在艺术的模拟中最大限度地完成精神的自我。一个路遥则要求在社会实践中最大限度地完成现实的自我。”他说:“从另一个视角看,这两种痛苦是恋土情结、恋美情结和恋史情结冲突的结果。这三者之间最后又是统一的。路遥以及他的乡亲父老只有经受文化断乳的痛苦,才能踏上历史的康庄大道,进入生活的新境界。这是对黄土地最深情的爱恋。恋土与恋史由是统一。职业固然使他的价值在历史实践活动中得不到实现,但通过审美创造,催化了这种历史创造,在精神上参与了这种历史创造,美的实现也就转化为史的实现。恋美与恋史由是统一。”(注:肖云儒:《文始文终记路遥》,《延河》1993年第2期。)之所以不惮其烦地引述这段话, 是因为确实比较准确地抓住了在路遥身上精神的自我与现实的自我之间的巨大冲突,在我看来,正是这两者之间巨大冲突才使路遥深陷在巨大的精神困境之中:在文学创作层面上,以爱情(爱情是真善美的一种象征)与制度之间构成冲突;在个体生命层面上,以感性与理性之间构成冲突;在人生哲学层面上,以历史与伦理之间构成冲突。但从作家主体生命体验上来说,这三个层面上的冲突所编织的巨大的精神困境正构成一种两极张力:农村与城市、乡土情结与现代意识、道德与历史、奋斗精神与自虐倾向,正是作家意识到这种两两相对的二律背反一步步把自己推向内心世界裂变的极致。所以,他在巨大精神困境面前必须寻找精神突围的契机,也就是说,他必须要从这种精神困境中超越出来以使自己的精神世界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于是,一种具有浓厚宗教情绪意味的审美机制就得以形成了。
我们知道,路遥是在深刻把握了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在文学创作中通过精心编织爱情的经纬,从而借以现代性伦理的叙事话语来表现个人奋斗者们的炼狱之痛和终极关怀。所以,在路遥心中,正因为他既无法消除这深刻繁复的巨大冲突,又必须超越这人生中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于是,他索性把文学创作、个体生命和人生哲学(信仰)由三元并立经审美心理机制转换成三位一体。当然,这无疑是别无选择的一种最后选择和精神升华,但这并不是说路遥已经解决了那巨大的精神困境;而是恰好相反,他用这种方式实际上只是走出了问题解决的第一步,而正是他迈开的这第一步,又使他必须倾付全力的代价才有可能使他达到另一个起点:这就是,他把个体生命的所有体验、感受和认识都投入在文学创作的冲动之中,借此塑造和建构那真正的人生哲学(信仰),在他看来,这时的个体生命体验在文学创作中的投入程度和对人生哲学(信仰)的终极追求是成正比的,生命投入越大、体验越真、对人生哲学(信仰)所关涉的伦理道德即对善的要求就越能可靠地获得,从而就越能获得美感上的人性共鸣。
那么,得以使路遥企图摆脱巨大精神困境的审美机制是什么?一般而言,每个作家都有其独特的审美心理,但由此作为一种机制存在于作家的观念中,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一些作家的日常生活之中,文学创作、个体体验与人生哲学(信仰)等基本是作为一种意义单元而存在,尽管这并不排除它们有时候被作家分别从其他角度加以综合的考虑。所以,有的作家先有了人生经验才进行创作而有的作家则为了创作才经验人生。但无论怎样,他们都是通过从感性与理性的方式去加深对文学创作的深刻理解。路遥则不一样,他是把个体体验和文学创作完全合一的。体验即是创作,创作即是体验,个人体验和人生哲学有多深,文学创作也有多深。这里,异同点还是昭然的:有些作家只有在置身于文学创作活动时,这三种因素才在刹那的艺术灵感中达到了完全合一,此前,他们还各自保有其清醒的分辨力和独立存在界限。而路遥则从投身文学活动开始,他就把三者视为一体,把生命和人生就典押给了文学。那么,不论是哪种情况,在作家审美心理中,又是如何实现三位一体的神奇遇合呢?大致说来,无论作家个体审美心理多么复杂,从其内在的方面区分主要有感性和理性两种,从其与外在现实世界的关系来看,则主要有主观的和客观的区分。而由此在形成审美心理机制方面:有的作家内在与外在相一致,即或为主观感性的或为客观理性的两种类型;有的作家则是矛盾的,即或为主观理性的或为客观感性的两种类型。前两种作家审美心理和文学创作是一致的;后两种的审美心理和创作是冲突的。从路遥审美心理机制的构成来看,他无疑是属于主观理性这一类的。现代主义的作家一般都属于主观理性这一类,但是,他们的审美心理机制的形成本身就是对以城市为象征的现代文明为主体的关于现代化诸种负面影响的批判为基础的;而路遥则与此却明显不同。路遥显然意识到现代文明的进步性,但站在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社会结构基础之上,他从理性立场上对现代文明给予理性承诺,即显然肯定其历史进步性,但从情感上仍皈依乡土;同时,由于个体生命体验、文学创作和人生哲学的合一性,使他对那种现代主义的抽象理性和变形符号缺乏认同感,而代之以寻找具体的理性现象来体现其生命存在形式。于是,他的现实激情充满了艺术想象,成为自己生命形式的精神漫游,艺术创作反倒成为其现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一意义上,路遥的现实激情和理性智慧所形成的审美机制得以使他从精神困境中部分地解脱出来。这就是路遥更加自觉地以非理性的生命激情自觉构筑起了现实主义的文学丰碑。
(二)
路遥曾说:“我在构思时有这样的习惯:把对比强烈的放在一起,形成一种反差”。(注:《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452页。)这种反差包括主题、人物、情节、结构等各方面。 我认为,路遥这种奇特的色彩强烈的对比不仅体现在构思上,而且也体现在审美心理机制上,这就是在现实激情和理性智慧之间构成一种巨大的两极张力。这种张力一旦被投射到文学创作活动中,使作家的身心经受着炼狱般的痛苦,但作家并不是由生命痛苦而失去理性智慧,对路遥来说,深度人生中的生命越痛苦,理性智慧就使他越加清醒。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中曾真实地表达了这一审美心理特征。他说:“毫无疑问,这又是一次挑战。是个人向群体挑战。而这种挑战的意识实际上一直贯穿于我的整个创作活动中,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是这样,《在困难的日子里》也是这样,尤其是《人生》,完全是在一种十分清醒的状态下挑战。”(注:《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页。)所以, 在路遥的个体生命所经验的人生世界中,从他的审美心理机制特征出发,在他的外在社会行为所体现的现实激情方面由三种单元构成即奋斗精神、宗教情绪、苦难意识,与此相对立在他的内在心灵活动中所伴随的理性智慧则有孤独感、坚毅固执和禁欲自虐。正是在作家身上、在内外两极张力共构的审美心理机制的基础上,路遥达到了精神突围的最高峰。
在路遥的童年及青少年时期,饥饿、贫寒、卑微使他刻骨铭心,并深深烙在了他无限幽远深邃的记忆之旅。所以,他发誓要走出农村,要走出父辈们的生活困境,要通过自我奋斗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活下去,就别想指靠别人,一切都得靠自己。”(注:《路遥文集》第2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页。)正是这种强烈而特定的个人奋斗心理,不仅生动体现在作家身上,也体现在作品主人公身上。因而,无论《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还是《平凡的世界》那种梦魇般的现实生活场景所再现出来的逼真犹如一组组浮雕一样镌刻在对那个时代曾有过痛切记忆的读者身上。但这并不是作者所要致力寻找的终极意义,而是在这刻骨镂心的“吃饭哲学”背后,人们也不难读到那种“物质上的矮子,精神上的巨人”这一唯一能够支撑作家自我奋斗的根源所在。然而,当一个人过于早熟并超越同龄人而离开群体生存视野来寻觅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他因为缺乏志同道和的奋斗者而陷入于一种巨大的孤独之中,所以在路遥内在的心理世界中,他可能确实比别人更真切地体验过“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也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和价值。“情绪上的大欢乐和大悲痛往往都在孤独中产生。孤独中,思维可以不依照逻辑进行。孤独更多地产生人生的诗情——激昂的和伤感伤痛的激情。孤独可以使人的思想向更遥远更深邃的地方伸展,也能使你对自己或环境作更透彻的认识和检讨。”“当然,孤独常常叫人感到无以名状的忧伤。而这忧伤有时又是很美丽的,我喜欢孤独,但我也惧怕孤独。”(注:《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53页。)可以说,这是路遥在个人奋斗精神支配下一种最清醒的道白。他对“孤独”的这种“美丽”而又“惧怕”的审美心理感受,其实也正是他对个人奋斗所寄予的成功或失败的“事功”心理反映。因成功,是美丽的孤独,可能失败,他又忧惧于孤独的包围。因而,在个人奋斗精神之上,他具有一种浓厚的宗教性情绪。
路遥宗教情绪的弥漫自然有地域文化中那种神秘主义文化倾向的影响,但更多地来自于他在重重艰难中对自己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寄予一种可能成功的极大向往。所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对在二十岁左右“很可能在故乡寂静的山间小路上行走的时候,或者在小县城河边面对悠悠流水静思默想的时候”所萌生的一定在四十岁之前要干一件大事的念头,视为“命运之神的暗示”;在准备创作之前对故乡毛乌素大沙漠那种“充满虔诚的感想”和“接受精神沐浴”的神圣“朝拜”;在创作过程中他那种类似于举行“神圣的宗教仪式”而像宗教徒那样“艰辛地跋涉在朝圣旅途上”这种宗教情绪式的创作行为,在他的心理上就表现出极端地坚毅和固执。”(注:《路遥文集》第2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见第5-6、8-9、44、396页。)在他看来, 正是这种宗教情绪和坚毅固执能够保证他获得更加美丽的孤独,走上个人奋斗的成功之路。所以,他理所当然视承受苦难和“刻意受苦受罪”正是考验一个拥有宗教情绪的个人奋斗者所必须面对的原罪和灾难,只有在原罪和种种灾难面前,他才能说明自己孤独的价值、固执的根由,也从而使作家更多地带来某种畸形的殉难冲动和自虐倾向。
在路遥并不算多的创作随笔中,和一些与路遥曾密切相处的人所写的诸多评论和回忆文章中,我们看到在路遥身上,有许多非寻常作家所具有的奇异的精神现象。据李沙铃在《无愧人生和世界》中说到路遥曾在一次地方作家会议上有一段极为精彩的演说,他说:“说到底,作家就是自己在对自己开枪,自己在打自己,只有战胜自己,作品才能步入‘大音稀声’之境……”(注:李沙铃:《无愧人生和世界》,《延河》1993年第2期。 )一位现代思想者汪晖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一个最终了解写作过程是一个自己反对自己的过程的人,才能体会到写作如同命运一样的含义。”(注:汪晖:《〈我不能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序》,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7页。)两相比较, 路遥思想的深刻警拔更令人产生一种心灵的颤怵。路遥对生活苦难的理解甚至达到了一种病态的崇拜。因此,当他以忍受苦难的方式换得外在行为的现实激情与内在心理的理性智慧以审美张力对立两极的最大平衡的时候,他觉得忍受苦难并不算什么;相反,在他身上忍受苦难和制造苦难的冲动一样强烈。在创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一方面他多次表达了为完成这一文学工程而愿“以青春和生命作抵押”。(注:《路遥文集》第2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页。)“我将要进行的其实是一次命运的‘赌博’。(也许这个词不恰当),而赌注则是自己的青春抑或生命。”(注:《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页。)为了“拼命完成此生的一桩宿愿”(注:《路遥文集》第2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页。),“你要么超越这个极限,要么你将猝然倒下。”(注:《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第45页。)另一方面,一旦他接受了命运的挑战,反倒从精神上“获得了大解脱,大宁静,如同修行的教徒绝断红尘告别温暖的家园,开始餐风饮露一步一磕向心目中的圣地走去。”(注:《路遥文集》第2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页。)。因而他“有一种急不可待投入灾难的冲动”。并且在文学创作中以一种清教徒的方式,“要排斥舒适,要斩断温柔,只有在暴风雨中才可能有豪迈的飞翔;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有可能弹拨出绝响。”(注:《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33页。)请注意,正是在这里,在苦难意识背后,作家已有了一种殉难冲动。在这一点上,有两位作家对他影响很大:一位是杜鹏程,一位是柳青。路遥在《杜鹏程:燃烧的烈火》中坦率地说:“他的(指杜鹏程——引者注)自我折磨式的伟大劳动精神,都曾强烈地影响了我。我曾默默地思考过他,默默地学习过他。现在,我也默默地感谢他。在创作气质和劳动态度方面,我和他有许多相似之处。当他晚年重病缠身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就不由想到了自己的未来。我感到,他现在的状况也就是我未来的写照。这是青壮年时拼命工作所导致的自然结果。但是,对某一种人来说,他一旦献身于某种事业,就不会顾及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这是永远无悔的牺牲。”(注:《路遥文集》第2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5页。 )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还针对自己为拼力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时告诫自己:“如果不抓住命运所赐予的这个机遇,你可能真的要重蹈柳青的覆辙。这就是真正的悲剧,永远的悲剧。”(注:《路遥文集》第2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5页。)只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路遥他那献身于某种事业的永无追悔的牺牲精神和自我折磨式的伟大劳动精神,这构成了一个作家独具魅力的存在方式。
(三)
由此,从作家审美的心理机制的形成看,路遥的人生轨迹本身所构成的正是建国以来的一部个人精神变迁史,他的这种以个人奋斗意识为核心的精神现象,无疑成为那个时代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本身所规定的历史发展轨迹的一种注脚。确实,正像这种制度自身所曾具有的合理性那样,任何一种个体乃至有限群体的现实突破还并不能证明这种合理性已经丧失。但是,这种企图取得现实突破的行为意识本身,又恰好代表了一种企图突破定式的变式趋向。这从作家审美心理机制两极构成的现实激情和理性智慧所分别包含的内外两方面即心理和行为单元构成就能证明。然而,从作家的审美心理机制的结构——功能角度出发,作家的这种心理和行为的单元构成只有投射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让读者在充分地进入文学阅读接受过程中,方能领略到作家的“心灵诗史”和“行为诗史”的复合性和完整性。但是问题恰好在于,当作家把文学创作、个体体验和人生哲学(信仰)通过审美心理机制的两极张力由三元并立转化为三位一体时,只解决了作家自身生命体验和人生哲学的问题,而作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却在两极张力中本来为达到一体化所不得不选择的叙事经纬,因为与其人生哲学外化的社会行为必须构成一种相反的作用力,才能加强与作家的人生哲学(信仰)和个体心理体验的完全合一。所以,为了显示作家的个人奋斗精神,他不得不选择宏大的社会生活场面借以衬托个人奋斗力量的存在,显示其真实性;为了展示作家的宗教情绪式的热情,他不得不以客观立场来显示中立性的价值诉求,以其节制来表现倾向性;为了陈述作家苦难意识的典型性,他不得不以建功立业的“丰功伟绩”来显示承受苦难的同时所获得人定胜天的蓬勃生命。但是,真正悲剧的是,作家企图通过文学创作达到精神突围的新一轮困境就接踵而来了。
在路遥的小说创作中,作家总是将其在现实激情支配下的主人公设计成一种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对宏大的生活场面,价值中立的客观立场和敢于迎受苦难命运的乐观精神的冷静叙述中达到与作家的审美心理机制相契合的目的。但这种达到深度人生后所获得的理性智慧却是一柄“杀手锏”,智慧即痛苦,越智慧,越痛苦;越痛苦,越清醒。正是这种悖谬,使路遥在文学创作中又不断地回过头反观自身,从而将自己心理行为世界的真实内涵在“超我”的监督下实现了层层过滤,这又正是他审美心理机制两极张力不可调合的一面。比如在他的小说中有许多关于“两小无猜”的温馨的情爱描写,这不过是对他童年及青少年时期苦难生活的一种过滤;比如在许多小说中,还有关于“雨雪”的描写,而洪水的泛滥也成为他使主人公命运逆转的关键,这实际上是他自幼年起对陕北干旱气候的一种忧惧的反映;比如他关于爱情婚姻模式中城市女性与农村男性这种类型的艺术编织中,女性总是比男性在家庭地位、知识等背景方面有无与伦比的“来头”,这种巨大的反差实际上也表现了作家在城乡二元对立社会结构中的一种希望突破现实生活的曲折的“向往”和“焦虑”的反映。正是这种受压抑的“无意识”在作家童年苦难生活和青少年时期立志自我奋斗所深深镌刻的心理印痕,使路遥在自我奋斗中总有一种如履薄冰或苦苦等待的心理痛苦和焦虑,这几乎使他和高加林、孙少平等曾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使他随时有可能面临像他们那样不得不再次回到农村的悲剧性命运。所以,如果说《人生》是路遥自身人生愿望在得以满足后“后怕式”的一种心理回顾的话,《平凡的世界》则是他将这种“后怕式”的心理回顾转化成“积极地寻找前景”的“前瞻式”后怕心理的一种正当释放。于是,他真正精神状态的心理感受如伴随着个人奋斗而产生的孤独、固执、禁欲、压抑、焦虑等因素进入不了他的理性智慧的视野,正像他的理性智慧只能容纳与个人奋斗者相伴随的另一种心理感受如向上、乐观、正义、刚毅、甚至满足等一样。
总之,在路遥个体生命现实激情的浪漫化和理想化面前,我们却发现在作家的文学创作中的理性智慧表现出极端的冷静和现实。当他的现实激情高扬到极致时,却在文学创作中以出奇冷静的笔调揭示出那激情下面平凡乃至卑琐的一面;而当他的智性人格一旦落入低谷时,作家又通过理想化的笔调来弥补着主人公精神人格的缺损和想象性前提的丧失。所以,在他的艺术活动中,我们总看到他在作为一个“凡人”像神性英雄那样对自己所开拓出的这条个人奋斗之路是那样艰辛而辉煌表示着欣赏;而另一方面,他又用一种神性英雄梦幻式的回顾把自己曾作为一个“凡人”在实际生活背后所孕育的失败意义和挫折感却毫无犹豫地忽略不提了。所以,他把希望留给文学,把绝望留给自己。在这一意义上,路遥的生命似乎是用人定胜天的乐感文化注定要跟自己的生命极限进行一场极富命运暗示意味的马拉松式长跑,这个跑道就是用文学铺就的。当他加速度地似乎已看到胜利的曙光时,他预感到最终的胜利者却是以自己过早地倒在文学的万里征途中而告终。这正是如路遥所说:这是“悲剧,一场悲剧”,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作家个体自然生命的悲剧,却是作家个体精神生命一次真正的凯旋。
收稿日期:1999年12月30日
标签:人生哲学论文; 路遥文集论文; 路遥论文; 文学论文; 平凡的世界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人生论文; 作家论文;
